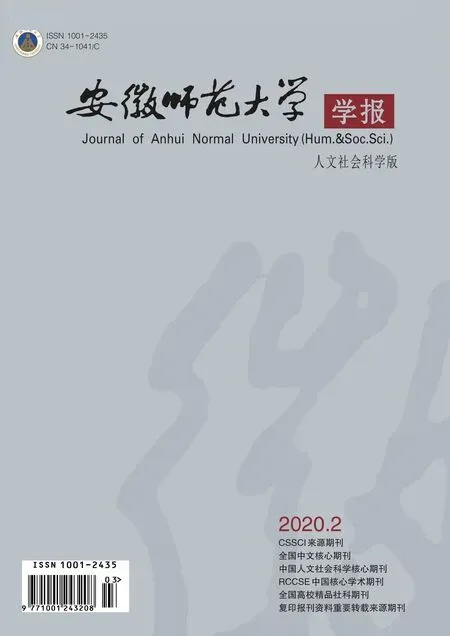王阳明的“去人欲而存天理”及其与朱熹理欲论之比较*
乐爱国
(1.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江西上饶334001;2.厦门大学哲学系,福建厦门361005)
对于王阳明,刘宗周说:“先生教人吃紧在去人欲而存天理,进之以知行合一之说,其要归于致良知。”[1]1认为“去人欲而存天理”是阳明学的基本思想;同时又认为,王阳明讲“去人欲而存天理”本就是“程、朱之言”[2]30-31。毫无疑问,王阳明的“去人欲而存天理”,作为其基本思想,来自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当然,二者又存在诸多的差异,但无论如何,他们都讲天理与人欲的对立,要求“存天理”,要求去除人欲。对于王阳明“去人欲而存天理”,阳明后学中的浙中王门与江右王门多有继承,泰州学派则多有变异,肯定人欲的正当合理性,且对王阳明“去人欲而存天理”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并不作出明确的区分。刘宗周以及黄宗羲明确将王阳明“去人欲而存天理”归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加之,清代戴震批评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并受到胡适的推崇,都没有提及王阳明的“去人欲而存天理”,以致于今人只讲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而罕言王阳明的“去人欲而存天理”,更没有就二者的异同作出比较。
一、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到王阳明的“去人欲而存天理”
朱熹讲“存天理,灭人欲”,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可以追溯到《礼记·乐记》。该篇说道:“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唐孔颖达解释说:“若人既化物,逐而迁之,恣其情欲,故灭其天生清静之性,而穷极人所贪嗜欲也。”[3]3313
程颐解《论语》“克己复礼为仁”,曰:“凡人须是克尽己私后,只有礼,始是仁处。”[4]286又说:“视听言动,非理不为,即是礼,礼即是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4]144还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4]312显然是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朱熹继承程颐的解读,说:“仁者,本心之全德。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日日克之,不以为难,则私欲净尽,天理流行,而仁不可胜用矣。”[5]133又说:“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6]225朱熹晚年还说:“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6]207其中“明天理,灭人欲”一句,在后来黄宗羲《宋元学案》中为“存天理,灭人欲”[7]1544。
与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反对《礼记·乐记》以及程朱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他说:“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论。若天是理,人是欲,则是天人不同矣。此其原盖出于老氏。《乐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而后好恶形焉。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天理人欲之言盖出于此。《乐记》之言亦根于老氏。……《书》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者多指人心为人欲,道心为天理,此说非是。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则曰惟危;自道而言,则曰惟微。”[8]395-396又说:“人心,只是说大凡人之心。惟微,是精微,才粗便不精微,谓人欲天理,非是。人亦有善有恶,天亦有善有恶(日月蚀、恶星之类),岂可以善皆归之天,恶皆归之人。”[8]462-463为此,他还说:“天理人欲之分论极有病。……《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若是,则动亦是,静亦是,岂有天理物欲之分?”[8]475
与陆九渊不同,王阳明接受程朱的“存天理,灭人欲”,而大讲“去人欲而存天理”。他说:“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9]31-32他还解《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指出:“学是学去人欲,存天理;从事于去人欲,存天理,则自正。诸先觉考诸古训,自下许多问辨、思索、存省、克治工夫,然不过欲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今人欲日去,则理义日洽浃,安得不说?”[9]36-37又解《大学》“明明德”。说:“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9]103解“诚意”,说:“意未有悬空的,必着事物,故欲诚意则随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归于天理,则良知之在此事者无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诚意的工夫。”[9]1066-1067为此,他说:“圣贤垂训,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经》《四书》是已。”[9]290又说:“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9]10应当说,王阳明此言与朱熹所谓“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一脉相承。
王阳明特别强调要学圣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他说:“人苟诚有求为圣人之志,则必思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私欤?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惟以其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则我之欲为圣人,亦惟在于此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耳。欲此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则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务去人欲而存天理,则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则必正诸先觉,考诸古训,而凡所谓学问之功者,然后可得而讲,而亦有所不容已矣。”[9]289认为要成为圣人,就要学习圣人“于此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因而要通过“正诸先觉,考诸古训”,以求得“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
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王阳明自明正德三年(1508)于贵州龙场悟道之后,接着讲“知行合一”,并在滁州“只就思虑萌动处省察克治”,又在南京讲“存天理,去人欲”,说:“吾年来欲惩末俗卑污,引接学者多就髙明一路,以救时弊。今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论学,只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为省察克治实功。”[9]1354-1364
关于王阳明的为学,门人钱德洪说:“先生之学凡三变,其为教也亦三变:少之时,驰骋于词章;已而岀入二氏;继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贤之 ;是三变而至道也。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自滁阳后,多教学者静坐;江右以来,始单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变也。”[9]1745-1746又有胡松说:“先生之学与其教人,大抵无虑三变。始患学者之心纷扰而难定也,则教人静坐反观,专事收敛。学者执一而废百也,偏于静而遗事物,甚至厌世恶事,合眼习观,而几于禅矣,则揭言知行合一以省之。其言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又曰:‘知为行主意,行为知工夫。’而要于去人欲而存天理。其后,又恐学者之泥于言诠,而终不得其本心也,则专以‘致良知’为作圣为贤之要矣。”[9]1505-1506认为王阳明讲“知行合一”,其根本在于“去人欲而存天理”。
王阳明门人王畿也说:“先师之学,凡三变而始入于悟,……自此之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亦复以此立教。……自江右以后,则专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习不虑,盎然出之,自有天则。……逮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信而从者益众。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10]33-34黄宗羲《明儒学案》则据此讲王阳明之教有三变。[11]181对于其中第一变“以默坐澄心为学的”,唐君毅说:“此正与朱子之重涵养本原之工夫相近。此一工夫,即意在存天理以去人欲。”[12]291牟宗三也说:“此龙场悟后之第一阶段,以默坐澄心、存天理去人欲为学的。”[13]153
此外,王阳明门人朱得之也说:“阳明始教人存天理,去人欲。他日谓门人曰:‘何谓天理?’门人请问,曰:‘心之良知是也。’他日又曰:‘何谓良知?’门人请问,曰:‘是非之心是也。’”又说:“昔侍先师,一友自言:‘觉工夫不济,无奈人欲间断天理何?’师曰:‘若如汝言,工夫尽好了,如何说不济。我只怕你是天理间断人欲耳。’其友茫然。”[11]590-591
由此可见,“去人欲而存天理”是阳明学的基本思想;而这一思想将“人欲”与“天理”对立起来,无疑来自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关于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异同,学界多有讨论。然而,刘宗周则在《重刻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序》中说:“盖先生所病于宋人者,以其求理于心之外也。故先生言理曰‘天理’,一则曰‘天理’,再则曰‘存天理而遏人欲’,且累言之而不足,实为此篇真骨脉。……先生盖曰‘吾学以存天理而遏人欲’云尔。故又曰‘良知即天理’,其于学者直下顶门处,可为深切著明。程伯子曰:‘吾学虽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认出来。’至朱子解‘至善’,亦云‘尽乎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先生于此亟首肯。则先生之言,固孔、孟之言,程、朱之言也。”[2]30-31在刘宗周看来,王阳明讲“去人欲而存天理”本就是“程、朱之言”。刘宗周还说:“‘天理人欲’四字是朱、王相印合处,奚必晚年定论?”[1]52该句后来又被黄宗羲《明儒学案》论及阳明学时所重述。[11]199
不可否认,阳明学与朱子学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是,据《传习录》载,朋友观书,多有摘议晦庵者。王阳明曰:“是有心求异即不是。吾说与晦庵时有不同者,为入门下手处有毫厘千里之分,不得不辩。然吾之心与晦庵之心未尝异也。若其余文义解得明当处,如何动得一字?”[9]31这里所谓“吾之心与晦庵之心未尝异也”,与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所谓“予既自幸其说之不谬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9]145,是一致的,强调的是阳明学与朱子学的相通之处,而朱熹讲“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讲“去人欲而存天理”,便是最好的证明。
二、王阳明“去人欲而存天理”与朱熹“存天理,灭人欲”之异同
刘宗周认为王阳明讲“去人欲而存天理”就是“程、朱之言”,强调王阳明此说源自于朱熹,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他讲“天理人欲四字,是朱、王印合处”,这只是笼统而言。若由此以为王阳明的“去人欲而存天理”完全等同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则需要作深入的分析,而且王阳明对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也多有批评。
如前所述,程颐据古文《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解天理人欲,讲“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陆九渊予以反对,认为“人心为人欲,道心为天理,此说非是”,是人有二心。事实上,朱熹也不赞同程颐所谓“人心私欲”“道心天理”的说法,指出:“若说道心天理,人心人欲,却是有两个心!人只有一个心,但知觉得道理底是道心,知觉得声色臭味底是人心,不争得多。‘人心,人欲也’,此语有病。”[6]2010也认为程颐所说,是人有二心。朱熹又说:“人心亦未是十分不好底。人欲只是饥欲食、寒欲衣之心尔。”甚至还说:“人欲也未便是不好。谓之危者,危险,欲堕未堕之间,若无道心以御之,则一向入于邪恶,又不止于危也。”[6]2009-2010不仅把人心与人欲区别开来,而且认为人心、人欲必须有“道心以御之”。
为此,朱熹《中庸章句序》认为,“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而且“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因此要“惟精惟一”,“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5]14显然,朱熹强调“人只有一个心”,但有人心、道心之异,而应当使道心为主宰。
对于朱熹所谓“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王阳明提出批评,说:“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谓‘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语若分析而意实得之。今曰‘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为主,人欲又从而听命者?”[9]8认为朱熹讲“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是“二心”。如上所述,朱熹反对“二心”,而且朱熹也讲“道心是义理上发出来底 ”[6]2011,“ 道 心 是 本 来 禀 受 得 仁 义 礼 智 之心”[6]2018,因此,朱熹所谓“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以道心为主宰,实际上是要以天理为主宰,并非有二心,与王阳明讲人心、道心只是一心,是一致的。对此,刘宗周还说:“先生说人道只是一心,极是。然细看来,依旧只是程、朱之见。”[1]56该句后来又被黄宗羲《明儒学案》论及阳明学时所重述。[11]202
朱熹《中庸章句》解“天命之谓性”,说:“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5]17可见,朱熹讲“性即理”,既讲人之性,又讲物之性,且都是禀赋天理而来。也就是说,朱熹“存天理,灭人欲”之“天理”,不只是“道心”,也不只是人之性,同时也是物之理;因此,“存天理,灭人欲”包含了“即物而穷其理”“格物致知”的过程,由此而“诚意正心”“为善以去恶”,从而“克尽己私,复还天理”。
王阳明赞同朱熹所谓“尽乎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的说法,但反对所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他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9]2-3认为“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去人欲而存天理”,只是就心上讲求。因此,与朱熹强调“即物而穷其理”不同,王阳明多讲如何去除人欲。据《传习录》载,王阳明门人薛侃说:“尝闻先生教。学是学存天理。心之本体即是天理,体认天理只要自心地无私意。”王阳明说:“如此则只须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9]30认为“存天理”,无须“即物而穷其理”,而只须“去人欲”。他还说:“今为吾所谓格物之学者,尚多流于口耳。况为口耳之学者,能反于此乎?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时时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渐有见。如今一说话之间,虽只讲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间已有多少私欲。盖有窃发而不知者,虽用力察之,尚不易见,况徒口讲而可得尽知乎?今只管讲天理来顿放着不循,讲人欲来顿放着不去,岂格物致知之学?”[9]28认为重要的不在于讲明什么是天理,什么是人欲,而在于“省察克治”。据王阳明门人所录,“先生自南都以来,凡示学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欲,以为本。有问所谓,则令自求之,未尝指天理为何如也。”[9]1289
朱熹《中庸章句》注“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又注“君子慎其独”,曰:“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5]17-18认为“戒慎恐惧乎其不睹不闻”旨在“存天理之本然”,“慎独”则在于“遏人欲于将萌”。显然,在朱熹看来,“存天理”与“遏人欲”是不同的两种工夫。
与朱熹不同,王阳明讲“去人欲而存天理”,强调“去人欲”与“存天理”是同一的。他说:“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心之理无穷尽,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塞,则渊之本体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9]109因此,王阳明强调说:“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9]32又说:“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宁静不宁静。若靠那宁静,不惟渐有喜静厌动之弊,中间许多病痛,只是潜伏在,终不能绝去,遇事依旧滋长。以循理为主,何尝不宁静;以宁静为主,未必能循理。”[9]15-16认为无论是“戒慎恐惧”还是“慎独”,无论是“未发”还是“已发”,“去人欲”与“存天理”都是同一的,“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王阳明还说:“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廊清。到得无私可克,自有端拱时在。虽曰‘何思何虑’,非初学时事。初学必须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诚,只思一个天理,到得天理纯全,便是‘何思何虑’矣。”[9]18显然,王阳明只是讲“省察克治”,强调克去人欲,以为只有“去人欲”,才能“存天理”,这就是他所谓:“去得人欲,便识天理”[9]26-27。为此,他还说:“必欲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非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际不能也。”[9]74-75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王阳明的“去人欲而存天理”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存在诸多的差异,大致有三:其一,朱熹讲“性即理”,既讲人之性又讲物之性,并且认为人、物之性都是禀赋天理而来;与此不同,王阳明讲“心即理”,以为天理即人之道心,人之良知,所谓“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9]52“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9]81其二,朱熹认为,“存天理,灭人欲”首先在于“即物而穷其理”“格物致知”,然后“为善以去恶”,从而“克尽己私,复还天理”,他还说:“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游兵攻围拔守,人欲自消铄去。”[6]207与此不同,王阳明反对朱熹所谓“即物而穷其理”之说,认为“去人欲而存天理”只是就心上讲求,“存天理”只在于“去人欲”,“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其三,朱熹认为,“存天理”与“灭人欲”是先后不同且又相互统一的两种工夫,《中庸》“戒慎恐惧”旨在“存天理之本然”,“慎独”则在于“遏人欲于将萌”;与此不同,王阳明认为,“去人欲”与“存天理”是同一的,“去得人欲,便识天理”,并且特别强调去除人欲。当然,王阳明有时也赞同把“存天理”与“去人欲”分别开来,而强调“存天理”,说:“良知犹主人翁,私欲犹豪奴悍婢。主人翁沉疴在床,奴婢便敢擅作威福,家不可以言齐矣。若主人翁服药治病,渐渐痊可,略知检束,奴婢亦自渐听指挥。及沉疴脱体,起来摆布,谁敢有不受约束者哉?良知昏迷,众欲乱行;良知精明,众欲消化,亦犹是也。”[9]1286-1287
应当说,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讲的是先有“格物致知”,后有“诚意正心”,既要“戒慎恐惧”而“存天理”,又要“慎独”而“遏人欲”,强调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复杂过程;而王阳明的“去人欲而存天理”,则直指人心,只要在心上“省察克治”,去除人欲,这即是“存天理”,显然是一个快刀斩乱麻的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天理人欲问题是宋明理学的重要问题之一。陆九渊虽然反对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但仍然强调要“保吾心之良”“去吾心之害”,说:“将以保吾心之良,必有以去吾心之害。……欲良心之存者,莫若去吾心之害。吾心之害既去,则心有不期存而自存者矣。夫所以害吾心者何也?欲也。欲之多,则心之存者必寡;欲之寡,则心之存者必多。故君子不患夫心之不存,而患夫欲之不寡,欲去则心自存矣。”[8]380显然,“保吾心之良”“去吾心之害”,实际上就是“存天理”“去人欲”。朱熹讲“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讲“去人欲而存天理”,则明确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虽然不同于陆九渊,但都是要“存天理”“去人欲”。所以,就“存天理”“去人欲”而言,无论是陆九渊,还是朱熹或王阳明,他们之间只是大同小异。
三、阳明后学对于王阳明“去人欲而存天理”的继承与变异
对于阳明后学,黄宗羲《明儒学案》指出:“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然龙溪之后,力量无过于龙溪者,又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11]703按照黄宗羲所说,浙中王门的王畿以及江右的王门更为阳明学之正宗,而泰州学派则多为变异。这在传承王阳明“去人欲而存天理”中,亦可见一斑。
浙中王门的钱德洪(1496—1575)强调无欲,说:“昔先师别公诗有‘无欲见真体,忘助皆非功’之句,当时疑之,助可言功,忘亦可言功乎?……及久之,散漫无归,渐沦于不知矣。是助固非功,忘亦非功也。始知只一无欲真体,乃见鸢飞鱼跃,与必有事焉,同活泼泼地,非真无欲,何以臻此?”“君子之学,必事于无欲,无欲则不必言止而心不动。”[11]231-233还说:“古人以无欲言微,道心者,无欲之心也。研几之功,只一无欲而真体自着,更不于念上作有无之见也。”[11]237
王畿(1498—1583)继承阳明“去人欲而存天理”,把良知与人欲对立起来,说:“良知原无一物,自能应万物之变。有意有欲,皆为有物,皆为良知之障。”[10]456-457因此,他主张去除人欲,说:“古人立教,原为有欲设,销欲正所以复还无欲之体,非有所加也。”[10]27他还主张以静坐去除人欲,说:“古者教人,只言藏修游息,未尝专说闭关静坐。若日日应感,时时收摄,精神和畅充周,不动于欲,便与静坐一般。……若以见在感应不得力,必待闭关静坐,养成无欲之体,始为了手。”[10]11
关于江右王门,黄宗羲《明儒学案》指出:“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11]333邹守益(1491—1562)说:“良知之本体,本自廓然大公,本自物来顺应,本自无我,本自无欲,本自无拣择,本自无昏昧放逸。若戒慎恐惧不懈其功,则常精常明,无许多病痛。”又说:“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杂以私欲也。……圣学之篇,以一者无欲为要。”[14]511-515所以,他要求“学以去其欲而全其本体”[14]443,“学以存此心之天理而无人欲”[14]799。可见,邹守益也是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他还说:“天理人欲,同行异情,此正毫厘千里之几。从良知精明流行,则文、武之好勇,公刘、太王之好货色,皆是天理。若杂之以私欲,则桓、文之救鲁救卫、攘夷安夏,皆是人欲。先师所谓‘须从根上求生死,莫向支流论浊清’,吃紧为人,正在于此。如举业一事,言行相顾,便是天理;行不顾言,便是人欲。若谓因人欲以引入天理,则尚未稳也。”[14]517“天理人欲,同行异情”一句,来自宋代胡宏《知言》所言“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同行而异情”。对此,朱熹并不完全赞同,说:“盖天理莫知其所始,其在人则生而有之矣。人欲者,梏于形、杂于气、狃于习、乱于情而后有者也。然既有而人莫之辨也,于是乎有同事而异行者焉,有同行而异情者焉,君子不可以不察也。然非有以立乎其本,则二者之几微暧万变,夫孰能别之。今以天理、人欲混为一区,恐未允当。”[15]3556但是又认为,胡宏所言“下句尚可,上句有病”[6]2591,还说:“只是一人之心,合道理底是天理,徇情欲底是人欲,正当于其分界处理会。五峰云:‘天理人欲,同行异情’,说得最好。”[6]2015显然,朱熹反对的是“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而赞同“天理人欲,同行异情”。
聶豹(1487—1563)引宋代罗从彦所言“为学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见天理,则人欲便自退听”,说:“天理是本体,自然流行,知平旦之好恶、孩提之爱敬、乍见孺子入井之怵恻,不假些子人力帮助。学者体认到此,方是动以天。动以天,方可见天理,方是人欲退听,冻解冰释处也。此等学问,非实见得未发之中、道心惟微者,不能及。”[16]610
应当说,浙中王门和江右王门把良知与人欲对立起来,要求去除人欲,对于王阳明“去人欲而存天理”多有继承。与此不同,同一时期的泰州学派则较多肯定人的欲望的正当合理性。
王艮(1483—1541)说:“‘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良知之体,与鸢飞鱼跃同一活泼泼地。……要之自然天则,不着人力安排。”[17]10-11又说:“良知一点分分明明,亭亭当当,不用安排思索。”[17]43还说:“夫所谓王道者,存天理、遏人欲而已矣。天理者,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人欲者,不孝不弟,不睦不姻,不任不恤,造言乱民是也。存天理,则人欲自遏,天理必见。”[17]64他虽然也讲“存天理,遏人欲”,但他所谓“人欲”,并非指对于声色名利的欲望,而是指“人力安排”,不循天理的人为。
罗汝芳(1515—1588)则明确把天理与人欲统一起来,说:“万物皆是吾身,则嗜欲岂出天机外耶?……形色天性,孟子已先言之。今日学者,直须源头清洁。若其初,志气在心性上透彻安顿,则天机以发嗜欲,嗜欲莫非天机也。若志气少差,未免躯壳着脚,虽强从嗜欲,以认天机,而天机莫非嗜欲矣。”[18]353在他看来,天机与嗜欲,即天理与人欲,二者是统一的,可以相互转化。对于“志气在心性上透彻安顿”者,“嗜欲莫非天机”,人欲即是天理;而对于“志气少差”者,“天机莫非嗜欲”,天理即是人欲。尤其是,他还接受颜山农的“制欲非体仁”的观点,并且还说:“某以旧闻,谓人欲若不净尽,天理安得流行,终日终夜,意甚梗塞,后思原宪克、伐、怨、欲,至于不行,人欲可谓净尽矣。孔子乃曰‘仁则吾不知’,又何尝天理遂流行哉?”[18]317认为“人欲净尽”并不等于“天理流行”。
其实,阳明后学讲天理与人欲的关系时,并没有对王阳明的“去人欲而存天理”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作出明确的区分,且多吸取朱熹理欲论的观点。不仅邹守益讲“天理人欲,同行异情”,实际上也为朱熹所推崇,而且,罗汝芳接受“制欲非体仁”的观点而认为“人欲净尽”并不等于“天理流行”,也与朱熹的观点并行不悖。朱熹曾解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说:“私欲净尽,天理流行,而仁不可胜用矣。”[5]133但是又说:“‘克己复礼’,不可将‘理’字来训‘礼’字。克去己私,固即能复天理。不成克己后,便都没事。惟是克去己私了,到这里恰好着精细底工夫,故必又复礼,方是仁。圣人却不只说克己为仁,须说‘克己复礼为仁’,见得礼,便事事有个自然底规矩准则。”“固是克了己便是理。然亦有但知克己而不能复于礼,故圣人对说在这里。却不只道‘克己为仁’,须着个‘复礼’,庶几不失其则。”[6]1045可见,朱熹认为仅仅讲“克己”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复礼”的工夫,应当讲“克己复礼为仁”。
四、结 论
王阳明曾撰《朱子晚年定论》,以为自己的思想与朱熹晚年相一致,并引述朱熹《答梁文叔》所言:“近看《孟子》见人即道性善,称尧、舜,此是第一义。若于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圣贤,便无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说个第二节工夫,又只引成覸、颜渊、公明仪三段说话教人如此,发愤勇猛向前,日用之间,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这里,此外更无别法。……”[9]153据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所考,朱熹该书可能写于宋淳熙十一年(1184,朱熹55岁)。[19]225-226
刘宗周于明崇祯五年(1632)撰《第一义》,引以上朱熹《答梁文叔》所言,并给予高度赞赏,还说;“学者只是克去人欲之私,欲克去人欲之私,且就灵光初放处讨分晓,果认得是人欲之私,便即是克了。阳明先生‘致良知’三字,正要此处用也。”[20]302-303显然,在刘宗周看来,王阳明的“致良知”,其用功之处正在于“去人欲而存天理”,而根源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如前所述,刘宗周还在《重刻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序》中认为王阳明讲“存天理而遏人欲”,“固孔、孟之言,程、朱之言也”,又讲“‘天理人欲’四字是朱、王相印合处”。
黄宗羲《明儒学案》论及王阳明,不仅采纳刘宗周所谓“天理人欲四字,是朱、王印合处”的说法,而且还说:“先生心宗教法,居然只是宋儒矩矱,但先生提得头脑清楚耳。”[11]202在这里,黄宗羲既把王阳明的“去人欲而存天理”归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又强调二者存在差异,认为王阳明要较朱熹“提得头脑清楚”,显然是站在心学立场上。如前所述,笔者认为,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复杂过程,王阳明“去人欲而存天理”是一个直指人心、快刀斩乱麻的过程,这就是黄宗羲所谓“提得头脑清楚”。
需要指出的是,王阳明继承朱熹“存天理,灭人欲”而讲“去人欲而存天理”,受到了阳明后学泰州学派的挑战;罗汝芳较多讲天理与人欲二者的统一,肯定人的欲望的正当合理性,不仅与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根本不同,而且与王阳明讲“去人欲而存天理”、“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背道而驰。应当说,泰州学派肯定人的欲望的正当合理性,实际上又为清代戴震批评朱熹“存天理,灭人欲”开了先河,而这样的批评实际上也包含了对王阳明“去人欲而存天理”的批评,并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直至今日,朱熹“存天理,灭人欲”,包括王阳明“去人欲而存天理”,依然是学术界热门的话题。[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