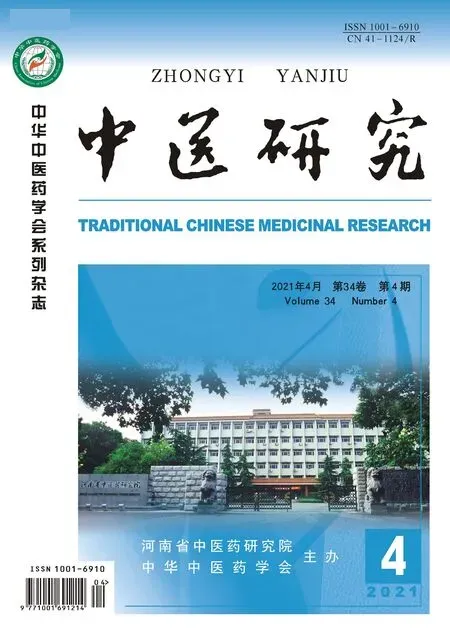脾胃病从痰饮论治探源及经验
汪龙德,杨 博,张 晶,任培培,吴红莉,张 萍,牛媛媛
(1. 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甘肃 兰州 730020; 2. 甘肃中医药大学,甘肃 兰州 730000)
随着社会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人们对饮食的要求逐步提高,饮食不节制易导致脾胃损伤。脾胃与饮食水谷的运化密切相关,若脾胃受伤,则水谷精微运化不畅,容易导致痰饮的产生。“脾为生痰之源”表明了脾胃在痰饮的生成中具有关键地位,而痰饮的产生会导致多种疾病的发生,变化复杂,故有“百病多由痰作祟”之说。痰饮停滞也会导致多种脾胃疾病的发生。从古至今,有关痰饮与脾胃疾病的论述非常丰富,其中东汉的《金匮要略》中所述的狭义痰饮病是这方面的滥觞,此后随着认识的深入,经历了宋代医学的一次大发展以后,关于痰饮与脾胃病的认识也出现了一个飞跃,认识到痰饮在多种脾胃疾病中都具有重要地位。目前,临床可见的消化系统疾病多与痰饮相关,因此在脾胃病中需要重视对痰饮的治疗。但是,痰饮变症纷杂,在临床实践中要明确认识实属不易,故笔者以临床所见结合古人论述,抛砖引玉,分别从痰饮概念的出现及发展、脾胃与痰饮的关系、痰饮所致常见脾胃疾病,以及相关的临床医案来进一步阐明重视脾胃病中痰饮存在的意义。
1 痰饮的源流
《黄帝内经》中虽没有“痰饮”的说法,但有诸多关于水饮和湿等水液代谢失常的论述,比如《素问·脉要精微论篇》中有“溢饮者渴暴多饮,而易入肌皮肠胃之外也”[1]32。《黄帝内经》中关于饮及水湿等的论述为后世痰饮病的滥觞。
痰饮的病名最早出现于东汉张仲景所著的《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篇》[2]43-50中,并且分为广义痰饮与狭义痰饮,广义痰饮又分为痰饮、悬饮、溢饮、支饮。张仲景不仅提出了痰饮病名,其对痰饮病的论述还对后世医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隋朝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痰饮诸病候》[3]中,在《金匮要略》痰饮病认知的基础上,开始依据脉象将痰与饮分论,但是两者在病因、病机及临床症状上并无明显区别。南宋杨士瀛在《仁斋直指》[4]174-182中将“痰涎”与“水饮”分论,并分别给予不同处置。此前医家论痰饮,多是关于饮病,此后医家开始重视对痰的论述。元朝朱丹溪在《丹溪心法》[5]70-79中单论痰病,将痰病分为湿痰、热痰、食积痰、风痰、老痰,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治法,并且认识到了痰在多种疾病的发生中起到关键作用。
《景岳全书·痰饮》[6]691-694中提出,痰饮虽然被认为是同一种类型的病邪,但是两者在质地、停留部位、发病机制上有所区别;认为痰的形成与脾胃相关(脾胃虚则“水谷不化而停为饮” ),五脏伤损亦生痰,但关键还是脾肾;认为“痰,即人之津液,无非水谷之所化”,进一步指出水谷精微运化失常在痰饮的形成中也很关键。
总而言之,痰饮虽有清稀者为饮、稠浊者为痰的说法,但均是三焦水道气化失常,水谷精微运化不畅,停留所致——饮多为有形之邪,固定停留于机体组织之间;痰则致病多端,可见于一身上下。笔者在文中将痰饮统一论述,不再区分。
2 痰饮的病机
痰饮的形成与水谷精微的运化输布不畅密切相关,脾胃为后天之本,水谷均需脾胃运化才能为人体所用。《内经·经脉别论》言“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而饮则“输于脾”,再“归于肺”,又“下输膀胱”[1]45,此表明水谷精微的运化流转依靠脾胃的正常运化与输布。《丹溪心法》指出,在治疗痰病时“利药过多,致脾气虚”,容易导致痰饮,并指出治痰的关键在理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5]70,78,可见痰饮的生成不仅与脾胃虚弱关系密切,还与气机郁滞息息相关。
三焦为水气津液流通的重要通道。《内经·灵兰秘典论》曰其为“决渎之官,水道出焉”[1]17,《难经》[7]言其为“水谷之道路,气之所终始也”“原气之别使也,主通行三气,经历于五脏六腑”,可见运行诸气与通行水谷精微是三焦的主要功能。若三焦功能失常,气机痞塞,水道不通,则水谷精微停聚而生痰饮。《诸病源候论》认为痰是由“血脉壅塞,饮水积聚”不消所致,而饮则因为“荣卫否涩,三焦不调”“饮水多,停积而成”[3];指出痰饮的形成与气机血脉壅塞不通所致津液停聚密切相关。南宋严用和也认为,气机条畅是水液正常代谢的基础,气道“顺则津液流通,绝无痰饮之患”,如果“气道闭塞,水饮停于胸膈”,则结而成痰[8],可见气滞不畅也是痰饮生成的关键。总而言之,水气津液运行不畅则停留而成痰饮,三焦功能失常是气血津液及水谷精微物质运行不畅的主要原因。脾胃与三焦功能密切相关。三焦分为上焦、中焦、下焦,脾胃处于中焦。脾主升清,胃主降浊,两者相辅相成,在调节人体气机升降中具有关键作用。《四圣心源》云:“中气者,阴阳升降之枢轴,所谓土也。”[9]可见脾胃在气机升降中具有关键作用。五脏之中,肝气左旋升发至极则化为心火,肺气右降敛收至极则化为肾水,脾胃为土,处于中焦,升清降浊,为气机升降之枢,且黄元御认为很多疾病的发生均与脾胃功能失常、痰湿阴邪内生致气机不能正常运转密切相关。可见三焦功能的正常与否与脾胃功能密切相关。
《金匮要略》云:“夫病人饮水多,必暴喘满。凡食少饮多,水停心下,甚者则悸,微者短气。”[2]43-50《医宗金鉴》中以其为痰饮病篇第一条条文,认为这是痰饮病的病因所在,注释中认为“暴喘满”是由于饮水过多,水气停于胸膈所致。如果“胃土不能游溢精气”,严重者水饮扰心为悸,轻微者则阻碍气机发为短气[10]。由此可见,脾胃虚弱为痰饮形成的一个方面,饮水过多是其另一个重要方面。为何饮水过多会导致痰饮的形成呢?《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篇》言:“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2]43-50此条经文被后世医家发挥成为治疗痰饮病的基本原则。前文中“食少饮多”当为脾胃虚弱不能正常纳受运化食物,可见食少;若患者又大量饮水,可导致水液不能运化,于是停留为痰饮。饮食水谷的正常运化,有赖于脾阳腐熟水谷功能的正常。若脾阳虚弱,无力运化水谷,则水饮停留为痰饮。
因此,脾胃与痰饮生成关系密切,而痰饮与水谷精微物质不能正常运化输布密切相关,具体表现在3个方面:其一,脾胃在饮食水谷转化为水谷精微物质中具有关键作用;其二,水谷精微物质的转化运输有赖于脾胃气机功能的正常发挥;其三,脾阳腐熟水谷的功能正常与否是水液能否正常代谢的关键。总之,脾胃运化功能失常致水谷精微物质积滞而化为痰饮,故有明代李中梓之“脾为生痰之源”一说。
3 痰饮在脾胃病中的表现
痰饮可导致多种疾病及症状的发生,饮多固定停留一处,而痰则随气上下,病变纷杂,有“百病皆由痰作祟”及“怪病多痰”之说。痰饮致病在脾胃病中表现各不相同,治法也各有侧重。
3.1 痰饮病
《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篇》中提到四饮,其中痰饮的表现为“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肠间,沥沥有声”[2]43-50,指出该病“当以温药和之”。与其同时代的王叔和《脉经》[11]中有引用仲景原文,其中均将“痰饮”作“淡饮”。四饮是以饮邪停留部位而分,临床表现因其停留部位不同而不同。痰饮停留在肠胃,可见肠鸣音亢进,沥沥有声。痰饮之所以停留于肠胃,总由脾胃阳虚不能化水所致,故临床可见脾阳虚弱的征象,如:纳呆,不欲饮食,胀满,饮食生冷则症状加重,大便稀溏或者泄泻,舌淡,苔白滑,脉弦细。治疗上应该“以温药和之”,经过后世医家不断发挥,将此看作是广义痰饮病的治则,也有部分医家认为此原则当仅为狭义痰饮所设,但是无论如何,就本病——狭义痰饮来说,“当以温药和之”是总的原则。故临床常用苓桂术甘汤以温阳化饮。
3.2 嘈 杂
嘈杂一证首见于《丹溪心法》。《景岳全书·嘈杂》言其症状为“腹中空空,若无一物,似饥非饥,似辣非辣,似痛非痛,而胸膈懊恼”[6]502。这些上腹部症状当与慢性胃炎及消化不良等病相参。《丹溪心法·嘈杂》认为此病是“痰因火动”“食郁有热”,治疗上应该“治痰为先”[5]131,明确指出其病因病机,并给出 “二陈汤加栀子、芩、连之类” 的治法。
3.3 呕吐恶心
呕吐由胃失和降、气逆于上所致。恶心,《丹溪心法》云:“恶心者,无声无物,心中欲吐不吐,欲呕不呕……宜用生姜,盖能开胃豁痰也。”[5]121-123。临床上,恶心、呕吐常多伴见,恶心为呕吐的前驱症状。《金匮要略·呕吐哕下利病篇》中谈到了多种呕吐的病症,并根据伴随症状的不同给予不同的处方进行治疗,如小半夏汤、大半夏汤等,其中多以半夏为君药。而半夏长于治痰,可见痰饮与呕吐的发病关系密切。后世医家也认为,痰饮在呕吐的发病中具有重要作用。《丹溪心法》指出:“呕者……有痰膈中焦食不得下者……有胃中有火与痰而呕者。”[5]121-123且认为,治疗当“以半夏、橘皮、生姜为主”。《证治汇补·呕吐》云:“有胃中有痰,恶心头眩,中脘躁扰,食入即吐者。”[12]由此可见,痰饮是导致呕吐恶心的重要因素,临床治疗上多以仲景小半夏汤加减。
3.4 胃 痛
胃痛又名胃脘痛,病机为胃气阻滞,胃失和降,导致“不通则痛”。痰饮也是胃痛的主要病因,脾胃虚弱致无力运化饮食,水谷精微停滞成痰饮,阻滞气血,而致胃痛。《医学正传·胃脘痛》认为,此病责之于“清痰食积郁于中,七情九气触于内”[13],《寿世保元·心胃痛》认为饮食不节,积损脾胃五脏而成痰,“痰火煎熬,血亦妄行,痰血相杂,妨碍升降”而作痛[14],可见痰饮停滞可导致胃痛的出现。胃痛与小陷胸汤证可互参,后者疼痛“正在心下,按之则痛”,且脉浮滑[15]57。此证由于痰热留结心下而导致疼痛发生,故用小陷胸汤。小陷胸汤由黄连、半夏、瓜蒌3味药组成,作用是清热化痰,宽胸散结。
3.5 腹 痛
腹痛的病机为脏腑气机阻滞,不通则痛。痰饮也是导致腹痛的主要原因。《丹溪心法》[5]233-236认为痰邪作痛是因为其“聚则碍其路道不得运”所致,即痰饮阻滞气机不通则痛;指出痰饮是腹痛的主要病因之一。《仁斋直指》云:“痰水……之痛,每每停聚不散。”[4]135可见痰饮是导致腹痛的重要因素。对于此病的治疗,《丹溪心法》认为“台芎、苍术、香附、白芷为末,以姜汁入汤调服”是基本方案[5]233-236。
3.6 痞 满
痞满以上腹部胀满,触之无形,按之柔软,压之不痛为主要临床表现。《伤寒论》曰:“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宜半夏泻心汤。”[15]59-61《金匮要略》曰:“呕而肠鸣,心下痞者,半夏泻心汤主之。”[2]64故半夏泻心汤证在除了心下痞满外,或可见呕吐及肠鸣。《医宗金鉴》称半夏泻心汤证为“痰气痞”,刘渡舟认为“本证的产生,由于脾胃阴阳不和,升降失序,中焦之气痞塞,寒热错杂,痰饮内生之所致”[16]。此外,还有“腹中雷鸣下利”的生姜泻心汤证,其亦与痰饮关系密切。
4 病案举例
4.1 泄 泻
患者,男,64岁,2019年10月8日初诊。主诉:间断性腹痛腹泻1年余。现病史:患者诉间断腹痛腹泻1年余,曾服用四妙散加减,未见明显缓解。刻下见:腹痛腹泻,每逢情绪变化加重,腹痛则作泻,泻后痛减,自觉肚脐左侧疼痛不适,眼干口干,纳呆,眠可,小便调。舌淡红,苔白厚腻,脉弦滑。查体可见:脐左有1个大小约0.6 cm × 0.6 cm 的疣状突起,余未见明显异常。辅助检查未做。西医诊断:慢性腹泻。中医诊断:泄泻,证属肝郁脾虚夹痰证。治宜疏肝健脾,祛湿化痰。给以痛泻要方加减,处方:炒白芍12 g,陈皮12 g,麸炒白术12 g,防风10 g,佩兰15 g,石菖蒲15 g,广藿香15 g,泽兰10 g,丹参12 g,柴胡12 g,川芎10 g ,牡蛎15 g,醋鳖甲15 g,浙贝母12 g,皂角刺6 g,炙甘草9 g。7剂, 1 d 1剂,水煎服,早、中、晚饭后1 h温服。2019年10月22日复诊:腹泻较前缓解明显,且脐周疣状突起较前变小,目前觉疲乏。原方去白芍,加赤芍12 g、炙黄芪30 g。7剂,服法同前。后随访2个月,诸症缓解,未见复发。
按 患者腹痛泄泻与情绪关系密切,每逢情绪变动则加重,痛则作泻,泻后痛减,脉弦,证属肝郁脾虚;且患者舌苔白厚腻,夹杂有痰饮,且脐周疣状突起,考虑与痰凝相关,故用痛泻要方加减。痰湿均为脾胃不能运化水湿所致,痰湿多互见,故用佩兰、石菖蒲、藿香芳香化湿,柴胡疏肝解郁,丹参、川芎活血行气,泽兰活血利水,并用牡蛎、鳖甲、浙贝母及皂角刺软坚散结化痰。治疗后患者症状好转而且疣状突起减小,故辨证准确,继续使用前方加减而效。
4.2 痰 饮
患者,男,44岁,2019年10月29日初诊。主诉:间断腹泻2个月余。患者2个多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腹泻,伴有腹痛,于外院行西医治疗(具体药物不详)后症状较前稍有缓解,目前仍有腹泻,伴有腹痛,肠鸣音明显,大便稀溏,纳眠可,小便可。舌淡红,苔白厚水滑,脉弦细。辅助检查未做。西医诊断:慢性腹泻。中医诊断:痰饮,证属脾阳虚弱证。治宜补脾温阳化饮。给以苓桂术甘汤加减,处方:茯苓12 g,桂枝10 g,麸炒白术12 g,炙甘草9 g,补骨脂12 g,木香10 g ,砂仁10 g ,淫羊藿15 ,制吴茱萸6 g,海螵蛸15 g,藿香15,佩兰15 g ,石菖蒲15 g。7剂,1 d 1剂,水煎服,早、中、晚饭后1 h温服。后随访,患者诉用药后诸症缓解;随访2个月,未见复发。
按 此患者肠鸣音明显,当为《金匮要略》中之痰饮。按照痰饮的治疗原则“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给予苓桂术甘汤加减,合用补骨脂、淫羊藿和吴茱萸以加强温阳散寒的功效,并用藿香、佩兰、石菖蒲以芳香化湿醒脾,木香行气止痛,砂仁温阳化湿,海螵蛸制酸止痛且能收涩止泻。全方共奏温阳健脾、祛湿化痰之效。
5 小 结
痰饮与脾胃病关系密切。如果不注意保护脾胃,暴饮暴食,伤及脾胃可致湿邪内生,聚而化痰。痰饮既是病理产物,又是多种疾病的病因。痰饮所致疾病症状多样,变化纷杂,有“百病多由痰作祟”及“怪病多痰”的说法。脾胃功能正常是水谷精微正常运化输布的关键,故在临床上,不仅要注意辨证论治以攻伐痰饮,还要注意保护脾胃。重视痰饮在脾胃病发病的重要性及脾胃在痰饮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是进一步防治脾胃系病证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