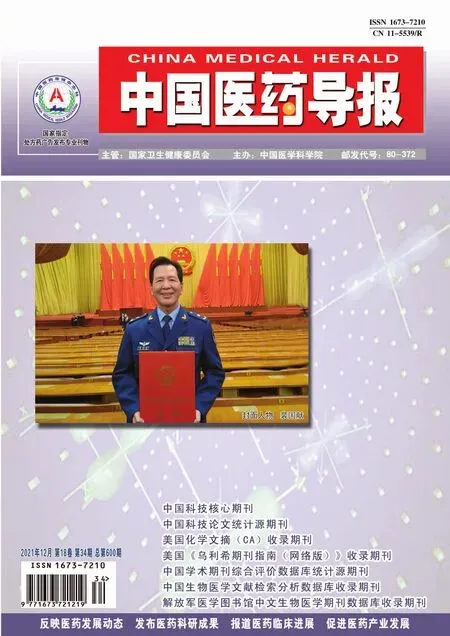槐轩医派刘子维用药特点分析
谷仁壮 于 晨 崔文成
1.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2.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3.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济南市中医医院儿科,山东济南 250012
槐轩医派是槐轩学派的分支,槐轩学派的主要核心思想是以儒为本,兼采佛道,槐轩医派即在此基础上形成。郑钦安师承自刘沅,郑钦安被认为是火神派的开山鼻祖,所以后世称刘沅为“火神之祖”,因此槐轩医派实为火神派的源流。刘子维为刘沅之子,继承了其父的学术思想,指掌槐轩医派二十余年,其医学思想存于《圣余医案诠解》中。近年来火神派及其思想在中医界广泛流传,影响甚广,而槐轩医派却不被人所熟知。刘子维的用药法度井然有序,特点鲜明,有阴阳互补、补木生火、火必敛藏、升降相依、补虚泻实、敛散相合6 个主要特点,现将其用药特点介绍如下:
1 阴阳互补
阴阳互补的用法,源自阴阳互根互用的理论。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故张景岳[1]曰:“阴根于阳,阳根于阴。”黄元御[2]曰:“阴阳互根……阴以吸阳……阳以煦阴……阳盛之处而一阴已生,阴盛之处而一阳已化。”刘子维使用阴阳互补的药物是考虑到阴阳互根互用的原理,使阴阳化生无穷,并可以制约药物的偏性,相辅又相制,最终达到阴平阳秘的目的。刘子维阴阳互补的用药特点不仅应用于肾脏虚损诸症中,而且适用于其余诸脏中。肾之阴阳互补中常用附子、肉桂、补骨脂以补肾阳,熟地、枸杞子、玄参补肾阴;脾之阴阳互补中常用干姜补阳,山药以补阴;肝之阴阳互补中,常用首乌、枸杞子、白芍、酸枣仁以补阴,杜仲、肉桂以补阳;心之阴阳互补中,用西洋参补气升阳,用龙眼肉、阿胶、柏子仁滋液润燥;肺之阴阳互补,常用黄芪、沙参培土生金,用麦冬、天花粉、五味子清降天气。
孙某,睡至半夜,心内不适,出汗至天明,舌不转,不能言语[3]128。刘子维认为本病由于肾水衰竭于下,夜半之时,虚阳上亢,导致心内不安,心阴不能内守而出汗;舌不转、不能言语也是由于肾精亏虚不能上荣于舌。刘子维认为命门为水火之根,水既虚则火不独留。因此用枸杞子、地黄、玄参以补水的同时,加用附子八钱以补火。玄参、地黄、枸杞子得附子,则水能升腾上济。因此附子在此方中与诸补阴药相合,发挥火降水升的作用。
李某,夜卧平静,次早周身不能动,四肢无力不能动,如痴人,饮食减少,饮食无味,精神少,下身冷[3]150。刘子维辨为阳虚痿证,认为诸症皆由脾肾阳虚导致,而肾命又为脾胃生化之源,本病以补肾阳为主。故用附子、肉桂、补骨脂温补肾阳,而无阴则火不能养,因此又在方中加用枸杞子、熟地以补肾阴。既发挥补阴配阳的作用,又可制约热药燥性。
某患者,咳嗽痰多,恶风,面白[3]139。刘子维认为本病由于火不生土导致脾虚生湿,脾虚则不能生金故咳嗽痰多。《金匮要略》[4]云:“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刘子维用肉桂、附子补火生土,姜、术、参补中生金,用陈皮、半夏、茯苓、益智仁治痰饮之标。”刘子维又用天花粉清气分,生地清血分,山药敛脾阴。刘子维谓此方补脾祛湿,且不助火、不耗气,而痰症自消。此方以扶阳为主,而用天花粉、生地以保阳中之阴,且有山药制于中焦,则可升可降,故有火之利而无火之害也。无阴则阳无以化,因此于下焦加用生地,中焦加用山药,上焦用天花粉,此为阴中求阳之妙用也。
2 补木生火
与现代火神派纯用辛温热药补火的方法不同,刘子维在生火、藏火、运火都有娴熟的方法,补木以生火为刘子维常用的方法之一。刘子维认为人在先天有木始有火,火中有生气乃能化出五脏,生阳之发源在肝木。根据五行相生理论,木能生火,木生之心火为顺生;水本能生木,补木而生之命火则称为逆生。不同的是心火须彰显于外,命火须潜藏默运。刘子维常谓,知补火而不知生火,犹之劫财而不知理财也[3]152。刘子维最常用杜仲温木以生火。《本草纲目》[5]:“杜仲色紫而润。味甘微辛,其气温平,甘温能补,微辛能润,故能入肝而补肾,子能令母实也。”因此杜仲能入肝以补肾,甘温生命火而治疗肾阳虚诸证。
在治疗胃纳不利,咳痰多,气紧,稍食多即不消化的医案中。刘子维认为胃纳不利、食不化、痰多为脾不能为胃散精于肺而为痰;咳逆、气紧为肺不能为胃布精留而为饮。因此痰饮贮于脾肺为标,脾肾阳虚不能温化寒湿是本病之本。因此本病当以生阳为先。刘子维谓:生阳之发源在肝木[3]134。用杜仲以补木生火为君药,再用附子、补骨脂补火,黄芪、白术以补土,用半夏、葶苈子、细辛散水饮。考历代医家杜仲多于肝肾阳虚之腰痛,刘子维用之补木生火消痰饮乃一创举。
刘太师母,腰胀痛,头两侧稍痛,心内觉不适[3]191。刘子维认为老人腰痛大都缘于肾虚,肾阳虚则寒湿留故腰胀痛;肾阳虚则肾水不升,心肝之火即升浮不降,故有两鬓胀痛、心内不安。所以本病之根在于肾阳虚,因此刘子维用附子温肾阳,用杜仲以温木生火。刘子维谓:“人皆知水能生木,讵知木亦生水乎?木生水谓之真水,亦即真阳,然非明于阴阳五行顺逆之理者,不足以语此也。”[3]192刘子维认为,肾为水脏,肾能生肝即水生木为五行顺生之理,而肝生之火藏于命门为五行之逆生。肾为坎卦,肾本为水脏,肾中藏有命火,以成水火之脏,因此真水即为命火亦为真阳。木生水中之火即刘子维所谓五行之逆生也。
3 火必敛藏
火必敛藏为刘子维于阴阳互补,补木生火之后招。刘子维认为相火位于命门不可离也,不离则生人,离则杀人,故补肾之法,必使命火寂然不动,而后生气下蛰,水可生焉。并且肝为肾子,肝阴不敛,火不藏也;土为火子,脾阴不敛,亦不藏也。火须潜藏默运,氤氲而发,升发于天而成君火。因此,初生之火须敛藏而发,升浮离散之火亦须敛藏归位。符合《素问》:“壮火食气,少火生气;君火以明,相火以位的思想。”[6]9,129因此,刘子维常在运用补火药的同时使用固精敛藏之品,如覆盆子、金樱子、沙苑子、黑豆、牡蛎、白芍、首乌、山药等。
刘子维治疗久病咳嗽。《难经》[7]言:“三焦者,原气之别使也。”《素问·咳论》:“久咳不已,则三焦受之。”[6]76认为久咳由于三焦之根不固,而三焦根于命门。三焦之气逆则上实下虚,下虚者须补下,而补火必兼敛藏,相火才能根于命门,而为少火生气焉。因此刘子维用补骨脂以温下,兼用黑豆镇摄,酸枣仁、牡蛎敛藏。使元海命门之火封藏,暗发氤氲,成为布散全身之本。周身运行之气,即命火所发之氤氲,必有藏而后有发,又必有通而后发者不郁,生机乃畅。刘子维又于火敛之后施以散通之品,以达火之用也,补之、潜之、达之各以平为期,这是刘子维火必兼敛,敛散相合之两合法也。
某患者,牙龈肿如茄,面赤,舌黄色白[3]269。茄色为黑红色,即水胜火之外见也。牙龈肿、面赤、舌黄皆热象,然未有实热证。牙龈肿而不痛,舌黄而带白,面赤,皆由于下虚而阳浮也。原批云[3]269:“此是元气浮于外而不潜藏,回阳收纳为要。”故用附子、肉桂引火归元,用白芍以平肝敛肝,然后火乃克降;又用山药敛阴守土,酸枣仁收敛上焦神气;又用沙参、生地、知母、菊花清金降火;最后加用金樱子、牡蛎固秘精气,潜之于下。这是刘子维火必敛藏之用法也。
4 升降相依
刘子维常于三个方面用到升降相依的方法,一是邪气阻隔导致升降失常;二是脏腑虚损或阴阳失调导致升降失常,三是脏腑本身即具有升降属性。人身本是一小天地,肝肾居于下焦象地,心肺居于上焦象天,脾胃斡旋中焦主枢机,地气上升为云,天气下为雨,天地气交,而成生化之机。因此刘子维常用清降天气之品使天地气交而收工。刘子维常用麦冬、沙参、阿胶、龙眼肉、柏子仁等润泽天气,五味子、枣皮敛降天气,使阳中有阴有下降之源。黄芩、连翘、栀子、木通、枳壳苦寒直降天气;黄芪、党参、鹿角、杜仲、肉桂甘温以升地气。
刘子维每于上焦邪实兼有中焦气虚时,于补虚泻实方中兼用升降之品。上焦邪实则心火不降,中焦气虚则清气不升,升降失序,则疾病见矣。在治疗咳嗽,痰多,周身麻木,四肢无力案中,咳嗽、痰多由于肺郁心火不降为上焦邪实。而痰饮之本在脾,久咳亦伤及脾胃,脾虚不能升清四达,则四肢无力,此为中焦气虚不升。补中气则有碍心火下降,降泻心火则重虚中气。因此于升补中气药中佐以降气泻火之药。而火又随气降,肺气降心火亦降也。用百部、枳壳降天气,用栀子、连翘直折心火,再参用健脾升清之品。因此刘子维常于补虚泻实药中参用升降之品,而补虚之药常兼升性,泻实之药常兼降性,常常一举两得。
治疗黄思望之叔母,久病,面青白,口子午干苦,足冷,右胁有包,今春误药吐血,现胃口不开,作咳有痰,四肢无力,不能坐起[3]145。《素问·通评虚实论》曰:“气逆者足寒也。”[6]57《解精微论》曰:“阳并于上,则火独光;阴并于下,则足寒。”[6]201口子午干苦,足冷者,寒气厥逆而火不降也。诸血皆属于心,口子午干苦者,由于吐血后,离中之阴虚而火不降也。四肢无力,不能起坐者,脾虚也。因此本病由于阳虚于下,而阴虚于上,水火失交。脾胃虚,故补以白术、参、芪;寒在下,故温以附片,使地气上升;热在上,故凉以生地、黄芩,清以麦冬,散以薄荷,降以木通,使天气下降;胃口不开,生姜宣发上焦,为附、术之使以开之;右胁有包,香附、佛手开郁利气,为参、芪之使以运之。故用生地补离中之阴,以治火不降之本,黄芩、麦冬、薄荷则清金散火,以治火不降之标也。此即脏腑虚损,阴阳失调导致升降失常,治疗必须参用升降之品。
治疗阳虚不食、不语、神少案中,用补火敛藏生发之品最后又加用天花粉清降,沙参、龙眼肉滋润使阳中得阴,天气而后下行,气血得以生化。治疗阳虚痿弱,四肢不能动,饮食少、精神少诸症中,五味子与黄芪同用,谓唯五味子能驭黄芪之气为治节之气,垂雨露于洪钧。这与生脉散、李东垣清暑益气汤、张锡纯玉液汤升地气,降天气而成生化的理论用法一致,源于肺为华盖,居于上焦象天,肺气降则天气下,成天地气交。这是基于脏腑自身具有的升降属性而选择具有升降属性的药物。
5 补虚泻实
刘子维治疗无论正虚导致的邪气内生,还是因为正虚招致外邪侵袭,都考虑到虚实两个方面,常补虚泻实齐用。认为邪正不两立,一胜则一负,故必以补正为祛邪之本,而后克伐诸药乃得以成祛邪之用。刘子维谓:“夫操刀杀贼,必假健儿之手,非刀自能杀贼也,用克伐药祛邪,必籍脾胃之运,非克伐药自能祛邪也。”[3]136若有泻无补,则既虚之脾胃方苦不克承当。关于补泻之度,总需保持上焦得通,心火得以下交为度[3]136。这句话的意思是邪气侵袭上焦,郁而不行,祛邪药得补虚药之手,使上焦得以宣散,若补药过用,则外不得散,内亦壅也,病成痼疾;上焦邪实则心火不得降,而补虚之药性常甘温气升,若过用补虚之药则心火不降甚矣,因此补泻之度,总需保持上焦得通,心火得以下交为度。
治疗风邪客于手足阳明经导致的头痛时,除了常用的祛风行气活血药外,还重用黄芪一两,三付即痊愈。认为“邪之所凑,其气必须”,虚不补则邪难出,故重用黄芪协诸风药,以成祛邪固表之功。刘子维的此举用法与黄芪桂枝五物汤、玉屏风散的旨意不谋而合。
在治疗因寒湿有余,寒饮客于肺脏导致的咳嗽痰多案中,除用补气生阳以治寒湿之本外,用葶苈子泻肺饮之实,生姜宣肺窍之闭,细辛散肺饮之寒,而又须用黄芪治节于上,黄芪亦用至一两。认为饮之初由于气不运,饮既成则又气不舒,徒补虚则盛盛而固邪,不舒者愈不舒;徒攻邪则虚虚则伤正,可散者复可聚。唯黄芪与葶苈、生姜、细辛相辅而行,则各展其长,互制其短,溃以成之坚,杜未来之渐[3]134。黄芪与细辛、葶苈子、生姜成补虚泻实之组合。
于肾水不足,心火不降而致的心馁、心跳案中,肾水不足则心阴亦不足,心阳无所系,心火亢于上成燎原之势,不得下交于肾,而成为邪实一端。肾水不足,肾中阴阳亦呈偏态,肾水不足则相火偏盛。总之,水不能升,火不能降,呈上盛下虚之候。刘子维常用玄参补肾水、制心火,栀子、连翘泻亢盛之火,使心火得以下降;用玄参、生地、熟地、枸杞补肾水,亦须泻有余之肾火,此泽泻之用途也。人体内阴阳水火失调,有一隅之虚,就有一隅之亢,成虚实互见之势,补虚泻实、泻南补北是其法也。
6 敛散相合
敛散相合亦有两层含义,散者散邪实也,敛者敛精气也;敛者敛逆气也,散者达正气也。散敛与敛散各有侧重,一者以邪实为主,一者以正虚为主。散者须敛,而敛者亦须辛散以达之。犹之善用兵者,必能守而后能战,敛阴以为阳之守。邪气盛须散,散则耗散正气,必收敛之品与散邪之品同用,散邪而不伤正,与补虚泻实意义相近也。下虚气逆时,用补火敛藏法,常用到大量镇摄敛藏之药。刘子维谓敛阴者必利阴气,在用大量补益收敛药的同时又常兼用辛散通达之品,敛必兼通之意也。刘子维敛上焦常用五味子、杏仁;敛中焦常用山药、白芍;敛下焦常用金樱子、牡蛎、酸枣仁。散上焦常用生姜、防风、金银花、薄荷;散中焦常用陈皮、青皮、香附、大腹皮;散下焦用艾叶、鹿角,前者利阴气,后者通阳气。
在治疗痰饮咳嗽案中,用葶苈、生姜等辛散药散邪的同时,又佐五味子酸敛药收敛精气。谓有形之痰,虽宜攻散;而无形之精气,则宜静藏。刘子维此法与小青龙汤中干姜、细辛与五味子同用亦同一源流,散邪气,敛正气,邪去而不伤正。
刘子维治疗一患者,脚痛,卧床月余,痛难堪,不能行,痛无定处[3]159。刘子维辨为风寒湿合而为痹,风寒湿三气内应肝脾肾三脏,必三脏之不足,然后三气得以深入。本病治以扶正为主,祛邪为次。用黄芪、白术、甘草、益智仁、附片、肉桂、巴戟天、鹿茸、枸杞补正;桂枝祛风,木香理气,当归活血,皆为补而兼通所用;又白芍一两平肝敛阴,以节制诸辛温辛热之刚,犹桂枝汤中桂枝配白芍,发中有收,以静制动。三付服后,又加用首乌八钱、金樱子五钱、黑豆八钱入肝肾之阴,以静制胜,与方中温热诸药所生之阳转为封藏之阳。又加用防风二钱,敛后又兼通,使生气能流行周身。认为人以生气为主,阖则能含生气之本于宥密,开则能畅生气之标于一身。故用药之妙,往往开中有阖,阖中有开,前方中白芍,后方中用防风即是此意也。前方通补兼敛,后方敛阖兼散。
7 结语
刘子维的用药特点符合中医的阴阳之道,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升中有降,降中有升,敛中有散,散中有敛,总使阴阳平衡,阴阳合和,达到疾病向愈的目的。而阴阳互补,升降相依,敛散相合等用药特点,合而参看则又符合中医整体观。因此,刘子维用药的阴阳观与整体观非常值得学习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