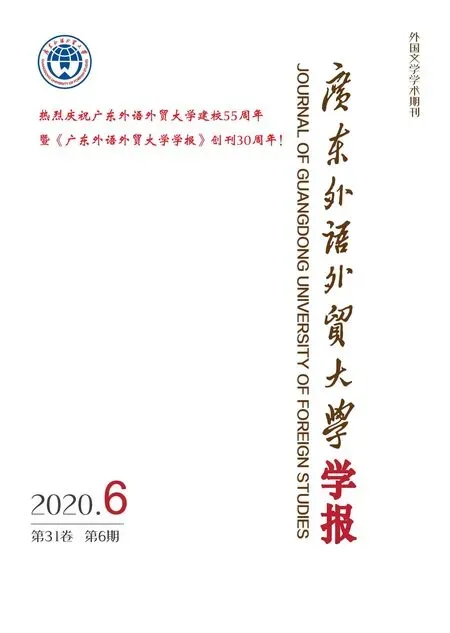蒂泽对阿多尼斯神话原型功能的揭示及其效果
张鸿
引 言
法国现代文论家埃莱娜·蒂泽(Hélène Tuzet)的《阿多尼斯的死亡与复活:一则神话的发展史研究》(以下简称《阿多尼斯研究》,1987)是一部文学神话学研究著作①。作者以阿多尼斯神话为线索,分析了欧洲古今三十余位学者、诗人或作家对该神话的研究和创作,以此说明该神话在神话学和文学两个范围内的演变史。蒂泽的文学意象研究经历了从某地理区域到宇宙整体再到单个神话的发展过程,其文学理论和批评突破了纯粹文学的局限,蒂泽关心“整体人类学、关心科学作品和艺术作品中的意象、关心上述不同领域的相互作用”(塔迪埃,2009:108)。但迄今国内外学界对蒂泽的诗学思想尚未充分研究。为了阐明蒂泽研究阿多尼斯神话的方法和意义,本文将通过原型概念对《阿多尼斯研究》进行分析,从三个方面说明蒂泽对该神话原型功能的揭示及其效果:该神话的原型特征和内涵,该神话原型的外延,该神话的发展规律、相关文学创作的变化趋势和蒂泽的诗学观。
阿多尼斯神话作为原型的基本特征及内涵
蒂泽在书中并未过多提及“原型”概念,但阿多尼斯神话具有明显的原型性质。文学原型就是“反复显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可识别的叙事策略、行为模式、人物类型、主题和意象”,“死而复生的主题”是“原型中的原型,它以季节的转换和人的生命的有机轮回为依据;这种原型被认为是发生在每年帝王献身的原始仪式中……以及众多的各类文学作品中……”(艾布拉姆斯,2009:25-27)。众多诗人和作家对阿多尼斯神话进行了再创作,从而使该神话具有原型的实质。较原始的阿多尼斯神话有以下基本情节:亚述国王之女生阿多尼斯于没药树;因阿芙洛蒂特与冥后之争夺,宙斯裁决二女神一年内轮流拥有阿多尼斯;阿多尼斯在狩猎中死于野猪攻击,死后化为银莲花,阿芙洛蒂特哀悼之。以下简要概括蒂泽所列部分阿多尼斯题材作品的内容,以说明该神话的原型特征和蒂泽的研究思路。蒂泽的研究涉及相关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见表1,表1仅涉及内容,而不关注文体、风格和语言等问题。我们将看到:阿多尼斯是反复出现的人物类型,他的故事是反复出现的意象,他的名字是“死而复生”的代名词。

表1 韩中日FTA竞争现状

十九世纪中后期及二十世纪初柰瓦尔之《东方之旅》(Voyage en Orient,1851)、《火的女儿:伊西斯》(Les Filles du Feu:Isis,1854):阿多尼斯代表自然、植物、激情和痛苦中的太阳、变形的种子、仁慈的河流、冬季的受害者,包裹在“大女神”神话中,与基督混同,受祭拜并复活。福楼拜之《圣·安托万的诱惑》(La Tentation de Saint Antoine,1875):阿多尼斯死后未返人间;与女神之爱象征太阳与地球的结合,神婚中迸射出宇宙生命;野猪象征衰落;异教和基督教祭仪的统一性。邓南遮(意大利)之《圣·塞巴斯蒂安的受难》(Le Martyre de Saint Sébastien, 1911):阿多尼斯象征太阳(神)、种子、春天,具有双性别,带来生育,不断死亡和重生,其死亡等同于基督受难;描写阿多尼斯葬礼。
如表1所示,阿多尼斯神话是普遍出现的题材,贯穿整个欧洲文学史,这也是该神话被认定为文学原型的主要原因。这个原型是逐渐生成的,且从原型发展为原型群。以阿多尼斯人物本身为例,他不断获得多种身份:丛林男孩、理想情人、牧人、诗人、受害者、拯救者,并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春天、植物、绿色、新鲜、阳光、清晨、河流、朝气、更新、美、纯洁、死亡(早夭)、小麦、种子、太阳(神)、基督、太一、形式之父。从人物类型看,阿多尼斯和维纳斯代表儿童原型和女神原型。从情节看,原型也很丰富:出生、人神恋、神婚、死亡、地狱行、复活等。单个意象构成的原型有树、花和猛兽等。该神话包含的各种原型代表了人类生活的各方面,涉及人与自身、与自然以及与神的关系。比如植物象征生命的普遍特征:阿多尼斯生于没药树,死后化作银莲花,说明物质不灭,生命不息,生命以不同形式不断存在,形式的变化意味着生命力的创新。这个过程反映了人类的某种原始思维,即通过具体可感的方式表达对生死的基本见解:生和死并不表示存在和非存在,或者如卡西尔所说的生和死“是作为同一存在物的两个相似的、同质的部分”,在原始思维中“根本没有确切的、被清楚地界定的瞬间,在这一瞬间生变成死,死变成生”,生是“一种回复”,死是“一种生存”(卡西尔,1992:42)。野猪象征人类的生存境遇,它是人类面临的众多困难的缩影。再如死亡,这则神话描述了一种悲惨的死亡形式:早夭。该故事的各种元素都在变化,唯独英年早逝这一点始终留存,归根结底,这是人类对某种显著的生命现象的观察结果。生与死的强烈对比所产生的震撼是这个神话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人神恋和神婚表达的是早期人类希望永生不死的愿望,实现愿望的方法就是与不朽的存在物发生密切的联系。地狱行则说明了人类想象死后所进入的世界。这些原型的象征意义表明了该神话的核心,即生与死这一对永恒的问题,这种反映人类最基本问题的功能也解释了该神话原型普遍出现的原因,并使该神话具有精神性的遗传特征。
程金城(2008:186)认为原型有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其中内涵是原型的“逻辑起点”,是“一元”的。笔者认为阿多尼斯神话原型的基本内涵就是生死问题,这是阿多尼斯神话的起点和核心,各种情节都围绕这个核心而生。历代诗人和作家都从这个核心出发对该神话进行重构,将其哲学化、世俗化或进一步宗教化。后世阿多尼斯作品与原始阿多尼斯神话相比有很多变化,但作者们都无法脱离这个基本内涵。原始阿多尼斯神话是该神话原型内涵的最初表现方式,也是这个故事发展的基础,但其作用有限。该神话原型的变化、生成和丰富主要是创作者连续构建的结果。各时期阿多尼斯作品之间构成了延革和并置的关系,这个关系也是《阿多尼斯研究》的基本框架,蒂泽以此对各时期作品进行比较,揭示了该神话的原型特征。
阿多尼斯神话原型的外延
人们重构阿多尼斯神话,不断为之附加新意义,从而发展了这个神话原型的外延。程金城认为原型的外延是多维的:“生理”“心理”“哲学”“文化”等。这些维度说明:原型的基础是“人类的生理本能”,原型的不断重现就是“类似的或共同的心理现象的反复”,原型具有各种文化重现方式;其中哲学之维将原型分成了“原”与“型”两个层次,“原”表示“原始”和“开端”,“型”是“类型”“范式”和“结构”的意思,“范式”能够被“反复用”,可以被填充或重现(程金城,2008:186-195)。分析阿多尼斯神话原型的多维外延也有助于说明蒂泽揭示该神话原型功能的方法。
蒂泽以不同的阐释角度将历代学者对阿多尼斯的研究进行了分类,以时间先后或国别将阿多尼斯文学文本进行了排列。笔者认为多角度阐释和多样创作正反映了该神话原型外延的多维特征。学术发展史和文学发展史一同促成了该神话向原型的转变。在各种阐释中该神话原型的自然性基础以及反映共同心理的本质特征得到体现。关于该神话的自然性起源,蒂泽所研究的某些神话学者认为该神话产生于原始人类对太阳运行以及果实的成熟和死亡的观察。人类又将自身与天象、物象相联系。因此不少学者都认为阿多尼斯神话反映了原始人将外部世界与自身的生理现象结合的过程,比如将植物的死亡等同于人的死亡。这一结合又伴随着某些情绪和心理模式,所以人的死亡和植物的死亡引发相同的情绪。因为太阳落下又升起,植物种子或果实的腐烂导致发芽和生长,面对这些景象,人们心中既有悲哀,也有喜悦。例如某些古代学者认为阿多尼斯的死亡反映了“种子在地下的死亡”或“镰刀割下的麦穗的死亡”,这种死亡导致“发芽和生长”,引起“农人的喜悦”(Tuzet,1987:46)。弗雷泽的阿多尼斯研究也强调这一结合和引发过程,他认为原始人类将“植物的生死”与“人类自身的生死”相结合,将自然现象与“个人的经验”和情感——“悲伤”“恐惧”相结合(Tuzet,1987:60)。在文学文本中该神话原型反映人类心理的本质更加明显。上表说明各阿多尼斯文本之间的关联源于原型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相似心理,如拜翁和邓南遮的相关作品:无论是公元前三世纪还是现代社会,阿多尼斯的死亡永远使其信众痛苦、哭号。再如拜翁与马里诺作品:因为阿多尼斯象征生命或太阳,所以自然界所有神仙齐聚一堂哀悼死亡的阿多尼斯。人类面对生死而产生的生理经验导致了某些固有的心理,生是欢乐,爱和美值得赞赏和追求,死亡带来惊奇、迷惑、惋惜、恐惧、悲哀和希冀等。
从哲学维度看,阿多尼斯神话的“原”是指该神话最初的元素,其整体构成了它的“型”。“原”决定了“型”的基本走向,“型”被填充以新的人类思想和行为,保证阿多尼斯神话的“原”持续存在于人类的精神中。故事的本原与各种异文之间的关系对应于“原”和“型”的关系。蒂泽叙述阿多尼斯故事最古老的内容和形式是“正源”,是确立这个故事所反映的早期人类文化形态(比如阿多尼斯祭仪)。由上表可见,梳理各时代的相关作品说明了“型”如何被填充。创作者通过各种演绎使原始的阿多尼斯神话从短暂性和单一性上升至持久、多元的“型”的态势,获得了“范式”的牢固性。蒂泽对该神话流变的研究不仅再现了基本的文学创作事实,也将人们对阿多尼神话的认识从一个普通神话的层次上升到原始或普遍意象、“范型”的层次,将一个故事构建成一种叙事模式。另外阿多尼斯的“原”与“型”的紧密连接还需要一个不变的核心,即上文所说的人类对生死的基本见解。阿多尼斯故事以个人偶然经历体现了整个人类命运的走向,反映了人类的普遍生存经验,表现出广泛意义上的人类精神生活。阿多尼斯作品虽然多变,但通过蒂泽的研究,读者认识到古今人类面对生死在情感和心理方面的一致性。从表面上看,蒂泽的研究对象是神话故事的演变和创作者的想象心理;但从深层看,这一研究说明的是人类某种精神现象的源与流。
文化维度反映原型的再现或传播方式,以及传播的广度。蒂泽汇集的各类文本说明阿多尼斯神话除进入文学,还成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蒂泽分析了从一世纪到二十世纪十几位西方学者对阿多尼斯的研究,他们的研究角度说明该神话涉及的文化领域包括神话学、哲学、天文学、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和宗教学等。试举三例:神话学意义阐释——阿多尼斯神话的发源地比布鲁斯(Byblos)是“世界之脐”(Tuzet,1987:62);天文学意义的阐释——“阿多尼斯回到维纳斯身边”意指“太阳回到黄道十二宫居上的星座中”,“白昼变长”(Tuzet,1987:49);宗教学意义的阐释——阿多尼斯处于“激情和苦难双重状态”,这反映“秘传宗教”概念,即通过苦难而“升华、纯洁化和救赎”(Tuzet,1987:53)。阿多尼斯神话对于学者和诗人来说是一种文化类“情结”,“情结”最初是个人或群体的生理和心理体验,后来通过某种文化方式得到外化。神话进入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使包含在神话中的人类体验变得容易把握且有趣味,同时神话本身也获得具体可感的、可传递的性质,即得到外化。蒂泽的研究说明每当阿多尼斯成为学者和诗人的阐发对象,其文化影响力就得到增强。人们阅读阿多尼斯作品,对早期人类的体验产生共鸣,即使是在文明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人类对生死问题的迷惑和恐惧依然如故。个体和集体经验只有借助某些文化形式才能得到具体表达,并为后人所感知。因为神话的本质就是反映人类对自身生存及生存环境问题的具体见解,所以卡西尔(1992:5-7)认为,神话不是纯粹的虚构,它具有强烈的主观真实性。“正是在文学中,人类具体的见解才得到其表达”(洛夫乔伊,2015:22)。
学者的研究其实也具有阐释的效果,他们与诗人一起参与该神话原型功能的构建。也许学者认为自己的解释是科学的,但从上文可以看出原始阿多尼斯故事并不必然包含哲学、人类学和天文学等知识。可以说学者的研究与诗人的创作一样具有鲜明的艺术气质。这就是蒂泽对学者和诗人的一贯看法:他们思考和创作的主要动因就是想象力。我们借用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概念,将蒂泽所列出的学者和诗人看成阿多尼斯神话的读者,这些特殊的读者接受原始阿多尼斯神话故事时各自发挥了阐释该文本的“科学或艺术”手法(伊格尔顿,2007:64-86),而科学或艺术的阐释和再造填补了伊泽尔(Wolfgang Iser)所说的原文本的“空白”(贝西埃,2010:587)。这个过程不断远离原文本。从下文的分析可知造成远离的原因:阐释和再创作必定包含个人喜好、时代风尚和特定文化背景。
阿多尼斯神话原型的外延隐含在蒂泽的研究中。文化发展过程中该神话原型功能的形成应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该神话在古代社会的初步生成与流传,第二是学者及诗人对该神话内容和意义的丰富,第三是对相关学术文本以及文学文本的比较。蒂泽的研究属于第三个阶段。
蒂泽揭示阿多尼斯神话原型功能的效果
蒂泽揭示阿多尼斯神话的原型功能产生了某些更宏观的效果。表1虽能说明蒂泽的研究过程,但细节众多,不利于读者把握创作者演绎该神话所遵循的规律。下文从三个角度对此进行说明:创作者与时代的关系、作品分类以及该神话题材作品书写方式的变化过程,并由此推导出蒂泽的诗学观。
第一,创作者从多大程度上尊重阿多尼斯神话传统取决于作者的主观性与时代风尚的结合。从个人和时代的关系看,该神话在文学创作中的变形应遵循“每一个时代所特有的真善美标准”,这样才能使一则神话“显得真实可信,在艺术上和谐,在道德上为人普遍接受”(叶舒宪,2012:14)。古代风尚以古希腊诗人为例,仪式感以及现实人物和神话人物身份的混同是那个时代诗歌创作的某些特点。比如表1中的希腊诗人忒奥克里托斯,他注重阿多尼斯祭仪,描写贡品、器物、场地的装饰以及信众的情感。这个特点反映该神话最初是一种宗教仪式,经由“亚述、叙利亚、阿拉伯半岛和塞浦路斯”传至古希腊,“阿多尼斯祭仪很早就被希腊化了”(Tuzet,1987:29)。在古希腊社会,阿多尼斯祭仪也是节日,受到王室的奉行。诗人为了彰显阿多尼斯节日的仪式感,将其作了相应变形。正如蒂泽强调的那样:原版神话中阿多尼斯将一年时间分给了二女神,但在忒奥克里托斯笔下阿多尼斯只用一天时间就分属于二女神,诗作突出描写的是年轻的半神阿多尼斯与女信众之间的关系,渲染“爱”“欢乐”的情感和“哀悼”场面(Tuzet:1987,87)。另一位古希腊诗人莫朔斯的作品《拜翁的碑铭》混同了诗人拜翁和阿多尼斯的身份,他们是“牧人”“猎人”“歌者”以及“诗人”(Tuzet,1987:91)。近代作品以维加的《阿多尼斯与维纳斯》为例,如表1所示:阿多尼斯是丛林之子,这是近代田园文学的典型形象;恶意的诸神窥视人类的“纯洁力量”,用诡计杀死“质朴”“自负”的人类少年(Tuzet,1987:106-112)。一般情况下,仇恨并妖魔化诸神不是古代诗人的做法。
第二,英国学者约翰·怀特提出“原型预示”理论。怀特用该理论对具有神话成分的现代小说进行分类,即根据神话出现的显隐程度把现代小说分为四类,并提出“完全地重新叙述”“部分叙述”“参照模式”和“暗含”等标准或概念(转引自叶舒宪,2012:230-232)。笔者借用这个模型对蒂泽所列古今文本进行大致分类,并在怀特的基础上对各类型的特征进行说明。第一类作品重述阿多尼斯神话,增加人物,使情节丰富、背景多变。比如龙沙和马里诺。第二类作品较完整地重述该神话,并使其成为现实世界的“参照”,以说明作者的思想或现实世界的问题。如莎士比亚和雪莱。第三类作品中起主要“参照”作用的是该神话的某些情节,这些情节之前未受重视,其参照功能是某种创新。如奈瓦尔和邓南遮作品中阿多尼斯之死对基督受难的参照作用。这个分类说明创作者使这则神话得到丰富,也使其向现实社会靠近,同时其传统意义也有逐渐被弱化的倾向。原因在于:一味重述该神话的传统样式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该神话虽包含很多联想,但读者若事先掌握了其中的大多数意义,创作者则被迫另辟蹊径,发现或重构其象征功能。此时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该神话本身,而是其与当代社会或与某种思想的关系,且越出乎意料的关系越能引起读者的兴趣。神话不断重现的过程其实就是创作者不断创造新关联的过程。
第三,弗莱(Northrop Frye)认为文学表现有两极,即从神话到现实主义,“在这两极之间是传奇”。神话通过“隐喻”手法用“神的……超人性”表现“人类欲望”,但逐渐高涨的“理性思维”迫使“神话趋于消亡,但变形为文学而继续存在”。传奇“是从虚构过渡到写实的整个文学过程”,“神被置换成了人”(转引自叶舒宪,2012:13)。我们应该在弗莱的看法之上更进一步。笔者认为《阿多尼斯研究》显示该神话的书写方式经历了从神话、传奇到现实主义又转向神话的过程。以下分两个阶段来说明。
在第一个阶段,个人想象的历史以及人类社会文化的演变过程的融合导致创作者对该神话的重述经历了从纯粹神话到现实主义的演变过程。每部阿多尼斯作品必须使该神话变形才能符合时代的审美标准和道德风尚,以迎合读者的趣味。这个过程中原始欲望遭到压制,理性思维逐渐突出,所以阿多尼斯人物的神性逐渐变弱,写实色彩渐浓。笔者认为在阿多尼斯神话的发展过程中,表现这则神话神性消失最典型的例证是莎士比亚的阿多尼斯作品,其中的人物形象与原始版本有相当距离。按照蒂泽的话说,莎士比亚笔下的阿多尼斯故事“所有神圣的感受都消失了”(Tuzet,1987:145)。总结蒂泽的分析可知:莎士比亚作品中的阿多尼斯是“英国式的可爱男孩,内向、喜爱运动和狩猎”,死后未复活;维纳斯“不知羞耻”“懦弱”,无休止地想要征服阿多尼斯;阿多尼斯是她的“猎物”,她自己是“情欲的猎物”;甚至之前象征邪恶、作为地狱使者的野猪都变成了一只“肥胖的猎物”,更“没有受到诸神嫉妒心理的煽动”。另外莎士比亚还删除了阿多尼斯从没药树中出生、在二女神之间分割时间以及人间和地狱对比等神话性质的情节;这首戏剧诗表现的是那个时代的某种“宿命论”观念和对于爱情的“悲观情绪”(Tuzet,1987:145-151)。人物的神性消失,神已被置换成人。至此阿多尼斯故事获得最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叙述方式。弗莱认为在神话和现实主义之间还有传奇这个阶段。笔者认为纯粹的阿多尼斯传奇并未出现,只有马里诺和拉封丹的阿多尼斯作品中有传奇的成分。根据蒂泽(Tuzet,1987:172)所说,马里诺作品是一种“神话、田园诗、骑士、科学启蒙情节”的“混杂”体;拉封丹的作品传奇色彩更鲜明,作者将阿多尼斯神话“去神圣化”,突出描写了阿多尼斯“高贵而勇敢”的形象,拉封丹称自己的作品为“田园诗”,但他也“借鉴了前人的史诗作品”(Tuzet,1987:208-211)。
在第二个阶段,笔者发现阿多尼斯故事又还原了神话色彩。总结蒂泽研究的十九世纪中后期至二十世纪初阿多尼斯作品的特点就能说明该神话如何在文学中重拾神性:(一)作家笔下的阿多尼斯成为多神教的核心人物;(二)“神婚”受到普遍关注,大女神兼具母亲、情人、保护者的身份;(三)阿多尼斯重生而成为战胜死亡的神,或不返回人间,反映的是“原始人对太阳死亡的焦虑”;(四)作者混同阿多尼斯与基督,以此颂扬基督教的智慧及其“规范来自神秘现象的盲目力量的能力”;(五)作者们继承或重构古希腊以来的阿多尼斯祭仪,比如参照“圣星期五”的庆祝仪式,描写阿多尼斯出生时的“圣子”形象、信众向阿多尼斯——基督的伤口致敬的场面、自我鞭笞——来源于基督教的实践活动等;(六)野猪变成了天相(Tuzet,1987:220-243)。此时的阿多尼斯是东方的,不是希腊的,但并非纯粹的原始神话,而是宗教气氛浓重的神话。蒂泽(Tuzet,1987:217)认为这种变化有三个原因:“天启论运动(illuminisme)”、十九世纪初神话研究的创新以及受到学者们普遍关注的“起源”和“统一性”等人类学概念。如上文所言,这些作品的显著特征就是阿多尼斯故事的某些情节被重新阐释,并起主要参照功能,比如阿多尼斯的鲜血。阿多尼斯祭仪不再是古希腊样式,阿多尼斯不再是年轻的凡人,而是“自然的力量”,拥有受难的“神的荣耀”(太阳神祗)。作者们对阿多尼斯—自然神—基督的激情来源于犹太-基督教关于痛苦能够救赎和净化的观念或曰“痛苦有益论”(Tuzet,1987:218-219)。这些作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十九至二十世纪初欧洲学界或文坛的某种新风尚。
蒂泽将个体文本纳入一个体系中,用巴赫金的对话或复调理论来理解,即“一系列孤立的”作品的对话关系构成了文学的“体系”(贝西埃:2010,569-570)。蒂泽不创造个体文本,但是创造了意义。按照巴赫金的启示:个体结成的统一体的意义大于个体之和。以阿多尼斯为中心的统一体的价值应有多种体现,如该神话原型功能的生成、该神话发展过程的揭示以及文学发展趋势的揭示等。这反映了蒂泽的诗学观:在系列作品中研究同一题材有利于为文学史构建某种体系。研究者从多样文本的复杂性中总结出整体性,这是原型、题材以及意象等批评方法的基本理念,并且与巴赫金的“历史诗学”(贝西埃,2010:570)、阐释学以及接受美学的心理一致,即“一心想把种种分离的感觉整合为可以理解的整体”(伊格尔顿,2017:79)。
结 语
以上分析旨在借助原型概念阐明蒂泽的研究所呈现的体系性效果。阿多尼斯神话是面向所有人的预设。学者和诗人都参与该神话原型功能的构建,但他们不是这种构建的意识自觉者。蒂泽使该神话作为原型的功能得到彰显。有学者反对过于文学性的神话观,但以上分析说明:学者和诗人使该神话成为贯通多领域的复合文化概念。神话的发展和传承有赖于文学,文学通过神话而获得叙述对象、模式或参照;一则神话的发展还映射了文学发展的规律。文学史是否存在统一体?蒂泽暗示:构建统一体有其现实性和价值。蒂泽对阿多尼斯神话及宇宙意象的研究都表达了这种文学研究理念。有学者认为设定统一体有决定论的嫌疑,对此笔者认为蒂泽有一种未言明的回应:在阿多尼斯神话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原有版本存在可发挥的空间,所以产生了众多文本;各文本之间的关系或紧密或松散;统一体的形成受到个体文本的制约,而各文本又受制于多种必然及偶然因素;即使抽绎出统一体,也无法决定未来同题材作品的创作,因为人类的想象力是不可预知的;因此不应夸大原型和由此产生的统一体的决定性作用。蒂泽既承认个体的复杂性,也相信统一体的必要性。总之,构建某种统一体可以促成对文学史的有效认识。
注释:
①埃莱娜·蒂泽(1902-1988):法国现代文论家及文学批评家,客体意象批评代表学者之一,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其著作除《阿多尼斯的死亡与复活:一则神话的发展史研究》(MortetRésurrectiond’Adonis:étudesdel’évolutiond’unMyth)外,还有《浪漫主义时期西西里的法国旅行者》(VoyageursFrançaisenSicileauTempsduRomantisme,1945)及《宇宙与意象》(LeCosmosetl’Imagination,196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