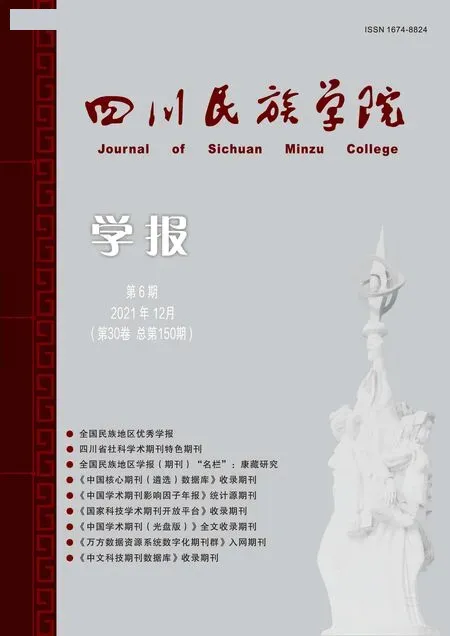栖居的形式
——当代锡伯族诗歌的空间诗学观照
崔 悦
(伊犁师范大学,新疆 伊犁 835000)
早在十八世纪,莱辛的《拉奥孔》就对诗与画进行了比较,并认为“时间上先后承续属于诗人的领域,而空间则属于画家的领域。”[1]然而,随着约瑟夫·弗兰克《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一文的发表,文学中的空间形式问题得到越来越多批评家的重视,并引发了批评理论的“空间转向”。尽管弗兰克分析的是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问题,但在他的论述中隐含着一个前提,那就是现代诗歌能够捕捉“纯粹时间”的瞬间体验,表现出了“空间形式上的努力”[2]4。在他看来,“‘纯粹时间’根本就不是时间——它是瞬间的感觉,也就是说,它是空间。”[2]15当诗人将瞬间体验凝聚笔端,种种意象便汇聚在有限的时间范围之内,并在诸种联系中构成了一个全新的整体空间,如空间哲学家爱德华·索娅所说,是“艺术家和诗人纯创造性想象的空间”[3]。
诗歌是锡伯族作家于文学创作中起步最早且发展相对成熟的文学样式。锡伯族分居东北和西北的独特地理空间、在驻防屯田中形成的社会空间、多民族交往交融的文化空间,共同形塑了锡伯族作家的审美理想,使当代锡伯族诗歌形成了独特的“幸福空间”(巴什拉语)意象:牛录、山河、国家。在上述空间意象的相互参照中,当代锡伯族诗歌构造了一个美好的精神家园,使其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普遍关注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矛盾与焦虑的大潮流下,保留了难能可贵的单纯与执着,为身处现代性焦虑之中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安稳的心灵栖居地。
一、安放身心的“地方”——牛录
“地方”是与“空间”相联系的一个概念。在海德格尔看来,地方是人类栖居、归属、守护的世界。[4]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中指出,地方是时间堆积出来的空间,它能够固定住人们共同的经验和绵延的时间,因而拥有将人们维系在一起的过去和未来。[5]为此,段义孚认为“地方展现的是一种稳定性和永远性的形象。”[6]22当我们对空间感到熟悉,并在那里获得深刻的体验时,空间就变成了地方。与空间相比,地方是“存放着美好回忆和辉煌成就的档案馆”[6]126,更让人感到安稳和依恋。“牛录”是当代锡伯族诗歌中的一个代表性地方意象,处于锡伯族沉淀下来的价值观中心,承载着族群记忆和动人的诗意。
牛录亦作牛鹿,意为“箭、大箭”,满洲八旗军政组织的基本单位。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锡伯人全部被编入满洲八旗,分属于各牛录。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清政府派遣锡伯族军卒“防御10员、骁骑校10员、兵1000名,携其家眷3275人”[7]前往新疆伊犁驻防屯田。此次大西迁成为锡伯族历史上的一次壮举。西迁以后的锡伯族官兵迁往伊犁河之南(今新疆伊犁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并组建了锡伯营。至此,锡伯族有了自己的牛录。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牛录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1938年,锡伯营在历史上消亡,牛录随之成为“乡”一级的行政单位,有了故乡的新内涵。由此可见,牛录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也是锡伯族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
牛录是锡伯人生活的地方,有温度、有气息,让人感到亲切。“牛录想起来很温暖/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在老高老高的坡上/随便望望/而牛录就在这儿/在满是草木气味的地方……”[8]279(阿苏《牛录》)当牛录从生活空间化为诗意空间,它就成为一个会说话的存在者和承载了伟大历史感的审美意象,为当代锡伯族诗人提供了一个想象的庇护所。在那里,诗人可以与远古的民谣相伴,卸下所有的疲惫与空阔,获得归家的幸福感。牛录于是成为一个“地方”,石头、阳光、芨芨草和亲人们……共同构筑了一个整体空间,万物如其所是地伸张着自己,人们也在这里舒适自在地生活,“二三声犬吠/自柳条篱笆后而袭/使整个村庄生动起来/这时候,亲人们脚步飞驰/走进与酒有关的好日子……”[8]274(阿苏《堆齐牛录》)然而,这只是当代锡伯族诗人记忆里的牛录,是梦境和回忆的融合,它保存着过往岁月的美好,带给人温暖和幸福感,是超出了地理空间界限的牛录的意象。因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锡伯族原生态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对此,顾伟在诗中写道:“族兄是厌倦/独家独院的自给生活/向往白皙的手和脸”,而“失去杂草相陪的庄稼/是寂寞的单纯的/正如头痛与土地”[8]294。面对锡伯族传统生活方式消逝的危机,当代锡伯族诗人流露出对牛录生活的强烈渴望,阿苏想象着“八个吉祥的牛录啊/于炊烟之上/盛开花朵的芳香/辛劳的人们脚步缓慢/一路向晚/踏响了母语的歌谣”(阿苏《花朵开遍牛录》)。因为牛录作为新疆锡伯族世代生活的地方,留存了丰富的锡伯族传统文化印记,守望牛录就是守望锡伯人的精神家园。
牛录不仅是锡伯族人存在的敞开场所,也是勾连锡伯族当下生存与历史记忆的一个中介。牛录原本只是一个军政组织的基本单位,直至西迁的锡伯族军民在伊犁河南岸建立了自己的牛录以后,才逐渐有了家园的内涵,并成为让人怀念的地方。因此,锡伯族的大西迁是牛录的内涵发生变化的历史节点,也是锡伯族诗人一想起牛录就会忆起的族群历史。正如诗人阿苏所写:“堆齐牛录是个吉祥的牛录/在古朴而神圣的母语里/咀嚼着沉重的岁月/坐守在这里/是谁的目光让我的灵魂/疼痛九万次”[8]275。诗人每每想到祖先的西迁壮举都会无比疼痛,因为那是一段充满了艰辛的旅程,蒙古高原的寒气侵袭、杭爱山的暴雨冲刷、温都尔汗的戈壁、克鲁伦上的飞沙走石……无不威胁着西迁的锡伯族军民。而西迁以后开辟新家园也是一段艰辛的历史,他们在“准噶尔人的废墟里艰苦创业,一手拿着弓箭枪矛守卡伦保边关。一手拿着铁锨斧头修大渠开荒地,为西陲边界的安宁洒热血流大汗!”[8]247经过多年的不懈奋斗,牛录终于被建设成为富饶美丽的幸福家园,那场锡伯族历史上的“大西迁”也永远留存在锡伯人的记忆中,积淀为牛录这个意象世界苍凉的底色。牛录因此成为一个既包含漂泊感又给人安稳感的当代锡伯族文学的经典意象,体现出包容历史和现代双重阐释空间的特点。
二、民族精神之寄托——山河
如果说牛录是当代锡伯族诗人安放心灵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的创造则需要可见性的“物”——山河来实现。正是有吸引诗人注意力的“物”,诗人才会凝望并赞美“地方”,而这些“物”在进入诗人感知世界的同时,也创造了它们自己的空间。在我国,锡伯族主体人群大多偏居边地,尽管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过程使地方经验受限,但是以立足本土、依托族群经验为主进行创作的锡伯族当代作家,依然通过田园牧歌式的抒情笔调抵抗着现代社会带给人的生存焦虑,探索着西部边地人的精神出路,并呈现出以“物”为中介设置空间,进行空间叙事和抒情的特点。因此,对族群空间内特定的“物”——地理景观的书写,成为当代锡伯族诗人观照生活、思考历史、寻找精神家园的主要方式,与此同时,“物”也在诗中道说存在,并成为“可栖居之物”[9]。
新疆锡伯族主要生活在伊犁河南岸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那里南有乌孙山,北有伊犁河,加之浇灌万亩粮田的察布查尔大渠,共同组成了锡伯族人生活的自然地理空间,使得当代锡伯族诗歌融自然山川、人文历史于一体,体现出独特的地域风情和民族精神。
乌孙山介于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与特克斯县、昭苏县之间,绵延百余公里。早在2000多年前,乌孙部落西迁伊犁河谷,据说乌孙山以此得名。[10]当诗人把作为“物”的乌孙山“从单纯的对象性中拯救出来……让物能够在整体牵引的最宽广之轨道范围内居于自身之中”[11],乌孙山就化为言说的存在者,一个诗意的空间意象。在阿吉·肖昌笔下,“走过漫长岁月的乌孙山/离阳光很近了/但飓风始终在那里/与生灵挑战……一位神在贫瘠的原野上/痴迷地追赶太阳/瘦骨嶙峋的马/在悲凉的戈壁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8]287。在诗人眼中,雄伟挺拔的乌孙山是家园的屏障,尽管历尽沧桑依然至坚至韧。历史的纷争已经在乌孙山落下帷幕,“铁蹄早已被阳光的/汗水淹没”[8]287,然而在新时代“追赶太阳”的路途中,战马流干了鲜血,最终被掩埋于乌孙山沉积的残雪中,乌孙山却依然挺立,静默地看着世事变化。与此同时,“大地上飓风在逍遥/守望岁月的伊犁河/犹如一位失去母亲的婴孩/在悲凄而黑暗的酒坛中哭泣……伊犁河幽幽的眼睛里/流露出人间无尽的忧伤”。[8]288这滚滚不息的伊犁河与乌孙山一起记录了西域锡伯人的悲怆奋斗史。西迁之后来到新疆伊犁的锡伯族军民,仅靠伊犁河南岸原著居民留存的万余亩土地根本无法满足口粮需要。为了生计,他们只有另行开渠,扩大耕地面积,发展农业生产。面对严峻的现实问题,锡伯营总管图伯特带领锡伯族军民努力寻找生存之路,在实地考察和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提出开挖大渠引伊犁河水的主张。于是,锡伯族军民“挥舞铁锹/把血汗在身上流尽/营造了叫作察布查尔的东西/这脉活命的水呵”[8]280察布查尔大渠为驻守边疆的锡伯族人带来了生机和希望,“金黄的麦穗酒醉似的/羞得抬不起头来/喘着粗气的黑牛/不知磨破了多少个铁掌/鼓起肚皮的粮仓”[8]290。这个锡伯族西迁的驻防地成了真正的金色粮仓,也成为锡伯人守望的故乡。
段义孚曾在《文化地理学》中提出“宽敞的形象”这一观点,他认为“宽敞与实现自由的感觉密切相关。自由意味着空间,意味着有力量和足够的地方去活动。”[6]42“无论是森林覆盖的山峦还是绿草如茵的平原,它们是否能够树立起宽敞的形象都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历史经验的类型。”[6]4618世纪的锡伯族大西迁让三千多锡伯族军民离开熟悉的家园来到西域荒芜之地,他们不仅要改变渔猎、畜牧的生产生活方式转而发展农业,更要适应和改造新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实现自由的生存。在此过程中,乌孙山、伊犁河、察布查尔大渠成为历史经验中锡伯人顽强生存意志的投射地和族群奋斗的见证者,承载了锡伯人坚韧不拔、苍凉悲壮的民族精神,并成为当代锡伯族诗歌中“宽敞的形象”。
三、 民族认同之归属——国家
锡伯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既古老又年轻的一个民族。作为“想象共同体”的现代意义上的锡伯族大约在明朝末年才正式生成,但从“鲜卑说”这一族源角度来看,锡伯族生成的历史纵深性又让它可以被称为一个古老的民族。[7]100然而,无论是古老还是年轻,锡伯族都是一个坚定拥护国家政权和祖国统一的民族,并为维护祖国边疆的安定做出了贡献。无论是在驻守新疆边防的任务中,还是在反抗沙俄侵略保家卫国的斗争中,锡伯族的民族命运始终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锡伯族的历史经验也与国家空间的建构和维护紧密相连。
国家空间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空间,新中国的建立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也构建了一个独立的政治权力空间——国家空间。尽管文学想象空间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深受诗教传统影响的锡伯族作家文学从产生之日起就体现出浓厚的爱国主义色彩,反映了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特点,具有极强的功利性。《离乡曲》(锡笔臣著)、《来自辉番卡伦的信》(文克津著)和纪念凿渠功臣图伯特的三篇纪念文章是清代后期至民国初年的锡伯族文学代表作,这些作品运用空间叙事的手法生动再现了锡伯族历史上的西迁、换防、凿渠等大事件,讴歌了远离故土的锡伯族人坚强的生活意志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视阈下,锡伯族诗人则以独特的空间意象——自然风景,来表达对现代民主国家的认同。
自然风景作为当代锡伯族诗人政治抒情的主体意象,是被想象的风景,不仅承载着诗人的民族国家想象,也成为显现诗人对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符号。因此,在锡伯族当代诗歌中,自然风景的书写与国家形象的构筑相互蕴含,诗中所表达的也不单纯是对自然形式本身的赞美之情,还饱含着锡伯族对民族国家的深切认同感,彰显了国家建设边疆的成就。例如,锡伯族著名诗人郭基南在《我要弹奏》中写道:“看啊!冰雪消融山林翠,河水荡漾碧波生,春天啊正把生机撒向祖国的四面八方!”[8]179这是一首唱给新中国的颂歌,通过充满活力的自然山水的变化表达了诗人内心的喜悦之情。这种爱国的诚挚之情在很多当代锡伯族诗人的作品中都有体现。顾尔佳·忠浩的《心声》起笔就将喷薄的爱国情感与自然景观相结合,“像涌流的泉水,似喷射的火花,我们热爱祖国的情怀,美丽而荣光,纯洁而忠诚。”[8]230在诗人富伦太的笔下,祖国是高山“在暴风中坚固,在骤雨中绿化。”[8]238祖国是路,“今天是疾行路,今天的路是引向科学的路;改革的风融化积冰,改革之路通向知识的海洋。”[8]244当代锡伯族诗人沿袭着祖先的爱国意志,对国家充满热爱和强烈的归属感,并在自然物象上投射了对国家的想象性建构,表达了一种“深沉的依恋之情”[12]。
当代锡伯族诗人对国家的认同还通过赞颂祖国的壮丽景观和锡伯族对神圣国土的守护加以表达。正如诗人佘吐肯在献给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成立50周年的诗歌中所写:“这是一片神圣不可侵犯的疆域,是祖国西陲富饶美丽的锦绣河山,尽管是野猪狐兔出没的无垠荒地,那只贪婪的北极熊早已虎视眈眈,国土如何守卫人民何以安居乐业?”[8]246面对列强的侵犯与国家安危,锡伯族人置族群安危于不顾,战胜艰难险阻西迁至祖国的西北边陲,奋勇抵抗外敌入侵,将国家的利益置于族群利益之上,表现出强烈的国家荣誉感和认同感。因此,在全球化语境下,面对现代化转型的冲击,当代锡伯族诗人往往求助于祖先的丰功伟绩来建构一种身份标识,从而获得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为此诗人阿苏不无悲伤地写道:“最后的牛车走在落日的边缘/辙印深刻/辚辚之声如祖先的泪光/直抵我的内心//漫长的岁月背后/牛车飘摇/孤独且忧郁/我穿过时间的河流/以诗歌的方式,同牛车接近”。在这里,“牛车”是落寞的锡伯族传统文化的象征,尽管这辆“牛车”曾经满载着族群悲壮西行的荣耀,但在现代化的狂风中却飘摇如茅草,充满了英雄末路的悲凉。但是锡伯人永远忠于祖国,就像诗人西榆写的:“一个早在乾隆时代,就冲破千难万险西迁到伊犁/牢牢守卫着祖国西北边陲的锡伯人,难道还有什么过不去的沟沟坎坎?……我的血脉里,就永远流淌忠于祖国的鲜血!”[8]260
“栖居”是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重要命题,“栖居乃是终有一死的人在大地上存在的方式。”[4]156因此,“栖居”与空间和物有着重要的关联。栖居的观念本身就包含着对空间有限性的确认和人与其逗留的大地之间物的关联。当代少数民族诗人“普遍以一种‘内置的物像视点’转向对族群空间内的物种气候、风俗仪式、空间区位、地理景观等的书写,在物的切面甚或背面建构起诗歌的精神世界,甚至已然升华为某种精神原型,成为他们观照生活和思考未来的坚实根基”[13],在这一“物的转向”的背景下,当代锡伯族诗人通过一系列聚合了族群情感和对国家高度认同感的物象,建构了一个诗意的栖居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