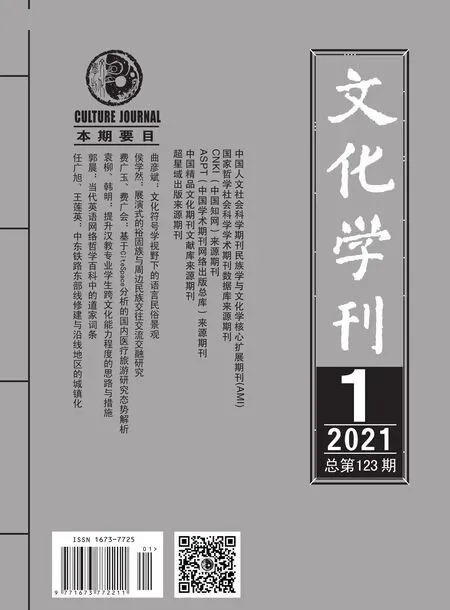顽童的山花野草
——王勇英儿童小说《弄泥小时候》分析
周梅芬
《弄泥小时候》是王勇英的一部儿童乡村小说,讲述了小女孩弄泥的成长记:从只会爬的“弄泥蛇”到自由奔跑,在山花野草中踏遍每一寸泥土,用心体验着童年的点滴。王勇英细腻、淳朴的语言,清澈的文字,充满了客家风情的描述,犹如一条潺潺的小溪,流进儿童文学文坛,摒弃热闹和喧嚣,带来宁静与清澈。正因如此,《弄泥小时候》在喧嚣的文坛上才显得如此可贵。
一、童趣的语言
童庆炳先生在《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一文中认为:“几乎每一个伟大的作家都把自己的童年经验看成是巨大而珍贵的馈赠,看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的源泉。”童年经验作为一种先在性意向结构,对创作主体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因为“对作家而言,所谓先在性意向结构,就是他创作前的意向性准备,也可理解为他写作的心理定式。根据心理学的研究,人的先在性意向结构从儿童时期就开始建立。整个童年的经验是其先在性意向结构的奠基物”[1]。童年经验会给作家的灵魂带来不可磨灭的影响,渗透到作家创作的每一个阶段的文字中。王勇英曾说过:“这是我的童年足迹,写我在广西博白县东平镇大车乡村度过的童年时期最纯真、美好的回忆。”[2]作者以自己的家乡为背景,以自己的童年为故事原型展开叙事,散发着浓郁艾草香味的南国风情,就如曹文轩笔下的苏北水乡,沈从文笔下的凤凰小镇,独具特色。
小说童趣十足,作者依靠自己的童年经验及回忆性叙事,辅以客家方言,小说便有了山花野草般的质感,真诚、充满想象。地域色彩浓郁的人名地名,如弄泥、瓜飞、风尾、天骨、乳渣、亚蛇、沙蛭、牛骨田、灯盏窝、秧地洞、马脚楼等,简单朴素,诸如“话多过米”“可它们很鬼”等句子俯仰可拾。作者对壮族语言系统十分熟悉,运用起来得心应手,或将壮话直译,阅读时新鲜感和陌生感并存,展示出壮族语言文化的独特魅力,给读者以唐代宋之问《经梧州》中所说“南国无霜霰,连年见物华”的惊喜。
语言对情节画面感的营造和典型场景的刻画功不可没。小说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有一天我问妈妈:“外公的胡须为什么不能摸?他又不是社王神。”
妈妈说:“摸外公的胡子就是对外公的不尊重。”
我又问:“可是我见外公总是摸他自己的胡须。他自己为什么不尊重自己?”
妈妈顿了一下:“自己的胡须自己是可以摸的。”
我明白了,各人的胡须各人摸。
“唉,以后我只能摸我自己长的胡须了。”我有点难过地摸摸自己的下巴。
弄泥做梦都想要摸一把外公的胡子,她觉得“外公的头发不是脱了,有可能是长到嘴巴周围来了”。天真的弄泥本身就是童趣的代表,她机灵随意,打破砂锅问到底,直击事物的本质,让人无法反驳。
弄泥对秧地洞这个地方很好奇,妈妈说“远天远地的”,奶奶说“别去哟,路远得能走断脚”,但她一个红薯没吃完,十六哥已经跑了一个来回。“有时候远有时候近,有些人行断脚也没到,有些人去了又回脚也没断。”作者善于使用壮族方言并将其口语化,简单幽默,这是她小说的标识。二哥吓唬弄泥“泥巴把你吞了”,下田后弄泥反驳“泥没有把我吃到肚子里”,语言充满幻想,日常简单的对话妙趣横生,调皮勇敢的弄泥被刻画得栩栩如生。“我的脚挨到湿湿的泥田了,田水被太阳晒得有点烫,可是当脚板没入泥土下面时就感觉凉凉的,就像用脚吃冰棍一样。”这种体验式的语言需要有对生活足够的热爱和丰富的生活经验。作者对自己的童年有细致入微的体会,才能用饱含深情的笔调去描述,将平凡的童年生活写得五彩缤纷,充满童趣。当“我”把二哥的书剪满窟窿,被二哥理直气壮地打哭后,“我哭着回去找奶奶。奶奶和姑姑一起责骂二哥。爷爷回来了,我再哭一次,爷爷责骂二哥。爸爸回来了,我再哭一次,爸爸也责骂二哥。傍晚,妈妈从田里收工回来了,我再哭一次,妈妈也责骂二哥”。简短几个句子,赖皮的弄泥呼之欲出。
小说以短句为主,很多段落只有一个短句或词语。语言组合上以简单对话为主,心理活动为辅,这种留白的形式为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便于他们参与到文本中,体会语言故事的趣味。这种叙述故事的形式与儿童读者的接受能力和心理特征相契合,富有童趣。当作者为自己的创作寻找到一个独特的意象和文化支点之后,其文学赋写也能贴切而自然地跟上节奏,带着泥土气息的语体特色即是王勇英的辨识度所在。朱自强认为:儿童文学是一种“朴素”的文学,是一种“简化”的艺术形式,只有将儿童认识生活和世界的方式进行最大化的“简化”,文学才能够更鲜明、更清晰、更准确地逼近事物和生活的本质。用最朴素的表达,讲述最有趣的故事,这就是王勇英的选择,与朱自强的观点不谋而合,她将自己的童年经验化入语言,展现出语言美学维度中的童趣特点。
二、独特的文化
小说用童趣的语言将读者带入充满神巫色彩的故事,除去对钟灵毓秀家乡的描画,作者对朴素的内在人性力量的凸显,对壮族民俗文化的描绘也非常精彩。王勇英对故乡的眷恋和欣赏,对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刻的文化认同,都在描写弄泥小时候的字里行间流露出来。从热闹的“校园小说”转型到“乡土小说”,寻找到文化支点之后,王勇英激发了对乡土文化的想象力。成年文学需要乡土书写,儿童文学更需要在对乡土的书写中传承传统文化。自我童年资源是推动儿童文学的第一动力,文化自觉之后,作家需要从文化、人文印迹中挖掘写作素材,建构自己的文学世界。对如何重新赋予民族文化、乡土文化鲜活的生命力,使之成为乡土童年书写弥足珍贵的资源这一问题,王勇英积极尝试,而《弄泥小时候》便是一次大胆的、效果显著的尝试。
广西壮族有烧艾的传统,目的是驱除热毒瘟邪,保佑一年平安,是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神秘风俗,王勇英在小说中提到:年三十最让牛骨田的小孩害怕的是要被“烧火”,即烧艾。主持烧艾的是个穿着一身黑色麻布衣服,头发很白的老太婆,叫“巴澎”。虽然爸爸说这是民间医术,相当于针灸,能治病,但是弄泥觉得“在大人眼里,我们还小的时候好像满身都有病,每年都要烧火好几次”“大人们说,小孩子就要常常被巴澎用艾草烧一烧才能健康地长大”。在她眼里,烧艾是可怕的“烧人”,“大人好像是随心所欲地想烧我们就烧我们”。这种天真稚气,令人捧腹。在轻松、缓慢的叙事中,王勇英将客家的风土人情,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独特的人文传统缓缓道来,在氤氲文字里传递的人生滋味让人怦然心动。客家方言本身已构成了作者所要表现的乡土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作者再将客家文化的神巫色彩和大自然的神秘感有机结合起来,让读者在阅读的同时,不仅能领略到客家文化的原生性,还能感受到人情的淳朴与真诚。
作者脉脉含情地叙述着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小事:“我们村有个风俗,从外地工作回来的男子和嫁到远方几年才回来一趟走亲戚的女子,只要生活稍富裕,但凡回村都会带很多糖果或饼干、爆米花,全村挨家发给孩子们吃,讨吉利。”世外桃源般淳朴而厚重的风土人情描写,让人心生向往,团聚的时刻,乡亲聚在阿莲家聊着天,孩子们的心思却放在一堆吃食上。这是一个大同世界,处处凝结着人性之善的果实,沁人心脾。对于绝大多数的儿童读者而言,这是一次不可多得的带着“异域”风情的文化体验,领略和城市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去那片屋三哥家,她阿妈做甜酒糟,今天开一缸让人尝。”三妞站在上高屋巷口的一堵旧城墙下大声宣布消息。在村民朴素的观念中,好的东西是要大家一起品尝的,那一缸香香甜甜的酒糟勾引着村里小孩子们的馋虫,也牵住了读者的胃。“她奶奶坐在禾秆墩上,用一种浆果制成的汁液把小鸡的头顶绒毛染红,这样方便在村里的鸡群里认出自己的鸡。”这种静谧、和平、与世无争的客家乡村,在王勇英笔下慢慢勾勒。客家人希望女孩子聪明能干,奶奶给弄泥和小女伴们穿上了耳洞之后说:“你已经穿了耳洞,也戴上草耳环了,这还并不能做好新娘。当新娘还要学会做针线,安纽扣,锁扣眼,缝缝补补,做衣衫,补袜子。还要学会做各种帽子,老人的暖冬帽,月婆坐月子时戴的防风帽,小孩儿的夏凉帽、秋风帽、冬暖帽。”儿童视角的使用,将这些独特的客家风俗用质朴又充满趣味性的语言表述出来,让读者对壮族的乡土风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而愿意去了解一个淳朴的乡村世界,一种传承着淳朴、厚重又充满诗意的民俗文化。
不同的地域文化赋予作家不同的气质和个性,同时也成为他们创作时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故乡赋予王勇英勇敢、淳朴和自信,驱使她以熟悉的南方地域文化为背景,挖掘深埋内心的童年个人经验,以富有童趣的语言创造出一个怡然自得的小村庄——一座仿佛尚在人间却又游离世外的小桃源。这是一个作者童年回忆中的小村庄,又是一个在书写中被重新激活的小村庄,这个小村庄具有独特的文化气质,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假如没有王勇英的叙述,这座小村庄将会一直以不为人知的姿态存在下去。
文化的活力来自它的多样性和独特性。生活在都市的孩子也许很难体会到王勇英笔下的乡村美景、弄泥们的童年趣味、村民的淳朴自然、温暖的人情世故,但是作者尝试用她的笔去搭建一个可以在客家文化和当下儿童阅读接受之间,在自己的童年生活和当下儿童生活之间沟通对话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达到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之间,一种文化和另一种文化之间的理解与容纳。
三、诗意的童年生活
在电子产品充斥着现代孩子童年生活的当下,阅读《弄泥小时候》就成为一种难得的人生体验,这里有奔跑于山花野草间的欢乐童年,有对外在世界的好奇和对未来的向往。小说的儿童视角有独特的亲和力,传递着弄泥对生活、对成长和对世界的理解。
王勇英在作品中将一个孩子充满乡野气息的生活一一展现:三岁的弄泥还像蛇一样在地上溜,因此被称为“弄泥蛇”,但她一站起来就像风一样,再也无法停留,在山野间疯跑,“会走路后的我好像要把以前错过的路都补回来,拼命地走呀走,像小野牛那样东奔西跑,还经常撞人撞树又撞墙”;误将“豆娘”认为是黄豆、黑豆、绿豆、豆芽它们的娘,惹得大姐笑得肚子疼;村里的奶奶们天天给孩子讲老虎外婆的故事,到最后大家都怀疑自己的奶奶是老虎外婆并去寻找证据,奶奶们从此再不讲老虎外婆;小伙伴们“一手抱着一碗粥,一手拿着一个红薯。我还看见他们的粥里插着一把铜勺子。他们每天中午都这样结伴到门楼去,排排坐在门楼前的砖阶上吃”;因为“青蛙一叫就跺跺脚”,我们在田间玩到了深夜;弄泥拿爷爷冬天要穿的布袋袜子去摸田螺,因此她也拥有了一双红色花布做的布袋袜子,只是这布袋袜子略微有些尴尬,“穿了布袋袜子后,就套不上布鞋了,袜子太厚,鞋子就变小了。我只好去穿二姐的鞋子,却又太宽,不稳。最后我只能穿着布袋袜子套着木屐”,当大人笑着问是冷还是热时,弄泥机智地以“不冷也不热”来回答;弄泥的乳牙弄丢了悄悄哭,善良的爷爷告诉她老鼠把乳牙叼屋顶上去了,每个村都有一只老鼠专门负责给粗心的孩子捡牙齿;为了在头上理一只蜻蜓形状,专门跑去淋屋檐水,期待着长狗头疙瘩,结果却因疙瘩太严重理了光头。每天可以“擦火花”“拼秆蛇”“数青蛙”的多彩童年,充满着欢声笑语。这些欢乐的故事可能有人经历过,但经历过这些故事的人已将童年遗忘;有些人从来没有经历过,童年不在乡村的人也许还不知道童年在乡村的人会有那么奇怪有趣的故事。
《弄泥小时候》是一部儿童乡村小说,一幅民俗风情图,更是一部儿童成长史。弄泥想学哥哥钓鱼,却不小心钓到了三婆家的小公鸡。爸爸用镊子把鱼钩取出来,给它上药,“我们要把小公鸡嘴里的伤治好了再还给她。如果治不好,就由三婆到我家任挑一只鸡来抵换”。鸡是村民的重要财产,弄泥却没有被粗暴责骂,“爸爸说这只小公鸡是我钓伤了的,我应该对它负责,看好它”。弄泥细心地照顾着这只小公鸡,甚至将一根树枝放鸡嘴里用纱布缠稳,免得它乱吃东西感染伤口。这种责任心以一种喜剧的方式呈现出来,虏获了小公鸡的“芳心”。在村野田间长大的孩子,还有着对大自然的尊重和感悟:
三妞和风尾被我的惊叫声吓了一跳,停在她们头发上和肩膀上的蜻蜓们纷纷飞走了。这时我看到也有几只蜻蜓从我的头顶飞散开来。原来也有蜻蜓停在我的头上和肩膀上!我们虽然一只蜻蜓都没捉到,但都觉得好开心,因为有很多蜻蜓曾停在我们身上。
随着王勇英的忆态叙事,这种诗意般的童年生存状态被还原。朴素的生活场景,真实生动的生命面貌,犹如一幅乡村画卷在延展,有一种别致的美。
四、结语
当我们站在童年和儿童成长的立场来思考现代生活时,童年已经给出了答案——单纯的文化风景的描写和文化现实的单向批判并不可取。当我们有了和乡间孩童一起奔跑的勇气,记录生存和成长的瞬间后,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是这个孩子在童年时代眼睛里装进的风景、风俗、文化在他现在、未来发展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种朝向“此刻”与“未来”的关照和远眺,才能让我们超越抽象观念的束缚,脚踏童年最踏实的土地。这才是诗意童年美好状态的意义所在,小说的童年生活才如此璀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