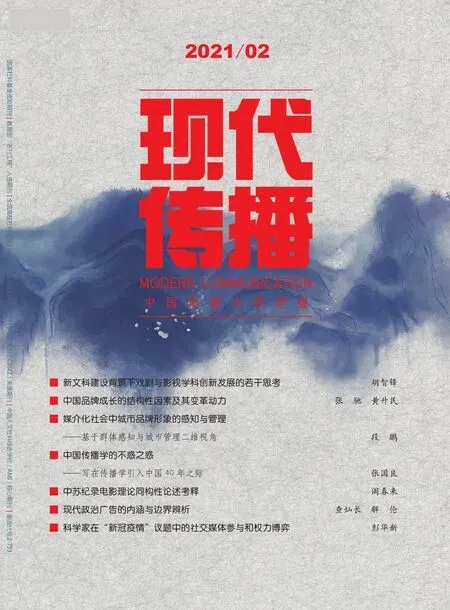再现、互构、生产:中国都市电影中的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
■ 黄 珞 李明德
一、问题的提出:作为理论与实践的女性主义
长久以来,无论在物质生产、社会生活还是文化语境中,男性都是秩序与话语的中心,被观看、被支配、被定义成为了女性的既定命运。自启蒙运动开始,“人”的价值被重新评估,被视为“第二性”的女人们开始觉醒,性别问题也逐渐浮上水面。所谓女性主义(Feminism),就是要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男女平等。进一步说,女性主义就是以男女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平等为基础之上的妇女权利主张。①女性主义在发展初期主要表现为女性主义社会运动(也称为女权运动),先后出现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及20世纪60至70年代欧美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她们通过创办妇女报、参与政治会议等方式,在原有的城市公共空间中加入了女性的立场和身份,以社会运动的形式向世界宣告她们的平等诉求,主要体现在经济权、受教育权、选举权、婚姻恋爱自由等生存权上。如果说社会运动总是以胜利或失败作为结束,理论研究则成为了女性主义更为长远的实践之路。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20世纪60至70年代)出现了从社会运动到理论研究的转向。这一时期出现的女性主义理论著作主要观点吸收了现象学、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哲学思想的精神,其哲学本质是对女性长期处于客体位序的抵抗与主体身份的确认。进入信息时代,新媒体“消解了传统的议程设置功能,在网络上通过影像和声音聚焦热点事件和话题,形成强大的舆论”②。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是一种特殊的认识论——不仅关乎一半人类认知世界、理解世界的方式,同时也将以实践的方式直接或间接作用于社会现实。
需要注意的是,文中所提及的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并不是将性别研究(理论)和女权运动(实践)进行简单的二元区分,而是以意识(consciousness)-现实(reality)为谱系的哲学逻辑。作为理论与实践的女性主义,在都市电影中有哪些现实表征?随着技术的进步,它的传播方式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女性主义在新的媒介形态下又是如何影响社会现实的?本文通过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都市女性主义电影,希望厘清以上疑惑。
二、女性主义与中国都市电影
妇女解放,堪称改变本世纪(指20世纪,引者注)中国的社会思潮之一。③电影作为一门年轻的大众艺术,是女性试图通过文化领域打破性别桎梏的重要媒介。中国城市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从未缺席。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出现了以阮玲玉、黎莉莉等为代表的女性演员,出演了一批以《神女》(1934)、《都市风光》(1935)、《新女性》(1935)为代表的电影。女性以“备受欺辱”“自我牺牲”的形象登上中国电影的历史舞台。在“十七年”(1949—1966)电影中,他们关注女性劳动者,有不少影片反映作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的女性,展现了社会主义初期女性生产生活的图景,如《女篮五号》(1957)、《红色娘子军》(1959)、《李双双》(1962)等。妇女作为无产阶级的生力军,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一时期银幕上的女性虽然从家庭空间转而参与到社会空间中来,但性别问题几乎完全被阶级问题遮蔽,性别差异被弱化。女性社会地位和女性意识之间并非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只是作为“革命叙事”的话语。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女性地位是通过行政立法手段确立的,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女性的思想解放则是作为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内生动力而客观呈现的。然而有趣的是,改革开放带来社会秩序的重建,一开始反而加速了男权的再次确认。女性地位经历着由缓慢而急剧的坠落过程。④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与女性自我指认的意识觉醒,以中国城市化进程为题材的都市电影成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重要的创作来源,银幕上的都市女性形象、都市女性题材创作逐渐进入大众视野。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于1993年颁布《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改变了计划经济下电影“统购统销”的局面,电影作为文化的工业产品正式进入到社会的生产流通中来。1993年以降,大众文化的迅速扩张和繁荣大举入侵了民众的社会日常生活。电视机、电影院的数量逐步增长,“文化”的概念已经渗透在人们的“全部生活要素中”⑤。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I》中提出一个立场,在我们定义都市女性主义电影这一研究对象时同样适用:“要廓清女性的处境,仍然是某些女性更合适。”⑥因为男性总是“通过描写不同女性之间的差异来表达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其价值仅在于解决了将女性问题从男性话语中脱离出来的基本问题;而女性则是为更私密层面探究女性内部世界的自我挣扎,是由表层向内层的深层次发展”⑦。因此我们讨论的女性主义电影,仅指由女性导演或编剧执导、以女性为主要角色或视角,带有明显女性意识的影片。
三、现实的再现:女性意识与社会现实的镜像关系
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认为,电影是唯一用于记录和表现实质的媒介。电影作为视听艺术,自诞生之日起就彰显出再现生活的美学特性。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进入深化时期,资本已逐渐苏醒。市场经济体制激活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这为女性从家庭空间走向公共空间提供了精神和物质上的条件。都市是一个地区经济、政治、文化最为发达的聚合空间,同时也是先锋思想发轫和传播的物理场域。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一大批有胆识的年轻人纷纷选择下海。根据国家人社部统计显示,仅在1992年全国公职人员下海人数就达到12万余人。孙亚芳、董明珠等知名女性企业家就是在90年代选择放弃了稳定的体制工作,投身于市场经济。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女性主义思潮的传播,女性导演与女性编剧开始关切都市空间中的女性现实际遇、追问女性的个体价值。作者将自身的女性意识投射于电影创作之中,电影的银幕空间与现实空间形成再现的镜像关系(见图1)。

图1 女性主义电影与社会现实的再现关系
(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生存意识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揭示了性别差异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关系的不对等,没有独立经济基础的女性其生存空间注定是狭小而窘迫的。“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即物质生活本身。”⑧改革开放初期,大量商品的出现刺激着人们的需求与欲望。在电影《北京,你早》(导演张暖忻,1990)中,主人公艾红的最初目的不过是“买几件漂亮裙子”“给家人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艾红身上最具女性主体意识的一点就在于,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她一反被命运捉弄的女性形象,成为自己全部生活的行动主体。一方面受“下海潮”影响,艾红选择离开体制,从公交车售票员成为服装批发的个体户;与此同时她也自主地选择理想的婚姻,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在另一部被译为“Shanghai Women”的电影《假装没感觉》(导演彭小莲,2002)中,经济(物质基础)独立的重要性尤为突出:电影围绕着改革开放以来最具时代特征的经济产物——“住房”来展开叙述。离婚后的一系列遭遇让阿霞妈妈逐渐明白,女性的物质(经济)独立,是精神独立的必要前提与有力保证。影片细腻地展现了都市女性的内心情感,同时也触及到彼时社会结构的根源性问题。母女二人从到处借宿,到拥有自己的独立住处——这是一个从隶属关系走向独立主体的过程。影片结尾处母女走进一间属于她们房间的场景也暗含着女性权利的回归。
(二)从幽闭空间走向社会职场的主体意识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曾在其作品《一间自己的房间》(1928)中描述彼时社会环境下女性的不幸处境并指出其主要原因是空间的分散。她认为女性不容易形成同盟的原因是她们作为单独的个体分散在无数男性境遇中孤寂地进行着现实抗争。而男性大部分都活跃于汇聚性的公共场合,如政坛、战场等,共同交换对社会的看法并进行有效传播。⑨在这两种物理空间的背后,是凝聚与分散、主动与被动的生产关系导致的差异。当女性长期生活在分散的、被动的空间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使大多数女性深信自己属于家庭空间,而非社会空间。在《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等乡土女性题材电影中我们总能看到女性作为被凝视的客体不仅被限制在宗法秩序里,同时也被框定在幽闭的隔离空间中,“呈现出缺乏质感的鬼魅感和精灵化”⑩。而都市女性则更容易获得进入公共空间的权利。电影《女人TAXI女人》(导演王君正/编剧乔雪竹,1991)直接赋予双女主颠覆性的职业角色来拓展女性的生存空间。天资聪颖、英气十足的青年科学家和泼辣豪爽、车技过人的出租车司机——原本在人们刻板印象中类属于男性气质的职业角色——在该片中均由两位女性扮演。电影中的镜头组合形成银幕内外的女性空间,并直指女性进入职场空间的“两座大山”:生育后女性的再就业问题、女性职场的性骚扰问题。车内后视镜悬挂一支安抚奶嘴来意指司机张改秀仍在哺乳期,却仍需要通过劳动来增加收入;而秦瑶在遭遇了男导师的性暗示之后却反而被诬陷是小三,企图“借机上位”,在情感欺骗和道德绑架的双重压力下被迫走向绝境。两种不同职业事实上代表着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阶层差异,素昧平生的两位女性因偶然相识,开启了一段末路狂花之旅。影片结尾处二人最终打破阶级藩篱并站在同一战线,展现了90年代初期女性的职场生存图景。
职场空间是社会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指涉着权力和资源的分配与整合,都市作为地理标志是中国近40年来社会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都市白领的“办公室工作”也成为都市女性的理想栖息地。人们逐渐发现,女性在脑力劳动方面并不亚于男性,甚至更为细心、更具优势。随着都市女性精英力量的崛起,“女子力”或曰“女力”(Girl Power)成为文化研究领域所提及的一个重要概念。电影《杜拉拉升职记》(导演徐静蕾,2010)的主角杜拉拉正是“女力”(也就是“大女主”)形象的典范。作为经典的女性职场电影类型,影片通过塑造杜拉拉自信、知性和时尚的人物形象,强烈地彰显出作为女性个体的权利意识。她反复强调“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是生活底线。”在杜拉拉看来,恋爱与择偶的主动权都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进入职场并不只是求得丰厚的收入,而是通过自我奋斗实现人生价值的主体性追求。电影中女性角色像服装模特般不断地向观众“展示”不同的时尚服装,象征着女性掌控自己身体权利的回归。在大众传媒对女性的议程设置中,杜拉拉这个角色“混合着关于既知性又时尚的当下新型女性的想象”,“杜拉拉”一度成为现代都市职场女性的代名词。除此之外,电影中杜拉拉跳槽的细节也直指职场性骚扰问题,与日后在社交媒体爆发的“Me too”运动形成某种互文性。
四、互相的建构:身体、文化与家庭中的性别政治
“性别政治”(Sexual Politics)是女性主义的重要理论之一。在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看来,作为性别的身份是“迟来的、虚构的”,本原“被暂时生产出来”的一种操演(performativity)的结果。而这种操演的背后,是现代社会网状权力机制的运作,具有主体性与能动性。女权主义者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在其著作《性政治》(Sexual Politics,1970)中将男权制/父权制引入女性主义批判理论中来,并且赋予其双重含义:第一,指男性统治女性;第二,指长辈(一般指男性)统治晚辈。这个观点是尖锐而犀利的,它跳出了性别二元对立的思维,而将其放置在社会生活语境中为弱势群体发声,驳斥和声讨因权力不平等而导致的各类社会恶性事件及问题,如性骚扰、性侵犯以及对性少数(LGBT)的歧视等。对不同场域中弱势群体的关注,实质上都有广义女性主义的倾向。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女性主义在网络空间中呈现出独特的聚合力,逐渐印证“性别操演”理论的运作机制。近年来,真实存在却不被大众了解的,甚至触及道德伦理最底线的恶性事件,在新媒体时代受到大众的强烈关注与讨论,例如:南京火车站养女猥亵事件、滴滴女乘客遇害事件、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鲍某性侵养女案……性别议题和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数量明显增加。女性主义创作者直击当下痛点,试图建构出女性主义者理想中的生活图景,并通过网络空间影响社会现实。电影作品经由网络的二次传播形成新的互动空间,极大地拓展了女性主义的传播路径(见图2)。

图2 女性主义电影与社会现实的互构关系
(一)“我的身体我做主”:身体与性别政治
父权制的胜利将女性纳入男性的时间系统,主体性的沦落使其成为客体的物。女性的年龄、长相、身材(的好坏/优劣)几乎全部由男权/父权话语定义。年轻貌美的女性不但更容易成为男性的猎物,而且在受到侵犯甚至被杀害后还因“穿着暴露”“言行轻佻”“举止不雅”等行为“获罪”。受“红颜祸水”美与罪并存的传统观念影响,现代社会的“受害者有罪论”业已成为人们的集体无意识。电影《嘉年华》(导演/编剧文晏,2017)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受害者有罪论”的有力驳斥。电影没有一个镜头展现性侵过程,全片用冷峻克制的影像语言对抗着由“家庭内部秩序、社会外部关系和女性的同构性关联等伦理性话题共同搭建起的,笼罩在女性意识之上的牢笼”。影片展现了被父权社会整体编码的女性群像,并显现出不同程度的女性意识。撕扯裙子、剪短头发等“去女性特征”的方式反映小文母亲被父权价值观念收编的事实。玛丽莲·梦露巨型雕塑作为男性视角下的性欲望符号,在影片中同时作为小米内心的隐秘空间,分别经历了凝视、拆解、挪移的变化。小米最后终于在公路上加速狂奔,隐喻女性的自我解放。
性侵事件包含着成人对孩童、男性对女性、强者对弱者的三种叠加的欺凌。当弱势群体遭受暴力侵犯时,施害者绝不是单独的某一人,而是整个社会。导演文晏直言不讳地表示,电影不是要展现性侵事件的偶然性,而是要讨论社会的必然性问题,这部电影可以作为讨论的起点,而不仅仅只是大众的情绪宣泄。电影生产和网络二次传播引发大众对热点话题的广泛关注与道德质问,许多女性在社交媒体高喊“我的身体我做主”的口号,以对抗长期以来的男权话语。《嘉年华》与韩国电影《熔炉》(Silenced,2011)、美国电影《聚焦》(Spotlight,2015)等形成某种互文性,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人们对于性侵问题的集中关注,在网络信息技术的加持下,借由“艺术-舆论-法律”的流动话语空间在女性的社会生活与政治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2017年以来,我国已先后在江苏、广东、浙江、湖北等地设立试点,组建性侵儿童犯罪者信息数据库并向社会公开信息;2020年4月30日,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意见》,加速对未成年人(特别是女性未成年人)的保护及立法工作。
(二)出走的娜拉:文化中的性别政治
中国古代社会对女性的规训建立在一种“道德政治”的框架之下,权力结构总以道德机制的形态出现、运转。电影《无穷动》(导演宁瀛,2005)大胆深入地触及了当代变革时期中国社会成功女人的内心世界,打破了传统概念中“柔弱、顺从、压抑”的东方女性形象。无论是银幕中的四位女性角色妞妞、拉拉、琴琴以及夜太太,还是银幕之外的四位演员洪晃、刘索拉、李勤勤和平燕妮,都是在影视、文化、政治和经济领域均获得社会承认的成功的精英女性。个人的情感经验与历史的、当下的时空交汇,形成了独特的关于年龄、记忆、性快感与政治实践等女性话语的空间。四位女性话语中的文化场域与她们身处四合院所指涉的宗法父权之间极具张力。四合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位序结构的空间能指,由传统建筑所圈划出的“内帏”成为束缚女性身体活动与精神思想的物质场域。幽闭的空间压抑着女性的欲望,成为一种不可言说的内部情绪。影片中吃鸡爪的段落饱含着对女性气质刻板印象和女性“谈性色变”的反叛,对银幕中女性作为被凝视的性对象进行颠覆性解构。电影的剧作核心全部围绕着妞妞丈夫——一个缺席的男性,而这种缺席实质上表现出父权无处不在的“在场”。除此之外,张妈妈同样作为父权的象征不断地打破女性话语空间,参与叙事。无论是四合院所指涉的传统文化,还是现代都市空间所代表的资本秩序,都在不同程度上折射出了女性对父权空间的批判。四位女性勾连出被压抑的无穷欲望,最终以娜拉式“集体出走”的姿态表达当代女性的文化反思。
(三)母职困境:家庭与性别政治
现代社会中的女性往往都身兼几重身份,一部分是社会职业,即社会属性;另一部分是母亲,即生物属性。在女性逐渐从依附到独立、从他者到自我的主体性建构过程中,几乎不可避免地仍会遇到另一个困境:即家务劳动(包括生育)与职场工作之间的矛盾,也是现代女性生存压力的主要根源。波伏娃认为,生育束缚是阻碍女性步入社会空间的重要原因,因为“生育功能经常使得女性处于道德上消极被动的地位,她们很难自身创造出超越性的价值来颠覆原有的社会结构”。不仅如此,女性时常面临的是“性别与母职的双重赋税”。法国哲学家加里·古廷认为,将波伏娃讨论的女性的生物学问题置于女性主义的争论背景之中大有裨益。影片《找到你》(编剧秦海燕,2018)中三位母亲的形象,真实地揭示了现代社会不同阶级女性的现实境遇:无论是社会底层女性孙芳、职场精英李捷还是全职家庭主妇朱敏,她们在现存的家庭-社会结构中都难以找到平衡。她们的悲剧故事是对父职的深刻诘问。编剧秦海燕坦言道,她在编写剧本时融入了自己的女性主义观点,丢弃了以往女性贤妻、慈母的标签化印象,追求自由和两性之间的平等关系。影片中的“妈宝”丈夫以及婆媳两代人格格不入的思想观念、偷拐孩子的情节设置真实地触动了大众的神经,让人唏嘘不已。
关于“母职”的大众话语成为新近出现的性别议题。2016年起我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要不要生孩子、为什么要生孩子、生完孩子谁来管、怎样管……这些在传统观念里的母职思维定势,如今却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点。人们总用一百分完美的道德标准来要求母亲,而父亲表现“一般”“凑活”就已是理想状态,这极大程度上说明了家庭结构中权利与义务的失衡。女性/母亲在繁忙的工作与科学育儿理念下的抚养重任中难以获得一丝喘息的空间,女性个体经验的话语不断堆叠聚集,形成母职对父职的集体“控诉”,也促使女性重新审视生育权的问题。从试点推行二胎政策到全面放开二胎的6年间,中国人口出生率没有显著上升。其中2016年二孩生育率最高,随后逐年降低。数据还显示,夫妻双方都是单独家庭生育二孩的意愿没有显著提高,这与媒介中女性现实问题的真实呈现以及受众的重新聚焦与再讨论不无关系。
五、空间的生产:媒介融合时代的女性主义实践
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中颠覆了传统思维对空间的简单化理解,他指出,“生产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社会存在,或者说是一种空间存在;它们将自身投射到空间里,在其中打上烙印,与此同时它们本身又生产着空间”。早在信息技术发展起步阶段,就有女性主义者开始关注由信息技术搭载的虚拟空间对女性主义传播与发展的影响。不少女性主义者对于新技术所呈现的新经验持乐观的态度:英国女性主义者赛迪·普兰特(Sadie Plant)在其《论母体:网络女性主义的模拟》(1996)中指出,虚拟技术和女性之间存在着亲和性和共同感,“虚拟的空间能够让女性摆脱男性所支配的物质空间的约束”。互联网的出现打开了第三度空间的大门,男女无论在公共的社会空间,还是私人的家庭空间,都可以在网络中找到自己的同盟。网络空间扭转了物理空间中女性个体分散的境地,使得女性意识更具聚合力与向心力。女性的现实境遇-女性群体的集体创作-建构大众话语空间-影响现实生活,女性主义在“银幕-媒介-现实”的流转可视为女性空间生产的基本样貌(见图3)。

图3 女性主义电影与社会现实的空间生产
(一)银幕内外的女性话语空间
长久以来,女性被传统与历史抽象为日常的、家庭的、妻性的,基于性别差异的个体经验被男权话语覆盖,女性内心情绪和欲望的言说权利被抹除。女性主义力求破除男权中心秩序下的元话语,建立新的话语规则。《送我上青云》(导演滕丛丛,2019)是近年来出现的最为大胆的一部女性主义电影。在大多数电影中“性”元素通常以男性快感的视觉体验呈现,而该片则将剧作核心放置在长期以来被避而不谈的女性性体验中。主人公盛男作为一名27岁未婚的“大龄剩女”,竭力摆脱以男权视点为参照的年龄焦虑、身体焦虑,为使自己的人生体验更完整,主动追求性体验。影片摆脱了电影中“男性-性欲望”的单一结构,回归到女性纯粹的生命体验之上,肯定女性对性愉悦书写和言说的权利,并对传统道德秩序中的“女性-性禁忌”提出质疑。影片的导演(滕丛丛)、主演/监制(姚晨)均为女性,她们通过银幕内部的符号系统建构着女性话语,同时借由新媒体延伸至媒介空间、现实空间等公共领域,使女性议题在不同空间内聚合共生,拓展了女性话语的边界。
“公共领域已经不仅仅是形成多元话语的场所,同时也是颁布社会身份,形成身份认同的场所。”影片《找到你》除了塑造出银幕中的三位经典女性/母亲形象,还在电影宣传发行时邀请两位主演马伊琍和姚晨参与线下的城市主题观影活动。作为现实中的“超级辣妈”、社交媒体上的“微博女王”,她们通过银幕-媒介-现实的流转连结银幕角色和现实身份,在二胎政策的时代背景下围绕“生育与母职”的社会议题引发大众“现象级”讨论。影片一经上映便获得2.85亿的票房收入。在视频网站的二次传播中,该片已有61.2万人参与讨论,拥有1.1亿次点击量。以电影社区豆瓣电影为例,参与短评的讨论有近5万条,最高话题浏览量达到35.9万次。其中,“每个女人都是一座孤岛”“请给她们多一点善意”“在国产电影里充当道具的女性,终于为自己发声”等带有明显女性立场的讨论标题不仅诠释了电影中的人物形象,更反映出受众强烈的性别意识。
(二)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女性主义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认为,女性的“主体性”问题不能仅靠文化中的身份认同来解决,它必须同时依靠政治、经济等现实层面来改变其根源性问题。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电影从业人员中一种普遍的偏见是“女导演们是否能制作出和男人一样的影片”,那么近年来的电影作品呈现出的女性主义则是从镜像中跳脱出来的先锋姿态。女性不再是电影银幕上被展现的客体对象,也不只是电影文本的创作者,而是成为了电影工业的生产主体。这种生产关系上标志性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自2002年《英雄》开启大片时代以来,中国的电影产业日渐成熟。作为现实的再现,银幕中女性的就业、职场、生育等问题被继续放置在社会现实中并提出新的诉求;作为文化工业中的一员,越来越多的电影从业者仍坚持女性立场,她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参与社会生活,并产生影响。《杜拉拉升职记》中的徐静蕾,除了塑造“女子力”的杜拉拉都市白领形象,还参与到电影工业生产流通中,并成为内地首个票房破亿的女导演。李玉以商业电影导演的身份出场,开启“女性欲望”的叙事单元,其作品《观音山》《二次曝光》《万物生长》等分别获得7000万、1.1亿、1.5亿票房的成绩,成为当年的口碑电影。2017年,经国家电影局批复的中国首个官方国家级国际女性电影节“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在四川成都设立,旨在“彰显女性力量”。演员海清在2019年“FIRST青年电影展”闭幕式上与姚晨、梁静、马伊琍等共同发表“女演员宣言”,呼吁导演制片们给予中生代女演员机会……银幕、媒介与现实三元空间中的女性话语不仅加强了性别平等观念,而且在经济生活中刺激着女性消费。在“她经济”力量的推动下,女性议题相关的艺术沙龙、电影展映逐渐增多,女性主义在都市这个巨型容器中扩大它的领地和范围,通过实体的或虚拟的空间形式再造着人们的现实生活。
六、结语
女性面对的通常是一种镜式生存——这种困境一方面来自于语言和规范的囚牢,另一方面来自于自我指认的艰难。中国都市电影中的女性主义分别在银幕空间、媒介空间与现实空间呈现出再现、互构与生产的三种样态,是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统一性的自证。不可否认的是,新的媒介形态让人们快速、高效地获取信息,并参与到社会热点事件和突发事件中来。大众观点通过新媒体传播、发酵,在短时间内能够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舆论场域。然而数据的流动“来得快,去得也快”,许多轰动一时的新闻很快会被众人淡忘,电影艺术便在此时彰显它的力量。女性主义电影往往并不是先验的,但它是一个当下的注脚,一个具有持续生命力的空间。与其说作为媒介的电影与新媒介(新媒体)之间呈现出一种媒介融合的态势,不如说电影和新媒体保留了其自身形态却又互相补充。在这个独立而互构的媒介空间中,女性主义正在运用网络信息技术的红利传播、发展。正如列斐伏尔形容的那样:“空间是生产模式的产物,产生于社会运动的过程中;同时空间又是社会活动演变发生的场所,它可以孕育新的因素从而改变社会进程,塑造现实社会的样貌。”
除此之外,近年来影视作品都争先恐后地塑造了不少“大女主”的形象,对此我们应当保持审慎的态度。从本质上说,“大女主”形象只不过是将传统意义上成功的男性角色进行了性别置换,并没有脱离男权的语境。也就是说,女性依然作为客体身份去复制和效仿男性的成功经验与路径,她们依然不是实践的主体,现实中真正的女性生存境遇被悬置。不少宣扬所谓女性主义的影视剧,都无法通过贝克德尔测试(Bechdel Test),而被影视作品虚构的所谓“女权”很可能会反噬女性意识,最终落入男性中心的窠臼。
最后,我们面对网络空间也应保持理性。大众传媒与影视文化的耦合为女性主义实践与传播赋值,但同时也极易与商品经济合谋,使女性看似独立自主,实则站在女性意识的对立面:一种主动的自我物化,即通过物质堆砌不断地将自己精美包装来获得主体性和满足感,成为资本的“他者”。有研究者认为,网络空间作为性别认同和政治的新边界,不会自动改善女性的地位,女性需要以经验、兴趣、知识等改变不平等的单向流动,使之成为稳定而持续的生产空间。“五四”时期就有观点指出,女子解放,就是男子解放,同时也是社会解放。这一观点在100年后的今天看来依然保存着其正确的现实意义。只有更清晰地描绘出“女性实在”的轮廓,才能更好地参与到“人类共在”的发展进程之中。
注释:
① [英]莎朗·史密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妇女解放》,金寿铁译,《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7期,第82页。
② 李明德、朱妍:《社会思潮的传播特征及引领——以互联网视听平台为对象》,《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4页。
③ 冯媛:《以女子立场看五四遗产》,《妇女研究论丛》,1999年第1期,第35页。
④ 戴锦华:《昨日之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5页。
⑤ 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
⑥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I》,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2页。
⑦ 孟君:《性别叙事:凸显差异的女性书写——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的作者表述之一》,《当代电影》,2007年第6期,第55页。
⑧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⑨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吴晓雷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4年版,第57页。
⑩ 肖慧:《〈无穷动〉和〈千里走单骑〉的性别政治和文化反思》,《文化研究》,2009年第0期,第2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