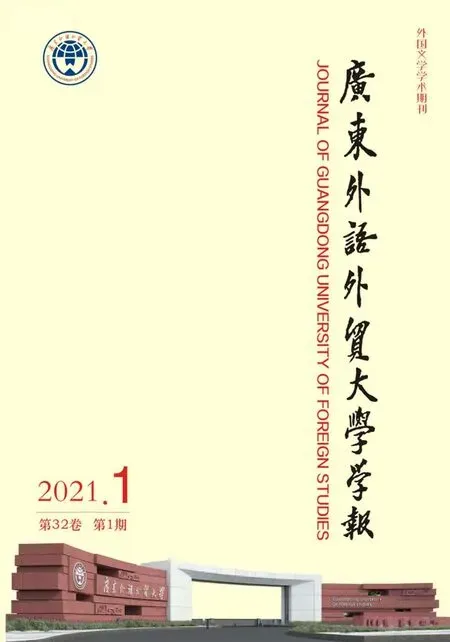异托邦的“守望者”
——塞林格笔下的麦田、权力与身份
罗益民 汪希
引 言
乌托邦概念①始自托马斯·莫尔(Thomas Moore,1478-1535)的名著《乌托邦》(Utopia,1516),意图是要构建一个理想的大同社会。这方面的文学主题形成一股历史洪流,贯穿历史长河。其实,创世纪神话中的伊甸园故事和柏拉图殚精竭虑要构建的哲学家治天下的《理想国》是这方面的滥觞。及至浪漫主义时期以及在此之前的传奇作品、田园描述,都有这方面的精神和情调。与此并行的,则是反乌托邦传统,到斯威夫特、赫胥黎和奥威尔手上推向高峰。后来,波德莱尔的《恶之花》,T. S.艾略特的《荒原》则在诗歌领域里,以另一种形式演绎了这个主题。评论界未曾注意到另一个有关联的概念,是法国哲学家福柯提出的“异托邦”(heterotopia)。就西方而言,在《镜与灯》的作者艾布拉姆斯所编的多版《文学术语词表》(AGlossaryofLiteraryTerms,10th ed.,2012)和企鹅版《文学理论、术语词典》(A. Cuddon,ADictionaryofLiteraryTermsandLiteraryTheory,5th ed.,2012)中都未及收入这个由概念形成的术语。同样,在外研社出版的两卷《西方文论关键词》(2016;2017)中也未曾收入此词。但这个基于社会权力话语的社会学概念,却可以奇妙地解释文学传统中介于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之间的另一种空间状态。本文研究发现,美国现代作家塞林格的杰作《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一部活画出来的,关于由权力、身份等因素演绎出来的典型的异托邦空间的艺术作品。
《麦田里的守望者》(TheCatcherintheRye, 1951)是美国现代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J. D. Salinger,1919-2010)创作的经典小说,被誉为二战后美国文学史上的经典著作之一(Steinle,2008:129)。塞林格在这部小说中塑造了霍尔顿·考菲尔德这样一个具有复杂矛盾身份的十六岁少年形象。他一方面没有真正准备好进入成人社会,另一方面却又因为将自己“敏感的灵魂过度暴露在成人世界的刺眼光线下”(Moore,1965:161)而无法回归到纯真的儿童世界。小说中围绕霍尔顿所展开的也是一个个互相矛盾的世界或空间,海伦·温伯格(Weinberg,1966:441)就认为霍尔顿不仅生活在公共空间之中,在他的内心世界还隐藏着一个秘密空间,所以“霍尔顿在公共场合使用不同的冷漠、粗野且通常是虚假的粗俗语,而在他自己的秘密世界中则使用文雅的语言”。除此之外,小说中还有诸如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城市空间与自然空间这样的一个个互相矛盾的空间。根据福柯的“异托邦”理论,霍尔顿在这部小说中所提到的“麦田”其实就是一个与常规空间相异的,既存在于霍尔顿的幻想中,又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异托邦”空间。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异托邦”理论极具反抗性,与福柯本人的思维模式有着紧密地联系。正如阿甘本(Agamben 2009:7)评价福柯所说,“福柯终其一生都在反抗着,反抗那所谓的普遍性原则。他反对大写的国家、真理、权力及主体”。“异托邦”的存在既是对常规空间的映射,也是对常规空间的颠倒与抗议,它能以一种“不在场”(absence)的视域观察权力在常规空间的运作。塞林格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创造出霍尔顿心中以“麦田”为代表的一类象征着霍尔顿心中那些纯真、善良、自然却又真实存在的空间与福柯的“异托邦”理论有着高山流水般的契合。霍尔顿这个出生于富裕家庭的中产阶级男孩享受着高等的教育,穿梭在繁华的都市间却提出了“麦田”这样一个田野间嬉戏的空间,这对于霍尔顿所处的常规空间来说的确是一个“异托邦”的存在。
本文拟通过福柯的“异托邦”理论将《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各种矛盾性上升到哲学和理论的层面进行讨论。这样不仅能突出常规空间与“麦田”空间的对比,更加清晰、客观地对常规空间进行剖析和批判,也能更加清楚地看到游走在各种空间中的霍尔顿的身份变化历程,从而探寻到这种变化背后所反映出的后现代主义空间理念。这为《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阐释角度。
塞林格笔下作为“异托邦”的“麦田”
“异托邦”(Heterotopia)是福柯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原本是一个医学术语,是异位移植的意思,是一种异常但是现实的技术或者现象。但福柯在他的哲学中从未对这一术语下过明确的定义,他也仅有三次曾在他的发言或著作中准确地提到这一术语。这个术语的准确含义,仅可以从上下文得到领悟和阐释。从福柯的这种做法中可以看出,他的“异托邦”理论不是一个僵死的教条,而是具有极大的开放性与广延性。不过有关他的“异托邦”理论,依然可以从他的哲学思想中窥见一斑。福柯(Foucault,1998:178),认为“异托邦”是一个相对于“乌托邦”的概念,并曾在他的《不同空间》(DifferentSpaces)一文中说道:“在所有文化与文明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这样一些真实的场所:它们被话语体系书写入社会体制自身内,它们是一种反位所的场域,它们是被实际实现了的乌托邦。与乌托邦相异,我称它们为异托邦”。“乌托邦社会”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一种社会理想状态,处于这种理想社会是没有阶级压迫和剥削以及资本主义一切弊端(刘茂生、罗可蔓, 2019: 37)。换言之,“乌托邦”是存在于理想中的不能实现的空间场所,而“异托邦”则是处于现实空间之中但是需要想象才能发现其存在的空间场所。为了进一步阐释这个理论,福柯在1966年的一次演讲中将“异托邦”比喻为孩子们的游戏空间。例如在一个真实的教室里,孩子们可以扮演成国王或者骑士。在这个真实且异位的空间之中,孩子所扮演的角色与自己在现实中的学生角色发生断裂,国王或骑士作为异质空间中的主体在这个断裂中被建构出来成为可能(Hjorth,2005)。从这个比喻中可以看到“异托邦”是一个结合了真实与想象的空间。
另一个有关“异托邦”的生动例子是福柯曾对博尔霍斯在自己的作品中援引了中国某本百科全书中有关动物分类的发笑。中国人对动物的分类方法颠覆了福柯以往的西方思维,福柯(Foucault,1994:2)认为“这种笑声动摇了我们思想所有熟悉的东西,动摇了我们习惯于用来控制种种事物的所有秩序井然的表面和所有平面,并且将长时间地动摇并让我们担忧我们关于同与异的上千年做法”。在这里,“中国的分类学就是一种外在,它像镜子一样以外部的视域折射出福柯所代表的西方世界的逻各斯”(张锦,2016:99)。中国对西方世界来说就是一个“异托邦”的存在,通过这个“异托邦”,西方得以从另一个“不在场”的视域观察自己的各种政治、文化、社会状态。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在他的《东方学》(Orientalism)中所用到的观察方法与福柯的“异托邦”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萨义德(Said,1978:9)认为,东方不仅与欧洲相毗邻,它也是欧洲最古老的殖民地,是欧洲文化的竞争者,是欧洲最常见的“他者”(the Other)形象之一。在这本著作中,萨义德正是因为拥有熟悉殖民地和帝国主义两套话语的双重身份,才没有像以往的东方学研究者一样从西方传统思维模式出发,而是站在东方的角度,才得出“每一个欧洲人,不管他对东方发表什么看法,最终都几乎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帝国主义者,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中心主义者”(Said,1978:163)这样一个颠覆性的结论。东方这个“他者”相对于西方人所处的常规空间来说,正是一个“异托邦”的存在。这便是“异托邦”的重要作用,能够为人们提供另一个视角观看、剖析自己平常所处的常规空间,观看微观权力在其间的暗流涌动。有学者认为,霍尔顿也是“一个观察者”(Laser,et al.,1963:14),他以另一个不同的视角观察着自己所处的常规空间。
在《麦田里的守望者》这部小说中,“麦田”是一个重要的意象,也是一个重要的空间位所。它是霍尔顿想象中的孩子们的玩耍之地,象征着以弟弟艾里、妹妹菲比所代表的天真无邪的儿童世界;象征着以修女为代表的善良美好的心灵;也象征着自己内心所向往的那个林中小屋,那片处于自然中的静谧之地,这些都既是霍尔顿想象中的空间,又是真实存在的空间。因此,“麦田”也是霍尔顿所处的常规空间中的一个“异托邦”空间,它既是霍尔顿想象出来的空间,也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那些美好纯洁的心灵以及宁静朴素的自然。正是因为霍尔顿站在“麦田”这个“异托邦”的角度,他才能够以一种更加清晰的状态观看到自己所处的常规空间中的各种虚假与伪善。与这部小说同一时期创作出来的戏剧《推销员之死》(DeathofaSalesman, 1949)同样,也揭露了当时美国社会的残酷与现实,但由于主人公威利·诺曼的思维视域一直处在常规空间之中,而没有一个“异托邦”空间帮助他看到现实社会中人们所普遍认可的那些规则与价值观对人的规训和异化,所以他至死也没有认清所处社会的真实面貌。
根据福柯在他的《其他空间》(OfOtherSpace)中所提出的“异托邦”的六大特征②可以看出,塞林格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设置了“麦田”这个“异托邦”空间的确是匠心独运的。首先,作为“异托邦”的“麦田”能够使其与霍尔顿所生活的常规空间之间形成一种横向的比较,从而达到对常规空间的剖析与批判。其次,“麦田”也能与不同时期的空间进行纵向比较。“麦田”既是处于现在时的霍尔顿对纯真童年的怀念,也是曾经积极向上的美国与20世纪50-60年代的那群“垮掉的一代”之间的鲜明对照。再者,“麦田”还能将各种毫无关联的场所叠加在一起,让它们跨越时间与空间的鸿沟而得以在这个“异托邦”中集中表达。孩子们的纯洁、修女们的善良、自然界的宁静共同绘制了“麦田”这样一个霍尔顿心中的向往之地。不仅如此,这样一个“异托邦”既开放又闭合,对霍尔顿充满了无限的诱惑力,但是又因为霍尔顿无法达到要求的条件而又不能真正走进这个“异托邦”空间。霍尔顿虽然内心善良,但他也不由自主地受到所处常规空间的影响。例如,虽然他讨厌身边那些满嘴脏话、性、毫无道德的同龄人,但他自己的行为也总是与他们如出一辙。因此,他无法真正地进入“麦田”,像孩子一般自由自在地嬉戏,也不愿掉入“悬崖”下的常规空间,因而只能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异托邦”之镜子:常规空间的权力流动
本文在研究《麦田里的守望者》时,引入福柯“异托邦”理论的一个主要目的便是突出这部小说中“异托邦”与常规空间之间的映射和对比,从而揭示各种微观权力在常规空间中的暗流涌动。正如福柯本人在阐释自己的哲学思想时,总是选择从监狱、疯人院、性这样的边缘题材出发来揭示主流社会的微观权力一样,因为一种“不在场”的视域更便于看清常规空间的本来面目。在阅读《麦田里的守望者》时可以发现,在这部小说中,大多数人几乎都生活在一个被普遍规则所规范的常规空间之中。学校和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有统一的规范和标准,在学生群体之中也有着一个个小团体,而在社会上从事不同工作的人似乎也都在按照一种同样的方式生活着。霍尔顿则与那些身处其间并对这些社会规则深信不疑的人不同,他以另外一种视角看到了常规空间的“监狱”本质,主流话语的霸权以它所制定的社会规则、价值观为工具规劝、改造着生活在其中的人,从而使这些人成为权力所需的规范化、统一化、有用的主体,而像霍尔顿这种与主流话语唱反调的人“则不是被拒绝,就是被边缘化”(福柯,2000,14)。这样一种主流话语的霸权现象正如福柯(Foucault,1977:151)所说:“人并没有从一次次战争中逐渐进步,达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境地。最终只是法制取代了战争状态;人在规范系统的范围内使用它的暴力,然后从控制到控制”。
如前文所述,乌托邦是凭借想象中的标准、指数或参数等这些具体的细节以及之前成竹在胸的柏拉图相论(又称“理念”或“理式”论)式的蓝图来构建一个柏式“理想国”式的城邦或社会,反乌托邦则否定了这种空间建制、机制、价值、效果的可能性,比如讽刺辛辣的《格列佛游记》、栩栩如生的《动物农场》《1984》,都是这样的作品。塞林格的艺术空间则不属于前两者的做法。若从心理与审美机制的角度看,与克罗齐和英国诗人约翰·济慈倡导的移情和通感颇有如出一辙的殊途同归之妙。换一句话说,是一种物我同一的映射式空间塑造,在想象形体之中,通过位移的手法,托异之邦置于另一对应的空间。
可以看出,霍尔顿眼中的麦田对象空间,即是一个“美妙的新世界”。这里的新,是托异而移置的对象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构成这个空间的组成部分、因素以及如中国哲学家朱熙所说的理即是“所以然之故”和“所当然之则”,“则”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柏拉图艺术模仿论所说“隔真理两层”而不真实的说法。
霍尔顿在所生活的常规空间中一直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人物,他痛恨常规空间里的人和人们所自发赞同(spontaneous consent)③的普遍规则与价值观,常规空间同样也拒绝了不遵守规则的他。在学校,老师希望学生能认真学习、遵守规则、按照学校对学生的培养标准去成长。正如霍尔顿的历史老师斯宾塞所说:“人生的确是场大家按照规则进行比赛的球赛”(塞林格,2018:9)。例如,在英文课的“口语表达”考试中,英文老师有一套考试标准,即每个学生都需要在课堂里站着演讲,并且不能离题,一旦离题就可能会面临低分或者不及格的后果。老师和学生们都严格遵守这个规则,但霍尔顿却不一样,他讨厌规则,所以他说道:“我喜欢人家离题。离了题倒是更加有趣”(塞林格,2018:9)。于是霍尔顿自己也因为离题而得到了不及格的惩罚。在学生群体中,每个学生都需要融入小团体并遵守小团体里面的规则,不融入的学生则会遭受到排挤。霍尔顿在爱尔敦·希尔斯的同学詹姆斯·凯瑟尔便是因为不肯融入和妥协,最后受到学生小团体的欺凌而跳楼自杀。但是霍尔顿对于这样一个不遵守规则的人却是极其欣赏、喜爱的。
在家庭中,霍尔顿厌恶哥哥DB那种父母认同的成功典型:到好莱坞工作,买一辆凯迪拉克汽车。他也厌恶父亲的律师工作,认为自己父亲与其说是救人性命,不如说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当红律师,获得更多的金钱、更高的地位。在纽约,霍尔顿厌恶那些以宾馆的妓女、紫丁香厅的金发女郎、出租车司机为代表的金钱(利益)至上、只关注自己的人们,他讨厌资本主义那一套被人们奉为真理的利己主义思想、假模假样的交际方式。因此,在常规空间的任何地方,霍尔顿都显得那么格格不入。而他所向往的“麦田”空间则更加说明了在霍尔顿心中常规空间的各种普遍规则与真理所表现出的压抑、控制、虚伪与自私。
我们注意到,乌托邦文学及与此相关的传奇文学(Romance)都是把美好的构想艺术地建设在一个心理映射的对应空间,在现实世界体现为强悍的理想主义。莎士比亚因为有这方面的倾向,他才被《暴风雨》里普罗斯佩洛管理的世界理解为殖民地性质的“神奇/美丽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相反,也有艺术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才有了文学中的反乌托邦传说,比如前述的斯威夫特、奥威尔、赫胥黎等人的讽刺作品。塞林格笔下的霍尔顿与马克·吐温笔下的哈克·贝利芬应是同一文学源流。历史老师的球赛规则、英语老师的扣题规则、同学们建立的小团体是在构建他们的殖民地乌托邦理想空间,霍尔顿与他的同学凯瑟尔则是既不属于乌托邦理想界的,也不属于反乌托邦现世界的,他们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这种困境使后者选择了自杀,这种情形霍尔顿这个青春期的少年人也面临着。他讨厌DB兄弟这种所谓的成功典型,讨厌父亲伪善的救人工作,讨厌一切因利益而成的妓女、金发女郎以及其他利己主义者。这些在霍尔顿那里最终促成了以“麦田”为代表符号的反位所异位移植,在现实中构成他想象中虚拟的异托邦空间。
可以发现,各种普遍规则背后所隐藏的却是权力的暗流涌动,因为“规训‘塑造’了个体;它是权力的特殊手段。个体则被权力视为既是对象,也是其运用的工具”(Foucault,1995)。权力通过规训,使人达到规范化,因此可以“消除一切不规范的社会的和心理的因素,通过改造精神和身体达到一种‘脱胎换骨’,塑造出温驯和有用的主体来”(福柯,2000:8)。在这部小说中,教师、学生、家长、妓女以及其他的社会人士都在无形中被主流话语的霸权规范着,这种主流话语正是为美国当时的政治和资本主义的权力而服务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所揭示的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刚结束二战,正处于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统治下的政治恐怖时期④。美国社会经济状况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资本主义盛行,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提升,精神却逐渐匮乏,美国需要更加稳定的社会,更加发达的资本主义。因此在国家政治与资本主义所制定的法律法规以及文化和意识形态霸权的控制下,人民群众被权力所制定出的一系列规则改造成为一群规范化、统一化,符合权力需求的人。在霍尔顿所生活的常规空间中,人们都有一套普遍规则和真理,都有一套类似的利己主义的生活方式和假模假式的处事原则。比如霍尔顿在紫丁香厅遇见的那几位女郎一直都只关心自己的事情,所以当霍尔顿和金发女郎一起跳舞时,那位女郎一心只想看到自己喜欢的明星,对霍尔顿的谈话漠不关心,心不在焉地与他交流着。在纽约的出租车司机们对霍尔顿所关心的中央公园的那群鸭子也丝毫不感兴趣。而霍尔顿最为尊敬的安东里尼老师也对他说出了“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塞林格,2018:206)”这样典型的资本主义利己思想。人们的这种状态在1951年出版的《白领——美国中产阶级》中得到回响,作者米尔斯(Mills,1951:xii)认为中产阶级的白领们在权力的规范下最终成为“别人的人、公司的人、政府的人、军队的人,是一个自己站不起来的人”。在现代社会,微观权力以一种毛细血管式的方式渗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中。权力按照自己所需要的方向制定出一系列所谓的普遍规则来对人进行改造,因而在这样的权力规范下人也逐渐丧失了自己的主体地位,而成为被权力所奴役的人。通常情况下,处于常规空间视域的人们很难认识到控制自己的权力,而“异托邦”正像一面镜子,映射出常规空间中权力的暗流涌动。
在霍尔顿的“异托邦”空间世界里,权力、规诫、规范化、统一化都是他针对性一对一产生想象映射的异托邦声称因素。他想象中竭力位移、“殖民”的,是新柏拉图式的回忆,离开污染一切的物质和物欲,比如出卖肉体和灵魂的妓女、出卖崇高的律师,回到人类起始的伊甸园时代——那个时代被包含在至善、至美、至高的“太一”之中。对于霍尔顿,“麦田”是他的伊甸园,那些孩子们则是上帝眼中以及他的手下制作出来的种着生命之树、智慧之树,养着无忧无虑的亚当和夏娃的极乐世界。这是一种心理的位移,一种空间的想象式殖民。少年的霍尔顿没有权力可以依仗,没有普罗斯佩洛手中的魔杖,政治家口若悬河的口诛,没有斯威夫特辛辣的笔伐,因而,异托邦建设成了他的理想,他奋斗的方向。可以这样说,一切有思想的文字都不是写给孩子的,而是写给成年人的。同样,《麦田里的守望者》也是写给胸怀理想的成年人的,它的目标是削减可怖的欲望,缓释不善的权力。华兹华斯在他的一首短诗《我一看见高天彩虹》里说,“孩童是成年人的父亲”(The Child is the Father of the Man)。其实,这只是一种理想,塞林格描绘的霍尔顿这个人物所寄托的异托邦是他心目中的伊甸园和柏拉图式的艺术型“理想国”在现实中的移植。这是与柏拉图和创世传统不同的风采与表达方法,也正是塞林格欲说还休的婉转而高明的地方。
霍尔顿的身份转变:从边缘人到“守望者”
霍尔顿构建异托邦的具体手段,如果以异托邦理论来解读,是以边缘人到“守望者”的身份转变的实现来进行的。要知道,霍尔顿既回不到他的伊甸园式的儿童时代,也进入不了成人的社会群体,因而,他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在身份方面“做”一些工作。
塞林格将《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主人公霍尔顿设置为一个处于青春期的人物,这样的一个特殊年龄阶段正符合霍尔顿矛盾、焦虑的身份特征。他一方面并未脱离儿童的稚气,另一方面却又面临着即将进入成人世界的迷茫。所以小说中的霍尔顿才刚十六岁的年纪却生出许多白发,他的言行时而幼稚时而成熟,想必这正是塞林格对霍尔顿身份焦虑的暗示。以“异托邦”的视域看,霍尔顿是一个游离在常规空间的边缘人物,他的种种言行都并未遵守主流话语的规范,他不认为人生是场需要遵守规则的球赛,痛恨学校老师对学生所制定的种种规矩,不认可身边同学、老师、甚至父母亲人那种假模假样的处事方式。福柯认为,“一旦存在权力关系,那么就会有抗争的可能”(Rabinow,1984:249)。霍尔顿正是这样一个努力与常规空间中主流话语霸权进行抗争的少年。但霍尔顿这样的人物始终是常规空间的边缘人物,势单力薄,甚至可以说,他既无势又无力,因此,很难与常规空间的权力抗衡。因而,最终像霍尔顿这样的边缘人要么像凯瑟尔那样以自杀来抗议,要么就像霍尔顿那样时而表现出软弱,时而被排挤,被拳打脚踢,甚至最终被常规空间所认定的“正常人”关进疯人院。
对“麦田”这个“异托邦”来说,霍尔顿同样是一个处于边缘的人物。霍尔顿讨厌常规空间中那些满口谎言、道貌岸然的人,而他自己却同样是一个爱说谎话并以此为乐的人:他讨厌学校的那些学生小团体,但他自己也会因为胆小怕事而不得不融入那些团体,以一种虚假的方式和同学相处;他痛恨那些在菲芘的学校墙上写下“x你”的人,而他自己却同样满口脏话和性话题。因此,霍尔顿虽然向往“麦田”那样充满童真、善良、宁静的地方,但他的很多言行和观念因被常规空间的许多普遍规则以及各种意识形态所同化,而无法真正去到“麦田”空间,只能游离在其边缘。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个人身份所显现的特性具有过渡性、矛盾性和无可奈何的复杂性,在这种复杂、矛盾、混沌的状态下,当他在家中同妹妹菲芘谈话时,他说到自己想成为一个麦田里的“捕手”(catcher),以保护那些纯真的孩子不会掉入悬崖下那个被主流话语权力控制的常规空间之中。该字中catch乃“捕捉”之意。海勒(Joseph Heller,1922-1999)的名作Catch-22中,catch视作“规范”“戒律”解释。同时catcher也是一个棒球术语,是“接球员”的意思,在英国俚语,还指教师或教士。《麦田里的守望者》这部小说还以俚语、土话多为特色,自然隐含霍尔顿的“教师”或“教士”的形象,所以仅从这些角度看,catcher含有“治病救人”或“救赎”之意,他之所以想做一个“捕手”就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无法真正回归到纯真状态,而只能做一个处于“麦田”边缘的“捕手”,在那些纯真、善良的人快要堕下悬崖之际,伸出手将他们拉回。这也可能是他最初想到的摆脱边缘人复杂状态唯一可行的办法。
当霍尔顿的身份从常规空间与“异托邦”的边缘人转变为“麦田”里的“捕手”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在这两个互为对立空间中的边缘人身份。一方面他不愿意进入常规空间,像其他人一样按照常规空间的规则行事;另一方面他也满足不了进入“异托邦”的条件,因此只能选择“捕手”这样一个具有牺牲性、悲剧性的身份。但从边缘人到“捕手”的过程中,霍尔顿并未完成身份的完全转变。在小说最后,霍尔顿安静地坐在公园椅子上看着菲芘去抓旋转木马前的金圈儿却没有阻止她时,他才完成了从“捕手”到“守望者”的全部转变。在上文中说道,“catcher”有传教、救赎的意思,没有中译本中的“守望者”之意⑤。“守望”,顾名思义,坚守和看望,而没有付出行动去捕捉之意。笔者认为这本小说的施咸荣译本的处理方式与书中霍尔顿最终的身份之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霍尔顿不会妥协于常规空间的规则,堕入“麦田”下的“悬崖”,而会一直坚守住与常规空间相异的“麦田”异托邦,让人们意识到其存在,却并不会伸手去将他们捕捉、束缚在“麦田”空间中。正如霍尔顿在小说末尾所说的那样,“所有的孩子都想攥住那只金圈儿,老菲芘也一样,我很怕她会从那匹混账马上掉下来,可我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孩子们的问题是,如果他们想伸手去攥金圈儿,你就得让他们攥去,最好什么也别说。他们要是摔下来,就让他们摔下来,如果说什么话去阻拦他们,那可不好”(塞林格,2018:229)。这里的意思,如棒球术语所示,应有“守门接球”之意,暗示霍尔顿在一定程度上“保住”他所倾慕的这一异托邦之所,但又不会强行将人捕捉、围困在这个异托邦之中。
霍尔顿最终选择了“守望者”这一不再去规劝、救赎、捕捉那些将要堕入“悬崖”的人的身份看似是在常规空间与“麦田”之间做出的一个无可奈何的妥协,如奥曼(Ohmann,1976)认为《麦田里的守望者》是对资产阶级生活状态的严肃批评,但小说却没有提供这种社会切实可行的替代品。事实上,霍尔顿的这一身份选择正体现出很多后现代主义者的主张,即“倡导被边缘化的个体和团体起来反抗主流话语的霸权,打碎旨在将个体整合到规范同一体中的话语框架,促成各式各样的微观话语自由发展和增生繁殖”(福柯,2000:14)。他们同霍尔顿一样,无意于使一个“异托邦”替代常规空间,从而成为另一座控制人的监狱,而是希望倡导一种多元性、差异性、增值性的空间共存方式。因此,霍尔顿最终从一个希望“麦田”替代常规空间从而成为主流话语的“捕手”即传教士、救赎者身份转变成一个为“麦田”这样的“异托邦”中的边缘文化发声、倡导多元文化共存的“守望者”身份。但霍尔顿的力量毕竟是微弱的,所以他最终还是被常规空间中权力所制定的文明关进了精神病医院中,这种文明实际上“就是秩序、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群体的无形压力以及整齐划一的要求”(Foucault,2001:x)。否定了这些秩序与规则的霍尔顿在常规空间中被判定为一个疯癫者,这从“异托邦”的视域来看,霍尔顿才是那个主流话语霸权之下难得清醒的人。塞林格通过《麦田里的守望者》塑造了霍尔顿这样一个敢于反抗常规空间的先行者,而现代社会则需要更多像霍尔顿那样的“异托邦”的“守望者”“守护者”。
结 语
塞林格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构建了“麦田”这样一个特殊的“异托邦”空间,它既虚幻又真实,代表了儿童心灵的天真无邪、修女一般内心的善良以及与城市相对的自然的静谧与干净。福柯的“异托邦”理论为这部小说中以学校、家庭、出租车、宾馆、夜总会为代表的常规空间提供了“麦田”这样一个不在场的“异托邦”视域。“麦田”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映射出常规空间中的权力流动,这种主流话语的霸权以一种微观的形式渗进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权力既能以制定法制法规的方式强制人们遵守规则,也能以文化和意识形态渗入的手段获得人们对其规定的普遍规则与真理的自发赞同,从而将处于常规空间中的人改造成自己需要的那种规范化、统一化、有用的人,使人丧失自己的主体地位转而成为被权力压抑的对象。通常情况下,思维视域处于常规空间视域的人是无法意识到这种权力流动的,往往需要借助“异托邦”视角才能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常规空间的真实面貌。
霍尔顿正是从“麦田”的视角才认识到自己所处常规空间的伪善模样,所以他才成为一个拒绝常规空间的普遍规则、游离在常规空间的边缘人物。但他又因为受到了常规空间的同化,所以无法真正进入“麦田”空间,因而也只能成为“麦田”的边缘人。随着他在纽约的经历,他内心逐渐走出身份所带来的焦虑感、找到一个新的定位,那就是成为“麦田”的“捕手”,阻止那些纯洁善良、天真无邪的人掉入常规空间,救赎他们,使其不被常规空间的权力异化。但最后他在妹妹菲芘的身上发现,自己无法真正阻止那些纯真心灵的人掉下悬崖,而只能做一个不付出任何行动的“守望者”。然而,霍尔顿最终的选择并不意味着他的妥协,而是寄予他的另一种希望:那就是他无意于使“异托邦”替代常规空间而成为另一座监狱,而是不断地为“异托邦”所代表的边缘文化发声,从而倡导一种多元性、差异性、增殖性的空间共存方式,这一点也是许多后现代主义者的共同心声。
如果仅从孩子的角度看文学题材,塞林格这类以一部长篇小说定天下的作家决然不是什么大作家,这个只要想想荷马、维吉尔、弥尔顿、歌德,甚至他的模型塞万提斯,塞林格都高不过,即使他模仿了碰巧也姓塞的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塞林格仍在他之下,更不用说无所不通、无所不能的莎士比亚。有一个很明确的印象,莎士比亚不写儿童,不拿儿童说事儿。马克·吐温不服莎士比亚,以儿童为题材,终究在莎士比亚之下⑥。但是,仅就我们生活的时代而言,塞林格在文体样式上可以与马克·吐温媲美。就这一点而言,他的高明之处是在笔下描述了异托邦的隐喻世界,而这个隐喻世界,是刻画给成人的。作为成人也有他的孩提时代和青春期,霍尔顿这代表指涉,是在青春期怀念他的童年时代,或许这才是塞林格的本意,这可能是他不同于塞万提斯,高于马克·吐温之处。
注释:
①较早注意到并把这个概念推广应用的,是瑞典社会学学者赫洛斯(Daniel Hjorth)与丹麦艺术家肯特·汉森(Kent Hansen),他们合作进行的一个研究课题《视觉行业》(Vinsonsindustri,IndustryofVision)在《管理咨询学报》(Journal of Management Inquiry, (2005)4:386-398)上发表了论文《企业组织与异托邦创造》(Organiz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with de Certerall on Creating Heterotopias(or Spaces for Play))。
②福柯在其文章“The Other Space”中总结出“异托邦”的六大特征: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文化不参与建构差异地点(异托邦);每一个社会,就如它的历史所展现的,可使既存的差异地点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运作:因为在每个社会中,各种差异地点都有它精确而特定的功能,而且,相同的差异地点,会根据它所在的文化的共时性而发生这种或那种作用;差异地点可在一个单独地点中并列数个彼此矛盾的空间与基地;差异地点通常与时间的片段性相关——这也就是它们对所谓的差异时间开放;差异地点经常预设一个开关系统,以隔离或使它们变成可以进入;差异地点是人们在真实世界中建立起来的乌托邦。译文参看包亚明.2001.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③“自发赞同”(spontaneous consent)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在其著作《狱中札记》中提出的一个术语,即“统治阶级除了强制性的立法、司法、武力以外,还会通过宣传和灌输思想与价值观让人民心甘情愿地接受统治。强制的权力(coercive power)固然需要,但是更高层次的统治离不开自发赞同(spontaneous consent),才可能产生领导权或霸权(hegemony),在平民社会中形成情愿受统治的氛围”。转引自朱刚.2006.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详情参看Antonio Gramsci.1971.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M]. Quintin Hoare, Geoffrey Nowell Smith(trans.).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④美国从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掀起了一场以“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为代表的反共、排外运动,其影响涉及到美国政治、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
⑤本文所用的中译本为2018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施咸荣译本,在该译本中,将“catcher”一词都译为了“守望者”。
⑥参见James Shapiro.ContestedWill:WhoWroteShakespeare?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10.在该书中,作者叙述了马克·吐温花钱雇人“实证”莎士比亚是伪托而失败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