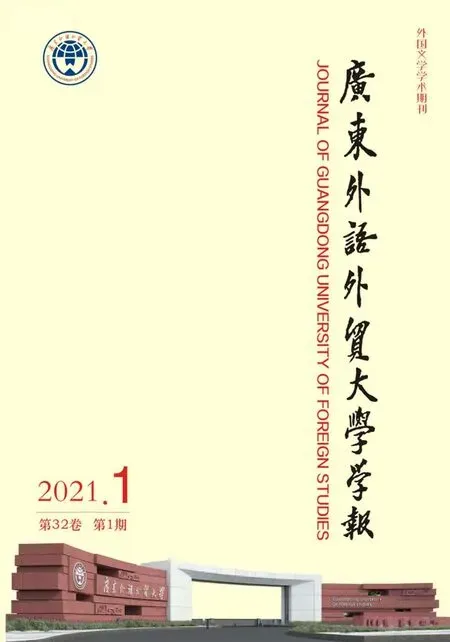物性书写:安·贝蒂《两面神》的物叙事研究
郭颖
引 言
安·贝蒂(Ann Beattie,1947-) 是当代美国久负盛名的短篇小说家,与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齐名。纵观国内学界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新现实主义、极简主义、女性主义、互文性等。比如,李晨歌(2011)着力在后现代消费社会的视域下解读小说,从而揭示出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的本质特征;黄姗姗(2019)则从“观看”方式的角度探讨了女性在性别权力斗争中的命运;笔者(2017)也曾将她的《大大的外部世界》(Thebigoutsideworld)与海明威的名篇《雨中的猫》(Catintherain)进行互文性对比分析。毫无疑问,这些评论都从不同侧面深入地剖析了作品的内涵,但若细读,不难发现,安·贝蒂很多时候会花费大量的笔墨对物件进行细节描述,从“极简主义”大多惜墨如金的笔风来看,贝蒂物性书写的匠心着实值得充分关注。
小说用以叙述故事的方式和途径有很多,比如通过人物、话语、行动、心理等等,当然还有通过物,只是这种“物叙事”往往鲜于被提及和研究。然而,“物性”作为世界文学图景的一部分,是沉默的事实,是文本新力量的来源之一(田洪敏,2017:56)。这种“物叙事”既是一种耐人寻味的技巧,也是一种效果显著的方式。在近10年的国内外研究中,“物转向”(turn to things)已明显露出头角(Breu,2014:7),这种转向使研究者的目光重新聚焦到客体本身,探索人类中心以外的“物”的本质(韩启群,2019:91)。
《两面神》(Janus)是安·贝蒂短篇小说创作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入选她自选的《纽约客故事集》(TheNewYorkerStories),是作者自视较为得意之作,同时也颇受读者欢迎。故事主要围绕房产经纪人安德烈娅对一只大白碗的无比依恋展开。目前,国内外关于此作品的研究较为少见且角度散乱。能查找到的仅有路德维格(Ludwigs,2014)从如何推动叙事进程的角度对文本所进行的分析以及曹艳(2009)重点探究其“无家可归”的主题性等。本文聚焦《两面神》,主要以其中出现了多达45次之多的“碗”为剖析对象,认为安·贝蒂在叙事策略中赋予了“物”特殊的神秘力量,是拉图尔(Latour,2005)口中的“行动者”,从而使“物”不再只是作为用来烘托气氛的背景而存在,更具有自己鲜活的灵性和力量,更能够推动甚至影响叙事的进程和发展。
《两面神》的神秘力量:碗的灵性
物质生态批评扎根于21世纪初兴起的新物质主义,这种“物质转向”是对持续三十年的“文化转向”的纠正(唐建南, 2020: 93)。在“物转向”的众多研究视角中,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将“物”的灵性、力量和主体性突显出来。“灵性是生命的前提,‘物’的价值既是内在的,又存在于与其他‘物’的关系中”(尹晓霞、唐伟胜,2019:79)。“物”在《两面神》中的重要地位从文章的开篇就显而易见。“这只碗是完美的。它可能不是你面对一架子的碗时会选择的那只,也不是在手工艺品集市上势必吸引众多眼球的那种,但它真的气质不俗”(90)①。“碗通常被放在一张咖啡桌上,不过最近她把它摆在一个松木被毯柜顶上,还有漆器桌上。有一次它被放在一张樱桃木饭桌上,上方是一副博纳尔的静物画,而它也拥有自己的生命”(90)。小说的一开头就通过大量的物描写,尤其是对碗的描写,使读者感觉小说的真正主角就是这只让安德烈娅爱不释手、随身携带且起着重要作用的碗。
当然,仅凭开场白和篇幅并不足以说明“物”在小说当中起到的巨大作用,最关键的还是作者赋予它的神秘力量:“这只碗最妙的一点,安德烈娅觉得,就是它既含蓄又显眼——一个集矛盾于一身的碗。奶油白的釉色,似乎无论在什么灯光下都会发亮。还有一些色彩——一抹抹小小的几何图案——有些带着几点银斑。它们像显微镜下的细胞一样神秘;很难不去仔细审视,因为它们闪烁不定,刹那变幻,又随即恢复原形。色彩和随意的组合颇具动感”(90)。来看房子的买家们虽然不会第一眼留意到这只碗,因为它并不招摇,然而,但凡注意到的时候都无法将视线从它身上移开。这只碗对买家们是充满了神秘的吸引力的,甚至安德烈娅还接到过来自买家的电话,专门询问碗的出处和购买方式。凡是放了这只碗的房子,就经常有人出高价并成功被售卖,宛若着了魔似的,而安德烈娅因此赚了不少钱,她“傻傻地想,要是碗有生命,她会感谢它”(91)。
碗的神秘力量不仅来自对买家的吸引力,更体现在对女主人公的影响力上。安德烈娅平时将这只珍贵的碗摆放在家中足够大的一张咖啡桌上,并且她从不让丈夫把钥匙或其他杂物扔到里面,她认为这只碗是神圣的,“应该空着”,“因为她喜欢看”(91)。“她从没想过自己可能打碎它。她心无焦虑地把碗洗干净、擦干……碗只是被她拿着,安全地放在一个平面或另一个平面上”(93)。然而有一次也不知怎么的,安德烈娅竟然把碗落在待出售的房子里了。当她想起时,全然不顾房主异样的眼神,发疯般地冲进屋把碗取走,生怕出了什么差池。安德烈娅对于自己会把碗遗忘的行为百思不得其解,她甚至想起曾在报纸上看到有人把小孩忘在哪里而开车去了下一个城市的新闻。心中浓烈的愧疚感使她在之后的日子里反复梦到这只差点被遗弃的碗:“她清楚地梦见它。它在眼前如此清晰地聚焦,有一刻她很吃惊——是每天注视的那同一只碗”(91)。她害怕失去它,她不敢想象自己的生活如果没有那只碗会变成怎样……这只充满灵性的碗,就仿佛一直陪伴在安德烈娅身边的恋人一般,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言而喻。
小说中多次提到女主人公对碗的存在的思考:从察觉到质疑、到确信、再到恐惧,一步一步证实了“物”的神秘力量。碗给安德烈娅带来了一系列的好运,她的所有策略都和碗有关,他们的关系包含着一种“未曾报答的好运”(92)。这使她不得不思索,自己跟这只碗到底有什么深层次的联系——“某种亲密关系?她修正了自己的想法:她怎么可能想出这样的事,她是人,而它是一只碗。荒唐。”(92)……然而,正是这谜一样的物件,拥有神秘而强大的力量,渗透在她生活的全部,成为萦绕在心间却不能开口与丈夫言说的永远的秘密。“碗只不过是碗,这一点她丝毫也不相信”,“那是她所爱的东西”(92),对此,她深信不疑。
《两面神》的叙事进程:碗的主体性
在叙事理论中,有一个重要且不可忽视的概念,那就是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提出的“叙事进程”(narrative progression)。他认为这是具有“文本动力(讲述发生了什么)和读者动力(接受讲述的人不断发展的反应)的叙事”,是“文本动力与读者动力的综合体”(张德霞、颜英俊,2019:34)。也就是说,“进程可以通过故事中发生的事情产生,即通过引入不稳定因素(instabilities)——人物之间或内部的冲突关系,它们导致行动的纠葛,但有时冲突最终能得以解决。进程也可以由话语中的因素产生,即通过紧张因素(tensions)——作者与读者、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冲突关系——涉及价值、信仰或知识等方面重要分歧的关系。与不稳定因素不同的是,紧张因素无需解决叙事也可以结束”(唐伟胜,2008:8)。
既然“碗”在《两面神》中被赋予了如此神秘而巨大的力量,那么它所扮演的则不仅仅是作为普通物件而存在的简单角色,而是能够推动整个小说叙事进程的关键主角。因此,在叙事研究中更应该突破以往的局限,突现“物”的施事能力,着重考察“物”扮演的主体功能,探讨“物”是怎样“影响(甚至决定)人物的行动,推动(甚至构成)叙事进程,参与(甚至构建)叙事作品的美学特质”(尹晓霞、唐伟胜,2019:80)。在简·本妮特(Jane Bennett)看来,“物”是实实在在的施事者,它们并非被动,而是有着自己的运动轨迹,充满了“物的力量”(thing-power)(Bennett,2010:3)。正如贝蒂笔下的“碗”,它是具有自主性的“物”,是小说中不容小觑的主角,在叙述中影响着叙述本身。
故事层面的“不稳定因素”
在《两面神》的故事叙事进程中,对物品尤其是碗的集中描写占据了文章的大量篇幅,而对于人物等剧情转折仅仅只有寥寥数行,由此可见,对碗的描写代替了对人物性格、行事动机和心理活动的解释,这种花费在笔墨上的悬殊对比,一定程度上说明“碗”这一物品是小说的行动者,而不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装饰物。这时候,“人的行动成为一个谜,这迫使读者像侦探一样,聚焦于物所呈现出的蛛丝马迹,深入每个场景的褶皱,以展开被折叠的事件”(殷世钞,2019:155)。
当然,仅凭借篇幅无法完全确定“碗”在小说中的主体性作用,但聚焦故事发展本身不难看出其所起到的推动故事发展的关键性作用。如上所述,从安德烈娅对待碗的各种细节可以看出,一方面她是非常喜爱和欣赏这集矛盾于一身的物品的,甚至可以说是充满敬畏和感激的,因为她坚信碗所具有的灵性并深深地认为自己在事业上的成功绝大部分都得益于此“物”的加持。然而另一方面,她又对“物”的灵性和具有的神秘力量感到不安乃至恐惧。“焦虑成为主导的力量”,“恐惧的是消失的可能性”(92),这一切都使她忧心不已。实际上,这一矛盾正好构成《两面神》故事层面上最重要的“不稳定因素”,从而使故事的运动逻辑能够得以更好解释。
首先,作为一名房产经纪人,安德烈娅深知这只既含蓄又显眼的碗绝非只是用来促成买卖的伎俩那么简单。因为在她看来,这不是一只用来装杂物的碗,它是与生命联系在一起的容器。安德烈娅的这只碗某种程度上延续了这一传统,但又不尽相同。它充满了世俗的韵味,指向的是具体的人和事。它是女主人公每天都注视着的碗,乃至于在梦中也能清晰地聚焦着它的身影。由此可见,它不只是用来点缀的装饰之物,更是在工作和生活中无时无刻陪伴在女主人公左右的亲密伴侣,所受到的喜爱与珍视溢于言表。
碗在安德烈娅的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唯一的一次忘了把碗带走,都让她惊慌不已、悔恨万分。正是这种如亲人般的感情,使女主人公越发不安。毁坏的念头一直在安德烈娅的心头萦绕:如果意外发生了会如何?如果碗消失了,自己的生活又会变得怎样呢?她开始惧怕“物”的灵性,因为她很困惑“这种情况会有怎样的结局”(92),也不敢相信自己离不开的竟然是一只碗。“碗”的存在以及后续的去向成为决定故事层面“不稳定性因素”的关键所在,一步步推动着小说的叙事进程。不过,仅仅停留在“故事”层面,读者很难理解为什么安德烈娅会对一只碗产生如此深厚的感情,从现实层面上来说会让人不容易信服。因此,应将研究笔触诉诸小说中叙事话语的张力,以便考察安·贝蒂更大的叙事目的。
话语层面的张力
如上文所述,《两面神》以对碗的大量描写为叙事开端,对女主人公安德烈娅则仅以“房产经纪人”五个字一带而过。由于作者和读者之间存在知识差异,这种有悖于一般故事开头的叙事,使读者不仅迫切地想知道接下来的情节将会如何发展,更给予读者一种暗示:这只浓墨重彩的碗一定有着与众不同的神秘之处。
有趣的是,读者对小说的阅读与安德烈娅对自己故事的阅读形成两条并置的平行结构,而两者的内聚焦又都同是指向不可逃避的结局。安德烈娅变得越发焦虑和不安,她痛苦地预设着最后的灾难——碗的毁灭或消失;读者同样也在等待结局:这只碗最后到底是毁坏了还是丢失了?是以怎样的方式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与女主人公截然不同的是,读者并不会有任何的焦虑或是恐慌,他们的期待单纯只是来源于未知的悬念。但是故事并没有在此达到高潮,悬念是通过融入“碗的历史”这一关键信息得以解决的:读者终于知道了,安德烈娅曾经有个恋人。这个时候,读者充满好奇,想得到一切相关信息,于是很自然地把注意力转移到过去。
原来,安德烈娅第一次见到这只碗是在几年前,是和情人秘密去逛手工艺品市集时看到的。她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徘徊不去。于是,情人就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并赠予了她。跟其他的礼物相比,碗就仿若裹挟着个体记忆的传记之物,使得她更为依恋了。通过新的信息来重读小说,一些细节就有了不同的层次和额外的意义。例如,文章中提到碗的丢失对安德烈娅而言就像失去恋人的时候,我们知道她不是抽象地泛泛而谈,而是在心里真的想着恋人。她的情人曾责怪她太迟钝,无法了解自己真正爱的是什么,只是一味地扮演着不愿改变的两面派。“后来他又做了一次努力,就离开了”(93)。安德烈娅失去了恋人,他的离开摧毁了她的意志,引发了她终将失去碗的预感。由此可见,“碗”作为小说叙事的动力主轴,填补了空白信息,使读者产生好奇、回顾过去并不断调整阅读期待,从而也增加了故事向前发展的悬念。“读者需要保持清醒,不断调整阅读期待才能适应叙述者的节奏,发现叙述者的真实意图”(张德霞、颜英俊,2019:38)。这两个叙事方向并连互动,在“读者动力”与“文本动力”的双动力作用下,小说的叙事进程得以重新建构,产生出更为复杂、震荡且来回拉锯的张力,带领读者踏上了陌生化的美学之旅。
结 语
在近十年的哲学领域、文学批评领域中,“物转向”已成为方兴未艾的学术热点之一,安·贝蒂的短篇小说《两面神》为勾画、探究人与物的关系(物转向)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又典型的文本情景。在小说中,作者通过大量的物视角展现出“碗”无论在故事层面还是话语层面所表现出的神秘而强大的力量,推动整个叙述进程的发展。在此进程中,“物”的灵性和主体性使其摆脱了人的操纵,成为拥有主动权的生命体,并作用于人的心智和行动上,使人陷入不断的焦虑与恐慌之中。放大物性实际上也是一种思索方式的放大,在这不足七页的字里行间里,安·贝蒂鞭辟入里地颠覆了传统的“人”与“物”的关系,极大程度地突显了“物”的能动性,使“物”在真正意义上成为独立的个体,拥有自己的话语权。这种物性书写是文本物质性的重要载体,具有“去人类中心”的基本精神。它更是对传统文学叙事的新突破,有助于学界对如何深入挖掘文本中的“物”的意义提供思考和研究的新方向。
注释:
①小说《两面神》引文均出自:安·贝蒂. 2014. 两面神Janus[J]. 周玮,译. 青年作家(2):90-93. 此后仅随文标明页码,不再详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