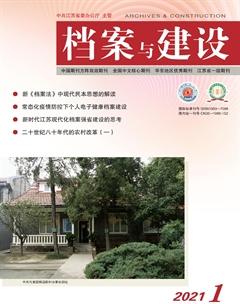隋文帝开山阳渎考论
滕汉洋
摘 要:隋文帝开皇七年开山阳渎,与嗣后隋炀帝大业元年开邗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工程,不能混为一谈。山阳渎的路线大抵循邗沟东道,这是唐宋时人的共识。清人刘文淇等认为山阳渎不循邗沟旧道,而是利用大小运盐河道新开运路的看法并不符合实际。山阳渎的修治,除了对整个运道进行疏通以外,最主要的还是集中于北端入淮口山阳县境内一段河道的整理,这也是此条河道得名山阳渎的原因。
关键词:隋文帝;山阳渎;邗沟;运河
对于隋代运河之开凿,一般皆委其功过于隋炀帝。实际上,隋文帝时期已经有两次开凿运河的工程。一次在关中地区,即开皇四年(584)循汉代漕渠所开的自渭水达黄河的广通渠;一次在江淮地区,即开皇七年(587)沿邗沟所开之山阳渎。对于广通渠的开凿情况,《隋书》等文献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历代甚少争议。而对于山阳渎,由于《隋书》的记载十分简略,后人对其运道及相关情况聚讼纷纷,颇多歧见。笔者不揣简陋,在梳理前人之说的基础上,就相关问题略抒浅见如下。
一、文帝开山阳渎与炀帝开邗沟之关系
《隋书》卷一《高祖纪上》“开皇七年”条记:“(四月庚戌)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漕”。[1]《北史》卷十一《隋本纪上》及《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陈纪十》“祯明元年”条也有相同的记载。隋文帝开山阳渎一事,有史为凭,确凿无疑,历来无人提出异议。山阳渎与后来隋炀帝所开的邗沟是否一回事,今人则有异说。
炀帝时期所开的运河,一般认为有四条,即通济渠、永济渠、邗沟和江南河。其中通济渠和永济渠的开凿情况,《隋书》等文献皆有明确记载;关于邗沟和江南河的开凿,《隋书》则未置一词。后世言及炀帝开邗沟与江南河事,皆据宋人司马光《资治通鉴》(简称《通鉴》)的记载予以论述。关于炀帝开邗沟事,《通鉴》卷一八○《隋纪四》“大业元年”条有云:“(三月)辛亥,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复自板渚引河历荥泽入汴;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自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四十余所。”[2]按照《通鉴》的记载,通济渠与邗沟虽然分属两个河道,但大业元年(605)的开凿工程是一体的。然而《隋书》对此年的运河开凿情况仅言通济渠而不及邗沟,这就不由得让人怀疑《通鉴》所记炀帝开邗沟一事的真实性。朱偰提出了疑义:“《隋书》本纪及《食货志》俱言大业元年开通济渠,而《通鉴》则于通济渠外,又言开邗沟,实则邗沟即山阳渎,早已在开皇七年开通,疑《通鉴》有误。”[3]这种怀疑是否有道理呢?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关于炀帝开邗沟一事,绝非司马光的臆造,而是源自隋唐时人已有的记载。前引《通鉴》文下,对于开渠之主事者皇甫议,司马光《考异》云:“《杂记》作‘皇甫公仪。又云‘发兵夫五十余万。今从《略记》”。[4]这里提及的《杂记》即唐人杜宝的《大业杂记》,《略记》即唐人赵毅的《大业略记》。此外,《通鉴》叙炀帝一朝事,司马光《考异》也曾多次引及两书。可知《通鉴》所言炀帝之事,除了取自《隋书》,还有一部分是来源于《大业杂记》和《大业略记》的记载。《大业略记》今佚,已难睹其原貌。但《大业杂记》留存大量佚文,如其曾记炀帝大业元年的运河开凿情况云:“发河南道诸州郡兵夫五十余万,开通济渠,自河起荥泽入淮,千里余。又发淮南诸州郡兵夫十余万,开邗沟,自淮起山阳至于扬子入江,三百余里。水面阔四十步,通龙舟。两岸为大道,种榆柳,自东都至江都二千余里,树荫相交。”[5]这段文字与《通鉴》所记基本相同,而且明确记载了炀帝开邗沟事,可见是《通鉴》的史源之一。杜宝为隋末唐初人,曾在隋炀帝朝任秘书省学士,入唐后撰编年体史书《大业杂记》,叙炀帝即位至王世充降唐间史事。赵毅《大业略记》当与此类似。且《大业杂记》序称“贞观修史,未尽实录。故为此书,以弥缝阙漏”,[6]显然有补《隋书》等唐初官修史书不足的目的。因此,对于开邗沟这样一个巨大的国家工程必然不会误记。正因如此,司马光才将《隋书》阙载而《大业杂记》等书记录的炀帝开邗沟事当作信史,采入《通鉴》。
邗沟开凿于吴王夫差十年,是春秋时期的旧渠,起沟通江淮的作用。但夫差所开邗沟由于时间仓促,基本只是勾连既有的天然水道,工程量并非很大,且自邗城出樊梁湖后,需要向东北方向绕道博芝、射阳两个大的湖泊,不但河道迂回,而且航行多有风涛之险。鉴于邗沟较差的通航条件,汉末陈登曾将其截弯取直,不绕道射阳湖而由津湖、白马湖至夹耶入淮;嗣后东晋时期为避津湖风浪,又于湖东开渠二十里入淮,进一步理顺了河道。历史上称汉晋时期改造后的河道为邗沟西道,春秋旧道则称为邗沟东道。这两条经过修治的河道依然各有其缺陷。东道迂回,且所经射阳湖浪大风急,来往船只常有覆没之虞;西道虽然较东道径直,但其南北两端地势较高,中间的高邮、宝应等处地势低洼,“若釜底然”,[7]邗沟南北两端常常由于河高淮低导致水浅难行。如黄初六年魏文帝曹丕伐吴至广陵,归途由邗沟北上,即因运路水浅而导致大量舰船搁浅在邗沟北端。[8]直到唐宋时期,这一情况依然是困扰邗沟航运的一大难题。因此,邗沟经过长期的历史变迁,尤其是经过魏晋南北朝近三百年的动乱割据和南北对峙,至隋时已经不能完全畅通。隋代对其重新加以疏通,实属历史的必然。
隋文帝开皇七年开山阳渎实是为南下伐陈作军事上的准备,次年分八道伐陈,但除陆路外,舟师仅有贺若弼一路取道山阳渎南下,另外一部分则由海路进发。可见,文帝所开之山阳渎本身并不是浩大的工程,如宋人程大昌所言:“山阳之渎,虽稍有增广,犹不胜战舰”,[9]并不具备大型舟船通航的能力。炀帝即位后三下江都,一路上龙舟及大量的随从能够顺利通航,绝非文帝草草疏治的山阳渎所能胜任,必然要对邗沟作进一步的截弯取直和疏通整理的工作,从而成为“后世运道直径之始”。[10]因此,文帝所开之山阳渎和炀帝所疏通的邗沟是不同时期的两個工程,显然不可混同。
二、山阳渎的行经路线问题
汉末陈登将夫差所开之古邗沟截弯取直后,后世所言邗沟遂有东、西两道之别。相较而言,邗沟西道较东道更为直近,也更为便利。魏文帝曹丕伐吴及嗣后的宋武帝刘裕和陈将吴明彻北伐,也曾取道邗沟,所走的都应是经过陈登疏治的邗沟运道。但由于邗沟西道相较于东道地势较高,常因水浅难行而影响交通,邗沟东道也并未废弃不用。如谢灵运《撰征赋》记其邗沟之行即云:“发津潭而回迈,逗白马以憩舲;贯射阳而望邗沟,济通淮而薄角城。”[11]其中明言过射阳湖,则其所经行的显然是邗沟东道。在隋文帝开山阳渎前,邗沟东、西两道应该都具有一定的通航能力。既然如此,文帝所开之山阳渎和邗沟东、西两道是什么关系呢?
《通鉴》卷一七六《陈纪十》“夏,四月,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漕”的记载之下,胡三省注云:“扬州治广陵,山阳县属焉。按《春秋》:‘吴城邗,沟通江淮。山阳渎通于广陵尚矣,隋特开而深广之,将以伐陈也。”[12]胡氏显然认为山阳渎乃是循吴故水道,即邗沟东道,只不过是在其基础上“深广之”,将其河道进行挖深和拓宽。胡氏的这一看法也是唐宋时人的共识。如宋人祝穆《方舆胜览》卷一四引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云:“昔吴王夫差将伐齐,北霸中国,自广陵城东南筑邗城,下掘深沟,谓之邗江,亦曰邗沟。自江东北通射阳湖,今谓之官河,一谓之山阳渎。”[13]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二四“楚州·淮阴县”云:“浊水,今谓之山阳浊,东南自州郭下,西北流经县北,流入于淮,即古之邗沟。……旧水道屈曲,多诸梁埭,隋文帝重加修掘,通利焉”。[14]皆认为山阳渎乃是循邗沟东道所开。朱偰也承此说,认为“山阳渎南起江都(今扬州),北至山阳(今江苏淮安),沟通江淮,大体上用的是吴邗沟故道。”[15]
当然,也有不同意见。宋人程大昌《禹贡后论》云:“邗沟南起江,而北通射阳湖以抵末口入淮者,吴故渠也。隋开皇七年开山阳渎以通运漕,比射阳、末口则为西矣”,[16]认为山阳渎末端射阳湖至入淮处一段较夫差旧渠偏西,并不完全重叠。清人刘文淇《扬州水道记》卷一则云:“隋文帝于扬州开山阳渎,盖由茱萸湾至宜陵镇,达樊汊,入高邮、宝应山阳河,以达于射阳。……宜陵之山阳河,吴王刘濞时已开通,专以运盐,非南北通行之路。隋文帝始由此道入樊汊,以通来往。炀帝又开广之。”[17]刘文淇认为山阳渎由扬州东北经茱萸湾,沿汉初吴王刘濞所开之运盐河至宜陵,再折向北至樊汊,再经高邮、宝应境内之山阳河通往射阳湖,然后达于山阳县之末口入淮。也就是说,山阳渎北段循邗沟东道,而南段则是利用了汉代刘濞所开的运盐河新开运道,嗣后炀帝开邗沟也是这条线路。现代学者嵇果煌则综合以上两家之说,认为:“隋文帝所开山阳渎,其位置既不循邗沟东道也不循邗沟西道,而是介于邗沟东、西道之间,利用当地一些纵横交错的运盐河道,加以疏浚、连缀而成”,[18]较刘文淇的观点更进一步,完全否定了山阳渎对邗沟东西两道的利用。
汉末陈登和嗣后的东晋南朝治理邗沟时已在北端入淮处另开新道,说明当时的末口可能已经逐渐淤塞。则程大昌所言山阳渎北端入淮处“比射阳、末口则为西矣”,只是入淮处的一小段与邗沟旧道稍有不同,尚不能证明山阳渎废弃邗沟东道不用。至于刘文淇的观点虽然独异,却经不起推敲。既然邗沟西道和东道在当时皆具有通航功能,即使这两条路线中的部分河道因种种原因偶有废塞,隋文帝也不至于舍弃现成的运河主干道而重开新线。历代人工运河无不追求径直以提高运输效率,而所谓的新线路,虽然可以利用一些现成的运盐河道,但较邗沟东、西两道迂回曲折过多,实在是舍近而求远,得不偿失。文帝为南下伐陈而开山阳渎,军事准备迫切,必不当如此行事。至于刘文淇认为文帝开山阳渎“不复由从前之运道,亦恐陈人觇之也”,[19]也只是推测之辞。隋人吞并江东之心,路人皆知,南北双方谍报频繁,无论隋文帝是否由旧道开渠,其实都很难逃过陈人之耳目。
实际上,刘文淇的观点乃是在其对山阳地名误解的基础上推导出的。其云:“山阳渎亦以扬州境内之地得名。江都、高邮、宝应皆有山阳河,后人或以山阳渎专属之淮安山阳县者,非也。考汉之山阳郡在兖州,今之淮安山阳,东晋义熙时始立郡县,……晋时山阳郡治在今宝应县射阳故城,即谓郡以境内地名山阳县得名,亦当在宝应境内。……《隋书》谓‘于扬州开山阳渎,则山阳渎在扬州可知。”[20]刘文淇这里对山阳县旧治的理解既不正确,其对《隋书》“于扬州开山阳渎”中“扬州”地域的理解也存在问题。《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江都郡”云:“梁置南兖州,后齐改为东广州,陈复曰南兖,后周改为吴州。开皇九年改为扬州。”[21]可知,开皇七年时的江都郡远较现代的扬州地域为大,江都县和山阳县都为其属县。又“江都郡”下“山阳县”条云:“旧置山阳郡,开皇初郡废。十二年置楚州,大业初州废。……开皇元年改郡为淮阴,并立楚州,寻废郡,更改县曰淮阴。大业初州废,县并入焉。”[22]可知,开皇初已改山阳郡为淮阴,治楚州,原来的山阳县成为楚州属县。开皇九年置扬州后,山阳县则彻底与扬州脱离了关系。因此,所谓山阳渎则不当与扬州有关,山阳渎是因隋时山阳县而得名是非常明确的。《通鉴》所谓“扬州”,实是取《禹贡》“淮海维扬州”之名,就隋时的江都郡而言,而非在现在的扬州市境内。至于刘文淇谓“江都、高邮、宝应皆有山阳河”,据此认定山阳渎在今扬州境内,其实也不确。前述宋人祝穆《方舆胜览》引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可以说明,唐时邗沟即存在官河、山阳渎等俗名,而江都、高邮、宝应皆为邗沟运道所经,各地自然也可将邗沟俗称为山阳渎或山阳河。综此,刘文淇的理解乃是以后觇前、以今隶古,在此基础上推衍出的山阳渎行经路线,在很大程度上当然也是因对地名的误解而强为解说。嵇果煌的推衍则是沿袭了刘文淇的错误更进了一步。唐宋时期即认为山阳渎大体依邗沟东道而开凿的传统说法,应是符合实际的。
三、隋文帝开山阳渎的主要工程
隋文帝开山阳渎之前的邗沟变动情况,郦道元《水经注》卷三○《淮水注》有详细记载:“昔吴将伐齐,北霸中国,自广陵城东南筑邗城,城下掘深沟,谓之邗江,亦曰邗溟沟,自江东北通射阳湖。《地理志》所谓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自永和中,江都水断,其水上承欧阳埭,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广陵城。……中渎水自广陵北出武广湖东、陆阳湖西。二湖东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间,不注樊梁湖。旧道东北出,至博芝、射阳二湖。西北出夹邪,乃至山阳矣。至永和中,患湖道多风,陈敏(引者按,当是陈登)因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径渡,渡十二里,方达北口,直至夹邪。兴宁中,复以津湖多风,又自湖之南口,沿东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自后行者不復由湖。”[23]
由《水经注》的记载可见,历史上邗沟的变动主要是在其南北两端,而中间一段一直少有大的变化。东晋永和年间,由于泥沙淤积使长江南移,导致邗沟南端无法引江水入沟,于是在原来的入江口设欧阳埭,南向开渠六十里至瓜步,引江水至广陵城下与邗沟相连。在唐代,由于长江北岸进一步淤积南移,迫近江心的瓜洲,开元时期润州刺史齐濣曾贯瓜洲南北向开伊娄河,使得原来绕六十里至瓜步渡江的路线进一步取直;大历以后,瓜洲终于与长江北岸连为一体,又自扬子桥开挖新河连通伊娄河,从而使邗沟南端延伸至伊娄河入江。当然,在隋文帝时南北隔江对峙的情况下,在邗沟南端入江口附近进行大规模改造是难以想象的,其运道基本仍应维持六朝时期的原状。隋文帝开山阳渎,当主要集中于邗沟中北部山阳县附近运道的改造,这也是其得名山阳渎的主要原因。
邗沟北端经过陈登等人的数次治理,已不绕道射阳湖。隋文帝开山阳渎本是为伐陈作前期的准备,开皇七年开工,开皇八年则举兵伐陈,为时甚促。且利用邗沟东道的既有水道,工程量必然不是很大,大抵即在已经治理过的河道上进行疏治的工程。对此,史念海云:“邗沟入淮本来是在末口,大概末口在这时已经湮塞,文帝不得不另外开一个水口。这次开凿的时期至为短促,实际的工程并不如预期的那样圆满。这本是为伐陈而开凿的,可是伐陈之役并未能充分利用,南征的舟师一部分绕道东海,并非完全出于邗沟。到后来,还是经炀帝另外开凿了一次。”[24]又云:“开皇时,文帝所经营的仅是淮水进入邗沟的水口,并非是邗沟的全体,所以炀帝在通济渠开凿成功之后,立刻又整理邗沟故道。”[25]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大体是符合实际的。
实际上,邗沟东、西道之别,主要在于其北端是否绕道射阳湖。邗沟北端地处淮河中下游地区,樊梁湖以北地区水网密布,河湖众多,从盱眙、天长等地区而来的山洪夹带大量泥沙汇集到这些运河所经的湖泊中,往往使河道淤塞不通,而白马湖以北地区又为沼泽地带。历史上这段入淮的路线,或走东线绕道射阳湖入末口,或走西线过津湖、白马湖一线至末口,变动不常,主要就是这个原因。文帝开山阳渎时,经过汉末和东晋南朝时期改造的邗沟西道的通航情况可能已经不太理想,所以他主要循邗沟东道进行施工。有学者认为山阳渎取东线是为了“迁就东线湖泊广阔,水源丰富,利于大型战舰通航”,[26]这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考量。不过,由前引程大昌称山阳渎“比射阳、末口则为西矣”来看,由于文帝的疏治而导致北端入淮一线比原来的邗沟东道偏西,这应该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对运道作出的适当调整。
当然,除了疏治入淮附近的运道,为使全线贯通,文帝必然也会对中段的水道进行整理。开皇八年隋兵南下伐陈,贺若弼所率的一支军队由此路渡江攻入金陵,可见经过隋文帝疏治的山阳渎虽然比不上后来隋炀帝重新开掘的邗沟,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邗沟的交通功能,为嗣后充分利用此条古老的运道奠定了基础。
*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唐代运河与文学研究”(项目编号:2020SJZDA019)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1][21][22](唐)魏徵:《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第25、873、874页。
[2][4][12](宋)司马光:《资治通鑒》,中华书局,1956年,第5618-5619、5618、5489页。
[3][15]朱偰:《中国运河史料选辑》,中华书局,1962年,第16-17、16页。
[5][6](唐)杜宝撰,辛德勇辑校:《大业杂记辑校》,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7](清)胡渭:《禹贡锥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94页。
[8](晋)陈寿:《三国志·魏书·蒋济传》,中华书局,1971年,第451页。
[9](宋)程大昌:《禹贡论山川地理图》,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41页。
[11](南朝·梁)沈约:《宋书·谢灵运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749页。
[13](宋)祝穆:《方舆胜览》,中华书局,2003年,第212页。
[14](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7年,第2462页。
[16](宋)程大昌:《禹贡后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19][20](清)刘文淇:《扬州水道记》,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3、24、12-25页。
[18]嵇果煌:《中国三千年运河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第512页。
[23](北魏)郦道元撰,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13年,第685页。
[24][25]史念海:《中国的运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53、167页。
[26]马正林:《唐宋运河述论》,唐宋运河考察队编:《运河访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