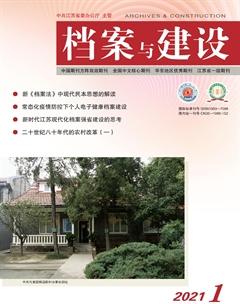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一)
编者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是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的奠基阶段,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原南通市委书记、江苏省政协秘书长吴镕,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共中央连续五个一号文件的起草者之一,全国著名的“三农”专家。作为江苏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参与者,他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细节,是现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鲜明的注脚。本文是吴镕口述回忆系列的第一部分,敬请关注。
前奏
1978年中共中央發出了一个三十七号文件,江苏省委研究室就派我带一个调查组,到武进县的鸣凰公社去调查了两个月。当时参加这个调查组的有纺织工业部长吴文英的哥哥吴志光,后来的无锡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解清,省乡镇企业局长、发改委副主任邹国忠等等。
当时的三十七号文件,讲要减轻农民负担。当时主持中共工作的华国锋同志是最熟悉农业的,又是搞农业出身,他多次讲过,在湖南时候就讲过,后来到北京也讲过,我们农民兄弟栽秧很苦,第一兜是给中央载的,第二兜是给省、地委,第三兜秧给县委,第四兜给乡里面,第五第六兜秧才轮到我们自己。一排秧就是六棵,他们讲兜,我们江南人叫六棵秧。当时由于工农产品的剪刀差,农民支持工业化,剪刀差上面的贡献超过1万亿元。当时稻谷非常便宜,一两毛钱一斤,我们根据调查结果就建议中央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把水稻价格提高20%-25%。这个报告从省委送到中央,然后中央就采纳了江苏意见。
1978年当年稻谷收购价就提高了22%。我想农村改革是一个组合拳,不是光一个包产到户,而是由扩大自留地、借田、开放集市贸易等组成的,特别是农产品提价的第一炮是非常关键的。这样就打开一个口子,使农民收入稍微增加了一些。所以我觉得这是农村改革的前奏。
包产到户
于光远说过一句名言:小小凤阳县,一次是出了个朱元璋皇帝,大明朝统一全国;二次是小岗村十八户农民盖手印搞包产到户,不久家庭联产承包制也席卷全国。
“大包干,最简单,直来直去不拐弯,交足国家的,留够自己的。”真是简单明了,一听就懂。2002年,杜润生同志九十大寿。7月18日,我们在北京京西宾馆聚会。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陈锡文同志讲到,年轻时从中国人民大学出来,到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在电梯上遇到杜润生同志,向他请教:“大包干就大包干,包产到户就包产到户,何必说得那么复杂,又是又统又分,双层经营,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杜老说:“小伙子,你从学校刚出来,可不懂得。在中国,有时候一个提法不当,是要掉脑袋的。”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告诫记忆犹新。
包产到户,1957年在浙江永嘉等地搞过,但当时永嘉县委书记李云河等都被撤职查办,有的还判刑坐牢,到1983年才得到平反。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明确表示,不准包产到户,《人民日报》还发过评论。
但是,安徽在1978年就做了试验。1979年2月6日,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就说了一段话:“包产到户问题,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都批怕了,因此使得一些干部见了‘包字、‘户字就害怕,一讲包产到户,就心有余悸,可以说是谈‘包色变。但是农民普遍希望包产到户,普遍要求包产到户。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正确的,有的可能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政策,也毫无例外地需要接受实践检验……”[1]
当时我在江苏省委研究室工作。邻近安徽的一些地县用大喇叭广播,“不让安徽包产到户妖风刮到江苏来”。但盱眙、泗洪等县农民自发搞大包干,获得大丰收。新华社记者写了《春到上塘》(上塘是泗洪县一个公社的名称),引起轰动。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带队去调查,促成了全省上下思想大转变。
在群众的推动下,中央的态度也是“年年有进步”。
1979年9月28日,中央下发《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仍然重申:“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适合我国目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不允许任意改变。”提倡搞“定额记工”“按时记工加评议”。不过,华国锋在1979年3月听取国家农委汇报时,倒是开了一个小口子:“包产到户,大家不赞成。但有些大山区孤门独户,那里有几块地,不能把人家赶下山来,造成浪费,可以包产到户。”这是中央领导最早的表态。
但事情反复多。1979年春,甘肃干部张浩致函《人民日报》,明确反对包产到户。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3月14日函告《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要报社“站出来说话”。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就发了张浩来信,加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重要按语”,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改革史上称为“张浩事件”。胡绩伟后来在南通对我说,“真理标准问题”顶住了,但“张浩事件”没有顶住,是个遗憾!但当时确实难顶。王任重还致电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万里答:“什么是好办法,能叫农业增产才是好办法。我们已经干开了,不宣传,不推广,不见报,搞错了省委检查。”
1980年9月,中央召开各省市党委书记会议,讨论农村改革,会上争论激烈。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与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针锋相对地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两人讲话都上了简报。会后,中央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1980年9月27日)的文件,即著名的“七十五号文”,是五个一号文件的前奏。其中为包产到户开了一个口子,称之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说“依存”,就是说本身并非社会主义,而只是依存和依附。但总算在“边远山区的贫困落后地区”等,“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为后来农村“分散决策”,责任制形式“可以、可以、也可以”打了一个基础。1980年11月5日,吴象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阳关道与独木桥——试谈包产到户的由来、利弊、性质和前景》的文章,后来得了经济学奖,杜润生在《自述》(《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改革重大决策纪实》)中也有描述。
事情正式出现转机是1982年一号文件,文件第二条正式肯定了包括“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理论的飞跃在1983年一号文件。文件指出农村最大的变化,影响最深远的是“普遍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而联产承包制的完善和发展,“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这段话起先执笔倡议者是林则徐的后裔、经济学家林子力。在中央政治局讨论该文件时,薄一波称赞中国包产到户(文件书面语多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大问题。万里几次说到,这个问题是几亿农民教育了党中央。小平、耀邦等同志一再肯定。陈云、先念都赞成。
1984年夏,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与胡耀邦会见时,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耀邦要杜润生考虑一下,联产承包制前缀“家庭”两字可否删去,以免国际友人疑虑。杜一传达,立即引起吴象等同志反对,多数同志认为“家庭”两字不可丢,这不是一般的修饰语,而是定性的:“联产联到心,基础是家庭。”
然而,事情还常有反复。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又有人提出包产到户是“方向上有问题”。1989年的国庆讲话把“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定语“家庭”两字略去了,引起了农民的不安。江苏、安徽农民的反应以小岗村为代表,通过国务院研究室的余国耀,于1989年11月24日报到了江泽民总书记处。江泽民在“全国农业综合开发经验交流会”上郑重宣布:“我主张八亿农民要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农村基本政策不会变,农村承包制政策不能变。……要给农民吃‘定心丸,让农民一百二十个放心!”(1989年12月1日于怀仁堂)
关于“包产到户”,再补充个细节小故事。江苏省委一次开包产到户方面的汇报会,各个调查组都汇报了,最后是一位老部长汇报。他说,我接到省委通知以后,三天没睡好觉,我是思来想去,翻来覆去。省委书记说,你不要翻来覆去了,你讲你的结论是什么?老部长讲,结论是四个字。书记问:四个字是什么字?老部长说:很难讲的。因为高压之下说不清楚和不敢说清楚。书记叫我说一说。书记说,你不能也是很难讲的。我说,是这样的,我已经印发一个材料,标题叫谈话记录,放在各位常委的座位上。书记说,你就讲讲记录是什么意思吧。我说,我是纯客观的记录,从记录上来看,越是干部大的越反对包产到户,越是基层的、贴近农民的,越是拥护包产到户。材料还附了盱眙县的调查表,区县公社大队那几个地方,包产到组的不如包产到户的,包产到户的不如大包干的一个产量对比表。
那么你的看法呢?我说,我的看法是我没有什么看法,我就是纯客观地反映。散会以后,省委的常务书记胡宏就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我理解你,干脆讲讲吧。我说刚才讲得很明确,包得越彻底,产量越高。胡书记桌子一拍,好,看来干部吃白搭的问题解决了。他是个四川人,因为过去粮食收到生产队的仓库里,生产队那个时候也没什么东西,有粮食了,开会夜里可以吃个夜餐,煮点稀饭喝喝。现在想想可怜。但是现在包产到户以后,农民的粮食多往自己家里送了,交集体也很少,所以干部吃白搭的问题解决了。这是一段插曲吧。
包产到户,到现在为止,大家还在争论。到底包产到户好不好?你华西大队和南街村不搞包产到户,不是也很好吗?所以,中国之大很复杂,不一定一种模式,可以多种模式,因而中央后来是讲的“可以、可以、也可以”。
关于包产到户的过程是这样的,开始是在1979年,中央农委开了个前门饭店会议,实际那个时候还叫向阳招待所,有6个省市区的6个农委主任到会,安徽农委主任叫周曰礼,他是有大功的。他一个人在会上讲了半天,讲了包产到户的必要性和好处,归根到底就是什么呢?就是从农民是私有者出发,把大田作为自留地那么种。我当年对杜润生同志说过:大公无私是圣人,先公后私是贤人,公私兼顾是好人,先私后公是常人,损公肥私是小人,贪污盗窃是坏人(这话发明权是江都的农村干部)。党的政策要从常人出发。雷锋那样的是少数先进人物。
中国国家太大,发达地区跟困难地区、三靠地区,差别也太大,所以应该分散决策,可以分散风险,这就叫可以、可以、也可以。这就是杜老发明的一个办法。试验、等待、妥协、逐步总结和推进。杜老告诉我们,每一个中央文件都是妥协的结果,是各方争论,然后求得最大公约数,来平衡一下,来协调一下,这样就发出文件来了。我们称赞杜老是“善于折中”。万里说:“我们说话太直白,经过润生这么一绕弯子,慢慢说,就说开了,说通了。润生有这个本事。”
我们江苏搞包产到户其实比凤阳还早了半年,泗洪县上塘公社有一个垫湖大队包产到户比凤阳搞得还早,现在他们也办了个包产到户的博物馆。当然,现在以凤阳县的小岗村为代表没有问题。一个事件总是找一个代表地区和代表人物,正如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代表人物胡福明,也还有别人的贡献。所以包产到户,池必卿、周曰礼等,是不可忘记的人物。后来杜老多次跟我講过,周曰礼不简单,在当时情况下,他一个人讲了半天。现在不知周曰礼还在不在人世。
改善流通
前面讲了农村改革是个组合拳,是多方面的系统工程。商品流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尚书》里面的《洪范篇》就讲国有八政:第一是食,民以食为天;第二是祀,祭天祭地祭社稷,可以天人和谐,是人伦之大事;第三就是货,货物的生产、流通。春秋战国时代的管仲就作这个文章,他讲通商,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范蠡,是商业之祖。匈牙利的学者科尔内写了一本书,叫《论短缺经济》(又译《短缺经济学》)。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前,基本上中国一直是短缺经济,那时什么东西都要凭票,吃西瓜要西瓜票,喝茶要茶叶票,买豆腐要豆腐票,我结婚的时候发了布票没钱买,还把布票送人了,所以钞票跟票证要正配。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三个月不吃猪肉,后来给高级知识分子发了半斤肉票,南京大学的一个教授就在肉票后面写了几个字:猪兄久违。卖猪肉的人阶级觉悟很高,一看就交到派出所了,他们以为是“反标”。这几个字是谁写的?后来全市一排查,是南大的一个教授、书法家写的。他说,我写的,我没有什么意见,我就是好久不见猪肉,我买了一块猪肉回来把它供在桌子上,朝他鞠了三个躬。猪兄猪兄,久违雅教,在下已三月不知肉味。1960年的时候,我们有一次跟江苏省长惠浴宇同志出差,到了常州,住在常州一个小营前招待所。早上吃早饭,端上来一笼热气腾腾的小笼包子。惠老一看,大发脾气,问谁搞的?市委书记杜文白说,我也不知道,是下面人搞的,既上来了我们就吃吧。惠老说,你就胆子这么大,毛主席三个月不吃猪肉,你敢吃。后来办公厅的金靖中同志就说了,他们首长是不能吃的,我们是老百姓随员,我们就吃点吧。惠老说也不行,谁也不能吃,哪个都不能动筷子吃下去。大家就嘴里咽着唾沫,眼睁睁看着那一屉热腾腾的小笼包子被端回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党风好,党纪严,确实是这样的。)
商品流通一向是管得很死,多环节,少渠道。我们国营商店卖的水果是留着好的卖烂的,卖了烂的又烂好的。到最后一个好的水果也不容易吃到。后来我们八十年代农村改革,每个中央一号文件都强调,抓生产必须抓流通。流通领域有几件大事,应该是从1979年起,国家大幅度地提高粮食等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我在前面已经讲了。
第二是开放集市贸易,第三是放开一部分农产品的价格。南方先放,放“两水”,即水果和水产。水果水产开放,吃西瓜就不要凭票了,就可以自由买了。
这样一搞以后,有个问题来了。我们讲一放就乱,一乱就管,一管就死。那么“两水”一放以后,放了不要票,价格就上涨了,上涨了以后有些人说不行,你赶快管。后来中央说不要急于收,等一等,看一看,结果放了,价格上涨了,生产上去了,生产上去产量多了以后,价格就自然降下来了,生产也平衡了。所以形成了一个“放—涨—上—降—平”这样新的格局,市场一派繁荣,多渠道少环节,改变了过去“收统—放乱—管死”的老格局。当然,由于小生产对接大市场,市场上多拉多来少拉少,还是难免的。
那个时候,我们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储江同志经常讲,农民的主要问题是买卖两难。他是用宜兴话讲的,特别有韵味。但是,主要靠市场调整,慢慢趋于平衡。
这时候,最早也是农民自发组织起来搞流通。江苏北部农民地多粮多,养鸡贩到人多地少的苏南,骑着自行车,披星戴月,渡江南下,赶早市。车队浩浩荡荡,被称为“百万雄鸡下江南”。万里等同志很欣赏。那些鸡贩子曾被讥为“二道贩子投机倒把”。胡耀邦同志则称赞,靠了这帮经纪人的中介,不是投机分子,而是搞活农村副业的“二郎神”。为他们正了名。农村专业户、饲养能手得利了,也不再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了,显得扬眉吐气。
当时我把这一景况写给《农民日报》,登上头版头条。一时间“百万雄鸡下江南”成为常用语和新风尚。
但是,事情总会有些曲折。在新闻评奖时,有人就说:“一是不严肃,比喻不恰当。毛主席说百万雄师过大江,怎么能比鸡呢?二是说了雄鸡,那么母鸡呢?”我答,母鸡在下蛋供城里人吃呀,小公鸡先卖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政治风波以后,社会上刮起一股风来。十三届五中全会就关于治理整顿写了一个决定,省委书记韩培信就到南通来,说老吴你看看这个稿子有什么问题,我一看确有不少问题。如在稿子上写了不准长途贩运,不准搞私营企业、搞批发。我就想了,“百万雄鸡下江南”不是长途贩运吗,而且不消耗能源,是人的生物能源去拉车,那个时候还没有钱用汽车运,这有什么不好的?后来正式定稿的时候,把不准长途贩运这一条删掉了。但有的还沒有改,如不准私人从事批发业务,这一段没有改,现在看来也很不妥当。当然后来逐步纠正了,但这些历程不应该被忘记,应该作为我们的教训。所以流通领域的改革,当时斗争也是很厉害的。
最后中央还是做了正确的结论,所以后来一号文件里面专门强调了,怎么来解决流通的少环节多渠道问题。我们在江都县的宜陵镇调查,写了供销社的体制改革,指出供销社是农民的合作经济,大商铺供销社要帮助农民小商小贩,这叫大鱼帮小鱼。费孝通就很欣赏,说老吴你们发现一个新的社会规律,过去是大鱼吃小鱼,你们现在大鱼帮小鱼,这个好。流通领域的改革,我觉得是一件大事情,也可以称农村的商业革命。
所以我说,农村是经历了几场革命,包产到户是农业本身的革命,乡镇企业是工业革命,商品流通大改革是场商业革命。
注释与参考文献
[1]余国耀,吴镕,姬业成:《中国农民命运大转折: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实》,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