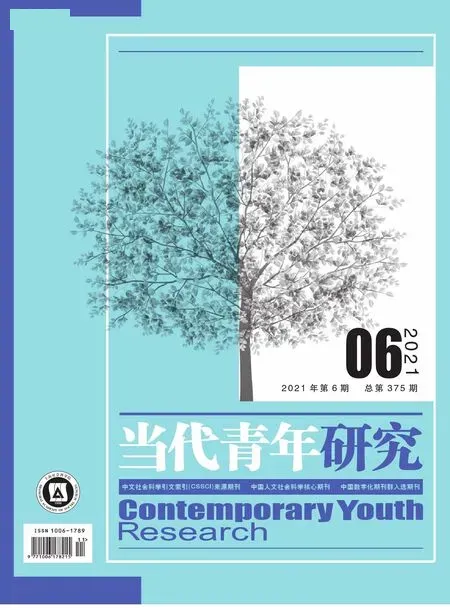新生代审美劳动者的劳动过程与自我锻造
万仞雪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城市中产阶级购买力的提升,以休闲娱乐为主的发展型消费成为都市主流的消费活动。诸如健身美体、时尚文娱、高档服饰、美妆品牌与星级酒店等新型服务业劳动力市场经历了快速的扩张,同时也见证了服务业内部产业结构与劳动形态的变革。其中,“审美劳动”作为继“情感劳动”之后的服务行业劳动新形态被提出,成为近年来服务业研究中备受关注的学术议题。[1][2]在过去20年里,在以巴黎、伦敦等全球城市为代表的城市中,上述服务部门就业增长率甚至超过IT行业,成为第三产业之最。[3]在我国改革开放40余年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步提升的同时,也见证了服务业结构的转型。一方面是以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为代表的传统服务业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逐年下降,另一方面是以健康、享受与悦己等为带边的“幸福产业”蓬勃发展。[4]
与传统服务行业劳动者相比,新型服务业从业者不仅拥有更为优渥的工作环境与薪资报酬,更为重要的是在劳动形态上,劳动者的外貌、身材、举止形态,甚至是生活风格本身的锻造,开始成为劳动的核心。在中国内地,这些行业从业者有近90%为“90后”和“95后”,是典型的新生一代;同时,近七成是为了工作从家乡来到一线城市的外来人口。[5]然而,尽管拥有更优渥的工作条件和更丰厚的薪资报酬,他们却处于比父辈更具张力的认同“拉力战”之中。本文将以一线城市的健身教练为例,将对健身教练自我认同建构过程的观察,置于与近年兴起并快速发展的“审美劳动”(aesthetic labour)的对话中。本文着力解释的问题是:作为审美劳动者的健身教练如何阐释他们在工作中的自我呈现?这种自我呈现与劳动者自我认同的关系又是怎样的,是顺应或是抵抗?本文以“劳—客”互动为分析框架回应这些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来理解新时期产业结构升级与劳动模式变革带来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与述评
(一)从“麦当劳化”到“定制化”:风格劳动力市场与“审美劳动”的涌现
风格劳动力市场这一表述最早出现在尼克森与赫斯特2001年所著的开创性论文“Looking Good,Sounding Right: Style Counselling in the New Economy”中。在以英国城市格拉斯哥现代服务业转型为案例的研究中,两人发现,自21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该市诸如健身美体指导、高端酒店服务人员和时尚顾问等就业人员大幅增长,几乎所有格拉斯哥的新型服务产业从业者都渴望“像‘三宅一生’(日本时装品牌)模特那样光鲜”。[6]对于他们从事的职业来说,“美”“身体呈现”与“自我表达”成为关键词,对风格的营造成为服务之上的新突破。在对21世纪的英国经济增长和风格劳动力市场扩张的讨论中,两人大胆地提出,相比知识经济,风格经济才是所谓新经济的核心驱力,“审美劳动”也因而成为新经济时代重要的劳动形式。随后西方学界涌现出大量围绕“风格经济”与“审美劳动”的研究。
在“审美劳动”之前,“情感劳动”是常被用来分析服务业从业者劳动形式的主要概念。20世纪80年代末,霍克希尔德在其研究中发现,与劳动密集型企业中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相比,服务行业的劳动者主要通过努力地营造某种特定的“情感状态”来换取劳动报酬。[7]然而,如上文所述,21世纪后新型服务业劳动力市场对情感状态的要求发生了变化,提供“定制”而非“麦当劳”化的服务成为新的工作伦理。它的兴起与风格劳动力市场的扩张和服务行业的消费需求,由获得“统一、便捷、匿名化”的标准服务需求向强调“个性化、人性化与专门化”营造的定制服务需求的过渡密不可分。[8]具体而言,“审美劳动”指劳动者“通过运用他们对外形、表情、举止和语言等身体资源、展示某种整体性等‘风格’或‘习性’去迎合、融入,甚至是培育和推广顾客的审美的一种劳动形式”。[9]
(二)是排斥还是融入:审美劳动者自我认同形塑的两种解释
认同是心理学、社会学与政治学中颇受关注的议题,它是个人对“我是谁”或“我们是谁”这一问题的反思性阐释。[10]学界关于认同的界定可分为本质论与建构论两类解释。[11]前者指“单个个体对自身特性的觉知、描述与理解”[12],受遗传、性格、认知能力的影响;后者对认同的理解源于欧洲社会心理学派提出的“社会身份”理论,它是“一个人对其所属社会类别或群体的意识”[13]。换句话说,个体对“我是谁”这一问题的回应是通过作为某社会群体的成员资格(如性别、民族、种族、阶层)建构的。本文对认同的定义采纳后者的理解,后现代社会中的认同不再是单一的、静止的,而是一个在多元的文化、结构因素和主体实践的互动之中不断流变的动态性概念。[14]
在现有研究中,关于审美劳动者自我认同的讨论有着排斥与同化两种取向。前者认为,在服务行业中,劳动者的情感处于管理方的控制与监督之中,个人的情感操演使劳动者形成“排斥性”的自我认同。如霍克希尔德在其关于空乘服务人员的开创性研究中展示了在消费主义席卷之下,一线服务行业劳动者情感上的“自我异化”。其后追随者在对餐饮业、保险、金融等商业服务业、高端酒店服务人员的研究也发现,以“塑造完美员工”为标准,劳动者的语言、衣着、举止、情感、观点都会受到严格的管理与规训。尽管工作环境提升,但劳动者实际与布雷弗曼研究的流水线上的工人并无二致,他们都经历着情感、心智的退化,处于低尊严、边缘化的自我认同中。[15][16]同化观点则看到了“审美劳动”与融入性的自我认同之间的关系。例如,国外学者在以时尚品牌服装店销售人员为案例的研究中发现,时尚公司的穿着规范和服务要求不仅没有令销售员焦虑,反而让她们形成了更强的“品牌依恋”,促使她们将自己想象成“品牌力”的体现,而非底层劳工的身份投入到劳动中。[17]同时,“有经验”的客户或消费者会对程式化的表演感到厌倦,相反,那些“打破常规”者(anti——routinization)通常有更好的就业前景和机会。劳动者在此过程中还可能制造各种不同的,会使劳动者体验到荣耀、自我认可并塑造新的自我认同。[18][19]国内研究者对新生代外来务工者的研究也有着类似的结论。例如餐饮业、美容美发业女工透过“制造微笑”“迎合审美”塑造了城市主体性的认同诉求,这又进一步促使她们积极地谋求新的文化身份。[20][21]
以上研究为理解工作与审美劳动者自我认同建构的关系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解释,然而,它们都将个体的自我认同形塑视作线性、单一的过程,这导致部分研究过于强调自我认同在个体身上体现出的张力。如前文所述,本文认为,自我认同始终处于不断流变之中,个体总是试图通过权宜性的行动去适应其所面对的复杂情境。基于此,本文以“劳—客”互动来理解审美劳动者自我认同的建构过程。这一理论将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放在研究的中心,同时采用诠释的方式理解行动者的观念和行为,即个体自身如何诠释自己的行动动机,如何选择并利用手头资源回应自我认同建构中的挑战。
三、研究对象、抽样方法与分析策略
本文选取健身行业为典型案例,是因为健身行业对健身教练的外貌、个人风格与服务的提供有着明确要求,劳动者从事着典型的“审美劳动”。本研究于2019年2月至2020年1月进行资料收集,在S市中心城区的W健身会所与东部城区的B健身俱乐部两家中高端健身连锁俱乐部展开。
研究地点和研究案例的选择出于两点考量:首先,选择S市作为调研地点是因为它作为全球城市中有着相对成熟的健身产业,行业从业者占整体近30%;其次,将健身俱乐部设置为中高端连锁店,是因为会员制经营模式下的消费者一般通过缴纳会费的形式获得入场资格,能够在私人教练的带领下,展开定期、固定的锻炼,这是劳动者和消费者发生稳定互动的前提。
实证资料的收集主要通过半参与式观察、半结构访谈与焦点小组三种形式获取。访谈对象的抽样以立意抽样为起点,通过滚雪球抽样的方式对包括管理者、受雇者和消费者在内共35人进行访谈。经验资料经过整理、校对后录入质性分析软件RQDA(R——based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先对访谈资料进行初始编码和再编码,再依据计算机辅助主题分析与笔者理论抽样中的主题分析,将自我认同的形成、调整划归为构建与整合两个部分。
四、审美劳动者的用户区分与自我构建
尽管对于管理者而言,外形或气质上的“有型”是促进课程售卖的关键,但实际招募的教练并不是在进入行业之前就已经在“风格”或品味上进行自我修饰。相反,他们有的刚从专科学校毕业,有的曾是退伍军人、体力劳动者,只有少数有直接相关的专业背景。因而,对于初入行的健身教练来说,比正规培训更具挑战的就是对健身文化的快速适应。学者马奎尔径直地将健身房文化理解为由新中产或精英阶层主导的一套生活风格和审美偏好。[22]健身教练对这一文化的适应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中,也就是教练与消费者的文化互动中。本文将其划分为两方面:一是通过对消费者外形与行为的观察,去诠释消费者的特定审美需求;另一方面则是以身体、情感作为行动资源,演绎消费者对审美需求的想象,力图树立“完美他者”的形象。
(一)审美“sense”的培育
我国大陆地区的健身产业化风尚始于21世纪初期,在近年快速扩张,形成了以会员制和私教课程售卖为主的盈利模式,因此会员招募与课程的销售是关键。尽管这使得私人教练在性质上与一线销售人员并无二致,但笔者通过对W与B健身教练培训与管理的观察中发现,关于销售本身的培训却是缺失的一环。在正式培训中,专业性是被着重强调的一环。这与我国大陆地区自身产业快速扩张造成的专业从业者稀缺有关。在对B健身俱乐部门店负责人的访谈中这一点也得到了验证,他认为:“我们招人的门槛没有想象的那么高,但我们后面会有一系列的培训,有的教练就是从刚来被我们培训成高端的。你工作一定的时间就必须去考证。运动医学课、形体课等,都是要求教练互相监督。”(MM02)
然而对健身教练而言,专业培训虽必不可少,但他们所认为更为重要的能力恰是正式培训里学不到的。这一能力在教练关于“sense”的表述中有明显的体现:“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那种‘sense’,不知道怎么形容。反正我刚来的时候很土,那个时候就几乎没法跟客户打交道,给人一看就是很难相信你有能力,没人愿意买自己信不过的人的课啊。这种‘sense’都是需要在这行混得够久才会有的。”(WM06)这种“sense”的建立就如谢尔曼在对高级酒店服务人员的研究指出的那样,是劳动者“审美社会化”的过程。[23]在这个意义上,“sense”可理解为健身教练对这一阶层的生活风格和价值理念从阐释到学习的过程。也有教练将它解读为看人的能力:“我们这个工作其实就是要学会看人。我身边有很多人讲理论什么的,但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你要不停地去了解他们,然后让他们喜欢你,你的东西才能卖出去。”(WM09)
在多数教练的口中,他们对潜在用户的搜寻针对不同用户特征的了解,大多来自和客户打交道的过程中积攒的非正式知识。从消费者推开店门的一刹那,他们与消费者之间的对话便开始,快速解读妆容、服饰、外形,成为他们看人的关键。在健身教练看来,穿着、身形、妆容与谈吐,不仅体现了消费者的消费意愿、消费能力和消费目的,更重要的,它们也是消费者品味和生活习性的表征,而对后者的了解则是获得客户的关键。除了外表,健身教练还会通过观察不同消费者在健身房里的行为,用和消费者搭讪的方式理解他们的消费动机。“有的女孩儿弄的倒是挺精致,但是你看她一会弄一下这个(运动器械),一会弄一下那个(运动器械),然后就是在跑步机上不停地跑,一看背也是歪的,跑步姿势也不对。这种就是没什么运动基础,大多这样,希望变得更瘦更美。”(WM01)
阿姨和健身小白是被健身教练谈论最多的两种类型,健身教练将前者的健身需求理解为享受、放松和寻求陪伴,是某种趣味的展示;后者的健身动机则被健身教练解读为可以通过“美”、自信返还到消费者自身的有效投资。对不同需求的洞察过程就是审美劳动者对象征着不同阶层习性和生活风格“符号”意义的阐释。对这些需求的背后也对应着要求,要赢得不同客户的订单,就意味着教练必须建立与不同需求相适应的期望和规范。这个过程是劳动者对消费需求的“解码”,它通过劳动者策略性的表演完成。
(二)扮演“理想的他者”
对于健身教练来说,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是一回事,如何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客户又是另一件事。后者所指涉的是劳动者透过实际行动将理想的审美“sense”具身化的过程,而无论是“制造感觉”还是“呈现微笑”,一线服务行业的劳动者在情感与身体展示上所做出的努力,是为了符合消费者对理想自我的投射。[24]
如《美丽的标价:模特行业的规则》中对模特身材的描述类似,“看起来对”和“看起来好”对于审美劳动者来说是一个没有尽头的标准,然而它并没有让健身教练像空乘服务员那样陷入情绪调控的困局。[25]在与W店的明星教练谈到高人气的秘诀时,对消费者需求的敏锐把握并付诸实践,被认为是成功的关键。“其实我从来不盲目去推销我自己,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想清楚你的客户期望从你这得到的是什么。你说为了健康、漂亮,那等于没说。而是那种很具体的,她想达到什么效果、去掉什么。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的直角肩啊、天鹅颈啊。现在我的会员就经常夸我这个,问我怎么练,那我就会说想变成这样就跟我练啊,哈哈!”(WF02)除了来自消费者的正反馈,对于处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的教练来说,满足客户的审美期待是业务能力的重要体现。“你的身材、打扮等,你整个人想要给客人什么感觉,这个是衡量一个教练能力很重要的一面,也是我自己的体会。像我每天坚持锻炼,保持自己的身材。但后来我发现,很多女客户,她就不太喜欢那种肌肉太大的教练,她可能更需要你看上去协调一点,有亲和力多一点,然后我就会朝这个方向去调整。”(WM01)
无论是健身教练还是星级酒店服务员,与生产领域相比,审美劳动者有着与前者不同的行动资源和策略。在传统生产领域中,地理空间的隔断、以体力劳动为核心的劳动过程,使劳动者与城市文化建立区分性的边界,以维续原有的自我认同。[26][27]但对于审美劳动者而言,认同的构建采取的却是相反的策略,即通过学习、洞察与实践去模糊阶层之间的象征边界,适应主流审美。
五、审美劳动者的角色整合与自我认同
虽然成为“理想的他者”是获得顾客好感与认可的要义,但从过往研究来看,随着互动的深入,审美劳动者可能会面对两重自我认同的压力。第一重压力是“劳—客”互动中从属性与自主性之间的冲突。如前所述,作为服务的提供者,审美劳动者在自我呈现上并没有自主选择权,他们的文化适应本质是劳动者与消费者之间象征权力不平等的体现,如学者在对西餐厅服务员的田野研究中,就有服务员将自己视作“穿着更为体面的奴仆”[29]。另一重压力则是标准化的表演和维持自我独特性之间的冲突。尽管审美劳动者塑造“完美他者”的努力方式不同,但以他人喜好为标准的努力又可能导致劳动者陷入千人一面的困窘,难以保持个体独特性。[28]
对于健身教练而言,业绩考核始终是压在每个人身上的大山,这自然使他们不遗余力地博取客户的好感。因而,此种“审美劳动”高压和自我认同构建之间的紧张关系自然是研究的考察重点。然而,在观察与访谈中,每当谈到工作中的压力和不安,挑战和成长都是相伴而生的主题。研究发现,与消费者的互动是健身教练作出正向自我阐释的关键。透过在“劳—客”之间建立多重身份关系,挖掘自身独特的性格特质,健身教练得以消解上述两重张力可能引发的认同危机,并成为“更好的自己”。
(一)多重身份关系的建立
除了在吸引客户时揣度消费者的审美品位,在正式获得客户信任并签订服务合约之后的课程教授过程,更是健身教练“审美劳动”的关键环节。在这一过程中,健身教练可能既是为消费者提供情感支持的激励者,也是拥有专业知识的老师或榜样。例如,在会员坚持不下去时,教练们会大声鼓劲加油,也会在会员有所进步的时候为其送上赞赏或是小礼物。
在真实的互动中,健身教练与客户的互动并不仅仅由市场规则中的权利——义务或消费——服务来定义。相反,两者互动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这种契约关系之外的熟人关系,它是消费者忠诚度的关键来源之一。消费者忠诚和信任又反过来给了健身教练持续从事“审美劳动”的动力,这在他们处理与客户的矛盾时尤为突出。“我是赚你的钱,但是人格上是平等的。我每带一个客户都是抱着交朋友的心态去的,当然会有的好,有的不好,那这就是个缘分的问题。”(WM03)除了情感支持,教练同时也扮演着老师或榜样的角色。“平时的话是很累,比如,有时候一天10节课,完了还得再去做自重训练。但是对于每个会员,我都会提供我最好、最专业的服务,如给你制定计划、教你怎么运动,甚至细微到怎么吃喝。我对他们是什么要求,对我自己就会做到加倍。当你看到会员练的都跟你很像的时候,会有无比成就感。”(WM07)
正如时尚行业一样,在风格劳动力市场中,身体在被观赏的同时,也成为后现代消费文化的文化符码,起着引导、刺激,甚至是重新教育消费者对外表的想象与再定义。这种定义依靠的是一系列专业知识的运用和自律、自我赋权等消费伦理的约束,它形塑着劳动者积极的自我认同。在上述访谈中,教练将自己对工作的全身心投入,视作与消费者构筑平等关系的砝码,教练对客户的要求更成了他们对自己的要求;许多消费者甚至直接称自己的健身教练为老师。对于健身教练来说,成为老师或激励者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服务业中“将顾客视为上帝”的权力设置,使原处于从属地位的身体和情感收获了自主性,因而也使得教练在自我的呈现中表现得更为积极。
(二)发掘独特的性格气质
健身教练在自我认同构建中面对的另一重压力就是审美文化的身体焦虑。这种焦虑表现为追求相似性与独特性的矛盾,组织文化研究将之称为组织中个体的“认同悖论”[31]。在访谈中,刚刚通过一年的职业训练、来到W健身俱乐部的教练与笔者谈论最多的就是自己在特定审美偏好下感受到的压力。“像我之前是拳击出身,我们拳击就是训练强度很大,所以要吃很多。我基本上已经习惯了那样的饮食。过来之后,就发现女教练每个都是小蛮腰、大长腿,我简直就是异类。那段时间每天都不吃主食,晚上跑5公里。”(WF01)后来在与消费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她逐渐树立了独特的竞争力,并感受到“自我突破”带来的快乐。由于接受康复训练的消费者普遍身体活动能力受到一定限制,大部分时间需要健身教练利用自身力量帮助消费者放松肌肉和关节,这对健身教练的肌力、体能和自身身体素质要求较高,而她因为更加壮实成为消费者在康复课程上的首选。此外,由于康复涉及的直接身体接触,大部分接受康复训练的女性会员都更加偏向选择女性教练作为康复指导。“因为之前是运动员,身体算是比较强壮。后来发现其实我这种是女健身教练里较少的,不论是专业上面,还是自己的体能上。现在觉得这是一种优势。你可以看我的肌肉,背部这一块,和其他几个(女性教练)是不是就很不一样?”(WF01)
不仅是身体上发掘并利用自己的性格特点,也是健身教练在情感整饰中协调相似性与独特性张力的关键。有的教练以开朗健谈和与生俱来的亲和力,成为健身俱乐部的师奶杀手;有的教练则凭借寡言的性格和俊朗的外形,收获了一众慕名而来的迷妹。总而言之,尽管健身教练的“审美劳动”过程如谢尔曼所说的那样,时刻处在“标志性的慷慨、阳光和体察入微”的状态中,但在实践中,健身教练都会通过有意识地“认同运营”为自己制作无形的个人名片。
六、“审美劳动”与自我锻造
近年来,审美劳动者自我认同的形成与变化成为备受组织管理与劳动社会学关注的新议题。[29]本文尝试以健身教练为例,通过对包括管理者、健身教练和消费者的访谈,对健身教练审美实践的观察,回应了审美劳动者自我认同的锻造历程。研究发现,对于身处健身俱乐部的教练来说,自我认同的锻造经历了“区分”与“整合”两个过程。初入健身行业的教练的自我构建是通过对消费者审美偏好的观察和模仿,培育并实践与之相适应的审美“sense”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通过观察、临摹、内化到最终的具身展演(embodiments),映衬了“审美劳动”中外型与风格的商品化的主导逻辑。尝试扮演着消费者心目中的“理想他者”,它本质上是健身教练在身体与情感上对健身产业所代表的中产与新中产消费文化的诠释、适应和演绎。然而,与以往强调劳动者自我认同的冲突不同,本文发现健身教练通过在“劳—客”互动中扮演诸如老师或激励者角色,结合自身的外形或性格特征树立独特的自我,消解了由原本高强度的身体和情感规训而产生的自我认同危机,并成为“更好的自己”。
理论上,本研究试图透过健身教练的劳动过程这一典型案例,与以往对服务业劳动者自我认同研究中存在的线性或对立的分析思路进行对话,通过呈现他们在理解与锻造自我认同中,做出的各种有意或无意的努力,为学界存在的融合或异化争论打开第三条理解路径。“审美劳动”概念弥补了以往“情感劳动”中对身体在情感操演中的重要性的忽视。在现代服务业中,消费体验需要在声、形、味等更为丰富的表象中浮现。对于服务提供者来说,“成为某一种感觉”不仅仅依托劳动者调动情感的表演,更是需要劳动者展示并成为消费体验本身,它势必造就劳动者更为复杂、多样的自我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