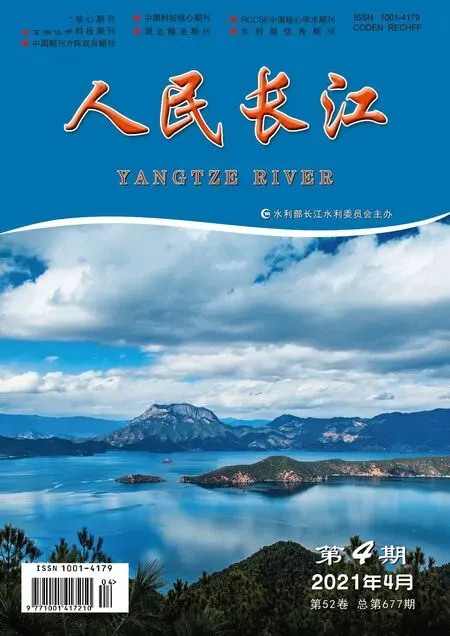河流生态研究热点与进展
柴 朝 晖,姚 仕 明
(长江科学院 河流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10)
河流是陆地和海洋联系的纽带,相比湖泊而言,具有纵向成带、急缓流并存,深潭浅滩交错等特殊的形态结构,在生物圈的物质循环中起着重要作用。在人类和社会发展过程中,过度开发河流的防洪、航运、灌溉等社会功能,破坏了河流生态系统,造成水环境恶化、多种水生物灭绝,河道生态系统退化[1]。随着人类对生存环境要求的提高,加强水资源保护,改善河流生态环境,研究河流生态越来越引起各界的关注。
河流生态研究源于水生昆虫和渔业生物学,是湖沼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以前,其研究主要集中在河流生物的形态、行为、生活史特征及生物间的营养关系上,落后于同时期湖泊生态学研究[2-3]。20世纪中后期,河流生态学研究中不断提出一系列新的概念和理论,包括地带性概念[4]、河流连续性概念[5]、溪流水力学概念[6]、流域概念[7]、洪水脉冲理论[8]、河流生产力模型[9]、自然水流范式[10]、近岸保持力概念[11]、河流生态系统结构功能整体模型[12]等。它们从不同角度构建了河流生态水文学的理论框架,并研究了自然力和人类活动作用下河流生态系统正负反馈调节关系、主要生境要素的变化、河流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河流生态流量(需水量)、河流生态修复等[13-15],促使河流生态研究逐渐发展成一个集水文学、河流动力学、生物学、景观学、地貌学等高度交叉型学科。
在广泛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对河流生境、河流生态流量、河流生态系统评价、河流生态修复等当前河流生态研究中的几个热点问题进行简要论述,并结合当前研究中的不足,提出了未来研究应加强的方面,以期能为该领域未来研究工作提供支撑。
1 河流生境
河流生境作为河流生物生存、繁衍、发育的环境,是河流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河流水环境、生物群落的组成和结构、生物多样性等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16-17]。Bisson等[18]在Montgomery和Buffington[19]河流分类方法的基础上,从流域、河区尺度、河段尺度、河道生境单元尺度对河流生境进行了分类(见表1)。但就实际应用而言,董哲仁[12]在考虑我国工业、农业和生活造成的水污染已对河流生态系统造成较大影响的基础上,提出河流生态系统的主要生境有水文情势、河流地貌、流态和水质。在以上分类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其他相关研究成果,笔者进一步明确了河流生境主要因子,如图1所示。

表1 河流生境分类方法[18]Tab.1 Classification of river habitats

图1 河流生境组成及主要因子Fig.1 River habitat composition and main factors
水文情势因子主要包括流量、洪水频率、变化时机、变化率等,其主要是在流域尺度影响河流生态系统。不同周期变化的水文情势将会引发不同的动物行为。天然情况下年周期变化的水文情势影响着鸟类迁徙、鱼类洄游,骤然涨落的洪水脉冲沟通了河槽和滩区,促进了水生生物和陆生生物之间的交流,对生物多样性具有积极的作用。而大量水利工程的建设改变了河道原有径流时空分配过程、增加了枯季的水量、影响了通江湖泊进入枯水的时机、消减了大洪水的脉冲作用等,造成下游鱼类洄游受阻、物种减少、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20-21]。随着人类对生态环境的逐渐重视和相关战略规划的提出,通过水库生态调度改变水文情势进而影响河流生态系统成为该领域研究热点[22]。如,张代青等[23]基于峰群算法建立了新丰江水库生态价值优化调度模型;长江水利委员会自2011年起组织相关部门每年在三峡水库开展促进漂流性鱼类繁殖的生态调度试验;金兴平[24]在总结长江流域水库群联合调度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集水生态调度、泥沙调度、应急调度等多目标为一体的综合调度支持系统。
河流地貌是水流作用下形成的各类侵蚀、堆积形态的总称,主要包括河型、河床侵蚀地貌和河床堆积地貌[25]。河流地貌的复杂性和空间异质性是生物多样性的基础,已成为河流健康评价和河流生态修复中的重要因素。其主要因子包括:深潭、浅滩、槽宽、弯曲度、游荡程度、河床组成等。其中,深潭和浅滩是河流地貌中最常见的地貌类型,其在不同的河流中会孕育出不一样的生态系统。如,在石质河床的山地河流中,浅滩上底栖物的密度和多样性一般高于深潭;而对鱼类而言,山地河流浅滩中急行鱼类较多,深潭中鲤科鱼类和幼鱼等较多,槽宽则主要是对鱼类运动模式有一定的影响作用[26-28]。对于不同的河型,弯曲河道由于沿程水面线及糙率的变化率相对顺直河型更低,相对更稳定,并且具有更为丰富的阶梯-深潭系统、河床断面形态、动水和静水环境(牛轭湖、漫滩沼泽)、植被等,可提供多样化的生境空间,促进各类生物的生长和繁衍,同时,其弯曲度和边滩的横向发展对无脊椎动物和植被具有重要影响[29-31]。对河床底质组成而言,粗糙河床底质一般具有极好的地貌条件和生物多样性,砂质为主的多组成河床次之,砂质河床最差[32]。
河流流态包括流速、水深、水温、水力坡度因子等。时间尺度上,这些因子随水文和气候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空间尺度上,这些因子随河流地貌的改变而变化,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流速和水深作为鱼类繁殖、生长发育的关键因子,是流态因子研究中的热点。由于绝大多数鱼类具有趋流性,且趋流性的鱼类要靠流速的存在和大小来判断游泳路线甚至洄游的路线[33],因此,鱼类适宜流速和水深是此类研究的重点。如,刘稳等[34]得到鲫鱼的喜好流速上限为0.60 m/s;杜浩等[35]根据实测资料发现体积较小的鱼喜好较低的流速和较宽的流速范围,体积较大的鱼喜好较高的流速和较窄的流速范围,规格小的鱼喜欢的水深明显大于规格大的鱼,喜好的水深范围也宽于规格大的鱼;杨庆等[36]的研究结果表明草鱼洄游的适宜流速范围是0.40~1.00 m/s;鲑鱼和鳟鱼幼鱼期的喜好流速和水深情况如图2所示[37]。但是,大型底栖动物的流速偏好与其摄食方式、生活型和形体结构相关,对水深的偏好性差异较小,另外其漂流密度随流速的增加呈减小趋势[38-40]。水温因子对水生生物的生存、新陈代谢、繁殖行为以及种群的结构和分布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控制性水库群建设及气候变化引起的水温变化而导致的生态效应方面[41-43]。

图2 鲑鱼和鳟鱼幼鱼期喜好流速和水深变化曲线Fig.2 Change curve of preferred velocity and water depth of salmon and trout in their juveniles
虽然有关河流生境对河流生态系统影响的研究很多,但研究集中在中小尺度上,且生物指标相对单一,今后应对流域尺度的生境因子变化规律及其累积影响、河流生境与多种河流生物适配性关系、多尺度河流生境质量评价等研究予以重视。
2 河流生态流量
与生态流量类似的概念有很多,如生态环境需水量、生态基流、最小可接受流量、生态需水量等。由于研究者的视角及重点不同,其内涵未得到统一,但仍提出了很多的计算方法,主要包括:水文学法(Tennant法、7Q10法、流量历时曲线等),水力学法(湿周法、R2CROSS法),栖息地评价法(IFIM模型、CASIMIR模型),整体分析法(BBM法)[44-47]。这些计算方法主要是考虑河道物理形态、所关心的鱼类、无脊椎动物等(整体法考虑整个生态系统)对流量的需求来确定最小或最佳的流量。
国内外研究者在应用或改进这些计算方法上做了大量的研究。如,Meier等[48]在瑞士布瑞诺河水电站生态流量确定中采用了栖息地评价法;Angela等[49]基于生态学家和水文学家的经验,在深入调研了鱼类生活习性的基础上,提出了DRIFT法,并应用在莱索托河上;King等[50]基于澳大利亚穆雷河实际情况建立了适用于多物种的非生物手段刺激鱼类产卵的生态流量计算方法;倪晋仁等[51]提出了生态环境用水量及其阈值确定的各项原则;郭文献等[52]采用改进的河道湿周法计算了长江中下游各河段的最小生态流量;洪思杨等[53]采用栖息地评价法计算了大渡河流域的最小生态流量;尚文绣等[54]结合栖息地模拟与水文参照系统特征值,建立了一种面向河流生态完整性的生态需水过程评估方法,并将其应用在黄河下游生态流量计算中。对于水电工程下泄生态流量而言,以2006年颁布的《水利水电建设项目河道生态用水、低温水和过鱼设施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指南(试行)》为节点,其计算方法从简单的水力学和水文学方法逐渐向生态水力学方法和生境模拟法转变[55]。
虽然关于生态流量的计算方法及应用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存在生态指标(鱼类为主)选取单一,对不同地区、不同流域、不同类型河流、同一河流不同河段的生态需求考虑不足,计算结果以最小生态流量为主等问题。2020年4月17日,水利部印发了 《关于做好河湖生态流量确定和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河湖生态流量内涵明确为:为了维系河流、湖泊等水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需要保留在河湖内符合水量要求的流量(水量、水位)及其过程。今后的研究应在多目标河湖生态流量计算方法、分区分时生态流量确定、生态流量动态过程、生态流量管理机制等方面予以重视。
3 河流生态系统健康评价
水量的减少和水质的恶化造成河流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破坏,进而影响河流供水、纳污、防洪、航运、景观等自然和社会功能的发挥,不利于河流及周边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河流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是河流生态环境质量评估和河流综合治理考核中的重要环节,是河流生态研究中的热点之一。
国外河流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最初采用河流水质理化指标作为评价工具,而后考虑到水质理化指标不能全面反映河流生态系统的状况,提出了生物指标才是河流生态系统状况评价的主要指标[56]。随后,国外研究者提出了一系列河流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方法,可概括为指示物种评价法和多指标评价法2种。指示物种评价法(如IBI法)是采用代表性生物来反映河流生态系统的状况,应用较多的主要有藻类、底栖动物和鱼类。如,Virtanen等[57]发现硅藻可作为指示物种表征河流生态健康状况;Cheng等[58]采用鱼类物种丰富度为指标分析了流域健康。多指标评价法是采用一系列水文、生物、物理化学等多种类型指标从不同角度和深度评价河流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如,White等[59]提出的澳大利亚溪流状况指数法(ISC);Robert等[60]提出的瑞典农业景观区域河岸带与河道环境评估法(RCE);Pinto等[61]基于因子分析提出的河流健康评价方法。
国内河流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研究工作相对较晚,实质性的研究从2004年开始。评价方法基本借鉴国外的指示物种评价法和多指标评价法。但由于我国对河流的人工干扰相对较多,指示物种评价法无法充分全面地反映河流生态系统健康的变化,而且无法考虑河流生态系统的社会和经济功能,因此,国内学者采用多指标评价法针对长江、黄河、辽河、珠江等河流建立了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如,2005年蔡其华[62]初步提出的健康长江评价体系开创了国内系统化河流健康评价体系的先河;刘晓燕等[63]提出了黄河健康指标体系。而后,学者们利用建立的评价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判法、灰色关联度法、TOPSIS法、主成分分析法等对国内众多河流进行了健康评价(见表2)。但由于不同学者的研究方向及领域不同,所关注的河流生态系统功能不同,选取的指标、计算方法、指标标准的制定等均有所不同,评价体系的应用仍存在一定的局限,今后应开展长期的河道生态因子监测、河流生态健康评价标准的制定、大尺度河流健康评价等研究。

表2 中国典型河流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体系及评价结果(改自文献[64])Tab.2 Ecosystem health assessment system and results of typical rivers in China
4 河流生态修复
4.1 理论研究
1938年Seifert 提出的“近自然河溪治理概念”开启了河流生态修复的先河,但实际研究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提出了诸如亲近自然河流、生态工程、生态河堤、多自然型河流、自然型护岸、自然河道设计等理念[65],并将其应用在密西西比河、斯凯恩河、莱茵河、坂川河等河流整体生态修复中,实现了流域尺度下河流生态修复的成功。整体而言,国外关于河流形态修复的研究较多,对修复过程和机理的研究相对较小。
国内对河流生态修复的研究起步较晚,始于1999年“大水利”理论的提出。而后,国内学者基于国外相关研究成果,提出了一系列适合我国国情的河流生态修复概念和理论,如,高甲荣等[66]提出了河溪近自然治理的基本模式;董哲仁[67]提出了生态水工学概念;王超等[68]提出了五位一体的城市水生态系统建设模式;达良俊等[69]提出了近自然型人工水景观建设理念。2005年后,国内河流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进入应用实践阶段,各地采用河湖水系连通、生态护岸、调水补水、河流整治等措施改善河流生态,相关理论研究则以河流生态修复模式和方法研究为主,如,张玮等[70]提出了顺直河道水生态修复方法;叶春等[71]在对太湖湖滨带进行划分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类型湖滨带生态修复模式;陈小刚等[72]研究了黑臭河道的生态修复方法。
4.2 河流生态修复技术
河流生态修复并不是简单将河流恢复到原始状态,而是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法将其受损功能恢复到既能满足河流自身发展规律又能适应人类社会发展需要的状态。因此,不同阶段河流生态修复的目的和任务是不同的。对于自然阶段的河流,应当尽量保护和维持现状;对于工程控制阶段的河流,应尽量减少工程对水量、水质、水生生物的影响,使工程与生态系统和谐相处;对于严重污染阶段的河流,首先应完成污染治理,然后根据河流特点、河流定位、区域发展要求等确定河流主功能,进而进行针对性的修复。
根据修复对象可将生态修复技术分为:水质生态修复技术、水量生态修复技术、河道形态修复技术、水生生物修复技术、流域生态修复技术。水质修复主要是针对受污染水体采用生态岛(浮床)、人工湿地、机械除藻、稳定塘、底泥疏浚等手段和方法,使水质有所改善,目前研究集中在各种技术的研发和效果分析上,如童伟军等[73]分析了不同生物促生剂对垂直流人工湿地作用的影响。水量生态修复是采用生态输(调)水、生态调度、河湖连通等方式补充河流水量,在短时间内降低水体污染指标浓度,改善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研究重点为输水、调度及连通方式优化及其影响评价。如,Xu等[74]利用三维生态模型提出了一种生态友好型的调度方案。河道形态修复主要是对河道的平面、横断面形态等进行改造以恢复河道的多样性,相关研究主要关注河道平面、横断面、滨水带的形态设计,护岸形式及材料的优化等,得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成果,如复式断面是比较理想的横断面形式[68];植物、自然材料和土木工程相结合生态护岸技术等[75]。水生生物修复主要是对河流中的植物、动物进行修复,其中,植物修复是根据景观要求、河流地貌特征、水环境状况等在滨水带和水体中布置合理的植物群落;水生动物的恢复是根据食物链原理营造生物群落多样性,通过投放鱼类、虾类、河蚌等底栖动物,构建“水生植物-微生物-藻类-水生动物”食物链,实现水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这类技术一般与其他技术联合使用[76]。流域生态修复是指对河流从源头到河口有径流注入的所有水文单元进行修复,是一个集工程和非工程措施的综合技术。如,王思凯等[77]借鉴莱茵河综合治理方案提出了长江流域生态治理的方案,翟文娟等[78]制定了岷江上、中、下游生态修复措施。
4.3 河流生态修复后评估
河流生态修复后评价是对河流生态修复工程的有效性进行跟踪监测和评价,据此提出补救方案或改进措施。国外主要是采用指示物种法和指标体系法进行后评估,如,Rita 等[79]以鱼类为指示物质评估了Kamisaigo河生态修复工程的效果;Alexander等[80]选择河道内栖息地、水质、河道形状重塑、岸边带4个指标建立了河流生态修复后评价体系。借鉴国外研究成果,近年来我国也开展了一系列河流生态修复后评估研究,如,董晓军等[81]从河流生态效应、经济可行性和综合利用3方面构建了河流生态修复后评价指标体系模型;顾毓蓉等[82]结合浮游生物完整性和因子分析从生物完整性角度对松雅湖生态修复工程进行了评估。
河流生态修复研究已由起初的理论探讨、整治框架阶段向具体的修复方法手段和技术转变,且河流生态修复后评估工作也逐渐得到重视,但大多研究是模仿国内外已有案例的尝试和探索,今后应在多种修复技术的优化组合、流域整体生态修复、河流生态修复后评估指标和标准的确定、修复后的生态系统动态演变过程等方面加强研究。
5 结 语
目前,国内外关于河流生态的研究较多,除了上述4个方面,近期方红卫等[83]提出的生态河流动力学也是河流生态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相比河流生态学而言,生态河流动力学更注重泥沙输移及表面特性对水生态环境的影响,侧重中观和尺度理论体系的建立。但由于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人类干扰的不确定性等,给河流生态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今后应在全面考虑河流自身和社会属性的前提下,结合多学科理论和方法,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1) 河流生境方面,加强流域尺度的生境因子变化规律及其累积影响、河流生境与多种河流生物适配性关系、多尺度河流生境质量评价等的研究。
(2) 河流生态流量方面,应在多目标河湖生态流量计算方法、分区分时生态流量的确定、生态流量动态过程、生态流量管理机制上加强研究。
(3) 河流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方面,应进一步开展长期的河道生态因子监测、河流生态健康评价标准的制定、大尺度河流健康评价等研究。
(4) 河流生态修复方面,应在多种修复技术的优化组合、流域大尺度整体生态修复、河流生态修复后评估指标和标准的确定、修复后的生态系统动态演变过程等方面加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