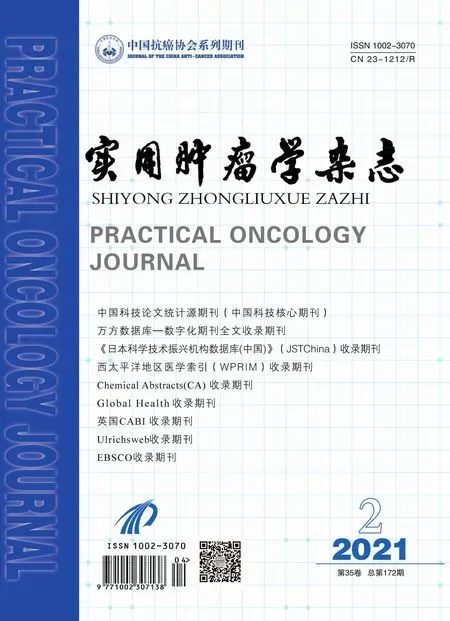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在外阴鳞癌和外阴上皮内瘤变筛查中的预测价值
熊巍 王丹 王瑾晖 张颖 曹冬焱
外阴癌是妇科第四大常见肿瘤,大约有90%的外阴恶性肿瘤为外阴鳞癌[1]现在学界普遍认为外阴上皮内瘤变是外阴鳞癌的癌前病变,外阴鳞癌是由各个时期的外阴上皮内瘤变发展而来的[2]。由癌前病变发展成癌主要取决于肿瘤与宿主炎性反应[3]。全身炎性反应被认为在外阴鳞癌变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4]。同时炎症也会造成外周血中白细胞的改变,最常见的就是中性粒细胞增多伴有相对的淋巴细胞减少[5-6]。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已被证明是一些癌症和癌前病变的全身炎症和免疫学指标[7-8]。然而,其对外阴鳞癌的预后价值尚不清楚。只有少数研究报告术前NLR与外阴鳞癌的淋巴结转移有关[4]。迄今为止,还没有研究评估过NLR是否与外阴病变的活检病理特征有关。本研究旨在探讨NLR是否可以作为一个辅助鉴别的指标为外阴鳞癌与其癌前病变提供一些诊断价值。
1 材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2012年12月—2020年6月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所有需要活检的外阴病变的患者进行研究。该研究符合《赫尔辛基宣言》的伦理标准,并得到了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纳入标准:(1)所有临床上可疑有硬化性苔藓(LS)、外阴上皮内瘤变(普通型外阴上皮内瘤变:隆起的界限清晰、不对称的病变;从白色、湿疣样变为棕色的病变;分化型外阴上皮内瘤变:隆起的白色斑块、溃疡性或红斑的病变)和外阴鳞癌(溃疡性病变)的患者;(2)做过一次或多次外阴活检或切除;(3)外阴活检病理诊断符合国际外阴阴道疾病研究学会诊断标准(ISSVD,2011)。外阴鳞癌按国际妇产科联合会(FIGO 2009)标准分类。
排除标准:(1)炎症性或自身免疫性疾病;(2)急性或慢性感染性疾病;(3)血液系统疾病;(4)可能影响外周血细胞的其他恶性肿瘤;(5)使用皮质醇或β受体激动剂的患者;(6)外阴其他病理类型的恶性肿瘤,包括术前基底细胞癌、外阴黑色素瘤、前庭腺癌等;(7)数据缺失的患者。
本研究共收集401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排除血液病4例,合并其他恶性肿瘤9例,活检前血常规缺失2例,剩余共有386例患者被纳入研究。根据病理组织学结果将患者分为三组:(1)良性病变:外阴硬化性苔藓组(LS);(2)外阴癌前病变:外阴上皮内瘤变组(包括普通型外阴上皮内瘤变和分化型外阴上皮内瘤变);(3)外阴恶性病变:外阴鳞癌组。其中LS组173例,外阴上皮内瘤变组87例,外阴鳞癌组126例。87例外阴上皮内瘤变患者中81例为普通型外阴上皮内瘤变(u-VIN),6例为分化型外阴上皮内瘤变(d-VIN)。126例外阴鳞癌组中,Ⅰ期58例(46.0%),Ⅱ期26例(20.6%),Ⅲ期37例(29.4%),Ⅳ期5例(4.0%)。肿瘤分级为G1级97例(77.0%),G2级20例(15.9%),G3级9例(7.1%)。
1.2 研究指标
临床病理结果和实验室数据均来自原始医疗记录。记录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年龄、体重指数、吸烟状况、症状和组织病理学数据。收集实验室检查相关基线资料,包括白细胞计数(WBC)、中性粒细胞绝对值、淋巴细胞绝对值、血红蛋白水平(Hb)、平均血小板体积(MPV)、血小板分布宽度(PDW)、血小板绝对值(Plt)。外周血血常规在活检或手术前一周内,在患者未接受任何治疗时采集。两个外周血相关的炎症指数:NLR和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R),使用血液学参数(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和血小板的绝对值)计算:NLR=中性粒细胞绝对值/淋巴细胞绝对值。PLR=血小板绝对值/淋巴细胞绝对值。
1.3 统计学方法
运用SPSS 22.0统计软件包分析数据,计量资料满足正态性和方差齐性时以均数±标准差表示,两组间比较使用t检验,多组间比较使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用Bonfferoni法进行校正。分类变量采用χ2检验和Fisher精确检验比较。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NLR对外阴病变活检结果的鉴别作用,计算灵敏度和特异性,确定NLR的最佳分界值。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活检病理结果(癌前病变与恶性病变)的影响因素。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特征
LS组、外阴上皮内瘤变组和外阴鳞癌组的平均年龄分别为58.2±10.6岁、49.2±14.5岁和63.8±12.7岁,外阴鳞癌组年龄明显高于外阴上皮内瘤变组(P<0.001)。与LS组相比,外阴鳞癌组中吸烟人数所占的比重更高,有统计学差异(P<0.05)。比较病变大小发现,外阴鳞癌组病灶(4.6±2.8 cm)明显大于外阴上皮内瘤变组(2.2±1.2 cm)和LS组(3.0±2.3 cm)的病灶(P<0.001),但三组间在BMI和肿瘤位置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1)。
2.2 外阴病变的血液学参数比较
外阴鳞癌组的平均中性粒细胞绝对值明显高于LS组和外阴上皮内瘤变组(P=0.001),外阴鳞癌组的平均淋巴细胞绝对值显著低于LS组和外阴上皮内瘤变组(P<0.001)。三组间两两比较发现外阴鳞癌组的平均NLR明显高于LS组和外阴上皮内瘤变组(P<0.001)。然而,LS组、外阴上皮内瘤变组和外阴鳞癌组的WBC、Hb MPV、PDW、Plt和PLR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2)。
在对外阴上皮内瘤变的亚组分析中,普通型外阴上皮内瘤变(u-VIN)和分化型外阴上皮内瘤变(d-VIN)组的年龄存在统计学差异,而中性粒细胞绝对值、淋巴细胞绝对值、WBC、Plt、NLR和PLR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3)。

表1 外阴性病变活检患者的临床特征

表2 LS、外阴上皮内瘤变和外阴鳞癌三组间血液学参数的比较

表3 外阴上皮内瘤变组NLR及其他血液学参数的亚组分析
2.3 外阴性病变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中,年龄≥65岁、NLR升高和病灶>2 cm与外阴恶性病变明显相关,而PLR、病变位置、吸烟状态与病理活检结果无关。其中NLR升高病理活检为恶性病变的风险最高(OR=4.84,95%CI:4.17~7.14,P<0.001)(表4)。

表4 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评估血液学参数和外阴癌前/恶性病变的关系
2.4 血液学参数对外阴病变病理结果的预测效果
对于外阴上皮内瘤变和外阴鳞癌的鉴别,NLR显示了很好的预测价值(AUC=0.79,95%CI:0.76~0.85,P<0.001),NLR的最佳分界点为3.01,敏感性为88.2%,特异性为67.8%,但是NLR不能很好地区别LS和外阴上皮内瘤变(AUC=0.551,95%CI:0.46~0.64,P=0.254)(图1)。

图1 ROC曲线分析NLR对外阴病变的诊断价值Figure 1 Diagnostic value of NLR in vulvar lesion with ROC curve analysisNote:a.NLR may predict the presence of vulvar squamous cell carcinoma(VSCC)from VIN with a high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b.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NLR is extremely low in discriminating vulvar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VIN)from lichen sclerosus(LS)
2.5 随诊情况
我们的资料中记录了71例外阴上皮内瘤变患者在随访期间监测病情复发和进展的信息。中位随访时间为51个月(6~78个月)。11例(15.5%)复发,55例(77.5%)治疗后未发现疾病迹象。5例(7.0%)外阴上皮内瘤变患者在随访中进展为外阴鳞癌。这些患者由外阴上皮内瘤样病变初次治疗后进展为浸润性癌的中位时间为4.3年,患者处在外阴上皮内瘤变期的平均NLR(1.75±0.36)低于外阴鳞癌期(2.95±1.47)(P<0.01)。
3 讨论
外阴鳞癌和外阴上皮内瘤变常造成患者严重而持久的瘙痒、疼痛和性精神障碍。近10年来,外阴癌的患病人数增长了6%[9],引起越来越多的临床医生的关注。累积统计显示,外阴上皮内瘤变患者发展成外阴鳞癌的风险为3%~10%[10]。一项挪威基于大规模人群的研究表明,外阴上皮内瘤变术后切缘阴性并不能阻止其进展为侵袭性外阴鳞癌[11]。因此,长期有效地监测对外阴上皮内瘤变患者,甚至是术后切缘阴性的患者至关重要。但不像宫颈癌有成熟的宫颈涂片和HPV检测作为筛查工具,外阴癌或癌前病变目前尚没有标准地筛查手段,对其监测仅能依靠外阴视诊。但是,因为这些病变常使外阴皮肤萎缩或阴唇结构变形,造成视诊困难,不易判断。通常临床大夫只能依据活检对外阴上皮内瘤变和外阴鳞癌进行组织学上的鉴别。因此,女性外阴上皮内瘤变患者很有可能需要在长期随访中进行反复活检。但及时的活检在临床上仍十分有限。大约30%的外阴癌患者因为活检被耽误而到病变发展到中晚期才被诊断[9]。因此寻找一种创伤小、有诊断价值的生物学筛查工具显得格外重要,这不但可以减少患者的不适,增强其依从性,还可以帮助临床医生对慢性外阴疾病患者做出正确的诊断,以便及时选择活检。
在临床实践中,评估肿瘤的全身炎症反应可能较为容易操作和更具成本效益比。近年来,NLR被认为是一种很好的评估肿瘤炎症反应的生物学指标。有大量研究证据表明妇科癌症患者NLR与肿瘤特征之间存在密切联系[12]。Baert等[13]发现NLR升高与卵巢癌的总生存率下降显著相关。Jonska-Gmyrek等[14]报道了治疗前NLR高预示着宫颈癌患者生存期较短,NLR可考虑作为宫颈癌患者预后评估的新指标。Temur等[15]的研究提示NLR对子宫内膜癌淋巴结受累和宫颈浸润具有预测意义。然而,尚未有一项研究评估NLR在外阴癌前病变和癌性病变中的鉴别价值。在我们的研究中,外阴鳞癌患者的NLR值比外阴上皮内瘤变患者高,NLR升高可能对外阴鳞癌有一定预测价值。此外,我们在对于外阴上皮内瘤变患者的随访期间发现有5例患者发展为浸润性鳞癌。与外阴癌前病变阶段相比,患者在外阴鳞癌期间的NLR水平明显升高。我们的发现为证实外阴病变患者的NLR值与活检病理特征之间存在相关性提供了依据。
炎症对癌症的发生和发展的重要作用可能是这些结果背后存在的机制[4]。外周循环中性粒细胞水平会随着肿瘤的进展而增加。中性粒细胞参与免疫抑制,从而支持肿瘤生长和转移进展。中性粒细胞通过分泌多种趋化因子和细胞因子直接促进肿瘤的生长,并促进肿瘤微环境中其他肿瘤支持细胞的招募[16]。另一方面,淋巴细胞是宿主抵抗肿瘤细胞的组成部分,淋巴细胞减少也提示了患者处于免疫抑制状态。NLR高表明机体处于一个支持肿瘤发生的微环境,而抗肿瘤的免疫反应相对较差。在这种情况下,机体中生长因子、血管生成因子和其他促肿瘤信号因子增加,从而促进肿瘤的进展并恶化[4]。与这些研究一致,我们发现不同水平的NLR反映了外阴病变引起了全身不同程度的炎症反应。本研究结果提示外阴鳞癌患者可能出现了持续的免疫功能紊乱,而癌前病变的外阴上皮内瘤变患者并没有出现类似情况,这可能是癌前病变患者的病变相对局限和肿瘤负荷较低有关。这些结果也为之前的研究所提出的NLR可能是癌前炎症状态和癌性免疫状态之间的标志物的理论提供了有利支持。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其回顾性的单中心研究设计,但我们使用严格的统计学方法使混杂因素最小化。
本研究首次评估了NLR在区分外阴癌前病变和外阴恶性肿瘤中的作用。NLR是一种廉价、重复性好、可广泛应用的血液检测方法,有望成为外阴病变患者管理、危险分层和早期发现高危患者的快速、相对准确的筛查工具。由于这一研究领域是一个新领域,在临床实践中引入NLR评估预测外阴鳞癌之前,需要对大量患者进行前瞻性多中心研究,以全面确定其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