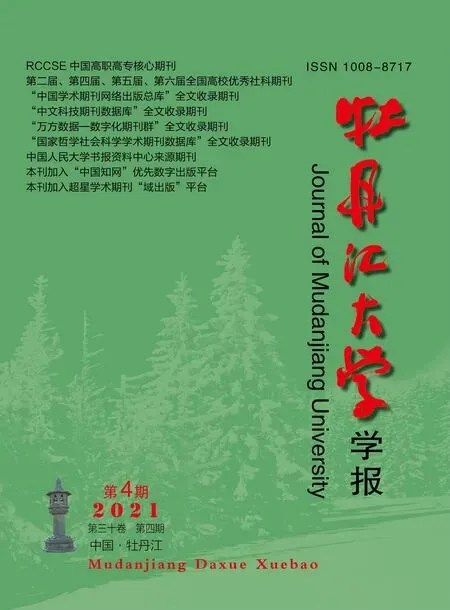1918-1939 德国的民主化、民族主义和它的战争
赵 伟
(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引言
自1939 年9 月1 日,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六年后柏林被盟军攻破,德国战败。二战,这个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章为无数学者所研究,人们研究它的起源、发展和影响,但现在大多数的研究多以1933年希特勒上台为起点,在论述战争如何爆发以及怎么爆发时,常常只追溯到1933 年,再往前就只论述巴黎和会,很少有人来分析战争爆发前的魏玛共和国的政治演变和战争的关系。曼斯菲尔德(E.D.Mansfield)和斯奈德(F.Snyder)认为,在过去两个世纪的统计资料表明,民主化国家(指向民主政体转化的国家)较那些政体未变动的国家更具有侵略性,这种倾向在民主化发生一年中最弱,而在十年时最强。[1]而当时的魏玛共和国就处在这样一种民主转型期内。笔者将研究背景置于魏玛共和国内,通过分析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化、民族主义进而导出它们与战争的关系。
一、德国民族主义形成的背景
徐迅认为,民族主义现象是指以“民族”为符号、动力和目标的社会、政治、文化运动,或以民族国家为诉求的意识形态,或以文化传统为依托的情节和情绪。同时他认为,民族主义的形成要经历三个阶段,即:(1)文化阶段:变现为收集和整理民俗,弘扬文化传统。(2)意识形态阶段:表现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进行社会动员,标志民族意识的觉醒。(3)政治诉求阶段:表现为文化复兴转变为政治诉求,要求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2]
德国的民族主义形成与传统的欧洲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德国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环境,使其民族主义从形成和发展来说注定要走一条不同于英国、法国的民族主义。三十年战争后,随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德意志分裂为大大小小几百个邦国,英国和法国那种在统一的王朝下萌生的民族主义在德意志的土地上销声匿迹,那种由边缘向中央的向心力对德意志来说可谓奢侈。“德意志,它在哪里?”来自德国诗人歌德的叩问,显示了德国民族主义自身的特殊性——一种分裂背景下渴望统一的诉求。就是在这个背景基础上德国的民族主义开始渐渐萌芽,在其自身特殊的轨道上慢慢生长,并且经历了不同的时期。
笔者在分析德国民族主义的形成背景时将意识形态阶段和文化阶段放在一起分析,因为两者往往是相伴而随同时发生的,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同时,在分析政治诉求阶段时,笔者并不打算着重于德意志民主国家的形成,而是将重点放在德意志民族国家形成后,国家内部的政治诉求和它特殊的民族主义表现。所以,在此篇文章中笔者将德意志民族主义形成的阶段划分为两个,即:文化方面的文化民族主义阶段,和政治方面的对立民族主义阶段。
(一)文化民族主义阶段
就德国民族主义的萌芽来说,17 ~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无疑对德国的民族主义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当时的德国并未统一,欧洲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使得德国分裂为大大小小上百个邦国,并且这些邦国又是分属于新教和天主教这两大不同的教派。可以说当时的德国在地域上和文化上都处于分裂的局面,由此导致当时德国的文人们转而向文化领域谋求民族主义的发展,由此形成了德国典型的文化民族主义的特点。这种鼓吹德意志民族至上的文化民族主义使得德国衍生出了强烈的民族至上论和种族优越论,他们相信德意志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由此德意志民族对其他民族的征服是合法的且应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发展成为“生存空间理论”,为德意志第三帝国的侵略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3]
(二)对立民族主义阶段
19 世纪随着崛起的普鲁士通过三次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并于1871 年建立了德意志第二帝国。在这一时期,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伴随着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以及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传播,德国的工人阶级中形成了一个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庞大群体。为了预防这些潜在的革命威胁,俾斯麦首相及其继任者着力于培养一个大众的政治支持基础,他们将眼光放在了新教中产阶级身上。德国的贵族统治者和经济统治精英将鼓噪富有进攻性的德国民族主义作为维持他们的优势地位的战略之一,他们将自己的政治基础固化在民族主义这个排外性的基础之上,将工人、社会主义者、天主教徒和波兰人描绘成德国人民的敌人。这种利用民族主义分裂人民的行为,使得中产阶级无法形成一个有利的同盟,向威权主义的德国叫板,软弱的中产阶级对充分民主的政治体制的诉求被无情的打压。[4]这种人为形成的对立民族主义在俾斯麦的威权主义统治下运行良好,形成了“钢铁黑麦”联盟,成为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政治统治的基础。然而,在民主化进程中的魏玛共和国,威权主义的丧失使得共和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约束这种对立的民族主义。严重对立分化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最终成为了魏玛共和国社会动荡的诱因和新的威权主义滋生的土壤。
1918 年以前德国的民族主义大致就表现为这两个基本的特征,这两个基本特征在时间上是延续的,并且彼此不具有相互替代性,相反,1918 年时德国民族主义所表现的这两个基本特征同时出现在共和国的土地上,并且夹裹着德国人民像一匹马力巨大发动机走向了1939 年秋天的战争,而生不逢时的德国民主化将成为这个机器的点火器。
二、德国的民主化和它的合法性困境
1918 年底,持续了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渐入尾声,随着美国的参战,德国在西线的境况越来越差,战线开始不断向后撤离。与此同时,在国内持续多年的战争使得德国经济陷入困境,民生也是一落千丈,国内民众的反战情绪越来越强烈。德皇威廉二世为了应对这种危机,不得不改制君主立宪并思考终结这场战争。然而一个月后一场革命就在德国爆发,威廉二世被迫退位,德意志帝国土崩瓦解。随后德国开始了从君主专制向民主共和的艰难转型。
德国民主化并不是一种自发生成的,与英国开始于17 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在持续数十年的大革命最终实现民主化不同。德国的民主化更具有突然性和短暂性,民主革命好像一夜之间就爆发了,随后又在极短的时间内民主政府就建立了起来,在帝国体制内被打压数十年的社会民主党一跃成为魏玛共和国的执政党,它的领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出任了国家总理,伴随着《魏玛共和国宪法》的出台和民主议会的建立,共和国的一切好像都步入了正轨,然而真的是这样吗?看似坚不可摧的民主共和国他的背后还蕴含着巨大的合法性危机。
合法性意味着被统治者对统治的承认,那么,魏玛共和国合法性被世人所认可吗?答案似乎不是那么乐观。1918年“十一月革命”以来,共和国虽然结束了旷日持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建立了民主议会并且颁布了《魏玛宪法》,然而成功的喜悦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打破。巴黎和会上对战败的德国所做的严酷的惩罚,给了德国人民当头一击,沉重的负担压在德国人民身上,很快他们就找到了自己的发泄对象,那个签订条约的人——共和国政府。其实,早在共和国还未建立的时候,德意志帝国军统部的将军们就已经谋划着寻找战败的替罪羊,他们谋求建立一个由社会民主党、天主教中央党、自由民主党组成的议会大多数政府,并由他们与协约国进行谈判,承担本应该由军国主义——保守主义的领导集团承担的战败后果。[5]虽然,他们组建立宪制政府的行为在“十一月革命”中遭受了失败,但是他们的目的在巴黎和会后达到了,这也是为什么上世纪30 年代原德意志帝国陆军元帅兴登堡能够出任德国总统的原因。同时,魏玛共和国宪法本身也有很大的漏洞,宪法赋予了总统过高的行政权力,使得总统能够利用紧急状态法令获得巨大的权力,成为实际上的独裁者。事实上在魏玛共和国末期,布吕宁、冯·帕彭、施莱歇尔与阿道夫·希特勒共四位总理政府实际上都是由总统选出来的独裁政权。宪法这个本应该成为自由民主保护伞的工具,最终成了魏玛共和国专制主义的源泉,这恐怕是当年那些宪法修订者所没想到的。与此同时,经济上的危机也动摇了魏玛共和国的民意基础,巨额的战争赔款和战后崩溃的经济,使得魏玛共和国的经济陷入危机,失业率高居不下,通货膨胀严重,加上法国、比利时对鲁尔区的占领使得德国的经济雪上加霜,美国提供的经济援助所造就的短暂繁荣被1929 年的经济大危机无情摧毁,经济上的危机最终导致了政治上的动荡,人们普遍对共和国抱有不信任感,并寄希望于专制主义和它强大的国家能力,使得国家有能力来改变这种状况。

7.1%至1932.07.31 6.1%从1932.07.31 至1932.11.06 8.9%从1932.11.06 开始1932.12.03 库尔特·冯·施·歇尔 8.9%1933.01.30 阿道夫·希特勒 42.5%至1933.05.05 52.5%从1933.05.05 开始1932.06.01 弗朗茨·冯·帕彭
魏玛共和国的合法性困境,成为了德意志民族主义滋生、发展的温床,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危机,使得德意志的民族主义蓬勃发展,同时这种民族主义的发展又进一步削弱了共和国的统治力。恶性循环中的魏玛共和国,统治的合法性不断丧失,社会分裂加剧,极端化倾向极其严重,极端对立的民族主义分裂了共和国的选民, 最终驱使他们选择了希特勒的极权主义统治。
三、德国的民主化和它的对立民族主义
俾斯麦在建构德意志帝国时,帝国逐渐形成了几个不同的集团,德意志的政党也从这些处于分裂状态的社会环境中寻找自己的支持者。其中较为典型的有,易北河以东的新教农业环境由大地产占统治地位的保守主义;以新教城市地区的中产阶级绅士社会为主的民族自由主义;以所有阶级中天主教徒的大多数为主的中央党;以及受工人和手工工商业者支持的社会民主党。
保守党的社会基础大多为帝国的统治阶层,即容克地主阶层。他们往往拥有土地,出任帝国的官员,抑或是在军队中拥有较高的地位。他们组成了帝国的既得利益者,主张尊重传统,维护君主统治,并且反对革命。在经济上他们主张发展农业,并且极端反犹。他们被称作“钢铁黑麦”联盟。

表2 威廉德国时代的精英和大众联盟1890-1914[7]
自俾斯麦时期的人为造成的选民分裂,到了魏玛共和国时期显得更加明显。彼时,这种民族对立作为俾斯麦统治的一种手段,在他的强权统治之下被很好地控制在了一定范围之内,并且成为其政治统治的工具。然而,在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下,这种局面被打破,开放的民主选举制度提高了大众的政治参与度,社会动员被普遍调动起来,原来受俾斯麦打压的政党和阶层一跃成为了议会的大多数。

表3 魏玛共和国:各党得票率[7]111
在1919 年-1933 年的魏玛德国,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巴黎和会后巨额的战争赔款使得德国政府背上了长期债务,加上对德国军事发展的限制,使得德国的军事工业备受打击,工厂停工,失业人数达一百余万人,与此同时从战场上归来的士兵的就业又成了社会问题。然而,雪上加霜的是,法国和比利时为了督促德国执行条约,出兵强占了鲁尔工业区——德国的经济命脉,由此德国当局号召鲁尔工业区中的工人罢工,并且大量的印制钞票最终导致了德国经济的崩溃,马克大幅度贬值,国内民不聊生,后来虽然继任的总理施特雷泽曼通过改革货币制,使得德国经济步入正轨,然而好景不长,几年后全球大萧条的到来,又一次使得德国经济崩溃,而施特雷泽曼自己在当年病逝。
可以说在魏玛共和国的历史中,绝大多数时间都伴随着经济危机,这种经济上的危机对工薪阶层的影响相对于有固定资产的阶层来说要大得多,由于失业率的居高不下,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民众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感到失望,民族主义情绪在社会群体中蔓延,各种民族主义组织犹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他们对现有的政治体制发起攻击。民主化所产生的软弱的魏玛共和国的中央权威、不稳定的政治联盟和强有力的大众政治这样的综合征,它把新的社会集团和阶层带上了政治舞台,政治领袖难以找到调和利益冲突的途径,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治联盟而依赖于短期凑合或者不顾后果的赌博,而新进精英也需要赢得大批支持者以巩固自己软弱的地位。这样,他们往往都通过呼唤民族主义来维系他们本来难以控制的政治联盟。
原本就极为对立的德国民族主义到了此时已经难以调和,传统的德国民族主义的对立,在俾斯麦的威权主义统治之下能够被很好控制,政治体制运行良好,然而,在民主化过程中的魏玛共和国,由于传统的国家能力的削弱,普遍的公众参与的提高,这种民族主义分裂被扩大化,民族主义的对立冲突增多。这种对立分裂造成了魏玛共和国离心性的民主政治体制,使得共和国在民主政体下的国家能力受到削弱,政府无法解决当时社会上的很多问题,政府效能的缺失使得共和国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和制度危机。[6]210林茨认为:如果民主政体本身无法解决危机,它的反对者们会把权威统治作为可替代性的解决方案。当时的魏玛共和国就是这么做的,在共和国统治的末期,依靠总统的紧急状态法令,共和国步入了民主政体下的权威统治之中,最后,在1933 年的选举中,人们把选票投给了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个极端民族主义的政党,他们早就在正式场合宣称要结束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并且在他们上台之后也很快兑现了诺言。
人们为什么将选票投给纳粹党?细看一下整个魏玛共和国历史不难发现,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右翼的民族主义政党的得票率一直在三分之一左右,这些政党大多代表了大商业利益者和传统的保守精英。魏玛共和国晚期的经济、政治危机使大中产阶级选民相信,这些精英领导的民族主义政党与他们同处于一个困境中,由此,小城镇的草根志愿团体的绵密网络纷纷转向一个民粹主义政党,这个政党使他们看上去属于当中的一员[7]112,同时德国的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乡村阶级等各种利益集团也不断地团结到这个极端专制主义的政党身边,原本对立和分裂的德国民族主义,在此刻被团结到了一起,他们对民主政体已经丧失信心,寄希望于重新建立那种俾斯麦式的专制主义来增强德国的国家能力,从而结束这种分裂的局面,实现经济、政治的稳定。
在纳粹政府执政之后,他们很快对民主制度发起进攻,他们首先控制了德国的警察系统,随后,通过国会纵火案打击共产党,并且确立了纳粹党的一党独裁制度,取消了公民权利。至此,原本民主的魏玛共和国转变成为了纳粹党的一党独裁制度。纳粹党借助这种专制制度下的强大的国家能力,对当时德国的经济、政治危机采取了快速而有效的行动,德国的政治逐渐稳定,经济逐步复苏,并且在战争前夕达到顶峰。然而,这种建立于狂热的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第三帝国,其往往要复归于这种民族主义以强化其合法性,于是,在1933 年到1939 年,德意志第三帝国一直表现出其强烈的民族扩张性,他们重新进入莱茵非军事区,吞并奥地利,割占苏台德地区,背弃凡尔赛和约扩军备战,种种措施无一在表现其狂热的民族主义,通过调动这种民族主义以获得民众的支持,最终,在1939 年,民族主义夹裹着德国人民跨过和平的边境走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四、结语
民主化转型中的魏玛共和国,其民族主义没有受到限制,民族主义在民众和他们的社会实践中根深蒂固,政党竞争、民众参与和自由选举成为了民族主义的助燃剂,最终驱使着德国人民背弃了民主制度,又一次选择了专制主义。由此可见,国家在民主化的过程中,要对国内民族主义活动的动向做到时时关注和稳步的控制,将民族主义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谨防在民主化转型的过程中,广泛的公众参与所形成的民族主义,夹裹着人民葬送民主的前途,走向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