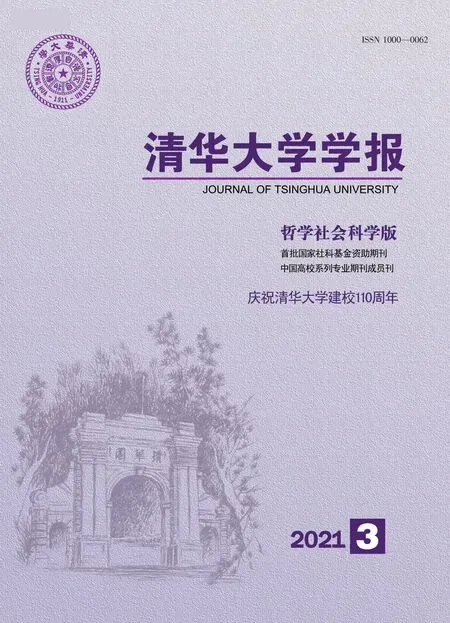论李白对佛教的接受及其文学表现
李芳民
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唐代文人所受到的思想影响往往是很复杂的,而李白在这方面最为典型。就李白的一生看,儒、道、佛、仙、侠、纵横等家思想,都对他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并在其作品中有所体现,但相较而言,佛教对于李白的影响则要更为复杂些。如何估量佛教在李白思想中的地位,向来认识上并不一致。龚自珍论李白有一段为人所熟知的话,谓:“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其斯以为白之真原也已。”(《最录李白集》)①裴斐、刘善良:《李白资料汇编(金元明清之部)》,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176—1177页。其中揭示李白与庄、屈及儒、仙、侠之间的关系,而未及佛教。刘熙载也说:“太白早好纵横,晚学黄、老,故诗意每托之以自娱。”②刘熙载:《艺概》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9页。亦不言佛教对白之影响。近代以来,李白与佛教的关系问题虽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但如何估量佛教对李白思想的影响以及准确认识佛教在李白文学创作中的表现特点,似仍有进一步探讨之必要。③对于李白与儒释道三者的关系,郭沫若曾说:“李白的思想,受着他的阶级的限制和唐代思潮的影响,基本上是儒、释、道三家的混合物……对于佛教,他也有相当的濡染,但深入的程度还不及杜甫。杜甫是禅宗的信徒,而李白却是道教的方士。”(见氏著:《李白与杜甫》,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0年,第94页)日本学者松浦友久则对李白儒、道、佛题材的作品比较后指出:“李白对佛教的关切,较之另外二教,明显缺乏内在的必然性。因此,这一问题可以说是李白研究史的一个悬案。”(见氏著:《李白诗歌抒情艺术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36页)近二三十年来,学界对李白与佛教关系的探讨虽有所深入,但成果仍然不是很多,其中重要者有葛景春的《李白与佛教思想》(《唐代文学论丛》总第9期)、章继光的《李白与佛教思想》(《人文杂志》1990年第1期)、姜光斗的《李白诗歌中的佛教意识》(《南通师专学报》1991年第4期)、须藤健太郎的《李白诗文的佛教描写》(《唐代文学研究》第10辑)、李小荣的《李白释家题材作品论》(《文学遗产》2005年第2期)、袁书会的《李白佛教诗歌略说》(《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等。另外,安旗先生有《平生无限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李白与佛教》一文(见氏著:《我读李太白》,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125—156页)。本文分析李白佛教题材作品,系年主要依据安旗先生主编之《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故文中历时性分析李白与佛教关系与安先生之文角度有相近者,而具体论析则有所不同。本文拟从李白诗文所涉及的佛教典故与语汇入手,来考察李白对佛教的接受情况,并分析佛教对李白诗文创作的影响及其表现特征。
一、李白诗文中的佛典运用情况
自汉末已降,经过众多西域来华僧人与本土僧徒及文人的共同努力,传入中土的佛经至唐代已有相当的规模。因此,研习佛典,对于一般文人而言,自然要有所选择,不过由于李白没有留下其有关具体佛经阅读与诵习方面的记述,因而要了解李白的佛经阅读情况是较为困难的。然而,对于文人而言,佛经的诵习,一定会经过积淀,在其创作中得到呈现,因此,通过李白诗文中的佛典与语汇的运用,也许可以对其佛经的研习做出一定程度的还原。
李白现存诗文中,直接涉及佛教或与佛教相关的作品计有诗歌37题38篇,文10篇,合计48篇。以下以清人王琦《李太白全集》的注释为线索,并参今人注本,对这些作品中与佛经相关语汇与典故出处作一勾稽,并以其作年先后,列作表1。

表1 李白诗文中与佛典相关之语汇及典故

(续表1)

(续表1)

(续表1)

(续表1)
从表1的梳理看,李白涉及佛教题材的诗文中,语汇与典故出于佛经者,共22篇,所涉佛经16部,依使用之频次排列,分别是《法华经》(14)、《维摩诘经》(10)、《楞严经》(6)、《弥陀经》(6)、《涅槃经》(5)、《观无量寿经》(5)、《华严经》(3)、《大般若经》(2)、《报恩经》(2)、《地藏菩萨本愿经》(2)、《贤愚因缘经》(2)、《金光明经》(1)、《心经》(1)、《梵网经》(1)、《圆觉经》(1)、《四十二章经》(1)。虽然不能根据李白诗文中所运用的这些佛经的典故语汇的数量,完全还原出李白所读的全部佛经,但据此可以肯定的是,其一,上述16部佛经,可能是李白比较熟悉的,而通过典故语汇的使用频率,也可以大致判断李白对具体佛经的阅读与偏好;其二,唐代佛教各宗派所宗之佛典不同,而从李白所读的佛经看,其阅读佛经的范围,涉及净土、华严、禅宗、律宗等各家经典,由此也可大致判断,李白对佛教思想的接受并无特别的宗派偏向。以上二点,可以初步判断为李白佛经阅读及接受的基本特征。
二、李白佛教接受的历时性考察
文人接触佛教并阅读佛教典籍,除了自幼受家庭或家族成员影响者外,常与其个人生活经历与特殊遭际有着密切关联。由此,他们对佛教的体认,也大都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而具体到对佛经的阅读接受,则往往与其个人经历或与其所交往僧人的影响关系甚大。柳宗元在谈及他对佛教的接受时曾说:“或问宗元曰:悉矣!子之得于巽上人也,其道果何如哉?对曰: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吾独有得焉。”①柳宗元:《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见《柳宗元集》卷二五,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71页。柳宗元自幼好佛,但对佛教认识的深化则在其贬谪永州以后,特殊的人生遭际使他与佛教更加亲近,其所接触的高僧如重巽等,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从而使其对佛教的体悟有了大的飞跃。李白对佛教的接受与体认,自也应有一个演变过程。
李白一生中何时开始接受佛教影响并阅读佛书,因资料所限难以判断。今所知者,李白少年在蜀中时,兴趣广泛,读书广博,自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第1243页)。又谓其“十五观奇书”(第599页),但“百家”“奇书”中是否包含佛教典籍?不得其详。②松浦友久曾猜测说:“‘十岁观百家’的记述,应指多种多样的诸子百家而言,也许还包括佛教典籍。”见氏著:《李白的客寓意识及其诗思——李白评传》,刘维治、尚永亮、刘崇德译,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65页。而就李白当时隐居读书与从师学习的情况看,其早年对道教神仙与纵横家之说可能更感兴趣,所读的书当以道家、道教及纵横家之书为主,但也可能因社会环境影响的原因,受过佛教的习染熏陶,阅读过一些流行的佛典,否则其出蜀初期作品中出现与佛教相关的语汇典实也就很难理解了。
对于李白一生佛教典籍的阅读与佛教接受情况,现在只能从其作品来把握,这也是今天认识李白与佛教关系最基本的途径。李白现存与佛教关涉的诗文近50篇,据今人之编年考证成果,其可系年者在90%以上,这对于我们历时性考察李白与佛教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而据李白诗文创作中与佛教相关的信息,我们可以将李白与佛教的关系分成三个阶段,即开元时期、天宝时期与至德以后至病殁时期。以下结合李白诗文,就此三个阶段的情况作一简要分析。
开元时期,李白涉及佛教典故语汇与题材内容的作品,计12篇(其中存疑诗1首不计在内),计诗歌11首,文1篇。最早者为开元十三年至金陵所写的《登瓦官阁》,最晚者为开元二十七年所作的《与从侄杭州刺史良游天竺寺》,文为游江夏时所作的《江夏送林公上人游衡岳序》。纵观李白这一时期涉及佛教或与之相关的作品,大致有一共同点,即其大都是与诗人游览佛教寺院或与方外僧人的社交活动相关,其诗文中佛教语汇典故的运用,也主要因诗文关涉对象而引发,其中很难看出李白对佛理本身的兴趣。就其表现方式而言,一则是出于环境与景物描写需要,以佛教典故语汇构建其诗语诗句;二是因与方外之士的交往,遂生发联想,以历史上文人与方外之士之交作为当时人物情事的映衬。关于前者,如《登瓦官阁》一诗,从全诗的描写来看,其主要以抒写诗人登瓦官阁后所见以及登眺所闻、所感为主。其中涉及佛教语汇典故者,为第五至第八四句,内容无外是切合所游之地的宗教性特点而写佛教寺院之氛围,并以佛教典籍的语汇来加以点染,显示所游之地的独特性。至于与方外僧人交往之作,其作为社交性应酬性是很明显的,如《秋夜宿龙门香山寺奉寄王方城十七丈奉国莹上人从弟幼成令问》中“凤驾忆王子,虎溪怀远公”(第654页),由当前诸人与奉国上人方外之交,而思接数百载,联想及慧远与陶渊明过虎溪的故事;《江夏送林公上人游衡岳序》中的“昔智者安禅于台山,远公托志于庐岳。高标胜概,斯亦向慕哉”(第1261页),以送林公上人游衡岳,而联想及智之驻锡天台、慧远之栖息庐山。另外还有一些诗,诗题虽与佛教有涉,但其内容却看不出任何佛教意趣。如《与从侄杭州刺史良游天竺寺》:
挂席凌蓬丘,观涛憩樟楼。三山动逸兴,五马同遨游。天竺森在眼,松风飒惊秋。览云测变化,弄水穷清幽。叠嶂隔遥海,当轩写归流。诗成傲云月,佳趣满吴洲。(第928页)
全诗写与杭州刺史李良游览天竺寺,但只见山水之美、逸兴之高,却没有天竺寺作为佛教寺院所应体现的宗教特征,也看不出与佛理的关联。
天宝时期,李白涉及佛教的诗文共有18篇(其中文3篇),不仅数量最多,且与前相比,与佛教的关系也有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出现了一些体悟佛理的作品,另一方面,一些作品还描述了其习禅的具体体验与感受。这表明,这一阶段李白与佛教的关系显然加深了。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天宝六载李白在湖州所写的《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一诗:“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第876页)诗是答复湖州司马迦叶氏之问的,因问者姓氏之特别,白之回答也就显得别有机趣。①在《维摩诘所说经》中,佛曾遣大迦叶向维摩诘问疾,迦叶曾被维摩诘所诘难,因慑于维摩诘的辩才而辞不敢往。《维摩诘所说经·弟子品第三》载云:“佛告大迦叶:‘汝行诣维摩诘问疾。’迦叶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忆念我昔于贫里而行乞,时维摩诘来谓我言……我从是来,不复劝人以声闻、辟支佛行。是故不任诣彼问疾。’”见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大正藏》第1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540页a。只是迦叶氏发问之语境与背景,诗中并没有交待。很有可能是李白本人的个性与作风引起了迦叶氏的好奇,比如他既好道求仙,又诗酒风流,既学佛习禅,又携妓远游,这在一般人似乎难以理解,故迦叶氏乃有此问。而李白的回答则显示其是又仙又佛,特别是以“金粟如来”之后身自期,在其与佛教关系的体认上,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金粟如来”即维摩诘居士的前身,也是维摩诘居士的别称。维摩诘是《维摩诘所说经》中主要人物。他是古印度毗离耶城的富翁,虽处红尘,而不离梵行,深达实相,而善说法要,且辩才无碍。《维摩诘所说经》谓其“虽处居家,不著三戒;示有妻子,常修梵行;现有眷属,常乐远离;虽服宝饰,而以相好严身;虽复饮食,而以禅悦为味……入诸淫舍,示欲之过;入诸酒肆,能立其志”。②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方便品第二》,《大正藏》第14册,第539页a。由李白此诗看,他对《维摩诘所说经》当有较深入的了解,对维摩诘其人也非常欣赏,所以他才于诗中,以“金粟如来”的后身自许。诗中体现的对维摩诘的认识与欣赏,已与此前诗歌的佛教表现有所不同了。
最值得关注的,则是这一时期的习禅之举。天宝四、五载所作《鲁郡叶和尚赞》中“了身皆空,观月在水”“寂灭为乐,江海而闲”的句子,已显示其对佛法的体悟比较深入了。“了身皆空,观月在水”,诸家注释皆未注其出典,其实《维摩诘所说经》有句云:“一切法生灭不住,如幻如电,诸法不相待乃至一念不住;诸法皆妄见,如梦、如炎、如水中月、镜中像,以妄想生。”③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弟子品第三》,《大正藏》第14册,第541页c。有可能《赞》文之语,即是李白由《维摩诘所说经》体悟而来,并用以来赞扬鲁郡的叶和尚。而“寂灭为乐”句,王琦注已指出其出《涅槃经》之“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第1338页)。总体看,此《赞》虽不长,却已显示李白对佛理的领悟,已进入了更高的境界。
李白这一时期与僧人交往,也逐渐开始超越一般社交性应酬,而有了更高层次的交流。天宝九载所写的《僧伽歌》对此有所显示:
真僧法号号僧伽,有时与我论三车。问言诵咒几千遍,口道恒河沙复沙。此僧本住南天竺,为法头陀来此国。戒得长天秋月明,心如世上青莲色。意清净,貌棱棱,亦不减,亦不增。瓶里千年舍利骨,手中万岁胡孙藤。嗟予落泊江湖久,罕遇真僧说空有。一言忏尽波罗夷,再礼浑除犯轻垢。(第406页)
诗一开始即交待其与僧伽研讨佛法,讨论“三车”之喻。这就深入到佛教典籍之中了。“三车”之典,出自《妙法莲华经》,是佛在给舍利弗说法时,谈其如何使众生离我见及有无见而得到解脱所用的譬喻故事:
舍利弗!若国邑聚落有大长者,其年衰迈,财富无量,多有田宅及诸僮仆;其家广大,唯有一门,多诸人众,一百、二百乃至五百人,止住其中;堂阁朽故,墙壁落,柱根腐败,梁栋顷危,周匝俱时欻然火起,焚烧舍宅;长者诸子,若十、二十或三十在此宅中。长者见是大火从四面起,即大惊怖而作是念:“我虽能于此所烧之门安稳得出,而诸子等,于火宅内乐著嬉戏,不觉、不知、不惊、不怖,火来逼身,苦痛切己,心不厌患,无求出意。”……尔时,长者即作是念:“此舍已为大火所烧,我及诸子若不时出,必为所焚。我今当设方便,令诸子等得免斯害。”父知诸子先心各有所好种种珍玩奇异之物,情必乐著,而告之言:“汝等所可玩好,希有难得,汝若不取,后必忧悔。如此种种羊车、鹿车、牛车,今在门外,可以游戏。汝等于此火宅宜速出来,随汝所欲,皆当与汝。”尔时,诸子闻父所说珍玩之物,适其所愿故,心各勇锐,互相推排,竞共驰走,争出火宅。是时,长者见诸子安稳得出,皆于四衢道中露地而坐,无复障碍,其心泰然,欢喜踊跃。时诸子等各白父言:“父先所许玩好之具,羊车、鹿车、牛车,愿时赐与。”①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譬喻品第三》,《大正藏》第9册,第12页b。
而“嗟予落魄江湖久,罕遇真僧说空有”句,也值得玩味。“落魄江湖”,很可能是指其天宝三载春由待诏翰林被“赐金放还”以后事。由于离开长安,由庙堂而处江湖,苦闷难遣,便冀望从佛教中寻求解脱,遗憾的是很少遇到像僧伽这样与之展开佛理探讨与交流的僧人。遇到僧伽,使他大有开悟,所以乃有末句“一言忏尽波罗夷,再礼浑除犯轻垢”之句。“波罗夷”“轻垢”亦皆释氏语汇,出《梵网经》。李白以为,与僧伽的交流,一言之忏悔,便可消除永弃佛法外的重罪,再经礼拜,轻垢之罪亦完全弃却。从李白的这些表述看,其与僧伽的交流,已是两人围绕佛法体悟的深层次对话了。
随着对佛理认识的深化,李白这一时期学佛习禅也有了更深的体验。《与元丹丘方城寺谈玄作》即对自己习禅体验做了细致的描述:
茫茫大梦中,惟我独先觉。腾转风火来,假合作容貌。灭除昏疑尽,领略入精要。澄虑观此身,因得通寂照。朗悟前后际,始知金仙妙。幸逢禅居人,酌玉坐相召。彼我俱若丧,云山岂殊调。清风生虚空,明月见谈笑。怡然青莲宫,永愿恣游眺。(第1059页)
诗写其与元丹丘谈佛之道,主要表现其对佛理的体悟。所谓“腾转风火来,假合作容貌”,也就是对佛教所讲的世间万物乃地、水、火、风四大元素假合而成,并无实性的要义,已深有体悟。因为深明佛理,故谓犹如大梦之觉醒,一切昏疑皆已灭除,身心亦得清静安适,同时也了悟佛所说的前、今、后三世之说。而《赠僧崖公》则对自己习禅的经历,做了完整的交待:
昔在郎陵东,学禅白眉空。大地了镜彻,回旋寄轮风。揽彼造化力,持为我神通。晚谒太山君,亲见日没云。中夜卧山月,拂衣逃人群。授余金仙道,旷劫未始闻。冥机发天光,独朗谢垢氛。虚舟不系物,观化游江。江遇同声,道崖乃僧英。说法动海岳,游方化公卿。手秉玉麈尾,如登白楼亭。微言注百川,亹亹信可听。一风鼓群有,万籁各自鸣。启闭八窗牖,托宿掣雷霆。自言历天台,搏壁蹑翠屏。凌兢石桥去,恍惚入青冥。昔往今来归,绝景无不经。何日更携手,乘杯向蓬瀛?(第542—543页)
从此诗看,李白的习禅,首从白眉空于郎陵,次为谒太山君时,三则从学于道崖。此诗之作年,詹锳与安旗两位先生皆系于天宝十三载,则从道崖学禅,当在此际。从白眉空学禅在何时?未有明载;太山君即太山神,白于天宝元年游泰山,则谒太山君时而又有习禅之举,其有可能在此时。根据此诗的叙述,则李白习禅而有所解悟,可断定当以天宝时期为主。
到了第三阶段,也即至德以后,方安史乱生,举国大乱,李白因报国心切,积极投身并参与报效国家的各种活动,并因此而造成其命运的跌宕起伏。至垂暮之年,居无定所,到处漂泊,因此,此一时期再无天宝年间那样比较集中的学佛习禅活动了。但这一时期他仍有佛寺中的交流唱和,与方外僧人的交往也没有中断,所以仍有不少与佛教相关的诗文之作。这一时期与佛教相关的诗文计13篇,其中诗、赞等韵文10篇,散文3篇。诗歌中,有在佛教寺院的宴饮、唱和、憩息之作,也有与僧人的别离酬赠之作。前者如《流夜郎永华寺寄浔阳群官》《流夜郎至江夏陪长史叔及薛明府宴兴德寺南阁》《与贾舍人于龙兴寺剪落梧桐枝望灉湖》《登巴陵开元寺西阁赠衡岳僧方外》《禅房怀友人岑伦》等;而后者如《将游衡岳过汉阳双松亭留别族弟浮屠谈皓》《酬裴侍御留岫师弹琴见寄》《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等。文的写作,大致则为出于请托的应酬。如《地藏菩萨赞》乃应扶风窦滔之请而撰,《江夏送倩公归汉东序》乃送别赠序,《为窦氏小师祭璇和尚文》也应是代僧人所撰。这些作品,特别是诗歌,其大多都不再涉及佛理探讨,尤其是再无李白个人的宗教体验性描写。如《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
我在巴东三峡时,西看明月忆峨眉。月出峨眉照沧海,与人万里长相随。黄鹤楼前月华白,此中忽见峨眉客。峨眉山月还送君,风吹西到长安陌。长安大道横九天,峨眉山月照秦川。黄金师子乘高座,白玉麈尾谈重玄。我似浮云滞吴越,君逢圣主游丹阙。一振高名满帝都,归时还弄峨眉月。(第443—444页)
诗的内容,以叙契阔别离之意为主,涉及佛教语汇者,仅有“黄金师子乘高座”而已。文的写作,唯《地藏菩萨赞》有数句涉及佛教思想,如“大雄掩照,日月崩落。惟佛知慧大而光生死雪,赖假普慈力,能救无边苦。独出旷劫,导开横流,则地藏菩萨为当仁矣”,以及赞语“本心若虚空,清净无一物。焚荡淫怒痴,圆寂了见佛。五彩图圣像,悟真非妄传。扫雪万病尽,爽然清凉天。赞此功德海,永为旷代宣”句(第1336—1337页),但也属一般性佛教教义的介绍,并不具有特殊的个人体悟与体验。所以,天宝十四载以后至李白的晚年,其学佛习禅活动可以说已基本消歇,对佛教思想的钻研与习禅体验的热情亦趋于衰退。
三、李白佛教接受及其文学表现的特点
从李白作品角度对李白与佛教关系作历史性的考察,可以看出李白对佛教接受的变化。如果再结合李白诗文所涉及的具体佛经以及诸经所表现的思想来考察,则对李白佛教接受的情况也可有更深入的认识。同时,李白的佛教接受,是通过其诗文作品呈现的,那么,其作品的表现又有何个性,也即李白佛教题材作品的文学表现与其他作家有何不同?这也是认识李白佛教接受及其对文学创作影响的重要问题。
李白的佛教接受,据前已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以下分别就不同阶段诗文所涉及佛经的特点加以考察,并兼及诗文中有关佛教语汇典故的运用情况。
开元时期,李白诗文所涉及的佛经主要有五:即《阿弥陀经》《法华经》《四十二章经》《贤愚因缘经》及《大般若经》。从这几部佛经看,其大致都是传播较广的佛教典籍。
《阿弥陀经》是佛教净土宗的主要经典,全名《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道经》,亦称《大阿弥陀经》。此经主要宣传净土极乐世界,称只要坚持念诵阿弥陀佛,则临终时阿弥陀佛即来接引其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自南北朝已降,此经已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原因在于此经所宣扬的净土世界极有吸引力,且其修行简便易行,故流行甚广。《法华经》同样也是备受佛教信众重视的经典。南北朝时,研究《法华经》已成专门学问,又因其“语言比较简练,脉络比较清楚。使许多杂乱无章的说法得以集中概括”,①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2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15页。故在佛教诸经中,也属于传播很广泛的佛教基本经典之一。《四十二章经》相传是最早传入中土的佛经,内容比较简单。它不是一部独立的佛经,而是辑录小乘佛教基本经典《阿含经》要点的“经抄”,相当于“佛教概要”一类的入门书。《贤愚因缘经》稍长,乃收集种种有关贤者与愚者的譬喻因缘而成,以叙事性故事性见长。《般若经》的情况则较复杂。它是大乘佛教空宗经典,是由般若部类众多经典汇编而成。汉末支娄迦谶最早所译名《道行品经》,被称为《小品般若》,姚秦鸠摩罗什所译为《大品般若经》,而集般若经之大成,则为唐玄奘所译的六百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佛教大乘空宗思想传入中国后,“般若”经影响很大,其中鸠摩罗什所译的《大品般若经》流传较广。李白阅读大乘般若经典,似应以罗什所译的《大品般若经》可能性为大,因玄奘所译,时间较晚,又卷帙浩繁,在李白青年时代,玄奘所译是否已广为传播,尚难以断定。
从李白开元时期诗文所涉及的上述几部佛经以及其传播情况看,李白青年时期应该是读过一些较流行的佛教基本经典的,从而具备了佛教的基本知识,并在其文学创作得到一定的显现。
天宝时期,从诗文所涉及的佛教内容与语汇、典故看,除了开元时期已经涉及者外,新出现者则有《维摩诘经》《观无量寿经》《报恩经》《涅槃经》《心经》《华严经》《金光明经》《梵网经》《楞严经》9部。
《维摩诘经》是备受佛徒重视与欢迎的佛经。自魏晋已降,此经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对于这样一部在士人中广为流传的佛经,李白的接受是非常自然的,只是李白何时阅读接受这一经典尚不清楚,开元时期的诗文作品,尚未见与此经相关的语汇典故,而天宝六载所作《答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一诗,李白以维摩诘居士自许,则他对此经必已熟稔无疑。《观无量寿经》乃净土宗的重要经典之一。自东汉末年始,宣传弥陀信仰的经典已传入中国,《无量寿经》为宣传弥陀信仰经典之一,其内容与《阿弥陀经》有诸多相近之处。李白开元时期诗文已涉及《阿弥陀经》,此一时期,出现与《观无量寿经》相关的语汇典故,也许是其在《阿弥陀经》接受基础上对净土宗经典阅读的进一步扩展。《报恩经》或即《大方便佛报恩经》,唐时传播情况不详。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一有《大方便报恩经》一卷,但称属阙本,王琦注释仅涉词意来源,不知李白确曾读过此经否。《涅槃经》即《大般涅槃经》,此经主要阐述涅槃常、乐、我、净四德,宣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阐提和声闻、辟支佛皆得成佛的大乘佛教思想,是佛经中影响很大的一部经典。佛徒讲习此经之风很盛,李白在天宝时期对学佛表现出兴趣时,极可能受佛徒的影响,对此经有所阅读。《心经》即《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此经在佛教诸经中地位至高,又因其将内容庞大的佛教般若经的内容做了浓缩,成为总括佛教般若空思想的精华,故流行最广。《华严经》全称为《大方广华严经》,是华严宗据以立宗的经典。此经武则天时实叉难陀曾重译,因受到武则天的支持,故以此经立宗的华严宗在唐时也较兴盛。华严宗当时是佛教界影响较大的宗派之一,故李白阅读此经也应在情理中。《金光明经》又名《金光明最胜王经》,此经将宣传佛法与护国利民结合,因与《妙法莲华经》《仁王护国经》合称为护国三部经。由于它所宣传的弘法护国思想,特别是其对国王的地位所给予的神学证明,因而受到了帝王的欢迎,其在社会上也流传较广。《梵网经》全称为《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第十》,为佛教大乘戒律经典。中土佛徒修行,颇重持戒,此经主要叙述释迦牟尼佛接大众至莲花台藏见卢舍那佛问众生修成菩萨之道及其从天宫下至阎浮提菩提树下复述卢舍那佛初发心时长诵一切大乘戒等,故其当为修持佛法者所重。李白接近佛教,学习佛法,想来定有僧徒介绍此持戒之佛典。《楞严经》也属佛教极重要的经典,据载乃唐中宗神龙元年(705)于广州制止寺译出,则其乃是初唐末期才译出的新经。李白之接受并阅读此经,则说明其对新经的接受应该是比较敏锐的了。
至德以后至其辞世,李白诗文涉及新的佛经数量最少,只有《地藏菩萨本愿经》与《圆觉经》2部。
《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内容是讲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为母说法时,知道自己快要涅槃,便将佛陀入灭、弥勒菩萨尚未下生成佛的漫长无佛时期的度生重任托付于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接受付嘱,担负起了救度六道众生之重任。这是具有宣扬孝道色彩的佛经,故被称为“佛门孝经”。这一点使其在普通民众中广有影响。《圆觉经》全称为《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是佛教大乘之经典,其内容述佛为文殊、普贤等12位菩萨宣说如来圆觉的妙理与方法。据传此经武后长寿二年(693)译出,为天台、贤首(华严)及禅宗所重,李白暮年文中语汇涉及此经,但不知其接受与阅读究在何时。
以上从三个时期,对李白诗文所涉及的语汇典故出发,梳理了相关的16部佛经的大致情况,从中可以看出李白佛教接受与佛经阅读的一些特点。
第一,李白的佛教接受,经历了由一般性接受,到学习与探索体悟,再到晚年逐渐消退的历程。李白在蜀中时自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及“十五观奇书”,并非虚语。可以断定,其当时所读之“百家”“奇书”,也当包括佛教典籍在内。天宝年间,其与佛教的关系趋于密切,这表现在其对学佛习禅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在习禅过程中通过个人的体验与体悟来理解佛理与禅境,所阅读的佛经也大量增加。至德以后则与佛教的关涉稍淡,作品所涉及的新佛经不多,这表明其阅读佛经的兴趣似较以前为低。
第二,从接受的佛经看,早期李白所接受与阅读的佛经,似以流行较广的佛经为主。其中一些是习佛者常读之经典。天宝时期,其阅读的佛经数量多,对佛理的探索也转而较为深邃。这当与李白对佛教兴趣的变化以及其对佛理积极探求的态度相关。晚年所涉及的两部佛经,则可能与其应酬为文的需要有关。
第三,由李白的佛经阅读与接受,也可对李白接受佛教思想影响的原因作出推测。李白佛教接受的高潮在天宝间,此与前后两个时期有着明显的不同。何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从李白的生活经历看,很可能与李白这一时期因个人政治遭际带来的情绪、心理的变化有关。李白天宝三载出长安,心情是极为不平静的。自天宝三载至天宝十载前后,他因政治失意,心情极为落寞与苦闷,但一时又找不到出路,因此便投入宗教中来寻求解脱。李白的学佛与习禅,其原因或即在此。只是李白本是热衷政治的人,其禀赋与个性也与佛教宗旨异趣,故其短时期的学佛习禅虽很认真,但佛教并未从根本上对其主导思想产生移易,他最终并未因佛教思想而影响其处世之基本态度。
由于李白对佛教接受的这些特点,其诗文中的佛教表现也就很有自己的个性。总括起来,有以下几点,似值得注意。
第一,李白诗文中的佛教题材作品,社交性、应酬性的数量较多。此一点前面曾有论及,今再以《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为例,见其诗之表现特点:
余闻荆州玉泉寺近清溪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其中有白蝙蝠,大如鸦。按仙经,蝙蝠一名仙鼠,千岁之后体如白雪。栖则倒悬,盖饮乳水而长生也。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枝叶如碧玉。惟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年八十馀岁,颜色如桃花。而此茗清香滑熟,异于他者,所以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余游金陵,见宗僧中孚,示余茶数十片,拳然重叠,其状如手,号为仙人掌茶。盖新出乎玉泉之山,旷古未觌,因持之见遗,兼赠诗,要余答之,遂有此作。后之高僧大隐,知仙人掌茶发乎中孚及青莲居士李也。
常闻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如白鸦,倒悬清溪月。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丛老卷绿叶,枝枝相接连。曝成仙人掌,似拍洪涯肩。举世未见之,其名定谁传?宗英乃禅伯,投赠有佳篇。清镜烛无盐,顾惭西子妍。朝坐有馀兴,长吟播诸天。(第897—898页)
僧中孚是李白结识的方外僧人,李白称之为族侄,看来与其相交融洽而关系密切。中孚以稀见的玉泉仙人掌茶相赠,兼赠以诗。天宝年间,李白已是诗名盛于天下的诗人,“谪仙人”的风神亦令天下无数人为之倾倒,因此,方外僧人与李白的交往,当不乏慕其诗名的因素,而赠茶赠诗之目的,当也在于希望得到李白的诗歌酬答。李白在《序》中已交待此诗写作的背景缘起,故诗中的内容也就主要以所赠茶之特点描写为中心,同时也对中孚多有称赞,对其所赠诗歌,也做了礼貌的表扬。这首写方外之交的诗歌,没有涉及佛教教义或禅理的内容,可谓是纯然社交性的应酬之作了。
第二,李白诗文中的佛典语汇,在作品层面,往往具有点染色彩,其并不对诗歌的主题、情境构成影响。而常以历史上儒、释交往的典型人事作为典实,呈现释俗交往关系之风流,乃是其佛教题材作品的一个鲜明特点。李白诗文涉及佛教典实者48篇,以南北朝僧俗之交来作映衬者,则约有10篇,约占25%。这在唐代诗人的创作中,是极为突出的。如“梁有汤惠休,常从鲍照游。峨眉史怀一,独映陈公出”(《赠僧行融》,第633页),“凤驾忆王子,虎溪怀远公”(《秋夜宿龙门香山寺奉寄王方城十七丈奉国莹上人从弟幼成令问》,第654页),“霜清东林钟,水白虎溪月”(《庐山东林寺夜怀》,第1075页),“今日逢支遁,高谈出有无”(《赠宣州灵源寺仲浚公》,第631页),“岩种朗公橘,门深杯度松”(《送通禅师还南陵隐静寺》,第836页)等等。
第三,李白的学佛习禅,以个人体验体悟为主,尤其与其政治失意有关,他希望借助佛理的解悟,化解内心的苦闷,但并没有成为佛教思想的信仰者,佛教思想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对人生与世界的看法,因此在诗歌的意境创造上,其并未形成诗境与禅境完全融合为一。比如:
茫茫大梦中,惟我独先觉。腾转风火来,假合作容貌。灭除昏疑尽,领略入精要。澄虑观此身,因得通寂照。朗悟前后际,始知金仙妙。幸逢禅居人,酌玉坐相召。彼我俱若丧,云山岂殊调。清风生虚空,明月见谈笑。怡然青莲宫,永愿恣游眺。
诗中“腾转风火轮,假合作容貌”“澄虑观此身,因得通寂照”等句,都是诗人习禅体悟与感受的描述,但禅的思想,没有融化于诗进而形成富有禅意的意境。这一点,与王维、柳宗元等人的诗歌相比,尚有所不同。当然,唐人诗歌习染佛教思想并能够将佛理与诗境融合,做到水乳交融的境界,这既与诗人对佛教的浸染程度有关,也与佛教与诗歌关系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李白的这一特点,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他生活时代的大部分诗人特点的体现,是颇具代表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