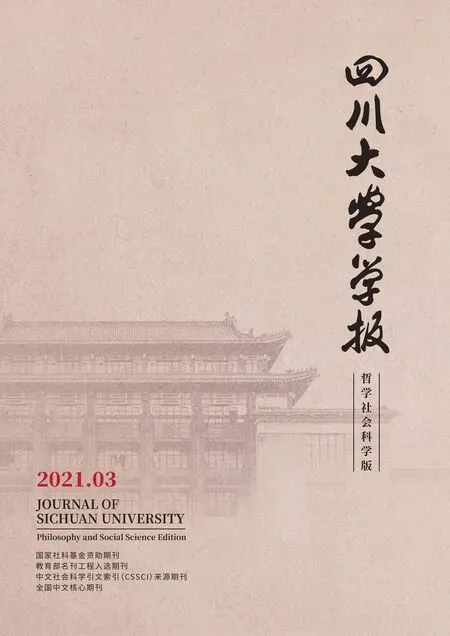圣哲之境:反思奥古斯丁对希腊古典哲学怡情理论的障碍性理解
高 源
一、引言:奥古斯丁与希腊古典哲学的关系

除去语言方面的因素,奥古斯丁对希腊语哲学著作也并不十分精通,其关于斯多亚主义知识的主要获得途径,乃是通过西塞罗的著作。(3)关于奥古斯丁与西塞罗的关系,参见Miikka Ruokanen, Theology of Social Life in Augustine's De civitate Dei,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3, p.121. 相关研究,亦见Sarah Byers, Perception, Sensibility, and Moral Motivation in Augustine:A Stoic-Platonic Synthesi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Carol Harrison, Augustine:Christian Truth and Fractured Humanit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Harald Hagendahl, Augustine and the Latin Classics,Göteborg: Acta Universitatis Gothoburgensis, 1967.西塞罗的《荷尔顿西乌斯》(Hortensius)是真正引导奥古斯丁进入“智慧”大门的第一本哲学书。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这样回顾:“我读到一个名西塞罗的著作,一般人更欣赏他的辞藻过于领会他的思想。书中有一篇劝人读哲学的文章,篇名是《荷尔顿西乌斯》。这一本书使我的思想转变……这本书吸引我,已是由于内容,而不是为了辞藻了……这本书引起我对哲学的兴趣。”(4)奥古斯丁:《忏悔录》,第41页。从后来的《论三位一体》的记录看,奥古斯丁所说的最早引起其哲学兴趣的,乃是西塞罗《荷尔顿西乌斯》关于斯多亚圣哲心灵秩序及其不动情品格的描述。(5)奥古斯丁《论三位一体》卷十四第十九章第二十六节提及了西塞罗的《荷尔顿西乌斯》,并阐述了斯多亚式的心灵秩序论对他早年的影响。Brown, Augustine of Hippo:A Biography, p.29.此外,西塞罗《图斯库卢姆辩论》(Tusculanaedisputationes)对斯多亚理论中普通人情绪的四种类型(乐laetitia、欲cupiditas、烦tristitia、惧timor)的描述,亦对奥古斯丁情感本质的认知产生了直接的影响。(6)Knuuttila, Emotions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Philosophy,p.156.
相比斯多亚学派,奥古斯丁关于新柏拉图主义情感理论知识的来源却复杂得多。一个重要的途径乃是通过拉丁文间接翻译。如《忏悔录》卷七第九章十三节所记述的,386年夏,奥古斯丁从一个不知名的朋友那里获得一批柏拉图主义的书。(7)Brown, Augustine of Hippo:A Biography, p.85.这些书包括普罗提诺(Plotinus)、波菲利(Porphyry)和非洲修辞学家维克多努斯(Marius Victorinus)等的作品。(8)关于新柏拉图主义者对早期奥古斯丁的影响,参见陈越骅:《神秘主义的学理源流:普罗提诺的太一本原论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王晓朝:《跨文化视野下的希腊形上学反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另一个重要途径乃是通过安布罗斯(Ambrose)。比如在386年左右,奥古斯丁阅读了安布罗斯的《证道集》,并接触了安布罗斯老师西姆普利肯努斯(Simplicianus)的一些基督教化的新柏拉图主义作品。(9)Brown, Augustine of Hippo:A Biography, pp.85-86; H. I. Marrou, “Synesius of Cyrene and Alexandrian Neo-Platonism,” in A. Momigliano, ed., The Conflict between Paganism and Christianity in the Fourth Centu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3, pp.126-150.此时,在奥古斯丁心目中,柏拉图主义与亚里士多德主义是“绝对正确的哲学文化”。(10)Brown, Augustine of Hippo:A Biography, p.84.
值得注意的是,与今天我们严格区分柏拉图主义(学园派)、亚里士多德主义(逍遥派)与新柏拉图主义关于情感心理学的做法不同,奥古斯丁在其著作中习惯将这些哲学流派的情感理论视作统一的、折衷的观点,以与斯多亚主义所主张的完全将情感剔除心灵之外的禁欲主义立场相区分。如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驳异教徒》卷九第四章中将(新)柏拉图学派与亚里士多德主义情感观相连通。他说:“关于灵魂的动荡,哲学家们有两种观点……这搅扰、情感,或性情,有些哲学家们说,也会降临到智慧的人身上,但是会受理性的节制和制约,只要他自己立法来统治心志,矫正到必要的模式上。柏拉图学派或说亚里士多德学派是这么认为的。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弟子,后来建立逍遥派。另外的哲学家,比如斯多亚派,就认为,性情不会降在智慧的人身上。”(11)奥古斯丁:《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中,吴飞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8年,第4页。以下《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中文,均引自吴飞译本。这里,奥古斯丁将希腊哲学情感理论分为两派,一个是柏拉图-逍遥派,另一个是斯多亚学派。奥古斯丁将亚里士多德学派作为柏拉图学派的承继者,混同性地认为两者均秉持“矫正/调控情感”的方法论,以与斯多亚哲学完全排除情绪干扰的怡情理论相区分。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奥古斯丁关于古典希腊哲学流派的知识,大多并非直接取自一手希腊语原始文献,而主要是通过拉丁文二手翻译或安布罗斯等师友介绍而获得。这种间接式获取途径,使得奥古斯丁对柏拉图学园派、亚里士多德逍遥派、新柏拉图主义等希腊哲学原始语言文献存在误读甚至混用的嫌疑。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在《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中,奥古斯丁居然无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主义与斯多亚学派关于圣哲和凡夫情感特质的重要区分,声称“斯多亚同柏拉图学派和逍遥派的分歧只是言词上的,不是实质的”。(12)奥古斯丁:《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中,第4页。奥古斯丁这些违反常识的、“冒失”的混同言论,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批评并引起学界长时间的争论。这些批评不仅出于奥古斯丁不擅长希腊文这一语言方面的因素,也涉及其对希腊东方的古典情感哲学基本理论的某些障碍性理解。以下,笔者试图以如上奥古斯丁与希腊古典哲学流派关系为背景,详细考察当前学界关于奥古斯丁障碍性理解的争锋性观点及其各自依据。
二、奥古斯丁关于希腊哲学怡情观障碍性理解的争论
牛津大学古典学教授索拉吉是较早提出奥古斯丁障碍性理解的代表性学者。其关于奥古斯丁的批判主要集中于世纪之交出版的名作《情感与心灵和谐》(13)Richard Sorabji, Emotion and Peace of Mind:From Stoic Agitation to Christian Temptati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撰写这部名作过程中,索拉吉访问了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宗教学院,并与芬兰学派重要代表如西蒙·科努提拉(Simo Knuuttila)、瑞斯托·萨瑞宁(Risto Saarinen)、曼多马(Tuomo Mannermaa)等奥古斯丁研究者有深入的互动。交锋性的观点亦体现于科努提拉的代表作《古代与中世纪哲学中的情感 》(Emotions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Philosophy)一书中。中。该书较系统地梳理了从斯多亚主义“心灵侵扰”观到基督教“诱惑”思想传统的教义演进,在古典学与奥古斯丁研究领域有相当影响力。其中指出,奥古斯丁对希腊古典哲学的怡情理论以及彻底根除情感波动的圣哲之境有实质性的误解;这种误解不单局限于“怡情”概念,而且是对斯多亚一系列情感心理学重要范畴均有连环式的理解障碍。(14)Sorabji, Emotion and Peace of Mind, pp.206-209,471.仅就“怡情”概念,索拉吉便指出奥古斯丁有如下两点“致命性”误判:
其一,奥古斯丁将圣哲才拥有的指向善好的理性价值判断与愚者情绪化的头脑错误价值判断相等同,明显混淆了怡情的不动情特质与凡夫情绪波动之间的界限,并臆断圣凡两种情感状态仅是术语之争,而非实质性的不同。(15)Sorabji, Emotion and Peace of Mind, pp.206-207.
其二,怡情展示的是古典哲学家不动情的精神理想,奥古斯丁却将此摒除尘世情绪波动的美好境界等同于“麻木”“冷漠”与“不仁”,这构成了奥古斯丁在思考社会道德与责任问题时的理解性障碍。(16)Sorabji, Emotion and Peace of Mind, p.206.
对斯多亚哲学“怡情”概念内涵的诠释,索拉吉采取了折中立场:一方面,“怡情”是“好的情感”,其本身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或许可以包含普通人的一些正确的价值判断,如理性支配下的情感状态,但却绝不含有“愚者”情绪盲目冲动这种错误的头脑价值判断;另一方面,“怡情”中的某些情感属于理想精神状态,只有圣哲才配享有。(17)Richard Sorabji, “Did the Stoics Value Emotion and Feeling?”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Vol.59, 2009, pp.155-156.因为“怡情”具有非常复杂的含义,既包括一些普通情感(仅限于理性完全掌控下的好的情感),也包括圣人完美的不动情的精神境界,所以,奥古斯丁对这一术语的解释是不全面的。为便于理解,笔者将索拉吉所阐述的“怡情”种类及其特质列示如图1:(18)索拉吉的怡情列表及其三种类型,取自安多尼库斯(’Aνδρóνικο)的《论情感》、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哲人言行录 και των εν 7.116)、西塞罗的《图斯库卢姆辩论》(Tusculanae Disputationes, 4.12-13)以及亚历山大城的克莱曼特( )的《杂论》(Stromateis 2.9.42)。见Richard Sorabji, “Did the Stoics value emotion and feeling?”, pp.150-162.

图1 怡情的种类及其特质
依照索拉吉的解释,怡乐是心灵的膨胀,谨慎则是心灵的收缩;怡乐可以明显看出是一种情感,谨慎则不必然如此;“怡情”这种圣哲式的理想情感状态及其三种类型皆是头脑的理性判断。换句话说,无论心灵的膨胀还是收缩,这些理想情感均是稳定与适宜的状态且兼具理性。(19)Sorabji, Emotion and Peace of Mind, pp.48-49.索拉吉认为,谨慎是对抗恐惧的一般性情感,因此,“怡情”事实上也囊括一些普通的情感,只不过这些普通情感也被纳入了理性框架下。这样,奥古斯丁容易被误导而形成怡情与普通情感无实质区分的结论。奥古斯丁将怡情这一指称圣哲心智的“良性判断”曲解成了凡夫所持有的冲动性情绪,从而导致了其障碍性理解。
在索拉吉看来,更深层次的障碍乃是奥古斯丁把古典哲学家所向往的怡情状态当成了冷漠。怡情或许包括一些冲动,但这些是理性的冲动。(20)索拉吉这里采取了殷伍德将怡情视为智者的一种“冲动”的说法。见Brad Inwood, Ethics and Human Action in Early Stoicism,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5, p.173.与其说是麻木或冷漠,不如说这些冲动是理性控制下心灵的自然反应。而且,怡情与善行紧密相连。从良善心理状态与善行这两个角度看,奥古斯丁均实质性地误解了希腊古典哲学中“怡情”这一指称圣哲状态的情感境界。(21)Sorabji, Emotion and Peace of Mind, pp.50-51.
奥古斯丁混同圣哲怡情之境与冷漠关系的观点,其实在殷伍德与布兰宁两位古典学家那里均已作了理论准备。比如殷伍德就提出“不动情即是怡情”:(22)Inwood, Ethics and Human Action in Early Stoicism, p.173.在理性的完全掌控下,无论冲动,还是不动情,皆是常乐平静的理想心理状态,且指向善行。“不动情-怡情-善行”的链条乃是怡情状态的题中之义,怡情与冷漠毫无关系。这种论断得到布兰宁的共鸣,并进一步指出斯多亚哲学家所指称的怡情之境并非一种冷漠,而是一种平静之乐与宇宙情怀。(23)Tad Brennan, “The Old Stoic Theory of Emotions,” in J. Sihvola and T. Engberg-Pedersen, eds., The Emotions in Hellenistic Philosophy, Dordrecht: Kluwer, 1998, pp.20-70,57,69.
然而,上述观点受到一些现代学者的质疑。如,彼得金与凡瑞尔就把奥古斯丁的诠释视为新解。彼得金认为,奥古斯丁某种程度上重新定义了斯多亚所追崇的理想情感境界,虽然奥古斯丁对不动情的解释可能出现了一些障碍,但他保留了这个概念的不动情特质,并将此理想境界阐发为末世论意义上圣民的情感状态。(24)Peter King, “Dispassionate Passions,” in Martin Pickavé and Lisa Shapiro, eds., Emotion and Cognitive Life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1.凡瑞尔则从亚里士多德主义“乐”的概念来解释奥古斯丁的立场。他认为,奥古斯丁表面采取了斯多亚的怡情术语,实质上却是套用亚里士多德的情感理论。因为,奥古斯丁接受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心灵三分论,而不是斯多亚哲学家完全排除情感的心灵一体论;在这种心灵结构论基础上,奥古斯丁认为未来上帝之城中,亚里士多德所谓的“乐”和“爱”这两种情感依然会保留。凡瑞尔指出,奥古斯丁实际上是把斯多亚的怡情理想与亚里士多德关于乐的定义进行了嫁接。(25)Gerd Van Riel, “MENS INMOTA MOTA MANE: Neoplatonic Tendencies in Augustine's Theory of the Passions,” Augustiniana, Vol.54, 2004, pp.522, 524,530.
综上所述,索拉吉、殷伍德与布兰宁等秉持奥古斯丁障碍性理解论的学者把怡情解释为理性完全掌控下的精神状态,比如理性冲动与理想之境等,但这些怡情特质没有一种与冷漠相关。这样,奥古斯丁将怡情混同于冷漠的做法犯了根本性错误。而彼得金与凡瑞尔所代表的另一种观点,则强调奥古斯丁保留了古典哲学家的怡情理想,并将其与亚里士多德的情感观相联系。接下来,笔者将分别回到斯多亚哲学家与奥古斯丁关于怡情的界定,深入考察圣哲与凡夫情感的异同。
三、斯多亚暨希腊古典哲学中怡情的种类及其特征
从索拉吉及其所诠释的古典哲学怡情特质可知,意志、怡乐和谨慎是圣哲情感状态的三种主要类型。对奥古斯丁而言,获得斯多亚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通过西塞罗的作品。其中,《图斯库卢姆辩论》占据相当的分量。在该著特别是第四卷中,西塞罗列举了一些斯多亚代表性哲学家有关怡情的定义。西塞罗认为怡情代表着一种理性,无论是神经冲动还是安静祥和的精神状态,均合乎自然秩序。依照情感的品质好坏与发生时间,可将情绪分为以下四种:兴高采烈(现在的好)、欲望(未来的好)、苦恼(现在的坏)、恐惧(将来的坏)。相应地,怡情也可以类似方式进行划分:怡然之乐(现在的好)、意志(将来的好)、警惕(未来的坏)。综合西塞罗所记录的经典斯多亚情感理论划分法,笔者将圣哲境界(怡情)与凡夫情感(情绪)的种类及特性进一步归纳如图2:

图2 怡情与情绪的种类及其特质
可见,怡情之境所包含的意志、怡乐与谨慎均指向心灵的理性收缩或膨胀且与美德相连,而情绪的四个种类则指心灵的非理性动荡,展现出心灵结构过度的、非顺从的运动状态。基于斯多亚这两种心灵不同状态的理论预设,我们可将圣哲与凡夫情感之异同总结如下:
首先,圣哲怡情之境虽指称心灵理性的扩张或收缩状态,其与凡夫的情绪均指向同样的外在对象并常常呈现出相类似的表征。在斯多亚哲学家看来,虽然怡然之乐与兴高采烈同样是心灵的扩张,但两者区分是显著的。然而我们从外在看,却很难评估其中的界限。它们的不同或在于,怡然之乐是一种引向安静满足的理性冲动,其基于一种良好的态度,而不是冷漠;兴高采烈却是心灵过度的冲动,与理性相违,且基于对外在对象的激进判断。例如,面对美色诱惑时,圣哲或智者会呈现一种淡然之乐(对外在诱惑进行谨慎评估),凡夫或愚者则表现为一种较强烈的情欲。然而两者均呈现外在的善好,其喜爱的倾向性并无显著不同。
其次,判断圣哲与凡夫情感的重要衡量标准是“是否合乎理性”以及“是否基于强力意志”,然而这种意志和理性的法度很难判断。合乎理性乃指心灵的所有冲动均在正确理性框架下指向善好。只要冲动是理性的,那么行为则不是“过量”或“不合时宜的”。相反,如果评估是非理性的,则相应的行为则是典型的过量和不健康的。然而,如何合乎理性以及何以评价的确非常困难。这就为解构圣哲情感而与凡夫情感相等同提供了一些可能性。
再次,圣人怡情之境虽与安宁、恬静、稳重的心智密切相关,然其与凡夫在面对诱惑时所呈现的满足自我欲望的深层动机是一致的。斯多亚学派认为真正的哲学家并不对外在事物做价值分辨,也不会升起特别的欲望或兴趣。这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评估。(26)Martha Nussbaum, The Therapy of Desire:Theory and Practice in Hellenistic Ethic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399.也就是说,斯多亚所标榜的圣哲不动情,在某些场合如面对美色诱惑时,并非与凡夫的欲望冲动有实质性的不同,因为两者均呈现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满足自我期望的选择特征。
可以看到,传统意义上斯多亚所崇尚的“怡情”是基于理性的正确价值判断以及强力意志控制下的善行,这种至善唯有极少数圣哲才能实现。然而,怡情并非与凡夫情感完全无契合点。在面对诱惑时,两者不仅显示出外在喜好的相似表征,而且内在的价值判断也皆具自我为中心的特点。无论怡情还是情欲冲动,均是心灵这一相同官能的扩张或收缩。这就意味着,“是否合乎理性”或“意志是否足够强劲”是衡量情感究竟属于圣哲还是凡夫的关键。换言之,“意志”和“理性”是评判情感品质问题的核心范畴。基于上述分析,让我们回到奥古斯丁文献来看他的诠释轨迹以及批判动机。
四、奥古斯丁诠释立场的转型及其对怡情问题的反思
在奥古斯丁早年的思考中,他倾向于将怡情解释为“不动性”。这种不动性可使人抵达心灵安宁状态。他强调,如果个人的心志紧随理性且意志不动摇,就可实现幸福生活和不朽的生命。而且,他赞同斯多亚关于圣凡情感分判的观点,认为圣哲享受一个更为稳定和圆满的存在,而凡夫因背离了至善而转向一种缺陷的状态。在如下早期著述中,奥古斯丁正面评价了斯多亚暨古典哲学主张的不动情的怡情状态及其连带的多种美德:
(1)理性(真理)本身即在那最高存在上,其中也包含不变性……如果不脱离理性(真理),心志不会被消灭……心志不会背离理性(真理)而遭受损失,否则它自身会堕入愚蠢。(27)《论心灵之不朽》第六卷第十一节。中文为笔者译。本文拉丁原文若非特别说明,均引自Brepolis电子数据库所收录的拉丁教父原文文献(http:∥www.brepolis.net/)。
(2)造成恐惧的原因基于不可否定的事实,即愚蠢的心智出于某些缺陷的状态,而智者享受一个更加稳定和圆满的存在。但不可怀疑的是,如果最聪明智者的头脑发现了真理并毫无改变地与其合一,并与圣爱联合,则其真理性就不可动摇了。(28)《论心灵之不朽》第十一卷第十八节。中文为笔者译。
(3)因此,心灵的需要唯有愚蠢。我说,它是智慧的对立面……幸福的生活应该是悲惨的对立面,其中没有中间状态……每个人不是愚蠢就是智慧。(29)《论幸福生活》第四章第二十八节。中文为笔者译。
(4)我们生活于伟大的心志安宁之中,使精神远离身体的羁绊,而且,远离欲火的侵扰。我们最大限度地遭受痛苦,乃是为了培养理性,即是说,依照精神的神圣的部分来生活,这个就是我们昨天同意的关于幸福生活的定义。(30)《驳学园派》第一卷第四章第十一节。中文为笔者译。
(5)审慎是我们应该追求和避免的知识……刚毅是心灵的性情,借此我们逃避所有不属于我们力量掌控范围的不合时宜的、悲惨的事情……节制是对我们的欲望错误指向的限制……正义是我们所说的美德而应赋予每个人。(31)《论自由选择》第一章第十三节。中文为笔者译。
奥古斯丁崇尚“不变性”力量,并认为这是最高存在的特性。如果心灵与永恒不动的理性合一,就会显示出一种稳定的状态而永不腐朽,如例(1)所示。在(2)(3)中,奥古斯丁强调,圣哲是心智与不变的理性(或真理)相结合,从而展现出圆满的怡情状态,凡夫则背离理性而呈现情感的愚蠢。远离情绪干扰、享受安宁稳定的生活是圣哲精神的特质,而愚者却往往为情绪或情欲所左右。非理性的心灵运动打破了静态平衡结构,使其变得失序、不确定,这与圣哲怡情“不动性”的完美之境相去甚远。此处奥古斯丁的论证与斯多亚强调理性和静态宇宙自然秩序的立场是相一致的。(32)罗明嘉认为奥古斯丁的自然秩序观受到了柏拉图主义静态宇宙结构论的影响(罗明嘉:《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中的社会生活神学》,第28-31页)。然而,此处笔者更加倾向认为,早年奥古斯丁关于心灵秩序的论述与斯多亚主义静态宇宙自然观的关系似乎更加密切。因此,在(4)(5)中,奥古斯丁高度赞扬了斯多亚不动情精神状态及其追求至善中所培养的美德。这些例子反映出奥古斯丁早年对斯多亚怡情心性理论及其背后的自然秩序论相当熟悉。然而,在晚年著作中,奥古斯丁的论调变得颇为不同:

起初,奥古斯丁关于怡情的阐述紧随西塞罗对斯多亚教义的刻画。他首先重复了之前关于怡情及其三种类型(意志、怡乐、谨慎)的特质,如指向真正善好、唯有圣哲拥有等内容,并与凡夫波动性的情绪相区别。这其中决定性的力量乃是“意志”,因为圣哲的意志指向善好。这些与斯多亚暨古典哲学家的教导相符。然而,“意志”这一衡量圣凡的标准,奥古斯丁在接下来的论述中表示了怀疑,因为“意志”可以是罪恶的。他援引《圣经》来重新审视之前的论点:“在地上平安归与有好的意志的人。”(34)奥古斯丁:《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中,第197页。同见《以赛亚书》(57:21)、《路加福音》(2:14)。奥古斯丁在此质问,假如意志仅指好的意志,为什么在意志的前面需累赘地加上“好”呢?而且,即便是在古典哲学家的著作中,一些“怡情”的类型如怡乐/喜乐等也与罪恶相关,而情绪或情欲也可作为好词用:
西塞罗这个最雄辩的演说家说:“元老院成员们,我欲仁慈。”因为他此处把“欲”当好词用……特伦斯在谈到下流少年不健康的熊熊欲望时说:“我所愿的,不过就是菲鲁美娜。”这里,他的意志指的就是淫欲……就在维吉尔极为简略地谈到四种搅扰的诗行中,他把“喜乐”当坏词来用:“有惧,有欲,有悲,有乐。”同一个作者还说:“心术不正的喜悦。”(35)奥古斯丁:《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中,第197页。
结合以上西塞罗、维吉尔以及其他古典哲学家关于怡情的描述,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驳异教徒》卷十四第八至九章中给出了如下三点评述:
(1)好人和坏人都可以有意志、谨慎和喜悦;换言之,好人和坏人也都可以欲、惧、乐。但好人以好的方式,坏人以坏的方式使用,正如人的意志可以正直也可以下流。
(2)至于哀,斯多亚学派认为,它不能在智慧者的心灵中发现,我们却发现它可以用在好事上,特别是在我们的圣经中。
(3)如果这个城中的一些公民行为节制,好像能控制情感,他们就会变得极为高傲,不敬之心更加膨胀……与其说他们得到了真正的平静,不如说他们彻底失去了人性。心硬未必就正直,麻木未必就健康。(36)(1)(2)(3)引文,见奥古斯丁:《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中,第197、203页。
这些语调已不同于斯多亚或其他希腊哲学家的教义了。首先,论点(1)明显违背了最基本的斯多亚立场,即“怡情”不可能是坏的,而只能指向真正的善好。然而,将“怡情”与“情绪”相等同,奥古斯丁甚至背离了他自己之前的解释。其次,论点(2)中所述的“哀”当然不属于斯多亚所说的圣哲情感,而奥古斯丁却说哀伤可以用在好事上。更重要的是,在论点(3)中,奥古斯丁将某些刚硬的公民(此处隐指斯多亚哲学家)所谓的心志安宁称作愚蠢和高傲,也与其之前的立场相异。如果我们把目光仅停留于此,索拉吉所谓的奥古斯丁误解斯多亚怡情观的结论似乎颇有道理。然而,奥古斯丁接下来的论述却发人深省:
(4)这种触动(笔者注:即波动的情绪),这些来自对善好的爱,来自神圣的慈爱,如果被称为罪过,那么我们就会把真正的罪过称为德性。
(5)主自己(笔者注:即基督)也取了奴仆的形象,屈尊过人的生活,他一点罪也没有,但还是在他认为该使用的时候使用那些情感……在临近受难的时候,他的灵魂也曾哀伤。
(6)既然我们要承受此生的虚弱,如果我们根本没有这些情感,那我们就不能正直地生活……如果我们要按照上帝正直地生活,在此生就要避免这无情;而在那所应许的永恒的真正幸福中,我们当然希望无情。(37)(4)(5)(6)引文,见奥古斯丁:《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中,第200-202页。
显然,奥古斯丁并非不希望拥有斯多亚哲学家式的“无情”或“怡情”的理想境界,因为,如果想过幸福生活,则持久的、安宁的、不动荡的心志是必需的。但这种理想的不动情在尘世中难以长久维持,而且如果完全没有情感,那生活就没有正义。这显示了奥古斯丁对斯多亚暨古典哲学家怡情之境的定位相当准确。然而,奥古斯丁把更多的目光放置于情感的正义性问题,特别是情感的波动性在此生中的价值。不同于斯多亚与希腊古典哲学家将强力的“意志”或“理性”视为评定情感好坏的标准,奥古斯丁看到了道成肉身的基督所具有的谦卑、诚挚的大爱,特别是其临近受难时所展示的包括哀伤、忧愁、落泪在内所有人类可能拥有的虚弱的心灵触动。这些情感非但没有罪过,而且显示了强大的力量。也即是说,奥古斯丁将衡量圣凡情感品质的“标杆”定格于基督的虔敬德性及其背后超越的神圣慈爱之上。从这种标杆再回看斯多亚以及古典哲学家所谓的刚强意志和情感,才显得自私、麻木甚至邪恶。(38)奥古斯丁:《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中,第203页。
由此可见,奥古斯丁对希腊古典哲学怡情理论的理解非但不是障碍性的,而且直击情感伦理的问题实质。其评价圣凡情感的标准已经发生了价值转型。作为希腊古典哲学家定义“美德”的核心性范畴“意志”与“理性”,在晚年奥古斯丁看来,均已不再可靠。因为,在原罪处境下,这些官能的根本功能已经被扭曲和削弱,显现出指向“自我”与“尘世诱惑”的“重量”特质。(39)罗明嘉较深刻地揭示出了“意志与爱的重量”概念所透射的偏离自然秩序而从高转向低的“倾向性”,参见罗明嘉:《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中的社会生活神学》,第41页。斯多亚与柏拉图-逍遥派一直强调情感需服从理性与意志。但现实情况是,由于罪的压倒性力量,人们的意志很容易顺从情欲与尘世的诱惑,指向私欲和骄傲,而不是追求真正的善好。从这种罪的棱镜角度来透视,古典哲学家所谓的圣哲抑或英雄的不为情所动的怡情状态,其实质正是冷漠、傲慢、不健康与非道德。为改变这种唯理性主义与唯意志主义的傲慢,奥古斯丁认为,“意志”应该服从“圣爱”。在笔者看来,这种意志的“服从”恰恰是因为“圣爱”展现了更大的诱惑、慈爱与甜蜜,将深陷罪恶捆绑处境下的“意志”解放出来,从而实现“意志”的扭转并协助情欲指向更高级的善好与自由之境,而不是堕落、腐败、私欲与邪恶。在这个意义上,神圣慈爱(圣爱)扭转下的意志才构成了奥古斯丁评估圣哲情感品质的新的标准,并深层次地透视出充满堕落特质的尘世“重量域”与未来神圣之城“自由境”间的动态人类学张力。
五、结 语
通过对斯多亚怡情观和奥古斯丁诠释轨迹的分析,可以看到,奥古斯丁早年追随希腊古典哲学圣哲不动情和怡情的精神理想,向往摆脱尘世情绪波动与情欲诱惑的生活状态。但其后来变得越来越悲观,认为圣哲如此完美的情感状态在尘世堕落境遇中是不可能实现的。“无情”的生活非但不正义,而且不健康。奥古斯丁对斯多亚暨古典哲学怡情理论的把握,显示了其诠释并非基于当代一些评论者所认为的“障碍性理解”,而是从动力人类学综合角度重新评估圣哲与凡夫情感特质及其实质,因为他深刻地意识到古典哲学家所依赖的核心评判官能“意志”与“理性”已经被削弱了。奥古斯丁对情感本质和特性的观察植根于其“双城”理论以及“意志与圣爱”关系的深度思考,对意志官能朽坏的洞见以及对神圣慈爱的依赖,使得奥古斯丁的视野展示出一种内在张力。正是这种“意志重量-恩典提携”间充满张力的视角,才透视出希腊古典哲学家(特别是斯多亚学派和柏拉图-逍遥派)唯理性主义与唯意志主义的傲慢。因为,不为情所动的所谓圣哲怡然之境,在晚年奥古斯丁看来,不仅仅意味着个人层面的堕落与非道德,也构成了社会伦理学意义上逃避苦难、自私自利与麻木不仁现象的一个深层次原因。(40)奥古斯丁:《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中,第203页。
综上所述,奥古斯丁把希腊古典哲学流派关于圣哲与凡夫情感属性及其种类的讨论转入神学人类学充满内在张力的动态视阈,其晚年对怡情理论的混同不是一种障碍性理解,而是直击斯多亚主义、柏拉图主义以及亚里士多德主义等哲学流派唯理性主义弱点基础上的故意等同,代之以神圣慈爱提携下的意志作为重估圣凡情感好坏的根本标准和原则,从中揭示出摆脱私欲与诱惑的可能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