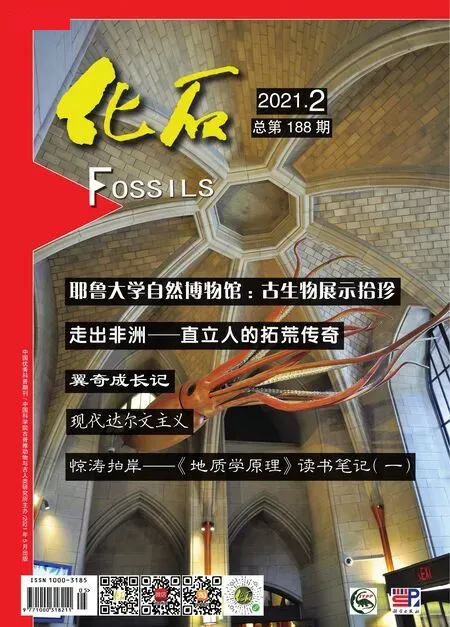现代达尔文主义
郭建崴 徐波
“现代综合进化论”诞生
前文谈到,20世纪20~30年代群体遗传学创立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在进化论中逐渐恢复了主导地位,其中最重要的三位学者——费雪、莱特和霍尔丹的作用尤为突出。但是这并不是要忽视其他学者的贡献。而且,这三位学者的著作满是艰深的数学语言,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对当时生物学界的影响。
实际上,英国数学家哈迪(G.H.Hardy,1877~1947)在1908年、德国医学家温伯格(W. Weinberg,1862~1937)在1909年就各自独立地提出了遗传平衡定律,指出在一个随机交配的大种群中,如果没有突变、迁移和选择等因素的影响,这个种群的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就可以稳定不变地代代相传,保持平衡。这个定律后来被称为哈迪-温伯格平衡。然而,他们的这一工作在当时也没有引起相关学者的注意。
几乎就在费雪、莱特和霍尔丹论证进化论的遗传学原理的同时,前苏联学者契特维里柯夫(S. S. Chetverikov,1880~1959)在1926年发表了题为《从现代遗传学观点看进化过程的某些特征》的论文,基于对果蝇自然种群的研究,指出种群内隐藏着大量的遗传变异;这些变异大多数是隐性的,在纯合状态下会致死,但如果以杂合的形式存在,则其基因频率就能以符合哈迪-温伯格平衡的形式代代相传;如果自然选择对它们产生作用,便会导致生物的进化;种群越大、显现出“隐藏”变异的可能越小,种群越小、显现出“隐藏”变异的可能越大,因此可以推测小种群比大种群进化更快。遗憾的是,契特维里柯夫的论文以俄文在前苏联发表,当时没有被西方学界所及时了解,随后又因李森科主义的流行而在前苏联绝迹。
不幸中的万幸,生于沙皇俄国的美国移民学者杜布赞斯基(T. Dobzhansky,1900~1975)把契特维里柯夫学派的影响带到了西方,并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于1937年出版了《遗传学与物种起源》一书,将群体遗传学的成就与摩尔根学派建立起来的染色体遗传理论以及自然种群中观察到的变异结果进行了综合,把达尔文的进化学说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以通俗的英语写成,很快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成为“现代综合进化论”诞生的标志。
进化的驱动因素
杜布赞斯基等群体遗传学家对有性生殖生物种群的遗传过程及进化深入分析的结果,可以简要地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有性生殖的生物个体,其基因型可能并非世代不变地延续,但种群的所有基因的总和却相对恒定。在一定时间内,一个种群组成成员的全部基因的总和被称为这个种群的基因库。
根据实验种群的遗传分析,摩尔根经典遗传学派认为,种群中各个基因位点上的正常型(通常是野生型)等位基因的纯合子占优势,突变等位基因在负选择的作用下保持极低的频率。但是对于自然种群的遗传分析表明,种群内大多数基因位点上存在着一系列的等位基因,它们以不同的频率保持在种群中;种群内大多数个体在大多数位点上表现为不同等位基因的杂合子。
对许多物种的自然种群的遗传结构进行分析后发现,自然种群中包含着大量的变异储存,这对种群是有利的,因为种群内基因型越多、其所对应的表现型范围就越宽,从而使种群在整体上越有适应于可能遇到的更加多样环境条件的能力。
哈迪-温伯格平衡只出现于理想种群中,而在自然种群中的实际情况是,突变、迁移、自然选择以及偶然因素等都能引起种群基因频率变化。
假设一种最简单的情况,以一个位点上的等位基因为例,假设这一位点上存在两个等位基因A和a,其频率分别为p和q(p+q=1),同时假设第一代亲本基因型为AA和aa,有性生殖产生的第二代个体基因型虽然有了AA、Aa和aa三种,但是在符合哈迪-温伯格平衡的情况下等位基因总和的频率并没有变,依然是p和q。
如果哈迪-温伯格平衡被某种因素打破,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首先看突变。假如等位基因A以每个世代为u的频率突变成等位基因a,而a变为A的回复突变不发生、或回复突变频率v远远小于u,那么,突变本身就构成驱动种群内基因频率定向改变的因素,也就是说形成突变压。等位基因A的频率就以每个世代up的速率降低,而等位基因a的频率则以每个世代up的速率增长。可见,突变是进化的一个驱动力;而且,突变率越高,突变压就越大,驱动进化的力量就越强。
但是大量的研究发现,高等动植物的突变率一般很低(每个基因每世代的突变率通常只在1/100000数量级上下),因此单由突变压引起的种群基因频率的改变过于缓慢。就u=1/100000的情况而言,经过10代以后,等位基因的频率只改变0.5%。因此,如果所有的进化都仅仅由突变单独驱动的话,地球生命从无到有、并发展到今天如此之多样繁盛,那是不可能的。
再来看迁移。对某一种群来说,迁出会造成基因的流失,迁入可以引进新的基因,结果都会产生种群内等位基因频率的变化。如果种群足够大,迁出迁入的影响都不会对基因库造成大的冲击,但时,小种群发生较大规模的迁移时,种群遗传组成就可能发生大的变动。
自然选择无疑是改变种群基因频率的重要因素,因其是重中之重,我们在下文中专门介绍,在此之前先来看偶然因素以及其他的一些影响。哈迪-温伯格平衡原理只能在大种群中体现,而小种群中的有性繁殖过程常常引起遗传组成的漂变;灾害、环境波动以及其他偶然因素也会造成小种群遗传组成的大变化。
此外,繁殖方式也会使种群的遗传组成发生改变。隔离状态下的小种群、自体受精的生物、运动能力有限和配子散布受限制的生物以及一些有特殊婚配习性的动物都可能形成长期的近交,即近亲繁殖,其后果是种群内部变异量减少、遗传均一化。这种状况往往不利于适应变化的环境,但在某种特殊的条件下有利于种群保持已获得的适应特征。这一点充分体现于人类培育家养动物(特别是宠物)品种的实践中。
自然选择的重释及其作用
提到“自然选择”就必须先谈“适应”,因为二者就好比是硬币的正反面。达尔文最初并没有定义适应的概念,他在阐述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原理时使用的是“最适者”(the fittest),而且很快采纳了斯宾塞的口号式表述:“生存斗争,最适者生存”。据此,一些进化论学者就把适应与生存联系起来:生存即适应。然而生存与死亡是“全或无”的概念,不能定量地衡量适应或适合的程度。而且,“最适者生存”容易被机械地误解为同语反复:“什么是最适者?”“生存者。”“生存的是什么?”“是最适者。”
对于19世纪的达尔文主义者来说,自然选择是残忍的。进化的成功是从在战斗中获胜甚至消灭对手的角度衡量的。例如角,长久以来只是被当作反击捕食者和雄性竞争者的有利武器。虽然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中提到过一种假设:角可能是作为吸引雌性的装饰进化而来的——“假如角像古代骑士荣耀的配物,增添了牡鹿和羚羊高傲的外表,它们很可能由于这个因素而部分地发生过变化。”然而他很快又否定地说到“没有证据支持这个观念”,并继续按照“斗争定律”来解释角,坚信它们的优势就体现在“反复拼死的争斗”中。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就有些自相矛盾。用“生存斗争,最适者生存”来表述自然选择,这与他实际上要阐述的原理本质上是相悖的:首先,达尔文认为进化是通过自然选择而使微小的有利变异逐渐积累的过程,而微小变异的效应不大可能导致要么生存要么死亡的“全或无”后果;其次,如果生物仅仅生存却不能留下后代或留下相对较少的后代,则不能算是“最适者”,因为生存不与繁殖相关联则对进化毫无意义。
实际上,在《物种起源》中也有这样的表述:“在能够生存的那些生物中的最适应的个体,假定它们向着任何一个有利的方向有所变异,就有比稍不适应的个体繁殖更多后代的倾向。”
现代综合进化论在重新解释自然选择原理时,用“繁殖”代替“生存”来衡量适应,创造了“适应度”(fitness)这个新概念来定量地衡量适应的程度——某一基因型个体对下一代基因库的相对贡献被称为“达尔文适应度(简称为适应度)”。
也就是说,某一基因型个体的适应度是指该基因型个体所携带的基因传递到下一代的相对值。例如,一对等位基因的三种基因型AA、Aa和aa所对应的表现型存在差异(例如生殖力与成活率差异),这种表现型差异就会造成三种基因型个体之间繁殖几率出现不同。如果AA基因型个体比aa基因型个体留下多一倍的后代,AA基因型个体与Aa基因型个体表现型无差异,则它们的达尔文适应度(D)为:

这意味着aa基因型个体的适应度与AA基因型个体的适应度有0.5的差值,这个差值被称为选择值:

选择值s(aa)是基因型aa的淘汰值。只要不同基因型的个体有表现型差异,而且表现型差异影响了适应度,那么就会发生自然选择;选择的强度由适应度的差值、即选择值的大小体现出来。
现代综合进化论依据群体遗传学对自然选择做出了新的解释——选择发生在如下情况下:1、种群内存在基因突变和不同基因型的个体;2、突变影响表现型和个体的适应度;3、不同基因型个体的适应度存在差异。繁殖过剩并不是自然选择的必要条件,只要不同基因型个体的适应度存在差异,自然选择就会发生;但繁殖过剩是自然选择的保障条件,因为有选择的淘汰使种群付出了代价(淘汰个体造成的损失),需要靠超量繁殖来得到补偿。虽然大量的可遗传变异存在于自然种群中,但如果变异不影响个体的适应度,自然选择就不会发生。自然选择的含义就是“区分性繁殖”,曁不同基因型有差别地延续。
自然选择因此可以解释为随机变异的非随机淘汰与保存。变异为选择准备了材料,而且变异的随机性是自然选择的前提,如果变异是决定性的或“定向”的,自然选择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同时,自然选择作用于表现型,如果突变不影响表现型、也不影响适应度,那么自然选择就不会发生。
随着研究的积累和深入,杜布赞斯基的一些认识也有所发展。在《遗传学与物种起源》最初的版本中,他认为自然种群中大多数的变异是非适应性的中性突变,因遗传漂变而存留。可是后来在与莱特合作继续进行自然种群遗传学研究中,他发现曾经被认为是漂变保留下来的许多中性变异却表现出适应性,显然是自然选择作用的结果,进而他强化了自然选择是最重要的进化驱动力、并且是保持遗传多样性重要因素的信念。
“站在巨人的肩上”,杜布赞斯基还强调了物种问题,指出物种是生殖共同群体,不同物种因彼此存在隔离机制(包括地理隔离、生态隔离、行为隔离、生理差异隔离等)导致无法相互杂交而分开。同一物种的变异会因隔离机制而形成遗传组成略有差异的不同种群(例如因地理隔离形成的不同地理种群),这样的变异是导致它们进化成不同物种的必要条件。提升到了物种问题,才彻底完成了对达尔文进化论的遗传学背书。因为,无论什么原因造成种群中遗传组成或基因频率的变化,那还只是进化的中间过程;唯有新物种出现,才是达尔文《物种起源》所论及的进化的实现。
现代达尔文主义的全面胜利
杜布赞斯基的著作《遗传学与物种起源》的问世对实验生物学家和野外生物学家均产生了巨大影响,吸引了生物学各个分支的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来探索进化论。不久,英国进化论学者赫胥黎(J. Huxley,1887~1975,“达尔文斗犬”之孙)主编的《新系统学》(1940)和著作《进化论的现代综合》(1942)出版,后者综合了达尔文主义在生物学各个分支领域的成果。现代综合进化论与现代达尔文主义成了同义词。随后,三位美国学者——动物学家迈尔(E. Mayr,1904~2005)、古生物学家辛普森(G. G. Simpson,1902~1984)和植物学家斯特宾斯(G. L. Stebbins,1906~2000)相继出版了《分类学与物种起源》(1942)、《进化的节律和方式》(1944)以及《植物的变异和进化》(1950)等著作。他们均认为进化是突变、基因重组、自然选择与隔离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突变本身并不必然导致进化,只是为进化提供了自然选择的新材料。至此,现代综合进化论、曁现代达尔文主义日臻成熟。
1947年,“遗传学、分类学和古生物学共同问题委员会”在普林斯顿成立,来自于生物学不同领域的30位学术权威重申了一个共同的观点,即自然选择是一切适应性进化的机制。
20世纪50年代分子遗传学的兴起进一步推进了进化论的发展,到了1959年,学术界纪念《物种起源》发表100周年,标志的是现代达尔文主义走向全面胜利。
现代达尔文主义把进化的思想扩展到生物学的所有分支,以消除进化生物学与生物学其他领域之间的隔阂,也把现代生物学中各个领域的进展尽量融入其理论框架之中。现代综合进化论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对突变的遗传学实质形成了统一的观点,认为不连续的、激烈的突变和渐进的、细微的变异都可以用相同的遗传机制来说明,同时彻底否定了获得性状遗传和融合性遗传。现代综合进化论还是对达尔文认为生物的一切适应性进化都是自然选择对种群中大量随机变异直接筛选的结果这一观点的再次肯定,并进一步认识到生物个体作为一个整体是自然选择的主要目标。同时,也强调了地理环境因素等隔离机制对新物种形成的重要作用,更加深入地说明了物种形成的进化是渐进化。
回顾现代达尔文主义的发展,杜布赞斯基在20世纪70年代留下了一句名言:如果不用进化的眼光看问题,生物学上的研究将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