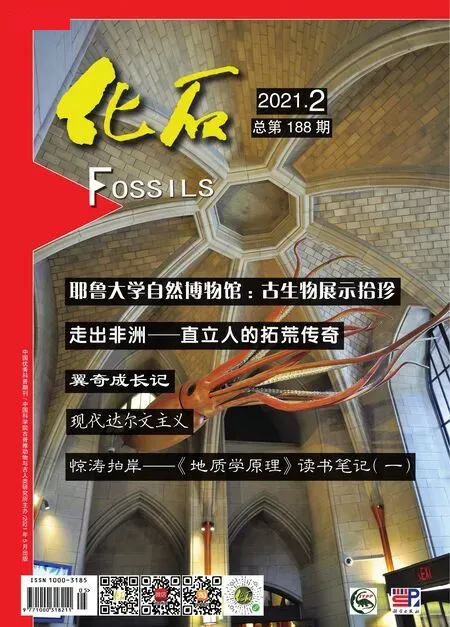中国公共考古及古生物科普活动的早期开拓者
——杨正纯(中)
陈宏光
古往今来,但凡是实绩大于虚名的文人学士,几乎都具有一种不计名利,倾心事业近至超凡脱俗的气质与境界。采访从小热衷于公共考古及古生物科普活动的杨正纯,大抵应证了此说。
多年以来,许多考古学家曾忽视了考古学与公众的关系,以至于使普通公众在考古学上没有什么话语权。而考古专业人士鼓励、组织公众考古爱好者参与考古活动,并在考古领域有所突破,有所建樹,才体现了公共考古学的威力所在。
杨正纯被称为“中国公共考古及古生物科普活动的早期开拓者”不是妄得虚名,而是在半个世纪以来不懈努力,在该领域多有突破性发现和学术建树为基础的。再略举一例,1985年5月,他和同事王世勋,根据宣威羊场煤矿子弟小学学生提供的线索,带领该校对考古感兴趣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在学校附近的一石灰岩溶洞进行考察,发现了一个新石器时代的洞穴遗址——花石洞遗址。其中有磨制石器、骨器和钻大圆孔的河蚌。这属于云南省曲靖地区发现的第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对曲靖地区史前文化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对抚仙湖水下古城提出质疑的第一人
只有真正的执着与诚心的敬业,才能使最平凡的人,在生命旅途的特殊时刻,闪烁出学识积累的亮丽光彩。在平凡中坚守是一种境界。
云南省玉溪市的澄江抚仙湖美景,可称人间仙境。而关于抚仙湖的种种神秘传说,更是引人入胜,甚至有些传说被称为“千古之谜”。其中,“古滇国”的历史是神奇之最,而围绕“古滇国水下古城”的探秘之举,曾几次引起轰动”。作为参与公共考古的热心人杨正纯,在“古滇国水下古城”探秘活动中,敢于利用自己考古学、地质学和建筑学的多学科综合优势,坚持公共考古人的独立学术观点,所做所为也令笔者叹为观止。以下,是根据杨正纯讲述的实录:
2001年6月3日,央视在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县举行了举世注目的抚仙湖探秘现场直播。对于此事,在2000年媒体报道抚仙湖水下遗迹发现之后,热心高原湖泊考古的杨正纯,就一直在关注此事。
直播这天,他一早就将录像机接在电视机上等候。当被中国最权威的建筑考古专家认为可能是古滇国古城遗迹的建筑构件一一在屏幕上显示出来,既是考古专家、又是地质专家、还曾经当过建筑工人的杨正纯,却感到权威专家的判断值得怀疑。在所有已发现的湖底遗迹、遗物中,除了那件底部破了一个洞的陶釜外,直播所显示的水下所有几何形态的大石块、石墙、台阶、广场和石间裂隙、石面孔洞、有圆弧转角的“人工地面用石板”以及用浮法打捞上来的“有人工雕刻花纹的建筑构件”和人工建筑粘合物等,好像都是自然形成的地质遗迹。为了慎重,上午10:38直播结束,杨正纯把录像带反复甚至定格仔细观看,认定了他自己的看法是有科学依据的。

报刊报道
但国家级著名建筑考古专家在直播前的媒体和直播采访中,却宣称;“抚仙湖水底肯定有人工建筑物遗址,确切地说,应该是‘构筑物’。因为目前还未探明,‘遗址’也应该说成‘遗迹’,而且不止一片,有很多片。所以说,抚仙湖水下目前应该有‘石头构筑物群遗迹’,抚仙湖下确实有石头构筑物群遗迹已经是完全证实的事实。”而且还将那雄伟的石建筑宫殿复原图展示给大家看。
看到这样缺少起码地质学依据的结论,杨正纯真是心如火燎,他担心这样的直播让国外既懂考古、又懂地质和建筑的人看了,会当笑话。于是他向直播现场的朋友打电话,想提醒他们不要随便下结论。但无法打通,后来才知道对参加直播到现场的人,都要求统统关机。
杨正纯实在无法,只好打到央视总部,请他们是否有办法将他的意见转达到直播现场?得到的回答是:“你有不同意见,可以在报纸等媒体上发表你的看法”。
但杨正纯想,央视热心热肠为云南做宣传,他去泼瓢冷水,会不会产生负面影响呢? 可是,他又考虑到,央视和国家级专家随便下结论,将给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大。他只好打电话到省委宣传部去咨询。得到的答复是:“没关系,这是学术问题,你可以将你的不同看法在报纸等媒体上发表。”于是,杨正纯的《水下难度大结论谨慎下》的文章于6月4日同报道6月3日央视《抚仙湖探秘》直播的新闻同时见报。
杨正纯的此篇文章,是与各大报纸报道央视《抚仙湖探秘》直播同时见报的第一篇对“抚仙湖下确实有石头构筑物群遗迹”首次提出质疑的文章,立即引起社会的广泛反响。
紧接着,一篇副标题为“抚仙湖水下之谜有新说”,而蓝色大字主标题为《杨正纯叫板考古队》的新闻,在报纸的头版刊出。
杨正纯见报后感到主标题这样写太过火,向报社总编提出意见,说这个主标题非常不好,人家考古队是国家级的考古队,而他只是个普通地质、考古工作者,怎么敢“叫板”,顶多只能是“商榷”。这样很不利于同行间的团结。主编却回答说:“虽然他们是国家级的,但他们只懂考古。而你既懂考古,又懂地质和建筑,对抚仙湖水下之谜提出的新说,一讲大家就明白,很有震撼力!你不用怕,我们认为,作为本媒体的‘一家之言’,用‘叫板’一词也非常的恰当。”
此文发表后,使得多家媒体记者前来采访杨正纯。多家报纸报道了采访“新说”第一人杨正纯的文章。但见报的这些文章,由于记者、编辑连夜赶稿,未经杨正纯过目,专业词汇错别字可不少。
杨正纯根据他从小对云南岩溶地貌予以关注和学习掌握的系统岩溶知识,以及他进行滇中高原第四纪地质和古人类调查研究时,对抚仙湖、星云湖和杞麓湖地质情况非常熟悉,知道抚仙湖是一个湖底和湖岸多为碳酸盐岩构成的高原岩溶断陷湖泊。用地质学原理与考古学和建筑学相结合,对水下几何形态的大石块、台阶、斜坡、“石墙”、广场和石间裂隙、石上花纹、石面孔洞等并非人工遗迹,而是自然地质遗迹加以一一说明。
利用自古以来人工砌石、砌砖要错缝而避免破缝的最基本建筑原理,指出那些厚度不等的近水平层状岩石被与层面垂直的一组节理破缝切割的岩石露头,不是人工砌的墙。若是墙,就不应当破缝。墙的里外两个墙面,应当竖立或平行。而岩石坎状露头,通常一面为与层面陡交的石壁,另一面为斜坡状层面。潜水探秘者耿卫发现的那个巨大石阶的大斜坡,实际上应当是湖底的一个单斜岩层露头,上面孔洞是天然溶孔。并指出,如果是人工镶的石板地面,相邻石板的花纹往往是不相连的。根据抚仙湖地质特点分析,湖中完全会沉淀出方解石粉末,这些粉末可以夹杂螺壳填充在湖底岩石裂隙中,而被误认为是人工建筑粘合物。
杨正纯强调,直播中显示了大面积的湖底台地,一堆堆散乱、垮塌状的岩块,台地上一片滚散的碎石块,犹如刚刚发生过地震与陷落一样,是研究抚仙湖成因和历史的珍贵地质遗迹。
当记者问杨正纯,你认为水下有古滇王国石建筑都城的可能性吗?杨正纯从考古学和建筑考古学的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从已知云南考古发现来看,从新石器时代的宾川白羊村和元谋大墩子遗址的粘土木结构房屋一直到清代几乎都是以土木结构为主的房屋建筑风格。明清以前云南的古城,也几乎都是夯土建筑。就连江川李家山21号墓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青铜房屋模型,晋宁滇王墓中出土“人物屋宇镂花铜饰物”的M6-22号和“杀人祭铜柱场面盖虎耳细腰贮贝器”上等4座西汉青铜房屋模型上显示的建筑,都属于“干栏式”建筑,也无石建房屋的迹象。
记者又问,你这样分析,水下石建筑遗址是不是不大可能?
杨正纯回答说,目前也不能这样讲,一般性和普遍性不能代替特殊性,或许古滇国都城真的出乎我们所料,具备了这一历代少见的特殊性,让水下考古工作最后确认了这里的确是一座水下古滇国都城石建筑群落遗址。但那时将又会给人们带来一个新的迷:为什么古滇国都城是石建筑,而石寨山、李家山等出土的滇王及其家族等墓穴却又是土坑墓?且石寨山的土坑墓旁几乎几米处就有与抚仙湖边同样的碳酸盐岩。杨正纯幽默的说,人们只好推测,2000年前的古滇王那时就有了“后事从简”的廉洁风范。(注1.2001年云南省省长李嘉廷腐败被披露)
记者又问杨正纯,那么你认为抚仙湖中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人工建筑遗迹?答:建筑遗迹肯定是有的,但那是华宁县地域抚仙湖东岸沉到湖中的大营村以及关圣宫的明清时期建筑,皆为土木建筑,水下发现过磨盘、青砖、瓦片。与附近寺内墙上石碑记载“乾隆五十四年”大营村沉入抚仙湖年代基本一致。
杨正纯对抚仙湖水下之谜提出的“新说”,赢得了云南省文化厅文物处、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绝大多数考古专家的认同和支持。
从水中唯一打捞上来200斤重的一块大石板,直播认为是一块人工刻有花纹的建筑构件,而杨正纯在屏幕上就认定是块自然石。后经云南多位未参加直播的专家进行详细鉴定,也认为是一块全天然的石板,上面的花纹都是天然花纹,并无任何人工痕迹。
报纸关注抚仙湖水下考古追踪报道称:央视直播大军一撤,一边是观众对其议论纷纷,一边还有专家否认或怀疑抚仙湖水下有古城。但杨正纯说:对于耿卫这个国际二星级潜水教练的水下探秘活动,不管水下有没有古城,耿卫的这种做法,这种精神,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这次央视直播结束后,探索者耿卫并没有放弃努力,他仍在水下不断地探索,希望再现水下古城的风貌,揭开水下古文明遗迹的谜团,发现了不少新线索。
五年之后,中央电视台与玉溪市合作主办,于2006年6月16日至22日,对玉溪抚仙湖进行第二次水下探秘。这次探秘活动,国家水下考古队和肯定水下有古城的最权威专家未再参加。参与的是向全国招募的潜水探秘选手和人数较多的涉及多门类、多学科的专家。而杨正纯作为特邀嘉宾,在电视上讲述了他认为抚仙湖水下“古城”遗迹是自然地质遗迹而不是建筑遗迹的依据和原理。
在第二次直播中,央视用了较多的时间考察、探究抚仙湖周边的文物古迹、神奇传说、历史文化和民族民俗,再现古滇国的历史文化。这给直播新添了不少知识性和趣味性。
至于水下发现岩石上的圆洞、“01”符号和人脸图像,被在场专家在电视屏幕上认定是人工刻制的文物,并声称“昨天一天发现就超过了5年前首次探秘的全部结果”。杨正纯坚持认为,岩石上的园洞,是溶孔,在湖下的碳酸盐岩上比比皆是。那张被认为是人工刻的人脸图形,是碳酸盐岩石面上典型溶蚀纹路显现的天然花纹、根本不具备丝毫人工雕琢特征。至于“01”符号影像没有显示,但在头一天发现的“IY”符号,具文字描述:“在石面上凸起来的,好像镶了什么白色的东西”,有可能是碳酸盐岩上方解石或白云石脉抗风化突出的天然花纹。

2020年5月,杨正纯再次来到抚仙湖原直播基地东风度假村
杨正纯的观点是,如果硬要把这些水下石头上的图形,说成是人工雕刻艺术品,那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人类一万多年前旧石器时代的崖画就相当具象了,以往在古滇国墓葬出土的许多青铜器,其上的人物、动物和建筑物那么具象、生动、精美,而能建盖那么庞大纯石建筑群的先民们,怎么石雕艺术水平会如此低下?
据在场有关考古专家对抚仙湖底所做的声纳探测显示推测,这座水下古城大约由8个石质建筑群组成,分布在南北长2公里、东西宽1.2公里的水域中,每个建筑群面积大小不等,区域面积约2.4平方公里。核心区域的5个建筑群基本连片,各个部分建筑体量各异,分布在9.8米至90米深的湖水中。
其中声纳扫描出的高19米,底部边长90米,被直播现场考古专家认为是祭祀高台的金字塔状物。但杨正纯从声纳扫描图上分析,觉得显示的是水下被溶蚀成的多台近水平层状岩石露头,特征很明显,不可能是人工建筑遗迹。
这次直播规定水下发现的东西一律不准拿上岸来,要原地保存。所以不会像上次直播那样,一大块“人工建筑构件”拿上岸来由专家详细鉴定而被否定。但这次所显示的视频图像非常清晰,对于有经验的既懂考古又懂地质的人来说,在屏幕或图片上是完全可以下结论的。
当时玉溪市、澄江县联手开展了这次大规模抚仙湖水下探秘活动。由新华网云南频道、玉溪新闻网、玉溪日报等联合,与央视同步对整个探秘活动进行全方位的网上直播,在第一时间通过互联网即时把水下探秘的过程、结果传向世界。然而开播仅仅40分钟,直播就神奇中断,草草收尾。观众明明感觉广告过后,回来就可以看见潜水员进入水下古城了,怎么后来就没有了呢,是不是突然发现了什么,所以只好把后面的节目减掉了?至今也不能找到当年的那段拍摄视频……而却在其他抚仙湖节目或网页上,出现了不少非常明显的水下人工建筑和水下“尸库人群”,但相伴的鱼不是高原淡水湖泊中的鱼,显示的人无论相貌穿着都是外国人。所以,“水下古城”迄今只是一种说法,尚无任何实证。
2009年7月,杨正纯辅导昆明南站小学在澄江举办探索和研究抚仙湖为主题的夏令营,特邀请著名水下探秘的国际二级潜水教练耿卫与小朋友搞了一次联谊晚会。会上耿卫讲述了他水下探秘的有趣故事,放映了杨正纯复录的央视探秘直播录相片。耿卫特意将他采集的抚仙湖不同深度的水样,赠送给夏令营。杨正纯赞扬耿卫说,无论最后探明抚仙湖中是否有古城,耿卫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2020年5月,杨正纯再次来到抚仙湖,在现划为樱花谷的原直播基地东风度假村,湖边精美的巨型石雕卷轴上,铭记了两次抚仙湖水下直播活动。但在挂着“水下古城遗址博物馆”大牌子的大厅内,全是游客休闲餐饮的接待场所。经仔细询问,才得知这里的“水下古城遗址博物馆”早已停建,在大厅边沿极不显眼
的一小片墙面上,稀稀拉拉挂着几小幅水下探秘照片,但那张被第二次直播认为是全部探秘活动中最辉煌的成就——祭祀高台的金字塔状物的声呐扫描图,图片说明中,却仅仅描述为“IVA区的水下遗址的声呐扫测图”。虽然此遗迹未定性人工或天然,但应当是整个抚仙湖水下探秘活动宣传中,对“水下古城”最科学、最实际和最负责任的提法。
为“玉出云南”增添了新的历史内涵
俗话说:“乱世藏金,盛世藏玉”。此说证明玉石由于特殊的美质和资源的稀缺而为世人视为珍宝。玉文化是中国从古到今传承不断的独有文化,更是中华文明史中极为灿烂的一页。先贤孔子以玉喻为君子品德,中华民族延伸数千年的玉文化更是创造性劳动的光辉历史。玉文化的核心是“玉德”,是“和谐”。玉文化的人文价值几乎代表了中华古文明的延续,也可称中华古文明的符号与载体。杨正纯从考古学、地质学和珠宝学(注2.杨正纯,2013。尊重翡翠民间俗语 正确理解心中有底。中国翡翠专业版,第二期。)多学科角度研究中华玉文化所取得的成果,必须提上一笔。
中华玉文化具有8000年历史,是根据迄今所发现最早用玉石磨制的饰品——内蒙赤峰兴隆洼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玉玦(距今年代为8000年)而定的(注:后来在黑龙江省饶河小南山史前遗址发现的玉器,碳14测年距今9000年)。
在此之前,人类是用玉石制造生产工具。80年代, 在辽宁海城小孤山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中,发现了一件用岫岩老龙沟产的玉石打制的砍斫器,距今一万多年。有的珠宝文献和互联网上,认为这是当时为止发现的最早使用玉石制造的生产工具。
其实,在比小孤山遗址更早,更漫长的旧石器时代里,我们远古祖先在打制石器所选择的石料中,就出现了岩、矿名称与玉石的岩矿名称相同的石料,只是存在是否达到玉质标准的问题。
那么,在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最早是什么时候使用玉石作为原料来打制生产工具的呢?
有一个长期被珠宝界不知、忽视甚至误传的事实是:1973年10月,考古工作者在对元谋人遗址进行发掘时,在距元谋人牙齿化石发现地点5米和20米处的相同层位地层中,发现了三件用“米黄色石英岩”打制的刮削器,被考古学家认为是元谋人打制和使用的石器。
从古至今,中华玉文化对玉石(或玉)的定义和分类,有狭义和广义,珍稀与常见,价值高低的不同而有不同认识。近现代矿物岩石学的科学理论和工艺技术及市场需求,与传统珠宝概念结合而成的珠宝科学,对玉石有了明确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在石英岩中,含杂质少,色泽美丽,质地细腻温润的就可以作为玉石,如北京郊区的京白玉,河南新密市的密玉,内蒙的佘太玉,以及东陵玉(也称东陵石)等。
经杨正纯观察,元谋人的三件刮削器的材质为细粒变晶结构,质地细腻温润,颜色米黄色,有一定的透明度,显然达到了石英岩玉的质量标准。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是我国迄今发现最古老的人类。因此,杨正纯认为,元谋人用石英岩玉打制的这三件刮削器,就成了人类使用玉石做工具的最早记录(云南珠宝2011年第四期P91)。

上图:元谋人用米黄色石英岩玉打制的三件刮削器;

下图:杨正纯与元谋人化石发现者钱方(右)合影
但以往的一些考古专家,他们只把传统的和田玉等玉石叫作玉。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以往的珠宝文献中,涉及到中华玉文化的历史,或者是云南玉文化的渊源问题,也有人往往会想到元谋人,但只懂珠宝不懂考古的人,却把元谋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3000年左右)中“用辉长岩、石英石等打制磨就的精美石器”误传为是元谋人化石产地发现的元谋人石器。
有趣的是,元谋人这三件刮削器的玉料,与当今盛世云南新出的中华美玉——黄龙玉很相像,化学成分和颜色、光泽、密度、硬度、折光率都相同。它们都属于石英质玉,只是因成矿条件不同,结构上有差异而已。石英岩玉为粒状变晶结构,而黄龙玉为玉髓的隐晶质结构。元谋人刮削器玉质的透明度和温润程度,不及黄龙玉中好的品种。
在元谋人遗址所发现的层位可靠且能称为工具的石器仅此三件,但都是用石英岩玉打制而成,其它的和采自地表的10多件石制品,绝大多数也是用石英岩玉打制。证明距今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就认识到这石英岩玉质地坚韧、细腻而温润的性质,对这种玉石情有独钟。但是否对这种象征国色的玉石颜色, 就有了原始审美意识而钟爱,则不能做定论。因为这些黄色(包括黄龙玉的黄色)往往是在后来埋藏的地层中经氧化铁离子染黄的。元谋人当初选料时,不一定是黄的。
笔者认为,杨正纯对“玉出云南”的历史含义,在原有翡翠出自古云南和翡翠文化出自云南的基础上,又为“玉出云南”增添了新的内涵。虽然还不能定论,但至少可以为玉文化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想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