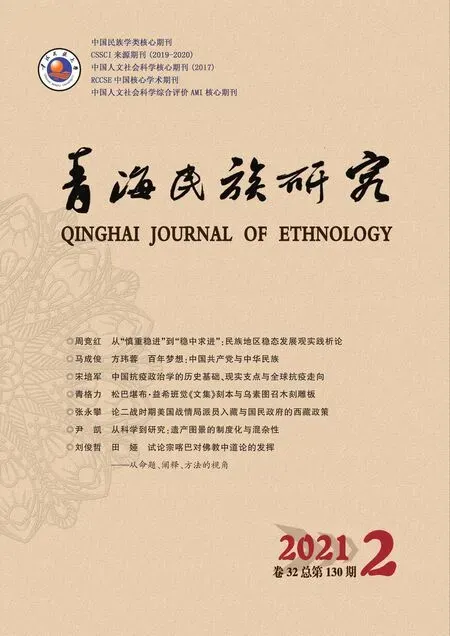医疗与建国:抗日战争时期西北开发中的夏河县卫生院研究
储竞争
(兰州大学,甘肃 兰州 730020)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列强交侵与军事、政经改革不尽如人意的压力下,国民身体的改造被视为“提升族力与国力的辅助手段”和国家改造的前提,由此“身体”成为国家权力的从属物,“在20世纪初叶变成一个众所瞩目的焦点”。[1]“病夫”想像的原罪感,亦“使得国民身体素质的检讨批评成为新的思想课题”[2],振兴“科学的医学”“注意民族健康”“把卫生思想普及于民众”,被认为是“民族复兴的先决条件”。[3]时至抗日战争爆发,以支持抗战、复兴国族为主旨的西北开发思潮勃兴,建设医疗卫生事业自然成为西北开发的内容之一。有鉴于此,本文以甘肃省夏河县卫生院为考察对象,探究社会政治特别是医疗卫生事业与边疆少数族群身体生成间的关系,以及西北开发中民族国家建构的实践经验。①
一、身体国家化与夏河县卫生院的建立
近代民族国家将“身体的‘殖民’权利由家庭和礼教体系转移到国家的手上”,“以身体的国家化作为建国和立国的基础”。[4]因此,民族主义者除强调国家对国民身体的规训外,同样关切人口的数量。如孙中山讲民族主义就“盛称列强人口增加,数目惊人;而仅仅以中国人口日渐减少为虑”[5]。他指出:中国“生长了四万万人”,这是“各国人所以一时不能来吞并的原因”。并警告说“如果我们的人口不增加,他们的人口增加得很多,他们便用多数来征服少数,一定要并吞中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不但失去主权,要亡国,中国人并且要被他们民族所消化,还要灭种”。[6]抗战爆发之后,“曩者认为荒凉不堪之西北”,一跃“成为中华民族之一大生命线”。[7]国人对西北的重视,与他们认识到“中国人口数之多与土地之大,实同为抗战必要之基本的二大因素”[8],特别是“就国防的见地说,人的因素也是同样的重要”[9]不无关系。在此认识下,战时西北开发思想虽不尽相同,但“消弭狭隘之民族界限,而完成大中华民族之建设”[10]构建人口繁众的国族,则为其共同目标。1941年,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加强国内各民族及宗教间之融洽团结,以达成抗战胜利建国成功目的之施政纲要”[11],正是国民政府及爱国精英力图把边疆各族群纳入国族范围之内,实现国家权力对边疆各族群“身体”的掌握以增强抗战力量的努力。
在上述背景下,拉卜楞寺所在的甘肃省夏河县,因其沟通汉藏的地理位置以及丰富的族群资源、特殊的宗教文化,被国人视为以实现国族团结统一、增强国家认同的理想之地。他们指出:地理上拉卜楞实为“川、甘、青、康的藏族心脏区域……与任何蒙藏区域,都有久远的历史关系,与浓厚而密切的感情,若言开发边疆,建设国防,拉卜楞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不会磨灭的”[12];宗教与文化上,“拉卜楞是西北一个喇嘛教的中心……其所辖的寺院在一零八个以上,分布于青、康、甘、川四省的边境……若能据住这个西北宗教的中心地方,得到一般人民的信仰,则不仅可以安藏,同时亦可以安蒙了”,同时“拉卜楞地方在汉藏民族的边缘”,[13]故“欲沟通汉藏文化,此实为枢纽要地”[14];经济上,“拉卜楞是一个汉藏贸易的要地……如能把握此点,使拉卜楞的经济与内地得到一密切的关系,则西北藏民对中央向心力亦必增强”[15]。总之,“夏河为西北藏族之中心”,“凡言发展边疆复兴民族者,此正为枢轴所在,不可以其偏僻而忽之”。[16]
然而抗战时期夏河县的实况,却离团结、康健的国族理想有不小的距离。一方面,拉卜楞地区虽设夏河县,但蒙藏同胞“极少政府之认识,故县府政令之不能推行”[17]。直至1940年,代理夏河县县长江树春仍报告称:“夏河设县,迄今十有三载,然边番榛莽,依然如故,多数部落,尚不知其为夏河所属”[18];另一方面,出于对“身体”的重视,“一般关心边疆人士,对于藏族人口问题都非常关心”[19],但据时人观察,拉卜楞藏族人口递减问题严重。而“藏族人口递减的原因……主要的是花柳病的传播”,具体来说:藏族“盛行婚前性的放任”,“很多人在年龄极年轻的时候就患花柳病”,加之“缺乏医药治疗,人民缺乏卫生常识”,“以致妨碍生殖”。[20]1941年的调查也显示:“夏河疾病甚多”,“加以社交自由花柳遍地,生育减少,死亡日多,人口繁殖,日频危殆”[21]。医疗设施与卫生常识的缺乏,不但阻碍了藏族人口的增殖,同时也严重侵害了他们的身体健康,以至“藏胞们外表看来好像个个都非常强壮”,但“流行在他们中间的疾病是太多了”。[22]从而使得西北开发事业因“人民生活体格不能健全,虽有良好建设,也无用处”[23]。
为解决夏河县在西北开发与国族建构中遇到的政令推行与医疗卫生问题,时人认为非在夏河“广设卫生机构,选派大批能够吃苦耐劳的医生护士携带药品前去解除他们病人的痛苦”[24],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因为,“先解除伊等切身疾病痛苦,易于接近藏民”,“政令推行”自会便利[25]。故此,1939年甘肃省卫生处成立后,虽“限于经费、人力,只能先择人口较多,地方重要之县份筹设卫生院”[26],仍于1940年首批在夏河成立卫生院,相较于甘肃至1946年底“尚有十九县局无卫生机构”[27],可知地方政府对于夏河卫生事业的重视。
二、夏河卫生院概况及发展困境
1940年,甘肃省卫生处派遣国立北京医科大学毕业生山西人吴炉青,前赴夏河筹备卫生院,并兼任院长。[28]同年10月10日卫生院开诊之日,夏河“各机关商号赠送对联锦标以相庆贺者计二十七八”。[29]至1944年“蒋介石允许拉卜楞致敬团之请”筹设拉卜楞医院,同年9月1日,“夏河卫生院医务人员,全数划入拉卜楞医院”,仍以吴炉青为院长。[30]夏河卫生院存在时间虽短,但作为甘肃西南的中心卫生机构,它的建立打破了夏河县“无医院及卫生处科之设置”[31]的历史,并承担着改善边疆少数族群健康状况、传播现代医疗卫生知识,乃至宣扬政府德意增强国家认同等方面的重任。因此,有必要对夏河卫生院职员、财务概况及工作中面临的困境作一梳理,以进一步深化我们对战时作为民族国家建构手段的医疗卫生事业在少数族群地区实践的认知。
(一)夏河卫生院的职员及财务
夏河卫生院作为甘肃省卫生处的下属机构,其医务人员的聘任,均须经卫生处审核后派发“委任状”方“完手续”。[32]卫生院所需药械及医务人员的薪资、办公费等开支亦均由卫生处提供,并执行严格的财务预算、决算制度。
职员方面,夏河卫生院初创之时仅院长兼医师一人,助产士、助理护士、事务员各一人。此后卫生院职员虽略有增加,但受经费与环境的限制,医务人员整体素质不高,不但专业医师严重缺乏,即便是稍具医疗常识的助理护士等也鲜有能长期坚持者。这些可由如下笔者借助档案还原的夏河卫生院职员信息概况表1中略窥一二。

表1 夏河卫生院职员信息概况表
除医务人员外,夏河卫生院还雇佣各类工役管理日常杂务。职员与工役的俸给费是卫生院财务支出的重要方面。如卫生院初创之时吴炉青“月支薪160元,助产士谢秀桐月支薪俸95元,事务员李敏月支薪俸70元,助理护士王东考月支薪俸30元,工役二名月支工资共30元”[33],共计385元。此后,随着职员增加和通货膨胀的加大,卫生院俸给费支出越来越多。如1942年卫生院新增医师张仁溥的月薪达240元。[34]同年,卫生院仅草地巡回医疗队的俸给费共为1,530元,其中俸薪1,130元,包括“队长兼医师一员月薪300元,护士二员月各支薪190元,翻译一员月薪160元,事务员一员月薪170元,录事员一人月薪120元”;工资400元包括“工役一人月支80元,厨役一人月支80元,饲养役三人月各支80元”。[35]
俸给费外,药费亦为夏河卫生院重要一项财务支出,如1942年卫生院全年药费为4,800元。[36]但药费因由卫生处以药品的形式按期分拨,故受环境与通货膨胀等因素影响不大。与之相对,卫生院的办公费,常因夏河“物资缺乏环境特殊,日用各物……系由临夏转运此地贩卖”,加以“一般货价均以硬币价值增减为起落,因之物价高涨”,每月“不敷甚巨”。如卫生院初创之时办公费“每月60元”,后虽“每月增加60元”,[37]但随着“物价逐月高涨”,卫生院办公费超支无年不有。其中1943年卫生院“全年度共计超支洋10,451元”[38],1944年“二月份起至十二月份止,共计超支洋11,429元”[39]。
需要指出的是,自1942年夏河卫生院参与“藏民区合作事业”开展“草地巡回医疗”工作后,卫生院每年在草地工作8个月,夏河4个月,故其财务支出亦分为草地与夏河两部分,且草地部分比例较高。这从卫生院1942年经费分配预算表2中能够清楚看出。

表2 1942年夏河县卫生院草地巡回医疗队经费预算表 单位:元
(二)夏河卫生院面临的困境
纵观夏河卫生院四年的发展历程,院长吴炉青曾感慨道“经费、药品、人才极端缺乏,规模尤为简陋!”[40]这一点我们从上述卫生院职员及财务状况表中可以想见。造成此一困境的原因,既有战时西北开发中普遍存在的经费、人才缺乏的问题,又有因夏河地理、族群环境而产生的特殊困难。
从经费上来看,战时甘肃省财政“异常拮据”,用于建设者“每年仅定30万元”,即便如此也常“因省库支绌,不能按额筹拨”。[41]而这些经费能用于卫生事业者,又属寥寥。1935年至1939年,甘肃省对卫生事业的投入仅占全年财政总支出的0.118%、0.508%、0.52%、0.29%和0.46%。[42]在此背景下,夏河卫生院能从卫生处获得的经费自然十分有限,职员月平均薪金在1941年也仅为105元,远低于夏河国立初级实用职业学校的201.66元。[43]此外,国民政府1942年的分税制改革,也对卫生院的建设造成一定困扰。如同年卫生院因“现有器具不敷使用”而请示添置药柜等设备,但卫生处以经费“改归国库直按拨发后……手续繁杂”为由,要求“暂行缓办”。[44]
此外,夏河县政府微薄的财政收入及境内特殊的社会生活习惯,更使卫生院本就捉襟见肘的财务雪上加霜。首先,卫生院为县行政机构之一,本应得到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但事实上,抗战以来夏河县“每年征款甚微”,“建设经费,则一文不名”。[45]所以当卫生院初创之时,县政府虽“将教育款产楼房四间借用”,转于1942年向卫生院催收房租(全年1,500元,1944年涨至8,400元)。卫生处则以“利用官产办公,自毋庸交纳租金”为由拒绝交纳,双方函电往来互控于省政府;[46]其次,卫生院所入经费均为法币,但夏河“买卖交易,完全采用硬币,硬币与法币之差,常在五倍以上”,故各项开支无形增大,常常“超过原预算甚巨”;[47]再次,卫生院职员多为内地籍贯,如吴炉青、张仁溥、李敏、马火炎等均为山西人,他们日常饮食以面食为主。但夏河“食粮物品”均由临潭等县运来,“物价高昂异常”[48]。1941年间在夏河每月如欲“除面食外有时吃几顿米饭,则须五十至七十余元”,[49]而当时卫生院职员平均月薪仅105元,除院长、医师外,其余职员月入已不能维持生活。由是之故,其职员多有因生活所迫而离职者。如1940年,助理护士王东考因每月薪俸仅30元,“购棉裤一条鞋袜各一双即费去32元,每月薪俸除伙食外须工作4个月方能剩余”,而“呈请辞职”。[50]1943年,助理护士马荣福也因“物价高贵每月薪津不能维持生活、负债甚多无法工作,恳祈准予长假另图他谋”[51]。
夏河卫生院药械方面,不仅“日用药品”“甚感缺乏”,[52]就连“普通卫生材料”也常处于“已用完急待需用”的状态。[53]这一方面是因为省卫生处发放药品不足且不准时,另一方面则因夏河境内“山岭险阻,交通闭塞,距离四省政治中心均有相当距离”[54]。卫生处分配的药械由兰州发出到达夏河,不但运费高昂则需延宕十数日。如卫生院1941年1月17日方收到上年9~12月份药品,且“药品由兰运至夏河共需脚价洋43元”[55]。卫生院1942年1~3月份“应领卫生材料”,也迟至6月22日方“由建设厅洪工程师带往”,而卫生院收到时已到7月1日了。[56]为了节省运输费用及时间,卫生院的药械除邮寄及派人赴兰领运外,还常托人代运或由拉卜楞司令部驻兰办事处便车运送。[57]但无论何种运输方式,因路况太差,药品在途中的损失总不能免。如1941年3月,因“邮运途中颠覆”,“蒸馏水破坏53支”[58]。同年7月,拉卜楞保安司令驻兰办事处带运的药品中“肾上腺二十五CC完全损失”[59]。
除上述困难外,夏河卫生院的草地巡回医疗工作甚至还要面临着生命危险。草地巡回医疗,本为解决远道病人因“盗匪遍野,畏前慑后,裹足不来”的问题而设。[60]而鉴于“藏民生性强悍好事劫掠,凡走草地者不论官兵商客均携抢自卫,以防杀害”[61]的现实,1941年巡回医疗队在出发前,不得不呈请省府核发“手枪四枝、步枪四枝,子弹四百粒、步枪子弹一千粒”[62]以保安全。
三、夏河卫生院的医疗卫生工作
抗战时期夏河卫生院虽存在时间较短,且长期处于经费、人才、药品极端缺乏的状态之下,但卫生院全体医务人员在院长吴炉青的率领下筚路蓝缕,在解除当地民众切身疾病痛苦“为边区祛病患,为民族增健康”[63]的同时,也大大增强了蒙藏人民对政府的认同,促进其国家意识的形成。据时人记载,夏河卫生院建成之后不仅“藏蒙民众因病入院求诊者已日渐众多”[64],还使广大藏族群众“逐渐信仰新式医药”[65]。卫生院院长吴炉青也强调:草地巡回医疗可宣扬政府“关心民瘼之至意,如遇久病沉珂,医好数人,则对科学医疗之信仰,日益加深,其内向之心,自更巩固”。[66]时任甘肃省卫生处处长的姚寻源也表示,夏河卫生院等医疗机构的建立可借“卫生工作为联络感情,并宣扬政府德意,意义至为重要”[67]。
作为县级卫生机构,诊疗为夏河卫生院最主要的工作。卫生院“门诊时间,虽有规定,但不拘泥,以方便群众为宜”[68],成为夏河各机关中“与藏民最有关系的机关”。据俞湘文1941年观察,“每日来院的病人络绎不绝,拥挤异常”,平均每日诊病“约三十名,其中十分之八为藏人”。[69]此外俞湘文统计了从卫生院开诊至1941年6月19日,8个月内夏河卫生院施诊情况见表3:

表3 夏河卫生院施诊科别统计表 单位:人
除诊疗外,夏河卫生院还积极开展各类卫生保健及防疫工作。据统计,卫生院自建立起至1941年4月,共开展的健康检查、产前检查、产后检查及接生人数,分别为69人(其中学生56人)、8人、4人与2人,种痘327例(其中学生141例)。[70]全年种痘人数,1941年至1944年,分别为377人、375人、525人与805人。预防霍乱、伤寒人数,1941年与1942年分别为92人、280人。[71]但总体来看,卫生院“限于经费不足,院址窄小,工作人员不敷分配,故预防工作不克普遍推进”[72]。
尤为难得的是,夏河卫生院的诊疗防疫对象非仅限于城镇居民。如1941年,甘肃省卫生处就鉴于夏河“草地病人,困顿床褥,辗转数年,甚或数十年,不得一医”,且“藏民失教愚昧”,对于国家设施“不明真意,往往趔趄,不易奉行”的事实,特令夏河卫生院组织“草地巡回医疗队”,“解除伊等切身疾病痛苦”,便利政令推行。[73]草地巡回医疗队的工作区域“不限于夏河县境,凡甘肃、青海、四川等边疆相连地界为藏民所居住者”均是其工作对象。但受环境与人力限制,草地巡回时间每年分二期每期四个月,其余月份返回夏河办理工作。[74]据1942年夏河卫生院草地巡回医疗队预算书显示,当年参加草地巡回医疗队成员共有队长兼医师一人,职员五人(分别为护士二人,翻译、事务员、录事员各一人),工役五人。购置价值1,200元的“各医疗器械”及特制药 箱。[75]
除定期的草地巡回医疗外,卫生院还会派员对就医不便的区域作短期巡回医疗,如1941年底有“隆哇一带就诊病人,声称该村附近病人甚多,以卧床不起不能来院望医殷切”,吴炉青随即派“技士张仁溥、翻译才老携带医药前往距县六十里之隆哇一带作巡回医疗”,四日内“共计诊治患者47人”。[76]夏河卫生院除自行开展巡回医疗工作外,还时常派医师配合其它机关开展工作。如1941年,夏河卫生院派人“携带医药等物”,与拉卜楞民众教育馆“随行合作”前“赴隆哇一行”,以便利民众教育馆“工作之得以顺利推进至藏民区”。三日内卫生院医师“施诊医病”与民教馆“协同工作,收效极佳”。[77]
此外,也可从夏河卫生院药品的使用量上窥得其医疗卫生工作的大概。档案显示,卫生院药品除“常用药品如硼酸、酒精、棉花、棉纱及绷带材料”[78]外,以被当成“圣药”的“九一四”(治疗花柳的特效药)及各类防疫药为多。如1941年2月,卫生处发给“九一四注射剂95针”。[79]1942年3月,卫生院呈请卫生处“速发各量九一四200支以资应用”[80],同年卫生院又代办“九一四”70支[81]。1944年1-6月,卫生院代办“九一四”50支,[82]7月卫生处准发“九一四”50支。[83]在防疫药品的配给上,卫生院于1941年3月,查收“牛痘苗50打”[84],7月收到“霍乱疫苗及混合疫药”等“共装一箱一包”[85]。1942年1月查收“疫苗10打”[86],3月卫生处又发给“新鲜牛痘苗30打”,5月“再发牛痘苗10打”。[87]7月,卫生院又领“防疫药品、霍乱疫苗20瓶,霍乱伤寒混合疫苗10瓶”[88]。1943年3月,卫生院领到“痘苗20打”[89]。1944年1~6月,卫生院分配有牛痘苗30打[90],全年用“伤寒霍乱混合疫苗十瓶”[91]。
在此需要注意者,夏河卫生院医疗工作的顺利开展与成绩的取得,与夏河地方实力派尤其是拉卜楞保安司令黄正清(五世嘉木样的哥哥)的支持密不可分。黄正清对夏河地区医疗卫生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939年,黄正清就自任队长成立“拉卜楞藏民文化促进会巡回施教队”,施教队下设医药组前往安多藏区各部落“注射各种药针,宣传卫生常识”。[92]夏河卫生院创设之后,药械运输也多赖拉卜楞司令驻兰办事处“便车设法代为带往”。如1940年卫生院9~12月份“所需药品”“交拉卜楞保安司令驻兰办事处装车带往”。[93]1941年1~4月药械“交由拉卜楞保安司令驻兰办事处带往”[94],5~6月药品同样“由拉卜楞保安司令驻兰办事处运往”。[95]1941年,在夏河属黑错地区召开的“夏临卓三县局行政保安会议”上,黄正清等地方实力派就发展地方医药卫生设备提出具体计划,要求“充实夏河卫生院设备”[96]、“特设巡回医疗队,以辅助卫生院工作之不足”等。[97]1944年,黄正清率拉卜楞致敬团“赴渝致敬,并捐巨款,献机庆祝”,同时对夏河“亟待举办之医药、交通、教育诸端,提具详细方案”[98],其中就有创建拉卜楞医院的规划。在医院筹设之时,黄正清还任该院建筑委员会主任委员,为该院的创设出力 甚巨。[99]
四、结 语
实现边疆族群的国族化,为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主要内容。因此抗战爆发后,族群庞杂的西北边疆受到举国关注,西北开发思潮亦由此勃兴。在西北开发者看来,欲实现国族的繁荣、团结以抵抗外侮,如“于卫生一项,缺而不讲,可谓忽其大者”[100]。因为,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不仅使“边地民众永享安康,得等寿域,而于民族间情感融洽,知识启发,亦必收效甚巨”[101]。正是在此认识之下,甘肃省卫生处在汉藏交界之地的夏河县建立了甘肃西南医疗卫生的中心——夏河卫生院。
夏河卫生院创建之后受战时甘肃建设经费、人才缺乏,以及夏河地区特殊的地理、社会环境的影响,医务人员严重不足且流动性极大,经费与药品供给也远不能满足日常工作的需要。即便如此,在各级政府及地方实力派的支持下,卫生院医护人员仍殚精竭虑在拉卜楞地区广泛开展各项医疗及卫生防疫工作,从而在维护藏族群众健康、传播新式医学卫生知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政府行政机构之一的卫生院“已甚得当地人的信仰”[102],成为国家建构国家意识,强化国家认同的重要场域。
注释:
①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医疗史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多,但研究区域分布上的不平衡性比较突出,特别是西北地区的研究较为薄弱,现有的成果亦多集中于对西北医疗卫生的行政及医疗事业的宏观描述上。相关研究有:李玉尚:《民国时期西北地区人口的疾病与死亡:以新疆、甘肃和陕西为例》(《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1期);毛光远:《抗战时期甘南藏区医疗卫生建设研究》(《西藏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凌富亚:《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现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以甘肃省为例》(《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李佳晔:《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甘肃省卫生处研究》(兰州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