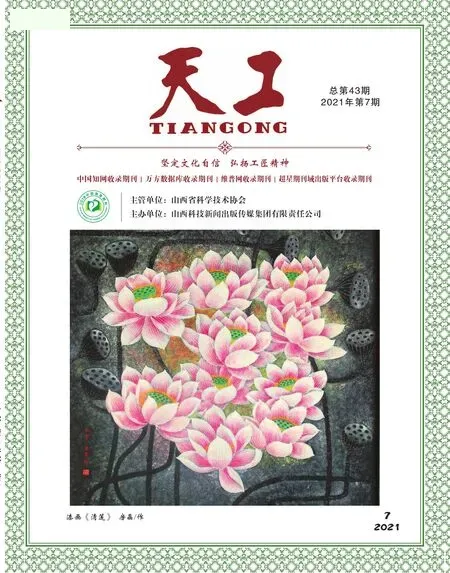尚白视野下,商周兽面纹的图式源流探究
周 霞 湘潭大学艺术学院
兽面纹旧称“饕餮纹”,研究至今,相关论文和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而对其原型和寓意的探究,始终是困惑着学界的一个难题。如李缙云、刘淑娟、吕军等人认为兽面纹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红山文化玉器中的“带齿兽面纹佩”。日本学者林巳奈夫(Hayashi Minao,1925—2006)则认为兽面纹最早可以追溯到河姆渡文化的太阳鸟纹饰。周苏平、张懋镕等人认为其渊源可追溯到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文化。李学勤先生则指出商周青铜器兽面纹与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兽面纹有明显的继承关系。总之,因资料过于零散,缺乏可读的史料佐证,均简单地将某一特定的史前文化或某类特定的器物和纹饰作为文化的原型,众说纷纭,使论断呈现“泛渊源化”的倾向。
从目前出土资料来看,发掘最早的遗址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如华南地区距今7800年左右湖南高庙文化的高庙遗址的白陶残片上线刻的獠牙兽面纹(如图1)、中原地区距今6000年左右的半坡文化陕西临潼马陵遗址出土的葫芦陶瓶上彩绘的与鱼配伍的獠牙兽面纹(如图2),华北地区距今8000年左右的磁山文化河北易县北福地遗址的陶质面具(如图3),以及内蒙古距今8000年左右的兴隆洼文化内蒙古林西白音长汗遗址出土的玉雕神面(如图4)等,均以当地盛产的红陶、白陶或玉石为载体,绘刻抽象的动物面图式。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贺刚在《论中国古代的饕餮与人牲》一文中指出:“它(兽面纹)至少可上溯到距今7400年左右的高庙文化时期,且要比商周时期的这种物象要简单得多。”①贺刚:《论中国古代的饕餮与人牲》,《东南文化》2002年第7期,第52页。遗憾的是,他仅从人牲与兽面纹共同的现象分析,笼统地将湖南高庙文化的兽面纹认定为殷商时期兽面纹的最早源起,而未对假设展开严谨的论证。著名学者巫鸿指出:“纵观礼器艺术的发展,这种艺术的基础可以说是包括了4种基本要素,即材质、形状、装饰和铭文,在礼器的发展过程中依次扮演了重要角色。”①巫鸿:《中国古代礼器艺术的兴衰》,《艺术市场》2018年第2期,第74页。因此,本文以此为依据,结合文献资料和远古传说,以“殷商尚白”为线索,从礼器材质、兽面纹的风格特点和装饰方法等方面来比较分析殷商时期和高庙文化兽面纹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厘清其在礼制文化上的生成过程,证实两者之间的源流关系。

图1 六方白陶钵

图2 葫芦陶瓶

图3 陶质面具

图4 玉雕神面
一、饕餮实名及其族属的历史缘由
饕餮纹虽然盛行于商代,但“饕餮”一词却不见于甲骨文和金文之中。最早见于东周诸多典籍中,为“三苗”部族的别称。《尚书·虞书·舜典》中记载:“(虞舜)流共工于幽洲,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群书治要·卷二·尚书》注解:“三苗,国名也。缙云氏之后,为诸侯,号饕餮也。三危,西裔也。”即“饕餮”是缙云氏之后的三苗的别称。同时,《汉书·表·百官公卿表》中述:“易叙宓羲、神农、皇帝作教化民,而传述其官,以为宓羲龙师名官,神农火师火名,黄帝云师云名,少昊鸟师鸟名。”《通典·职官·历代官制总序》注解:“春官为青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也。”“缙云”是黄帝时封在南方的夏官,一种与天文历法有关的官职。而“缙云氏”是以官职而命名的部族称谓,即三苗国的先祖。《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尧),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窜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延鲸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天下恶之,比之三凶。”宋裴骃集解引贾逵曰:“缙云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当黄帝时任缙云之官也。” 黄帝时代,三苗国的先祖——“缙云氏”为炎帝的后裔姜姓部族首领,有自己的属地,位于上古江淮、荆州一带,国名为“三苗”。到尧舜时期,由于其“贪婪、害人”的恶行,被虞舜定为“四凶”之一,流放戍边并冠名以“饕餮”。后世史籍对兽面纹的“人设”基本就圈定在周人设定的形象范围内的附会。如《神异经》云:“西南有人焉,身多毛,头上戴豕。性好强,好息,积财不用,善夺人谷物。强者夺老弱者,畏群而击单,名饕餮,言三苗性似,故号之。”由此可见“饕餮”是周代商之后,统治者对商人以“兽面纹”为代表的礼制文化从源头上的故意篡改,是激烈的族群斗争之后,新生政权对政治话语权的重建。同时,也说明商代兽面纹最早的源头是江淮、荆州一带的三苗国文化。《战国策·魏策》亦云:“昔者三苗之居,左彭暴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由此推测,上古三苗的活动范围,肯定包括现今的湖南地区,尤其是洞庭湖周边。且在黄帝时期之前,已经创造出令中原刮目相看的文化,主要分布在湖南沅水流中上游、洞庭湖区、湘江流域等地的湖南高庙文化(距今7800—6300年)与传说中“三苗国”的地理位置大致相当。
二、“尚白”观念下,殷商时期与高庙文化时期祭礼传统同源性的分析
《左传·成公十三年》有言:“国之大事,在祭与戎。”先秦时期,祭祀和战争是国家头等重要的大事,而目前遗存的祭牲和祭器也是最能客观反映祭礼的真实资料。青铜器和玉器分别是史前和三代占主导性地位的礼器,于是,学术界普遍将兽面纹的研究重点锁定在玉器和青铜礼器上,而对史前其他材质的礼器的研究甚少,尤其是对最古老的陶质、骨质祭器的关注度极低。即使是兽面纹最盛行的殷商时期,由于白陶出土的数量少,且多为碎片,以致对白陶礼器表面兽面纹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诸多文献记载,殷人尚白。如《礼记·檀弓上》载:“殷人尚白,大事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史记·殷本纪》也云:“汤乃改正朔,易服色,尚白。”自商汤征伐得天下之后,五行尚金,以白为贵。祭祀、战争、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以白色之物与之相配。所以,当史前最古老的祭器红陶和黑陶都退出历史舞台后,白陶在殷商时期却盛极一时,与青铜器并重,被统治者用于各种重大礼仪。从考古发掘来看,殷商出土的白陶仅局限于其所属方国的王陵大墓和宫殿宗庙区的大墓及遗址,且品质或工艺水平皆创历代之最高,是特定阶层所垄断的特殊器物。与同期的陶器相比,数量只占万分之一,与青铜礼器相比,比重也非常少,足可见其珍贵程度。如李济先生在《殷墟白陶发展之程序》一文中,就小屯出土白陶的三座墓葬所出的白陶和青铜器的数量指出:“白陶与青铜器的数目上的比例,至少为 1∶5,在5倍以上。”②李济:《殷墟白陶发展之程序》,《张光直·李济文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他还指出:“自殷商时代墓葬包含物的内容推断,我们可认为,在为死者安排的仪式顺序上,白陶显然比铜器更占高贵的地位。”③李济:《殷商时代的陶器与铜器》,《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1955年第9、10期合刊。因此,在殷商时代,青铜礼器是以白陶祭器为主导的“尚白”传统下的补充和新的发展,而不是其礼制文化的全部。
另外,从甲骨卜辞的祭牲来看,商代祭牲之牛,有白牛、幽牛、黄牛、物牛等色,幽为黑色,物为杂色。白牲多为祭祀直系祖先及其配偶专用,而杂色牲多为祭祀其他自然神祇所用,“尚白”背后隐含了对祖先、神的敬仰之情。如甲骨卜辞曰:“贞:燎东西南卯黄牛?燎于东西侑伐卯南、黄牛?(合278)”“贞:侑于王亥,惟三白牛?(后上28·1)燎白牛于唐,侑南?(乙3336)用白牛祖乙?(乙5540)”。“帝”“燎”“卯”“伐”“侑”“沉”等皆为祭名或祭法。从中可知,“黄牛”之为牲,是祭祀“东、南、西、北四方神祇 ,属于正方位祭礼的专用牛牲。而“白牛”之为牲,是祭祀王亥(殷人先公)、唐(商汤大乙)、祖乙(商人先王)等商人先祖,属于祖先神祭礼专用牛牲。殷商是以宗法血亲为纽带的朝代,在“天、地、人”的祭礼中,祖先神的级别虽低于帝神,但却是他们获取上帝护佑的中介。所以,规格最高,次数最多,并以白色祭器、祭牲与之配位。同时,有学者指出:“古代游牧民族以牧羊为业,从对羊的肤色的熟悉而喜尚白色或淡色东西,因而都有尚白的共同习俗,如羌族崇敬白石、匈奴族以白马为盟、契丹族以白马祭天、满族献二白马于神、拓跋族祭用白羊等等。”①朱祯:《“殷人尚白”问题试证》,《殷都学刊》1995年第3期,第16页。因此,白牲、白陶和兽面纹象征的祭牲符号与商人的祖先崇拜互为表里,是源于渔猎时代三位一体的殷商“尚白”文化的物质化语言,是中华礼制文化的根脉。
同时,湖南高庙遗址出土了创烧年代最早的白陶,其器表有浅线双刻的兽面纹、凤鸟纹、太阳纹为代表的主题纹饰体系。一方面,狩猎的野生动物和驯养的家畜是高庙先民主要的食物来源。从出土的大量打制石器和动物骨骸来看,当时属于渔猎与采集型的经济模式,无稻作农业迹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袁靖先生对部分猪牙床进行鉴定,认定属于被驯养的家猪。另一方面,兽面纹还是以白陶为主载的最高级别的祭器。同期出土的虽然还有大量的红陶,以及少量玉器、骨器和象牙,但从数量和形质上分析,红陶为大宗,为生活用陶,而白陶为小宗,质地上乘、制作精细,实为祭祀用器。同时,玉器和象牙等均素面无纹,而白陶器型规整,无一例外均饰有精美图案,具有明显的“以纹为贵”的时代特点。无独有偶,1991年在洪江市高庙遗址的一个大型祭坛遗存中,还发掘出一件颈部篦点戳印有以兽面纹为中心的复合纹样的白陶罐(如图5)。通过现场考察发现,其整体的构成元素和框架结构与祭祀遗址的实际布局完全吻合。另外,高庙文化北部的洞庭湖区还发现了比白陶更早的白衣陶。其胎质为泥质或夹细砂的红陶,而器表有意施加了一层薄薄的白色陶衣,造成一种类白陶的效果,俗称白衣陶。如彭头山文化晚期的汨罗黄家园遗址中期遗存,时至皂市下层文化时期,白衣陶更为普遍。由此可见,高庙文化以白陶为祭器的传统,绝非因白陶原料的特殊性,而是以白为贵的传统观念。湖南高庙遗址不仅出土了最早的白陶和兽面纹一类的祭祀形制的主题纹饰,而且还出土了比白陶更早的白衣陶。因此,其代表了殷人“尚白”最早的文化原型。

图5 白陶罐
三、美学格调上,殷商时期与高庙文化时期装饰法则的同源性分析
殷商白陶的装饰风格主要受同时期青铜礼器的影响,艺术语言几乎如出一辙,均为浅浮雕的“三层花式”装饰风格。著名学者郭沫若将其审美特征定位为“高古”:“在这一时期的器物中最为高古,向来为古董家所重视,气制多凝重结实,绝无轻巧的倾向,也无取巧的用意。”②郭沫若:《青铜时代·彝器形象学试探》,科学出版社,1957,第304 页。如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兽面纹白陶双系尊(如图6),高22.1厘米,深腹敛口,矮小圈足,两侧有一对宽圆系,器表通体布满兽面纹和云雷纹。兽面纹为主纹,占满白陶尊的腹部。头宽身长,以高高凸起的扉棱为鼻准线,对称的分布,口部咧口阔大,下颚和长尾呈尖钩形,尾部上扬内卷凸起于器表。再以云雷纹为底纹,顺应主纹尾部的走向进行填充。凸起的主纹表面再以阴线勾勒几何纹,形成诡异神秘、富丽繁缛的“三层花”,与同时期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印纹硬陶(如图7)和原始瓷器(如图8)清新明朗的简单几何装饰大相径庭,再现了以日常用具而为的设计目的与以庙祭而为的设计理念下,“神”与“世俗”在艺术追究上的分野。

图6 白陶双系尊

图7 印纹硬陶罐

图8 原始青瓷豆
湖南高庙文化时期白陶的装饰风格,完全不同于史前中原文化圈以古朴为美的彩陶和东南文化圈以素面为美的白陶和黑陶,却和相隔将近4000年的殷商时期的白陶相近,属于浮雕的“三层花式”装饰手法。先在白陶器泥坯凹陷处戳印阴纹,再以留白的形式,在陶器表面凸出兽面纹,呈现浅浮雕式的立体效果。而构图上,以陶器为本体,采用“纵横交错”的构图原理,横以口径为视中心,以进行“+”形等分;纵以颈、肩和腹为参考线,以带状层叠的方式将白陶器表分成两层或三层,再在各层填充相应的主题纹饰和几何纹样,形成精细繁缛的地方艺术风格。如洪江市高庙遗址出土的晚期的白陶罐(如图9),其颈肩部分别分成三层,口沿部的上层为几何纹,颈肩部的中层和下层,分别在凤鸟纹的双翼上以留白的方式饰有凸出的獠牙兽面纹。另外,兽面纹的装饰位置程式化,釜、罐类器物多饰在颈、肩部,而碗、盘和豆等圈足器多饰在外壁和外底,并多为倒饰,与现在民间巫术祭祀仪式的陈设习俗一致,需倒置才能阅读。如洪江市高庙遗址出土的晚期的白陶簋(如图10),腹壁的凤鸟纹为倒置,圈足的外底有翼獠牙兽面纹,充满整个外底,与商代青铜器底部的图形铭文的装饰手法一样(如图11)。即以龙、凤鸟、龟(蛙或鳖)、蝉、虎和马等几种动物纹饰,以线刻的方式,装饰卣、盘、尊、簋和觯等器物的外底,且充满整个底部。为正常放置所不见,带有特殊的寓意。

图9 白陶罐

图10 白陶簋

图11 虎噬人形青铜卣
四、结语
湖南洪江市高庙遗址不仅是兽面纹的源头,也是白陶质礼器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客观地再现了艺术和哲学在同一逻辑下演变的历史真理,对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独立起源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在距今大约7000年的高庙文化晚期,随着高庙文化向周边的扩张进而北上,在环洞庭湖地区“尚白”的文化传统下,进一步东传至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在千年后的良渚文化的玉质礼器上再次孕育重生,并一路北上到达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最后汇集在中原地区,从而奠定了殷商时期兽面纹的基本图式结构,清晰地再现了先秦时期文化传播上的一条连续有序、清晰可辨的白陶礼器之路。同时,接受和传播兽面纹的不同文化共同体、部族之间,必然有大致相同的宗教传统和社会结构形态。因此,关于兽面纹背后的图像生成和思想演变研究对于重新认识中国早期艺术和思想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