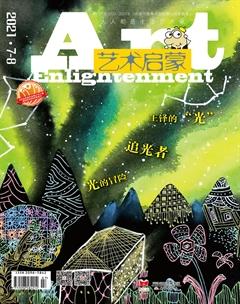追光者
呢喃



“绘画唯的材质,就是光。”野兽派先驱安德烈·德朗曾如此断言。人类对光的渴求,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光不仅驱散了黑暗,还化身为“真理” “正义” “理想”的代言人。如果你听过太阳神乌或普罗米修斯盗火的传说,那便不难理解光的重要性——光让我们看见世间万物,更照亮了人类的精神世界。而对于那些向着光奔跑的艺术家来说,他们所追寻的是光投射出来的无限的灵感。
描绘光的人
我们偏爱印象派,那些温暖、鱼紧紧锁住了我们的目光。可那些瞬间的“印象”常与主人的名字混作团,让人傻傻分不清。现在,请收下这份简易版《印象派画家分辨指南》吧
印象派画家笔下的孩子、女子、大地,在阳光的照耀下都显得那样温柔可亲。沐浴在这种暖洋洋的色调中,我们很难将它们与古典主义绘画联系起来。然而,画家们正是受了卡拉瓦乔、伦勃朗、维米尔等“光线大师”的影响,才创作出了这些充满戏剧效果的作品。
卡拉瓦乔真是位光的“理性剪裁师”,他从不把画中人置于日光下,而是把他们请到褐色的密室里,让光线垂直照向他们,背景则是片浓郁的黑。光与影如同镜子的两面,只有绝对的黑才能衬托出人物自身的光芒。他的这种用光方法被称为“明暗对照画法”或“酒窖光线画法”。观画者像戴上了3D眼镜,能透过光影直观地感受到画中人的立体感与鲜活感。
荷兰绘画大师伦勃朗也是位生痴迷于光的画家。无论是画肖像画、历史画,还是风俗画、风景画,他都像打光师 样,用光将主演、群演笼罩在富有戏剧性的情景之中。在《哲学家的冥想》中,伦勃朗展示了光线的双重作用:哲学家既在被动接受左侧日光的照射,同时又成为个“自主发光”的光源。伦勃朗用光影变化烘托出了人性之美。
伦勃朗的布光方法能有效地让画面显得立体、有层次感,又比较贴合现实生活中的光照环境,因而被广泛借鉴到影视作品的打光技巧中。2007年,电影导演格林纳威还将伦勃朗的代表作《夜巡》搬上银幕,整个电影的用光和布景都在极力还原伦勃朗的绘画风格,使得电影的观感如同 幅流动的古典主义画卷。
如果说伦勃朗的画高贵、精致,那么维米尔的风俗画则多了许多单纯、天真。維米尔短暂的 生极为穷困,虽专注画画,但画得极慢,留存下来的作品全部拼到起,估计都不如伦勃朗的《夜巡》画幅大。但维米尔始终拥有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美的天赋。
维米尔画过很多荷兰乡村女子,画中的她们总是在窗前看书、写信、弹琴、画画或做家务。画家喜欢用冷色调铺满整间屋子,让从窗户中透出的光洒到这些女子的脸上,画面便生出了和谐优雅的气息,给人以宁静、愉悦之感。
无论璀璨还是暗淡,伟大的画家都懂得如何用光来说话,讲述出或朴实、或真挚的故事。绚丽丰富的色彩、引人注视的脸庞、庄严质朴的主题,都离不开自然之光的照耀,更离不开灵感擦出的火花。
布置光的人
我们以为我们能看见光,殊不知大多数的光是不可见的;我们以为我们没法儿触摸到光,可好在有群有趣的装置艺术家,让我们有机会与光亲密接触。
印象中,英国人总是随身携带把长柄伞,见面时会聊聊天气。丹麦艺术家埃利亚松决定为伦敦“造”个太阳,于是《天气计划》诞生了——由好几百个黄色点光源组成的圆形光盘悬挂在泰特美术馆大厅中。艺术家特意调节了展区的湿度,还摆放了许多蜂蜜气味的香薰,为的是让观众体验到傍晚在海滩散步时的随性与惬意。
“艺术可以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有时颠倒乾坤,有时别有洞天——我希望为参观者带来些这样的启示和疑问。”基于这样的信念,埃利亚松为缺乏电力供应的贫困地区的儿童仓』作了《小太阳》。这些无需插电就能发光的太阳能LED台灯,既能为孩子们提供实际的帮助,又能让他们在夜间欣赏光影的艺术。
造过太阳不过瘾,他还偏要造个月亮。在《深镜(黄)》中,埃利亚松把镜子切掉小半,置入黄色单频光,而后把第二层镜子放入凹陷处。观众在行走时,就能看见不同形状和风格的“月亮”。这位被称为“现代达·芬奇”的埃利亚松最擅长的就是用物理的方法呈现光的魅力。
同样喜欢“用光说话”的还有美国的艺术家詹姆斯·特瑞尔。还记得罗斯科的方形色块画吗?如果说罗斯科的画 直在探讨颜色与空间的关系,那么特瑞尔的光感雕塑就是在探索光与空间的关系。
特瑞尔把阳光、紫外光、荧光灯、LED灯与户外美景融合交织,创造出了大名鼎鼎的《云景》。这件作品“藏”在地下,你需要从入口走进条长达十五米的隧道,累了可以坐在圆形长凳上,通过椭圆形天窗观望天空。这时,你的视线已无法进行正常地聚焦,而是被指引到无限远的地方,甚至能让你进入冥想状态,在忙忙碌碌中找到个放空心灵的去处。
据说达·芬奇学画时曾画过三年鸡蛋,不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如何,鸡蛋倒是真的不好画。椭圆的曲线难以控制,要想画好三大面、五大调的明暗排线,也非 日之功,这都足以看出表现光影的复杂性。不过版画艺术家福瑞德·佩奈尔和视频艺术家杨尼克·雅凯决定把光影关系搞得更麻烦些。
结合了木刻版画和三维投影技术的《机械推论》便是他们的异想天开之作。机械回路不停地运转,像加了光影效果的多米诺骨牌,艺术家通过结构连接、循环路线打造出虚实结合的光影效果。只是我们很难说清它到底表达了什么主题,那就请你发挥你的想象力竞答 下吧
另一件互动性更强、更具沉浸感的数字艺术装置是teamLab团队的作品。参观他们的展览如同走进了布满彩色光线的世界:你可以观察到身边的花朵正经历四季流转,你可以通过触碰光弹奏乐曲,还可以尝试坐上“水果滑梯”或者画 座彩绘水族馆。在这里,“光”就是神奇的颜料,你能在任何物体上展开创作。设计光的人
好在有发明家创造了会发光的灯,好在有艺术家创造了比太阳和月亮还要亮的心灵之灯。“比太阳月亮还要亮的灯,其实就是每个人心中的光。点亮你心中的光,生活中任何平凡的东西都可以变得美丽。”灯光设计师英葛·摩利尔如是说。摩利尔试图赋予灯泡以诗意,从长着翅膀的灯泡到奇特的灯光装置,再到建筑物中的照明设施,他的每次创作都由幻想开始,但如何让幻想变成现实?等待技术的成熟有时需要花费数十年之久。
他的代表作Lucellino由表示“光”和“小鸟”的意大利语单词组成,它是款用便签条做灯罩的吊灯,上面写的也许是最优美的乐谱、最动人的诗篇,也许是最俏皮的素描手稿和爱人的留言。三十多年来,摩利尔就这样带着对光的迷恋从事艺术创作。
设计,在些人的眼中并非无中生有的创造,而是帮助人们察觉那些被忽视的珍贵。灿烂的阳光、皎洁的明月、波光粼粼的涟漪,本都是自然存在的美,可我们却常常视而不见。于是,日本设计师吉冈德仁的愿望是设计时间、空气和光。
他喜欢用透明色、白色以及其他容易表现光感的材料。在他的面包椅子、玻璃茶房、彩虹教堂、葡萄酒瓶收纳架、品牌汽车展厅以及“龙卷风”和“感知未来”的展览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类材料“出镜”。透明的材质看似无形,只有当光穿过时才会显形。自然的能量、时间的流逝与光的不可捉摸,都在提示我们与它们相处的方式——只需观看,无需抗争。
东方气韵
比起那些疯狂而热烈的追光者,东方艺术则显得内敛了许多,比方说我们在水墨画中很难直接发现光的身影。但是,我们在评价 幅水墨画时,常常称其“气韵生动”,其实这时我们已经在表扬画家对光的运用了。
古代画论把“光”归入“气”的范畴之内,明朝顾凝远在《画引》中说:“六法中第气韵生动,有气韵则有生动矣。气韵或在境中,抑或在境外,取之于四时寒暑晴雨晦明,非徒积墨也。”其中的“晦”和“明”就是指光的强弱。
气韵,有可能体现在画中,有可能只是画作本身带给观者的体验。这句话听起来颇有玄学的意味,不过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为我们做了注解:“中国画的光是动荡着全幅画面的种形而上的、非写实的宇宙灵气的流行,贯彻中边,往复上下。”不信,你就看看北宋画家王诜(shēn)的《烟江叠嶂图》吧 苍茫的烟江,远山和树影,流水与碎石……水墨五色与流动线条构成的江波青澜之景,难道不正是光的神韵吗?光真正的魅力,只有用心才能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