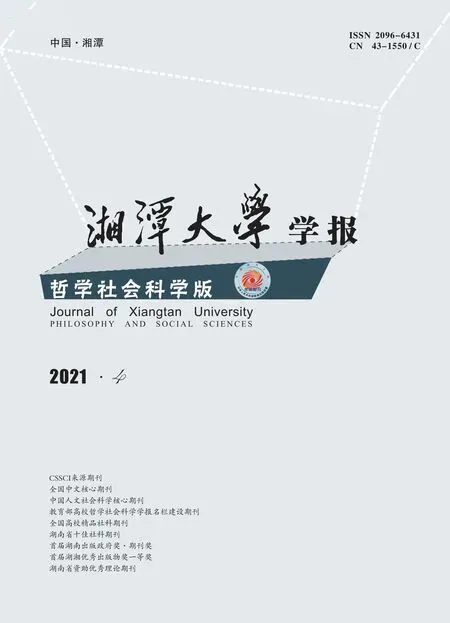企业集团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陈赤平,孔莉霞
(1.湘潭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2.湖南工程学院 经济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4)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而外部资本市场上金融资源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实体企业的需求,导致许多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但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部分企业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降低成本、形成规模经济而形成企业集团。企业集团作为一种现代化的高级组织形式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已广泛运用,这种金字塔结构推动着相关利益企业的经营与发展。集团化经营在一定程度上能发挥内部资本市场功能,降低外部融资约束和信息不对称程度,将优势资源从低效率企业流入高效率企业,提升制造业整体发展水平。同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也离不开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蔡昉,2017)[1]6-19。但近几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逐渐放缓,TFP的年均增长速度在3%~5%之间波动,这可能是受到了外部资本市场的影响,主要由于金融发展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姚耀军,2010)[2]68-80,而外部信息的不对称可能导致企业面临较高的融资约束和投资风险从而抑制生产效率。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企业集团化经营能否有效发挥内部资本市场功能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对从企业组织形式入手研究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希望为推动我国企业改革提供借鉴意义。
从国内外相关文献来看,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集团化的经济后果上。一方面是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不完善的外部资本市场进行有效替代,并快速获得其成员企业信息,利用其信息及激励特点合理配置资源(王峰娟和粟立钟,2013)[3]70-75,将优势资源分配给边际收益最高的成员企业,提升资源使用效率(Gertner et al.,1994)[4]1211-1230;二是缓解成员企业的融资约束(蔡卫星等,2015)[5]114-130,集团下属成员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为企业获得更多资金(Shin and Park,1999)[6]166-192,增强了企业负债能力(Ahn,2006)[7]317-337,分担了成员企业存在的财务风险(苏坤,2016)[8]127-143;三是企业集团能够降低交易成本(郭晨曦和吕萍,2017)[9]139-155和代理成本(Ferris et al.,1995)[10]319-335,提升了企业创新能力(江轩宇,2016)[11]120-135与投资效率(刘媛媛等,2016)[12]99-109;四是集团式的组织结构对公司管理决策产生积极影响,提升成员企业价值(Khanna and Palepu,2000)[13]867-891。
另一方面为消极影响,主要由于企业集团内部的复杂性极易造成内部资本的无效配置(邵军和刘志远,2007)[14]114-121,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王鹏和周黎安,2006)[15]88-98。且当企业集团相对于独立上市公司持有更多现金时,会加重下属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窦欢等,2014)[16]134-143,控股股东为获得自身利益,急于扩张使得整个集团面临财务杠杆上升的弊端,增大财务风险(李焰等,2007)[17]117-135。而外部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和监管不严也容易造成集团大股东侵占小股东利益,出现“掏空”上市公司的现象(李增泉等,2004)[18]3-13。
国内外学者从投资效率、创新产出、经营绩效等方面对企业集团化的经济影响进行了研究,但对企业集团化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比较少,因此本文通过识别企业集团探究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从以下两方面丰富了现有研究:第一,已有文献多是从企业生产要素方面研究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则从组织形式角度研究企业集团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提供新的方向;第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背景,本文拓展了不同程度金融发展水平下企业集团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这为进一步深化我国企业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提升金融供给质量提供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企业集团化、融资约束与全要素生产率
企业集团化影响融资约束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企业集团一般会与银行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减轻外部资本市场不完善所带来的问题,而下属成员则会依托大集团优势,降低银行贷款门槛,获得充足的资金投入到生产中;第二,企业集团化运作极易获得内部成员信息,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和企业融资成本,投资现金流的敏感程度也随之下降,有助于实现企业价值创造(王化成和曾雪云,2012)[19]155-168;第三,集团内部成员之间可以互相担保,担保能力的大小是影响企业贷款多少的重要因素,成员之间担保数量的增加提升企业融资能力,降低了贷款规模的限制(Jia et al.,2012)[20]2295-2313;第四,由于集团内部拥有充足的资金,使得集团总部能够帮助成员企业分担其财务风险进行资金拆借,将资金分配给陷入财务危机的企业,不仅减少了成员企业陷入破产的可能性,而且提升了企业获得外部资金的能力,增强企业实力。
而融资约束的缓解则进一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一方面融资能力的增强提升了企业投资效率,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企业面临着投资不足的风险,而融资约束的缓解使得企业所持有的现金流增多,投资项目具有更多选择权,激励管理者投资一些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改善企业的低效率(李红和谢娟娟,2018)[21]38-54,最终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企业的研发投入周期一般较长,融资约束程度的降低有利于增加资金供给,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和企业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而推动生产效率的提升。据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1:企业集团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进而提升投资效率和创新投入,最终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二)企业集团化、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
技术创新作为企业获得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保障,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企业集团化通过内部资本市场解决技术创新的信息传递问题,有助于成员企业发挥知识外溢功能,形成知识共享的创新环境,更好地促进企业之间相互交流学习,同时创新成果在各个成员企业之间分配使用,提升技术创新水平进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其次,企业集团雄厚的资金有利于增加研发投入以促进创新产出增加,提升技术创新的回报率(蔡卫星等,2019)[22]141-159。并凭借天然的优势更容易吸引高层次、高技术人才,加快了企业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增强企业的研发能力。再次,集团化经营有助于整合创新资源(黄俊和张天舒,2010)[23]91-102,最大程度地实现创新资源优化配置,减少资源浪费,最终提高技术创新效率。最后,企业集团有利于减少政府干预,激发管理层的创新意识,形成良好的创新环境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2:企业集团化通过提升内部技术创新进而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7—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并进行以下筛选:(1)剔除金融企业、房地产企业及其服务业等,只保留制造业企业;(2)剔除样本期内ST的企业以及数据缺失严重的企业。最终获得1 763家制造业企业样本。本文数据均来自东方财富Choice数据库与CSMAR数据库。为剔除极端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1%的缩尾处理。
(二)变量定义
1.企业集团化。本文借鉴蔡卫星等人(2019)[22]141-159的识别方法。具体判断标准为:在同一年度,如果某一个最终控制人同时控制两家及以上的上市公司时,则该最终控制人控制的这些上市公司都属于企业集团。其中我们将属于企业集团的上市公司记为group=1,否则为0。经识别发现,国有企业集团平均占比71.4%,非国有企业集团平均占比28.6%。
2.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分别采用LP法和OP法测算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采用半参数LP法利用以下模型进行估计得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tfp-lp):
lntfpijt=lnYijt-αjlnKijt-βjlnLijt-γjlnMijt
(1)
其中,Y用主营业务收入来表示企业产出;K用企业固定资产净额来表示资本投入;L用企业工资总额来表示劳动投入;M用企业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来表示中间投入。i表示企业,j表示行业,t表示时间年份,所有变量均以2007年为基期进行了价格指数平减。运用OP法(1)由于篇幅有限,OP法的计算步骤不再赘述。进行实证检验时,我们将企业主营业务变更和公司名称变更作为识别企业退出的依据。
3.控制变量。根据已有研究,本文选取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资产收益率(roa)、企业规模(scale)、企业年龄(age)、资本结构(lev)、企业价值(tbq)、地区金融化水平(fin)、行业集中度(hhi)、企业成长性(grow)和固定成本(fx)等指标。各变量说明和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三)模型设定
为探究企业集团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tfpit=α0+β1groupit+β2controls+∑year
+∑industry+∑province+εit
(2)
其中,tfpit表示全要素生产率,groupit表示是否为企业集团,controls为一系列控制变量,∑year、∑industry和∑province分别表示年份、行业和省份固定效应。下标i表示各个企业,下标t表示年份,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企业集团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如表2所示,前三列为LP算法下企业集团化对全要素生产率(tfp-lp)的回归结果,在第(1)列中,为了检验企业集团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并未加入控制变量,结果显示企业集团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系数为0.489,在1%的水平上显著。从经济意义上讲,相比于独立的上市公司,集团化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高出0.489个百分点。表明企业集团比独立上市公司更能有效地推动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第(2)列中不但加入控制变量而且控制了年份、行业及省份固定效应,结果同样表明企业集团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发挥积极作用。最后两列为OP算法下企业集团化对全要素生产率(tfp-op)的实证结果,其回归结果显著为正,这与我们预期结果一致。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二)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结果稳健性,我们将非平衡面板替换成平衡面板,回归结果为表3第(1)(2)列,结果显示企业集团化(group)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同时我们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进行检验,如下表(3)(4)列,我们发现滞后变量(L.group)的估计结果显著为正,综上,企业集团通过自身内部资本市场优势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

表3 稳健性检验
(三)内生性问题
为了缓解内生性对实证结论的影响,本文利用外部政策冲击来检验企业集团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党的十六大提出建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之后设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成立后提出鼓励培育企业集团,随后各地响应号召相继出台了有关方案与意见,均提出打造企业集团,例如天津2008年出台了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通知。我们将利用各地区的相关政策来构造工具变量。首先将政策出台之前的企业集团记为policy=1,政策出台之后的企业集团记为policy=0,然后将企业集团政策的虚拟变量(policy)与行业内是否是企业集团均值(mg)的乘积设为企业集团的工具变量,则IV=policy×mg。构造该工具变量的原因是企业集团政策(policy)是外生的,并不受企业的影响和控制,而行业内是否是企业集团均值(mg)又与企业集团(group)高度相关,因此满足工具变量的要求。2SLS的回归结果如下表4所示,研究发现工具变量(IV)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249和0.321,两者分别在10%、5%水平上显著。其中LM检验的p值为0.00,强烈拒绝不可识别假设;弱工具变量检验Cragg-Donald Wald的统计值为46.432,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考虑了内生性问题之后,结论与前文结论一致。

表4 工具变量检验结果
五、作用机制检验
(一)企业集团化、融资约束与全要素生产率
为验证融资约束这一机制的影响,本文首先检验企业集团化与融资约束的关系,结果如表5前两列所示。其中选取企业投资现金支出与总资产比值(ince)为因变量,以企业当期现金流除以总资产(cf)与企业集团的交互项(cf×group)为自变量进行实证检验,第(1)列中,企业的交互项(cf×group)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企业集团降低了企业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度,缓解了内部融资约束。

表5 融资约束机制
基于前文理论分析,融资约束的缓解提升了企业投资效率和技术创新,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为此我们进一步进行检验。其中第(2)列为融资约束与投资效率的回归结果,最后三列为技术创新的回归结果。其中融资约束用现金持有量(cf)表示,投资效率指标本文借鉴Richardson(2006)[24]159-189的研究,企业投资效率绝对值越大,投资效率越低。结果显示,企业的现金持有量(cf)与投资效率(inv)的估计结果显著为负,说明企业融资能力的提升会增强企业投资效率,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后三列中,现金持有量(cf)与研发费用(rd)、无形资产净额占比(ia)、专利授权量(pat)显著正相关,表示随着企业资金的增多,对企业的创新投入以及创新产出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由此我们证实了假设H1,企业集团化缓解了融资约束,成员企业利用充足的资金提升投资效率和技术创新水平,最终推动全要素生产率。
(二)企业集团、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
为了检验第二个假设,将研发费用(rd)、无形资产净额占资产总额的比重(ia)以及专利授权量(pat)作为衡量技术创新的指标,其中为了减少数据波动,研发费用(rd)和专利授权量(pat)取其对数。从表6中可以发现:企业集团化对研发费用(rd)和专利授权量(pat)以及无形资产净额占比(ia)的检验结果均显著为正。表明相对于独立上市公司,企业集团的研发投入更多,并且能够最大化的实现创新产出,进而激发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创造力和活力(李松龄,2021)[25]3-11,推动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由此假设H2成立。

表6 技术创新机制
六、拓展性分析
(一)企业集团、所有权性质与全要素生产率
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国有企业通过兼并、收购和重组逐渐发展形成一大批企业集团。并且我国企业集团大部分受政府政策的影响,多具有国有企业性质。因此,在不同所有制下企业集团是否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不同的影响,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具体结果如表7所示。由下表可知国有企业集团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而非国有企业集团化的回归结果却不显著。表明国有企业集团化更好地发挥了内部资本市场功能,提升了生产效率。这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国资委履行监管职能推动国有资本逐渐完善,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金、技术的流通更加高效,激发了国有企业的活力,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

表7 异质性分析
(二)企业集团、地区金融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
受不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企业融资约束程度的高低可能也会存在差异,那么企业集团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地区产生的影响是否有所不同?为检验该问题,本文用非国有部门贷款比重作为衡量地区金融化发展水平(fin)的指标,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第(1)(2)列为全样本估计结果,企业集团与地区金融化发展水平的交互项(group×fin)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企业集团化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外部资本市场的不足从而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后四列为分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两种算法下,国有企业集团与地区金融化发展水平的交互项(group×fin)均与全要素生产率显著负相关,说明国有企业集团在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方发挥了内部融资的作用,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而非国有企业集团对LP算法下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而在OP算法下的回归结果为负但不显著,意味着企业集团在金融化水平低的地区没有发挥内部融资的功能,更多的是“掏空”行为。这与我们上文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大体一致。主要是因为在金融化水平低的地区,国有企业集团受融资约束的限制更小,内部资本市场促进效率明显,集团内资金的拆借能够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而非国有企业集团的约束水平较高,面临投资不足的风险,而大股东为了自身利益侵占小股东利益,对公司的资金、资产进行转移,借助内部资本市场掏空上市公司。

表8 不同金融发展水平地区分析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2007—2017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的数据,对企业集团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企业集团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企业集团这一组织形式有效地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2)从机制上来看,企业集团一方面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与创新投入;另一方面通过内部知识共享推动成员企业的技术创新,最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3)国有企业集团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国有集团的估计结果并不显著;同时在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国有企业集团更有效地发挥了内部资本市场功能弥补了金融发展短板,非国有集团更多表现出来的是“掏空”上市公司的行为。结合本文研究结论,给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优化国有资产管理,完善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机制,提高国有企业的运营效率进而推动生产效率。同时鼓励以市场化为导向进行兼并重组,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增强行业竞争力和影响力。第二,坚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以完善外部金融市场,建立多元化融资渠道,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同时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督与管理,防范金融风险,促进形成良好有序的外部资本市场环境。第三,加强对企业集团的内部监管,保障集团资金配置的效率性,完善终极控制人和集团内部资金配置等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对控股股东制衡制度以防止大股东侵占小股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