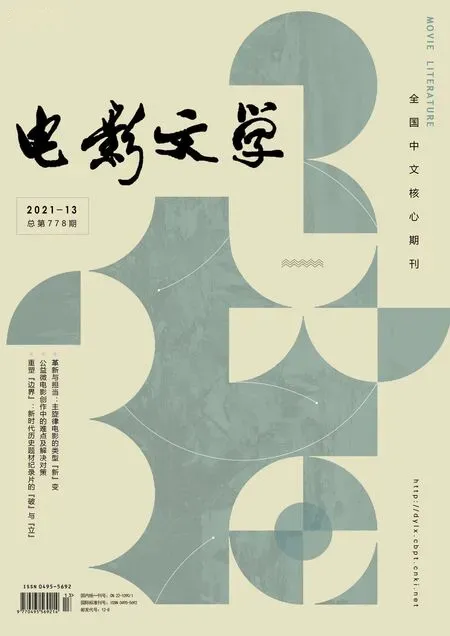新时期以来乡贤影像的建构与传播——以山西农村题材影视剧为例
王 琳 张丁心
(1.太原师范学院,山西 晋中 030619;2.三江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近年来,我国乡村发展进入转型跨越的关键时期,曾在传统乡村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乡贤文化再次引发关注。2014年9月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当代乡贤文化对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性意义,并呼吁以新乡贤力量引领乡村的全面发展。2016年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进一步诠释了弘扬“新乡贤文化”的意义。此后“新乡贤”“新乡贤文化”频繁地出现在各类会议文件及新闻报道中。所谓乡贤文化,即围绕乡贤文化形成的文化场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乡贤内涵的变化不断生发出新的特质。新乡贤文化是在传统乡贤文化的基础上,契合时代脉搏,形成的一种道德、信仰、风俗、文化的多元复合体,“它以乡情为联结,以乡情为纽带,以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嘉言懿行为示范引领,以基层干部、道德模范的嘉言懿为示范引领,具有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爱等特点”。如何建构乡贤文化,助力乡村振兴,成为新的研究热点,这对当代颇具影响力的大众传播媒介——影视艺术中乡贤文化的考察尤为迫切。同时,乡贤影像作为影视长廊中一个独特的景观,亦有着值得总结的丰富性。本文以新时期以来山西农村题材影视剧为例,从乡贤形象的书写、乡贤故事的讲述与乡贤精神的重塑三个层面探究影视艺术中乡贤文化的建构与传播,以期为当下的文艺创作提供参考。
一、乡贤形象的书写
乡贤形象是乡贤影像建构的核心,是乡贤文化的构建者与践行者,乡贤故事与乡贤精神的传播皆围绕其展开。“乡贤”虽古已有之,但其内涵随着动态的历史不断变化。传统乡贤主要由士绅阶层构成,“他们长期作为地方精英而存在,在乡村社会建设、风习教化、乡里公共事务等方面起到主导作用,是乡村权力的实际掌握者。这与我国长期实行的‘自上而下的国家统治’与‘自下而上的乡村自治’相结合的双轨制度密不可分”。而现代新乡贤的内涵愈加丰富,泛指“乡里德行高尚,且于乡里公共事务有所贡献的人”。易言之,新乡贤基本延续了传统乡贤的社会功能,又融合了时代特色,在年龄、地域、行业上分布广泛,普遍拥有现代道德观念、民主法治意识及创新进取精神。
纵观新时期以来山西农村题材影视剧创作,大体存在着四种相互流动的乡贤类型:“德乡贤”“官乡贤”“富乡贤”“文乡贤”。“德乡贤”接近传统乡贤,强调道德层面的示范引领作用,如电影《暖春》中传统美德化身的老字辈宝柱爹,他排除万难先后收养了弃儿宝柱和小花,并给予他们无私的父爱;电影《暖秋》中恪守仁义的战斗英雄立生爹,他不仅为家乡的发展奉献终身,还竭力挽救了逐渐堕落的高官儿子;类似的还有电影《阴晴圆缺》中自费救助残疾人士、振兴福利工厂的道德模范王启迪及电影《二十五个孩子一个爹》中热心收养25个孤儿、开办公益学校的善良农户赵光等。而“官乡贤”是乡贤形象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以特殊身份来维护农民的利益,如电影《红山雨》中有真实人物原型的大学生村官郭奇,他毅然舍弃城市的优越生活,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带领村民勘测水源,为了保护同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电视剧《村官》中大公无私的村党支部书记高秀民、电影《梨花情》中兢兢业业的大学生村官陈大毛亦是此类代表。“富乡贤”多指带领乡民脱贫致富的“乡村能人”,如电影《咱们的退伍兵》中兴办集体企业的返乡军人方二虎,电影《枣儿红了》中的振兴家乡特色产业的乡镇企业家高全林,电视剧《山羊坡》中带领村民植树造林、治理荒沙的老知青蒲春雨。“文乡贤”即乡村的文化精英,他们以科学知识、专业技能改变乡村文化落后的面貌,如电影《骑行天使》中频繁往返群山间普及卫生常识、治病救人的“摩托医生”刘新明,电影《一个人的学校》中的胸怀大爱、谆谆育人的教师代表高志远及电影《黄土坡的婆姨们》中以先进理论指导乡民粮食加工的余技术员等。
在新时期不同的历史阶段,山西影视作品展现的乡贤形象各有侧重,这种身份建构的变迁反映出影视艺术与时代背景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在新时期初期,山西尚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乡贤形象的建构注重道德榜样与政治引领的作用,因而德才兼备的乡镇基层干部、转业军人成为典型代表,他们带领村民在改革的阵痛中摸索前进,《咱们的退伍兵》《山村锣鼓》《假如都像他》《新星》等作品均是如此,叙事格调高昂激进,也伴有人物概念化的倾向。进入市场经济繁荣时期,经济优势逐渐取代道德、政治与知识优势,成为建构乡贤身份的首要条件,投资实业的“富乡贤”大行其道,甚至出现了一些官商勾结、谋取私利的“伪乡贤”,人物刻画走向圆形立体,以《明天我爱你》《老寨》《喜耕田的故事》《县长夫人》为代表,叙事格调趋向写实,带有一定的反思意识。在转型跨越的新时期,山西影视剧的乡贤叙事走向成熟,商业化元素增加,反映现实的横切面扩大,一是乡贤形象的多元化,如“文乡贤”已被细化为大学生村官、教师、工程师、医生与技术员等,且多立足于文化视角反思城市现代性输入乡村的过程;二是与时代契合的新乡贤形象涌现,如电影《花塔人家》《美丽乡村那些事儿》中回乡发展电商贸易的大学生,《一个不落》《耿二驴那些事儿》中深入大山、心系民生的扶贫干部等。
二、乡贤故事的讲述
乡贤故事是乡贤影像建构的重要依托。它主要通过正面书写乡贤形象扎根乡土、建设乡村、奉献乡村的义举,来复原乡贤精神、传播乡贤文化。与时下一些以矮化农民形象、调侃农村生活来赚取收视率的影视剧不同,新时期以来山西影视作品中的乡贤故事主要围绕着乡贤形象在乡村治理、乡村经济、乡村文化等方面的突出贡献展开。
乡村治理是传统乡贤最重要的功能,他们以地方权威、意见领袖等隐性形式辅助官方治理,这在新乡贤身上也得到了延续,反映在新时期以来山西影视作品中则为健全基层民主制度、加强党内团结、攻破治理难题及改善治理生态等方面。如电影《老寨》生动描绘了以村委会副主任马昌平为代表的乡村基层干部推行民主选举制度的艰难历程。马昌平因不满村主任周东明长期贪污腐败、假公济私愤而辞职,他一边与非法利益团体周旋,一边积极组织村民写信上访,最终在新任镇党委书记宋汉志的支持下成功实现了老寨村的“四权分立”。这不仅解决了老寨村长期存在的权力寻租问题,最大化维护了村民权益,还全面净化了治理生态,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而轰动一时的电视剧《新星》则将焦点对准了锐意革新的青年干部形象,古陵县新来的书记李向南上任不足一月便解决了不少民生问题,被乡民称为“李青天”。为了实现制度优化,他敢于挑战传统观念,甚至不惜牺牲个人前途,终使改革的观念深入人心。此外,《村官段爱平》《站长的烦恼》《村支书》等影视作品亦反映了乡村的组织体系建设、村务规范设置及监督机制完善等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乡贤故事的广度。
新乡贤助力乡村经济发展亦是乡贤故事着力表现的部分。新时期以来山西影视作品对此的描绘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是践行精准扶贫,推动共同富裕;其二是改造生态环境,适应农业生产;其三是发掘特色产业,创立地方品牌。如扶贫电影《一个不落》即围绕扶贫工作队在梨花村的真实经历展开。队长李向东在遍访困难户的基础上制订了详细的帮扶计划,他带领队员逐一解决了村里残疾户、贫困户、孤寡老人及留守儿童的生计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筹建了光伏发电、移动网络等生活保障设施,还鼓励村民集体创业,定期开展种植、养殖竞赛,创办特色农产品加工基地,打造从生产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同时,扶贫队协助梨花村发展旅游经济,举办大型相亲活动,兴建希望小学,开设成人扫盲班,推动物质与精神的共同进步。电视剧《右玉和她的县委书记们》则书写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代乡贤改造自然、发展生产的辉煌历程,从县委书记到普通百姓,坚持70年植树造林、修建水库、治沙开荒,终现了“塞上江南”的理想风貌。右玉借此不仅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还实现了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类似情节还出现在电视剧《古滩》《幸福生活万年长》中。而电影《黄土坡的婆姨们》《大峡谷的女人》则另辟蹊径,集中展现了女乡贤建设经济的力量,令人眼前一亮。
新乡贤积极投身乡村文化建设,这在新时期以来的山西影视创作中主要表现为道德引领、教育普及、科技兴农及医疗完善等方面。道德榜样在乡贤故事中较为普遍,《假如都像他》《父母官》《情系故乡》等影视剧的模范引领、净化乡风的作用显而易见。如电影《暖春》在激起社会各界讨论的同时,还引发了一系列学习热潮,许多乡民自发组织观摩活动,并捐款筹建儿童福利院。电视剧《父母官》播出后反响强烈,“人民好书记”孙文龙的形象家喻户晓,成为基层党员效仿的对象。《无字的歌》《大山深处的烛光》《地气》等影视剧则聚焦服务乡村教育的教师队伍,他们大多是心怀理想的返乡青年,致力于改变大山落后的面貌。他们借助有限的教学资源,将学子们送出大山,甚至仅剩一名学生仍不放弃,表现出惊人的毅力。同时,他们带来的新理念、新知识、新气象也为大山增添了一抹亮色。科技兴农也是乡贤故事的关注点,如电影《明天我爱你》中直接描绘了机械使用与技术引进对农业现代化的作用,河东村正是在青年干部许三多的先进理念指导下,通过科技联合、设备改良及技术革新等手段后来居上。这些乡贤故事的讲述无疑增添了山西影视作品的厚度,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乡贤文化的传播。
三、乡贤精神的重塑
作为乡贤文化的核心载体,乡贤精神是影视影像建构的重点。现代乡贤精神是传统美德、时代精神与个体修养的多元复合体,它不仅参与影视作品的乡贤叙事,丰富乡贤文化的艺术表达,还能实现能量的正向传递,推动当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具体来看,新时期以来山西影视作品对乡贤精神的重塑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反哺桑梓、与时俱进三个方面。
以人为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新时期以来山西影视剧中乡贤精神着力凸显的品格。“以人为本”即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导向,注重个体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将个体的需要置于首位,努力提升个体的幸福感。如《喜耕田的故事》《烟流上,水流下》《乡村婚礼》《王长喜来了》等优秀影视作品立足于乡村社会现实,多角度描绘了新乡贤为改善民生做出的巨大努力。其中电影《烟流上,水流下》展示了新乡贤群体对乡村养老困境的特别关注。青壮年人口流失,沟口村的孤寡残病老人日益增多,急公好义的退伍军人庄梁毅然放弃回城经商的念头,并说服了父母与女友,用安置费修建了一所乡村养老院,不仅解决了留守村民的务工问题,还推动了互助养老的良性循环。而电影《乡村婚礼》则深入农民的精神层面,细致描绘了新乡贤在物质条件好转后如何帮助老辈农民摆脱精神枷锁的过程。河东村合作社社长萧丙河执意要为儿子办一场传统的乡村婚礼,在青年乡贤群体的巧妙分解下,他最终解放思想,实现城乡融合。此外,电视剧《羊头崖的思念》《希望的田野》《村支书》中乡贤群体表现出来的坚守仁义、乐善好施、正直公平等品格亦是以人为本的重要延伸。
反哺桑梓是乡贤精神践行的基础,这与传统乡贤一脉相承。尽管新乡贤在年龄、地域、行业方面分布较为广泛,但其共同特征在于反哺家乡。热爱家乡、建设家乡不仅是对传统美德的承继,更是现代国家中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因而成为山西影视作品中乡贤精神重塑的关键。这些反哺家乡的贤达人士往往掌握一定的资源,他们或是心系家乡的海外侨胞,或是热心公益的退休干部,或是事业有成的商界精英,或是回乡发展的知识分子,或是掌握技术的专业人员,为家乡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如电影《沂蒙小调》颂扬了海外侨胞陈子健的报国之心,他不仅为家乡建设提供了经济支持,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全新的发展理念,有效改善了沂蒙山区产业落后的状况。而电影《跟头》则聚焦在乡村发挥余热的武术演员谢武生,他退休后依然坚持开办免费的“跟头”学习班,并组织爱徒四处演出,既解决了乡村青年的生计问题,又推广了家乡的武术,成为一名优秀的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电视剧《沟里人》改编自陵川县开山凿路的真实事件,退伍工程兵贺小庄立志帮助沟里通车,他依靠科学技术与专业精神赢得民心,带领村民克阻排险,创造绝壁通车的奇迹。
与时俱进是乡贤精神永葆青春的关键。经过现代文明的浸染,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下,乡贤精神呈现出新的特质,这也突出反映在山西影视作品中。其一,强调创新精神。改革开放呼唤创新精神,随即出现了一系列以时代先锋作为主角的影视作品,如《新星》《山村锣鼓》《追梦》中的乡贤往往能精准把握时代脉搏,在探索与革新中谋求发展。其二,重视个体价值。传统乡贤精神几乎不涉及个体价值,而现代乡贤精神则更加包容,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影视剧在书写个体维护集体利益的同时,也并未回避个体从中获得的情感满足与身份认同。如《喜耕田的故事》中喜耕田回乡承包责任田时并非没有私心,他毫不掩饰自己求富的心理,致富之后回报家乡的行为也夹杂着些许虚荣心。其三,高扬国家意识。新时期以来山西影视剧中乡贤精神呈现出愈发鲜明的主流倾向,这与以宗族利益为主的传统乡贤精神相去甚远。如电影《土地志》反复渲染国家意识,德高望重的老党员马玉厚在宗族利益与乡镇发展之间果断选择了后者,并在镇长韩长河的点拨下,充当了国家与地方、官员与百姓之间的润滑剂,逐一化解了土地流转的种种矛盾,维护了凤凰台村的安定团结。这种对国家意识的自觉强调,尤其是对国家凝聚力的书写,已然超越了传统的家国情怀,重构了现代乡贤精神。
结 语
乡贤精神与乡贤形象、乡贤故事互为补充,共同勾勒出山西影视剧中乡贤文化的美好图景。文化传承关乎一个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未来,如何建构与传播乡贤文化,提升乡贤文化的吸引力,进而振兴乡村文化,推动当下乡村建设,成为影视艺术研究与实践的重要课题。从目前的传播现状来看,多数影视作品所蕴含的乡贤文化并未得到充分挖掘。同时,这些影视作品的传播渠道较为单一,主要停留在传统主流媒体的播出平台,如中央电视台、省级卫视及各县级电视台,受众基础薄弱,社会讨论热度较低,部分影视剧甚至只在小范围内公映,直接制约了传播效果的实现。为此,需要加大对影视作品中乡贤文化的建构与传播研究,除从内容上不断贴合社会热点,差异化满足受众需求,及时做好互动反馈外,还要结合微博、微信、短视频等平台特性,做好内容传播和热点营销,打造乡贤文化的影视传播矩阵,加快形成粉丝社群,以增强受众黏性,形成社会讨论议题,从而有效提升乡贤文化的传播力与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