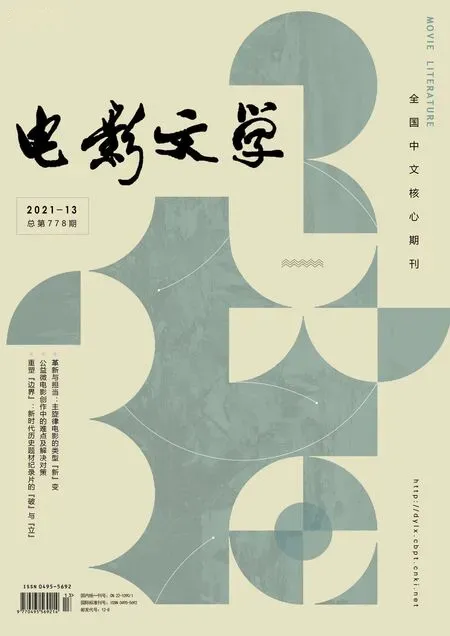广西少数民族电影剧作特色
(潍坊科技学院农圣文化研究中心,山东 寿光 262700)
广西是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份,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12个少数民族世居于此。电影作为关照时代变迁和地域文化的一面镜子,在关照民族文化和地域特色方面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广西电影人在广西这片文化多元的土地上创造了题材多样、数量颇丰的优秀影片。纵观广西电影发展史,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描写广西少数民族的影片一共有10部,其中反映壮族人们生活的影片有四部,分别是《刘三姐》《布洛陀河》《神女梦》《天琴》;描写苗族的影片有两部,分别是《远方》《血鼓》;影片《金沙恋》《雾界》《鼓楼情话》《碧罗雪山》则分别描写彝族、瑶族、侗族、傈僳族。从时间上,这10部描写广西少数民族的影片跨越中国飞速发展的半个多世纪;从题材内容上,这10部影片有历史题材、民间神话题材、爱情题材、创业题材或者多种题材融合的杂糅题材。
为了便于从剧作角度对广西少数民族电影进行研究,笔者将以1961年《刘三姐》、1989年《布洛陀河》、1991年《金沙恋》三个影片为研究样本。之所以将这三个影片作为研究样本,基于以下三方面考虑。一是这三个电影是所属年代中较具有代表性的电影作品,近代学者王国维曾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推而导之,凡一代有一代之电影,每个时期的电影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气息,体现相应时期的电影创作水平。二是从电影剧作结构层面考虑,汪流在《电影剧作结构样式》中将电影结构分为戏剧式结构、散文式结构、心理结构、混合结构、西方现代主义电影结构等。三个影片从结构形式上皆属戏剧式结构。所谓戏剧式电影借鉴了亚里士多德的传统戏剧理论形成戏剧式电影——主张把事件安排起来,形成情节,强调戏剧冲突律,致力于表现人物的外部冲突。三是从影片影响力层面考虑,影片《刘三姐》的出品时间虽然已过去60年,然而2010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还曾对其做过正面评价,称电影《刘三姐》无意中给一个城市做了个大“广告”,让观众牢牢记住了有秀美山水和动人山歌的广西桂林。时至今日,该片在国内知名社区网站豆瓣网上评分仍较高,为8.3分,这些无疑印证《刘三姐》是一部叫好又叫座的影片。但是,反观1989年《布洛陀河》和1991年《金沙恋》两部广西少数民族电影始终未能引起太大波澜。
具有相同结构形式的三部广西少数民族电影,其影片影响力和关注度却相差甚大,剧作方面的差异是导致此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故本文将以《刘三姐》《布洛陀河》《金沙恋》为研究样本,从人物形象、人物关系、情节设置、台词对白四个维度对广西少数民族电影进行剧作分析,以期把握少数民族电影剧作个性与电影剧作共性之间的生成机制,从而对我国少数民族电影创作生产实践产生积极的指导作用。
一、人物形象:用民族特长个性化、意蕴化人物
美国著名剧作大师悉德·菲尔德表示人物是电影剧本的基础,人物是故事的心脏、灵魂和神经系统。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其受众对象是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的普通百姓。因此,选择多大年龄、何种性格特质的角色作为主要人物至关重要。戏剧理论家乔治·贝克在《戏剧技巧》中把剧作中的人物分为概念化人物、类型化人物和圆整人物,《刘三姐》《布洛陀河》《金沙恋》三个影片中的主角都属于类型化人物,类型化人物性格鲜明突出,人物特征较为明显,辨识度较高。影片《刘三姐》的创作者在精准把握类型化人物特点的基础上,增加刘三姐的个性化、民族化和意蕴化特质,《布洛陀河》主要人物形象塑造过于单一表面,《金沙恋》主要人物目标诉求不明确,人物形象塑造存在一定问题。
(一)主要人物形象塑造分析
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说:“诗人应该向优秀的肖像画家学习,他们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求其逼真而又比原来的人更美。”通过表1可以看出,《刘三姐》《布洛陀河》《金沙恋》三个影片皆以容貌姣好的年轻女性为主角,三个主角有理想有追求,且都有一定的民族特长,刘三姐承袭壮族人民擅长唱山歌的特点,达念则擅长壮族民族服饰设计制作,玛吐薇擅长跳彝族舞蹈。然而,三个主角虽同属类型化人物,但其知名度却大不相同。电影《刘三姐》中的主要人物刘三姐已成为跨时代的国内外名人,成为桂林乃至广西的文化名片。《布洛陀河》和《金沙恋》两部影片的主要人物由于辨识度较弱,未能给受众留下深刻印象。

表1 主要人物形象塑造分析
(二)主要人物的个性化、民族化、意蕴化
乔治·贝克在《戏剧技巧》中提出:“个性化是从类型中间,把人物区分开来,从粗略的划分到很精细的差异,个性化是从大家熟知的范畴发展到大家不太认识或者根本不认识的范畴。”《刘三姐》人物形象塑造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在宽泛的 “类型化”基础上精雕细琢“个性化”民族人物。先秦思想家墨子曾提出“聚敛天下美名而加之”的人物类型论。影片创作者在对刘三姐的人物形象塑造上将墨子这一理论运用到极致,将刘三姐的个性化彰显到极致。刘三姐巧用山歌特长体现人物性格,展现人物个性,她用歌声和人性之美征服观众,让观众不由自主地移情代入看刘三姐如何用山歌化解生活中的各种困难,用山歌改变自身命运。影片中,刘三姐用山歌乐观地唱出被地主迫害、有家不能归的遭遇,用山歌团结宽慰广大受欺压的贫困百姓;用山歌勇敢地与地主莫怀仁斗争,用山歌嘲讽地主莫怀仁对自己的拉拢,用山歌机敏地传递被绑消息,用山歌大胆争取自己美好爱情。如此集人间大美于一身,做人做事讲原则有底线,对敌人像秋风扫落叶般无情,对朋友像春天般温暖,行事果敢利落,机敏聪慧,谈笑风生间击垮嚣张地主,刘三姐个性之鲜明,灌注生气于外在形状之意蕴,堪称一个“仙”字。虽然出身低下,却凭借唱山歌特长迸发无穷能量的“歌仙”刘三姐,放在任何时代都让人着迷。
悉德·菲尔德表示人物即行为,人物即动作。电影中的人物最终通过自身的行为、动作展现在观众面前。《布洛陀河》《金沙恋》中主要人物形象塑造不够鲜明,缺乏让人移情的个人魅力。《布洛陀河》主要人物达念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主动性不足,难以体现个人能力,在个人情感态度上游离不定,无所作为。在影片开始部分,达念为了实现当服装设计师的理想毅然决然离开照顾培养自己十几年的师父兼养母,离开生活十几年的壮族山寨,去城里寻找发展机会。此时,达念追求理想的决心非常坚决,观众期待看达念如何突破重重困难实现理想并凭借一己之力把壮族民族服装推广到全国。然而刚出山寨不久,达念便遇到服装设计师特康,在特康的帮助下顺利进入服装设计公司,依托服装公司平台,达念参加电视台举办的民族服装大赛并夺得冠军,在电视上将壮族四季女儿装呈现给广大观众。在追求事业的道路上,达念通过外力的帮助,实现自身的梦想,使其自身能力特长展现不足,难以看出她在困境面前的个人能力和爆发力。另外,达念在个人情感态度上较为暧昧。在矮马比赛中达念拒绝接受师父儿子古洛的定情信物,却在影片中后期被情敌李四娇从公司赶回山寨后再次回到古洛所在的师父家,对特康看似喜欢,却不接受他的表白,情感态度忸怩造作。影片《金沙恋》中设置了性格、职业相差较大的双女主,妹妹玛吐薇和姐姐玛乃薇。姐姐玛乃薇遇事忍让,为了妹妹甘愿放弃学业,放弃爱情,在片中整体存在感较弱。妹妹玛吐薇在片中目标诉求不明确,影片意图将其塑造成有理想有追求的新时代女性,但其在事业上未遇到任何阻碍,未在事业中展现出独特的人物性格和能力;亲情方面,女主玛吐薇为了姐姐玛乃薇一味拒绝追求者罗纳,却未从根本上帮助姐姐走出困境;爱情方面,玛吐薇对待追求者罗纳和同事阿龙的情感态度不明确,整体人物形象塑造存在一定问题。
黑格尔在《美学》中曾说:“理想”是理性内容和感性形象的统一……外在的因素,对于我们之所以有价值,并非由于它所直接呈现的,我们假定它里面还有一种内在的东西,即一种意蕴,一种灌注生气于外在形状的意蕴。那外在形状的用处就在指引到这意蕴。电影剧作中的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一定要呈现出人物身上这种灌注生气与外在形状的意蕴。刘三姐身上的意蕴通过唱山歌的民族特长在片中淋漓尽致地个性化呈现出来,而达念和玛吐薇这两个主要角色却因为缺少意蕴支撑的个性而单薄无力。刘三姐人物形象塑造上的民族化、个性化、意蕴化对少数民族电影人物形象塑造具有较好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二、人物关系:人物关系的戏剧化彰显
人物关系是指影片中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如果说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是处于一定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中的人,那么影片中的人物则处于更集中、更典型、更具有戏剧性的特定环境和特定关系之中。人物关系对塑造人物形象、体现影片主题具有直接能动作用。《刘三姐》在剧作上设置了单一人物关系,《布洛陀河》《金沙恋》在人物关系上则设置了多重人物关系。好的人物关系有利于塑造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展现电影创作者意欲表达之主题思想。
(一)人物关系分析
电影剧作中的人物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冲突型、对比型和映衬型。冲突型人物关系是指剧中两个人物在思想感情和性格上存在差异,且在行动中又相互发生了抵触。《刘三姐》《布洛陀河》《金沙恋》中的人物关系皆属冲突型人物关系,三个影片的人物关系设置都有些老套,但《刘三姐》人物关系设置胜在稳扎稳打,于不断变化的人物关系中见各类人物性格,生发彰显矛盾冲突,《布洛陀河》《金沙恋》在老套的人物关系设置上存在诸多问题(见表2)。《刘三姐》在人物关系建构上正反双方阵营鲜明,以刘三姐为首的正方和以莫怀仁为首的反方对抗清晰,张力十足;《布洛陀河》的人物关系之间建立纠葛却未能彰显,女主达念的情敌正是其经理李四娇,却未就此深入展开冲突,导致看点不足;《金沙恋》中人物关系稍显混乱,且主要女性人物玛吐薇和主要男性人物阿龙情感关系不够明晰。

表2 人物关系分析
影片《刘三姐》正反双方阵营鲜明,正方阵营是以刘三姐为代表的“刘三姐—李老头儿—阿牛—舟妹—歌迷”,反方阵营是以莫怀仁为代表的“地主莫怀仁—管家莫进财—陶秀才—李秀才”。整部影片围绕正反双方的对抗展开,莫怀仁欺负压迫贫困百姓,逼迫百姓缴纳各种杂税,刘三姐凭借自身机智和唱山歌的特长与莫怀仁斗智斗勇,惩恶扬善。影片在不断变化中展现人物性格。影片中后期地主莫怀仁见刘三姐难以对付,便试图拉拢刘三姐,用绫罗绸缎、锦衣玉食收买她,此时人物关系产生变化,莫怀仁和刘三姐之间的人物关系由绝对对立到暂时缓和,但刘三姐立场坚定,不被物质诱惑,拒绝接收莫怀仁的“糖衣炮弹”,致使两人关系升级到更加紧张激烈的程度,莫怀仁恼羞成怒,继而要杀掉刘三姐。不断变化且逐步升级的人物关系让刘三姐的性格更为动态地体现出来,让观众钦佩刘三姐的性格和勇气,却又担心刘三姐的人身安危。影片《布洛陀河》围绕男女主人公构建两组三角关系,以女主达念为中心设置“养母儿子古洛—达念—设计师特康”情感事业人物关系,以男主特康为中心设置“达念—特康—经理李四娇”情感事业人物关系,但这些颇为纠葛的人物关系却未能彰显生发矛盾冲突。古洛作为达念养母兼师父的儿子深爱女主,面对他的表白,女主没有任何顾忌直截了当拒绝,仿佛在拒绝一个刚刚认识不久的异性,白白浪费了两个人物之间设置的纠葛关系。另外,达念和经理李四娇之间,达念和特康之间也同样存在建立纠葛却未充分彰显的问题。影片《金沙恋》围绕妹妹玛吐薇设置“同乡罗纳—玛吐薇—导演阿龙”三角情感关系,围绕姐姐玛乃薇设置“阿诺宝—玛乃薇—罗纳”三角情感关系,围绕罗纳设置“阿龙—罗纳—阿诺宝”兄弟关系。在玛吐薇和罗纳的人物关系处理上,玛吐薇一味让罗纳去接受自己的姐姐玛乃薇,两人之间本应有的情感纠葛没有用来做具体冲突。另外,罗纳一直将阿龙当成情敌,但当阿龙彝族身份揭晓时,罗纳立刻将阿龙当成亲兄弟,并不再追求玛吐薇,对玛乃薇也突然亲近很多,人物关系的转变突兀给人以别扭和虚假感。
(二)人物关系的戏剧化彰显
复杂纠葛的人物关系本身容易出戏,“在编织人物关系的时候,一般不要编织得太单一,人物可以是多重的,甚至可以是对立的。多重,是指人物与人物关系有多重关系,而不只是一种”。我们提倡做复杂纠葛的人物关系,但建构纠葛人物关系之后,一定要在此人物关系基础上体现人物性格,生发矛盾冲突。影片《刘三姐》人物关系设置虽然单一,却在单一人物关系上很好地体现刘三姐性格,并层层推进正反双方冲突。《布洛陀河》《金沙恋》虽然设置了纠葛的人物关系,却未能戏剧化彰显这些纠葛关系。另外,影片《金沙恋》在少数民族角色和异族角色之间建构起一定关系,设置了香港人阿龙与彝族女主玛吐薇的人物关系,但该人物关系设置未能把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展现出来。因为阿龙和玛吐薇未确立恋爱关系,所以“彝族人只能与彝族人通婚”的族规没有给两个人物关系带来任何影响,致使最后阿龙彝族身份揭晓时未能给人带来过多感触。
人物关系建构同人物性格、影片主题、戏剧冲突等互相交织、互相影响,纠葛复杂的多重人物关系建构犹如一把双刃剑,使用得当事半功倍,使用不当损失惨重。对于冲突型多重人物关系的建构,首先,要体现人物的性格、思想和感情。剧作中的人物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人物关系的发展变化是人物选择的结果,人物的选择必然会体现人物性格或思想感情。其次,人物关系建立后,要用戏剧性充分彰显。戏剧性彰显不仅存在于一定人物关系下人物和人物之间的性格冲突,还产生于人物关系变化而引起的人物内心冲突。建立纠葛人物关系却不彰显,不仅不利于人物性格塑造,而且会让受众为复杂人物关系所累。
三、情节设置:民族地域文化的“大众化”叙事
情节实质上是电影艺术家根据现实生活和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通过加工、提炼、集中概括的方法,加以精心编织和巧妙安排的结果,从而使得人物性格通过情节的开展得到完整的表现。电影根据情节设置的不同可以分为“大情节”电影和“小情节”电影。“大情节”电影强调外在冲突和情节安排之间的因果关系,尽管人们常常具有强烈的内心冲突,但重点却落在他们与他人、社会机构或自然力的斗争上。“小情节”电影则淡化因果关系,着重刻画人物性格和内在戏剧张力。《刘三姐》《布洛陀河》《金沙恋》皆选取具有普世价值观的情节,围绕压迫与反压迫、亲情与爱情等善恶是非、爱恨情仇展开,但最终由于情节设置的不同导致可看性大相径庭。
(一)情节设置分析

《布洛陀河》《金沙江》从情节设置上归属于矛盾冲突不甚强烈的“小情节”电影,但又缺少“小情节”所推崇的内在戏剧张力和细腻人物性格刻画,使其在情节设置上陷入较为尴尬的境地。《布洛陀河》核心事件少,情感和事业外部阻碍力量不足。女主达念在追求当服装设计师这一理想的过程中,仅仅遇到领导李四娇的外部阻力。李四娇嫉妒特康爱达念,醋意大发的她停止收购达念所在山寨的蓝靛。于是,达念果断辞掉工作,再次回到山寨。然而最终李四娇为了公司生意只得登门道歉,请求达念重回公司。影片中的戏剧冲突本就不够强烈,少有的主动戏份和纠结冲突戏份还落在次要人物身上。《金沙恋》中情感戏表现平淡,影片设置了较有矛盾冲突的人物关系,即妹妹玛吐薇和姐姐玛乃薇喜欢同一个男人罗纳,但当妹妹玛吐薇意识到姐姐玛乃薇深爱罗纳这一事实后,便主动退出远离罗纳,这种情节设置看似是妹妹为了姐姐放弃所爱之人,但这种“大度”既不符合人性之真实,又刻意规避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影片中后期情节设置重复,一直围绕“罗纳追求玛吐薇,玛吐薇劝说罗纳接受姐姐”这类情节重复进行,缺少冲突性和悬念性(见表3)。

表3 情节设置分析
(二)民族地域文化的“大众化”叙事
首先,要利用矛盾冲突推动情节发展。矛盾冲突一般分为三类:人物和外部环境的冲突,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冲突,人物的内心冲突。不论是“大情节”电影还是“小情节”电影都要考虑清楚影片重点以哪一种或者哪几种矛盾冲突为主,在不同的阶段围绕哪种冲突重点展开,在具体情节上不可规避冲突,一定要直面、深入挖掘不同阶段、不同方面的矛盾冲突。其次,要做好悬念营造和细节设计。悬念犹如一个钩子,能引发受众的情感期待,让观众在两小时的观影时间里被其深深吸引。细节和悬念有时是相互补充的,细节可以作为特定悬念给受众一定的暗示作用,同时细节也能丰满人物性格,丰富情节层次,关联性的细节能给观众一定的暗示作用,吸引观众持续观看。最后,对少数民族电影而言,电影创作要面向大众,讲求情节叙事的大众化策略。少数民族电影常会不自觉地陷入民族景观话语超越情节本身的怪圈,所以在设置情节时,要让民族文化特色成为情节结构的组成元素,把少数民族地域文化和影片情节安排紧密结合在一起,把民俗奇观融入情节叙事,且不能本末倒置,专注于民族抒写而忽视情节叙事。
四、台词对白:台词对白的个性化、民族化
(一)台词对白分析


表4 台词对白分析
影片《布洛陀河》人物台词表意不明且不足以体现人物性格,在台词对白处理上总体表现一般。达念是一个擅长做民族服装的壮族姑娘,但其台词未能体现出她的身份、特长、性格,未能推进情节发展。经理李四娇要将达念赶出公司,达念说:“我是要走,但要我告诉你,山里人不是好欺负的。”这句台词本意想体现达念性格的倔强不服输,但随后的剧情却是达念回到北山师父家痛哭,之后再未有任何行为体现其不服输的性格。影片中后段,特康来北山寻找达念被古洛打伤,达念给特康送药,特康趁机向达念表达爱意,达念拒绝的台词对白却让人难以理解。达念:“你把我忘了吧。”特康:“原来你是软弱的。”达念:“按山里规矩我不能那样。”此时,达念对特康的拒绝台词——“按山里规矩我不能那样”,让受众很是疑惑。两人发生何种事情会违反山里规矩,影片中未有提及。而且这句台词与她在片中展现的人物性格不相符合。
影片《金沙恋》的台词对白出现两极分化,在家务农的姐姐玛乃薇台词对白较具民族特色。例如,当玛乃薇知道罗纳深爱妹妹玛吐薇时,她找到罗纳说:“一树难开两样花,你跟吐薇好,我也很高兴。”方言俚语的加入衬托了玛乃薇无奈的心情。在剧团工作的妹妹玛吐薇的台词对白则较为口语化。例如,罗纳去找玛吐薇,看见她在拍电影很吃惊,罗纳问:“你怎么拍电影了?”玛吐薇回答:“不好吗?”罗纳说:“好,可……有点意外。”玛吐薇说:“演员嘛,什么都要试试。”最后这句台词意在表现玛吐薇有一定的职业追求,这时如果能用一句俚语代替这句直白台词会更有味道,更符合人物民族身份和职业特点。台词对白的两极处理也许是创作者基于姐妹职业身份差异而设置的,但妹妹玛吐薇在影片中并不是完全脱离山寨,她在家乡与同乡们相处的情节较多,且其工作单位是民族特色明显的民族剧团,将同父同母共同生活的姐妹俩在台词对白风格上生硬区分,有牵强附会之嫌。
(二)台词对白的个性化、民族化
电影作为一种视听艺术,通过画面和声音传达故事,少数民族电影在对声音的运用上具有天然的优势。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台词对白,如若使用得当,对凸显人物性格,推进情节发展,渲染环境气氛具有事半功倍的作用。
中国古典人物理论非常重视人物语言等方面的个性化,金圣叹特别欣赏《水浒传》,认为“《水浒传》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这就告诉我们在台词对白方面,一定要讲求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个性化语言是区分各类人物的外在标签。另外,对少数民族电影,还要注重人物语言的民族化,让人物的台词对白符合人物的民族特征、身份特长,像民族谚语、方言俚语这些极具地域文化特色的台词对白要与人物性格、人物身份相适应,并巧妙地嵌入情节之中,让普通大众在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共情、欣赏、感受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异域文化。
结 语
故事是生活的比喻,《刘三姐》《布洛陀河》《金沙恋》三个广西少数民族故事皆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出去。刘三姐为了躲避地主莫怀仁,同阿牛以神仙眷侣的形式被迫离开家乡;《布洛陀河》中的达念在改革开放大环境下,为了推广壮族传统服饰,大胆走出贫穷的壮族山寨。《金沙恋》中的玛吐薇在家人的支持下离开彝族山寨,做了州剧团舞蹈演员,并在单位的举荐下远赴日本学习深造,弘扬民族文化。影片内容隐喻电影创作者对广西少数民族电影走出去的期许,但广西少数民族电影能否走出去,能否叫好又叫座,归根结底在于能否讲好民族“好故事”。“好故事”就是值得讲而且世人也愿意听的东西。少数民族电影创作者既要深入挖掘提炼值得讲的民族“好故事”,又要探索如何讲好民族“好故事”。具体到电影剧作上,要注重人物形象和台词对白的个性化、民族化、意蕴化,善于用纠葛的人物关系戏剧化彰显矛盾冲突,借鉴“大情节”“小情节”电影之优势,走情节叙事的大众化叙事策略。唯有虔诚汲取别人之精华,发挥自身之优势,才能让少数民族电影真正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