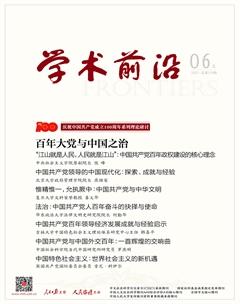传统防疫法规到近代防疫法规的历史转型
张亦斌
【关键词】清代 防疫 法规 历史转型
【中图分类号】R18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11.010
清代瘟疫多发,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威胁。本文旨在从制度层面上的法律法规角度,看待瘟疫防治的手段与效果,尤其是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末东北鼠疫推动防疫法规由传统走向近代的思路转变。本文讨论的清代前中期,主要是指顺治元年(1644年)清入关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这一时期。近代则为1841年以降至1911年宣统颁布退位诏书为止。
清代前中期的防疫应对
三代以后,历朝对包括抗疫在内的医疗卫生活动曾经采取过积极的支持态度,在中央设立种类繁多的职业医官。根据《周礼》可知,西周时期已有医师、下士、府、史等医官之设,以掌“医之政令”,承担为周天子及文武百官治病之责;之于黎庶,则有专司“掌养疾病”的疾医中士。秦汉魏晋时期设太医令丞、尚药监管理医药事务。李唐时期,各州设医学博士,负责治理民间百姓疾病;元代在中央有太医院与御医院的情况下,在各路增设医学教授,加强对民间疾疫的治疗与管理。清朝入关以后,据《清史稿》记载,医学科在府州县分别设正、典、训科无品级小吏一人,管理地方医药事业。[1]
除了在中央和地方设置常设性的职官对公卫事务作出部署以外,当瘟疫暴发之时,政府往往会设置临时救济性机构对群众进行救治。在清代以前,最典型的应当是各式各样的惠民药局。惠民药局形成于宋,而蒙元与明朝前期,基本承袭了惠民药局的设置,在瘟疫暴发时收治疫民。明代以后,各地惠民药局逐渐废弃,至清朝定鼎中原后,政府层面上不再续设。
瘟疫流行时,清代统治者有时会立即发布上谕,救治疫民。康熙十九年(1679年),三藩之乱已近尾声,与平叛战场上的胜利相伴随的,是大量因战争而失去家园的西南百姓开始逃荒。至六月,大量灾民涌入北京,康熙“命五城粥厂再展三月,遣太医官三十员分治饥民疾疫”。[2]道光元年(1821年),河南等地村庄因“河水漫溢被淹”暴发瘟疫。上谕“著姚祖同、迅即遴派妥员。前往详细查勘。饬令该地方官、将积水赶紧疏消。如有应需抚恤调剂之处。即行奏明办理。其睢州等州县传染瘟疫之处。该抚现已合药发往。务饬知该地方官、分投施散。尽心疗治。期于民命多所全活。以纾轸念。将此谕令知之”。是年七月,北京暴发瘟疫。谕内阁著步军统领衙门等有司衙门,设局延药,广为救治,并“著设局散给棺槥。勿使暴露。俟疫气全消之日停止。分别报销。用示朕救灾恤民至意”,其后又著“都察院堂官、于五城地方、揀派满汉御史各一员、分司查察。其京城内外设局之处。该堂官不时自行察访。务使认真拯济。多所全活。傥查有怠玩从事。奉行不力者。即行据实参奏”。[3]八月,再次“以时疫流行。命发广储司银二千五百两,分给五城。以制备药料棺椁之用”。瘟疫发生时,除了统治者会通过发布命令等方式作出救济指示外,社会力量积极抗疫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圣祖年间,金陵大疫,士绅杜宏“建医舍,延药散”,救活乡民无数。朝野似乎在瘟疫暴发时,并非毫无作为,都作出了积极的应对,那对瘟疫的良好防治效果应当是可以预期的?实际的情况和我们想象的并不相同。
据医疗社会史的学者考证,总体而言,清代瘟疫多发,防治效果欠佳。[4][5]笔者认为,原因是复杂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清末东北鼠疫以前,清代统治者缺乏对瘟疫危害性的科学认识,处理瘟疫态度消极。根据《清史稿》和《清实录》对瘟疫的记载,几乎每年皇帝都会收到地方官员对于辖区内暴发瘟疫的报告,但却鲜见上谕对事件本身进行处理的指示,更多的是在疫情过后的善后中给出免税赋等政策优惠。前文所述的皇帝明确对救疫具体工作作出指示的记录并不多见。比如,圣祖时期,就曾多次免除染疫地区民众税赋。康熙六年(1667年)五月,“以山西临县历年荒疫。特免康熙五年分额赋”。康熙七年(1668年),“以甘肃宁州、安化等五州县、及庆阳卫,康熙六年分、民遭疾疫。将丁银豁除。并免地亩额赋一年”。[6]官府对疫情本身的救助更多的是出于官员自身的个体行为,而非秉承上谕。比如,康熙六十年(1721年),左都御史朱轼往山西赈善灾民时,以“积聚易生疠病”为由,设厂医治灾民;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沈善富为安徽太平知府时,会逢大疫,乃“设局施药施瘗,绝荤祈禳”。[7]
清代在中国传统社会王朝中对突发事件的处理一向是为史家所称道的,对洪水、地震等灾荒都会引起足够的重视。在瘟疫面前为何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事实上,瘟疫并不像洪涝灾荒等自然灾害对统治秩序产生直接的威胁,农民起事等叛乱事件与自然灾害的发生往往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如唐代王仙芝起事前,关东大旱,官吏催缴租税,民众无路可走,遂拥王起事。相较于自然灾害,瘟疫对国家安全与统治秩序的威胁相对较小,毕竟皇亲国戚居住在京师的深墙大院之中,瘟疫传播到京师本就不易,更遑论深宫?事实上,除了清朝初年流行于满蒙八旗的天花外,宫廷内部的染疫记录事实上极为罕见。优渥的物质生活与相对良好的卫生条件使得八旗贵胄们染疫的几率显著降低。疫病鲜少能直接威胁到统治阶级的贵胄,同时,普通群众也很少因为单纯的瘟疫而觉生活无望从而铤而走险,帝制时代的统治者自然不会像对待洪水等自然灾害一样对瘟疫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二,抗疫的复杂性。清代战争频发,军队中暴发大规模瘟疫的记录并不在少数。曾国藩、左宗棠围剿太平天国期间,军队也曾多次受瘟疫困扰。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曾国藩围金陵时“疾疫大作,将士死亡山积,几不能军”,[8]左宗棠攻富阳时“军仅万馀人,皆病疫,宗棠亦患疟困惫”。即使在现代战争期间,如果战后的卫生清理工作得不到有效开展,瘟疫也很容易传播,更遑论19世纪的传统中国?再加上从应对手段的角度来看,清末东北鼠疫以前,面对突发疫情的救治,主要的治疗手段为中医,中医讲求辩证,染疫民众成千上万,症状不一,很难做到人人对症下药,瘟疫的防治效果自然难谈可观。
第三,民间防疫力量存在不稳定性。清末以前,政府层面对防疫的态度并不积极,民间以士绅阶级为主导的地方贤达在很多时候承担起抗疫的主力军作用,当瘟疫暴发时,许多地方贤达都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展开救济。尤其是在古代中国,士绅中间精通医理者并不在少数,当这些背负儒家济世救人理想的读书人同时具备士和医的双重社会属性时,自觉对疫病开展救治几乎变成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如光绪年间,平湖就有士绅施药的传统“诸生张培宇……以医自显,精痘疹,虽贫弱者不避风雨趋视延药也……”;[9]“张轸宇,字汉聚,精痘疹,率以意为治多奇验,病童多赖其资助”。[10]另外,善绅贤达们还通过印發单方、建立隔离场所等种种措施为家乡进行抗疫。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平湖乡绅设普济堂,规定:设养老房40间,每间可住3到4人。如有偶患子恙,延医服药。倘患疫疠疮疡,易致传染诸症,即移居养病房,延请专科医治。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温州地方官以疾疫传行,相继乃设立施医局留养病人,又虑穷民乞丐体素羸弱,最易感染,故隔别安置,冀免积气熏蒸多所传染。[11]饭岛涉曾对此评价“传染病流行时,这种由民间团体作出应对的情况,在中国社会中是极为常见之事,善堂等民间团体、乡绅、会馆、公所等对清末地域秩序的形成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2]但这种寄托在小团体或者个人身上的抗疫行为很多时候都存在极大不稳定性。首先,必须认识到,这些民间的救疫活动和当地的物质生活水平以及个人小团体的财力水平都密切相关。以地区而言,生产资料丰富的江南地区相关的记录较多,而云贵等地的资料相对较少。另外,从小团体个人来看,延医纳药建立隔离场所都需要不小的物质开支,而个人的财富并非恒定不变,当抗疫活动的资金来源存在波动时,行为本身也就存在难以为继的风险。
清代前中期防疫法规体系的构建
步入近代以前,清代防疫法规的内容以消灭传染源的预防与出现瘟疫后的隔离措施为主。如顺治二年(1645年),奉上敕“凡民间出痘者。即令驱逐城外四十里。所以防传染也……如有违上奏行者按律治罪”。[13]另外,在《大清律例》中,对防疫的规定虽然稀少,但并非完全没有,如针对狂犬病,规定“凡马牛及犬有触踢咬人,而畜主……若有狂犬不杀者笞四十”。[14]
由史料可知,晚清以前政府关于防疫的律例主要集中在消灭传染源的病犬猎杀和疫情暴发后的隔离措施这两方面。虽然有学者认为,对城市污水和粪便的处理规定也应当纳入防疫法规的范畴。如《大清律例》沿袭《大明律》规定“凡侵占街巷……其穿墙而出污秽之物于街巷者,笞四十”。[15]但实际上,在清朝,对粪物污水的处理更多是出于农业市场对这些天然肥料的需求,而不是现代卫生防疫的需要。一些西方传教士在他们的著述中曾提到过这样的现象,“官方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解决城市的卫生问题。他们将这件重要的事务交给民间去做,处理污物这个行业能够带来可观的收益……因为它确确实实是一个能够赚钱的行当。他们在大街、小巷、街角及客流量大的主要干道上都修建了厕所”。[16]另外,出自官方的对污水粪便的规定本身也乏善可陈,即使有,很多也流于形式。如鄂尔泰所编官书《授时通考》曾规定北方需如同南方一样,家家修建厕所,不可随地大小便。但在嘉庆年间,我们从很多官员的笔记中仍然可以看到,在北京,百姓随地便溺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当道中人率便溺,妇女辈复倾溺器于当渠。”[17]很多外国传教士对北京城随地可见粪便污秽,臭气熏天都有过真实的记录,在现代科学彻底走进群众生活以前,政府和民间皆未认识到污秽粪便和传染源的关系,因此,并不重视对其的处理应当是一个事实。
清代前中期防疫法规受限于科学认知水平,存在许多法律空白,最典型的莫过于缺乏对水污染问题的规定。恰如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所描述的“古代城市经受着因水质污染而强化的传染循环,以及许多以昆虫为媒介传播的传染病”。[18]清宣宗年间,上元发水灾,满河之水腥臭不堪,大疫肆虐,死者不可计数,进士梅伯言就曾批评家乡上元沿河居民“日倾粪桶污水,荡涤无从”以致“病症日作”。事实上,对河道水利事业,在古代中国,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投放了足够的精力加以治理,因为它事关农业灌溉以及交通航运,水患的救治也是每一代的统治者需要应对的命题。明清两代更出现过潘季训、于成龙等治河名吏,出台过大量兴修水利保护河工的敕令。但这些规定鲜少涉及水污染的问题,清末以前也少见最高层对此的回复与命令。这种现象一直维持到晚清,随着中国与世界的接触日益频繁,西方卫生观念和制度的引入、传播以及西方殖民者在租界的卫生实践,水污染与公共卫生的关系越发吸引国人的注意力。
1911年东北鼠疫对传统防疫法规提出的挑战
东北为清朝龙兴之地,被视为关内少数民族政权一旦不能维系后的最终撤退之地,对其重视程度不言自明。清朝政府对东北的人口迁移政策作出过多次调整。在立国初期,曾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鼓励关内人口向关外迁移,对于招纳移民工作出色的官员进行授官晋级奖励,大量山东、河北等地的民众走向辽东。康熙年间,随着东北移民的日益增多,迁徙而来的华北民众对东北原有的旗民生活产生冲击,从保护旗民的角度出发,清廷宣布永禁东北招纳移民活动。咸丰十年(1860年),为应对俄国不断蚕食清朝领土的现实危机,清廷接受黑龙江将军朴溪奏议,正式开禁放垦。数以万计的华北等地民众再次涌向东北。至宣统末年的1910年,东北地区总人口已逾1800万。密集的人口与发达的铁路交通促进了东北经济的发展,也催生了很多大城市,如哈尔滨。这些大城市人口集中,交通发达,商品经济繁荣,但当瘟疫暴发时,便利的交通与高度集中的人口也为瘟疫的防控带来艰巨的挑战。
宣统二年(1910年)7月,大量在俄罗斯猎取土拨鼠皮毛的中国劳工染上鼠疫,被遣回国。清政府在疫情暴发初期,应对失措,导致疫情快速蔓延。至11月,仅哈尔滨一地病死者已逾6000。[19]面对愈演愈烈的疫情,宣统政府选择任命旅欧医学专家伍连德博士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总抓黑吉奉三省防疫工作。伍连德曾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受西方现代医学训练多年,抛弃了以往传统中国时期政府对瘟疫的应对路径,选择了通过解剖尸体,明确病源,隔离观察等西医手段对鼠疫进行防控,并出台了大量的防疫法规,从制度上降低了疫情进一步传播的可能性。本次鼠疫应对过程中采取的防控手段许多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和传统时期截然不同。这些防控手段有医学、也有法律层面的,在当时的环境下很难将其完全割裂,故在下文合并讨论。
清末防疫法规的近代化转型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加剧与世界交往的日益频繁,中西医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日益增多,一些现代医学中的医学理念也由香港和上海等通商口岸引入中国,对中国传统的医药与防疫文化造成冲击,比如,对于形成瘟疫的原因,中西医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古代中国时期,对于瘟疫形成的原因基本形成了鬼神司疫与疫气致疫的二元并存的认识。早在汉代,民间就有在新年时举报“傩礼”以驱赶疫鬼的习俗,到了宋元以降,江南地区也一直有信仰“五通神”“五瘟使者”等瘟神的习俗。延至明清时期,从当时一些士子的笔记、日记中,我们可以发现瘟疫由鬼神所司的观念在当时确有市场。比如,针对天花,民间就有贡奉“痘神娘娘”的传统。
鬼神致疫的理念在当时虽然信奉者众,但毕竟难以指导临床实践。所以相当数量的有识之士提出瘟疫由疫气所致的主张。当时的传统医学主流观点认为,形成瘟疫的疫气是由不合时令之气混合暑湿秽恶尸之气形成的。如清代温病学派喻嘉言即认为“夫四时不正之气,感之者因而致病,却不名疫也;因病之死,病气、尸气混合不正之气,斯为疫也”。[20]雍正年间昆山名医龚炜对发生在十一年间的大疫也作出死于昆山的流民者众,尸体的臭腐之气,是瘟疫形成原因的判断。[21]
可以看到,神鬼司疫与疫气致病的理念在当时是并驾齐驱的,对于白丁百姓,秉信鬼神司疫的不在少数,但在具备一定知识素养与医疗常识的士人当中,疫气为致病病原的理念似乎更具市场。对于不同的病原致病学说,群众自然会采取不同的应对模式。在信奉鬼神司疫的百姓中,春节燃放烟花爆竹、端午悬挂钟馗画像、重阳节登高远足,这些都含有驱疫避鬼的意味。士人则普遍认为,在瘟疫暴发前,可以通过养生之道提升身体正气,如光绪年间举人陈虬就认为修习内功,禁欲可使正气充足,邪不可犯,若不节欲,病不可医,药石难效。[22]士人注重养生防病的观念,古已有之。至于庶民百姓,虽朝夕为生计奔波,难有投放养生的时间精力,却也存在行之有效的防病之法,如吃饱穿暖睡早,提升正气。这其实和现代医学按时作息,防止免疫力下降的理念已经相当接近。
1840年以后,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明显,从而推动防疫法规的演变。沈家本主持清末修律期间,《大清新刑律》设置专章“妨害饮料水罪”,规定“污秽供人所饮之净水,因而致不能饮者,处五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一百元以下罚金”,并对其他污染水源问题作出了不等处罚,最高可至处死;另设置“妨害卫生罪专章”,禁止“违背预防传染病之禁令,从进口船舰登陆或将货物搬运于陆地者”,违者同样处五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一百元以下罚金。在《大清新刑律》颁布的同一年,民政部颁布《违警律》,第八章“关于身体及卫生之罪”,设专条对“未经官府批准售卖含有毒质之药剂”“于城市及人烟稠密处开设粪厂”,以及污染水资源的行为皆处以半月以内的拘役或者数额不大的罚金。[23]前文已提及,清朝传统时期的水污染问题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诟病,但能认识到水污染与瘟疫流行之间关系的有识之士属于少数,而从《大清新刑律》和《违警律》的规定来看,在1908年时,这种情况已经明显得到改观,而到了1911年东北鼠疫时,这种趋势进一步加深,大量法规从西方现代防疫学的角度出发,将隔离、消毒、观察、严格处理尸体等现代医学对疫情防控的手段从制度上加以落实,使防疫工作有本可依。如1911年1月10日,长春防疫会制定《禁令八条》,禁止变卖变色变味果品,禁止堆积秽物、倾倒积水,禁止道旁及田园间废置尸棺任其暴露等;19日,防疫院制定《防疫所病院规则》,规定“凡染疫者所住之房及所用之医被、器具等,死后固需消毒,即愈后亦当消毒,其衣被、器具,可焚者立即焚毁,以杜传染”。[24]
1911年东北鼠疫期间,各地各部门出台了大量的法规文件,以遏制疫情与保障社会秩序,除了上述《防疫所病院规则》《京奉火车防疫章程》外,还有《清洁规则》《消毒规则》等规章,再加上鼠疫过后作为总结性防疫法律文件的《防疫章程》,这些法律文件的出台使全国性的传染病防治法律体系得以形成。辛亥革命爆发后,北洋政府总结吸收前述文件中的立法精神和有利条款,出台了《传染病预防条例》《清洁方法消毒方法》等诸多传染病防控法规,1920年以降,包含瘟疫防控、公共卫生等多方面内容的民国防疫法规体系得以建立。
注释
[1][清]赵尔巽:《清史稿》卷一一六《职官三外官》,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12册,第3360页。
[2][清]赵尔巽:《清史稿》卷六《圣祖本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2册,第201页。
[3]《清实录·宣宗实录6卷》。
[4]余新忠:《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与社会对瘟疫的反应》,《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5]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1页。
[6]《清实录·圣祖实录22卷》。
[7][清]赵尔巽:《清史稿》卷二八九《列传一二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36册,第1141页。
[8][清]赵尔巽:《清史稿》卷四五零《列传一九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39册,第11913页。
[9][10]光绪《平湖县志》卷18《人物*列传四*方技》,北京:中华书局,第1879、1882页。
[11]浙江通志編撰委员会:《浙江通志》第79卷《医疗卫生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81页。
[12][日]饭岛涉:《鼠疫与近代中国》,朴彦、余新忠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6页。
[13]《清实录·顺治朝实录》。
[14]《大清律例》,田涛、郑秦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426页。
[15]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瘟疫与帝国医疗体系的应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民国九十三年六月,第346页。
[16][英]麦高温:《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朱涛、倪静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56页。
[17]阙名:《燕京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4页。
[18][美]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余新忠、毕会成译,北京:中信集团出版社,2018年,第53页。
[19]奉天全省防疫总局编:《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第1编第2章,沈阳:奉天图书印刷所,1911年,第12页。
[20][清]周杨俊:《温热暑疫全书》,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14年,第80页。
[21][清]龚炜:《巢林笔谈》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0页。
[22][清]陈虬:《瘟疫霍乱答问》,《中国医学大成》,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第4册,第707页。
[23]邓实辑:《光绪丁末(卅三年)政艺丛书》上编(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二十八辑》,台湾:文海出版社,第1813~1814页。
[24]长春社会科学院编辑:《〈盛京时报〉长春资料选编》宣统卷下,杨洪友编校,长春出版社,2005年,第601页。
责 编∕肖晗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