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观:文学史观、阐释体系和价值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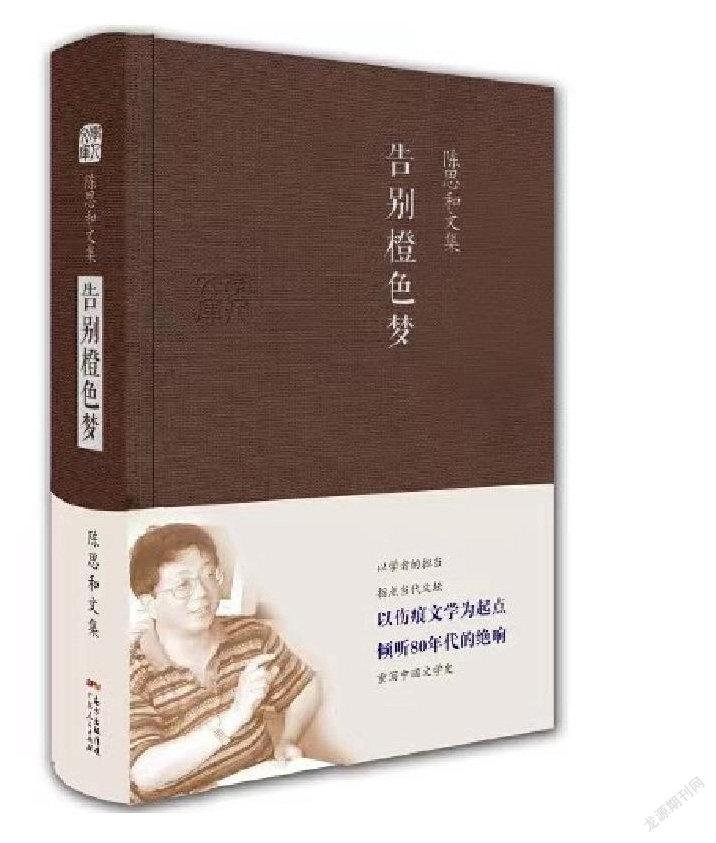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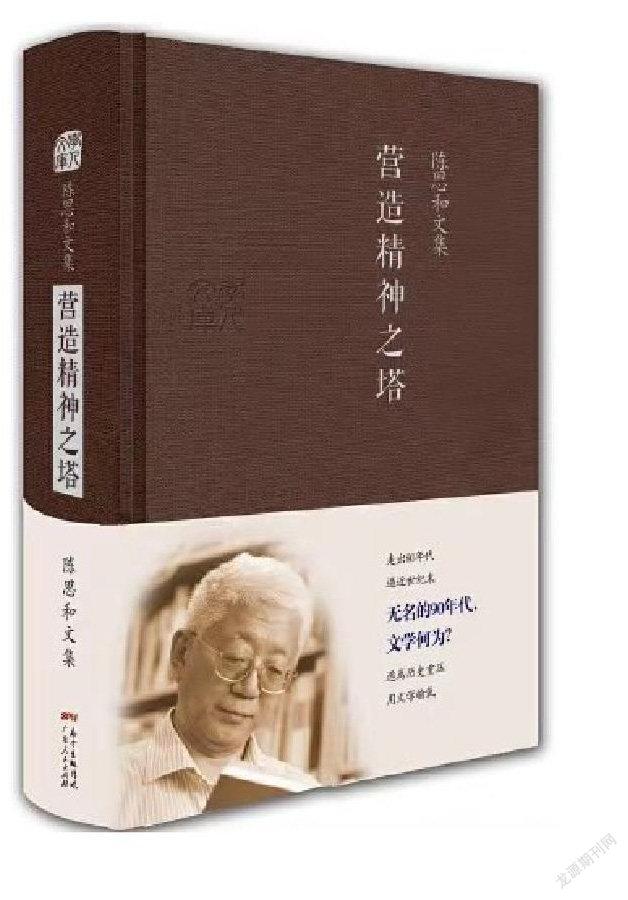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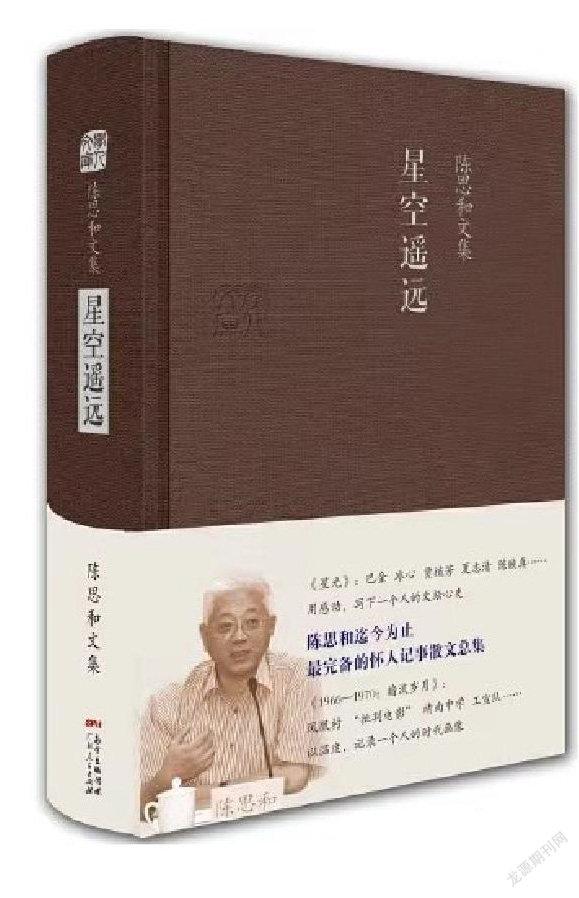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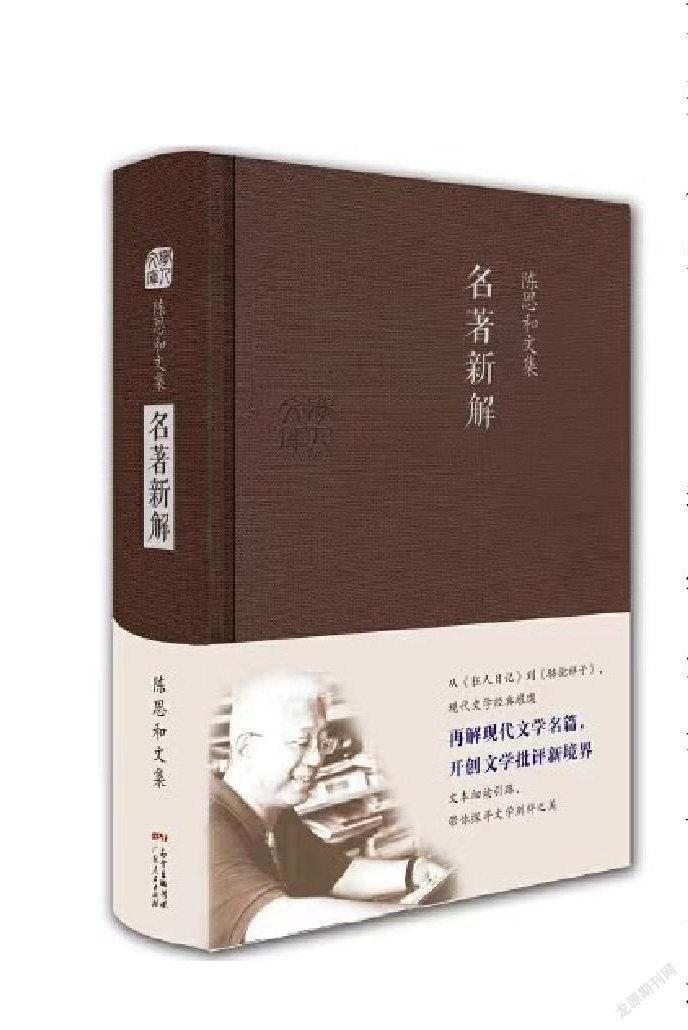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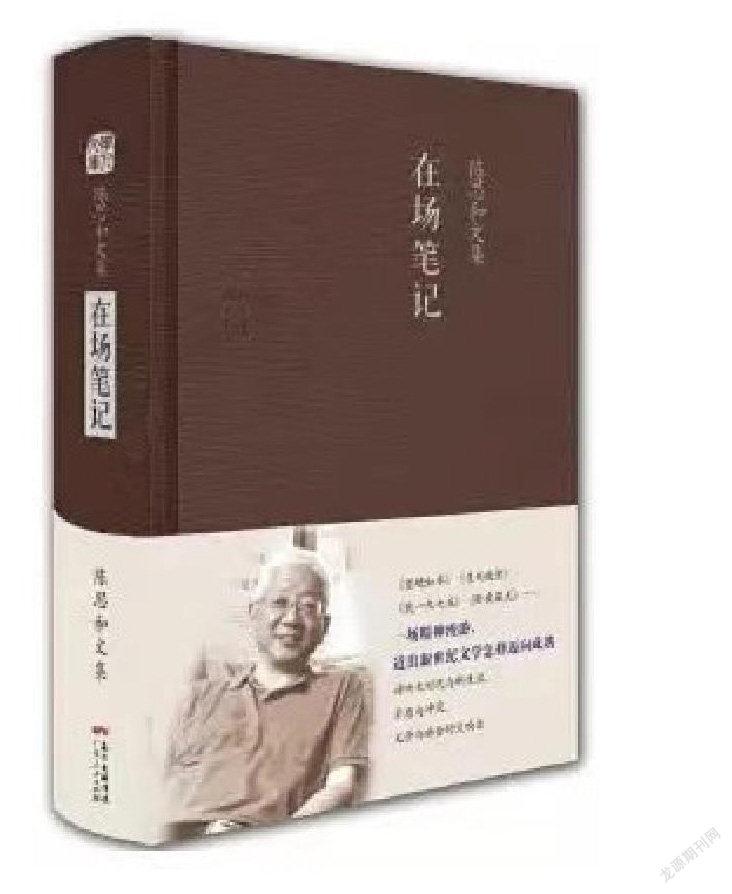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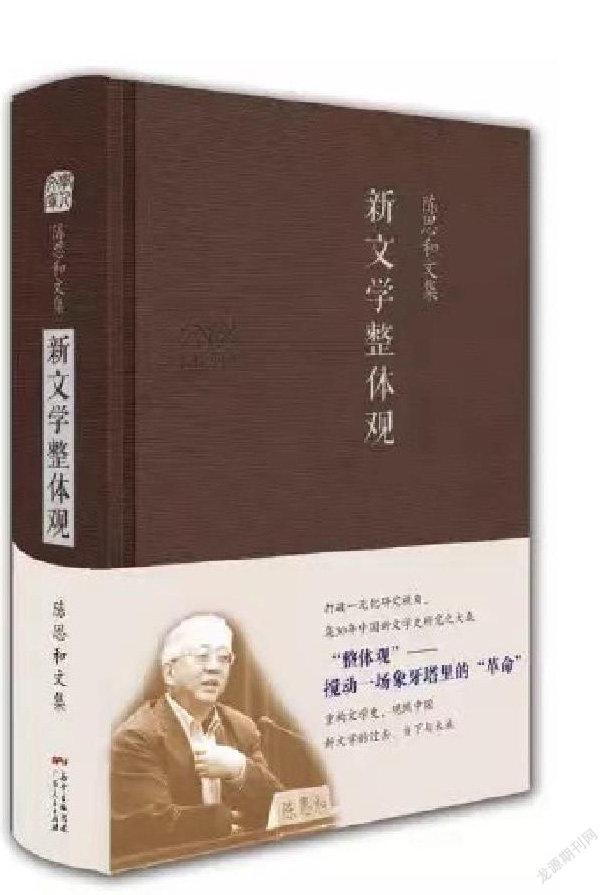
陈国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
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形态是近现代知识转型的产物,它“涉及晚清以来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五四文学革命提倡者的自我确认,以及百年中国知识体系的转化。”①1903年清廷颁布《奏定大学章程》,其中“中国文学门”的科目包括“文学研究法”“历史文章流别”“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和“西国文学史”等。值得注意的是章程在介绍《历代文章流别》时提到“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②大约从那时开始,中国便以文学史的编撰與讲授作为文学教育的核心。此后一百多年来文学史的编撰、出版与教学成为历代中国文学学科学术研究、教学实践的重要内容。③对于高校中文系学生来说,文学史是一门必修课程,有着不证自明的知识体系和学术规范。文学史的编撰不仅是现代民族国家主导意识形态构建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史述主体历史观和立场的体现,是知识范式转型的学术成果。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是当下文学史建构中的一个典型。自1999年出版以来,其学术价值已经被学术界广为阐释,在此重提的原因,就是要厘清陈思和文学史写作与学术史之间的关联和互动。从文学史观、知识转型和价值立场等层面阐释陈思和文学史写作的意义,彰显新时期第一代学人在文学史写作上所做的多维探索及存在的历史局限。
一、新文学史的整体观
陈思和关于文学史研究的论著和教材主要有《中国新文学整体观》④《新文学整体观续编》⑤《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⑥以及尚待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等等。在文学史理论的探索过程中,陈思和始终秉承了整体观的文学史观。
所谓整体观文学史观,具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将20世纪中国文学纳入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框架中来考察、辨析;其二,将20世纪中国文学看作是一个整体的动态并且不设下限的文学,打破了原来教育部设置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分界,并直接连接到下一个新世纪;其三,将港澳台的殖民性文学、多元的少数民族文学作为新文学的整体,使新文学成为一个内涵极其丰富、源头众多的文化现象;其四,打破文学内部学科界限,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予以整体性关照,摒弃艺术形式的分割,将电影、绘画、戏曲、歌词等艺术形式引入文学的整体参照体系。由此可见,整体观的文学视野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研究方法,它紧贴中国文学的古今流变,聚焦20世纪中国文学,在纷繁多变的创作潮流、皓若星辰的作家作品、多元无序的文学现象中发现人文精神的源流与发展,艺术精神的追求与嬗变,时代脉象的扫描与探析。整体观的文学史观或研究方法是以文学史为背景全面考察文学创作现象,梳理文学思潮脉络、解释文学演变的踪迹,揭示文学史的某种过程。整体观作为一种文学史观和研究方法,就是用历史的眼光去认识作品中的新因素,及时发现这些新因素在文学史上的渊源和意义。
也许这样描述比较抽象。且举一个例子:1984年陈思和发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现代主义》一文,此文后来收录《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成为其中的一个章节。我们把这篇文章看作是陈思和整体观理论的实验也不为过。这篇文章针对当时学术界围绕如何评价西方现代哲学思潮和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争论而作。20世纪80年代国内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不甚了解,盲目的恐惧、排斥情绪导致了深刻的误解。陈思和没有正面分析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特征、代表性作家等常识性的知识,也没有从理论上深入解读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复杂内涵,他只是把当下有关现代主义的争论置放于20世纪文学史的框架之下,考察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西方现代主义是如何传入中国,是谁在介绍传播,在实际传播中产生了什么作用。陈思和如数家珍似地列举了大量的例子,鲁迅、郭沫若、沈雁冰、周作人……长长的一份名单,证明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最初引进中国,是推动了新文学运动,有利于激进主义文学思潮的开展。相反的是,反对、嘲笑、抗拒现代主义思潮的,恰恰都是反对新文学运动的保守派。这些例子本来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常识,但是长期被不正确的政治意识形态遮蔽而且歪曲,造成了人们对西方现代主义的错误认识。陈思和的论文发表最受到鼓舞的不是学术界,而是一批热衷文学实验的作家,他们的实验性创作获得了有力的支持。正是通过这样一篇篇幅不大的论文,把文学史、当下文学创作、西方文学、文学理论都联系了起来,文章的最后讨论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差异和融合的可能性,又涉及比较文学和翻译学、东方文化等领域,也许今天我们可以批评陈思和的这些探讨过于粗疏,浅尝辄止,缺乏理论深度,但在当时要解决一个众说纷纭、盲人摸象似的文化难题,陈思和依靠庞杂的整体观,交出了一份有说服力的答案。其特点就在于,整体观既是文学史的研究,又参与推动了当下的创作实践。
不同的文学史观都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现代文学”“当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新文学的整体观”等概念都是在特定时期特定历史语境中提出的。洪子诚先生曾经详细论述了20世纪50年代“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取代“新文学”这一概念的过程。⑦这一概念生成不是简单的词语置换,而是涉及文学史的性质、学科的建制以及研究的方向等。20世纪80年代初朱德发、⑧许志英⑨在各自的文学史论述中,阐述了不同于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观,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文化运动。这种论述新文学的立场恢复到30年代《中国新文学大系》所确立的“人的文学”的立场;同时,又与80年代初期人道主义潮流相互呼应,拉开了新启蒙的序幕。20世纪80年代中期,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20世纪中国文学”、陈思和的“新文学整体观”、王晓明的“20世纪作家文化心理局限”等理论创新相继成为学术热点,京沪两地的优秀学者几乎同步倡导整体性的文学史观,试图整合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之间的断裂,拓展中国20世纪文学史的研究空间。这些理论主张本身包含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借用黄修己的分析,中国文学史的编撰模型(这里主要指研究范式)开始从阶级论的阐释体系转向启蒙论的阐释体系,把长期以来制约新文学研究的政治视角,扭转为文化视角,从文化史、思想史的角度来重新认识新文学史。⑩
当然,这种具有蓬勃学术活力的理论提出也与20世纪80年代大力提倡思想解放、推动改革开放的时代氛围有着密切关系。1985年,从总结现代思想史的角度,李泽厚提出著名的“救亡压倒启蒙”理论主张。陈思和多次声明《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源于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结构主义整体论思想的影响,同时在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获取了学术灵感。可以说,新文学整体观的提出,既是陈思和个人敏锐的学术发现,也是时代精神的交汇闪光。
相对于黄子平等人论述“20世纪中国文学”时的简约、浮泛,陈思和的“新文学整体观”显得略微具体、将“整体观”的文学史观或研究方法落实到具体的文学史现象,如《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圆型轨迹》《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忏悔意识》《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浪漫主义》……这些论文观点鲜明,视野开阔,纵横捭阖,酣畅淋漓,能够抓住人们的眼球。但是现在看来,某些论述过于概略和简约,有些篇什观点鲜明而论据不足。其实,这又何尝不是20世纪80年代学术研究的特点呢?这或许也是陈思和对这部著作不断修改,以至于成为他著述中版本最多的原因之一。同时,以启蒙文学来概括20世纪中国文学,容易导致将中国现代文学的问题简单化、肤浅化,从而忽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化历史的复杂性。20世纪90年代以后,陈思和的新文学整体观得以丰富、拓展,并逐渐体系化、理论化。
二、整体观文学史的阐释体系
新文学整体观不仅是一种文学史观、一种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更是一种“史的批评”,即“以批评的眼光,勾勒新文学整体精神的流变”,“是打破线性时间限制之后,在整体联系的框架中,对具体文学现象的自由解读”。11整体观文学史是一种坚持启蒙立场的多层面阐释体系。
新文学整体观的构建是建立在厚实、丰富的材料以及大量的阅读基础之上的。“就现代文学研究来说,就是对于原始材料的广泛搜集和综合研究。任何思想都不会凭空产生,即使你能够在一些外来的理论方法触发下产生出新鲜的见解,也不过是你已经熟悉了你所要研究的材料的缘故。”1220世纪80年代初期,陈思和跟随贾植芳先生进行“外来思潮流派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资料汇编研究工作,搜集资料、编写年表、大事记等工作,编辑《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1898—1937)》13上下两册,其主要内容涉及“外国社会科学思潮和理论评介文选”“外国文学思潮、流派和理论评介文选”“各国文学史、文学运动与作家评介文选”“外来影响大事记”等。同时,陈思和系统翻阅了《新青年》《晨报副镌》《学灯》《顺天时报》《小说月报》等70多种报刊,阅读了上百种现当代文学作品。只有对大量材料的综合分析研究、给予新的评价和判断,才能使材料获得新的生命,也才能修正原有的学术偏见,提出更有说服力的理论观点。
同样,整体观文学史叙述的实现,需要通过对原文学史上已有定论的作家作品、创作流派和文学现象的“重写”来完成。自1988年第4期至1989年第6期,陈思和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主持“重写文学史”栏目。所谓“重写文学史”,旨在提倡一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风气,改变过去文学史叙事的大一统学风,以历史的、审美的標准来重新评价名家名作和文学现象。构建“审美标准”的文学史叙事模式,是“重写文学史”专栏最突出的特征,批判那种仅仅以庸俗社会学和狭隘的政治标准衡量文学现象的文学史观。陈思和试图从“新民主主义论”的阐释模式中逃逸出来,冲破各种所谓“公论”,以审美的艺术视角来探讨文学史研究的多元性和可能性,通过启蒙的立场、激情的反思、感性的叙述给20世纪文学研究赋予当代性的气质。“文学史研究不是单纯的编年式的历史材料罗列,它是一种以文学演变为对象的学术研究,综合了考证、批评、规律探讨等各种研究方法。”“文学史是‘写’出来的而不是‘编’出来的,研究者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导致了文学史研究必然会出现多元化的状况。”14
不过,20世纪80年代的遽然终结,“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匆匆收盘,还是给学界造成了一种震惊的体验,许多知识分子不得不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就此告别。当然,重写文学史的学术实践还在继续,但是作为文学运动的“重写文学史”只能成为美好回忆。站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再回看“重写文学史”专栏的相关成果,这种建立“五四”文学正统地位的学术努力,未免有画地为牢之嫌。而要改变这种状况,便是“反省‘五四’立场,超越‘大系’的眼界”。1520世纪9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学术实践在海外得以延续,当时国内停刊多年的《今天》在海外复刊,马上续接了《上海文论》,举办“重写文学史”专栏达十年之久(1991—2001年)。该栏目的第一篇稿件就是王晓明的论文《一份杂志与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16陈思和则在该栏目上发表了《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17这两篇文章后来都被王晓明收录《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王晓明认为在“重返‘五四’”的同时,还应该从“五四”文学传统的阴影下走出来。陈思和提出民间文化形态的概念,与权威庙堂、精英广场并置,试图以民间文化形态作为一个自在的文化小传统,与“五四”启蒙文学的大传统相结合。无论是王晓明的“走出五四”,还是陈思和的“礼失求诸野”,都试图从“重写文学史”的精英意识和“纯文学”的立场中退出,进入重新反思“五四”传统的层面。
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并不是一个横空出世的概念,也不是陈思和、王晓明等人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有着深远的社会历史原因,是和时代互动激荡、学术潮流相互呼应的结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政治领域上,“拨乱反正”“平反冤错假案”等工作逐渐展开,大量被遮蔽的历史细节得以重见天日。原有的话语体系已然失效,新的话语体系尚未建立,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建立,“重写文学史”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便是顺理成章。但是“现代文学研究者现在缺乏的不是史料,倒是真正充足的理论”。这“需要文学史家的胆识与眼光,也需要文学史家不同的理论架构”,陈思和憧憬“如果提倡个人写的文学史,也可能在理论构架上出现若干新的尝试”。1820世纪90年代以来,陈思和不再幻想依靠个人的理想去解决经国大业,而是强调专业人士坚持人文理想和岗位意识。这些问题的提出本身具有实践性和探索性。陈思和集中对1949年以后的文学史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通过理论探索,为文学史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话语空间,从而改变文学史既定的结论,诸如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民间文化形态、共名与无名、世界性因素、先锋与常态,等等。后来,这些成果结集为《新文学整体观续编》。这些概念和范畴成为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关键词,参与构建了当代文学研究的规范,极大地推动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工作。从这些概念和范畴中,我们可以看出陈思和在坚持启蒙立场的基础上,逐渐摒弃文学史的本质论叙述而试图在多层面上阐释20世纪中国文学的流变和脉象。“引入‘多层面’的概念就是为了打破传统的一元的文学史视角,使当代文学变得丰富起来。”19
黄修己先生曾经将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分为几种阐释体系:进化论、阶级论、启蒙论以及现代性的阐释体系。20这种从文学史观的角度将中国新文学史的编撰模式予以分类有历史合理性,至今也没有失效。但是理论阐释无法厘清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史写作的内在差异。如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和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就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别,两者显然都属于启蒙论的阐释体系。实际上文学史的阐释体系不仅具有文学史史观的维度,同时也有方法论的维度。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当然属于启蒙论的阐释体系,但是他更多地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中吸取理论资源,偏重文学制度与文学生产研究,从而实现了“从本质论向建构论的转换”。21而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作家作品为依据,“以批评的眼光,勾勒新文学整体精神的流变”,从而实现了从本质论向“多层面”的转换,超越了之前一元化的阶级论文学史阐释体系。
整体观文学史的阐释体系在坚守启蒙价值立场的基础上,警惕各类二元对立认识论的陷阱,以作家作品为本,聚焦多层面的发掘,使得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实践日益丰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陈思和不断丰富整体观文学阐释体系,推动文学史叙事从“阶级论文学史”的阴影中走出来,成为本土化、系统化的当代文学史理论范畴,为中国文学学术理论体系的本土化构建做出了突出贡献。
三、整体观文学史的价值立场
新文学整体观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史观和研究方法,而且是超越文学史观和研究方法本身的精神关怀。贯穿陈思和文学史研究始终的是强烈的知识分子精神,从而形成文学史对当代人文价值立场的建构与映照。“文学史更内在隐藏的是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文学史所呈现出来的曲线,正折射出一个时代知识分子心灵被扭曲的现实。”22
在陈思和看来,新文化传统并不是一个大而无当的宽泛概念,而是有着具体的能指。所谓新文化传统:“一是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的确立,二是坚持由鲁迅、胡风延续下来的独立批评立场。”23也就是说,新文化传统是在具体的学术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当然,文学史整体观的价值立场也是多层面的,它不仅仅坚守了鲁迅、胡风“战斗”的一脉,同时它也继承了胡适、周作人的文化传统。陈思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24中对此有精彩的论述。
“80年代”是“以社会主义自我改革的形式展开的革命世纪的尾声,它的灵感源泉主要来自它所批判的时代”。典型的“80年代的论题”几乎都来自20世纪50至70年代的社会主义历史,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潘晓事件”等。而“‘90年代’却是以革命世纪的终结为前提展开的。经济、政治、文化以至军事的含义在这个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尽管两个年代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后者绝不是前者的自然延续”,不同力量与新自由主义的对峙以及20世纪形成的价值系统和历史观的深刻危机。25“市场化进程加速了社会科层化的趋勢”,职业化的进程和学院化的取向逐渐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阶层逐渐蜕变为专家、学者和职业工作者。26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术实践中,“知识分子人文激情被实实在在的资料发掘和边缘拓荒所取代”。27王晓明甚至感叹:“常觉得自己无话可说,因为找不到一个能令我真心服膺的批判立场。”28李泽厚曾经将知识界的这种变化描述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29
20世纪90年代以来,立场的缺乏、精神的失语等现象遍布文学、社会学和哲学等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同时,长期以来学术界似乎难以提出真正的“问题”,某些所谓“问题”仅仅只是海外学术热点的刺激反应,崇洋尚“名”,各类泊来的概念铺天盖地,学者们几乎丧失了分析批评能力。人文精神逐渐萎缩和失落,学术研究日益缺乏地气和底气。面对这些令人心急如焚的现状,陈思和与王晓明等学者共同发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成为当时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事件之一。人文精神是“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一种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真诚的关怀,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总体思考”。30寻思人文精神就是从对知识分子的自身反省开始的。陈思和等学者旨在重拾知识分子人文传统和精神传统,“激发那些愿意自救者的勇气和理性,使他们能更深入地透视当前的文化现实,也更深入地透视自己”。31陈思和在进行文学史研究时,始终将人文精神贯穿始终,热情探索中国文学自身的知识传统和人文传统,回溯中国人文的精神血脉,竭力追索文学史的内在精神,探寻知识分子的梦想史、奋斗史和血泪史。
时代已然巨变,社会剧烈转型,市民日益分化,这些都呼唤知识发生变化。这种困惑和失落其实是时代转折下知识体系转型空窗期带来的焦灼感和失落感。陈思和一如既往地以人文精神建构文学史的价值立场,强化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彰显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精神担当。而构建知识分子的专业传统和多元价值体系,是完成学术专业化和民间化的根本举措。陈思和从提倡“现实战斗精神”到反省广场意识和提倡岗位意识,并不是一种理论上的退却,而是对知识转型的反应。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当然包括敬业精神,但是又不等同于敬业,它是在民间岗位上对人文传统的寻求和继承,是守先待后,薪尽火传。
陈思和称新文学整体观就是“史的批评”,即以批评的眼光勾勒新文学整体的流变。陈思和倡导理论观点要从研究当中完成,在生活中发现问题,在研究实践中发现问题。文学从来都不是独立的,都是与现实生活矛盾、困惑联系在一起,混杂在一起的,批评家的困惑应该和文学的困惑联系在一起。正如汪晖所说:“单纯地诉诸历史轴来思考中国问题已经不可能,现在迫切的任务是辨别中国在新的全球关系中的经纬度,即时间轴线上的位置与空间维度上的位置。”32近年来,陈思和秉承新文学整体观,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的撰写工作,在“长时段”和世界文学视野中观照20世纪中国文学,已经公开的理论成果如先锋与常态、殖民地文学等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正如陈思和所言:“我运用整体观的目的,仍然是想通过对二十世纪文学史的研究,来探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道路和命运,是对当下知识分子处境的一种意义探询。”33陈思和文学史写作实践始终坚持开阔的整体观视野,坚持开放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具有鲜明的美学追求和价值倾向。新文学整体观贯穿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立场,以现实战斗精神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作品及作家做出客观评判,发掘新的史料,总结新的文学史概念,以广阔的民间视野建构文学史的多元化格局,构建了具有鲜明特点的文学史范式。
注释:
① 陈平原:《“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载《假如没有“文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3页。
②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594页。
③ 1904年,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馆的国文讲义《中国文学史》,章节安排完全依照学部章程的要求,并且坦承此乃“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
④ 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初版,2001年第2版。其他版本有台湾业强出版社1990年增订版、韩国青年社1995年韩文版。
⑤ 陈思和:《新文学整体观续编》,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台湾新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2012年版,改名为《文学史理论的新探索》。《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和《新文学整体观续编》两书内容有部分重复,后经作者修订,分为两种书,出版合订本《新文学整体观》,(《陈思和文集》第6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⑥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其他版本有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改名《当代大陆文学史教程1949—1999》);韩国文学村出版社2008年韩文版。
⑦ 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
⑧ 朱德发:《五四文学初探》,山东人民出版1982年版。
⑨ 許志英:《“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再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1期。
⑩20 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3,279—300、293页。
11 郜元宝:《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序》,另载陈思和:《陈思和文集: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17页。
12 陈思和:《方法·激情·材料——与友人谈〈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书林》1988年第7期;另载《陈思和文集: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13 贾植芳、陈思和:《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1898—193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4 陈思和:《关于“重写文学史”》,《文学评论家》1989年第2期;另载《陈思和文集:告别橙色的梦》,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45—346页。
15 陈平原:《学术史上的“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1期。
16 王晓明:《一份杂志与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今天》1991年第3、4期合刊。
17 陈思和:《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今天》1993年第4期。
18 陈思和:《要有个人写的文学史》,《文艺报》1988年9月24日,第3版;另载《陈思和文集:告别橙色的梦》,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45—346页。
19 陈思和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21 陈培浩:《文学史写作与90年代的知识转型——以洪子诚的研究为例》,《文学评论》2018年第2期。
22 陈思和、张新颖:《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对话》,《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6期;另载陈思和:《谈虎谈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3 王晓明、陈思和:《知识分子的新文化传统与当代立场》,《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3期。
24 陈思和:《中国现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另载:《陈思和文集:名著新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25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2页。
26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载《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60页。
27 陈思和:《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概述》,《同济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另载:《陈思和文集:新文学整体观》,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15页。
28 王晓明:《太阳消失之后——谈当前中国文化人的认同困境》,《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5期。
29 李泽厚:《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李泽厚对话集·九十年代》,中华书局2014年版。
30 陈思和:《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的三封信》,《天涯》1996年第1期;另载《陈思和文集:告别橙色的梦》,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57页。
31 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页。
32 汪晖:《世纪的诞生——20世纪中国的历史位置(之一)》,《开放时代》2017年第4期。
33 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责任编辑:斯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