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何处不知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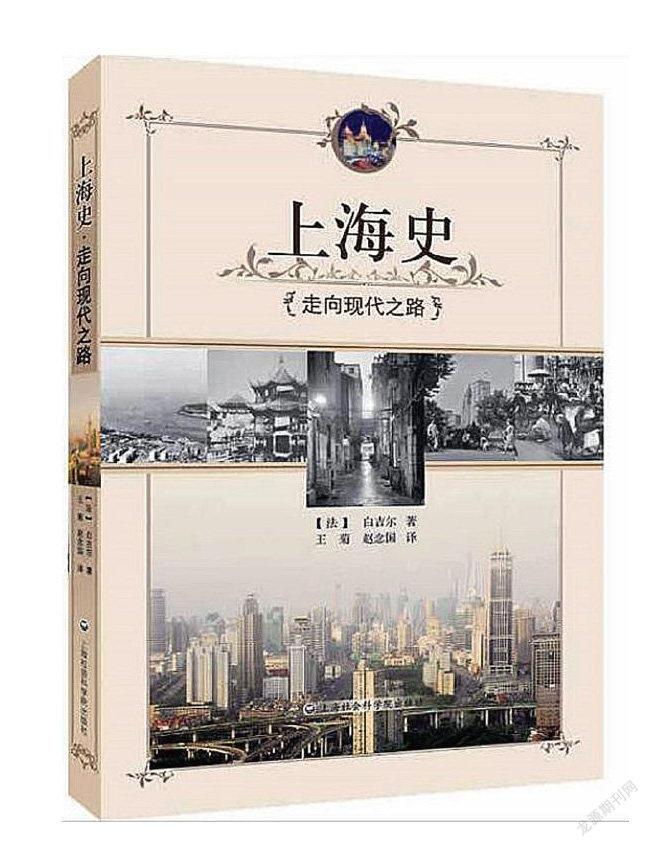
李志茗,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189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五十周年的纪念日,公共租界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这天,阳光明媚,云淡风轻,一大早外滩就悬灯结彩,旌旗飞扬,横幅高挂,其中之一赫然写着:“世界何处不知上海?”①此标语简洁明快,在强调上海的发展繁荣享誉全球的同时,也揭示了这次庆祝活动的目的和宗旨。上午的庆祝活动之一是英国传教士慕维廉在外滩的演讲,②“慕维廉先生手持皮凳而来,放在空地中,卓立于上”,面对环立四周的中外听众宣讲开埠通商以来各事。③他着重介绍的是西方人引进西方文明建设上海所取得的成就:“上海是我们的高度文明和基督教对整个中国产生影响的中心。……为了他们和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曾经在他们中间引进了什么东西呢?我们很可能指向我们在此间建立的英国家宅。……还有那些经营商业的富丽堂皇的洋行;我们可能特别谈论到最高法院,在与人们向我们描述的其他地方现存机构的显著对比下,那是以处理法律事务的公平正直行为著称的。总之,看一看租界的全貌吧——煤气灯和电灯照耀得通明的房屋和街道,通向四面八方的一条条碧波清澈的水道,根据最良好的医学上意见而采取的环境卫生措施。我们为了与全世界交往而拥有轮船、电报、电话;还开办了外国发明创造的棉纺织厂、造纸厂、缫丝厂;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北部的铁路,充当了将要在全中国范围内到处可见的设施的先驱。遵照我们自己的司法和市政当局的要求,法律和秩序在二十万人口中间极为美好地保持着。”④从他的演讲中可知,经过西方人半个世纪的经营,上海租界面貌发生巨变,环境优美,卫生、交通、通讯、照明等条件明显改善,社会秩序也更加安定和谐。
一、开埠后的上海巨变
那么,慕维廉所言是否“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呢?还真不是。1886年,在上海开埠五十周年庆典举行前7年,《纽约时报》记者到访上海,感叹公共租界近十年来所发生的巨变,说“各个方面的成长,使这个城市矗立为远东第一商埠和东方的一颗明珠”,从而担心美国对华贸易将受到威胁。在该记者的眼里,上海市政管理井然有序,是远东最美的风景、社交的天堂,非常适宜定居。⑤他说“世界上很少有城市的市政管理像上海这样运转良好”,⑥因为上海地势低而平坦,而黄浦江的潮位又高,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租界却修建了一个通畅的排水系统,并且运转得很好。接下来的问题是供水,“在远东地区,由于饮用不清洁水而死亡的人数要比其他所有原因致死人数的总和还要大”,⑦令人惊奇的是,租界在城中修建了一个过滤河水的储水池以及水塔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上海有一个了不起的供水系统,为居民提供优质饮用水”,“万一有火灾发生,消防队也可以因此获得强大的水压”。⑧除上述以外,上海警队的组织相当完善,警力充足;主要市区用电照明,郊区道路上使用汽灯;消防队设施先进,配备了新式救火机;街道以碎石铺成,显得井然有序。
外滩是上海最著名的景点,风景优美。这里和黄浦江之间有两排绿树和一片美丽的草地,总是保持得非常漂亮。还建有一座公共花园,仲夏夜的黄昏,有乐队演奏,几乎每个西方人都喜欢到那里去,有些女士还定期光顾。外滩上的建筑美观辉煌,让居住在这个城市里的人感到无限荣光。人行道上,你会看见来自各个国家的人。离开外滩,走进租界,会途经五花八门的各式商铺,“这里任何一个商店里,都能买到所有的东西,欧洲货或清国货一应俱全”。⑨美国国内的人一般认为,生活在上海的美国人大概不会有什么社交活动。“实际上,来到这里的女士们会发现,她们可参加的活动真是应有尽有。上海每个晚上都有舞会、家庭聚会或是富丽堂皇的宴会。这里还有歌剧。业余爱好者们拥有一个可爱的小剧院。……此外,打猎也是洋人十分喜爱的活动。长江下游沙洲之地,苇草丛生,野鸭、候鸟随处可见,都是洋人喜爱的猎物。英国人为了到长江和其他河湖里打猎,特别设计了一种华丽小船。每届春秋假日,风和日丽,便三五结伴,泛舟于上海附近的江湖水面上,出没于茂盛的芦苇中,一边打猎,一边休息。他们每个季度都会有三到四场演出。另外,還有巡回剧团每年都到上海来举行大型巡演。”⑩
由于租界各方面的条件都逐渐完善,洋人生活舒适,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开始把上海当成自己的家,而不是像先前那样,要等着在此赚一笔钱后再回家娶亲。他们先就结婚了。如此一来,这里聚集了很多已婚的年轻人,他们再不满足于清国旧式的宴会,而经常发明或引进一些新的娱乐方式,来唤醒沉默的旧时代”。11上海市场货物充足,应有尽有。“目前,凡是这个城市及其周围买不到的东西,都可由蒸汽轮船带进来。想吃日本的牛肉吗?这难不倒上海。而‘楚府羊肉’绝对是你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所能吃到的最可口的佳肴。即使在l月份,青豌豆、番茄和生菜也可从广州运来,而所有热带的水果都可从香港运来。”12在这里,家庭主妇悠闲自在,非常轻松,因为有仆人可用,“一切就会像上了发条的时钟一样,井然有序地运转起来”。13仆人们忠诚可靠,主妇坐享其成,根本无须操心。
总之,在《纽约时报》记者的眼里,1886年的上海租界已经非常适宜居住,洋人在这里生活舒适安逸,体面优越。到了1893年,租界再经7年的发展建设,自然又有所进步,可见,慕维廉的上述演讲并非自吹自擂,而是实话实说。
二、上海何以发生巨变
开埠四五十年后,上海租界面目一新,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如何做到,靠的是什么?有的说靠引进西方文明,有的说是上海自我发展的结果,也有的说靠的是租界制度,而法国学者白吉尔教授认为靠的是现代性。据她自称,1957年首次访华,上海给她留下深刻印象,让她“产生了一丝迷恋之情”,回到法国后,她“一头扎入了上海史研究之中”。14经过多年努力,于2002年推出法文版《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一书,3年后中文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该书时间跨度很长,从1843年开埠一直写到2002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止,涉及上海160年的历史。为什么要做如此长时段的研究,白吉尔教授直言是“试图采取另一种观察角度,即着眼于漫长的时间跨度中的变化”。在她看来,上海的历史极其复杂,但“从远处观察,在异地遥望,这部剧烈动荡的历史似乎由一种定式操纵着,一种超越一切的寻觅,即追求现代性”。15
何谓现代性?白吉尔指出现代性与现代化不同,“现代化是指变革的过程,是动态的过程,结果不能预料;而现代性是指由现代化及其成果所唤起的相应的精神状况和思想面貌”。16与中国其他地方不同,上海还没有等到现代化降临就开始追求现代性了。就在这个城市,“胜于任何其他地方”,中西两种文明走到一起来,西方“在十九世纪到达奇葩吐艳、盛极一时的阶段的各种组织制度”“各种价值准则的态度和规范”,都被移植过来。17鸦片战争后,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地被迫开放通商,其中,宁波是府城,福州、广州都是省城,上海只是县城,地位不高,也不那么起眼,为什么会发展得最好,成为中国最大的西方文明输入窗口呢?对此,学者早有兴趣,并做了相当多的探讨,其原因无非是上海地理位置优越、腹地宽广,并且本身是移民社会,不排外,容易接受新事物,经济基础较好,等等。白吉尔当然了解这些看法,但并没有老调重弹,而是进一步提出自己的新见解,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上海并不完全是殖民地。因为在上海中外商人是密切合作的,“如果说外国人把握了上海与西方市场间的纽带,中国人则继续控制着开放口岸和内地省份的物流管理。上海经济的运转依赖于这种中外商人的相互合作”,所以“不管上海怎么异化,她还是一座中国城市”,是中国人填满了租界的空间,“没有他们的认同与合作,任何规划都不能实现”。18
二是上海重利轻文。“上海从来就不是一座闪光的文化重镇。在这里,中华文明与西方现代性的相撞是以实用主义的方式来达到平衡的。当地上海对外来事物的接受和外国人在适应新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时,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困难,因为就中外双方来说,这里涉及的主要对象不是文化人,而是商人和冒险家,他们的目的是要尽快地使各自的谋利手段合法化,他们毫无约束的灵活性把异常的活力传递给上海社会。”19
三是上海城外有城。上海租界是建立在老城之外,这里受条约制度的保护,外国人享有自治权力,他们“建住宅造仓库,经营管理买卖,举行宗教仪式,说自己的方言土语,吃异国的食物,组织表演活动,服从他们自己的法律”,很快就将之建成一座欧化的新城。因此,她成了“动荡不安的中国领土上相对安全的小岛”,吸引了前来寻求利益的各国商人和众多中国人,“并为他们提供了多种文化接触的机会。”20
四是两种租界模式并存。在上海的欧洲新城里,公共租界、法租界“两大租界享有清廷批准的治外法权。每个租界有权按照西方政权模式进行管理和运用先进科技来改善居住条件”。它们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公共租界采用大不列颠的自由主义制度,法租界则奉行雅各宾派的传统”。两租界的“这些做法在经常与外商计划合作的中国精英们眼中,已经非常熟悉”,“西方的价值观就这样随着其精神原则转化为物质的进步而落地生根”。21
上述观点不入俗套,非常有力地揭示了上海何以能够在五个通商口岸中后来居上,成为中西文化交融的前沿基地以及具有现代性的内在原因,令人信服,体现了白吉尔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洞见。值得一提的是,她还强调上海的精英们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积极学习西方,但他们并不抛弃传统,“相反,利用传统为新的目标服务,使之与改革中的新事物取得和谐”。正因为这种学习不是简单的模仿套用,自19世纪以来,上海的现代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且内化为上海的城市精神。“上海优势的奠定,应归功于她创造的现代性。”22
三、憧憬上海:传奇永不消逝
开埠后的数十年间,上海从一个其貌不扬的中国县城一跃而为国际性巨埠、世界第五大城市。对于这个灰姑娘变身白雪公主的传奇,许多外侨认为是他们的功劳,是他们引进西方文明并加以建设的结果,所以上海是他们的上海,他们的家园,他们的骄傲。但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认定上海是西方重商主义在经济上剥削中国的明显象征,是中国对西方列强所处的不平等条约地位的主要提醒物”,一致予以批评。饶漱石甚至直言“上海是寄生虫的城市,是罪犯和难民的城市,也是冒险家的乐园”。外侨据此认为,“共产党干部和农村士兵对城市怀着本能的不信任感,而对上海人的不信任则纯粹是敌视”。23因而1949年共产党军队进驻上海前后,他们纷纷撤离。
紧接着,很多西方国家不承认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也封锁沿海,联合国实行禁运,凡此种种都对上海的发展十分不利。当时正在撰写《上海——现代中国的鑰匙》一书的美国学者墨菲非常关注上海的政治形势,密切追踪共产党实施的上海政策。如他针对上海第一任市长陈毅发表的声明,为把外界封锁的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我们必须有秩序地疏散人口,并且把工厂迁移到内地任何可去的地方”,在书中评论说:“纵使这种重新安置的规划可能是由于非经济上的理由而决定的,著者的意见却认为,至少在整个中国经济体制的现阶段,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该项措施是不明智的”。24不久,他发现上海方面把工厂迁往外地的议论渐渐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上海市的工业生产落在农村需要的后面”以及“共产党政府雄心勃勃的工业化规划”,拟在东北、华北、华中、华西、华南等地分别建立工业中心的报道。对此,他认为“从工业的角度来看,上海的有利条件也不大可能会被消除”,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只要“保持其贸易、商业、金融上的重要性”,“上海很可能将会依旧接近整个中国市场的中心”。不过,墨菲悲观地指出“这样长期的观点,在当前中国政府计划制订者的心目中,可能是不存在的”,但他坚信“上海的经济领导地位在地理上的逻辑,很可能会证明比任何政治论据更加强大有力,更加令人信服。大城市不会偶然地出现,它们不会为一时的狂想所毁灭。地理上的事实曾经创立了上海;一旦和平在东亚恢复,这些事实将会使上海在未来的岁月里繁荣昌盛”。25
墨菲的书出版于1953年,尽管他只能从相关报道中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上海的一些情况,推测上海在中共全国一盘棋的战略下地位下降,“形势是令人沮丧的”,26但他认为上海的基础和实力摆在那里,无论如何不会走向衰落,前景一定很光明。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一书的第四部分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是接着墨菲研究共和国时期上海的历史。据其研究,墨菲的上述论断大体正确。“从1949年起,上海的一部分经济活动就已萎缩”,“没有给上海的国际性和企业精神留有空间”。27但作为中国最发达、综合实力最强的地区,她又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支柱,承担巨大的责任:一方面,中央政府出于地区发展平衡的需要,不能给予她支持;另一方面,她还必须为国家建设做贡献,如人力物力支援。而更为重要的是财力支援,“从1950到1979年间,上海向中央上缴的财政收入超过了上海自身市政预算收入的13倍。一般是将税收的87%上缴北京”。总之,“在毛泽东时代,上海对国家的发展贡献巨大”。28
当然,这种巨大贡献是以巨大付出为代价的,人才流失使上海企业的技术力量有所下降,可支配财政收入减少迫使上海市政府把资金主要用于发展工业生产,而忽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其结果是上海本身发展不平衡,工业领域蓬勃发展,而城市建设严重滞后,并形成恶性循环。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海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至改革开放初期达到极致。有学者梳理了新中国成立30年上海发展的成绩单,共计“十个全国第一”“五个全国倒数第一”,前者主要由工业生产创造,后者则与城市建设欠债过多有关。29尤其住房紧缺显得更为严峻,“1980年,13万家庭没有住房,超过40万的年轻人,虽为合法结婚,但因没有住房而不得不分居”,30给上海人民的生活带来严重困扰。
于是,上海该往何处去,要建设什么样的上海,成为许多上海人思考的问题。但因为自1978年起“邓小平推行的改革是渐进式的改革”,致使“改革开放的前十年中,上海不仅获益不多,而且出现发展速度放缓的局面,城市的基础设施始终得不到更新”。31这种局面至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逐渐得到改观。“到了1990年代,改革出现了新一轮的飞跃,上海也终于被确定为改革发展的中心和‘龙头’地位”,结果成效明显,“上海的经济呈现出惊人的发展:增长速度加快,产业结构重组,浦东新区也初具规模。从1992年起,上海的经济增长率赶上了南方的省份:1995年,超过了14%,直至世纪末,也从未低于10%”。经济的发展使上海的复兴蔚为壮观,“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成为20世纪90年代上海最为经典的语句。原来的城市顽疾——交通、设施、住房、环境等问题逐渐得到解决,“上海人又重新拾起了他们祖辈在1930年代就产生过的憧憬:拥有舒适居所中的幸福之家”,“恢复了以往那种讲究穿着的传统”,“上海人终于能够享受休闲生活了”。与此同时,“上海的干部们对文化抱有极大的兴趣,同时也把文化当做漂亮实用的工具,……让这座城市闪烁出与其经济实力相符的艺术文化光环”。32文化具有凝聚社会力量的作用,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文化建设,两者相互促进,相互提高,使上海社会得以自我更新,再现辉煌。
20世纪下半叶,上海从被改造为单一功能城市,失去往日的光环,到实行改革,恢复多功能城市,重振雄姿,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由此,白吉尔感叹“上海的命运,就像中国的命运一样,有赖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她认为在这个重获活力和生机的过程中,上海依靠的是一个半世纪的盛衰所创造的传统,“即驾驭西化,因地制宜,自我完善,改造社会——这也是十几亿中国人民所感受到的现代性的传统”。对于迈向21世纪的上海,她也做了展望,上海会“以混合式体制主导当前的发展,并继续利用自身的优势发展壮大:外商云集,地理位置优越,历史的传统和独特的文化”。33与墨菲一样,白吉尔对上海的未来也充满信心,只要上海保持贸易、商业、金融等方面的多功能性,就一定能够续写传奇。
结 语
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一书原是针对西方读者而写的,后来被引进中国翻译出版。在中文版序言中,她写道:“向中国的民众尤其是上海的读者叙述描绘上海的今昔,对一个法国历史学家来说似乎有些过于大胆,甚至有些可笑。谁还能比那些从父辈、祖辈起就和这块土地存亡与共的市民更熟悉和理解这个美丽的大都会呢?……相比那些缔造与分享这个城市和她的居民的共同命运的参与者的体验,一切来自外部的关注点都可能显得不太恰当。由此,投向一个中国都市发展过程的所有的非中国人的目光,也同样可能被设想为是看不到问题的关键,即演变中的巨大的文化活力和适应力。因此,我必须接受一些读者的批评。”然而,读罢该书,可知白吉尔所言完全是自谦。她从一个外国人、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来观察上海的百余年历史,目光如炬,洞若观火,往往能够识得庐山真面目,纠正中國民众包括上海史研究者“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认识缺陷和盲点,这从国际知名的上海史专家张仲礼先生阅读该书后,有感而发,下笔千言予以推介就可见一斑。
白吉尔这部著作是一部引人入胜、极具特点的上海通史,时间跨度长达160年,从1843年一直写到该书法文版出版的2002年。以一人之力,有限的篇幅,要完成这么长时段的历史书写,难度很大,但她胸有成竹,驾驭自如,而且主次分明,详略得当,内容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足见其研究基础扎实,史学素养深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该书第四部分有关当代上海的研究尤见功力,因为这部分内容现成的研究成果很少,都要靠她自己搜集资料,包括实地调查、访谈等来完成研究。据张仲礼先生透露,白吉尔访问中国至少15次,基本以上海为目的地。在书中,她对20世纪最后十来年上海的某些新的社会现象、民众心态、婚姻家庭等都做了十分准确到位的描摹刻画,若非亲炙,恐难做到。
白吉尔这部著作开宗明义要追寻上海城市的现代性因素。她确实做到了全书以现代性为主线贯穿始终,把众说纷纭、错综复杂的上海历史既简明扼要,又生动传神地呈现出来。现代性表面上看是静态的,实际是动态的,上海人接受现代性有个过程,一旦接受,又能消化吸收,深入骨髓,流淌在血液里。现代性造就了近代的上海,促成她改革开放后的后来居上,“目前,上海利用她继承的丰富遗产,从当年在她土地上风行的形形色色的外国影响中吸取精华”,“她的效率和魅力——科学技术发明的志趣、经营管理的能力、优美精致的建筑和服装设计意识——在前租界提供的范例上得到了充分的发展”。34
除了现代性外,白吉尔在著作中还强调近代侵略上海的西方列强各有利益,各有诉求,并非铁板一块。它们的矛盾冲突、各自为政,不是分割上海、撕裂上海,而是展示帝国主义之间不同的价值观和多元的观念,这事实上对上海有好处,有利于培育上海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和文化品格。她还指出外国人和中国人之间也不完全是有人认为的那样相互仇视、对立,不仅有和平共处,还有中外商人间的互相合作,共同获利。上海在近代的跨越式发展,不是谁策划和主导的,恰恰是中外人士共同努力、共同打造的结果。作为西方文化的橱窗、近代中国最洋化的城市,上海也不是一味崇洋媚外,对西方经验照搬照抄,而是有所扬弃,有所借鉴,加以创造性转化,形成自己的城市特色和品位。上海之所以能成为全球的上海,对世界有吸引力,就在于她的与众不同、别具一格。这些论断朴实清新,给人以启迪和深思。
注释:
①14151618192021222327283031323334 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王菊、赵念国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83,1,中文版序第3页,中文版序第3页,前言第4、2页,前言第2、3页,第18、19、23页,前言第3页,97、101、103、104、101,中文版序第4页,298,322、282,320、321、319,334,363、370,370、373、384、385、386、389—390,399,中文版序第2页。
② 《工部局谕》,《申报》1893年11月17日。
③ 《赛会志盛》,《申报》1893年11月18日。
④17242526 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7,6—7,30—31,244—249,241页。
⑤⑥⑦⑧⑨⑩111213 《1886年的上海:租界见闻》,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1854-1911》,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57—63,58,58,58-59,62,62,63,63,63页。
29 沈峻坡:《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解放日报》1980年10月3日头版。
(责任编辑:李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