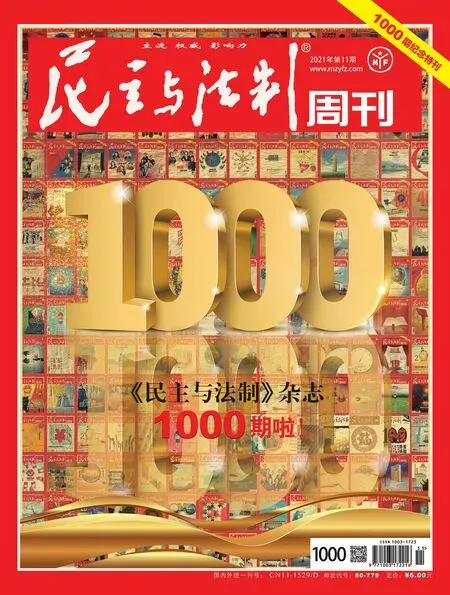为《民主与法制》1000期点赞!
马利
建党100周年之际,喜逢《民主与法制》杂志出刊第1000期。向党献礼,可喜可贺!
离开《民主与法制》已经有20多年了。作为一名记者,我是从《民主与法制》起步的。是《民主与法制》培养了我,让我从专业文学创作的队伍走进了记者的行列。

>>马利 资料图
从文学创作到新闻记者
说来也真是缘分。1990年《民主与法制》在庐山开通讯员会议,邀请了《人民日报》陕西分社的首席记者孟西安。当时我在西北大学作家班读书,毕业前夕到孟西安家做客。他正在为难,因为有个紧要的采访任务他无法应约参加会议,就问我是否可以去替他?我当时就回答:行!因为我从小就有当记者的情结。
1991年,我正式调入《民主与法制》。作为民主与法制社记者,我第一次到抗洪一线采访。那年夏天,江河泛滥,洪水肆虐,村庄沦为孤岛,公路变成码头,暴雨滂沱持续不断一片汪洋。江苏告急!安徽告急!大半个皖东浸泡在水里……抗洪救灾!总理亲自来到前线视察灾情指挥抗洪抢险。哪里有灾情,哪里就是战场。作为新闻记者,我主动请缨上前线。
大坝决口了,几十米高的水柱喷涌而出。解放军战士奋不顾身,扛着麻袋往上冲……抢救孩子的民工,背着老人的战士,泡在水里的指挥员……只有亲眼见到那个现场,你才有真切的感受。一种感动,一股激情,我边采边写,甚至在回北京火车上还赶着写稿。洋洋洒洒5000多字,大家都说写得很感人。我还没来得及得意,王树人总编辑拿着打好的稿子来找我说:“写得是很感人,可是你稿子上的人名和地名不清楚啊?这个站在洪水中指挥的人叫什么名字?”马上就要上版了,总编室主任急了。我更急啊!马上打电话去联系,那可是前线,所有的人都没有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怎么联系也找不到我采访的对象。老大哥朱克辛安慰我说,别急别急,第一次采访已经很不容易了。他看了看手表说:“这样吧,你马上走,返回现场去找。你不用急着往回赶,你补充采访的内容打电话给我,我在这边直接定稿。”首次采访就给我当头一棒,瞬间打得我晕头转向。当时,我觉得采访我应该会呀,我文学创作时,也经常到一线去采风啊!那时候我下基层采访到一个生产队,呆了近一年的时间。我们当年到一线采访,每次至少十天半月的。采访,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题啊!可我真是忽略了文学创作和新闻采访的截然不同。文学的典型是虚构的,或者说是依据生活提供的事实重新升华和塑造的,也可以说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文学创作更注重的是去体验和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内心世界、精神状态及命运起伏。即使是真人真事也必须要隐姓埋名,生怕读者对号入座。就像鲁迅所说:他“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然而,新闻恰恰相反,必须严丝合缝对号入座,5个“W”一个也不能少。
记者与作家的创作规律有许多不一致之处,比如记者更重视事实的实录,作家则强调想象力及创作力的深刻。就这个问题,我经常和时任《民主与法制》副总编辑倪正良讨论。他很认同我的观点,他就认为当年许多作家写的法制文学作品引起的种种侵权性的民事纠纷,多半都是因为想象的渗入、激情的失控,从而使文章出现失误。那么,如何把作家和记者的经历有机地合在一起呢?既要牢牢记着它的新闻性,又不只局限于此。在事实基础之上,又加进了文学对时空的穿透,把文学性也牢牢地把握在纪实原则之下。老倪对这个问题还是很重视的,也经常组织年轻记者一起参与讨论。
怎样做好一个记者?是《民主与法制》给我上了最重要的一课。
言传身教,革命者永远年轻
我到《民主与法制》的时候,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仲方同志是《民主与法制》名誉社长。沙洪同志是《民主与法制》社社长,总编辑是王树人,还有副总编辑张贻玖。我特别敬佩他们。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们的老总和副总,两个老同志,每天上班下班都背着一个沉重的大包。特别是王树人老总,每一天下班都要把我们明天要上版的稿件背回家,看完第二天又背回来给编辑部发稿。兢兢业业每一天,认认真真阅改每一篇稿件。言传身教,老一辈革命家带队伍就是不一样,讲道理深入浅出,谈写作入情入理。著名歌曲《你是灯塔》的歌词就出自我们沙洪社长的手笔。他谈到写这首歌词的创作经验时说:我十几岁就参加革命了,因为年龄小、个子矮,排队总站在最前面。当年我们的队伍行进在河北大平原上,就看见一轮特别红、特别大的太阳迎着我们的队伍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一直照耀着我们队伍。我非常感慨,那时年轻容易热血沸腾就写了那首歌词:“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他说,在实践中的感受是最深刻最难以忘怀的。景以生情,情以生景,情景交融就有了灵感……
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仲方同志,作为我们《民主与法制》名誉社长,经常参加我们的活动,经常跟我们年轻人讲当年他们参加革命的故事。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说当年他给毛泽东主席当速记员的事。他说:“你们现在的条件多好啊,都用上电脑了,当时我们只能用头脑。延安的条件很艰苦,我在速记班当班长,我们每个人脖子上挂一个小黑板,毛主席到哪里去讲演,我们就跟着去速记。记录整理出来再交给毛主席审阅,修改之后就是一篇文章了。”他记忆犹新地说到1941年的大年初一,他和几个青干校的学员用手帕包了花生、红枣到杨家岭给毛主席拜年的事。他说毛主席化开了半冻的毛笔,在白纸上写下了一行字:“肯干、肯学、又是革命的,必定是有意义的,必定是有前途的!”经过了多少年的战争风雨,他始终保存着这幅珍贵的题词。这几句话,一直是鼓舞他在人生和革命的征途上奋进的座右铭。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的小速记已经成了白发老人,成了著名的法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然而,一谈起这些往事,又像回到了延安,回到了青年时代。
无论是王仲方会长、沙洪社长,还是总编辑王树人,岁月留给他们的只是年龄的痕迹,革命却使他们的思想锋芒永葆青春。这都是老一辈革命家留给我们《民主与法制》年轻人的最宝贵的财富,也是给我们年轻人留下的最深刻记忆。是他们的言传身教,教会了我们如何当好一个合格的《民主与法制》记者。
前方一个记者,后方一支队伍
《民主与法制》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尽管我们前方只有一个记者,但他的背后却是整个《民主与法制》社。
《民主与法制》社气氛非常好,像一个大舞台。每一个编辑记者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都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
我是学中文的,开始对法律一窍不通,一切都得从头学起。可那时候我挺胆大的,什么都敢写。因为我的背后有一批学法懂法而且是法律知识水平很高的编辑和记者,他们就是我的支撑和靠山。
那个时候,《民主与法制》刚从上海迁到北京不久。我们的编辑、记者包括出版发行的队伍,大家都不分彼此,经常在一起商量选题、讨论稿件,有时候也争得脸红脖子粗,也真吵架、真生气、真拍桌子。但也真好、真团结、真开心、真快乐!生活在这个氛围里,每一个人都很有精气神。“化繁为简三秋树”,那时候大家都很简单,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跑基层,写好稿,办好《民主与法制》,不计较个人得失。
当年,我写的《用匕首收割的爱》。线索是张所菲提供的,也是她联系的采访对象和采访单位,责任编辑是朱克辛。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是我们三个还有发行部的刘巍一起去贵州采访的。因为涉及法律法规,那次采访,我们非常认真,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一起讨论采访提纲,包括要采访的要点等等。
张所菲是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朱克辛就来自法制战线,当过审判长,在刑庭、民庭、经济庭都干过,特别干练。他熟识法律法规,特别是对案件的处理、细节的把握等都考虑得特别周密。从选题、采访到案情分析等等,没有他们的帮助,这篇文章我肯定是写不好的。现在想来那时候也挺奇怪的,为什么最后只署我一个人名呢?尽管是我执笔写的,但成果应该是大家的呀!说老实话,那时候我们对署名都没那么在意,谁也没有想过要联合署名,我自己也没有想起来应该和大家一起署名。现在说来还挺内疚、挺惭愧的。功夫不负有心人,文章发出来以后效果非常理想,反响较大。后来,有专家评论这篇文章说:《用匕首收割的爱情》这篇文章与其说是事件本身吸引读者,不如说是入情入理的剖析,让读者耳目一新。
的确,犯罪学是一门复杂的学问。一个罪犯的心理复杂冲动往往由多种因素构成,大学生亲手杀死自己崇拜钟爱的偶像,正是由一种自卑膨胀出来的狂妄自私、滋生出来的凶残所驱使的。这种文章读后,使我们对法律、对教育、对人性等,都应该引起反思。对于罪犯的道德沦丧,只用一些激烈的言辞谴责是没有力量的,要紧的是笔笔入微、丝丝入扣、句句衔接、篇篇入理,真正找出医治人心的穴位。
后来,我又写了很多有关法治方面的作品,比如《畸形的爱》《残酷的爱》《用匕首收割的爱情》,还有《一个儿子对母亲的控告》《原始的残暴》等等。还有一些反映社会问题的,比如《忧虑·历史丑的复活》《警惕·假股票上市》《特殊工程》等等。有一篇文章,我还要特别说一下,就是《套上玻璃小鞋的举报者》,发表于《民主与法制》1993年第13期。因为写举报信而入狱的是农业银行一个普通职员,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因为一份告状信,使自己失去人身自由,被关进大牢。他是母亲、妻子和儿子的唯一依靠。妻子四处告状无门,母亲就是个农村妇女,也没有文化,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抱着两岁的孙子到处求神拜佛。以至于这个两岁的小男孩儿在很长时间内,见到菩萨,哪怕是摆在地摊上叫卖的小泥菩萨也跪倒磕头,用稚嫩的声音祈祷菩萨保佑,保佑我爸爸平安无事。这个细节挺让人心疼的,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然而,天真的孩子并没有为父亲求来保护神,使他爸爸得以解脱的仍然是公正的法律。
这个事件一波三折,我们的采访确实花了不少的力量。我一直清楚地记得受害者那张胆怯的面孔,他千方百计地找到我说:请你务必谨慎,我不是英雄我也不想当英雄,我并没有奢望,我只是想从此以后能平平安安地生活,顺顺利利地工作,以更发奋的努力,用自己的工作成绩来报答你们,报答帮助我、主持正义、给我关心支持的人们。至今我还保存着受害者给我写来的5封信以及他的单位给我们发来的信函、公文等。
1993年,八一出版社结集出版了我在《民主与法制》杂志上刊发的文章。时任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仲方同志亲自给这本书作了序。他说:“《民主与法制》杂志社的女记者,将自己两年多来写的法治类纪实文学结集为《用匕首收割的爱情》出版,值得祝贺,这是法治文学中的一个新收获。”这本书也可以说是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共同关怀帮助下完成的。没有大家的帮助,就没有这本书的问世。这本书也是我作为一个法治记者对《民主与法制》的汇报小结。
记录时代要求的、人民需要的
《民主与法制》创刊于1979年8月,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激流勇进的也是唯一的一本法制刊物。正如刘桂明同志所说:“当年还没有其他任何法制期刊,我国最大的法制媒体《法制日报》创刊于1980年8月,也比我们《民主与法制》晚了一年。《法律与生活》创刊于1984年,比《民主与法制》晚了5年,所谓最老是指在目前所有法制期刊与法治报纸中,《民主与法制》的创刊已经40年有余,再没有比我们《民主与法制》更老的法制期刊了。”也可以说,没有比《民主与法制》更火的杂志了。《民主与法制》是当年各报刊亭最好卖最畅销的主流杂志之一,最高的发行量每期达268万册。
什么是主流媒体?简单地说就是党和人民都需要的,都爱看都想读的,就是好作品、好刊物。什么是好记者呢?我觉得一个记者首先要对自己的文章负责任,对人民负责任。把好关、把好度,掌握好分寸,这是一个法治记者要具备的基本素质。当记者就是要有眼光,看得清、认得准,这是对一个好记者的魄力、眼力和写作能力的要求。记者当久了,文章写多了,自然而然也就会随着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了。
《民主与法制》经常报道一些有争议的人物和文章。我们的社会正处于转型阶段,人们的价值取向多元化。我们党内对一些新生的事物看法,在短期内也不可能都统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有争议的人物有争议的事件。如果我们主流的媒体不发声不过问,不理不报道,就很难把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现在是信息化社会,堵是堵不住的,回避和掩饰,都有可能让我们处于更被动。与其堵倒不如疏。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法制宣传还是非常深入的,反映法治活动的文学作品也很多。但不容忽视的是,那时候也有许多文章是借着重大案例,渲染犯罪细节寻找感官刺激的作品,在一些地摊杂志和报纸上也充满了这种社会新闻,并引起过很多非议。
那么,我们要怎么写民主与法治的文章?怎么来反映改革开放中遇到的各种难题?怎么去写一个大学生在光天化日之下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同学这个事实?《民主与法制》当时影响非常大,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编辑记者以认真严肃的态度洞悉社会,分析人物发生的种种波折,不为猎奇,重在剖析。让我们所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都要能写到让人读后掩卷沉思,如闻警钟才是效果。
办好《民主与法制》是党和人民的要求。一切为了人民大众!顺应历史的潮流,站在时代的潮头,认清前进的方向。一本杂志、一个记者没有明确的方向,不知道你的彼岸在哪里,那么什么风对你都不是顺风。只有认清了形势,看准了目标,有明确的方向,才能够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作为《民主与法制》社的一个老记者、老兵,我由衷地为《民主与法制》出刊第1000期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