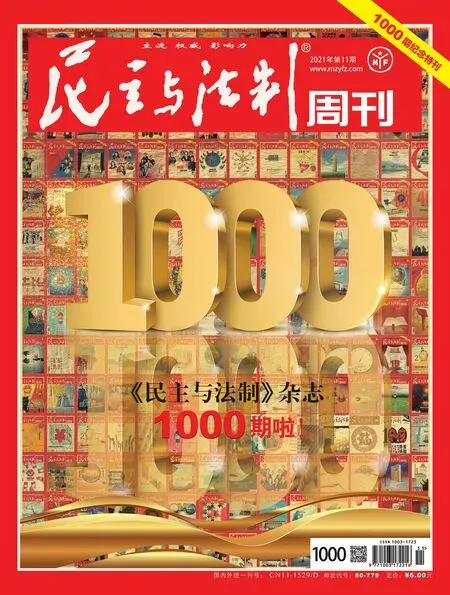我与《民主与法制》的不解之缘
王晋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就与《民主与法制》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0年,我考入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在那个知识匮乏的年代,在经历了从一名军人到工人再到学生的身份转变之后,我迫切渴望着能够汲取知识的养分,课余时间几乎都泡在学校的图书馆。
于是,在那个金色的秋天,在图书馆的书架上,我与《民主与法制》不期而遇。翻看内容,第一感觉就是这本杂志图文并茂,很接地气,往往从老百姓的家长里短说起,引申出背后的法律问题,兼顾了故事性和法律知识性,读起来让人欲罢不能。
自此之后,定期阅读最新出版的《民主与法制》,便成了我以及很多同学的一个习惯。在阅读的同时,我们会运用学到的法律知识分析杂志里反映的一些社会问题,同时带着这些问题回到课堂上,与老师、同学进行更深一步的讨论。
在求学时代,《民主与法制》无异于我的良师益友。而在参加工作之后,机缘巧合之下,我与《民主与法制》的缘分更进一步加深了。
1986年年初,鉴于第一届全国法制知识竞赛的巨大成功,《民主与法制》应邀与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了第二届全国法制知识竞赛。
彼时,我已经从母校顺利毕业进入黑龙江省委政法委工作。作为一名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我和周边的许多同事一样,都很希望能够通过参加这样一场活动,来检验大学四年学到的知识到底成色如何。

>>王晋 作者供图
记忆中,那一届预赛阶段知识竞赛的题没有一道题看起来很难,都是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但是,实际回答起来却不并容易,因为没有标准答案,需要每个人去认真推敲分析。
鉴于全国范围之内参加这项活动的人数达数十万之众,在我将答案寄出之后,便抱着顺其自然的心态,继续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了。
不久,我被调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随即又被临时抽调到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前往贵州省毕节地区大方、赫章两县,进行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状况的调研工作。
1986年5月中旬,正当我在大山深处进行调研工作的时候,突然接到了赛事组委会的电话通知,告知我顺利通过了法制知识竞赛的预赛,需要我赶回北京参加决赛阶段的比赛。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我在惊喜之余还有着一丝忐忑:决赛的集训准备时间本就只有一个星期,而赛事组委会经过黑龙江省委政法委、最高检、中指委等辗转联系到我,已经用了几天时间。当我从交通不便的大山深处,历经汽车、火车和飞机的舟车劳顿,千里奔赴回到北京的时候,准备时间已经只剩了一天。
在这种情况下,我索性就抱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心态参加了决赛。
决赛是在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厅进行的,全场录像,参赛选手都是从预赛中选拔出来的,共二十人,分组进行现场答题比拼,最后评选出获奖人员。
当时的场景,如今还依稀在目:我的爱人获得了预赛三等奖,也以观众的身份去了现场,给我参赛鼓劲;还有一对爷孙同台竞技:时年58岁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勇飞和与时年22岁在北京市宣武区法院工作的堂孙女王静;而后来曾担任过河北省高级法院院长的卫彦明,我最高检的同事周苏民、米陆明等等,也都参与了这届竞赛并获奖。
比赛过程中,我的发挥还算不错。一路过关斩将,但是在回答一道案例题:被告人触犯几个罪名、应处以何种刑罚的问题时,我却在分析对了人物所触犯罪名和应分别判处的刑罚的情况下粗心忽略了数罪并罚这一知识点,从而以微弱的分差与特等奖失之交臂,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小小的遗憾。
这件事也在今后的工作中时刻提醒我,法律非常严谨细致、容不得半点马虎,从事法律工作一定要慎之又慎。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能够获得这次竞赛的一等奖,也算上意外之喜了。而一等奖的奖品,一台当时最时兴的上海牌立体声双卡收录机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伴随着我的工作生活。在最高检外事局工作期间,我之所以能够迅速使用外语,这台收录机功不可没。而我爱人的奖品也很有意义,她获得的那台缝纫机,在当时还属于紧俏货。当时她单位的一位同事结婚,因为买不到缝纫机而发愁。正是这台缝纫机解了燃眉之急,也算是一桩成人之美的好事。
后来,我在检察系统的多个岗位上历练,还曾担任湖北省检察院检察长,日常精力被案山文海占去。阅读每一期《民主与法制》已经不可能,但每逢见到这本杂志的时候,我都会翻一翻看一看,如老友重逢一般亲切。
千期小杂志,百年大文章。
与浩如烟海的法学长篇大作相比,《民主与法制》看上去就是一本小小的杂志,但它却忠实记录和见证了我们国家数十年来民主与法治的发展历程和巨大成就。
在《民主与法制》出刊1000期之际,聊作此文,纪念我和《民主与法制》的难解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