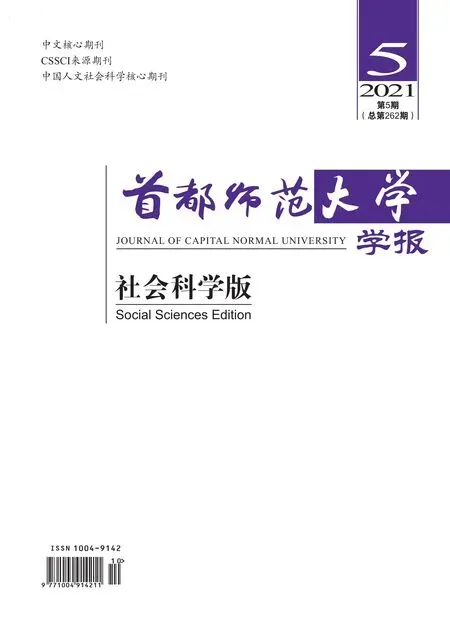促进高层次协同知识建构的CSCL可视化支持系统研究
任剑锋
一、知识、知识建构与协同知识建构
知识是一个日常用语,但又是一个受到众多领域重视的专业术语。从哲学上看,知识是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从共同体的角度看,知识是人类对世界的有组织的认识,是“对事物属性与联系的认识。表现为对事物的知觉、表象、概念、法则等心理形式”①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而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个人所拥有的知识是个体头脑中的一种内部状态。如根据皮亚杰的建构主义,知识则是“通过与环境相互作用而获得的信息及其组织”②邵瑞珍:《教育心理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8页。,但此界定过于忽视知识的客观性和公共性。传统上讲,知识是客观的人类共有的财富,是共同体所共同拥有的对于世界的有组织的信息。或者可以说,个体拥有的知识是对社会共同体知识的重新加工,是具体的并有个性化特征的关于外部世界的有组织的信息或反映。这种个人内部心理状态,再以约定的符号和规则表达出来,即显性化后,即具有公共知识的特征,它可能只是已有人类知识库中的沧海一粟,也可能在已有知识库中本不存在,因此增加了人类知识的总量,那么此知识就是新建构出来的知识。
从上述意义上讲,个人的知识获得,可能只是接受了(经过某种自己个性化的理解加工,从建构主义的角度讲实际上是用自己已有的组织原则解释了新信息表达的知识)既定的知识,也可能创造或建构了新的知识。传统的知识观是客观主义的、绝对主义的,反映在教育理念上则是传授主义的,所以学习即被认为主要是对既定知识的获得。而建构主义知识观认为知识具有主观性和相对性,学习者总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来建构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知识。然而,学习的结果及学习所建构的不仅仅是对这些共有知识在个人心理内部的个性化的组织,而且包括了个人的体验、价值观等“身份”方面的建构,即“学习使一个人变成了另一个人”,这是一个使个体身心参与到特定共同体的文化融入的过程。
在CSCL(Computer 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中,知识建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CSCL基于建构主义、情境学习等新的学习理论,知识的获得被认为不是学习者的被动接受,而是个体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积极主动地建构意义的过程,是以学习者已有的组织原则来建构对世界的解释的过程,所以用“知识建构”来代替以前知识的获得,这两者间是有明显区别的。
一般认为,知识建构一词首先是由著名的CSCL研究专家Scardamalia M.(马琳·斯卡达玛丽亚)和BereiterC.(卡尔·巴雷特)首次引进。在此之前,“知识建构”一词主要为商业研究所用,其含义指知识创建。①赵建华:《知识建构的原理与方法》,《电化教育研究》2007年第5期。作为知识建构在教育领域的创始人和最为活跃的研究者,Scardamalia和Bereiter认为,知识建构指对共同体有价值的观点和思想的产生与不断改进的过程②Scardamalia and Bereiter,“Computer Support for Knowledge-building Communities,”In T.Koschmann,CSCL:Theory and Practice of an Emerging Paradigm,NJ:Lawrence Erlbaum,1996,pp.249-268.。Nancy Law和Elaine Wong则认为知识建构是一种协作的、有目的的活动,通过对有关知识的优点、缺点、应用、局限性和未来的发展潜力进行分析,以达到提高知识本身的目的。③Law N and Wong E.,“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in Knowledge Building:An Investigation,”In Wason B,Ludvigsen S and Hoppe U.,Designing for Changing in Networked Learning Environments,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2003,pp.57-66.
可见,知识建构强调学习者间共同的努力,其结果是为共同体创建共享的智慧产品,同时个人也从中建构了属于自己的知识。以上的界定体现出了知识建构是一种协同的社会性活动。Stahl也曾指出,协作基本上可看成一种共同建构意义的过程,意义建构不能被视为参与者个体的心智表征,而是多人互动的结果。④基思·索耶等著:《剑桥学习科学手册》,徐晓东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16页。以多人的依次发言为例,此时的发言与老师让学生单独分别(其他学生不在,不参与)的发言不同,意义不是由单个学生的单个发言产生,意义的产生通常依赖对共享情境的引用,对之前发言的隐性继承,同时也为后续发言定下了基调。
知识建构的协同进行的特征或其社会性特征,也可以从知识的公共性或社会性中得到解释。例如知识的基础是语言、约定和规则,而语言是一种社会的建构;个人的主观知识经发表而转化为使他人有可能接受的客观知识,这一转化需要人际交往的社会过程,因此客观性本身应被理解为社会性,等等。考虑到知识具有社会性,并且社会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之“意义建构”是一种社会性人际互动活动,个人的建构建立在社会性的人际互动基础之上,所以可以把所有的知识建构都理解为是社会性的,是在人际互动中产生的。因此在CSCL中,较常用“协同知识建构”来强调通过有效地“共做”来创造有价值的共同智慧产品。协作知识建构所解释的是在一个共同体中如何表达个人观点并与其他成员进行社会交互的过程,这里知识的形成是共同体成员相互建构的结果,它不能独立于所处的社会文化情境而存在。
笔者曾指出,协同知识建构有不同的层次:浅层的协同知识建构在有信息共享的条件下(如浏览早期的静态web网页文章)即可发生;比较高层次的协同知识建构则需要有主体之间的社会互动(如通过BBS的交流),但协同仍可能是较低水平的;较高水平的协同,实际上发生在“实时共做”的层次上,如通过共享的虚拟画板,学习者持续地、实时地为完成共同目标而努力,但这仍未必产生最高质量的“共做”的智慧产品,因为对于如何有效地“共做”,推动协同知识建构向前发展,缺乏应有的办法。①任剑锋:《基于策略的可视化协同知识建构支持系统研究》,《电化教育研究》2016年第1期。笔者早前的一项研究和其他一些相关调查研究均发现,把学生安排到一个共同交流的空间(面对面或在线)中,如果没有相应的策略推动,高质量的协同知识建构是很难出现的。②任剑锋:《远程CSCL交互行为促进策略的研究——CSCL研究的新课题》,《电化教育研究》2007年第10期。可见,CSCL中更高层次的协同,应该表现为有效地持续向前发展的基于有效策略支持的“共做”,相应支持系统应该嵌入这些有效推动协同发展的策略,把人类指导者的烦琐工作转变成相应支持系统的自动引导。
二、CSCL中可视化技术应用与协同知识建构可视化支持策略
可视化技术是一种计算方法,它将信号转换成直观的图形或图像,将“不可见”变为“可见”,丰富了科学发现的过程,给予人们深刻与意想不到的洞察力。把可视化技术应用到CSCL领域,用于提高计算机支持的协同知识建构质量的研究,目前已经比较多。这样的较高水平研究主要体现在历次的CSCL国际会议中。为了较全面地分析CSCL中应用可视化技术的研究,我们对2010年以来的近4届CSCL国际会议(CSCL国际会议每两年召开一次)上发表的论文进行了调查,找到直接相关的文献共25篇进行分析和总结。从这些文献看,可以把相关研究归结为三个方向:偏重协同知识建构过程可视化的研究、偏重协同知识建构结果可视化的研究、对过程和结果均有涉及的研究。
第一个方向的应用偏重协同知识建构过程可视化。如Mei-Hwa Chen等人研究认为群体中知识是通过持续的询问轨迹产生的,随着对话的进行,原有的想法会不断更新,并且在同伴之间通过交互形成更进一步的想法,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据此,他们开发出了一个基于时间轴收集知识图谱的工具ITM(Idea Thread Mapper)。③Mei-Hwa Chen,Jianwei Zhang and Jiyeon Lee.Making,“Collective Progress Visible for Sustained Knowledge Building,”in Rummel,N.,Kapur,M.,Nathan,M.,&Puntambekar,S.(Eds.),Learning across Levels of Space,Time,and Scale:CSCL 2013Conference Proceedings Volume 1—Full Papers&Symposia.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the Learning Sciences,pp.81-88.Allan Jeong等人制作因果图,使对话和因果产生过程得以可视化。④Allan Jeong and Woon Jee Lee,“The Sequential Analysis,Modeling and Visualization of Collaborative Causal Mapping Processes and Effects on Causal Understanding,”in Rummel,N.,Kapur,M.,Nathan,M.,&Puntambekar,S.(Eds.),Learning across Levels of Space,Time,and Scale:CSCL 2013Conference Proceedings Volume 1—Full Papers&Symposia,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the Learning Sciences,pp.248-255.Kate Thompson,David Ashe和Dewa Wardak等在设计任务学习中对工具使用的模式识别和描述实践进行研究,他们采用的可视化方法是收集协同设计过程中图片、音频和视频。他们使用iPad投影到白板墙,此外还使用了录音机,每12秒对学生工作的图像进行拍照并整合,以分析协同过程中学习者不同类型的行为与工具的使用情况。⑤Kate Thompson,David Ashe,Dewa Wardak,Pippa Yeoman and Martin Parisio,“Identification of Patterns of Tool Use and Sketching Practices in a Learning by Design Task,”in Rummel,N.,Kapur,M.,Nathan,M.,&Puntambekar,S.(Eds.),Learning across Levels of Space,Time,and Scale:CSCL 2013Conference Proceedings Volume 1—Full Papers&Symposia,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the Learning Sciences,pp.478-485.
第二个方向的应用偏重对知识建构的结果进行可视化处理。如Roberto Martinez和Judy Kay等人的一个研究用雷达图来可视化相关协同的结果。该种图展示出以触控次数为表征的身体事件和以秒为单位的口头参与时间(展示了身体和口头的动作),以便进行直观分析。Roberto Martinez和Judy Kay还使用了贡献图来提示参与者对协同任务的贡献。该种图中用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参与者。每个协同成员的所有动作一起导致了最终协同结果的改变,贡献图显示了每个队员的动作占团队动作数量的比例。⑥Roberto Martinez,Judy Kay and Kalina Yacef,“Visualisations for Longitudinal Participation,Contribution and Progress of a Collaborative Task at the Tableto,”in Spada,H.,Stahl,G.,Miyake,N.,Law,N.(Eds.)(2011)Connecting Computer-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to Policy and Practice:CSCL2011Conference Proceedings.Volume 1—Long Papers.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the Learning Sciences.pp.25-32.
第三个方向的应用同时考虑到了协同过程与协同结果的可视化。如有学者在一个有关教师关注对协作学习影响的研究中,采用多点触控桌面、多桌面展示板与投影仪结合的形式来实现可视化,每个桌面都有一个放置在相同尺寸高清显示器上的26英寸的PQlabs多点触控层和表层深度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可以检测在任何时候任何一个学生触摸交互的表面。这样,运行的主机应用程序记录每个学生的不同的动作。多桌面展示板是在手持设备显示的一个业务流程工具,该工具使教师能够掌控课堂活动,给学生提供实时指导,控制各组的任务进程。多桌面课堂提供了组织桌面的功能,教师通过控制它向主机应用程序发送命令触发动作,例如锁屏和进入下一学习阶段,也可以利用系统所连接的投影仪展示各小组桌面的作品。①Tomoko Hashida,Koki Nomura,Makoto Iida and Takeshi Naemura,“Inter-Personal Browsing:Supporting Cooperative Web Searching by Face-to-face Sharing of Browser Pages,”in Rummel,N.,Kapur,M.,Nathan,M.,&Puntambekar,S.(Eds.),Learning across Levels of Space,Time,and Scale:CSCL 2013Conference Proceedings Volume 1—Full Papers&Symposia,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the Learning Sciences,pp.224-231.另外,Melanie Erkens等人的研究发现可视化的引导能够使小组学习参与者产生更多的解释性信息,这些信息被应用到后续工作中从而更好地处理问题。②Melanie Erkens and Daniel Bodemer,“Which Visualization Guides Learners Best?Impact of Available Partner-and Content-Related Information on Collaborative Learning,”in Smith,B.K.,Borge,M.,Mercier,E.,andLim,K.Y.(Eds.).(2017).Making a Difference:Prioritizing Equity and Access in CSCL,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CSCL)2017,Volume1.Philadelphia,PA: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the Learning Sciences.pp.127-134.
国内也有少量的有关可视化知识建构的研究:况姗芸等研究了可视化用于辩论从而促进知识建构实施模型;③况姗芸、蔡佳、肖卫红、陈文红、卢昀:《知识建构的有效途径:基于知识可视化的辩论》,《中国电化教育》2014年第10期。夏红讨论了在儿童概念建构中应用可视化表征的方法;④夏红:《知识建构的有效途径:基于知识可视化的辩论》,《内蒙古教育》2017年第3期。汪晓婷基于知识建构理论中“观点的持续改进”原则,设计并实现了一个支持协作讨论的可视化在线平台,该平台支持参与者的观点生成、联结与改进。⑤汪晓婷:《基于知识建构原则的可视化在线讨论平台的设计与实现》,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从上述CSCL可视化的现有研究来看,信息和知识可视化和多方面的技术都被较好地应用到协同知识建构的过程中,并产生了一些具体的和有特点的工具,这无疑能对CSCL协同知识建构的过程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些研究虽然都各自找到了某种角度的可视化途径,却没有形成对可视化知识建构问题的比较系统的分析。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这些可视化方法缺乏相应的宏观或微观活动支持策略的引导。引入这些新技术,并没有真正解决协同学习之“协在何处”的问题。这相当于我们发现以前为学生提供一个文字或者说抽象的共同交流空间还不够,因此又使用新技术使这个共同空间变得直观形象了一些,但实际上还是没有解决学生之间如何做、相应系统如何支持才能使得协同更有效这一更重要的问题。
可见,要使可视化技术得到充分应用,就需着手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建立一个系统地分析可视化应用策略的框架;二是研究把这些策略具体化并嵌入相应CSCL支持系统的办法。
要建立较系统地分析协同知识建构的支持策略框架,首先需全面分析协同知识建构的影响因素。笔者曾从教育传播系统的角度指出,CSCL学习环境中学习系统仍由教师、学生、传播信息、媒体等要素构成,但师生的角色地位和媒体与传统教育传播系统均有很大不同。⑥任剑锋:《远程CSCL交互行为促进策略的研究——CSCL研究的新课题》,《电化教育研究》2007年第10期。这个分析对CSCL协同知识建构的认知性影响因素做了较好的概括,但当时过于关注认知性因素,没有涉及情感、社会文化、支持技术环境等支持性因素。情境认知理论认为学习本身包括意义和身份两大方面的建构。综合上述各角度,在强调学习核心系统要素的基础上,增加动力情感要素、社会文化要素及信息化环境等支持性因素,笔者曾提出了一个较全面分析CSCL协同知识建构影响因素的框架,主要由如下方面构成:(1)协同学习活动与行为的组织与引导(包括宏观的活动组织方式及微交互行为方式);(2)学习者个体的认知策略与元认知水平;(3)组策略及其他社会文化因素(包括小组的分组及互动方式、虚拟共同体机制及其他社会文化因素);(4)动机情感因素;(5)信息技术资源与环境支持。①任剑锋:《网络协作学习中的协同知识建构引导策略研究》,《教育信息技术》2017年第6期。
根据这个影响因素框架,可以发展出引导协同知识建构向高层次发展的可视化策略框架,具体如下:(1)学习协同活动过程的可视化支持;(2)协同知识建构中的人际网络的可视化支持;(3)微交互行为的可视化引导与支持;(4)认知及元认知方面的可视化支持与引导;(5)虚拟的组织群体、场景、氛围的可视化支持;(6)动机、情感方面的可视化支持(让学习者随时能够看到自己及他人的表情、情绪、积极性、身份、贡献等);(7)相关数据、信息资源的可视化;(8)个体知识与协同共享的知识的可视化支持。
然而,这个策略框架各个侧面的具体策略如何?如何把这些策略嵌入到相应的CSCL支持系统中作为其功能的一部分,使之能够替代CSCL学习组织、支持者或教师的烦琐工作?
三、引导协同知识建构向高层次发展的可视化CSCL支持系统
建立了可视化CSCL协同知识建构支持策略框架以后,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把这些策略具体化并嵌入到相关系统中的办法。笔者前期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个别的类似策略在CSCL支持系统中的嵌入。②郭丽娜、任剑锋:《基于Silverlight的可视化协作知识建构工具的设计与实现》,《电化教育研究》2012年第4期。本研究则旨在全面和系统地将相应策略嵌入到可视化CSCL系统中,以期更好地推动协同知识建构向高层次发展。
(一)相关策略嵌入系统平台的设计思路
为了降低相关系统初步设计的难度,此处我们对上述支持策略进行了简化,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研究相关策略嵌入CSCL支持系统的思路:
1.宏观的协同知识建构活动组织及微交互行为的可视化引导与支持策略
宏观的协同知识建构活动组织的可视化支持思路是在系统界面嵌入图形钮表示的一些有效的CSCL组织程序,比如以嵌入笔者早先研究提出的“分布讨论型CSCL组织程序”③任剑锋:《分步讨论型远程CSCL交互活动的组织策略及相应系统的研究》,《中国电化教育》2007年第8期。为例,要求学生从点击程序第一步骤开始学习(如果前面的步骤没有完成,则不能进行后续步骤),这样能保证在程序上避免无程序性策略(或有某种程序但是需组织者有意记忆并在心理层面时时监控其执行从而增加认知负荷)带来的效率低下问题。
微交互行为的可视化引导设计思路是将相应的微交互行为引导策略进一步嵌入上述宏观程序中。笔者曾按照功能的不同对微交互行为进行详细地划分,主要有解释型言语、展示型言语、发展型言语等总共15类。④任剑锋:《网络协作学习中的微交互言语》,《现代教育技术》2010年第9期。理想协同知识建构中的微交互,从总体和个体层面都应具备适当的频度、多样性(多角度)、高的相关度、良好的发展性等特征。在主要基于语言的协同中,这些特征可以通过对相关微交互言语行为的统计和计算得到。我们研究了不同情况下的学生协同行为的表现,分析如何给予不同的处理,因而实际上是设计了一套处理规则,作为相应CSCL支持系统“自动”引导学习者协同发展的“产生式”规则。下面举几个不同侧面的具体例子。
在微交互言语的频度方面,对各种类型言语的发言量统计能够说明成员在知识建构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如果成员思路狭窄,其发言类型往往也会比较单一。例如在协同讨论过程中有些成员的发言集中于对其他人观点的认同或否定,仅仅用“某某说得对”“某某做得好”来进行发言,这是不利于协同知识建构达到高质量的要求。针对类似情况,我们设计当发言类型过于集中时的提醒策略,即当某一种类型的发言数量多于一定数量时,提示“可以试着表达一些有关主题的其他方面的想法”;如果“展示型”言语的发言量超过本人发言量的一定比例,则提醒“在充分表达个人观点的同时,请多关注一下其他成员的发言,并与之互动”等等。
在协同知识建构过程中,批判性的言语往往更能激发成员之间的热烈讨论,有利于知识的更深层次的建构,所以当学生进行批判性发言时,给予及时的引导更有意义。根据对批判性言语的发言量统计结果设计了针对批判性发言的提醒策略,比如当批判性发言较多时,提醒“注意要有合适的依据哦”;当没有批判性发言时,提醒“欢迎积极进行批判性发言”或“积极互动又独立的批判性发言,更有利于我们的学习”。
此外,我们也设计了一些具体策略用于改进参与者交互的频率与相关度。在基于文本的协同知识建构过程中,发言的频率过高会导致其他成员来不及阅读,发言频率过低则可能意味着缺乏充分交流。因此,根据对发言间隔时长统计结果提出相应的提醒策略,比如当两次发言间隔大于一定时间界限,即设计类似“发言不够积极哦,加油吧”等提示,而当两次发言间隔在合适的时间内,则提示类似“积极发言又能给自己充分的时间思考,做得不错”等话语。在体现个体参与内容的相关度方面,成员之间的依赖度和独立性是相对的一对属性,我们借助统计各类微交互言语类型的比例等方法,可以给学生言语行为以实时的针对性帮助,设计给予类似“是不是也发表一下您的高见呢”“看看他人有没有道理”等一些引导语。
2.人际网络可视化策略
在对协同知识建构中的人际网络的可视化支持方面,由于跨小组的成员之间互动很少,本研究只考虑组内的人际网络可视化。由于异质分组本身的特点,组员数量最好在3~5人之间,所以人际网络关系相对简单,分别用三角形、四边形和五边形表示相应数量成员数之间的关系。组员的互动关系设计可以随时查看,促进参与度,也能够在远程情境下增强在场感,并促进CSCL中的身份建构。
3.认知及元认知方面的可视化支持与引导策略
在协同任务发布后,对成员进行元认知问题提问并记录成员的回答,以此引导学生进行认知或元认知方面的思考。这些统计结果可以和协作学习完成后的学生自我评价相比较,用于分析个体学习效果和社会技能的提升以及协作任务的解决程度,如设计参与者回答“我熟悉该任务的内容吗”“本次任务的目标是什么”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协同的质量。另外,有些微交互行为的可视化引导与支持策略也常常涉及认知及元认知方面的引导。
4.相关数据、信息资源的可视化支持策略
在相关数据、信息资源的可视化支持方面,设计在协同知识建构过程中收集学生的相关数据,以文字和图表的形式实现其可视化,用户可获得更直观的感受。
(二)基于策略的可视化系统的实现
1.异质分组
在进行异质分组时,往往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分组依据,所以本系统设计了四种可供选择的分组种类,即按照专业、区域、系别、性别进行分组。教师在对学生进行分组时可以按照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图1是按照专业进行分组前后的对比图。

图1 分组前后对比图(左:分组前;右:分组后)
2.宏观协同知识建构的组织过程及远程实时共作的可视化支持
这部分对笔者前期研究①郭丽娜、任剑锋:《基于Silverlight的可视化协作知识建构工具的设计与实现》,《电化教育研究》2012年第4期。实现的功能做了一些改进。该部分在系统界面嵌入了如图2左侧的组织程序,学生点击相应步骤有序地进行协作学习,如果前面的步骤没有完成,则不能进行后续步骤,可以保证学习活动有效地向前发展。同时,能够提供远程共享“画板”(见图2)。参与者可以选择不同颜色笔等属性,和异地组员实时协同作图,进行思路沟通及共同知识产品的建构,从而大大改进远程协同的质量。

图2 对宏观协同知识建构活动过程及远程实时共作的可视化支持
3.学生微交互言语的提醒与引导
微交互行为的引导除实现前述的设计外,按需要查询数据库和不需要查询数据库两种情况分别实现。这也是相应“产生式”规则的一部分。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有些较简单的处理可以不需要操作数据库就可以实现,如在学生发言时设置一个时间间隔变量,当间隔小于一定时间时,提示“发言频率过高,请稍等片刻再发言”,当间隔大于一定时间还未发言时,提示“请积极发言哦”等等。再比如,可以简单统计学生发言的文本字数,即统计所发送的字符串长度,当字数多于一定规定时进行提示“字数过多,请进行简短发言”。另外,在协同知识建构的不同阶段,学生可能有脱离该阶段任务的行为时,给予相应的引导。二是需通过查询数据库,根据结果判定是否要进行相应引导。如发言类型过于集中时的提醒和独立发言数量过多时的提醒都需查询数据库。可通过查询数据库获得每类发言的次数。如按照建立的规则,当查到某类型的发言次数大于一定规定时,系统能够自动给出类似“可以试着表达一些有关主题的其他方面的想法”等的学习引导;而当查询到在一定时段,有学生的独立发言太密集,大于或等于规定的频率或数量时,则给出“请注意多结合其他人的观点发言”等引导。
4.主界面实现
主界面是学生使用最多的界面,在此界面中实现了主要的协同功能,如实时协同作图和言语讨论,并把推进协同的程序性支架与讨论的微交互言语类型等进行了关联,使得系统可以自动地随着协同步骤的进展,给协同中的沟通予以相应不同的有针对性的支持和引导。其中协同作图的图像实现了矢量化的处理,可以大大降低对网络带宽的要求,同时也实现了参考资料可视化、上传和下载等功能(如图3所示)。

图3 主界面
在本系统平台上,学生可以下载平台中的任何参考资料到本地计算机,也可以将自己认为有必要分享的材料上传到本平台。当学生想查看小组内其他成员的所有发言时,可以在左上角的下拉框中选择“聊天记录”,本组所有学生的聊天记录对话记录将会以预先设置好的格式显示在内容文本框内。
个体可视化界面是小组成员查看个人在协同知识建构过程中相关统计数据的界面,其可视化形式主要以文字和图形来实现。其中依赖度、平均发言时长、本次在线时长、独立发言比例和相应的提示都是以文字形式来实现其可视化。各类型言语数量、各阶段持续时长、对小组其他成员依赖情况的可视化都是以柱状图和饼图来实现的。
(三)使用测试效果
经过开发测试,工具本身可以顺利运行,实现所设计的功能。在局域网小范围使用中,受测学生表示本平台与Black Board等无策略支持的学习平台相比较有明显优势;嵌入的协作活动程序与自由协作相比,协作能更深入;协同画板“使人眼前一亮”,对协作作品的完成很有用,协作过程中对发言类型及组内关系等数据的可视化展示等功能“比较炫”。图4(a)、图4(b)和图4(c)展示了部分使用测试过程。

图4 使用测试图
四、小结
本研究提出了较系统地把CSCL协同知识建构的可视化支持策略嵌入相关系统的方法,设计和实现了一个可视化协作知识建构支持系统平台,能够较好地支持CSCL协同知识建构在高层次进行。如前所述,笔者的相关前期研究在较小的视野中(主要涉及CSCL协同知识建构影响因素的认知性因素)形成相对多层面的解决方案,并在彼时予以部分实现(未涉及可视化技术),后来又在个别侧面探索了可视化实现。本研究则基于更广的视野和框架,借助可视化思路与技术,较全面地实现了相关支持系统原型,特别在实时地针对性引导策略上形成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并予以实现。当然其他相关研究也有一些很好的解决思路与方法,对本研究颇有助益,如著名专家Scardamalia的CSCL知识建构支架对本研究涉及的认知及元认知支持策略框架有启发。然而如前所述,相关研究可能提出了某种独特的角度和可视化途径,但没有建立和形成在较宏观视野下解决相关问题的比较系统的框架与具体实现方法,特别是在可视化地实时引导学生交互过程的策略及将这些策略嵌入支持系统从而成为系统功能方面。本研究即针对这两个主要问题进行探索,把相关策略功能化,可以多方位地促进CSCL协同知识建构进程,尤其能够针对不同学习者的协同参与进程,给予适切的及时引导。当然本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本系统原型的测试运行只是在局域网小范围的情况下进行,尚未进行大面积测试,可能功能上的某些问题无法发现,我们将在后续研究中继续进行改进。
(感谢郭华、郭丽娜两位硕士研究生在编码等方面对本文的支持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