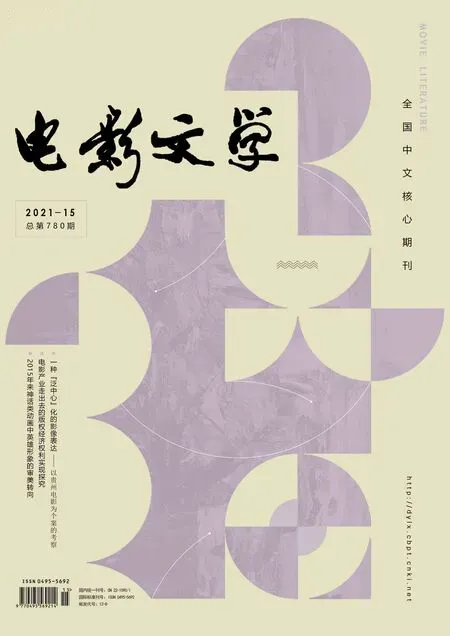2015年来神话类动画中英雄形象的审美转向
刁 颖 (四川美术学院公共艺术学院,重庆 400700)
神话是“各民族在上古时代(或原始时代)生活和思想的产物”。它让世界不同的文化有着相似的共通性。笔者认为:中国一直以“万物有灵观”作为中国动画神话类型中固定的类型程式,类型表征保持着三个固定的空间层级关系,上层为神界,由佛、神、仙构成;中层是人间,是人的世界;下层为妖界,由妖、魔、鬼、怪构成。这三个层次等级分明,界线明确。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这个宇宙之中存在着某种秩序”,这是中国人对宇宙秩序的认知,来自中国人对“天、地、人”的传统区域划分,千百年来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如同八卦中的乾坤;长沙辛追汉墓中的《“T”型帛画》等都有着对天界、人间,以及地下世界描绘的构架,影响着千年来中国人的神话思维。之后它又延续到小说、戏剧、电影等不同的媒介,建立起当下中国人相对固定的神话空间想象。
中国神话类型动画电影形象转变的节点出现在2015年《大圣归来》,之后包括《小门神》《白蛇缘起》《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哪吒重生》等作品中形象都悄然发生着改变。它们主要受到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后人类主义等美学观与艺术观的影响。改变是在全球语境下,这些作品主角人物形象虽然不同于迪士尼动画中过度戏谑与调侃等特征,仍然保持着中国神话作品中主角人物相对严肃的美学形象,但总体来看,这些形象的变化依然符合“神话并非神学,而是人类经验的总汇”这一神话学中公认的原理,这也让神话类型作品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相同或相似的审美价值观点。
一、“英雄谱系”下的新英雄形象身份的审美确立
英雄形象谱系包括:民国时期左翼电影中“抗战英雄”形象,如《中华儿女》《长空万里》《八百壮士》等;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电影中的“人民英雄”形象,如《青春之歌》《钢铁战士》《林则徐》等;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现实主义语境下的“英雄群体”形象,如《血战台儿庄》等,“伟人英雄”形象,如《开国大典》《大决战》等;新千年后,在商业市场的影响下出现了《英雄》等商业大片,之后主流电影开始崛起,出现“抗战英雄”《集结号》、“特战英雄”《战狼》、“行业英雄”《夺冠》等形象。由此来看这个英雄谱系连续且从未断代,有着相对完整的英雄历史谱系体系。众多英雄依附在“主流电影”下成为其中不可缺少的主题元素。正是这样的英雄形象谱系历史演变,培养出中国观众的“英雄性审美”情感,对影像中各色“英雄”形象不但不会感觉到陌生,甚至还有一定亲切感和依赖感。
在这样“英雄性审美”体系的背景下,动画电影也出现了如《草原英雄小姐妹》《小小英雄》《半夜鸡叫》等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英雄。除此之外,还有大量以神话叙事为背景的神话英雄形象。这说明动画电影同时受到真人影像和中国神话叙事的双重影响。真人影像中英雄人物与真实历史共同的架构关系,使得他们往往是严肃的,不能被随意调侃和戏谑的。有国外的学者认为:“中国有英雄崇拜的传统,其实这些英雄正是神话人物,但被当作了历史人物。”其实准确来说,应该是我们将历史中的英雄与神话中的人物进行了身份对接,赋予他们更多的神性,迎合人们对英雄精神神话性的审美想象。中国动画电影中的英雄形象虽然在历史性上较弱,但同样遵循相对严肃的英雄性审美观念,造就了《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天书奇谭》《宝莲灯》《雕龙记》等作品的审美体系一致性。
20世纪中国动画英雄题材主要来自传统文学的改编,有着典型的民族色彩,也是它们成为“中国动画学派”的前提条件。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工作的决定》要求创作的电影内容“除组织新的创作外,应尽量利用为人民所喜爱的我国现代和古典的优秀文学戏剧作品改编为电影剧本。”1957年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在优秀影片授奖大会上的讲话“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社会主义的民族新电影”中指出:美术片“最近几年来更加注意到选材与艺术表现的民族色彩之后,尤其有显著的进步”。他的讲话进一步鼓励和巩固了中国动画电影走民族之路的信心,因此,在1995年的美术电影(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前的神话题材作品,几乎全是中国传统文学、小说、戏剧等题材的改编。它们不同于美国DC、漫威电影中的“超级英雄”,如“超人”“美国队长”等;日本神怪中的“民族英雄”,如“桃太郎”等。可以单独称之为中国式“神话英雄”形象。神话性是它们最大的特征,由于遵循特伟先生提出的“主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创作观点,这个时期中的神话人物在意识形态、阶级观念上被选择性地弱化,它们所呈现的人性善恶是相对单一的,英雄与恶怪之间对立是绝对的。
新千年以来,美国动画电影中童话英雄出现改变,现象级的起点是2000年的《怪物史莱克》,之后又有《青蛙与公主》《长发公主》等。它们对传统童话故事中的“英俊王子解救美丽公主”这一固定“英雄”形象配对认知是一个重大颠覆。调侃与戏谑的手法充满仿佛诡异般的“达达主义”“解构主义”的破坏和重构的美学思想。它建立在美国的历史文化中,与嘻哈文化、无主流、无权威同样具有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审美倾向。个性化的认知对艺术作品并不寄托着乌托邦的美好想象,而是往往以破坏、消解来完成创作者极具个性化的新解释,力图建立起新的后现代主义的审美价值。当世界艺术被分解重构,童话世界中的“英雄”形象也发生了颠覆,“英雄审美”由此改变。在这样的影响下,近五年来,中国动画电影中主角相对严肃的正面形象也出现了变化。
笔者认为,作为中国新“神话英雄范式”的形象出现在2015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以下简称《大圣归来》)。它结束了1961年《大闹天宫》中孙悟空的范式形象,转而成为一个更加贴近生活,更加具有“人性”的“新”英雄形象。它极具个性的范式特征并不仅表现在创作的外形上,而在于它相对颓废的人物精神层面上。卡林内斯库认为“颓废”作为现代性的五个面孔中的一个,有着现代性的美学价值。“19世纪中后期在西方各国出现的众多‘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团体正是‘颓废审美化’的集中体现”。《颓废审美风格与晚明中国现代性》一文认为它最早来自《后汉书·翟酺传》,是从自然意义的层面向精神文化维度流变的,虽然有“消极”的一面,但表征出个性解放的价值意义。《大圣归来》中的大圣正是个性精神层面上的变化,不遵循传统“美猴王”的人设甚至还是相对“丑”化的。从这个丑化的、颓废的小人物上升到突破自我、拯救生命的英雄,这样的人物形象跨度巨大,变化符合动画名字中“归来”二字。在不少中国动画人心中,它不仅是人物的归来,还有中国动画学派的归来,从这个颓废的人物精神层面看到了当下小人物心中也有勇于改变、化身英雄的情结。
克罗齐在谈到“颓废主义”时认为它有着新审美特征:它的新倾向有着“印象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之类运动,是一种符号化的审美设定。当颓废人物形象与英雄人物形象并立时,它是现代青年人的精神和性格符号特征。正如《罗小黑战记》中“哪吒”等神话人物只是通过身体上标志性的符号来识别。符号化的标志是一个新的能指表征,它将现实生活小人物与神话人物对接,打破人们对传统英雄人物神采奕奕的精神面貌身份审美认知。在动画电影发展中这个审美认知来自《大闹天宫》中孙悟空的范式形象的确立,当时万籁鸣导演曾评价他“神采飞扬,勇敢矫健”。但2015年《大圣归来》的孙悟空形象是“颓废”的,有着现代主义色彩,审美认知随之转向。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哪吒形象是颠覆的、断层式的、跳跃式的,审美认知更加个性化与感性化,有着解构、戏谑、颠覆传统,有着后现代主义特征。同样,2020年上映的《姜子牙》,一个神话智者形象转变为神话英雄的形象虽然也有着颓废的状态,但人物的坚毅、严肃、勇敢等塑造是借助在中国电影“英雄形象谱系”下产生的新形象,因此他也是容易被接受的。
由于十七年主流电影中英雄形象多是正义凛然和严肃的,在这样的审美传统认知下,《大圣归来》以及《哪吒之魔童降世》等作品中主角颓废和颠覆的形象被不少人指责,认为它们破坏了审美标准。然而,当动画所特有的“绘制性”、非写实性本质构成了巨大保护伞将这些作品实现,可以说动画为多元化的审美标准提供了技术条件。从精神层面上来看,人们发现“神话”语境可以弱化“英雄”的历史,它的形象可以是非真实的,无约束和边界时,开始寻找新英雄的英雄性审美特征。当人们发现《哪吒之魔童降世》中,虽然“哪吒”的外形是个“魔”的化身,但精神层面上仍然是一个充满理想、内心善良、渴望被认知的角色。人物仍然具有明确的反叛世间的不公平和非正义思想,作品中所提倡的教育意义是明确和深刻的。这样的身份认同其实并没有脱离民众对“英雄”正义、道德品质上的认知,仍然被拉回“英雄性审美”范围之内。
2020年,影片《姜子牙》中主角姜子牙颠覆了传统的智者形象,转而成为一个有着高超武艺、巨大神力的传奇人物,成为中国影视神话中一个“新英雄”形象被大部分人所接受。不同的是,2021年春节档上映的《哪吒重生》中,哪吒形象再次突破,打造出一个有着类似美国“超级英雄”的少年形象。电影中除了兵器作为特定身份符号,有着相对明确的能指特征,并没有其他的符号性特指,更不要说所指的突破。同时,时空的脱离,让不少观众对这个少年有着明显的陌生感,对这个新英雄形象的认同感不强。
二、神话中英雄性审美特征转向
中国神话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神话,都是对虚拟世界的一种想象,是一种宇宙观想象性的构建。这种创建建构在“原始人受到自然界的束缚,活动规模是很狭小的,然而他们的想象却很阔大……因各民族所居住的环境与所遇的经验,而各自不同”,因而就形成各自不同的神话及神话中的英雄。这些不同神话同古代的唯心主义哲学一样都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唯一的区别在于哲学的世界观认知是相对理性的,并不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例如柏拉图的“理念世界”等都是从理论到理论的抽象解释。而神话则有明显的情感色彩,如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因此体现在世界其他国家神话中就有战神、爱神、智慧神等区别,中国神话中则有后羿、哪吒、二郎神等英雄人物。姜子牙同样也是智者出身,但在影像中成为一个以战斗力为主的英雄。神话人物的形象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正如《神话与神话学》一书在分析电视动画《哪吒传奇》时所说:神话人物形象是对神话的重构。这一观点说明神化人物的演化一直存在,因为:“‘文雅’的后代人不能满意于祖先的原始思想而又热爱此等流传于民间的故事,因而依着他们当时的流行信仰,剥落了原始的狂野的面目,给披上了绮丽的衣裳。”近五年来,神话类型人物身份转变情况有几种情形:
第一,对神界中的起着绝对性作用的神从实体的身份变成了虚拟的身份。虚拟神的设定会更凸显出为人或作为其他神的英雄形象。其实,在神话世界中各国的民众都公认有一个至高神存在,开天辟地,创造世界,并高高在上。它维持神话世界,遵循着一套伦理道德体系。它高于普通的神界,当人、神、妖的矛盾不可调和时,它就会出现。例如,希腊神话中“命运”,就仿佛是一个捉摸不到的虚拟世界。而在《姜子牙》《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罗小黑战记》中都有一个比神更高的虚拟神,起着维护和最终解释的作用。
第二,神话新英雄身份的人性特征和个性特征增强。正如姜子牙公然对抗了三界中最高界的权威,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这样的英雄人物身份的转变是自然的,甚至观众已经想不起他在小说中的原型是一个“智者”形象。这个新的身份中人性的特征是明显的。他是一个有着正义感的中年大叔形象,由于逻辑的合理性,他的身份转向是相对成功的。这样的身份设定与《大圣归来》中大圣略显“颓废”的中年人形象类似。《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哪吒典型的熊孩子形象也是儿童特征的表现。他们不再是20世纪神话英雄故事一开始就设定好的英雄或小英雄形象,而是有一个由人到神话英雄的大跨度转变过程。影片中经典的语言“我命由我不由天”:“这都是中国电影对社会理想与人生志向的当代表达。”
在神话类型表征的固定构架中,神与仙是最高等级,人、怪、妖等下级身份想成仙都必须经过重重考验,想从一个层级中上升到高一层级是极为困难的。《封神演义》讲述的是中国早期神的故事,有早期神话的反抗神与主宰神的叙事内容。“在早期神话中,还有一些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神。这些反抗神与主宰神之间虽然存在对立,但他们坚贞不屈的反抗精神和一往无前的执着追求得到了人们的肯定。这是对主体生命精神的赞扬。”这样的转变也让“他者”的眼光和视角发生了变化,让观众能从人的视角来看待上下两界,认同“众生平等”的价值观。让三界的界限不再如以前一样分明,是非对错也可以由人,而不是神来决定。
第三,现代社会语境下,建立起全新的无等级的神话世界。2019年《罗小黑战记》中虽然没有明显的英雄,但它所建立的神话世界是明确的,神话世界建立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下。它与2016年《小门神》《年兽》一样打破了神话世界以古代为主的时空观,这并非类型程式的突破,而是神话类型当代语境的演变。它们以现实社会为起点创建出自己对当代神话世界的新宇宙观。《罗小黑战记》中,创作者设计了一个人、妖、神共存的新宇宙,立足当下现实世界,是一种新空间的生存关系。首先,它既是神话性的,但又是现实性的;其次,它的三界没有上中下层级,关系是整合为一的。三界中人、妖、神共同生活在一个空间中,它们之间有融合、冲突、矛盾等关系。整部影片讨论着在现实的语境下人与人、妖、仙、怪如何能平等、自由地生活在同一个空间中的话题。面对这样的宇宙观其实就是一个人生境界,是一个人对环境的审美关系的认知,是一个内在的理据,讨论哲学人生观其实也必然涉及人的审美认知观念。
在之前的神话类型中,三界空间中人、神两界代表绝对的正义,而矛盾的对立面往往都在最底层的妖界。但“它们遵守同样的法则,并由同样的神圣物质所构成。在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本体论鸿沟”。《姜子牙》中宇宙观是相对宏大的,在这个宇宙观中只有人与神可以得以生存的权利,神界代表一切的正义和可传达的话语权,人界代表生存与繁衍的能力,而这两界要共同面对的对立面仅仅为狐妖。影片中英雄人物姜子牙的认知中解救的也只是人界与神界而非妖界。他虽然说的是人人平等的概念,却并没有包括妖。故事的结局只有反对面的狐妖成为牺牲品,它们被神界利用,被人界所唾弃,最终也没有能够得到解脱与救赎。我认为这是《姜子牙》影片的不足之处,未达到仙、人、妖、怪几者的自由平等。这点也是可以想象的,因为当远古神话中女娲(神)造人的时候并没有创造“妖”,他们的源起是不正的,因此是邪恶的。正义与邪恶的对抗是天理,是矛盾的最原始呈现方式,同时也是观者最容易接受的方式。
第四,平行时空下的三界各自独立的神话世界。2016年《大鱼海棠》建立的空间却并非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神话世界,虽然影片中的形象多以《山海经》中的神话生灵为主,但它割裂了历史时空,建立出的世界也不是一个有等级的世界,而是一个与人类世界平行的、平等的世界。它们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一个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神话世界观,这个演变是大胆的、作者化的。
第五,宗教仪式化的场景世界。在尼尼安-斯马特宗教构成的“八个维度”中提到了“神话的或叙事的”成为维度之一。指明了神话与宗教有着天然的联系性,神话是宗教的最初形式;宗教是神话诞生的一个温床。在世界各国早期的宗教仪式中暗含着不少神秘性,当神秘性被赋予一定的叙事情节后,神话的特征就很明显了。影片《姜子牙》中姜子牙与师尊的第一次矛盾冲突是通过如同道家道场“杀狐仪式”而来的。这个构图场面巨大、气势恢宏的仪式场所彰显了宗教的神秘性。《姜子牙》所设计的主角就可以通过完成“杀狐仪式”从具有神力的人上升到众神之长,成为一个真正的神。故事的矛盾恰巧在这里,他没有为了身份的转变而失去成为人的品质。在《姜子牙》中他更看重人的生命,是拯救苍生,而不是为了要成一个更高等级的神。《大鱼海棠》中“成人仪式”“打通人类世界天窗”等场景也具有仪式性。当神话被赋予了宗教性,它的场域就更加地清楚和明确了。
第六,游戏化的神话世界。《白蛇:缘起》作品中的游戏场景转换最为明显,人物的中心视角,玩家的第二人称视角,相对固定化的游戏场域,渐进性的游戏等级场景等都表明了它建构了一个具有游戏特征的神话想象。
这些影片在三界的类型表征中都有所体现,由于三界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各种形象的具体表现是各不相同的。如果我们将三种空间进行区分,第一种好比是一个塔,最下面是妖,中间是人,上面是神,这是最传统的三界图形方式,如《姜子牙》;第二种好比是一个圆,神、人、妖各占三分之一,如《大鱼海棠》;第三种好比是一个混沌,大家不分彼此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如《罗小黑战记》。这些多种变化都是基于神话性的叙事空间,在神话的叙事空间维度中,弱化了历史,不再强调英雄在历史中的作用,只是为了强调英雄的身份及他们的价值取向,这样的审美观是相对纯粹的,没有了历史的压力,更自由、更轻松,这也让作品审美的边界更广泛。
三、神话“英雄”符号性身份转向与道德观念
同希腊神话一样,在中国神话的天界是一个多神的世界,从某个角度上看是人间世界的镜像反映,这些神仙具有人的品质。与希腊神话不同,中国神话中神仙的角色似乎更要符合人间的道德品质,只有品质高尚的才能符合人们对神与仙身份的想象,决定了神话类型动画电影具有奇观性和神圣性。当下神话以动画的方式出现,成为娱乐休闲的附属产品,“成为一种言说方式”。因此,罗兰·巴特就认为:“神话是一种意指样式,一种形式。”
既然神话是一种意指样式,神话中的符号样式就自然成为寻找认同身份的契合点。例如,姜子牙不年轻的形象,披着蓑衣静坐在水边等鱼上钩。“沉稳”“不苟言笑”这些都符合小说人物精神面貌,而“鱼钩”“蓑衣”等作为特写符号而存在,证明了他的身份是姜子牙而不是孙悟空。正如哪吒的“红尖枪”、孙悟空的“金箍棒”属于符号中“能指”的特写身份物件。同样这是英雄形象的符号关系,对于反派的符号在动画中也很明确,这是“神与英雄与此变为圣王与贤相,妖怪与此变为叛逆的侯王奸臣”,这也是《姜子牙》叙事中遵循的原则。为此将怪诞的、善变作为矛盾的对立面——狐妖和纣王的形象。神话中的矛盾对立面是普遍存在的,除《姜子牙》外,《哪吒闹海》中吃人的龙王,《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申公豹,《白蛇:缘起》中的国师,《金猴降妖》中的白骨精等,都有着丑、恶的符号表征。在这点上,神话类型中,二元对立形象的符号化设计是明确的。
严格来说,近五年来的英雄形象都是一种反神话类型的影片。1961年的《大闹天宫》《哪吒闹海》这些不可撼动的经典,无数中国人心中认定的英雄及“英雄”形象成为符号,能指为具体的孙悟空、哪吒身份。当姜子牙的“纤细”“瘦弱”“苍老”形象颠覆了人们对英雄“高大”“帅气”“英武”“年青”的想象,形成巨大反差。它又一次重新定义了“英雄”作为一种符号文化的想象。在动画神话类型的叙事中,决定性的符号被赋予神力,往往是“扭转乾坤”结局的所指。结局一般是美好的是正义战胜邪恶的,符合观众对伦理道德及正义的意指想象。“神话不可能是一个客体、一种概念或一种想象,它是一种意指样式、一种形式”。在这些想象中道德伦理价值往往有着人们赋予英雄共同的人性价值观,“英雄”成为一种符号,担负起如“人人平等”“除恶扬善”等的价值观。《姜子牙》中有两大矛盾关系:一个是姜子牙与九尾狐的矛盾;一个是姜子牙与上清宫师父的矛盾。两者的矛盾越深刻,故事情节的传奇和神话色彩就越明显。影片《姜子牙》中的神仙代表“师尊”并没有遵守这样的法则,不承认“万物平等”的概念,以上帝般的眼光去改变世界的秩序,定义物种的高低。因此,姜子牙反抗形象就具有了“英雄”般的特征,这是对神界强权的反抗。姜子牙作为新英雄形象也被树立起同样的价值观:没有牺牲“小我”与“大我”的权衡选择;没有“他者”与“自我”的等级;没有利益价值高低的区分,力求符合中国佛家讲究的“平等”价值观。对道德和品质的要求,支撑着人们对美、对善、对真的审美认知。因此,无论他的外形如何,人物内在的精神设定是至善的,是对“英雄”品质的要求,也是观众对影片价值的认同。
神话叙事能将悲惨的生活弱化,让人们在神话的世界中弱化现实,甚至能找到可以解脱之处。因为“神话是一种交流体系,它是一种信息”,在通往另外一界时,往往有相关的符号作为中介。《姜子牙》中“骨铃”就是这样一个符号。主角在神话叙事中参与想象,与观者产生共鸣。C.A.托卡列夫和E.M.梅列金斯基认为,“神话具有不自觉的艺术性,神话思维和神话的叙述语言都具有隐喻性和形象性”,加上中国人对“英雄”本身的道德品质认同,将赋予故事更多的神圣性,以及人物更多的超自然能力和奇观性身份想象。影片中姜子牙以超级战斗力砍断人与九尾狐的链条,击碎上清宫与人间的链条,这样的设定是惊人的,但又符合对英雄神话人物无所不能的想象,他作为“新神话英雄”的大义大善形象在影片中是成立的。
在中国长篇小说中英雄形象与智者形象总是出现在一个团队中,他们由于能力的不同身份也自然不同,在叙事中的作用也不尽相同。这样成就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臣与武将的两种角色,因此,成功往往通过这样的一个团队的力量完成。有时一个团队中英雄可以是多人角色,但智者的形象相对固定,如《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水浒》中的吴用、《封神演义》中的姜子牙。他们总是以书生的形象出现在作品中,不具备高超的武艺和天生的神力,往往是通过无双的智慧来达到扭转乾坤或稳定时局的作用。影片《姜子牙》虽然弱化了《封神演义》中的智者形象,让人物从“智者”到“英雄”的想象中缺少逻辑关联,这样的缺失建构在神话叙事中是可行的,从伦理、善恶的角度去思考,会发现《姜子牙》与《大圣归来》不同的是妖不是绝对的恶,对于妖界,它们的地位是低下的,与上层之间的界线就不但是身份的定性甚至有道德层面上的定性。九尾狐就是祸国殃民、残害生灵的代表形象。当身份被定性,它们即使被上清宫利用后也难以说出真相,有值得同情的一面。《天书奇谭》《大闹天宫》《宝莲灯》《西岳奇童》中同样神仙不都是绝对正义和美好的。这些神话作品让我们思考:妖界为什么是邪恶的,为什么在拯救与救赎中不能包括妖?在三界中“人人平等”真的是平等关系吗?而在《罗小黑战记》中为什么人、神、妖共同生活在一起是符合当下的伦理道德的呢?正如王怀义所说:“在神话世界里,万物之间的界限不是静止的、固定的,而是混合的、流动的,天地万物之间不存在截然分明的本质区别,神话意象可以随时生成。”万物没有绝对的对错,关键是看你站在哪个方面看待它。
四、游戏叙事下神话“文化英雄”身份的公共性
在神话学的“文化英雄”中,也包括了“祛凶除怪、消除世间混乱、为人类确立较为普通的社会生活秩序的神话英雄”。。按照这个观点,姜子牙也是一位典型的文化英雄,甚至包括了《大闹天宫》中的孙悟空,《哪吒闹海》中的哪吒也是如此。在中国神话中为人类做贡献的还包括不少帝王,例如:大禹、启等。“神性的英雄被化归为圣王的臣属,从而使得人间帝王具有了独一无二的神性。”因此,它们也属于“文化英雄”,在当下的文化传播中他们的身份除了“英雄”性还具有一定的公共性。
现代信息传播体系中,“游戏”作为一种媒介方式同样起着文化传播的作用。影像与游戏在技术上的亲缘性让动画电影具有游戏叙事的特征。《姜子牙》与《白蛇:缘起》一样具有典型的游戏叙事特征:首先表现在场景调换的对接上,游戏的场景往往是平行对切的关系,为了不影响游戏玩家的流畅性,往往会省去叙事中的“过渡”关系,场景进行直接的跳接,所以我们会觉得游戏的叙事节奏更快。同样,《姜子牙》中也有这样的快节奏的跳接方式,甚至是场景拼贴关系,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如同波普艺术中的复制、剪切和拼贴。其次,游戏关卡中的场域设定。《白蛇:缘起》中典型的是“塔楼地下室”关卡,而在《姜子牙》中是“纣王山洞”的设计。由于游戏与动画技术的相似性,游戏叙事的特征出现在影像中是较多的。它改变了中国传统神话叙事中的“慢”节奏,改变的是叙事中的诗性色彩。如《哪吒闹海》中“小鹿追逐仙鹤远去”的缓慢的长镜头叙事。这样的节奏关系让我们与西方动画大片在叙事上越来越接近,但缺少了中国人在电影本质中诗意化的叙事特征。
在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的语境下,中国传统神话中人物身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个身份是拼贴式的,是符号化的,更是游戏角色式的。艺术的后现代性导入影片中,人类女孩妲己变化为动物并没有遵循矛盾所说的:远古神话中“典型的人化为动画的神话”方式,而仅仅是在身体上增加了像妖一样的特征,狐狸的耳朵。这样的拼贴与组合让其身份形象呈现多元化的、个性化的特征。
当下游戏语境中早已不只有中国化的想象,它同样包括西方神话世界对英雄认知的想象。在古希腊的神话英雄与中国神话世界的英雄一样,有着悲天悯人的人格情感。例如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偷来了“火”。而中国神话中鲧为人类偷来了“土”,他们都受到了高一级神的处罚。但相对于人间,他们的道德品质都是高尚的。在《姜子牙》中姜子牙为了解救人类小女孩不惜放弃自己前途,牺牲了自己可能拥有更高的神权的机会。虽然游戏叙事在节奏方面缩小了世界动画格局上的差异性,但它作为一种相同的文化传播介质同时拉近了大众审美差异,将姜子牙这个文化英雄进行教育和道德价值的传播是有益处的。姜子牙被定义成了并列于“孙悟空”“二郎神”“哪吒”等之后的“新英雄”形象,力图从动画影像中构建出一个相对完整的中国神话类型世界。当“神话更被自觉地纳入重新建构富有中国特色的当代公共艺术文化体系的社会政治行动之中”,此时的神话是公共性的、大众化的,符合当下大众审美认知的。
结 语
新“英雄”形象及身份作用在近五年的长篇动画电影中出现了变化。包括英雄及英雄性的审美特征转向,英雄符号化的凸显,新英雄伦理道德带来三界等级关系的层级变化等,它们共同影响了当下英雄形象边界的模糊和扩容。当下公共的文化语境是多元的,早已不是对与错、好与坏的二元式的简单对立。在面对世界多元艺术的冲击与中国传统神话思维约束的双重作用下,复兴“中国动画学派”的愿望愈加强烈。多年来我们力图打造一个新的世界动画电影格局,而中国动画电影中以神话类型建构最为完整和丰富,它同美国童话类型、日本的神怪类型、欧洲的民间故事类型共同构成动画电影四大格局的样态。因此神话类型的中国动画电影,这些作品负有引导观众纵观世界与回望历史,回归中国人自己的审美价值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