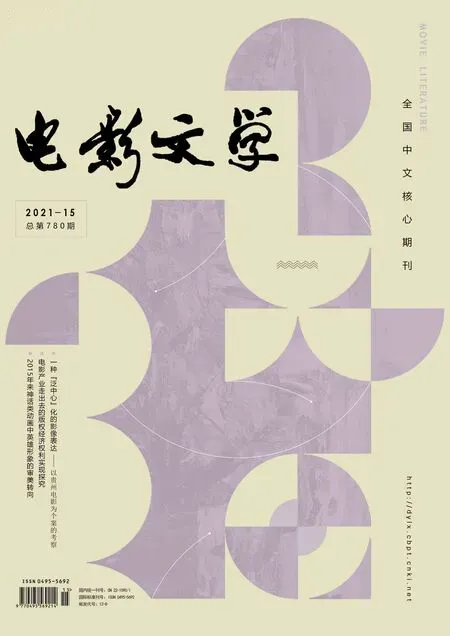青年的影像:对国产青春电影的青年叙事和青年形象的研究
郑文杰 吴春彦
(1.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4;2.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4)
纵观历史,1919年中国青年学生以独立的社会团体组织了五四爱国运动,这是青年学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首次以其先锋性和先进性迈上时代的舞台。尔后,在互联网技术的全面渗透下,新一代青年借助信息技术开始主动生成,创造新的青年亚文化实践活动,并积极反哺日常生活甚至主流文化,从而建构出属于青年群体自身新的文化样式。
历史地看,从最开始的五四运动到现在的青年亚文化实践,青年群体都当之无愧地成为新生事物(新媒体、高新技术产业)热情的实践者和追捧者。所以,在较长的时间内,青年形象和文化所表征的进步性与现代性、启蒙性经验遥相呼应,异质同构,它本身所负载的表意、叙事与象征功能可以作为展现时代风貌、社会症候、民族与国家形象的能指。而电影的“照相性”也说明了电影媒介借助对青年生存状况的展示,完成了影像对国家政治、历史、文化结构发展和变革过程的再现。不论是整个左翼电影运动前后上映的《三个摩登女性》(1933)、《十字街头》(1937)、《马路天使》(1937),还是“十七年”电影的《青春之歌》(1959)、《我们村里的年轻人》(1963),以及今天像《无问西东》(2018)这类现实主义电影,它们对青春记忆和经验情有独钟,纷纷以中国青年身上带有的先进文化烙印来勾勒出特定时代与社会的变迁轨迹。
一、青年的故事:从怀旧纯爱叙事到伦理化情感叙事
中国古典美学建立在天人合一基础上的主体与客体交感和合的体验论之上,而艺术作品中的审美意象便正是在主与客、意与象、情与景的直接审美感觉中相契合而产生的升华,审美意象中主客、意象、情景在民族创制的艺术作品中呈现出一种不可分离的关系。明代美学家王廷相所说的“言征实则寡余味也,情直致则难动物也”,正是说明了情要与景互相统一才能构成审美意象,“情”必然要通过“景”来表现。审美意象中“情”与“景”结合的方式主张“化景物为情思”“以景结情”,那么文艺作品不仅要实现对“景”的复现,更要通过“景”实现“情”的揄扬与传递。包括影像在内的文艺作品“表意”的目的便是着眼于“传情”,也就是说影像意义释放的最终目的是建立观众与故事之间的情感联结和代入枢纽,而作为文艺创作的电影对于故事的表达本质上也是诉诸人在心理体验、普遍认同感的开启和传达,以此达到共情、合意的审美效果。由此,以情动人的情感化叙事策略往往成为电影实现审美表达的惯用经验。
2013年《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便确立了国产青春电影以校园怀旧的纯爱故事为基本叙事模式,作为现代工业生产的电影所具有的机械复制属性与文化消费属性使其自发性地延续着这种叙事建构。尔后直至2018年《后来的我们》,国产青春电影皆以堕胎、出国、车祸、分手等可供复制的类型元素来强化悲情与虐恋的故事基调,并借由残酷式、戏剧化的叙事内核瓦解了作为电影本性“照相性”的真实。所以,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国产青春电影心照不宣地把对青年群体情感的书写和表达紧紧地扎根于爱情的土壤之内。
其实不然,中华文明与历史的凝聚绝大多数是以传统家庭关系的维系为根基的。中国哲学由天人合一的基本精神所产生的对天崇拜的情结便产生了浓厚的血亲情感关系,由此,中华民族的天人合一便指向了血缘关系的合一。随后世代相承的“集体主义”思想以及“血浓于水”“落叶归根”“舐犊情深”等根植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念则揭示了人们对亲情和血缘的依赖,“家庭”这一基本的社会单位构成了每个人成长过程的原初情境。国产电影的创作自然也受到了民族文化传统与历史积淀的耳濡目染,所以电影故事中以情动人的“情”很多时候是以家庭伦理中的亲情为滋养的。中国早期长故事片《孤儿救祖记》(1923)奠定了国产电影“影像传奇叙事”的美学范式,影片借由杨氏家族的承嗣风波宣扬了惩恶扬善、劝学忠孝的社会性主题,由此开创了国产电影伦理化情感叙事的先河。在此之后“影像传奇叙事”的发展如电影《空谷兰》(1926),灵魂写实主义的《小城之春》(1948),“十七年”电影佳作《舞台姐妹》(1965),第五代影人的经典作品《黄土地》(1984)、《红高粱》(1987),当代现实主义电影《相爱相亲》(2017)、《地久天长》(2019)等,伦理化情感叙事便早已一脉相承了。这些电影都是把对一系列现实与历史问题的揭露转换表达为对夫妻情侣、父母子女及其同窗之间的情感故事的阐释上来,以此应对时代话语的瞬息万变。虽然中国电影历经百年发展产生了各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种积淀已久的情感经验在国产电影的创作中却保持着惊人的稳定性,或许这更有利于消弭电影故事与观众之间的心理隔阂,达成电影基于情感叙事编码与观众解码的默契。至于爱情,它早已作为一个泛化元素而广泛贯穿、渗透于亲情话语之中,在以家庭伦理为纽带的根基之上,各类电影通过泛化爱情元素的点染来完成伦理化情感叙事的情节转折、情绪烘托与主题表达。
相较于其他类型的电影,家庭空间之于国产青春电影有着至关重要的存在价值。年青一代受制于年龄的束缚而使他们不得不接受来自原生家庭的照顾和管束,因此家庭场所、家庭关系在国产青春电影所展示影像空间之中也占据重要的地位。虽然“家庭”这一概念在此前校园怀旧纯爱叙事的电影中也随处可见,但它在故事中呈现为一种被架空的视觉假象,仅仅只是强化悲情与虐恋叙事的始作俑者,成为与血缘亲属毫无关系的虚幻构建。从《小时代》(2013)到《六人晚餐》(2017),父母一辈对青年当事人爱情的极力阻挠成为影片悲剧结尾产生的根源,这些电影对家庭空间和关系的营造基本上是“伪现实”的,与当代年轻人记忆中有关“家庭”的经验相去甚远,又对社会现实的映射与影片主题的构建并无裨益。
直到最近几年上映的以《嘉年华》(2017)、《狗十三》(2018)、《快把我哥带走》(2018)、《过春天》(2018)、《少年的你》(2019)等为代表的电影序列,它们逐渐释怀了国产青春电影对纯爱叙事的执拗,转而用更加锐利的眼光触及到了当代青年群体的成长经历及其与父辈、长辈、同辈之间的情感纠葛和关系变化。“家庭”在国产青春电影的创作中逐渐承担起反映社会要素、关系、结构的能指,并与现实产生了明显的互文与对话关系。《嘉年华》将目光聚焦于来自离异家庭的受害者小文,母亲对她所遭受的伤害麻木不仁,父亲在其成长中不仅“缺席”,面对强权亦无可奈何,无父无母的“黑户”小米为求自保又对真相缄口不言,影片借此诠释了男权经验笼罩下作者对女性弱势群体公平与正义的呐喊;《狗十三》借由13岁少女李玩因为两只“爱因斯坦”而与父辈、祖辈的周旋,隐喻了90后年青一代的纯真年华在校园、家庭、父权意识形态多重钳制下逐渐遭到泯灭的残酷现实;《快把我哥带走》更是让暌违已久的手足之情重回银幕,电影借由妹妹时秒与哥哥时分关系的对峙到和解,暗指了现代家庭中的独生子女与血缘手足境遇的差异以及家庭结构(父母关系)的完整性对子女的影响;《过春天》借由16岁“单非仔”少女佩佩以“水客”的身份游走于深圳(母亲)-香港(父亲)之间,牵连出作为他者的香港人在深港(陆港)离散局面下遭遇的身份认同障碍和身份属性异质性的尴尬;《少年的你》把三个青少年的原生家庭刻画得更为细致、深入,影片展现了陈念——母亲在外躲债逃亡、父亲始终缺席,小北——自幼缺少家庭关爱、被父母抛弃,魏莱——母亲极度自私伪善、父亲强势和冷暴力的家庭关系,重在揭露青年亚文化群体在社会—校园之外边缘与灰色地带的生存状态。
所以,青年形象是指向社会政治内涵的替代性存在,而伦理化情感叙事又作为对群体文化心理的准确把握。国产青春电影逐渐从年龄的概念中跳脱出来,通过伦理化的情感叙事书写青年群体在家庭关系及空间观照下的普遍生存境况,从而把民生问题、社会弊病、时代症候、国家形象等社会性主题象征性地同构为伦理情感化主题,使国产电影通过对青春记忆、情感、经验的叙述进而构建出整个中国的文化风貌。
二、反叛的青年:离经叛道的亚文化群体
回首中国电影史,启用青年形象叙事的电影本就屡见不鲜,但银幕形象中的“反叛青年”首次出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第六代导演登台的阶段,分为前互联网时代的第一阶段和新千年以后互联网时代的第二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反叛青年”在媒介与文化视域下呈现出离经叛道的亚文化气质,他们皆出现于大规模都市化运动后的城市之中——一个各种礼俗、思想、身份鱼龙混杂的集合体。
(一)第一阶段:前互联网时代的“反叛青年”
第一阶段的“反叛青年”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前后,前互联网时代是以第六代导演为首的对社会底层青年边缘生活的书写。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与世界文化的接轨,打破了此前文化高度一体化的社会格局,而城市中的中国青年率先感受到了这种空前的思想解放浪潮。在多元思想的启蒙下,城市青年寻求个性发展、获得突出成就、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愿望同社会强制实施的主流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产生了强烈的冲突。因此,他们试图通过边缘化、颠覆性、对抗性的姿态完成对主流支配阶级文化霸权的反叛。
借鉴社会学与文化领域的相关概念,中国本土的亚文化理论是以本土具体的青年亚文化实践活动和对象为根基的,前互联网时代青年亚文化现象研究突出地表现在:摇滚乐研究、代沟研究、“越轨”研究等。而每个时代艺术文本的表达与当时的文化观念、社会实践常常是相统一的,第一阶段的“反叛青年”与前互联网时代的青年亚文化的研究重点产生了无意识的耦合。
1.尖锐的摇滚乐:赋予青年群体反叛的内核与实质
有众多电影创作者纷纷体现出了他们对“摇滚青年”的偏执,例如张元的《北京杂种》(1992),管虎的《头发乱了》(1994),路学长的《长大成人》(1995),甚至第五代导演田壮壮的《摇滚青年》(1988)从片名上就直接体现出了他对“摇滚乐”这一青年亚文化现象的青睐。归根结底,中国摇滚乐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走向鼎盛,它在前互联网时代的青年文化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也恰好在时间上体现了它与电影银幕上出现的“摇滚青年”的吻合。作为一种宣泄的方式,摇滚乐能够替代性地抚慰青年群体在社会生存与情感生存中的挫败感。他们借用“摇滚”符号的象征意义完成主体意识的书写,自由精神归属的建立,并深深借此标榜自己与主流社会/成人世界的决裂。所以,摇滚乐在青年抗衡主流文化众多的尝试中,不仅是一种独立的现代文化形态,更“具有尖锐的批判向度,预示新的文化意识的产生和推广”。而众多电影创作者大量借用摇滚乐和“摇滚青年”的亚文化现象来赋予青年群体反叛的内核与实质,其实是通过对社会行为规范的破坏来赋予自身追求自由,探寻理想生活的权利。
2.代沟的差异:家的式微使青年的反叛顺理成章
“当变迁的速率过快且幅度过大时,代与代之间就会发生隔阂。”20世纪90年代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西方文艺思潮的汹涌而来加速实现了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的现代化社会转型,中国青年的思想观念、审美价值和人生理想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前辈的生活经验在社会快速的变革中早已显得不合时宜。所以,代沟问题是前互联网时代青年亚文化实践直接导致的必然结果。而第六代导演对代沟的书写则围绕“家”的概念,以“反家庭化”和“去家庭化”的叙事策略来呈现中国青年的反叛及其与隔代人在意志上的背道而驰。因为社会权威力量对中国青年的“规训”主要是以家庭对他们个性的约束来实施的,也就是说在影像中对“家”的力量的弱化或者虚无化是建构“反叛青年”行之有效的策略,这意味着传统的家庭寓言和神话在此时的电影中表现出若有若无的式微状态。“反家庭化”体现为家庭地位和作用的形同虚设,父辈一代对青年个体的干预逐渐变得力不从心,导致他们与家庭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例如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1994)中的无视父母管束,整日在外厮混的马小军;王小帅的《极度寒冷》(1997)中不顾家人劝阻,执着于行为艺术的齐雷。又或者青年个体为了追求独立与自由而呈现出对家庭的叛逃,例如《头发乱了》中从广州奔往北京学医的叶彤,《长大成人》中远赴海外学艺的周青,贾樟柯的《小武》(1997)中终日在外游荡,最后被父亲赶出家门的梁小武。青年个体为冲破家庭囚禁个性的牢笼,而毅然对家选择了漂泊、远走式的背离,本质上也是一次切断家庭桎梏的对“反家庭化”的深层表达。
“去家庭化”对代沟问题的表现则更为大胆激进,电影创作者直接隐去家庭在影像中的空间结构,使其不复存在,青年个体得以直接跳过或脱离来自家庭力量的规约,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从而赋予了青年反叛人格存在的合法性。例如《北京杂种》中流浪的北京青年摇滚团体;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1993)里遗忘了家庭住址的小东,以及他的《十七岁的单车》(2000)中从一开始就隐匿了家庭背景、在北京混日子的小贵。“流浪的基本属性就是物质和精神生存境遇中那种失根或无归属感,以及与此相应的流动不定的生存状态。”不论是“反家庭化”家庭结构的残缺而带来的无归属感,还是“去家庭化”家庭空间的直接缺位而带来的失根,基于代沟问题所造就的“反叛青年”在精神向度上其实是对西班牙小说中流浪汉形象的承袭和流变。16世纪西班牙的“流浪汉小说”(西班牙语:La novela picaresca)《小癞子》《古斯曼·德阿尔发拉切》被证实是关注边缘亚群体的早期文本,正是因为当时西班牙长期的积贫积弱而产生了大量的流浪汉,导致他们整日没有穷尽地流浪在外。正因西班牙小说中的流浪被认为是对“家园”母题的反叛,是对传统和谐、稳定、安全家庭生活的背离,所以第六代导演在关于亚群体的影像创作中有意削弱或消解了家的完整性,正是为了诠释离家在外的青年个体在行动和精神上漂泊无依的流浪。而流浪被赋予有悖于传统的冒险、探索和自由之意,所以,银幕上的“反叛青年”对家园/家庭/父辈呈现出积极的叛逆姿态,迫切走出压抑个体自由发展的“铁牢笼”,借助青年亚文化的启蒙思想来与社会主导的意识形态相抗衡,并由此揭开底层流浪生活的千姿百态,从而寻求个性解放、自我发展、梦想达成的人生之路。即便像马小军和齐雷尚未彻底走出家的束缚,但身处家中,父辈意志与自身的颉颃所造成的无助、迷惘和无归属感也使他们不得不在精神上眺望理想的乌托邦世界(在精神上流浪)。
3.越轨行为:反叛青年宣告对社会主文化的极端偏离
改革开放高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使城市边缘青年被迅速抛出社会主体结构之外,青年个体的目标和价值如果长期被主流社会忽视就会促使其产生偏离的行为,而犯罪和越轨则是他们宣告自身与社会主文化对立、偏离的实践活动,例如偷窃、斗殴、凶杀等。也就是说中国青年的越轨行为是前互联网时代的青年亚文化实践活动的极端形式,而第六代导演在银幕形象上塑造的“反叛青年”正是通过这种反文化反社会的极端形式来宣告自身与主流价值的疏离。如娄烨的《周末情人》(1993)中为了报复告密的同学而将其打死的阿西,因为感情纠葛一怒之下将阿西刺死的拉拉;《头发乱了》中关掉病人输液管,目睹其死去的叶彤;《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在小胡同斗殴,在卢沟桥准备打群架的马小军及其同伴;《小武》中整日以扒窃为生的梁小武;张元的《过年回家》(1998)中失手用扁担打死于小琴的陶兰。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青年浸淫在新思潮与新事物的发展之中,各种异质文化的冲突导致他们价值观的失衡,在亚文化研究的视域下,中国青年越轨行为的文化根源正是由于文化冲突下家庭功能的失调(父母缺席的马小军、梁小武、陶兰)、学校教育的偏颇(同学告发恋情的偏激、阿西暴力裁制)、青少年亚文化的贫困(出入于游艺厅、导致价值观偏差的拉拉)、社会主体文化的内在分裂(从归依到推翻传统文化、拥抱新文化的叶彤)等所造成的。而身处底层的中国青年遭受社会带来的不公与失意后,以极端、激进、疯狂的亚文化实践活动来瓦解社会规范和伦理道德对自身的牵制,借助这种想象性的方式完成了对自身生存困境的解围。这些具有越轨行为的“反叛青年”皆凌驾于社会主导文化之上,是对道德与法律的双重僭越,他们的肆意妄为势必会比“摇滚青年”给社会带来更多的麻烦和困扰,也势必会比“摇滚青年”在社会上更具“存在感”。
(二)第二阶段:互联网时代的“反叛青年”
新千年之初,第六代导演也仍在积极进行着青春电影的实验,但其中一些导演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靠拢或妥协下,完成了从叛逆到归依的创作变奏,银幕上的“反叛青年”开始迷途知返,逐渐退去了曾经“嚣张”的气焰。虽然此时仍有一些电影作品中的青年还残留着反叛的身影,但银幕上的青年故事大多还是让位给了像《开往春天的地铁》(2002)、《绿茶》(2003)等讲述都市男女青年世俗化的情爱缠绵。
新千年以来,“致青春”开启了国产青春电影类型创作的神话,在青春类型元素的加冕下,不厌其烦地诉说着校园青年男女的纯爱童话。但基于校园怀旧纯爱叙事的电影所塑造的青年并不具有反叛与抵抗的亚文化特质,其间讲述的世俗化的爱情故事在文化立场上就已经默认了电影本身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仰赖。而真正具有亚文化特质的银幕青年形象应当属于近几年上映的伦理化情感叙事中的“问题少年”,伦理化情感叙事的青春电影皆呈现了青年个体与家庭关系的异化,本质上是对前互联网时代青年亚文化“代沟”理论的延续,也是对第六代导演所描述的“反家庭化”叙事策略的迭代表达。而青年个体只有通过对家庭这一基本单位的对抗才能完成对社会权威力量的对抗,所以,只有围绕“家”的概念而创作的电影文本才有构建“反叛青年”的可能性。
1.互联网促成了“反叛青年”温和的特质
“网络新媒介的无深度感、暂时性、分裂性和全球化特征促使在其基础上生成和传播的青年亚文化不再坚持抵抗任何单一的政治体系、主流阶级和成年文化,他们甚至不同程度地弱化了某些‘抵抗’特质”。诚然,在网络时代,中国青年对主导文化的反叛和抵抗不再像前互联网时代的摇滚乐和越轨那么引人注目了,而是以挪用与拼贴、同构与狂欢、表征与意指等形式,杂糅了文字、图像、影像、声音等媒介载体,在日常生活和文化消费中实现隐形、温和的抵抗。进一步联系当下的社会现状便会发现这种“温和”的抵抗特质并非无迹可循,原生于互联网的“屌丝”文化、“佛系”文化和“丧”文化等,其所反映的并非集体单纯的“精神胜利法”,或许是借以群体自嘲之名在面对激烈的社会矛盾之下企图用温和、缄默的方式来掩盖自身的无所适从。
而网络时代下的国产青春电影对青年故事与形象的书写,基本上与网络青年亚文化温和的特质是同气相求的。近几年上映的伦理化情感叙事的青春电影主要是以青年个体与家庭关系的异化来影射社会和国家的发展状况的,所以故事的着眼点被局限在了对“病态家庭”与“问题少年”关系的展示之上。《狗十三》开始时,父亲态度极为强硬、坚决,在不征得李玩的同意下,把她在学校选的兴趣小组改为英语,事后李玩只是以沉默和逃离来面对父亲示好。后来爷爷买菜的时候不小心把“爱因斯坦”看丢了,父亲又妄想通过一堆的“谎言”宽慰李玩,李玩也只是撇下父亲和爷爷等人独自外出寻找。继母和奶奶企图以假乱真,用另外一只外形相似的狗来冒充“爱因斯坦”,李玩在识破大人们的谎言之后也只是以青春期叛逆少女的哭闹和争吵来与之对抗。《快把我哥带走》中调皮捣蛋的哥哥时分用尽各种方式来整蛊妹妹时秒,妹妹也只是以带有幻想式的许愿祈求哥哥消失来表达对他的厌弃。《过春天》出生在单非家庭中的佩佩,港深的空间分界切割了她的父亲/学校/社会属性与母亲/家庭/家庭属性之间的关系。佩佩在打工时目睹了大陆游客丢戒指的行为后,她矢口否认了自己大陆人的身份,再加上她常以粤语/父语与他人交流,实际上表明了她对大陆人身份(母亲)的疏离与对立。因此,在家中她以情感关系的疏远以及对母亲/母语普通话的失语来与之相抗衡。所以,青年反叛与对抗的客体皆指向了自身的原生家庭,相较于前互联网时代在整个社会上具有规模化、团体化、尖锐化的摇滚乐,互联网时代下国产青春电影中对“反叛青年”的塑造已经没有此前那样尖锐了,变得温和了许多。
2.受制于主流文化制约的“反叛青年”
德塞托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把当下人们的消费行为总结为“消费的生产”,意味创造性地(反抗性地)消费主流文化产品,并产生属于消费者自己的意义。当下,网络青年亚文化在互联网中对于文本的创造基本上是以主导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和传统文化为材料进行的,最为常见的便是源自影视剧、综艺节目并风靡各大社交平台的表情包和鬼畜视频,他们通过对现有的主流文化资源草根式地僭越和袭击来昭示自身温婉的抵抗样态,成为一种满足自身娱乐、狂欢与宣泄需求的文化实践。或者说是以抵抗之名实现自身审美认知的创造性活动。而再以符号化体现出对原初符号的强烈依赖性,是以肯定的形式来装载否定的内容。也就是说,网络时代青年亚文化所昭示的抵抗姿态必须受制于主流文化的制约,青年群体只有借助主流文化之力才能完成抵抗的实践活动,其本质是在认同主流文化的基础之上进行反叛的。青年亚文化实践活动对主流文化的认同和追随也与近几年电影银幕上的“反叛青年”开始心意相通了,虽然他们身上边缘、叛逆的印记依旧没有消失,却产生了立足边缘眺望中心的积极倾向和姿态。《嘉年华》中在廉价旅馆做清洁工的小米,她企图利用“真相”讹诈来的钱换取一张“身份证”,目的是让自己摆脱“黑户”的身份而成为一名合法的中国公民;《狗十三》中处于青春期的李玩虽然性格叛逆、乖张,但她争取英语考试年级第一、物理竞赛全省第一的成绩却备受父辈与祖辈的认可;《快把我哥带走》中妹妹时秒许愿把惹是生非的哥哥带走无非也是出于对家庭和谐关系的维护;《过春天》中的佩佩加入“水客”团队,表面上是为了攒钱实现日本之旅,其实是出于被认同和需要的渴望,而这种渴望源自青少年对温馨家庭氛围的向往;《少年的你》中,不论是弱势群体陈念,还是校园霸凌者魏莱,她们皆是企图想通过高考——国内最为权威的选拔性考试使自己跻身主流,前者是为了奔往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北京,争取美好而宽裕的生活,后者则是为了得到父亲的认可。即便是街头混混小北惩恶扬善的品性也是为社会主流价值观所认同的。
结 语
正如青年群体所追随的步伐是与新生事物的孕育并驾齐驱的,所以青年文化一定程度上表征了现代性、先锋性与启蒙性经验。虽然带有亚文化气质的“反叛青年”是对世俗与主流的忤逆,但他们身上先进性的印记并没有消失。影像当中的“反叛青年”通过对已有界限的逾越,不断冲击旧规范、旧准则,并促使相应政策的调整,为当代的消费生活、文化思想、价值系统、科学研究都带来了耳目一新的重要变化。而文化创造的过程决定了社会创造力的发挥,所以亚群体的“反叛青年”与先进文化依旧是气脉相通的。
另一个心照不宣的事实是:国产青春电影从此前对男性长大成人的书写纷纷转变为对女性生存境遇的关照。伦理化情感叙事的青春电影皆以女性青年群体的青春记忆和经验来探究父权文化桎梏下“她者”的成长与崛起。正如带有亚文化气质的“反叛青年”是对世俗与主流的忤逆,而女性形象与“反叛青年”的耦合是对父权社会下女性道德神话的颠覆,也是对父权文化秩序下“贤妻良母”的反叛,从而努力从附属的“他者”跃身成为独立的“她者”。像《嘉年华》中的小文、小米,《狗十三》中的李玩,《快把我哥带走》中时秒,《过春天》中的佩佩,《少年的你》中的陈念,这些亚文化气质的女性形象褪去了以往光鲜亮丽的华丽外衣,或是性格叛逆怪异,或是经济条件窘迫拮据。电影纷纷借助女性身体与形象的丑化来瓦解自身作为欲望客体的能指,以此抗衡男性观众的“窥淫”欲。而这些电影对父亲形象贬抑化处理为女性主义的书写带来了一次有益的尝试,但更重要的是:国产青春电影尽可能规避掉了爱情这一重要的叙事元素,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影像对于男女两性和谐关系的展示,而此前国产“小妞电影”正是借助爱情的母题不断地言说着“一种自觉的归顺与臣服,一种由女性表达的、男权文化的规范力”,导致电影中对女性主体形象的塑造难以从父权文化的怪圈中跳脱出来。或许伦理化情感叙事的国产青春电影中银幕女性形象的成长与崛起表明了女性主义的影像化尝试又有了进一步的突破,在以女性自我意识为观照下力求实现女性在社会上自由、平等、独立的话语构建,更加深度探究当代女性在社会上的生存困境和情感问题,并造就未来电影中性别平等意识的普遍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