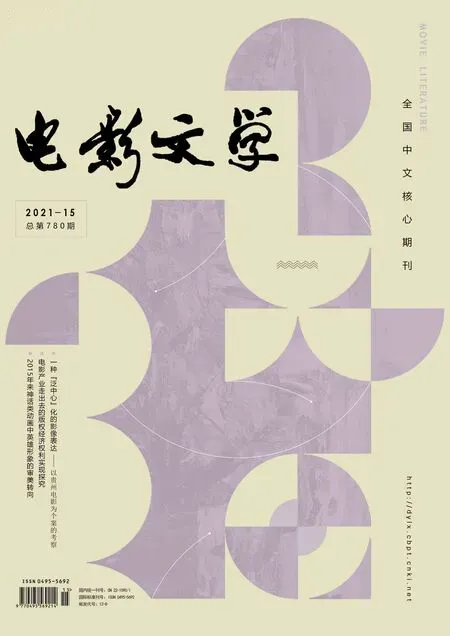欧美生态电影的“异质空间”
郝志华 (忻州师范学院公共外语部,山西 忻州 034000)
异质性空间这一描述性语词,译自米歇尔·福柯于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的“heterotopia”(异托邦)概念,指称一种建立在现代工业社会文明基体之上的“散落各处”的空间形态。断裂、差异、相互作用及其对抗是此类空间的突出表征。而在深层指涉上,福柯又从“话语与权力”的视角切入,阐释了异质性空间这种有别于主流秩序的存在,其本质可视作是一种重构人际关系、权力归属以及未来想象的探索性的社会实践。“恶托邦”“乌托邦”可以视作两种较为突出的异质性空间的表现形式。而福柯关于异质性空间这一携带美学思维、社会学批判理念的表述,也契合了当代欧美电影工业后现代转型中所标榜的自我变革的发展诉求,由此开始通过形塑奇观意象、建立灾难叙事等方式,融入电影文本的创制流程之中,并着重围绕对于“恶托邦”(反面乌托邦)、“乌托邦”的平行呈现,力求呈现能够容纳多种异质性元素的美学空间,揭露和批判生态破坏、能源匮乏、生存困境等一系列现实危机问题,展示西方社会主导的生态哲学理念与发展观,以此去均衡影片的观赏性、思想性以及社会性。而也正是借助异质性空间的建构,欧美生态电影文本得以清晰勾勒出了彰显灾难美学理念、传达生存反诘话语以及撒播核心价值的想象景观与现实图景。
一、异质性空间:欧美生态电影影像美学书写的新面向
(一)奇幻意象、现实指涉:异质性空间的构成要素
与福柯所描述的有别于现实社会群落、且反现代文明主流逻辑与秩序的“异托邦”相呼应,欧美生态电影渐次通过营造大量富于想象的奇幻的意象群,同时注重彰显现实批判理念,由此逐步建构了这一序列影片对于异质性空间的影像呈现样式与叙述机制,使虚幻、游离、碎裂等想象语义成为其最为突出的参数。而在借助想象对于历史记忆、当下现实以及未来时空进行奇幻意象打造的基础上,比如呈现文明高度发达且与世无争的世外之域、拥有智慧生命的地下抑或海底世界、奇异瑰丽而又神秘莫测的外太空等的同时,欧美生态电影又将视角聚焦于对时下真实的社会空间的镜像投射上,运用诸如隐喻、象征、反讽等多种修辞,去显影现实情境中已然积存、必将面临的一系列危难与困境,诸如各类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现象、能源枯竭等,从而令奇幻意象与现实指涉彼此映照,强化了异质性空间在电影文本中的在场性,渐次生成了该类影片具备标志性的美学影像样态。例如《2012》《阿凡达》《地心引力》等由美国好莱坞抑或西欧电影工业所输出的生态科幻影片,就渐次构成了当下欧美生态电影美学影像的代表性序列。如在影片《2012》中,“世界末日”到来之际、人类文明面临毁灭、唯有通过制造巨型轮船满载人类躲避这一灾难。为了凸显“末日”的破坏性、恐怖感,该片在视觉奇观上形塑了大量极具冲击感的奇幻意象,诸如太平洋海水喷涌吞噬美洲、亚洲、大洋洲等地的沿海城市,摩天高楼瞬间被海浪摧毁、跨海大桥剧烈摇晃然后迅速肢解、火山岩浆如泥石流般倾泻淹没山谷与公路。于是,人类所建造的现代文明空间被严重毁坏,随之出现的则是满目的废墟。而在劫难之后,该片又通过幸存者的对话,再次阐释了导致“末日灾难”的诱因:长期以来,人类不加节制地掠夺地球资源,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系统平衡。这就在打造视觉奇观意象的同时,也指涉了当前地球生态环境破坏这一现实问题的严重性。同样地,《阿凡达》中围绕奇异、富饶的潘多拉星球展开的资源争夺战争,也隐喻了人类在发展主义思维驱动下的扩张欲望,在潘多拉星球的河谷中、平原上、天空里所呈现的飞船与战机的惨烈争斗,既留下了科技与智慧剧烈碰撞后的震撼与余悸,也让转喻欲望与战争、失衡和毁灭的生存寓言被再次书写。
因此,该类影片普遍都围绕当下人类文明与地球自然生态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展开对于异质性空间的书写,在其运用各类影视特效构筑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的视觉奇幻意象的同时,又从生态整体主义的基点出发,对当下被生物学革命、科技迭代所遮蔽的生态破坏问题进行了揭露与思辨,形而下地传达出了颇具自省意味、寓言色彩以及警醒意识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使电影文本在创造全新的影像美学形态、给予观众观影快感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负载了应有的社会教育功能。
(二)“恶托邦”与“乌托邦”:异质性空间的两种存在样态
从欧美生态电影对于异质性空间书写的演进历程看,“恶托邦”与“乌托邦”可以视作是一对互为镜像的美学象喻,其在文本呈现中保持着相互独立、彼此映照的关系,渐次构成了舒展想象张力、投射人文色调的异质景观。其中“恶托邦”,抑或称之为“反面乌托邦”的这一异质性空间存在,往往被描述为所谓的“乌托邦”的对立面,即一种将现实社会进行“恶性”升级、“负面”扩大化的空间所在,携带着诸如“来自未来的、邪恶的幽暗之处”等的美学意味。比如《后天》《生化危机》等好莱坞生态灾难片,将“恶托邦”形而下地形塑为冰雪肆虐、火山遍地、病毒弥散的死寂空间,令现代工业文明被完全摧毁。在《后天》中,其基于由全球气候变暖所引发地球气候异变、冰河纪由此将重现地球这一描述建立叙事。随着海啸、地震、龙卷风等自然灾害难以遏制,现有的城市文明完全被摧毁、秩序也已然失控,人们不得不集体涌向美国与墨西哥边境躲避灾难寻求生存,由此导致情势更趋混乱、危急。于是,“恶托邦”就在该片中被具体形塑为了不适宜生存、抑或生存压力极大的有限空间,其既是对社会现实中由于生态危机加剧、干扰与压缩人类生活空间的一种再现,又通过夸张、象征等修辞,去凸显自然灾难对于人类文明的破坏性,并在几近毁灭的语境与情境中象喻着某种希望与生机。于是,在该片的结尾,人们基于赢得生存的共同目标,从而开始勠力同心、同舟共济,由此使抗争、重建、重生成为召唤人类发展潜能的动人话语。
二、现实讽喻和再批判:基于危情语境建构的“恶托邦”
(一)“权力”与“知识”:“恶托邦”的现实讽喻投射
在福柯对于“异托邦”的论述中,基于“权力”“知识”这一对符码所建构的话语机制,构成了异质性空间在文化认知、社会批判等面向上的现实主义内核。而基于福柯的话语理论,“权力”是一种生产性的力量,代表着彰显意志、维持既有利益与秩序、诉诸暴力的可能性,而“知识”,则是能够孕育个体与群体觉醒、抗争权力以及实现蜕变的力量。于是,在这一情境下形成的彼此区隔、分野、相互作用及其对抗的异质性形态,也渐次生成了一种颇具美学张力与省思意味的叙述脉络。也正是基于“权力”与“知识”这一话语设定,欧美生态电影中的“恶托邦”,普遍都在浅层审美上被形塑为死寂、荒芜、幽暗的反乌托邦空间,于深层上显影出对现实社会中的权力、知识之间的制衡关系的隐喻与反讽,突出表征即是凸显某种负面效应、人性阴暗面,使其投射出践踏契约、无视法治、僭越伦理等的“权力”的失控。而与之对应的,则是在由求生本能、能动意识等人类群体所特有的“知识”的驱动下涌动的觉醒与抗争等生命经验,如《雪国列车》中因阶级两极分化、资源争夺陷入白热化情势而最终由底层愤怒引发的暴乱,这种围绕“权力”与“知识”构建的叙述机制,以反讽与隐喻的修辞,批判性地展现了当今世界的生态现实,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投射出对由此所引发的各类社会现实问题的质询。
(二)隐喻与批判:“恶托邦”中的人性困境、社会危难
基于电影摄制与文学表达的互文关系,欧美生态电影对于“恶托邦”的书写,普遍强调以携带人文主义与现实主义叩问色彩、哲学思辨意味的表现手法,去剖析生态环境异化、人性之善恶转变、科技革命与社会发展等命题之间的勾连关系,从而借助隐性的投射、批判各类现实问题的方式,召唤人们体认、质询已然暴露的人性沉沦现象与社会危机。这就使隐喻表达与现实批判,渐次融入对“恶托邦”的影像呈现、叙述的内核之中。比如《极乐空间》就围绕地球生态趋近崩溃、能源危机全面到来这一情境,折射出未来的现实世界中可能会爆发的,由贫富加剧、善恶颠倒到阶层对立、两极分化的巨大的人性灾难与社会动乱。在该片中,富人与穷人被严格区隔为两类社群,前者居住在文明宜居的外太空空间站,后者则在疾患横行、灾难频发的地球上挣扎求生。而在地球上的“居民”奋力通往外太空空间站这一“极乐空间”的过程之中,象喻人性遭遇现实考问、阶层对立急剧升级、人类面临终极生存考验的批判图景也由此延展开来。而《逃出克隆岛》则通过展现克隆人摧毁海岛城堡内非法的器官试验场所,不愿再充当权贵阶层的牟利工具,最终完成从甘受奴役到奋起反抗的觉醒历程,写就了人性本真复归、重燃生存勇气、改变不公现实的史诗与神话。其既以隐喻的形式揭露了现实社会中由贫富差距扩大而引发的权力滥用、阶层矛盾激化等事实,又以不失理性的思辨批判了科技变革、生态异化以及人类生存前景等之间的制衡关系,使“恶托邦”成为投射人性伦理、现实社会的“他者之镜”。
三、精神重塑的诗化呈现:“乌托邦”的沉浸式想象
(一)“幻觉”与“补偿”:作为精神理想象喻的“乌托邦”
从福柯对异质性空间的论述中可以得见:“乌托邦”是“不真实的场所”,也是“完满的社会本身的投影抑或是社会的反面”,巨大的、无处不在的“幻觉”弥散其中,以满足人们对于理想化生活的情感寄托与思想投射。而这种作为异质性元素存在的“幻觉”,又具备随时消弭的可能性。所以,为了消解由“幻觉”灭失而出现的失落与空白,福柯又提出了所谓的“补偿性”概念:以一种自我想象去填补“幻觉”消失的主体缺位。于是,“幻觉性”与“补偿性”这一对并置符码,也就构成了福柯解构“乌托邦”这一异质性空间运作机制的两大支点。
(二)从科技自信到精神激励:“乌托邦”的奇观展示和社会价值
强调借助各类影视特效营造视觉奇观,显现西方世界科技的极度发达,是欧美生态电影对于“乌托邦”影像生成与呈现的重要形式、隐性话语。这种投射出鲜明的科技自信意识的表达,也成为该类影片建立诸如捍卫家园、追寻更为理想世界等叙事机制的精神激励来源之一,并升华为一种由个人美学舒展到群体感召的、具备史诗意味的社会图景。例如《逃出克隆岛》中以浮游海上的神秘岛屿为基体构筑的“乌托邦”空间,即是借助各类极具感官冲击力、震撼感与未来感的影视特效所打造的视觉奇观群落,其多角度展现了纯净唯美的自然景观、智能高效的生产生活样式。这一极具理想色彩的生存空间,又完全遵循着严格的现代工业逻辑与商业秩序进行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