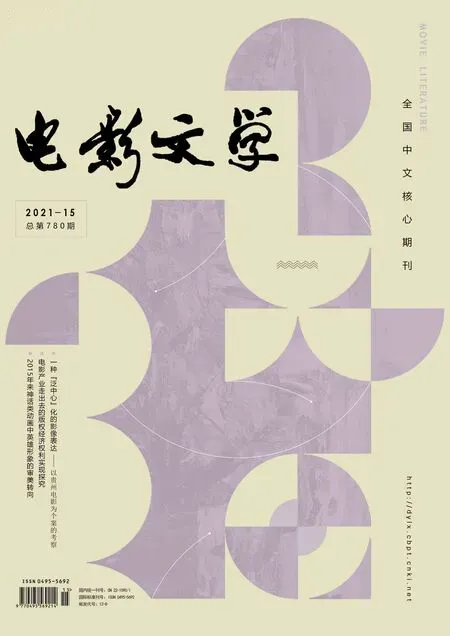论《第十一回》与陈建斌的主体性建构
李 鑫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重庆 401524)
在《一个勺子》之后,陈建斌又以表意丰富,舞台剧风格明显的《第十一回》给予了观众一次惊喜的“冒犯”,催动观众对生活中的虚与实,多变与荒诞进行思考。电影讲述的既是一部话剧一波三折的排演过程,一个多年前旧案真相的还原过程,实际也是马福礼等个体书写自身历史,完成主体性建构的过程,而导演本人的人文关怀意识也由此得到传递。
一、《第十一回》的内外主体性建构
主体性是哲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主体(subject)一词源自希腊语subjectum,后者本意为“处于底部的东西”。早年人类受限于认知水平,并不能从人本身来观察与评价周围的一切,自我与他者间的界限并不清晰。直至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启蒙运动蓬勃发展,人类掌握了理性这一武器,才开始确立主体性,从自我出发认识和改造世界。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就被认为是人意识到主观能动性的一种体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康德、黑格尔乃至马克思都在不断完善这一理论。如黑格尔认为,人在实现自由与解放时,其主体性才得到实现。而马克思则指出,主体性是“人在自身的对象性活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有意识地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对象化,并能够在客观对象中客观地标示自身掌握世界的实际能力的属性”。
电影正是人们介入主体性,建构主体性的一种方式。一方面,导演可以通过成为“作者”,在电影中张扬个体意志与个人风格,为电影赋予主体性,以使其区别于富有商业性的,消弭自我迎合大众的文化工业产物。在《第十一回》中,陈建斌正是如此。和其导演处女作《一个勺子》一样,陈建斌在创作活动中遵循的并非商业逻辑下的“传统语法”,并不以取悦观众为第一目的。早年曾出演先锋话剧,对于电影艺术有着自己独特思考的陈建斌在《第十一回》中进行了大量创造性的语言尝试:如采用章回体和“戏中戏”的方式,将电影、话剧和小说三种叙事媒介杂糅在一起,暗示着观众这是现实生活的三重镜像,而人们无法从中得知生活的全貌和真相;同时,现实生活本身又有着虚假、不可知、不自洽的一面,如邻居大爷并不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小马妈”,马福礼也不知道李建设和赵凤霞为什么在拖拉机下面会脱了裤子等,甚至观众到最后也不能知道马福礼的豆花究竟是淡了还是咸了。这些都是属于陈建斌的个人表达,电影与观众间的间离效果被人为地制造出来,观众的消费并不一定能换得轻松愉悦的观影感受。
另一方面,导演又可以在文本的创作中,安排电影中人去寻找和建构其主体性。在《第十一回》中,主人公马福礼早年身陷命案,度过了十五年的牢狱生活,人到中年靠开小吃店为生。他无疑属于社会地位低下,文化水平不高的边缘者。在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中,马福礼实际上是远离自由发展的,是没有表现出主体应具备的能动性、创造性和主导性的。而即使是地位要优越于他的人,如话剧团演员贾梅怡等,也生活在一种主体性缺失的境地中,事业与爱情都磕磕绊绊的她并没有实现精神层面上的解放。人们或是迷惑于自我身份,或是抗拒自我存在。而一部基于真实案件改编而成的话剧将马福礼与贾梅怡等人联系到了一起,人们在波折不断的生活中各自实现了成长。这正是电影最吸引人之处,也正是需要我们详加探讨的。
二、《第十一回》人物的多元主体认知与发展
在《第十一回》中,人物对主体性的寻回与建构,对“我”的认知与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角色身上。
(一)马福礼:“生”的反抗与“死”的超然
主人公马福礼是电影中人物弧光最为明显的一个。电影开始时,马福礼是没有自我的。如前面所提到的,白律师和屁哥对豆花的味道是咸是淡各执一词,而马福礼唯唯诺诺,人云亦云。这显然要表现的是马福礼缺乏个人见解,甚至不敢拥有个人见解。长期以来,他都活在别人的评价之中,依靠他人的意见来处理与自己利益交关之事。无论是白律师要他找回真相,还是屁哥劝他让死者安息,他的反应都是“你说得对,都按你说的办”。
然而马福礼最为清楚和坚持的,便是他并不是一个杀人犯。而他所能做的有限的反抗,便是试图改变话剧团的剧本。话剧团长以马福礼实际上有“马福礼A”和“马福礼B”的艺术加工论几乎打消了马福礼的翻案之心。不料随着继女金多多的怀孕,马福礼急切之下与妻子金财玲扮演起了一对怀上二胎的夫妻,以给金多多的孩子安排父母,此时马福礼的自我定位便是“小马爸”。而在金多多拒绝孩子的父亲是一个杀人犯的刺激下,马福礼才又执着地踏上了翻案之路。此时的马福礼,依然是一个在逆来顺受之上,稍作反抗之人,在“抓奸”失败后被贾梅怡斥责为“乌龟王八蛋”后,只能去街头喊叫发泄。
最终,站在血雨中的马福礼若有所思地面对台下空无一人的剧场时,他看清了当年拖拉机一事的真相,也才重新认识了自己,于是选择用开死亡证明,吊销户口的方式,杀死“马福礼A”,留下“马福礼B”做小马的爸爸,重新开启自己的人生。此时的马福礼尽管还是对妻子说“我们还过什么日子呢”之类的话,但实际上已经有了对自我身份的清晰定位和对人生的憧憬,不再是之前一个迷茫的、任何人都可以为他植入身份意识的马福礼。在这种主体意识下,他超然于之前的爱怨纠葛之上,达到了一种精神上的解放。
(二)贾梅怡:“赵凤霞B”与自我
贾梅怡的主体性建构则经历了一个从无我,到“赵凤霞B”,再到照见自我的过程。一开始,作为剧团新人的贾梅怡是一个“无我”者,对导演胡昆汀盲目崇拜,一如这一角色的谐音暗示的,她一开始是导演的工具。随后在排练中,她将自己内化为舞台上的赵凤霞。在《第十一回》中,贾梅怡是对《刹车杀人》最为认真的一个人。在排练时就反复追问:“我该如何演赵凤霞,我都不认识她”,想知道赵凤霞的真实声音,想了解她的心路历程,在胡昆汀与她躺在舞台上,胡昆汀只想着如何与她发生关系时,她依然替观众问胡昆汀:“在那个保守的时代,凤霞作为一个农村妇女,到底为什么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她老公就在拖拉机前面的驾驶室里的时候,跟另一个男人在拖拉机后面干那种事?”原本戏剧只是胡昆汀用以勾搭贾梅怡的一个载体,然而贾梅怡却在排练中逐渐看清了“我”的逻辑和情感,甚至一度为不满于赵凤霞的形象被修改而将气撒到了马福礼头上,用“你冒犯了我的自我”等斥责来维护自己的爱情。但此时她其实还是没有“自我”的。直到胡昆汀的真面目暴露,贾梅怡悄然离去,查清了拖拉机杀人事件的真相后,她才真正拥有了自我:她在舞台上代表自己而非赵凤霞对扮演李建设的胡昆汀说出不再见面的话,至此她不再为自己的炽烈欲望所遮蔽,在拯救自我的同时,也拯救了马福礼,以及过世的李赵二人。贾梅怡对主体性的建构,实际上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人对艺术和真理的纯真追求,这种追求是贯穿时代甚至引导时代的。
(三)金多多:身体权利的夺回
金多多这一条叙事线看似游离于拖拉机杀人事件之外,实际上她的经历对于马福礼的转变是至关重要的。金多多的成长体现在对自己身体的认识上。电影一开始,金多多在甚至需要偷钱堕胎,毫无经济实力的情况下怀孕,而她试图将孩子生下来以惩罚孩子已婚的父亲,为此不惜在医生面前以死相逼。正如福柯所指出的:“权力安置直接与身体、功能和生理过程挂钩。”此时她和她的父母尽管对堕胎的意见不同,但他们都从父权制出发对金多多的身体进行规训,金多多试图以生育来完成对对方的捆绑,这本身就是将自己物化与贬低的一种体现。同时,她与父母的对抗也隐然有着对自己私生女身份的维护。而在时间的推移中,金多多感受到了来自马福礼的爱,母亲生存的艰难以及孩子之父的无情和自私,她终于决定将孩子流掉,但在流产后,又给自己绑上了小枕头,暂且欺骗马福礼。在这段时间里,金多多认识了自己的身体,在审视自我时了解到了自己真正缺失的是什么,于是决定与过去挥手告别,以堕胎作为自己与男方断绝联系,掌控自我身体的第一步。电影始于马福礼夫妇开着车,金多多在车厢里被五花大绑,被父母送去堕胎,而在结尾时,则是金多多开着车,车厢里是畅想未来的马福礼夫妇,电影暗示着把握了方向盘的金多多也由此开启了对自主人生的追求。
三、《第十一回》主体性建构的现代启示
通过让电影中人逐渐看清自己的意志,完善自己的人格,《第十一回》以一种超越现实,鲜明张扬的影像风格,完成了对现实的关注。
一是电影主张了对弱势者话语权的归还。在马福礼力证自己不是杀人犯的故事中,观众看到的是社会边缘者的虚弱无力。在马福礼试图介入对《刹车杀人》一剧的修改之后,他实际上只有第一次对排练的叫停能够发声,之后的叫停者苟也武、屁哥和领导都各自从自己的利益而非从马福礼的利益出发来干预创作,而屁哥身为大款能够一掷20万让傅团长马上为金钱折腰,而领导则能够上纲上线让剧团所有人汗如雨下。马福礼的意见却是无关紧要的,死者李建设与赵凤霞也是小人物,赵凤霞的表姐也是小人物,李赵二人被扣上“狗男女”的帽子与否,案情的真相也同样是无关紧要的。在长期的失声中,弱势者为社会所忽略,失却自己的尊严。同样,女性也是社会的弱势者。赵凤霞和贾梅怡都被斥责为“搞破鞋”中的“破鞋”“骚货”,女性在两性关系中要付出比男性更为惨重的代价。而金财玲看似在家中有着高人一等的地位,她不仅掌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能够让马福礼“跪好”打马的脚,但在社会上,她依然是弱势的“他者”。为了给丈夫挽回声誉,在撒泼时只能借助自己的“孕妇”身份,以自己的生育价值来换取别人的退让三分。女性被以男性的标准来界定自身,长此以往,女性是难以有健全的人格的。
二是电影强调了建立一种和谐两性关系的必要性。在《第十一回》中,人们很难看到一种温馨美满的两性关系:李建设与赵凤霞是一对英年早逝,并且名誉被人肆意玷污的苦命鸳鸯;金财玲和金多多母女都未婚先孕,对那致使自己怀孕者心怀怨怼;胡昆汀游走于甄曼玉和贾梅怡之间,最终不得不净身出户,并遭到了甄曼玉带来的小伙儿们的殴打,在犹如丧家之犬之际,也遭到了贾梅怡的抛弃;即使是看起来最幸福,两人最愿意为彼此付出的一对,马福礼和金财玲,两人在婚姻中也并非时刻处于拥有尊严,精神自由的状态。当两性关系不和谐,人们无法与真正相爱者在一起,或是对亲密关系中的另一方持操控、欺骗态度时,人是无法获得健全人格和精神上的自足的。
应该说,陈建斌在《第十一回》中,对边缘者、弱势者的主体性乃至主体建构进行了一种积极的思考和探索,这在马福礼、贾梅怡和金多多等角色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拖拉机杀人事件的真相渐渐浮出水面之际,三人的自我认知愈发清晰,主观能动性得到增强,最终得到一个回目中所说的“花好月圆”的较为圆满的结局。而借助人物渐渐拥有自主权,渐渐看见自我价值的际遇,电影表达出了对弱势者话语权的关注和对两性和谐关系的倡导,这正是《第十一回》不可被忽视的人文价值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