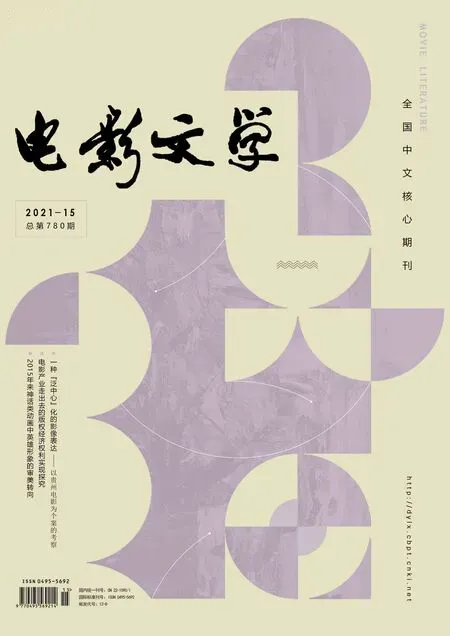类型美学视角下的《除暴》
左攀峰 (新乡学院人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0)
正如电影理论家道格拉斯·戈梅里指出的:“电影是一种利用画面、声音和故事进行价值生产的非传统商业。消费者为了一种愉快的体验付钱,没有一部影片能在经济语境之外创作。”类型电影的出现也正是经济语境下的产物,它以主动缝合电影生产机制与观众心理的方式,在消费时代中占据有利地位。而在国产类型电影中,犯罪类型片一直有一枝独秀之势,宁浩的《无人区》,刁亦男的《白日焰火》,曹保平的《烈日灼心》等无不凭借着对类型的美学自觉,对好莱坞成熟类型片范式的精准把握获得了公众普遍认可,完成了投资上“以小博大”的任务。由刘浩良执导,以张君案为原型的《除暴》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剖析国产犯罪片类型化特征的优秀范例。
一、合宜的题材选取
对于类型片而言,题材的选取直接关系观众的观影欲望。犯罪类型片无疑应当选择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反映社会意识的犯罪题材,而电影人往往又从现实生活出发,以真实案例为创作基础。一方面,新闻事件本身的知名度能得到有效利用,电影人将新闻的真实性和电影故事必备的假定性进行缝合后,就能形成二次传播,宣传效应得到叠加。这方面较具代表性的是由丁晟执导,根据吴若甫绑架案拍摄的《解救吾先生》,以及杂糅了季炳雄、叶继欢和张子强——香港“三大贼王”故事,由许学文、欧文杰、黄伟杰联合执导的《树大招风》。另一方面,选择与观众有一定利益相关的案件,能揭示出社会的弊病,形成一种对社会议题的集体讨论,最终满足观众的认知渴求和情感宣泄。如奉俊昊执导的《杀人回忆》和李俊益的《素媛》等,二者取材于在韩国无人不知的华城连环杀人案与素媛案。作为无法涉足刑侦领域的观众,他们对电影的消费,实际上也是一种对“破案体验”的消费。
《除暴》的题材源自有“中国第一悍匪”之称的张君及其犯罪团伙,在20世纪90年代制造的一系列抢劫杀人案。张君及其同伙曾经在十年里流窜于全国各地,非法购买枪支上百支,子弹不计其数,甚至还有手榴弹等,其犯罪导致50余人死伤,其中不乏警察,他们所抢劫的财物金额高达600余万人民币。其作恶时间之长,对社会危害之深重,是骇人听闻的。刘浩良敏感地捕捉到了张君案被改编为类型片的可行性:一则,具有一定知名度,尽管已过去几十年,但它与白宝山案、白银连环杀人案等,常年在各社交平台上为人们津津乐道,这保证了电影受众基础;二则,本身就具备犯罪类型片的叙事动力和改编空间。尽管张君的结局观众早已知晓,但这并不意味着影片全无悬念。张君等人手段残忍,丧心病狂,为满足私欲而滥杀无辜,并且逍遥法外时间较长,与警方长期较量,双方的二元矛盾关系是无可调和的,这就给予了编剧架设内容翔实,气氛紧张,富有不确定因素和戏剧性内容的创作空间。而尽管部分观众已从新闻或报告文学中了解过张君其人,但对其具体的个性,乃至何以长时间吸引一众同伙、情妇的“魅力”依然有着好奇心,电影可以提供一个更为鲜活和近距离的视角,让观众知晓其犯罪动机与过程。于是在刘浩良的设计下,《除暴》中的猖獗悍匪名为张隼,绰号老鹰,他所带领的犯罪团伙则叫“老鹰帮”。这伙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熟悉各类枪械和刑侦知识,其犯罪则以抢劫为主,取材于张君团伙犯下的湖南常德运钞车抢劫案、长沙东塘友谊商城黄金抢劫案等发生于闹市,能引发观众恐慌心理的真实案件。
而为了让电影叙事更贴近类型范式,实现效果的最优化,刘浩良还要对原型事件与人物进行一系列改造,而这种改造的依据,便是审美愉悦导向。
二、审美愉悦导向的叙事设计
在商业语境下,观众对电影的消费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审美愉悦的购买。带给观众充分的娱乐感与情感认同,成为电影这一文化产品的核心生命力。人们普遍认为,构思精巧、情节一波三折、拥有适宜节奏的叙事,是类型片必不可少的,而犯罪类型片更是需要与慢节奏、安稳而平淡乏味的现实生活保持距离,在短时间内迸发尖锐异常的冲突,才能让观众进入到惊心动魄的情境中,收获审美愉悦。如在刁亦男的《南方车站的聚会》中,小混混们因地盘分配矛盾而大打出手,随即又开始了一场闹出人命的飞车比赛,主人公周泽农迅速成为警方的通缉对象,让观众悬心不已;忻钰坤的《心迷宫》中,村里突然出现了一具身份难辨的焦尸,而少女黄欢又下落不明,当村民误以为死者就是黄欢时,观众明知黄欢依然活着,但也并不知道死者究竟是谁,由此便获得了一种信息差和好奇心带来的审美愉悦。
一般来说,在叙事上,犯罪类型片必须对真实案件侦破的冗长复杂过程进行精简与压缩,并且有必要遵从由兹维坦·托多洛夫最先提出的法则:“保持平衡/守护秩序——打破平衡/破坏秩序——重建平衡/回归秩序。”在《除暴》中,冲突爆发的时间,其激烈程度则被大大提前了。电影开始于一个满地狼藉的金店,随着一句“把他铐上”,正邪双方出现在观众面前。原来被铐上的对象竟不是匪徒,而是警察钟诚。被当成人质的钟诚在此居于绝对弱势。而随着钟诚被张隼丢到警察面前,电影才以回溯的方式,介绍了平衡被打破之前的情形:钟诚第一天来到常普市上任,而大街小巷,金店内外此时也一切正常,钟诚还与前来接他的警察一起撕掉了宣传画上的小广告。在钟诚讲清身份后,他回归到较为平静、安全的生活状态中,张隼一伙人则为下一次抢劫开始了计划制订和相关训练,平衡暂时得到了表面上的恢复。很快,新的劫案又爆发,平衡和秩序又被大肆破坏。而假张隼的落网,让警匪之争暂告一段落,局势又短暂恢复平静,直到钟诚锲而不舍地追到真张隼,并让其受到法律的制裁,平衡与秩序才得到了彻底的修复和重建。警方对匪徒咬死不放,而匪徒则愈发狗急跳墙,释放出强大的破坏力。在这样的叙事线中,情节一环扣一环,而冲突则一浪高过一浪,观众一直被剧情吸引,获得一种现实生活中难以得到的紧张刺激的体认和感受。
除此之外,电影中加入的张隼与杨文娟的爱情故事,也是一种审美愉悦导向下的设计。一方面,张隼的私人生活进入观众的视野,这一个反派的形象在癫狂、冷血之外又有了风流多情,孝顺母亲的一面,显得更加立体,一直快节奏的、充满血雨腥风的叙事舒缓下来,观众的窥探欲望得到了充分满足。另一方面,这也铺垫了假张隼被捕,真张隼逃之夭夭的情节。当观众看到杨文娟因为张隼提出分手而哭着剪两人的照片时,只误以为是她的伤心之举,而直到假张隼的李代桃僵,电影才交代了原来与杨文娟拍结婚照的是张隼的小弟陈骁,张隼在电话中说的“你跟上次见过的那个男人在一起”是一句暗语,杨文娟在警方的监视之下剪碎照片的行为实际上是对张隼真面貌的一种保护。这种叙事上的反转,既符合了原型中,张君以名为“龙海力”的假身份证与杨明燕结婚的情况,也满足了观众的期待视野。
三、充分的类型符号加入
类型电影中,类型符号是不可或缺的。犯罪类型片中,残暴、血腥元素如尸体、武器,乃至飞车、爆破、混战等场景,都是能承载叙事功能,为观众宣泄情绪的类型符号。不得不承认的是,残暴、血腥元素在犯罪类型片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带给人极大感官刺激的残暴、血腥元素正能配合犯罪片悬疑的剧情节奏,这恰如一套吸睛的组合拳,牢牢击中了消费时代中追求心跳的心理,以此来保障影片票房。”它们不仅能给观众带来视听上的震撼,也紧密关联于为观众带来智力挑战的悬疑叙事,隐藏了与犯罪者相关的重要信息。
在《除暴》中,这些元素被密集地加入,不断冲击观众视觉,释放观众的情绪,同时也让观众在道德上对为除暴安良付出惨重代价的公安干警肃然起敬。如凶残至极的张隼常常对被害人说:“讲个笑话,好笑的话,留你一命。”但话音刚落就开枪杀死对方,让观众看得头皮发麻。又如警匪多次在闹市区展开激烈枪战,匪徒沙皮在与钟诚的对峙中从天台摔下后,张隼一行人竟对其投掷手榴弹以灭口,随后在武江乐亚宾馆的枪战中,他们则将多名警察从楼上扔下以示报复。在抢劫运钞车及金店时,张隼不仅毫不留情地以手枪射击无辜群众,还沿街大肆抛掷手榴弹,警察屈光华正是为了抢夺匪徒手中的手榴弹而被炸断了右手。在飞车追逐中,更是充斥着玻璃崩裂、血迹四溅、自行车被碾碎等场景。
在电影的开头与结尾,刘浩良更是设计了两场钟诚与张隼一对一的有呼应意味的短兵相接。在开始,被匪徒劫入车中的钟诚在双手被缚,被枪指头的绝境之下,依然奋起咬掉了张隼耳朵上的一块肉。而结尾则是钟张二人在地面湿滑、水汽弥漫的澡堂之中的决斗,两人无法使用手枪等武器,只能挥拳肉搏,电影以此营造出了一种迥异于之前两人及手下利用各种掩体展开枪战的情境,在封闭的澡堂空间中,浴池里的水、地面的排水口等,都是两个人的武器,正与邪之间的较量方式更为多元,观众的神经又一次被挑动。
而有必要提及的是,使用已给观众留下某种固定印象的演员,也是类型片生产范式的一部分,这能够极为高效地将观众引导进认同机制之中。如扮演钟诚的王千源在《解救吾先生》中成功扮演悍匪张华,而扮演张隼的吴彦祖则也在《新警察故事》中出演玩世不恭,直言“恨透了你们这帮当警察的”的匪徒,二者都在观众心目中有着彪悍、强壮、破坏力强的硬汉印象。在《除暴》中,两人是叙事主体,也是残暴、血腥元素的制造者。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作为犯罪类型片的主要目标受众的男性观众,长期以来实际上一直拥有着一种自身被“雌化”或被“阉割”的恐惧,尤其是在当下的男性荷尔蒙被普遍认为存在社会性匮乏,传统的“男性气概”被认为渐渐失却的情况下。而电影中交手双方的硬汉形象,则能充分对这种恐惧进行慰藉。男性观众原本是“不在场”者,但是作为凝视主体,他们以观看的方式实现了某种“在场”,以与主人公共情的方式完成了对自己焦虑的想象性解除,无论是在作为反派的张隼从事种种暴力犯罪,抑或是作为正派的钟诚等人大显身手上,乃至在看到杨文娟对张隼的柔情与依附时,男性观众都能从其中感到自己主宰地位与统治力量的巩固。当然,随着新时代女性的自主意识与竞争力日益加强,对男性活动领域的充分进入,旧有的社会性别规范被动摇,犯罪类型片也会对此进行迎合。
当下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方兴未艾,国产商业电影的创作需要考虑类型化的规范,这已经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国产犯罪片对此表现出了可圈可点的美学自觉。以《除暴》来说,电影在题材选择,叙事设计以及类型元素的加入乃至营销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明确的类型美学意识。自始至终,观众的审美期待从未落空,其类型观影审美愉悦基本得到了满足。应该说,在国产商业电影一直努力践行类型美学,类型批评也呼唤着可资剖析的鲜活、典型样本的今天,犯罪类型片交出了《除暴》这样的合格答卷,是十分可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