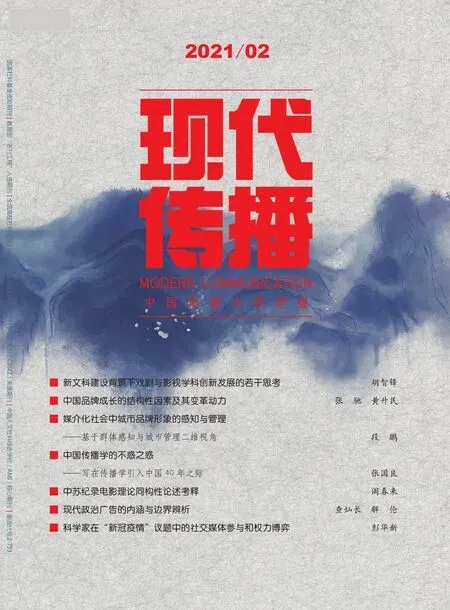榜样的力量何以无穷?
——以雷锋形象变迁为中心的考察
■ 俞 凡 王妍慧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而榜样之所以会有力量,是因为它能诉诸于接受者观察学习的过程。“学习并不仅仅发生在经典条件反射和操作条件反射中,我们也能通过看、读或听说别人怎样行为来学习。”①通过对他人的观察、模仿,我们同样可以体会其中所蕴含的精神品质和价值观,进而内化为自身的行动准则,这就是“言传”与“身教”的意义。
通过塑造榜样形象团结和教育民众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新中国建立后,掌握了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尽快建立起自己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完成对全体国民(至少是绝大多数)的“征召”(recruit)与“改造”(transform)的过程②,于是榜样教育受到了空前的重视,而现代大众传媒成了塑造与传播榜样形象的主力。从20世纪50年代(后文“20世纪”不再注明)起,新中国的媒体塑造并传播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大量榜样形象,他们的事迹和精神,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为建设祖国奉献自己的力量。
雷锋是新中国早期塑造的榜样形象中非常特殊的一个。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许多与他同时代的榜样形象已逐渐模糊,只有雷锋始终熠熠生辉。与他同时代的榜样中仍令当代人耳熟能详的,只有王进喜、焦裕禄等寥寥几人。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赋予了雷锋这种超越时代的魅力呢?
雷锋牺牲至今已近60年,绝大多数当代中国人对他和他所处的时代没有切身感受,我们对他的体认主要来自两个渠道:一是他人的描述即人际传播,二是传媒的塑造即大众传播。两种渠道的叙述为我们共同塑造了一个“可以追溯的过去”,使我们可以“在一个与过去的事件和事物有因果关系的脉络中体验现在的世界”③。同时,这两种渠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首先,大众传媒的作用显然要强于人际传播,许多直接的生活体认就是通过大众传媒才得以广泛传播;其次,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又影响着大众传媒对雷锋形象的塑造与解读,一个已经逝去的形象,如果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社会需求,也会被社会遗忘。所以,大众传媒必须根据社会需求和价值观的变化,对雷锋形象做出与时俱进的解读。因此,在考察前面我们提出的问题时,大众传媒的作用便显得尤为重要。
大众传媒对雷锋形象塑造一直是学者关注的话题之一。吴海刚④、袁光锋⑤、陶东风⑥都认为雷锋之所以成为榜样是由于特殊年代的政治需要,而几十年间这一形象经历了一个逐渐剥离政治性和阶级性的“去革命化”的过程,当下的雷锋已经从一个政治符号转变为道德榜样,吴海刚认为雷锋作为政治符号的力量随时可以复苏起来,而袁光锋、陶东风则认为雷锋形象的变化说明公民政治、公民道德与法律契约精神才是社会发展的方向。陈阳认为1963—2003年间《人民日报》对雷锋的报道可以被纳入“毛主席的好战士”等五个意识形态之中,而“无论媒介框架如何转变,都可以看成是党报的宣传任务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变化而发生的转变”⑦。海外学者方面,Reed认为后革命时代的中国人实际上是从雷锋身上学到了传统的儒家美德,同时也根据自己的信仰来建构对于道德榜样的印象,作为同时具备儒家传统美德和共产主义理想的道德榜样,雷锋仍将长期在中国儿童的社会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⑧程映虹认为雷锋是60年代解放军塑造的一系列道德榜样中最重要的一个,相对于之前的榜样,他体现出了对毛泽东的崇拜、通过自我批评与反省达到持续自觉的思想改造以及将忍受艰难困苦作为磨砺革命意志的方式等三个特征。⑨
前述研究具有相当的价值,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谈到了雷锋精神的普适化问题,并认为这是雷锋形象经久不衰的原因,但这却无法解释为何类似的形象无法延续的问题;此外,许多研究者关注到了不同时期媒体因应时代需要对雷锋形象的不同解读,却都有些大而化之;最后,研究者普遍关注了雷锋形象背后负载的政治含义,却大多对此浅尝辄止。有鉴于此,我们选择了60年代以来《人民日报》与《解放军报》(以下简称“两报”)上有关雷锋的报道作为分析对象,结合不同时期中国政治文化环境的变化,试图回答这样三个问题:第一,雷锋为什么能在60年代成为全民榜样?第二,雷锋形象经历了怎样的变迁?这种变迁说明了什么问题?第三,雷锋形象经久不衰的原因究竟何在?
一、雷锋何以成为榜样?
雷锋出身贫苦,解放后接受教育,1960年1月入伍,同年11月入党。由于在各项工作中表现优异且多次捐款支援灾区,雷锋成为所属部队的知名模范。1960年11月26日,沈阳军区《前进报》发表了《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12月又发表雷锋署名文章;26日,《解放军报》发表关于雷峰的通讯并配编者按《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开始具有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1961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苦孩子成长为优秀人民战士》,雷锋形象开始踏出军营,成为面向全民传播的榜样。
雷锋能够成为榜样,与其成长经历有关:新中国要建立的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证明新制度的优越性是媒体的一项重要工作,检视建国之初的报刊,“苦孩子”形象比比皆是,而雷锋的成长经历完美地契合了这一点,比如《人民日报》这样描写解放之初的雷锋:
雷锋带着满身脓疮,从深山里走出来。人民政府的乡长彭德茂拉着他的小手,送他到县人民医院去治病。……他一下扑到彭德茂的身上,叫唤着:“救命恩人呵!”彭德茂抚摸着他的头说:“小雷,我们的救命恩人是毛主席,是共产党,是解放军。现在,你可以为你的父母兄弟报仇了!”⑩
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之下,新制度的优越性不言自明,而这也成了当时的报刊用以激励人们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的主要号召,正如《解放军报》的编者按中所言:
新旧社会鲜明对比之下,正如雷锋所说:没有党和毛主席领导革命,哪能有今天?因此,我们也同雷锋一样,衷心感谢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决心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保卫伟大的祖国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幼年的成长经历和工作中的优异表现,是雷锋最初被发掘、塑造的主要原因。但如果仅停留在这种惯常的“旧社会受苦受难,新社会翻身做主,为革命努力工作”的叙事模式中,雷锋很难成为经久不衰的道德榜样,这一符号的形成,有着更重要的原因。
二、学雷锋宣传的第一次高潮及雷锋原生形象的形成
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殉职,这成了宣传雷锋精神的又一契机。17日,沈阳部队机关发出了向雷锋学习,争当毛主席的好战士的号召;24日,《解放军报》在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9月7日,又发表雷锋日记摘抄10则,同时配发雷锋战友曾光彩的回忆文章;11月1日,《解放军报》报道了雷锋生前部队展出其遗物的消息。《人民日报》也随即跟进:1963年1月21日,国防部授予雷锋生前所在班“雷锋班”称号,《人民日报》在25日报道了这一新闻;2月7日,又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辽宁省团委和军区组织的雷锋事迹展览、巡回报告团以及全省青年学习雷锋的活动,并用第2版几乎整版发表长篇通讯《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及宋任穷(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沈阳军区第一政委)、罗瑞卿(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的题词,配发评论《伟大的普通一兵》,还将第5版办成了雷锋专版,发表《雷锋日记摘抄》34则及5幅照片;15日,共青团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国青少年中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教育活动的通知》,学雷锋运动开始在全国上下开展起来。
2月,《中国青年》准备出一辑学雷锋专辑,请毛主席题词;22日,毛泽东亲笔书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交给杂志社;3月2日,《中国青年》第5—6期合刊发表了题词的手迹;5日,全国报纸都转载了该题词,学雷锋活动就此被推向最高潮。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领袖,毛泽东在当时的领导人中具有独特地位,他的亲笔题词自然是雷锋得以成为独特的道德榜样的一大原因,但得到毛题词的并非仅雷锋一人,为什么是雷锋成为了这样独特的道德榜样?毛给雷锋的题词有何特别之处呢?
《毛泽东年谱》共记录毛为个人题词33次,其中广为人知的,除了“向雷锋同志学习”之外,就只有给白求恩(“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和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两条了,相较于白求恩28个字的题词,7个字的“向雷锋同志学习”更利于传播;而相较于战争年代的刘胡兰,雷锋是一个更适合在和平建设时期传播的榜样。更重要的是,从语法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省略主宾的祈使句,被省略的主语使它具有了无限的适应性,被省略的宾语使它具有了无限的可能性,“雷锋同志”还赋予了它明确的指向性。总之,这句话可以被理解为“任何人可以向雷锋同志学习任何品质”,由此它便可以被无限解读,这也是雷锋形象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题词的发表,对雷锋的第一个宣传高潮也随之而来。在1960—1976年间,“两报”对雷锋形象的描绘,应当是最接近其原生形象的。通过对相关报道的关键词的梳理,我们发现,这段时间雷锋的形象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
1960—1962年是第一阶段。这段时间“两报”报道雷锋的关键词主要有忠于党和人民、忠于毛主席、旧社会受苦受难、助人为乐、艰苦朴素、刻苦学习等。总的来说,这一时期雷锋形象基本是一个典型的旧社会的苦孩子、新社会的好战士。
1962—1965年是第二阶段。随着雷锋日记的大量发表,他又被赋予了爱憎分明这一新特点,而“憎”的对象被明确界定为“旧社会”“阶级敌人”和“美帝国主义”,如《解放军报》首次发表的雷锋日记摘抄中便选了如下记录:
现在美帝国主义,又支持蒋该死(介石)准备窜犯大陆,我要用自己胸膛的鲜血,象黄继光一样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
这一变化体现出新中国榜样塑造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政治需要对榜样形象的影响,1962—1963年是中苏关系破裂的关键时期,双方矛盾的焦点之一便是对国际局势的看法,苏联坚持莫斯科宣言中的“和平过渡”方针,中方则坚持自己“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经验,在这一时期的宣传中强调雷锋痛恨阶级敌人和美帝国主义,随时准备“将革命进行到底”,正是这种政治需要的直接反映。
1966—1976年是第三阶段。这一时期“两报”上的雷锋一方面大体延续了之前的形象,一方面又将其优秀品质集中于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爱憎分明等,淡化了助人为乐、做好事等形象,并且着力强调雷锋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号召大家要像他一样“毛主席怎么说就怎么做”“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显然是这一时期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的影响所致。
三、新的政治环境下雷锋形象的变化
1976年10月,新中国的历史翻开新的一页,“两报”上的雷锋形象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1977—1989年间,“两报”对雷锋报道的最高峰是1977年,《人民日报》当年对雷锋的报道量是历年排名中的第三,甚至超过了1963年的数量;《解放军报》的数量则是历年排名中的第四,这一现象值得思考。1977年是新中国历史上风云激荡的一年。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华国锋成为新一代领导人;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逮捕了“四人帮”。“抓捕‘四人帮’之后,海外即有华搞‘非毛化’的舆论,国内也有华搞‘右派政变’‘宫廷政变’、为邓小平‘翻案’的流言。”所以,反击流言争取舆论成了当务之急。这一点上,作为曾经被毛题词的榜样人物,雷锋在赋予新领导人合法性问题上具有独特的作用。这一时期“两报”上的雷锋虽基本延续了之前爱憎分明的“毛主席的好战士”形象,但其形象落脚点已经变成了揭批“四人帮”、坚持毛主席路线的代表,如《解放军报》在1977年1月4日为一篇雷锋生前所在团揭批“四人帮”的报道所加的编者按中讲到:
毛主席关于“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永远鼓舞着我们,……我们要更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发扬雷锋同志的革命精神,深揭狠批“四人帮”,……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以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对雷锋的宣传在3月5日达到高潮。当天的“两报”头版并排发表了毛泽东与华国锋为雷锋题词的手迹,其政治意味不言自明。“两报一刊”社论更提出号召:
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响应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从某种意义上说,雷锋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充当了连接毛和华两个时代的纽带,也成为了华“沿着毛主席开创的革命道路继续前进”的重要标志。而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雷锋的形象也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立即着手工农业生产的整顿和恢复,并重新发出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号召”。在这种形势下,中央开始重新强调岗位责任制,这恰恰是“四人帮”坚决反对的,于是,雷锋又成了与“四人帮”进行思想斗争、捍卫岗位责任制、“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武器:1977年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雷锋生前所在部队学雷锋的报道,表示要“遵照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大打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抓革命,促生产”。4月11日关于整顿交通运输问题的短评中号召要“学习雷锋同志那种‘迎着困难前进’的大无畏精神……就能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和造成的损失尽快地夺回来”。而7月21日通过的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则正式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的群众运动”。
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正式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此后,政治话语在国家和人民日常生活中开始逐渐退场。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为当务之急。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的讲话中,正式提出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归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十个要点之一。所以,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成为了当时报刊的一项中心工作,而雷锋助人为乐、艰苦朴素的形象特点很好地契合了这一需要。1980年起,“两报”上的雷锋形象开始紧密地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联系在一起。1980年4月21日《解放军报》发表的《“兴资灭无”是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任务》是雷锋与精神文明建设相联系的开山之作,《人民日报》5月8日发表的华国锋讲话也强调要通过提倡学雷锋来对青年干部战士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以“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大规模的宣传从1981年开始,从1月1日《解放军报》的《发扬革命传统,建设精神文明》到12月31日《人民日报》报道广州警备区某团积极学雷锋做好事的事迹为止,贯穿全年。这一时期的报道多是关于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各地涌现出的学雷锋做好事的先进事迹,与之前同类报道相比,以往口号式的话语逐渐退场,政治性的意味大大减弱,就事论事的态度愈发鲜明,这也是80年代“两报”关于雷锋报道的一大突出特点。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迅速提高,这就给传统的雷锋形象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即重新解释雷锋精神与经济收入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讲工资、要奖金等被视为个人主义甚至是资本主义的观念一直遭到批判,而雷锋则是批判这种思想的重要理论武器。1963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著名劳模赵梦桃学雷锋的体会,认为一个工人劳动的好坏,绝不能“完全受工资多少支配”,而应该像雷锋那样,“拿出做主人的态度来劳动”。此后的报道和评论一直延续了这样的态度,即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没有改变。
社会的发展使得二者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两报”必须有所回应。1981年3月5日,《人民日报》转载《中国青年报》社论《再论雷锋》指出,“提倡学雷锋绝不是要否定合理的个人利益,更不是要大家去做苦行僧”,而是“要倡导先公后私和公而忘私的精神”。这表明那时的“两报”已经在这一问题上有所松动,不再一味地排斥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而是号召人们在合理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首先考虑为社会奉献。这也是此后几年里“两报”在这一问题上秉承的态度:1983年3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新时期与雷锋精神》写道“我们今天面临的具体任务与雷锋所处的年代不同了。我们学习、发扬雷锋精神,不能机械地套用过去雷锋的某些做法”;《解放军报》也在1985年7月29日的一篇采访记中借全国学雷锋标兵朱伯儒之口表示“我们讲实惠,应该首先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然后才是个人的实惠”。
但是,这种做法只是回避了问题,社会终究需要“两报”对雷锋精神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作出明确的解释,否则雷锋形象很难适应新的时代需求,那些年不断出现的所谓“雷锋过时论”便是明证。1988年2月28日,旅大警备区学雷锋标兵徐少林获得了2000元奖金,激起了全社会对拿奖金与学雷锋之间关系的讨论,这成了新时代“两报”雷锋形象建构的一个重要转折点。3月2日,《解放军报》在头版以《学雷锋拿奖金同样光荣》为题报道了此事,并配发编者按云:
当标兵和拿奖金并不是对立的。重视物质利益是政治工作的一个根本原则。我们强调思想教育,丝毫不忽视排斥物质利益,而是引导干部战士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同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关系。不能把干部战士追求正当的个人利益和致富意识看作是“个人主义”“一切向钱看”。
这是笔者所见“两报”首次表示“学雷锋”和“拿奖金”并不矛盾的态度,第二天,该报又报道曾经的学雷锋先进单位某部八连在地方开展有偿劳务的消息,并借该连指导员之口表示“在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搞劳务和学雷锋并不矛盾,关键是要处理好有偿劳务与无私奉献的关系”。这种认识在当时很难被社会所普遍接受,很快,《解放军报》又在5月12日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对此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这样一来,“学雷锋的意义、性质就变了,无形中降低或改变了‘学雷锋标兵’这个荣誉称号的标准”。此后该报又发表多篇读者来信讨论这一问题,总体上,支持与反对的意见大体相当,无论如何,改变的种子已悄然埋下。
四、90年代以来与时俱进的雷锋形象
1990—2019年间,“两报”上的雷锋报道从数量上呈现一种逐渐稳定的趋势。除1990年的突然增高以外,“两报”关于雷锋的报道数量的变化基本处于一个正常的范围,几次高峰期分别对应“题词”发表30、40、50周年和雷锋牺牲50周年纪念,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从具体形象来看,进入90年代后,面对着新的时代环境,雷锋形象急需进行一个再解读、再建构的过程,以使其重新具有时代感。故在90年代初,“两报”上的雷锋形象经历了两个重要转变。首先是对市场经济与雷锋精神关系的再解读。如前所述,虽然“两报”并没有对“学雷锋”与“拿奖金”之间的争议下定论,但社会发展的大势却不可逆转。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主席在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中国社会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的又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与之相伴随,在90年代初,学雷锋标兵拿奖金的报道开始增多。1991年6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马鞍山市向包括“学雷锋、送温暖”活动先进个人的“十佳人物”颁发“一定数额的奖金”的报道;《解放军报》也在1993年3月10日报道了战士汤志军被评为“见义勇为好公民”并获1万元奖金的事情。此后,同类报道渐趋常态化,这标志着雷锋形象完成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学雷锋”终于搭上了市场经济的快车。
其次是对雷锋传统形象的再解读。1990年1月9日,团中央发出通知,号召全国青年学习雷锋“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的政治立场”“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文化科技知识的钉子精神”“助人为乐、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要求,为祖国艰苦奋斗的思想境界”和“热爱本职岗位,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螺丝钉精神”,这五条标准便是党中央在新时期对雷锋精神的阐释和概括。虽然它们与传统的雷锋精神并无不同,但在具体的解读上,这一时期的“两报”却体现出了与之前不同的特征,具体来说就是“三变两不变”:
“两不变”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以及艰苦朴素的作风,尤其前者始终是“两报”在塑造雷锋形象时保持不变的首要特征。1993年3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雷锋精神首先在于“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热忱”;2018年3月5日《解放军报》社论也把“爱党爱国的坚定信念”放在雷锋精神的第一位。“三变”首先是对刻苦学习的解读。在此前的雷锋形象中,“刻苦学习”总是与“毛主席著作”“马列主义”等密切联系在一起,90年代以来“刻苦学习”开始普遍地与“学科学”“学文化”联系。其次是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解读,即帮助群众脱贫致富也是学雷锋的重要表现。1985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八名大学生自愿组成“济困扶贫”小组,帮助江西吉安贫困农民脱贫致富,被江西省团委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的消息,这是“两报”首次出现此类报道,也是1990年前的唯一一例;90年代以来,“两报”上此类报道开始大量出现,《解放军报》更在社论中明确指出:“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同雷锋生活的年代已有很大不同,学习雷锋,无论是在方式、内容和要求上都要有所发展。比如军民共建精神文明,帮助群众脱贫致富,在支援国家经济建设中贡献技术、智慧和才能等,都应努力去做。”最后则是对“干一行、爱一行”的解读。这一概念最初是在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学习雷锋》一文中提出的,本意是号召青年们要学习雷锋“反反复复地读毛主席的书,老老实实地听毛主席的话,时时刻刻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一心一意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而90年代的宣传,则号召大家“把学雷锋和个人的岗位工作结合起来,在本职工作中体现雷锋精神,出色地完成任务,用自己的行动为人民服务”,60年代强调个人绝对服从组织安排的意涵在90年代几乎看不到了。
这种转变同样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要发展经济,首先就要改变旧的经济体制,要改变国家包揽一切的制度,充分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尊重科学、重视教育,增强全民族的创新能力;还要鼓励人民敢于致富,勇于致富。这种改革不是要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绝不能有丝毫动摇;同时,发展经济,鼓励致富,并不等于在社会上倡导奢靡之风,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也不能丢。所以,90年代“两报”上的雷锋形象,正是在新形势下对雷锋精神做出的符合时代需要的新的解读。
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国家从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的现代性转型中会经历一个驱除巫术、魔法和神秘性,驱除“克力斯玛”的神秘光环,由魅力型统治向法理型统治转变的所谓“世界的祛魅”(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的过程。“两报”上雷锋形象在80—90年代的转型,首先便经历了这样一个“祛魅”的阶段。传统的雷锋形象诞生于60年代初,其原生形象的核心符号——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爱憎分明、立场坚定等,无不带有革命时代的鲜明印记,而其他的一些符号如艰苦朴素、助人为乐、刻苦学习等也都服从于这些核心概念。在这样的叙事模式下,雷锋被塑造成了一个完美无缺的革命化的榜样,这也是那个时代追求“高大全”的通常做法。当改革开放的大门开启,市场经济的大潮袭来,“革命”已经逐渐成为遥远的回忆之时,雷锋这一形象便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雷锋似乎已不再适应这个时代,且在事实上被不断边缘化,80年代初逐渐兴起的“雷锋过时论”也证明了这一点。伴随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贪污腐败、个人至上、拜金主义等新的社会问题出现,人们又开始普遍怀念革命年代的纯真与美好,从而重新意识到雷锋形象中的某些符号——艰苦朴素、助人为乐、爱岗敬业等的时代价值。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指导思想并未发生变化,雷锋形象的核心符号——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恰与其高度契合。于是,雷锋便又经历了一个“复魅”(enchantment)的过程——在保留了核心符号并对其他符号做了时代化的新解读之后,雷锋重新成为新时代的榜样。
总之,90年代以来,雷锋形象经历了一个“去革命化”的过程——他依然爱党爱国,从无改变;他依然艰苦朴素,但已不排斥适当的改善生活条件;他依然满怀斗志,但已不再是针对阶级敌人,而是要在经济建设中贡献力量;他依然刻苦学习,但已不再仅限于学习政治理论,而更要学好科学文化知识;他依然乐于助人,但已不仅限于帮大嫂买车票,而要承担起带领群众一起致富的责任;他依然爱岗敬业,但已不只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而更要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他已经可以靠劳动致富,拿大笔奖金,从一个“高大全”的革命者变成了商品经济时代的好公民。这一转变不仅使雷锋形象在新时代重新展现出其道德魅力,更使他获得了几乎永远的生命力。正因如此,进入21世纪,“两报”上的雷锋形象开始呈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态势,从“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再到“八荣八耻”“中国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历次党中央最新决策的宣传中,都能找到学雷锋精神、学雷锋活动的身影。
2018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抚顺雷锋纪念馆,《人民日报》在评论中指出,新时代雷锋精神是“信念的能量、大爱的胸怀、忘我的精神、进取的锐气”“是奉献精神”“是不受年代、环境、背景等条件制约的”。这是党的新一代领导核心在雷锋形象传承和精神诠释上的又一里程碑,雷锋形象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也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正如《人民日报》评论所言,虽然“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但雷锋精神焕发着永恒的魅力,激励人们无私奉献,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五、雷锋的伴生形象
在讨论雷锋形象演变的问题时有一个不能忽略的问题,就是雷锋的伴生形象,也就是不同时期出现的“××雷锋”们,这些形象从60年代起便不断出现,并主要集中在60年代以及80年代以后。
60年代雷锋最典型的伴生形象是王杰,他与雷锋有着相似的出身和经历,同样留下了大量“明革命之志”的日记,并在日记中以“做一个雷锋式的毛主席的好战士,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来自勉。因此,“两报”在报道王杰时,一直将他与雷锋相类比:《人民日报》在1965年10月31日为王杰日记摘抄配发的编者按中称其为“雷锋式的革命战士”;《解放军报》在11月4日的通讯中则直接用了“热情颂扬我们伟大时代的又一个雷锋”的标题,王杰成为了早期雷锋伴生形象中最重要的一个。
80年代雷锋的主要伴生形象是被中央军委授予“学习雷锋的光荣标兵”称号的朱伯儒。1983年1月25日,《解放军报》报道了朱伯儒帮助一位失足青年的事迹;26日又发表长篇通讯《炭火融融》,报道了他十余年坚持学雷锋做好事的经历;27日,《人民日报》也在头版报道了空军领导机关举行朱伯儒模范事迹报告会的消息,并在4版发表通讯《高尚的情怀》,自此,朱伯儒进入了“两报”视野,成为整个80年代与雷锋并提最多的模范人物。90年代这一角色属于“京城雷锋”孙茂芳,他的事迹在80年代便已零星见于“两报”。1993年3月5日,《解放军报》在头版发表长篇通讯,报道了他30年如一日坚持学雷锋做好事的先进事迹并配发评论《高唱新时代奉献歌》;6日,《人民日报》也报道了孙茂芳等全军学雷锋典型在京参加座谈会的消息;4月11日,又在头版头条发表长篇通讯并配发评论。“京城雷锋”孙茂芳就此成为90年代“两报”上雷锋最主要的伴生形象,并在进入2000年之后依然保持了这一地位,直到2008年之后,“两报”对他的报道才逐渐减少。
2010年9月19日,“两报”同时在头版头条发表介绍“新时期雷锋传人”郭明义的长篇通讯并配发评论;10月11日,胡锦涛总书记就学习宣传郭明义事迹作出指示,称他是“助人为乐的道德模范,新时期学习实践雷锋精神的优秀代表”;12日,“两报”又都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消息,从而掀起了“两报”对郭明义的宣传高潮。2013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两会”辽宁团审议过程中指出,雷锋、郭明义、罗阳所表现出的精神,“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最好写照,他们都是我们‘民族的脊梁’”;2014年3月5日,习总书记又给“郭明义爱心团队”回信,这些事件都在第一时间被“两报”以头版头条报道,并将对郭明义的宣传推向高峰。“两报”对郭明义的报道多与雷锋直接联系,作为2010年以来雷锋最重要的伴生形象,郭明义成了雷锋精神在当下最好的代表。
这些伴生形象对传承雷锋形象起着重要作用:雷锋的生命定格在了1962年,无论当初对他的宣传力度多大,形象塑造多完美,雷锋形象都不可避免地会随时间而逐渐淡化。我们所处的时代与当年雷锋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远,当下的受众很难对雷锋产生亲近感和体认感。要想让他们体会并接受这些已经逝去的榜样,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当代寻找一个现实的载体,而郭明义等人便充当了这样的角色:根据不同时代的需要,他们身上那些与雷锋相同或相似的品质被挖掘和放大,从而成了雷锋精神在不同时代的现实载体,而雷锋这一曾经的榜样也通过这种形式变得真实可感,从而更能激发人们向他们学习的动力。
那么,这些伴生形象为什么没能取代雷锋的地位呢?这首先是由于雷锋形象的先发优势(First-mover Advantages)。这是管理学的概念,认为先进入一个市场的公司可以利用其先行者的地位在利润和市场份额上获得更多的竞争力。借用这一理论来分析雷锋与其伴生形象之间的关系,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伴生形象都被冠以“××雷锋”或“雷锋式的××”之名,他们只能作为某一时段雷锋精神的现实载体,而没能成为具有新的精神内核的道德榜样。大众传媒不断地将他们的事迹与雷锋类比,从另一方面更加强了雷锋这一原生榜样形象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所以,他们只能是第二个、第三个雷锋,而不会是第一个王杰、第一个朱伯儒。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的题词使得雷锋这一形象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政治意义,“传播的仪式观强调参与、分享、联合以及拥有共同的信仰,并不是信息在时空意义的扩张,而是在时间意义上对社会的维系,不是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每年的3月5日成为了固定的纪念雷锋的时间点,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仪式,纪念雷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纪念毛泽东,纪念建国之初那段火红的岁月以及那些红色的理想和信仰,这也是所有的伴生形象所不具备的意涵。
六、结语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对雷锋形象经久不衰的原因作出如下结论:
第一,雷锋形象诞生于建国之初的60年代,他“旧社会苦孩子、新社会好战士”的形象完美地契合了当时宣传工作的需要,加上他本人在工作中的优异表现,这是雷锋形象最初被发掘、被塑造的原因。
第二,雷锋牺牲后,他的日记中表现出的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爱憎分明等特点符合当时政治工作的需要,使得他脱颖而出,成为“两报”关注的重点,而毛泽东的亲笔题词更使他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合法性,成为建国之初塑造的众多榜样中最特殊的一个。这也直接使他在“文革”结束后,成为了新一代领导人清算“四人帮”的重要武器,从而在70年代末再度成为“两报”宣传的焦点。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雷锋过时论”一度甚嚣尘上,而当人们意识到商品经济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时,又开始重新认识雷锋精神中那些弥足珍贵的要素。党中央也审时度势,对雷锋精神进行了一系列符合时代需要的新的解读。在经历了一个祛魅化和复魅化的过程之后,雷锋形象开始从一个革命好战士变成市场经济下的好公民,从而获得了几乎无限的生命力。
第四,雷锋形象演变过程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不同时期雷锋的伴生形象。这些产生于不同时代的榜样都因其与雷锋有种种相同精神而被大众传媒发掘宣传,他们成为了雷锋形象在不同时代的现实载体,使这一早已逝去的形象变得真实可感。同时,雷锋形象的先发优势以及他所具有的独特的合法性要素使得他具有所有的伴生形象都无法取代的优势,而不同时期对伴生形象的宣传从另一方面又强化了雷锋形象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注释:
① [美]罗伯特·J·斯滕伯格、温迪·M·威廉姆斯:《教育心理学》,张厚粲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217页。
② L Althusser,Trans.Ben Brewster.IdeologyandIdeologicalStateApparatuses.New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1.p.130.
③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④ 吴海刚:《雷锋的媒体宣传与时代变革》,《二十一世纪》,2001年第64期,第137-142页。
⑤ 袁光锋:《作为政治神话的“榜样”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雷锋”符号的生产、运作机制与公众记忆》,《思与言》(中国台北),2010年第4期,第23-84页。
⑥ 陶东风、吕鹤颖:《雷锋:社会主义伦理符号的塑造及其变迁》,《学术月刊》,2010年第12期,第103-116页。
⑦ 陈阳:《青年典型人物的建构与嬗变——〈人民日报〉塑造的雷锋形象(1963—2003)》,《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3期,第18页。
⑧ Reed,Garland G.Moral/PoliticalEducationi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LearningThroughRoleModels.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vol.24,no.2,1995.pp.99-111.
⑨ Yinghong Cheng.Creatingthe“NewMan”:FromEnlightenmentIdealstoSocialistRealities.Hawaii,American: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9.pp.93-97.
⑩ 军奋:《苦孩子成长为优秀人民战士》,《人民日报》,1961年5月5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