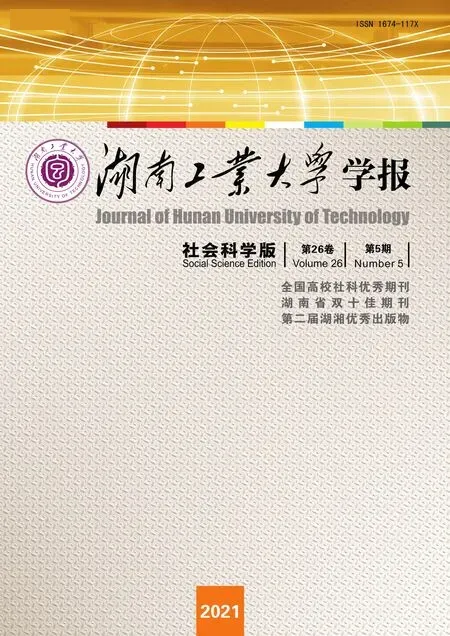网络时代粉丝群体的意识引导
赵亚曦,魏艳阳,金恩净
(1.中央广播电台 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北京 100045;2.中国传媒大学 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24;3.中国传媒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北京 100024)
“粉丝”一词源于英文中“fans”的音译,意为某人或某事物的狂热爱好者与拥护者。丹尼斯•麦奎尔指出粉丝的主要特征是密切关注吸引他们的事物,并经常对其他粉丝表现出强烈的认同感[1]。伴随着这一特征,当某个对象的粉丝数量逐渐增加到一定规模时,“粉丝群体”便由此形成。有学者认为不同的粉丝群体是根据不同的社会认同度凝聚而成的,并以此将粉丝群体分成不同组合类型的粉丝群体、不同功能类型的粉丝群体和另类的粉丝群体三大类[2]。本文提到的“粉丝群体”是以青少年一代为主,指崇拜对象覆盖各个领域的粉丝群体,其关注对象包括知名大咖、IP品牌、各界媒体等,而并非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这一群体积极追随他们热爱的对象,给予大量甚至过量的关注,同时热情地向周围的同类粉丝靠拢聚集,形成了具有凝聚力的集体,因此,将其作为本文的粉丝群体研究对象是充分合理的。
在社会学领域中,对于粉丝群体的行为研究与大众文化研究的范式转型密切相关。从文化研究诞生至今,文化研究范式几经嬗变,从最初以马修•阿诺德为代表的认为“文化是世人所思、所表的最好之物”[3]的“文化与文明(culture and civilization)传统”到雷蒙德•威廉斯所提出“文化是对某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4]的社会学转向,再受到阿尔都塞所提出关注结构性权力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SAs)”理论影响进行的结构主义转向,以及基于葛兰西所提出的更加关注个体能动性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理论的葛兰西转向,再到后现代主义转向等,这背后也反映出学界对于大众文化的“受众观”的变化路径。这个曾经在命名时就被污名化的粉丝群体也从“大众/乌合之众(mass)”转变为消费者(customers),再至詹金斯所谓的文本盗猎者(Textual Poachers),最后成为积极的意义生产者(people)。尤其近年来,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新媒体和web2.0时代后网络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青年亚文化群体凭借社交媒体的话语赋权,在与意识形态领域“收编与反收编”的协商下进行的网络组织动员行为更是刷新了学界对于90后以及千禧一代的粉丝群体的看法。比如,近几年发生了“奥运会莫顿事件” “香港修例风波”等涉及国家利益问题,对此,“帝吧”联手粉丝群体在媒介舆论场中为维护国家在外网舆论中的形象而“出征”,这些行为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使得粉丝群体的研究逐渐重回主流学界的视野,学者也提出了互联网时代大众民族主义行为研究的新课题。
那么该如何理解网络时代粉丝群体的大众民族主义行为呢?在研究个体行为动机时,能动(agency)和结构(structure)这对展示个人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的矛盾一直是不同社会学流派学者关注的问题。在《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一书中,社会结构不仅具有制约性,而且具有使动性。一方面,社会结构通过其规范性制约着人们的社会交往与互动行为,它无法决定人们的言行,但对各种社会活动起到了规范的作用,使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有规律地运转。另一方面,行动者(agent)利用结构性的规则和资源,改变社会结构,从而最终实现社会的变迁。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既不是个体行动者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的存在,而是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5]。因此,本文尝试运用安东尼•吉登斯所提出的结构化理论视角,在曼纽尔•卡斯特所提出的“网络社会”这种新型社会结构的背景下,分析在中国语境下网络社会中的结构性权力与粉丝群体能动的组织动员行为机制,但并不是要落入所谓“大众文化中不加批判的民粹主义”[6]——文化民粹主义(Cultural Populism)分析的窠臼,而是力图将其还原为一个存在于具体时空中动态的霸权协商的场域。此外,本文试图将身体问题引入研究视野,借鉴著名神经认知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的观点,尝试从神经科学和认知心理学角度来解释粉丝主体性的产生以及意识形态沟通和组织动员行为得以产生的机制。回归我国语境下的互联网时代粉丝群体的大众民族主义行为现象研究,为我们探讨如何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使商业资本的力量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互协调发展、如何通过网络传播的手段将粉丝群体组织动员起来并正确引导青少年群体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案例分析,同时提示网络时代的媒体应当通过打破不同圈层的界限来凝聚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共识,对青年群体实现积极的主流意识形态引导。
一 粉丝意识结构的影响因素:商业资本的入侵与主流意识的传播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范式的兴起,曼纽尔•卡斯特所谓的“网络社会”成为如今粉丝群体所处时代的新型社会结构。由于网络社会的结构植根于由微电子技术、数字信息处理和通信技术所驱动的网络之中[7]19,所以对于权力关系的理解也应放在网络社会的语境下进行。作为社会各类机构的基石,权力关系很大程度上通过传播的过程在人们心灵中得以建构。权力来源于影响力,而影响力本质上是一种说服,常常需要借助策略性的传播,传播的权力由此产生。传播力是一切权力运作的核心要件[8]74。因此,网络社会中的权力分析就是传播力分析,关注的是其背后蕴藏的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协调与平衡过程。回归中国的语境,就需要将中国的传播问题放置在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脉络中去追根溯源。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不可忽视的关键节点。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党和政府的喉舌”的政治属性与商业化的市场运行模式同时并存,两者有机协调,共同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生态。
(一)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商业资本裹挟下全球消费主义话语入侵
世界在过去30年经历了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治理的霸权制度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中心向边缘扩散的过程[9]。这场变革的基本内涵在于使市场解除管制(deregulation),国家退出社会福利供给,将一切可能的因素纳入市场体系中,给资本在全球的自由流动松绑。新自由主义不仅仅是一系列政治策略和政策设置,而且是一整套意识形态与文化信仰的系统[10]。新自由主义导致的社会重组与面向消费市场的娱乐内容的崛起之间有着密切关联。面对资本裹挟下全球消费主义话语的入侵,在世界信息传播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开始对赫伯特•席勒所提出的“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产生担忧。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原本一体化的社会结构被打破,随着市场化改革浪潮不断深入、传媒产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外商业资本不断渗入国内正不断崛起的互联网视频平台公司。根据天眼查的数据显示,bilibili网站(简称B站)在2020年4月初就获得了来自索尼公司4亿美元的投资,双方承诺会继续在动画、游戏、音乐等多个领域开展深入的业务合作。由于商业化的市场运作模式,欧美剧、日韩剧等文化工业产品不断入侵、国内互联网巨头平台制作的相关文娱内容不断涌现,不少学者开始担忧其暗含的个体主义、消费主义至上等新自由主义式的消费主义话语不利于以青少年一代为主的粉丝群体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漫威超级英雄系列电影为例,它的总票房在全球系列电影中排名第一,在中国内地的总票房也已突破200亿元。美国超级英雄系列电影是美国文化跨国传播的重要助力,蕴涵着美国人的文化价值观,每一个角色的呈现都是美国民族文化符号的代表。漫威英雄处于困难境遇时总是一往无前,具有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这些电影大力宣扬个人英雄主义,与美国文化中追求个人幸福、信奉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相符合。同时,这些电影由夺目的视觉造型及高科技手段打造,创造出梦幻般的声像效果,以满足观影群的感官欲望。当漫威超级英雄系列电影朝大投资、高技术、多感官刺激的方向发展时,美国文化精神的呈现方式也变得简单化和符号化,流于商业消费文化。这些电影对于个人主义和科技主义的宣扬影响着不同地区、不同人种、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粉丝群体。因此,在目前的形势下,面对互联网时代商业网络媒体不断崛起的冲击,传播影响力式微的传统电视、报纸媒体如何协调好与商业资本的关系,并在以青少年为代表的粉丝群体中促进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二)“媒体融合”的影响:意识形态的主流争夺
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文化生产逻辑来主导精神产品的生产,必然导致这类产品的精神世界和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文化政治产生断裂[11]。所以国家进一步强化了媒介舆论场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地位:一是要统一协调,加强网络信息的安全管控;二是利用国家资本,推动跨界融合,搭建新的媒体平台[12]。2014年至今,“媒体融合”政策已经经历了以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为代表的央媒层面的媒体融合、以浙报传媒集团为代表的省级层面的媒体融合、以浙江长兴县为代表的各级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等多个阶段。可见中央对新闻舆论工作提出了媒介融合向纵深不断推进的要求,着力打造更多融合性的“新型主流媒体”。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当属在抖音平台上以“立足四川,观察全球”爆火的四川省级广电孵化的新闻资讯类短视频账号“四川观察”。截至2021年3月17日,“四川观察”抖音账号粉丝数已达4 462.2万,荣登地方新闻类媒体“抖音”第一网红的宝座。与此同时,“四川观察”不断开拓多平台矩阵,深挖短视频的运营奥秘,其快手账号粉丝数已达767.1万,微博账号粉丝数已达320万。正如“四川观察”总编辑岳学渊所说,“出圈”秘籍在于“你去关注用户,而不是让用户找不到你”[13],展现了在新的传播手段与技术面前,国家层面为维护媒介场域中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所付出的努力。媒体构成了社会化传播的主要来源,大众媒体通过对象征性事件的选择与加工、重新结构化,构成了向大众展示的信息环境,其具有遍及整个社会的潜在效果。通过对新闻和文化工业的媒体议程设置的接触,粉丝群体感知自身和世界,并由此形成思想框架进而作出行动。
二 粉丝主体性的产生原因:情绪认知、价值观沟通与征服心灵
传播网络的技术与形态不仅影响了网络空间中的权力关系,也塑造了粉丝群体的价值观沟通与动员过程。粉丝群体作为一个特殊的亚文化群体,在文化研究领域一直备受争议,对于追星这种文化消费现象,学界也一直存在两种相互区别的范式。一种是“强结构而弱行动”的悲观的文化消费观,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其在权力结构模式中考察流行文化,强调文化工业对大众的麻痹作用,给受众虚假的快感,致使人们失去理性批判的思考能力。另一种是“强行动而弱结构”的乐观的文化消费观,以约翰•费斯克及其学生亨利•詹金斯为代表。其认为粉丝群体对于文化产品的消费并不会失去理性的思考,反而会对文化产品的消费进行能动的积极抵抗。这种观念强调了受众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本文对此持中间立场,通过上述对于商业资本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互协调与发展的分析,本研究认为,全球消费主义流行文本可能会导致群体产生不理性的行为,但主流意识形态的入场与对价值观的再现在一定程度上共同塑造了粉丝群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评价视角、框架和语汇。
(一)具身视角:身体在场与情绪认知
意识形态主导在人们心中的特殊构建方式是激活情绪(emotion)[8]76。任何一次媒介事件,一定与背后的社会情绪密不可分。社会运动通常由情感触发,这些情感源于一些意义重大的事件,根本原因是情绪动机。以“新主流电影”的兴起为例,它是融合新时代精神,以爱国主义、民族精神为核心的,蕴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价值内涵的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形态。当下,新主流电影紧跟IP概念的流行趋势,《智取威虎山》改编自红色经典《林海雪原》,而《战狼》系列开发了全新IP,这些电影结合英雄主义与社会主流价值,体现大国崛起的力量,激发观影者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自豪感,由此可见,新主流电影兴起的背后离不开粉丝群体的深厚的情感基础。
在分析粉丝群体积极能动性得以产生的情感动机时,本文借鉴著名神经认知科学家达马西奥的情绪具身认知观,认为“感受的内容总是与产生它们的生物体的身体有关”[14],将身体问题引入情绪研究视野。在传播研究史上,“身体不会说话”,其一直是一个沉默的存在。自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以来,西方思想长期将感知视为主观的和不可靠的,情感只是理性的杂音,处于从属地位。但是作为媒介,身体既是主体物质性的寓所,也是感知世界的途径[15]。传播通过激活心理来分享意义,大脑以隐喻方式进行思考,但呈现的是物理结构。从生物学角度来解释粉丝主体性的产生以及意识形态沟通和组织动员行为得以产生的机制,则情感可以同时促进粉丝对媒体框架的理解,以及自发性的意识形态沟通与动员行动。所以,粉丝群体将自己对于偶像的情感平移到国家上,也就是“像爱护爱豆一样爱国”[16],传播以其不同的模型在决策过程中对于激活相关的神经网络发挥着主要作用,这是因为“当我们生活在一个故事中时,我们会使用大脑中一些相同的神经结构”,传播可以影响行为的一种方式是激活我们大脑中所谓的镜像神经元[7]131,镜像神经元诱导的神经模式对大脑相关区域的激活正是粉丝群体爱国情感的来源。因此,社会运动涉及大脑神经网络的相互关联,其信号刺激来自其周围环境中的传播网络,我们的神经网络和传播网络结合起来,最终说服大脑并使身体行动起来。
(二)互动框架:价值观沟通与征服心灵
处于不同时间阶段的粉丝群体的互动方式是不同的,回顾改革开放至今粉丝群体互动方式的变化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粉丝群体的主体性行为。有学者将改革开放后国内粉丝文化的流变概括为三个阶段:信息单向传播中的受众型粉丝阶段;市场变革影响下的消费型粉丝阶段;媒介激变背景下的互动型粉丝阶段[17]。整体而言,第一阶段大致时间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一阶段粉丝活动比较私人化,不仅粉丝与偶像之间存在距离感,粉丝之间的横向勾连也十分微弱。从学术的概念去理解,这一时期的核心特点在于“文本中心性”的私人追星。粉丝重要的日常实践就是和某个特定的文本,比如一首音乐、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等流行文化的文本建立情感关系,深度融入、强烈互动并把情感和自我投射其中。第二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直至21世纪前十年,这一阶段随着市场经济和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粉丝群体开始逐渐在线上汇聚,随着《超级女声》掀起全民参与选秀节目的热潮,粉丝群体商业价值日渐凸显,“粉丝经济”也逐渐成型,但囿于网络带宽与移动传播技术的限制,此时的粉丝群体之间的互动频率与互动效果仍然是有一定局限的。第三阶段时间点大致是从2010年至今。在今天,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上网成本不断下降,网络用户规模不断扩大,快速便捷的网络传播使权力更加分散、去中心化、去权威化,网络用户有更多选择的自由,粉丝群体之间的情感结合和横向勾连更加紧密,粉丝群体的主体能动性以及行动力不容小觑。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鹿晗公益联合应援站等27家粉丝团临时集结“666联盟”,联合向武汉抗疫一线捐赠物资。根据“鹿晗公益应援博”于2021年1月24日发布的微博数据显示,“666联盟”年度公益汇总捐赠物资多达19次。这一系列的实例验证了粉丝群体所蕴含的积极的公共参与的潜力,所以我国媒体在对粉丝群体进行正确引导时不能仅仅停留在文本层面的话语策略,更要从互动框架下思考如何运用新媒介在情感层面激发粉丝群体的主体行动力,让其从情感认知层面积极主动地进行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沟通。
真正有效的,并不单单是符号刺激,更重要的是彼此间情感激发的认同的力量、征服心灵的力量,这才是最值得关注的粉丝主体性产生的原因。诚如詹金斯在《文本盗猎者》中所言,“迷文化(fan cultures)仿若一个半结构的空间,对文本的诸种阐释与评估机制便于其中交相辉映、互相冲突、交流妥协,读者亦时刻思索着大众传媒的天性与自身的关系。”[18]
三 粉丝意识形态的引导关键:突破粉丝圈层,传播主流意识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粉丝们正凭借着彼此对于不同偶像的喜爱情感和在这种情感共振基础上形成的关系认同汇聚在一起,构建着一个个线上的“文化圈层”。而且需要注意的是,粉丝群体内部也并不是铁板一块,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其内部的分类构造。比如,同一个偶像团体的粉丝群体内部又可以分为“CP”粉、团粉、唯粉等,同一个偶像的粉丝又可以分为妈妈粉、女友粉、路人粉等,这些角色分类并不是完全孤立平行的,而是可能会相互重叠、动态变化的。粉丝群体的圈层化包含“圈子化”与“层级化”两个方面,不仅大圈子下的不同小圈子有不同的等级排序,而且这些小圈子内部也存在明显的等级结构,粉丝在圈层化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很大程度上与其消费能力和在现实社会中的影响力相关,这就使得粉丝群体的主体行为背后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因素。“圈层化”多元的连接形式、高强度的互动关系带来的各种紧密互动模式会产生强大的效果。粉丝群体内部鲜明的圈层结构和严格的组织构架加上其在追星过程中不断学习与掌握的各种媒介使用策略,使其表现出超强的舆论造势能力、信息传播能力与组织动员能力,他们主动规划、参与、应援、运营、推广,这些都成为新一代粉丝团体的“使命”[19]。粉丝领袖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需要辨别的是,粉丝群体的圈层分化一方面使得兴趣和价值观取向相似的人们能够聚集在一起,寻求某种“心理共同体”的庇护,从而获得群体归属感;但“圈层化”另一方面也使得大量同质化的信息和观点只能在圈内循环流动而难以“出圈”,个体对于所处环境内的“意见气候(opinion climate)”的感知极易出现误差,迫于群体压力的“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现象在此类粉丝群体中或许会更加明显。这不仅会对个体信息获取和思维方式产生各种约束进而造成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现象,更会导致群体间传播隔阂的增加,使得圈层间的立场产生分歧,甚至导致共同体间进行公共对话与社会整合变得更加困难。
这些处在“圈层”中的粉丝的群体性力量正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比如今年5月份由于《青春有你•第三季》综艺节目背后商业资本逐利乱象导致的“倒奶打投”事件,平台和资本合谋将粉丝文化“异化”为简单的流量至上行为,其中过度消费打投、非理性应援、买号刷数据榜单、请水军刷评论这一系列行为已形成多条灰色产业链,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粉丝群体行为异化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不得不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因此,粉丝群体的巨大能力该向何种方向发展以及如何引导粉丝群体的意识方向值得我们深思。2020年7月13日,网信办发起了《关于开展2020“清朗”未成年人暑期网络环境专项整治的通知》,其中第六条声称将重点整治诱导未成年人无底线追星、饭圈互撕等价值导向不良的信息和行为。2021年6月15日,中央网信办宣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此次专项行动将围绕明星榜单、热门话题、粉丝社群、互动评论等环节,重点打击应援集资、互撕谩骂、攀比炫富、刷量控评、干扰舆论等5类“饭圈”乱象行为。期间,将关闭解散一批诱导集资、造谣攻击、侵犯隐私等影响恶劣的账号、群组,从严处置“饭圈”职业黑粉、恶意营销、网络水军等违法违规账号,从重处置纵容乱象、屡教不改的网站平台。该通知发布后,微博、腾讯、豆瓣等各大互联网平台迅速响应,并公布了对应的整治措施,由此可见国家对于以青年群体为主的粉丝群体的互联网生态治理的重视。
因此,如何打破这些不同圈层的界限与屏蔽,实现圈层与圈层之间的横向整合、情感关联与价值沟通,在互动框架下充分调动粉丝群体主体性,在这些青年群体中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与凝聚是主流媒体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应实现社会共识和社会协同,对粉丝群体进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正确引导,避免其落入商业资本隐蔽架构的消费主义陷阱,因为谁掌握圈层,谁就掌握传播驱动的主控权[20]。今天,在线上构建一个新社会,是主流媒体真正可以发挥价值的地方,而且在这方面传统主流媒体是有优势的,因为它还有相当强的公信力及政府背景,可以依靠自身的载体优势和社会地位授予功能发挥作用,其在构建社会关系方面比互联网公司的初始条件有优势[20]。主流媒体的“破圈”尝试中最成功的当属在B站被粉丝们亲切称为“团团”的共青团中央。从微博微信再到知乎B站,共青团中央走上了更多青年人活跃的平台。自2017年年初共青团中央官方账号进驻B站以来,共青团中央不断在青年群体中“破圈”并已形成广泛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截至2021年6月1日,共青团中央的官方账号已经累计粉丝835.4万,制作发布视频达3249条,累计播放量15.8亿,累积获赞量1.6亿。青年群体是网络舆论阵地的主力军,如何让主流的声音在青年群体中传播出去,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力、影响力、公信力成为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2021年4月21日,国家信息中心发布《2020中国网络媒体发展报告》,报告总结了网络媒体的新表现、新生态、新责任。其中,新责任提出“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在媒体融合的大背景和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共青团中央不断丰富其多平台生态矩阵,在青年群体中积极“破圈”,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通过二次元与情感共振的话语策略、深入贯彻意识形态引导的内容主题、技术赋能多种样态的形式创新、PGC+UGC并行的合作模式这四方面的不断努力,共青团中央将更好地担负起引导新时代网络媒体的新责任。
本文在研究网络时代粉丝群体的大众民族主义行为动机时,按照结构化理论的视角,对中国语境下的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商业资本的相互关系以及两者间的动态协调过程进行了分析。但粉丝并非被强行拽入业已构成的文本世界,而是运用相应自主性来解读文本。从情感具身认知视角与生物学角度来看,“迷”们对文本进行消费并最终将其转化为积极的动力,通过镜像神经元激发相应情感,将他们对偶像的崇拜与喜爱情感平移到自己的国家那里,不断发现和发展自我、形成自我认同,认同的力量最终驱动粉丝群体大众民族主义行为的产生。
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迭新,当下粉丝群体内部的圈层化结构和高强度的互动关系蕴含着巨大能量,粉丝群体在网络性和执行力上是非常完善的。虽然互联网平台商业逐利资本异化粉丝群体行为的现象仍然存在,但我们从网信办所发动的专项整治行动中也看到国家层面对于青年群体所处互联网生态治理的努力。我们相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下,粉丝群体有潜力且有能力进行一些积极的主体性行动,比如为环保、慈善事业聚集力量、发出声响。追星不单单是一种娱乐方式,也能是另一种形式的蕴含积极力量的网络公共参与行为。比如“哈利•波特联盟”于2010年11 月发起“哈利•波特巧克力公平贸易”运动,这种“以流行文化联系社会议题的粉丝对话与动员,深挖文化核心隐喻来联系现实社会问题”的“文化针灸主义”行为[21],就充分展现了微观的生活价值观与公共政策的“实体”价值观之间建起桥梁的可能,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通过粉丝群体在网络上传播并确立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为了协调与平衡好商业资本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媒体应积极承担起对以青少年为代表的粉丝群体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引导的责任,不断创新地尝试多种“破圈”机制,激发粉丝群体的情感认知与价值观沟通,最终达到征服其心灵的目的。因此,我们需要不断思考如何用正确的方式征服并正确引导粉丝群体的心灵,并以此展望建设粉丝“公共领域”[22]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