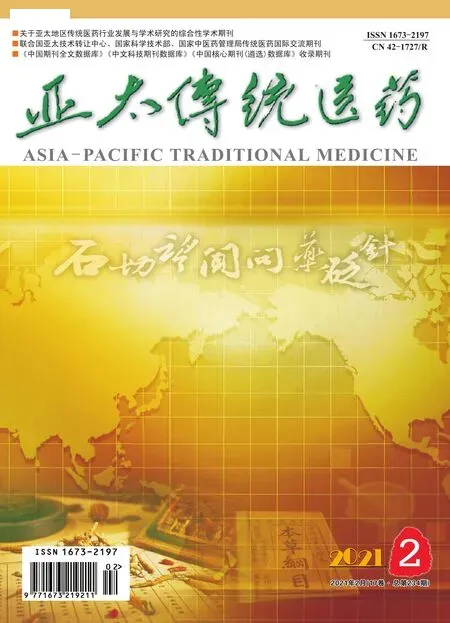余甘子应用源流考
杨崇仁,张颖君,王海涛,王建刚,丁艳芬,邵艳红
(1.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201;2.云南维和制药有限公司,云南 玉溪 653101)
余甘子(PhyllanthusemblicaL.)在我国有悠久的药用历史,既是我国民间常用食用和药用植物,又是重要的藏药资源,还曾是来自西域三果浆的重要原料。关于余甘子已有多方面的研究报道,本研究通过物种资源调查,阐明余甘子的生物学特性;通过民族医药学调查,梳理历史文献,理清源流,为余甘子的应用和开发收集参考资料。
1 余甘子的分类与分布
余甘子为大戟科(按新的APG系统归入叶下珠科)叶下珠属植物,广泛分布于亚洲热带地区,常见于西亚、南亚以及东南亚各地,在印度和中国分布较广。
余甘子又名滇橄榄、馀甘、榆甘子、喉甘子、油柑、油柑子、牛甘子、橄榄、土橄榄、鱼木果、望果等。印度各地对余甘子的称呼不一,梵语为:amalaka(amara为芒果)、 amlaki、 dhatri、dhatriphala、adiphala;北印度语和孟加拉语为:amla;印地语为:aonla;泰卢固语为:amalakamu和usirikai;旁遮普语为:amolphal;孟买语为:avalkati;泰米尔语为:nelli;古吉拉特语为:amali;孟加拉语为:amlb,bmlaki;尼泊尔语为:amla;伊朗语为:amuleh;波斯语为:amola,amala;英语为:fruit emblic,emblic leafflower fruit 或Indian gooseberry。译名有庵摩勒、阿摩勒、阿没勒、庵磨罗等,可能来源于北印度语和孟加拉语;汉译佛经译作庵摩落迦、阿摩落迦和阿末罗果(大唐西域记),则可能来源于梵语[1]。庵摩勒是通用译名。
余甘子在我国长江以南从西南至东南沿海均有分布,包括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广东、福建、海南、台湾地区等。余甘子是分布广、变异性大的多型性物种,其生态型既有灌木,又有乔木;结实多少和果实性状大小与其生态环境和树龄密切相关,而性状特征趋同性明显。余甘子对土壤条件要求不高,在贫瘠的土壤中能顽强生长,根系发达,主根深、侧根广,蓄水力强,固土作用好,可防止水土流失,改善干热地区生态环境,是荒山绿化的先锋树种。云南野生资源丰富,常见于海拔1 200~2 200 m的山区,特别是干热河谷两侧的疏林和山坡向阳坡地,有的地段形成优势灌丛或小乔木林居群[2]。余甘子在华南多有野生,有的地区已有栽培,福建等地已有种植基地,培育了多个品种。
2 余甘子在中医药中的应用
余甘子别名繁多,提示有复杂的历史和民族应用背景。余甘子在中医药典籍中多有记载[3]。
东汉杨孚《异物志》(公元二世纪)最早记载余甘子“盐蒸之,尤美,可多食”。晋代嵇含(304年)《南方草本状》言:“庵摩勒树叶细,似合昏,花黄,实似李、青黄色,核圆,作六七棱,食之先苦后甘。”陈藏器《本草拾遗》(739年)载:“梵书名庵摩勒,又名摩勒落迦果。其味初食苦涩,良久更甘,故曰馀甘。”唐代苏敬《新修本草》(659年)有余甘子在本草典籍的早期记载:“庵摩勒,味苦、甘,寒,无毒。主风虚热气。一名余甘。生岭南交、广、爱等州。”不仅记载了余甘子的性状、用途和产地,而且认为印度传入的庵摩勒(菴摩勒)与本土产的余甘子为同一物。
《千金翼方》(682年)认为庵摩勒:“味苦甘寒,无毒。主风虚热气。一名余甘。生岭南交广爱等州。”五代前蜀李珣(德润)所撰《海药本草》(约10世纪初)称:“庵摩勒,生西国,大小如枳橘子状。梵云:‘菴摩勒果是也。’味苦、酸、甘,微寒,无毒。主丹石伤肺,上气咳嗽。久服轻身,延年长生。凡服乳石之人,常宜服也。”提示中古时期余甘子除原产我国华南外,还通过北方丝绸之路来自西域,并随南方海上贸易渠道海运而来。
此后历代本草典籍多有记述,如北宋唐慎微 (1097-1108年)撰《证类本草》载:“庵(音谙)摩勒,味苦、甘,寒,无毒,主风虚热气。一名余甘,生岭南交、广、爱等州。”宋代苏颂(1020-1101年)编撰《图经本草》云:“庵摩勒,余甘子是也。生岭南交、广爱等州,今二广诸郡及西川蛮界山谷中皆有之。其俗欲作果子,啖之初觉味苦,良久更甘,故以名也。”我国10世纪以前最大的官修医药典籍《太平圣惠方》(978-992年)收录“余甘子散”专治乳石发热症状。《普济方》(明·朱橚等,1390年)收载“小三生丹”用余甘子预防金石之毒。《本草拾遗》曰:“梵书名庵摩勒,又名摩勒落迦果。其味初食苦涩,良久更甘,故曰馀甘。”《滇南本草》称:“余甘子味甘、酸、性平。治一切喉火上炎、大头瘟证。能解湿热春温,生津止渴,利痰,解鱼毒、酒积滞,神效。”《本草纲目》云:“余甘树,叶如夜合及槐叶,其树如柘,其花黄,其子圆,大如弹丸,色微黄,有文理如定陶瓜,核有五六棱。主治见虚热气、丹石伤肺,久服轻身、延年长生,有解金石毒、解硫黄毒。”
古代文人描写余甘子的诗词也有不少,如:“待得余甘回齿颊,已输崖蜜十分甜”(苏东坡《橄榄》);“粲粲庵摩勒,作汤美无有”(秦观《海康书事十首》);“世界庵摩勒果,圣贤优鉢昙华。但解折衷六艺,何须和会三家”(陆游《六言杂兴九首其一》);“补落迦山访旧游,庵摩勒果隘中州。秋涛无际明人眼,更作津亭半日留”(陆游《海山》);“庵摩勒,西土果。霜后明珠颗颗。凭玉兔,捣香尘。称为席上珍。号余甘,争奈苦。临上马时分付。管回味,却思量。忠言君试尝”(黄庭坚《更漏子·庵摩勒》)等。
中古时期余甘子常见于本草典籍,是清热解毒、利肺生津、延年益寿的良药,或作果品食用,很少在中医方剂中有应用。《本草纲目》将其移入果部,致使余甘子的主要用途停留在南方食用果类,始终未能像乳香、没药、血竭等外来的南药那样,进入我国传统中医药的主流。
3 余甘子在我国民族医药中的应用
余甘子是我国藏族、彝族、傣族、苗族、白族、纳西族、拉祜族、普米族、佤族、阿昌族、基诺族、布依族、瑶族、壮族,以及蒙古族、维吾尔族等十余个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常用药物。除蒙古族、维吾尔族等北方少数民族受藏医药的影响外,大多数南方民族均利用其居住地区自身的余甘子资源,形成各自的医药经验。在民族民间医药中,余甘子多用于感冒、咳嗽、喉痛、腹泻、消化不良、解热消炎、生津润肺、皮肤湿疹、水火烫伤等证。
余甘子为常用藏药,藏语称为究孺拉(觉肉拉、久如拉、居如热、久孺拉、居如拉)(gyu-ru-ra,ju-ru-ra,skyu-ru-ra)[4-5]。余甘子在藏医药中占有重要地位。藏医药早期典籍《月王药诊》和《四部医典》均记载了余甘子用于治疗培根、赤巴病和血病。《四部医典》又名《医方四续》(藏名《居悉》),是藏医学的主要典籍,成书于公元8世纪,作者是吐蕃初期著名藏医学家宇妥·宁玛云丹贡布,《四部医典》继承了西藏本土象雄雍仲本教医药学传统。余甘子载于《四部医典》提示其最早可能是通过古西藏象雄王国或苯教,由印度西北部传入西藏的。帝玛尔·丹增彭措所著《晶珠本草》描述余甘子“树生于热带,干长柔软,叶大,花淡黄色,光泽不鲜,叶如猪鬃疏松,果实肉核分离”,认为“果实采自树干者,味不浓,为次品”。余甘子是著名藏药三果汤的主要原料之一,也是藏药许多复方制剂的主要原料,如三果汤散、复方庵摩勒、佐母朱汤、郎庆阿塔、多血康、甘露清血散、甘露酥油丸、吉尼德协、藏诺参甘片、二十五味余甘子丸、二十味沉香丸、十五味龙胆花丸、十五味萝蒂明目丸、二十五味肺病丸、七味消肿丸、六味木香丸、五味余甘子散、四味余甘子方、三味姜黄丸等。藏药究孺拉虽在藏族地区已有多年的广泛应用,但基源不明,一直从南部的聂拉木和墨脱等地通过尼泊尔进口。墨脱有将刺苞省藤(Calamus acanthospathus Grif-fith)(棕榈科)的果实作余甘子代用品的做法[6]。直到上世纪60年代杨竟生先生考订藏药品种,通过实物比较鉴别,始确定究孺拉即为余甘子[4]。目前余甘子已载入《中国药典》藏药分册,并开发出多种现代藏药和健康产品。
4 余甘子在印度的应用及传播
在印度传统医药生命吠陀中余甘子占有重要地位,是印度神话中的仙药,也是印度医药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药物之一,还是妇女和儿童医疗保健的常用药物。印度妇女分娩后以及刚出生的婴儿用余甘子水沐浴,还将其用于妊娠期排尿困难和子痫、热证,以及用作洗浴、乌发和泻药等[7]。余甘子果实粉末与少量黄金、酥油和蜂蜜拌和,敷于新生儿体上可助骨质生成和增强抗病力。在印度医典《医理精华》中含有庵摩勒(余甘子)的药方非常多;《耆婆书》残卷收录的90个药方中,用到庵摩勒的有25个[1]。目前,余甘子在印度有广泛栽培,种植面积5万hm2以上,产量15万t。印度以余甘子为原料制成的医药健康产品和化妆品种类繁多,仅几个大药厂每年消耗果实就在1.1万t以上[8]。
余甘子是印度著名的三果浆(三勒浆)的组成之一。三果浆是古印度医典中最常用的神效果药浆,其得名来自印度文化。汉译佛经的三果名是梵语triplate的意译,即三种果药(myrobalans)。这三种果药分别为庵摩勒(余甘子)、诃梨勒(柯子)和毗梨勒(毛柯子)。三勒浆的名称则是来自波斯,勒是波斯吐火罗方言中这三种水果各自名称的最后一个音节。波斯语中,与诃梨勒、毗梨勒、庵摩勒对应的词分别为hahla、balila、areola,有相同的结尾音节la[1]。三果浆既是清凉可口的果汁露,也是治疗腹泻、咳嗽、热证等疾病和增强体质的常用药物[9]。三勒浆的名称提示三果浆早期是经过波斯传入我国的。
古印度的三果浆沿东西方向传播,西至阿拉伯、波斯及罗马。中古时期,中亚和南亚伊斯兰化,三果浆为无酒精饮料,符合伊斯兰教义。三果浆既能入药又能作浆,不含酒精颇受欢迎,从而在中亚地区流行,成为阿拉伯文化产物。丝绸之路开通后,波斯是印度与中国交流的中转站,三果浆入唐的途径虽史无明载,东向传播途中,在于阗、吐蕃、敦煌等地均留下许多遗迹,已出土的文物残卷中有不少的记载[1]。余甘子以及三果合用入药方,不仅在印度本土医药古籍,而且在丝绸之路的胡方中亦常见。
“赤脚波斯入大唐”,三果浆最早为胡人进献的贡品。隋唐时代进入中原的胡人或波斯人,大多是栗特商人。栗特人是生活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珊河流域的古老民族,属于伊朗文化系统。在地处欧亚大陆东西往来的主干道上,栗特人是善于交往和贸易的民族。公园4世纪初,栗特商人就已在丝绸之路上形成了贸易网络,中古时代栗特人长期控制着东西方的贸易[10]。栗特商人带有伊朗和中亚的文化特点,经营香料、药物、珠宝和贵金属等,丰富了中国社会的物质文化。他们有的还代表西域各国,向中国朝廷和官员贡献礼物。三果浆作为珍贵的礼品和商品,被栗特商人带入中原地区。古印度的三果浆在阿拉伯文化的影响下,进入中国并称为三勒浆[11]。
隋唐之际栗特商人进入中国被称为胡商或波斯人,他们在漫长的商路上跋涉,跨越不同的地域和文化,将三果浆由西域传入中国。作为珍贵的贡品,三果浆被献给隋唐宫廷和达官贵人,成为异域文化的代表,并成为与葡萄酒媲美的类酒,流行于上层社会。“河汉之三勒浆”是唐代皇室御用的外来高端珍稀佳酿。三果浆时兴一时,曾有唐代宗用三果浆宴请大学士的故事。三果浆及其制作方法由胡商从波斯传入,因此中古时期有三果浆“法出波斯”之说。作为异域饮品的代表,三果浆成为了唐代皇家贵族和上层社会炫耀的外来高端珍稀佳酿[11],余甘子作为三果浆的主要原料也逐渐被认识。唐宋以降,三果浆逐渐从中国社会淡出,未能在民间广泛流行,因其与国人品饮习惯以及自古以来的酒文化不符,也与三果浆的三果原料均产于热带地区不易收获运输有关,而今只留下落日余晖记载于古籍之中。三果浆的三种原料中,仅余甘子亦产我国南方,因古代中医典籍记载无多,更少方剂收入,仍未能在我国传统中医药中广泛使用,反而在藏族等民族中长期应用,民间经验丰富,特别是三果浆和余甘子均是藏医药的重要药物,在藏区应用广泛。
5 余甘子与佛教
三果浆是不含酒精的饮料,佛教兴起后,余甘子等三果是僧人一生都可服食的五种“尽寿药”之一。“尽寿药者,呵梨勒、毘酰勒、阿摩勒、荜茇、胡椒、姜”(东晋·佛驮跋陀罗共法显译《摩诃僧祇律》卷三,《大正藏》22:244),属于佛教尽形寿药的果药类,印度僧人用于疗病和养生的常备饮品,僧人念经口干喉燥时服用,可润喉生津止咳和提神醒脑。印度佛经《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卷一载:“所谓余甘子、诃梨勒、毘酰勒、毕鉢梨、胡椒。此之五药,有病无病,时与非时,随意皆食,勿致疑惑”(唐·义净译《大正藏》24:210)。在密教文献中,三果浆作为仪轨用物,不空译《文殊师利菩萨根本大教王经金翅鸟王品》云:“以安悉香酥,和三果浆,烧念诵,一切人皆敬爱。”《大佛顶广聚陀罗尼经》卷2用三果配制延年方,《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用三果配制眼药,三果浆也可作为原料配制各种饮品和食品。《遮罗迎本集》中有三果长年方、三果煎、三果酥、三果散、三果油、三果酒、三果糖浆等;《妙闻本集》中也有三果酥;《八支心要方本集》中则有三果长年方、三果酥和大三果酥;庵摩勒还用于沐浴、黑发等:“复有薰香洗浴之物,浮甎澡豆芬馥余甘,持用揩身并将涂发,能令发白更黑”(唐·义净译《大正藏》24:207)。窥基在《瑜伽师地论略纂》卷五中记载:“西方浴讫,以余甘子切碎暴干为末,以生胡麻香油和之,令其润腻,不硬不软,方以涂身,取其香洁润滑光净故”(《大正藏》43:83)。余甘子是佛教僧人常用的甘露丸原料,僧诗云:“阿那律陀天眼观,大千摄入一毫端。掌中谩说庵摩勒,无限苍生被热谩”(释慧远《楞严六根·非眼能见》)。称“佛经中所谓菴摩勒果者是此,盖西度亦有之”(宋·寇宗爽《本草衍义》)[1]。
汉译佛经将余甘子译为庵摩落迦和阿摩落迦,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称其为阿末罗果,均是由梵语翻译而来。由于仅在佛教僧众中秘传,庵摩勒在印度的应用未能与长江以南土生的余甘子和我国民间经验联系在一起,未能被我国传统中医药广泛认同。
6 余甘子健康产品开发
自古以来,中印两国均将余甘子作为长生果药用于保健,具有惊人的一致性[1]。余甘子在我国西藏和南方各地长期使用,不仅是传统藏医药的常用药物,南方民族民间亦广泛使用。不仅是许多少数民族的传统药物,而且是常用的食用植物和保健用品。余甘子已列入我国药食两用目录,开发了以云南维和药业公司研发的维甘片为代表的一系列健康产品[12]。初步统计已有批文的保健食品近百种之多,还不包括品类繁多的食品、饮料和日化产品等[13]。余甘子的社会知名度日益提高,产值已达数亿元。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完全有可能将余甘子发展为百亿元的产业。
謹以此文纪念藏药资源研究先驱杨竞生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