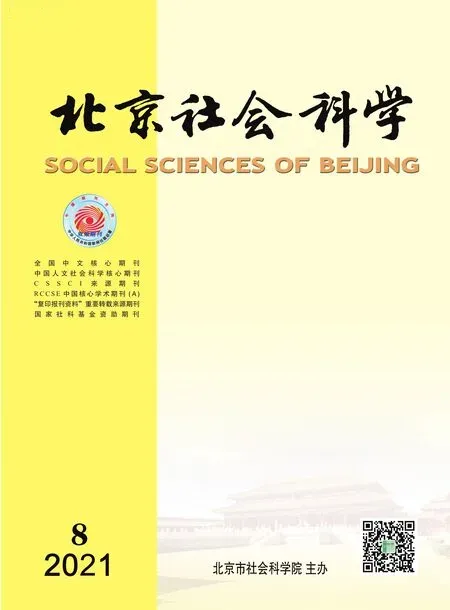论影片《桃花泣血记》的多重张力扭结
周仲谋
一、引言
卜万苍(1903-1974),安徽天长县人,是中国早期电影史上的一位重要导演。1921年,18岁的卜万苍离开家乡来到上海,从此结下了与电影的不解之缘。卜万苍最初在电影界担任摄影师,先后为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明星影片公司拍摄了《人心》《谁是母亲》《新人的家庭》等影片。1926年,卜万苍“摄而优则导”,在民新影片公司完成了他的导演处女作《玉洁冰清》,上映后颇受欢迎。此后,卜万苍又陆续执导了《挂名的夫妻》《湖边春梦》等影片。1931年,卜万苍在好友黎民伟的邀请下,加入新成立不久的联华影业公司,开始了与联华长达数年的合作,为该公司执导了多部影片,《桃花泣血记》就是其中颇有影响的一部。
《桃花泣血记》由联华影业公司于1931年摄制出品,卜万苍编导,黄绍芬摄影,罗明佑监制,黎民伟担任制片主任。时隔90年,重新审视《桃花泣血记》这部20世纪30年代的经典影片就会发现,该片既有着对中国电影本土化、民族化的尝试,又蕴含着追求爱情婚姻自主、争取女性自由解放的现代启蒙思想,并流露出同情底层民众、批判贫富差距的进步阶级意识,从而呈现出多重张力相互扭结的独特现象。
二、本土化尝试和民族化色彩
联华影业公司老板罗明佑颇具革新意识,他有感于当时中国电影市场被大量外国电影占据,国产影片陈旧老套、疲软不振等问题,在1929年12月提出了“复兴国片,改造国片”的口号,并身体力行地由经营影院业转向从事制片业,掀起了一场“国片复兴”运动。“国片复兴”既包含着振兴中国本土电影工业、抵制外国电影文化侵略和经济侵略的动机,“也包含着反对中国电影艺术表现上的‘欧化’风格,使其朝民族化、本土化方向发展的诉求”。[1]联华影业公司于1930年8月成立后,又提出了“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的制片方针,希望除去当时电影界粗制滥造的弊病,将中国文化的优势融入国产电影创作当中,力求推出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卜万苍编导的《桃花泣血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与联华公司“复兴国片”的口号相呼应,《桃花泣血记》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本土化、民族化的尝试和努力。如该片监制罗明佑所言,“国片编制,情节景物,皆被欧化,识者讥之久矣,然而积重难返。本片欲一除旧习,情事景物,处处皆以表现我民族之色彩。如西服器用,皆所废除。于此一端,可见其意”。[2]《桃花泣血记》中的人物衣着,都是长衫、短褂、斜襟衫裙、旗袍等中式服装,男子戴毡帽或瓜皮小帽,对当时不少国片中出现的西方衣着服饰一律弃之不用。房屋建筑以及室内悬挂的字画条幅、摆放的花瓶器物,也都是中式的。人物出行乘坐的也不是汽车,而是马车和轿子。当然,《桃花泣血记》的本土化、民族化色彩,不止于此,还集中体现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上。
(一)题材内容的本土化
从剧情内容上来看,《桃花泣血记》讲述的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故事:富家少爷金德恩爱上了佃户陆起之女陆琳姑,遭到母亲金太太的反对。德恩与琳姑同居,琳姑怀孕。在金太太的强烈阻挠下,琳姑被父亲带回乡下,陆起也被金家解雇。琳姑生下女儿后,艰难度日,病情加重。德恩闻迅,赶来相会。琳姑握着德恩的手抱憾离世。德恩悔恨交加,把琳姑葬在桃林中,发誓终身不娶。金太太也被两人的真情打动,承认琳姑是金家儿媳,并到琳姑坟前祭拜。
影片剧情若用一句话归纳就是,一对彼此相爱的青年男女因门第差异和男方母亲的反对而阴阳两隔的悲剧。这样的剧情,与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刘兰芝的不幸颇为相似,也与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悲剧有异曲同工之妙。影片遵循中国传统伦理道德逻辑,把琳姑和德恩在门第观念与家长阻挠下有情人不能成为眷属的故事讲得缠绵悱恻、哀感顽艳。在故事讲述上,《桃花泣血记》也比较偏重传统叙事。例如影片开头的字幕用六句七言诗:“胭脂鲜艳何相类,花之颜色人之泪。若将人泪比桃花,泪自长流花自媚。泪眼观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来暗指核心内容,就带有古典章回小说的味道。有论者认为,《桃花泣血记》与鸳鸯蝴蝶派文学和电影有一脉相承之处,“鸳鸯蝴蝶派的影响则体现在这个故事里注入的写实性和悲情基调……就文学的戏剧性和悲剧性而言,《桃花泣血记》具备‘影戏’和鸳鸯蝴蝶派的大部分共性,采用的是鸳鸯蝴蝶派最流行的‘伤感—情欲’模式”。[3]故事内容和叙事模式上与鸳鸯蝴蝶派的相似性,正是《桃花泣血记》本土化特征的体现。
(二)表现手法的本土化
在表现手法上,《桃花泣血记》最值得称道的是,把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古典诗歌中的“比兴”手法,创造性地运用于电影当中。《周礼·春官》云:“大师(乐官)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从《诗经》起,赋、比、兴就是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诗歌的三种常用创作手法。“赋一般指叙述、排比,相当于排比的修辞手法;比一般是比喻、对比的修辞手法;兴则是指托物兴起,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是诗人抒发感情的重要手段。”[4]《诗经·桃夭》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就是典型的“比兴”手法。《桃花泣血记》化用了《诗经·桃夭》中的“比兴”手法,用“桃花”比拟女主人公琳姑,影片开头便以字幕“泪干春尽花憔悴”奠定了全片的悲剧基调,用“春尽花残”喻示女主人公红颜薄命的悲惨结局。在临近结尾时,又出现了“昔日红花叶绿,今天枝折根枯”的字幕,将琳姑昔日的美丽容颜与现今贫病交加的情状进行对比,暗喻琳姑将不久于人世,如桃花般凋零。
《桃花泣血记》“比兴”手法的运用,并不限于字幕,而是把桃花、桃树、桃林等视觉意象与剧情发展密切地交织在一起,使“桃花泣血”成为琳姑不幸爱情悲剧的隐喻。在影片开端部分,陆起用牛车载着妻子和婴儿琳姑一起回家,途中经过一片桃花灿烂的桃林,陆起折了一枝桃花,正在哭闹的婴儿琳姑见到桃花就停止了哭泣。影片通过这样的情节,建构起琳姑和桃花之间的有意味联系,既表明她喜爱桃花,也隐喻她是桃花的化身。到家后,陆妻把桃枝种在院中,五年之后,桃枝长成了一棵小桃树。陆妻把一根红布条绑在小桃树上,教导幼年琳姑:“这株桃树和你很有关系,你将来做人做得好,它开的花必定鲜艳,倘是不学好,那末……”再次强调琳姑与桃树、桃花的关系。成年琳姑出场时,是坐在院中的桃树下面纺线,美丽的桃花与琳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纯朴农家女孩形象相互映衬,达到“人面桃花相映红”的艺术效果,并以桃花的含苞待放,比喻琳姑情窦初开的豆蔻年华,为琳姑和德恩的相恋做铺垫。当成年琳姑和德恩同游桃林时,影片以烂漫璀璨的桃花衬托两人情投意合的喜悦。琳姑与德恩一起逛庙会时,手里也拿着一枝桃花,这个小细节喻示了琳姑与桃花同生共荣、不可分离。琳姑随德恩进城后,桃花的画面便不再出现,说明琳姑的命运正在一步步走向悲剧。当桃树再次出现时,琳姑已被迫离开德恩,父亲也被金家解雇,即将搬离乡下原来的住处,琳姑拿着锄头,两眼含泪,要把自幼种在院子里的桃树挖出来。后来琳姑为生计所迫,不得已去找刘裕泰借钱,路过桃林,眼前桃花灿烂如昔,但早已物是人非,琳姑折了一枝桃花拿在手中,想起幼时母亲的教诲,悲愤交加,伤心欲绝,她将花枝折断,片片花瓣与泪水一起落在地上。这一幕不仅与前面部分构成了照应,而且桃花枝断花残的画面也暗示琳姑终将撒手人寰。影片中最后一次出现桃花时,德恩抱着孩子,与陆起、金太太一起去琳姑坟前祭拜,琳姑长眠于桃林之中,灿烂的桃花象征着她美丽却短暂的青春芳华,让人不由得心生唏嘘。正如有论者所说,“这种通过影像元素造成的以景生情、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诗意境界,在整个中国电影史上都是非常难得一见的景观”。[5]《桃花泣血记》对“比兴”手法的创造性运用,不仅把中国电影的本土化、民族化表现手法向前推进了一步,营造出韵味悠长的意境之美,而且也赋予了影片新的质素,从而与“旧派”的鸳鸯蝴蝶派电影区别了开来。
除了“比兴”手法的运用外,《桃花泣血记》的镜头运用也很有特点。例如影片开场的第一个镜头是牧人们在草地上放牧牛群的大全景镜头,气度恢弘;接着是牧人头领走来走去的中景镜头;再接着是陆起在自家屋外等待的中景镜头,通过房门可以看到产婆正在给刚出生的琳姑洗澡;再接下来是陆起喜悦、焦急、紧张的近景镜头;随后是牧人们觉察到险情的俯拍大远景;接着是表现劫牛贼在山岗聚集的仰拍远景镜头,镜头移动中,群贼由首脑带领着冲下山岗。在开场短短几十秒的时间里,镜头景别、角度的变化还是比较丰富的。琳姑与德恩畅游桃花林时,影片用了一个俯拍的横移长镜头表现桃花盛放的美景,镜头运动流畅自然。当琳姑得知金太太并未同意两人的婚事时,她怒斥德恩欺骗自己,影片用了一个纵深镜头表现琳姑离去前的伤心、愤怒、痛苦。《桃花泣血记》对交叉剪辑的运用也比较娴熟,当琳姑随父亲回乡后,影片使用交叉剪辑,一方面表现琳姑一家窘迫的生活状况,另一方面表现德恩被母亲关在家中不能外出的情形;琳姑临终前,影片再次使用交叉剪辑,把琳姑挣扎呼唤的场景与德恩闻迅赶来、在路上奔跑跌倒的画面交叉并置,营造出一种扣人心弦的紧张节奏和哀情效果。可以说,《桃花泣血记》以匠心独运的表现手法,形成了“清新、唯美、灵动、飞逸、于朴实中见奇的影像风格”。[6]
如上所述,在联华公司“国片复兴”运动中,《桃花泣血记》在剧情内容、叙事模式、表现手法上,均体现出本土化、民族化的努力,其中融入的“悲情、凄美”等中国传统审美内涵,符合当时市民观众的审美接受心理,使其在观看过程中不知不觉受到感动,产生情感共鸣。这是《桃花泣血记》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争取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启蒙新声
与《孔雀东南飞》、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相似,《桃花泣血记》也是悲剧性的。不过,影片通过琳姑与德恩的爱情悲剧,发出了“现代启蒙”的新声。
康德指出,“启蒙就是人们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7]有学者对此加以阐释,认为“‘启蒙’精神,乃是‘理性’精神,‘自己’精神,‘自由’精神,乃是‘摆脱’‘外在’支配,‘自己’当家做主的‘自主’精神”。[8]
可见,启蒙很大程度上是要以理性精神反对以往传统中愚昧、落后的东西,使人们从种种不合理的束缚、压制中挣脱出来,获得人的觉醒、独立、自由。
爱情婚姻的不自由,是人身不自由的突出表现。因此,争取爱情自由、婚姻自主,反对门第观念、父母之命对爱情婚姻的干涉,既是中国现代启蒙的重要内容,也是女性解放的重要内容。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谈到封建家长对子女婚姻的干涉和支配情况:“婚姻通常很早就定下了,而且由父母决定,不用得到当事男女双方的同意,或者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贞操是女子单方面必要的道德。伦理上的‘节’和‘孝’被视为社会中牢不可破的铁律……儿子若反对并且拒绝跟父母代为选定的女子结婚,就要被看成不孝或非常不道德,会被社会蔑视,而且被取消继承家产的权利。”[9]“作为思想启蒙运动的‘五四’本身,闪出思想解放的理性之光”“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反抗专制的家庭制度和伦理教条,批判不合理的旧式婚姻观念以及旧礼教对女性的压抑、束缚和戕害,争取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例如许地山的早期代表作《命命鸟》就“提出了追求婚姻自由与封建专制矛盾这一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封建家庭扼杀青年爱情的罪恶,写出青年的叛逆反抗”,[10]受到当时年轻读者的欢迎。
《桃花泣血记》反对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批判家长对子女婚姻的蛮横干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有一定契合之处。影片拍摄时,距“五四”运动已有十多年时间,尽管电影界顾及旧市民观众的欣赏趣味,影片主题表达上偏于保守,但“五四”的新风已多多少少吹拂到电影界,新的思想、观念已在潜移默化地产生影响。因此,《桃花泣血记》传达出的某些现代思想,与同类古典文学作品以及鸳鸯蝴蝶派电影相比已有所不同。在古代一些表达渴望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中,当爱情受到门第观念、家长干涉等强大外力的阻挠时,男女双方往往只能被动地接受不幸的命运,或者以死殉情,或者借助超自然的力量来实现在一起的愿望,如《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与焦仲卿自杀后化为连理枝和鸳鸯鸟,梁祝二人死后化蝶,牛郎织女靠喜鹊搭桥相会等。而《桃花泣血记》中的男女主人公在对待爱情上有着更明显的主动性,在遭遇阻碍时,也流露出更强烈的反抗性。这种主动性和反抗性在以往同类文艺作品中较为罕见,显然是现代启蒙思想影响下出现的新质素。
影片中的女主人公琳姑,与成年德恩相遇之后,彼此一见倾心。虽然一开始琳姑因自己的乡下人身份而感到自卑和疑虑,但在德恩的爱情誓言之下,义无反顾地与他走到了一起,表现出女性面对爱情的勇敢与主动。琳姑的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德恩未婚同居。琳姑因与德恩彼此相爱而同居,不顾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顾传统礼教世俗观念,表现出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和掌控权。二是对刘裕泰的拒绝。琳姑在去找刘裕泰借钱(一种变相的钱色交易)的路上幡然醒悟,奔回家中。她宁肯贫病交加,抱憾而逝,也不出卖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反映出女性的自尊自爱和人格的纯洁。当金太太拒不同意德恩与琳姑结婚时,琳姑怒斥德恩,也体现出她反抗性的一面。琳姑身上的自主性、反抗性等新质素并不突兀,影片中有两处表明了现代文明对乡村的浸润,一处是德恩用照相机给琳姑拍照,另一处是庙会上放映西洋幻灯片。这说明中国的乡村已开始接触到新生事物和现代文明之风,琳姑身上所具备的现代新质素是有一定现实基础的。
片中的成年德恩显然是受过新式教育的“五四”一代,他会使用照相机(现代文明的象征物),主张恋爱自由,在对待爱情上有很强的主动性。他厌恶城市女子“脂粉的美”,喜爱乡间女子不施粉黛的“纯洁的美”,他不顾门第差异和母亲反对,勇敢地追求琳姑,愿意与她终身厮守,反映出“五四”之后新青年们在爱情上的坚决态度。当两人被金太太强行拆散后,德恩长时间被困家中,固然有其软弱的一面,但他对琳姑的爱情没有丝毫动摇,并抵御住了“美人计”的轮番轰炸。而且德恩的软弱与他背负的道德感有很大关系。从影片剧情中可以看出,德恩自幼丧父,是母亲金太太把他抚养成人,母亲金太太肩负了父亲和母亲的双重角色。因而对德恩来说,他与金太太之间除了母子感情外,还多了一份对母亲的感激之情,这种感激使他背负上了道德重担,不到万不得已,他绝不可能违背母亲的意愿,否则就是忤逆不孝、忘恩负义。而金太太也屡次利用这一点对德恩进行道德绑架,阻止他去见琳姑。后来,当德恩得知琳姑病重垂危的消息,他终于冲破道德枷锁和封建家庭的束缚,把金太太推倒在椅子上,宣称“我从此自由了”,然后夺门而出。影片结尾,琳姑去世后,德恩又给金太太写信,要求母亲认可琳姑的儿媳身份,否则便永不归家,从而迫使金太太做出妥协和让步。德恩敢于同旧式家庭决裂、同专制家长抗争的勇气和行为,充分体现出他对封建专制家庭和旧的道德标准的反抗精神,“在旧市民电影对道德要求非常严格的家庭伦理层面出现了反伦理的暴力倾向”,[11]是带有“五四”个性解放的现代新质的。
正因为《桃花泣血记》批判了封建门第观念、父母包办婚姻对自由爱情的压抑与破坏,发出了为女性争取爱情、婚姻自主和个体解放的启蒙新声,所以在当时就赢得了一片赞誉。有论者称赞说,《桃花泣血记》是一部“纯以中国人的理性写成中国式的悲剧”,[12]“《桃花泣血记》的剧情,是打破阶级观念的恋爱,和门当户对的陋习,全局以乡村作背景,是一部完全中国色彩的佳构”。[13]
有意思的是,联华公司老板、同时也是担任《桃花泣血记》监制的罗明佑,对影片中德恩与琳姑的自由恋爱、未婚同居,持反对态度。他在《〈桃花泣血记〉弁言》中说:“时代之演进愈甚,则男女之界愈泯,然无论如何,必不及于乱。故曰,始乱而终成,犹非贤者所为,况终弃之耶!”“或曰,不成者,非男之无情也,家庭之顽固也,是须打倒。诚然。然家庭之顽固,阻力也,先阻力之不除,而求其所大欲,非舍本而逐末而何?其有后灾,固意中事,谓之自取可也。……巨创深痛,或足以振寝衰之万一也。”[2]在罗明佑看来,影片中德恩与琳姑在没有征得父母同意之前就未婚同居,是违背道德礼法的“乱”,因此后来一个“悲痛惨亡”,一个“终天报恨”,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是二人咎由自取。罗明佑认为影片中琳姑德恩爱情悲剧的意义在于令人警醒、引以为戒,有助于改变当时世风日下、道德寝衰的弊病。显然地,罗明佑是站在传统道德的立场上解读《桃花泣血记》的,以致于把琳姑德恩的自由恋爱悲剧视为不足效法的反面教训,将其贬低为悖礼出格的行为,而未能看到影片中所蕴含的启蒙新质,这也反映出罗明佑思想上的保守性。
四、左翼阶级意识的初显
《桃花泣血记》另一值得注意之处,是片中流露出贫富阶级对立的左翼思想萌芽。不同于当时一些表现“城乡二元对立”的影片,《桃花泣血记》没有通过城乡之间的差异对比来批判城市、褒扬乡村,而是把城乡差异与贫富差别联系起来,侧重表现不同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初步显现出同情底层民众的进步阶级意识。
20世纪20年代涉及城乡关系的影片,往往把城市表现为引人堕落的罪恶之地,而把乡村建构为民风淳朴、少欲知足的道德净土。例如1925年但杜宇执导的《重返故乡》,以及同年由张石川导演、郑正秋编剧的《上海一妇人》,都是通过乡下女性进城后受到欺骗、引诱而堕落,后来又幡然悔悟,离开城市重返乡村的故事,来批判城市的腐朽丑恶、骄奢淫逸,“每能变更人之生活,破坏人之佳偶”。[15]1927年侯曜编导的《海角诗人》,则通过“城里人下乡”的故事,同样表达了批判城市、褒扬乡村的主题。片中主人公孟一萍厌倦城市的喧嚣浮华,到海岛渔村隐居,他拒绝了城市女子尹美珍的追求,爱上了乡下姑娘柳翠影。在该片中,城市是蝇营狗苟、尔虞我诈之地,严重摧残人性;而乡村风光优美、质朴淡泊,能够让人身心舒展。在这些影片中,“城乡二元对立”的差异关系是很明显的,城市被表现为繁华堕落的负面形象,在道德上受到谴责,而乡村作为城市的对立面,被塑造成景色秀丽、善良和谐的理想诗意田园。
《桃花泣血记》的故事也是以乡村和城市为背景的,不过,与上述影片不同的是,《桃花泣血记》把以往影片对乡村的想象性诗意建构引向了社会现实层面。《桃花泣血记》虽然也表现了乡村平静恬淡的生活场景和优美秀丽的自然景色,如青草如茵的牧场,灼灼其华的桃花,绿树成荫的村落,长满庄稼的农田,蜿蜒曲折的小路……但是,影片并没有把乡村呈现为和谐宁静的世外桃源,乡村不仅有结伙抢劫的偷牛贼、为富不仁贪花好色的劣绅,而且也是故事悲剧的发生地。在表现城市时,《桃花泣血记》并没有像以往同类影片那样,聚焦于熙熙攘攘的城市街道或商品琳琅满目的百货公司等都市繁华景象,以此突出城市的喧嚣浮华、引人堕落,而只是围绕金公馆和德恩琳姑居住的房屋两处地方展开故事,片中的城市生活场景看起来甚至没有乡村庙会热闹。另外,尽管《桃花泣血记》像《海角诗人》一样,塑造了纯洁善良、美丽可爱的乡村女性形象琳姑,让她的健康、自然、淳朴气质对来自城市的男性德恩产生强烈吸引,令其发出“这是多么纯洁的美啊!在城里哪里找寻出来”的赞叹,并且让德恩像孟一萍那样拒绝了城市女子周娟娟,一心一意爱着琳姑。然而,与《海角诗人》中孟一萍和柳翠影“有情人终成眷属”不同,《桃花泣血记》没有给琳姑德恩安排下幸福美好的结局,而是让他们一个红颜早逝,一个抱恨终身,进而引发观众思索琳姑德恩爱情悲剧的原因。由此可见,《桃花泣血记》的重心,已从批判城市之恶转移,指向批判阶级差异和贫富差距,隐约勾勒出一条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的叙事线索。
影片开头部分表现幼年琳姑和德恩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亲密友谊时,用字幕含蓄地表达了对森严的阶级、等级观念的不满。接着幼年德恩在与乡间儿童玩打泥仗游戏时,被母亲金太太强行拉走,暗示出金太太根深蒂固的阶级、身份观念,也委婉地透露出,随着时间的推移,阶级差异将成为阻挠琳姑与德恩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后来剧情的发展印证了这一点,当成年琳姑与德恩彼此相爱、感情日增、形影不离时,金太太嫌弃琳姑是乡下佃户人家的出身,斥其为下流女子,命令德恩将琳姑送走。当陆起得知琳姑与德恩同居的事情,要求金太太同意二人结婚时,金太太当面说陆起父女不配与自家攀亲,提出赔钱了事,还蛮不讲理地辞退了看管牛场的陆起,流露出对穷人阶层毫不掩饰的鄙视。金太太之所以坚决反对德恩与琳姑结婚,正是由于两人出身于不同阶级和门第。可以说,阶级差异、门第差别、贫富悬殊,是造成琳姑德恩爱情悲剧的根本原因。影片通过这一悲剧,批判了阶级差异和贫富差距的不合理社会现实,以及以金太太为代表的富人阶层的趾高气扬、自私傲慢。
《桃花泣血记》中的阶级压迫和不平等,不仅表现在城市富人与乡村穷人之间,也表现在乡间地主富绅对穷人的欺压上。例如富绅刘裕泰垂涎琳姑美色,趁陆起被金家辞退后眼睛受伤瞎掉、一家人生计无着之际,落井下石,让房东王氏从中说合,假装好心要借钱给琳姑,实际上隐藏着占有琳姑的阴暗目的。刘裕泰的包藏祸心、卑鄙无耻,对陷入窘境的琳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令其本已受伤的心灵又蒙上了一层阴影,身心遭到又一重打击,再加上生活艰难,琳姑最终一病不起,撒手人寰。通过这一情节,影片表达了对乡村为富不仁的地主富绅阶层的批判。
影片还表现了以陆起为代表的底层穷人身上朴实、正直、善良的美好品质。金太太和成年德恩下乡视察完毕,临离开时,陆起夫妇手提活鸡鲜鱼前来送行,体现出乡下人待客的热情大方、周全厚道;陆起进城寻找琳姑,看到女儿穿着旗袍、高跟鞋,非常生气,责令她换回原来的衣服,表现出他对自己乡下人阶级身份的朴素本分的认知;当他得知琳姑与德恩同居,去找金太太讲理,要求德恩娶琳姑,以争得应有的平等权利时,金太太却提出赔钱解决问题,陆起愤怒地说:“谁要你的臭钱!”金太太恼羞成怒,解聘陆起,陆起毫不畏惧地说道:“你这老不讲理的东西,谁愿吃你的饭。”上述情节,充分刻画出陆起贫穷而不失人格尊严的正直形象,面对蛮横的有钱阶级,陆起进行有理有据的抗争,没有丝毫卑躬屈膝之态。更难能可贵的是,即便在被金家辞退之后,陆起仍然见义勇为,去阻止偷牛贼的抢劫行为,坚持“宁可人家负我们,我们不要负人”,表现出底层民众善良质朴的美德。
与20世纪20年代表现城乡关系的影片相比,《桃花泣血记》由批判城市之恶,转向批判阶级差异和森严的等级观念;从建构乡村的道德优势转向建构底层民众的道德优势,并对傲慢自私、为富不仁的有钱阶层进行道德谴责;这些都与后来兴起的左翼电影比较接近。可以说,《桃花泣血记》中彰显出的进步阶级意识,已初步具备了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的某些特征。
五、结语
民族化色彩、现代启蒙思想、进步阶级意识等多重张力的相互扭结,使《桃花泣血记》成为20世纪30年代初期一个独特的电影文本。最明显的例子是影片结尾,德恩写信给母亲表示要彻底脱离专制家庭,迫使母亲接纳已故琳姑的儿媳身份,一家人和解团圆,到琳姑坟前祭拜。这一结尾,一方面体现出对传统民族化叙事的借鉴,能够起到抚慰市民观众情绪的作用,使他们在痛哭流涕的感情宣泄之后获得了心理上的安慰;另一方面,德恩、陆起与金太太的和解,构成了对启蒙思想和阶级意识的消解,降低了故事的悲剧色彩,削弱了影片的阶级批判锋芒。该结尾正是影片多重张力扭结的表现。总而言之,《桃花泣血记》是一部“新旧杂陈”的影片,带有20世纪20年代旧式市民电影向30年代新兴左翼电影过渡的痕迹。影片中隐含的现代启蒙思想和进步阶级意识,为卜万苍后来执导《三个摩登女性》《母性之光》《黄金时代》《凯歌》等左翼电影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