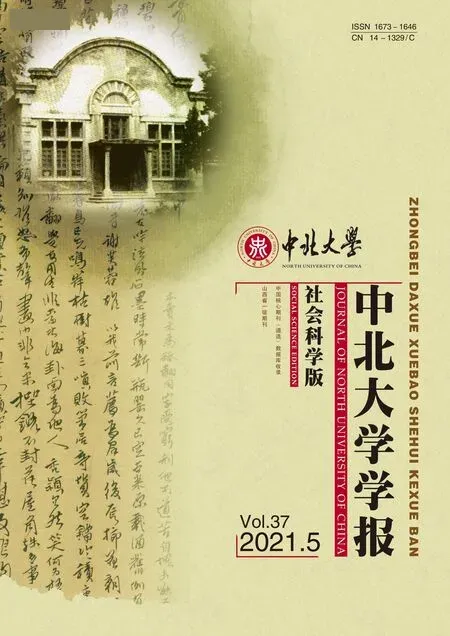论高适边塞诗听觉形象的生成及其文化内涵
王昕宇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作为盛唐边塞诗派代表人物,高适诗作数量众多,审美意蕴丰厚,常年戍边的切身体验,使其诗歌的听觉形象重于写实,甚至形成了一种基于声音而建构的“场”。在谢弗看来,作为时间与空间相统一的主体,声音在共时层面的场中形成了事件,声音事件的组合,最终形成了声音景观。在西方美学的认知范畴中,听觉通常被认为是与美联系最紧密的。玛克斯·德索指出:“当一个声音开始歌唱时,我们远没有听清其歌词与旋律便觉得已经深受感动了,有些音色会立即兴奋或和缓,使我们变得狂怒,或者又像微风一样轻抚我们。”[1]96这充分说明从声音到情感的转化,有着特定的传导路径,即由形象到情感,再到诗意表达。高诗中这一路径的运用,生动诠释了听觉形象的生成方式。一方面,声音的产生包含不同的内容,对接受者造成直观的听觉冲击,形成了一个个听觉事件;另一方面,特定的边塞环境,在时空的统一中形成了场域,听觉事件在边塞场域中不断组合,形成了高诗中独有的声音景观。最终,从形象到情感,生成的声音景观内化于作品,无论是人文之声、自然之声还是动物之声,都使读者感受诗境、体味诗情,进而与诗歌融为一体。
1 乐舞歌哭——以声寓情的人文之声
盛唐时期,胡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民生活,丰富多样的胡乐之声流入边塞诗的血脉。高适在异域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交流对话中进行创作,将满腔诗情投放于充满边疆色彩的战场之上。诗中的人文之声,表达了或慷慨豪迈、或哀怨不满、或批判反思的复杂情感,让边塞诗成为了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精神交汇的窗口。
在胜负分晓之前,声音总能先行触发感官。在营造大战的豪迈声势时,高适常常选用乐器金、鼓、角加以表现。作者由远及近、由弱渐强地描写乐器之声,刻画出战事紧张、兵马迫近、奋力厮杀的战场情境。视听结合的表现方式使得这种可转化为视觉形象的声音体验,无论深刻性还是感染力,都更胜一筹。另外,高诗常将乐器和兵器之声交汇描写,以展现战场的紧张局势。冷兵器的铿锵之声与乐器的奋起之声共同作用,充分强化了诗歌的表达效果。
“金”是钲、铙一类的军中金属乐器,行军敲击,指挥士卒行动,以壮行色。相较于其他乐器,更加厚重有力的“鼓”,常常用以演奏军乐。郭茂倩《乐府诗集》有:“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有鼓角者为横吹,用之军中,马上所奏者是也。”[2]309被誉为高适“第一大篇”的《燕歌行》中就有金鼓之声,“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3]97。全诗波澜起伏的场面描写,生动感人的形象塑造,洋溢着诗人强烈的爱国激情,彰显出雄浑悲壮的诗风。“摐”“伐”等动作都展示出敲击金、鼓爆发的强力。金鼓奏鸣震耳欲聋,直接反映出战场紧张刺激的场面,构建出一幅将士英勇无畏,辞家赴边,冲锋陷阵的图景。
“角”是古代常见的吹奏乐器。《晋书·乐志》云:“角,说者云,蚩尤氏帅魑魅与黄帝战于涿鹿,帝乃始命吹角为龙鸣以御之。其后魏武北征乌丸,越沙漠而军士思归,于是减为中鸣,而尤更悲矣。”[4]715经历次演变,角这种乐器被用做军号。在高诗中,角多用以强化战争形势。《送浑将军出塞》中的画角之声为:“城头画角三四声,匣里宝刀昼夜鸣。”[3]257战事一触即发,在听觉上首先用哀厉高亢的画角声铺垫了大战前的紧张态势。城头可以听到零星几点画角声,匣中的宝刀日夜鸣叫,想要挣脱出刀鞘浴血奋战。这一兀傲奇警的想象,从不同侧面刻画出浑将军骁勇善战的人物形象。故,赵熙批曰:“浑将军得此一诗,胜于史篇一传。”[3]258
边塞诗写战争,但不止于战争。兵戎相见,无可避免地造成生命的陨灭和亲人的分离。此情此景之下,羌笛、胡笳、刁斗等乐器多奏悲怆之音,以深化作者愤懑悲伤的情感。在做此类描写时,高适常直抒胸臆,不吝直接使用“怨”“愁”等情感词语,直截了当地表达对战争的辩证思考。
高诗中的“笛”,是盛唐与西北民族文化碰撞的产物。胡震亨《唐音癸签》有云:“笛有雅笛、羌笛。唐所尚,殆羌笛也……乃如《关山月》《折杨柳》《落梅花》,唐人咏吹笛多用之。”[5]以《金城北楼》为例:“垂竿已羡磻溪老,体道犹思塞上翁。为问边庭更何事,至今羌笛怨无穷。”[3]249苦苦追问战事如何,只闻得羌笛幽怨长鸣。羌笛本无怨,但是吹奏者心中饱含愁苦,自然奏出了怨声。笛声延展了情感留存的时间,也使得空间画面无限延伸。《和王七玉门关听吹笛》云:“胡人吹笛戍楼间,楼上萧条海月闲。借问落梅凡几曲,从风一夜满关山。”[3]347《梅花落》是汉乐府中二十八横吹曲之一,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历唐、宋、元、明、清数代一直流传不息。[6]982前两句描写实景,后两句描写乐声,虚实结合,丰富了艺术想象,绘制出一幅边地月夜风景图。《梅花落》寄寓的乡思随着一夜风吹,溢满关山。从无形到有形,笛声增强了表现力。月夜虽然平静,但思乡情感波动,动静结合,给予读者更加广阔的想象空间。
“胡笳”之声,据《乐府诗集》:“胡人思慕文姬,乃卷芦叶为吹笳,奏哀怨之音。”[2]860因胡笳声音悲凉,又名悲笳、哀笳。以高适《部落曲》为例:“蕃军傍塞游,代马喷风秋。老将垂金甲,阏支著锦裘。雕戈蒙豹尾,红旆插狼头。日暮天山下,鸣笳汉使愁。”[3]275“蕃军”“代马”都是典型的边塞风物,“雕戈”“豹尾”“红旆”等指代军旗,都用来渲染战事之频繁。“鸣笳汉使愁”,夕阳西下,敌人吹响了胡笳,声音悲凉。此处的听觉作为一种直接与情感建立联系的感觉,在胡笳声催发下,使边地战士心中郁结的凄恻愁苦之情倾泻而出。
白日“刁斗”用于烧饭,夜则击之报更,“刁斗”之声融合在士兵的战地生活中。“边庭绝刁斗,战地成渔樵。榆关夜不扃,塞口长萧萧。”[3]93刁斗声在寂静的边塞夜晚破空而来,打破寂静,越发衬托出环境的严酷。又如《燕歌行》中的刁斗声:“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3]97杀气如同乌云四面升腾,刁斗之声在凄冷的寒夜里使人惊颤,战场惊心动魄的场面通过视听结合的表现方法跃然纸上。“星河连塞络,刁斗兼山静。忆君霜露时,使我空引领。”[3]274霜华露重,星河低垂之时,本该一片寂寥,却闻刁斗时鸣,徒增万种惆怅。刁斗之声为动,而山势为静,一动一静,构成一幅苍茫壮阔的塞外关山图。
在宴乐之声衬托下,视死如归的战士与贪图享乐的将领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的抨击更加直露。《燕歌行》诗云:“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3]97“半死生”“犹歌舞”的鲜明对比,正说明战士以命相搏,奋不顾身,将领却昏聩无能,纵情声色。宴乐之声传达了作者的反思与深重批判。同样描写宴乐声的还有“降胡满蓟门,一一能射雕。军中多宴乐,马上何轻趫”[3]93。将骁勇善战的战士与昏聩无能的将领并举,通过对比体现出巨大反差。歌舞宴乐之声的感官刺激,更引起了读者愤恨情感的共鸣,在对比反衬中用讽刺的笔法进行不留情面的抨击。
高诗中交响着丰富的人文之声。无论是激扬豪迈的金声、鼓声、角声,悲怆悠长的笛声、笳声、刁斗声,还是军中腐败享乐的将领宴乐之声,凡此种种,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呈现出真实的人生百态,为盛唐诗歌提供了独特的审美经验。
2 更兼风雨——衬托人类强力的自然之声
高适边塞诗用形象化的方法表现自然之声,不仅展示了边疆风貌,同时,生动诠释了一切景语皆情语的“有我之境”,让情感的呼唤有了在诗语、诗境中实现的途径。正如钱锺书所说:“五蕴异趣而可同调,分床而亦通梦,此官所接,若与他官共,故声能具形。”[7]1464感官的联结,赋予自然之声具体形态,将其粗犷凌厉的总体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
“大漠风沙里,长城雨雪边。云端临碣石,波际隐朝鲜。夜壁冲高斗,寒空驻彩旃”[3]39便是高适眼中的边地自然百态。自然界的风雨不受时空限制,随时随地奏鸣,而花草树木之类,在自然风雨带动下发声,正所谓“草木之无声,风扰之鸣”[8]41。高诗塑造的自然声音呈现出生动、具体、鲜明的特征,在典型环境中让景语和情绪变化紧密联系。因此,他笔下的自然之景各自具有独特情状。
边风瑟瑟,“风声”总能烘托出战场寒冷凄恻的环境氛围。岑参笔下边塞的风是“九月天山风似刀,城南猎马缩寒毛”[9]460。边风似刀,带着刺骨寒意,令人瑟缩,易激发通感。关于风声的描写,高适诗中也很多见,《酬李少府》曰:“来雁无尽时,边风正骚屑。将从崖谷遁,且与沉浮绝。”[3]27“边风骚屑”,边地之风呼啸着,营造出惨烈的战场景象,生命在战争面前显得愈发渺小。同为边塞风声,也可以衬托出壮阔磅礴的情感。《同吕判官从哥舒大夫破洪济城回登积石军多福七级浮图》描写为“高兴殊未平,凉风飒然至。拔城阵云合,转旆胡星坠”[3]267。诗中描绘出作者登塔望远时的开阔景象,迎飒飒“凉风”而开襟,兴致更高。风声刺激着感官,凉风起处,战士神勇攻破城池,大战的场面波澜壮阔,气吞山河。虽有登塔之乐,但在飒然风中,更感胜利之喜。《东平路作三首》作“索索凉风动,行行秋水深”[3]152。诗歌所说的东行并非本愿,而是在有志难伸,进退失据之时,更兼秋风、秋水,作者的悲秋之情已然不堪忍受。索索凉风,摇动的不仅是秋天的凋零伤逝之感,更是听者心中的悲切苦闷之思。此情此景,正如别林斯基所说:“诗歌不能容忍无形体的,光秃秃的抽象概念,抽象概念必须体现在生动而美妙的形象中,思想渗透形象。”[10]249
“落雨飞雪”的声音,亦是自然界最常见的气象之声。边塞苦寒,大风之外,更有雨雪。由于听者的处境不同,面对雨雪之景,其苦乐之感自然有别。比起其它物象,雨雪极具动态的线条感。因此,也带来了更为强烈的视听冲击。
骤雨与大雪以其彪悍的声势,可以瞬间充斥人的视野与听觉,给本就艰辛的战事平添更多阻挠。“朝瞻授钺去,时听偃戈旋。大漠风沙里,长城雨雪边。”[3]39授钺于将,承领兵之任,放倒戈矛,得战争凯旋,是一派男儿豪迈之气。渲染自然风雪的强大威慑背后,更反衬出战士征服自然,一往无前的神勇气概。“近关多雨雪,出塞有风尘,长策须当用,男儿莫顾身。”[3]339以边关风雪,塞外苦寒,点明从军生活的艰难,却仍是劝勉友人时刻怀揣为国家建功立业、不畏个人生死的志向。将景物、行动、豪情相互交汇,使雨雪之声传达出豪迈无畏的情感。
高诗中战地的“泉声”从细处着笔,亦有不同。《金城北楼》中有泉流声:“北楼西望满晴空,积水连山胜画中。湍上急流声若箭,城头残月势如弓。”[3]249寥寥几句写出作者登上金城兰州的城楼,眼见一弯新月高悬在城头,听到近处的水流声势如离弦之箭,飞速奔流。这两句诗视听结合,将边地的战争气息融入自然景色的描写之中,有声有色,让读者感受到塞外边城的特有气氛。《使青夷军入居庸三首》云:“溪冷泉声苦,山空木叶干。莫言关塞极,云雪尚漫漫。”[3]219描写的是高适送兵青夷军回来,途径居庸关时的场面。孤寂寒冷,道路难行。西北地区的自然地理落差造就了尖锐凄厉的泉声和苦寒的环境。泉水“哗哗”作响似因严寒而呜咽。泉声呜咽,行者心苦,此处的通感手法使得行路的艰难和气候的寒冷,与内心的凄凉苦涩叠加起来。奇特险峻的自然景观与生动形象的声音表达结合,在边塞诗歌创作中具有无与伦比的独特性。
《文心雕龙·物色》曰:“诗人感物,联累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11]249古代诗人正是将眼中所见的自然之景与听觉之声联动,才产生了丰富的情感。高诗中异域风光随处可见,“像常见的陇水鸣咽、大漠黄沙、胡霜塞鸿、风卷百草、关山孤月、玉关辽海、云天低垂、天山飞雪……充分展示了广阔而立体的生活画卷,构建了雄奇瑰丽、粗犷浑厚的意境,洋溢着热情、新奇与野性,充斥着浪漫主义的乐观精神”[12]952。高适能够正视苦寒的边塞环境,发掘其中的美感,获得审美体验,正是因为他始终怀有对祖国壮美河山的深沉热爱,对人生意义的不断追寻。自然之声化入作者之口,在保卫国家的战争中体现着披荆斩棘、奋勇开拓的现实主义精神,既是盛唐气概的集中展示,也是热情自由、大胆豪迈的民族风度的生动表征。
诗人对边塞自然之声的感知过程,呈现了人类在面对自然时将情感由惧怕、惶恐转化为主观能动的审美,弘扬了强大的生命力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实现了对自然的驾驭与征服。其背后的乐观主义信念,是盛唐时期独特的精神品质,也促使唐代诗歌不断扩大自身的审美张力。
3 雁鸣马嘶——寄托主观感受的动物之声
走进高适的边塞诗,可以听闻旅雁悲鸣、夜深鸟啼、战马嘶鸣等动物之声,它们共同组成了庞大的动物听觉意象群,伴随着征人羁旅,无时无刻不在刺激着情感的生发,并成为其寄托,为战争这一特定文化背景提供了不同寻常的审美视角。
高诗中的飞禽类动物自由飞行,带来了视点的移动与空间的转换,造成情感波动,形成今昔之间的强烈对比。鸿雁迁徙,岁月无常,时间在异乡的战场上转瞬即逝,常引发战士的怀念故乡之情与羁旅伤感之绪。高诗中的鸟鸣声多出现在黄昏与夜晚时分,这也体现出这类听觉形象的活跃性。声音诉诸听觉,不再受夜晚光线的限制。昼夜鸟鸣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听感,夜间的鸣声不眠不休、急切纷乱,使人悲痛忧郁,难以入眠。《宋中送族侄式颜》中有“旅雁悲啾啾,朝昏孰云已”[3]102。时值大夫张守珪贬括州,使人召式颜。式颜此去适逢其志,但路远艰苦,虽然有张守珪提携,高适仍表现出了担忧的思绪。听闻北归的雁群在天空中发出悲鸣之声,难免触景生情。舍生取义,厮杀奋战,所取得赫赫战功以多少家破人亡的悲剧为代价。旅雁悲鸣,更悲战争中人的生命之脆弱,分离之悲痛。“荡子从军事征战,蛾眉婵娟守空闺。独宿自然堪下泪,况复时闻鸟夜啼。”[3]269将士在边地从军征战,只剩思妇独守闺中。凄清孤寂的夜晚,她们泪流不止,黯然神伤。更何况在这样的氛围中又传来了鸟啼声。鸟啼无意,听者有心。分隔两地的思念之情,全都被深夜的鸟鸣激发出来。鸟儿尚且能成双成对,可是家人不能团圆,声音显得越发悲切。
高适笔下的边塞征战不休,咏鸟、写鸟鸣声更多表现出因为战争分离丧生的悲惨境遇,或去国怀乡的无可奈何。所以,他笔下的鸟鸣声寄托遥深,有时讽时刺世,锋芒毕露。
唐代疆域辽阔,战场上的马,是常见的军备资源。《新唐书》曰:“马者,国之武备,天去其备,国将危亡。”[13]77马背征战的习武风尚、积极入幕的从军热情,都在骏马嘶空,刀光剑影中构成一幅幅雄浑激荡、动人心魄的征战图景。马嘶鸣声便是在战场上烘托氛围、呼应情感的重要媒介,或表现人马所处的恶劣环境,或表现人马奔行速度之快,或表现人马行程之远等,虽然落脚点在不同侧面,但都借战马之声,表现内心的追求与反思。
驱马远行,长路漫漫,战事未可知,更添离人愁。在送别友人情境下的马鸣声是“征马向边州,萧萧嘶不休。思深应带别,声断为兼秋”[3]336。此处的“萧萧”马嘶,表达兼秋、久别的感情。《唐诗解》中有“马向朔风哀嘶不息,其思幽深,以带别为然,声更凄绝,为兼秋更甚”[3]170。身世、家国之悲,藉由动物之声传达,更添愁绪。“更沽淇上酒,还泛驿前舟。为惜故人去,复怜嘶马愁。”[3]170此诗描写了高适送别魏八前往边地时的不舍之情,亦是告诫朋友若无知己,也不可明珠暗投。此处的马嘶声表达对朋友情感寄托的同时,也是作者渴望施展才华的自我劝慰。“征马嘶长路,离人挹佩刀。客来东道远,归去北风高”[3]338中“马嘶长路”“人挹佩刀”这两个生动传神的场面展现出高适和友人送别时的不舍。即将前往战场,东道远,北风高,征途遥远,时令苦寒,伤别、思乡之情更加强烈。征马亦感到前行路远,却不畏艰险,使得诗情豪迈高远。
马声哀厉,表现出了战场环境的艰苦。《自蓟北归》中“驱马蓟门北,北风边马哀。苍茫远山口,豁达胡天开”[3]46。作者描写了南行路途中看到的悲凉景象,着眼于边塞寒风与马嘶的描写。第一句运用顶针的辞格,在声律上十分连贯。北风呼啸,马鸣声哀,相互映衬下,这种悲苦艰难的气氛更加显著。环境的恶劣已经是切身可感,无可驱散,此时交错的声音里有作者主观推测出的“边马”之哀,更有“驱马”人感同身受的“哀”。两者互相感染叠加,让苦寒之感更加无法排遣。时值高适从蓟北南归的冬季,回想起疆场上的惨痛兵败,心有不满但无济于事,故作此诗。声音触发感知,虽时过境迁,仍能使人在脑海中进行场景重构,让情感不断延续。
大气磅礴的盛唐气象,开放包容的文化环境,培养出时人渴望建立功业、开疆拓土的价值追求。战马具有任劳任怨的精神品质,带着出征的将士奔赴边疆,也成为了他们的精神寄托。高诗中“行子对飞蓬,金鞭指铁骢。离魂莫惆怅,看取宝刀雄”[3]341。以马言志,骏马奔赴战场,建功立业的战斗激情跃然纸上,呼应着时代基调,其状其貌,其才其德,无所不备。
同为马鸣声,高诗中有“故交在梁宋,游方出庭户。匹马鸣朔风,一身济河浒”[3]60。“匹马鸣朔风”表现出战马面对着呼啸的北风嘶鸣,一心想要冲破禁锢披荆斩棘,是战士勇往直前的精神表现。同一时期的盛唐诗人写诗咏马,赞颂马的英勇无畏,亦是抒写自己的怀抱,是自己乐观豪迈精神的真实写照。高诗中无惧风雪、勇往直前的“马”,象征着他豪情万丈、意气风发的人格形象。高诗中马嘶形象的生成正是其现实主义倾向的典型表达。是故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评价高适:“事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自远。然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14]15盛唐帝国的风貌塑造了高适“雄浑悲壮”的诗风。其人其诗率直浩方,渴求建立功勋的心态,也决定了他直抒胸臆,尚质主理的动物之声的表现基调。
古往今来的古典诗词研究,多在其“色”,往往忽视其“声”。在边塞诗中,通过声音形象表现其画面性,更能凸显诗词的美感特质。高诗中的丰富听觉形象,强化了艺术感知效果,增添了文化的多元化色彩,创造出不同寻常的边塞之美。故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评价高适为“七言古中时带整句,局势方不散漫。若李、杜风雨纷飞,鱼龙百变,又不可以一格论”[15]161。高适诗中运用听觉形象表达情感时的真情激荡,既是其“立节贞峻,植躬高朗”“负气敢言”性格的真实呈现,又与其“自然沉郁”的语言艺术一脉相承,对后人的抒情方式和语言风格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