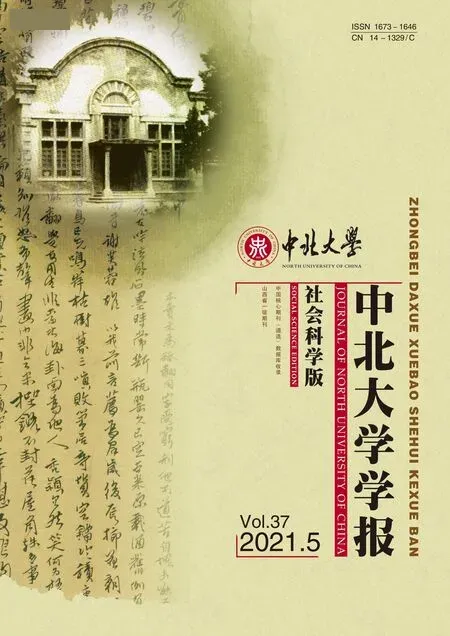杨丘文《柳溪玄心寺洙公壁记》考论
——兼谈辽代儒学之发展水平及特征
魏崇武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在辽代儒学研究领域,20世纪90年代诞生过若干重要成果,其中以孟广耀先生的论文集《儒家文化——辽皇朝之魂》最具代表性。该书分别探讨了辽朝的基本国策、儒化过程、儒士群体、伦理观、华夷观、政治观等,较为全面和深入。[1]此外,还有些学者探讨辽代儒学的发展阶段,分析其对辽代政治、教育、习俗、信仰等方面的影响及作用等,亦颇具参考价值。(1)主要有武玉环《辽代儒学的发展及其历史作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5期);黄凤岐《论辽朝的教育与科举》(《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4期);顾宏义《辽代儒学传播与教育的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等。然而,将近30年过去,后续研究却并不多见,尤其是缺乏有分量的成果,这可能主要受限于辽代文献之匮乏。因此,如何在有限的材料中继续努力发掘、充分利用,是辽代儒学研究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杨丘文《柳溪玄心寺洙公壁记》(以下简称《壁记》)一文,对我们了解辽代儒学之水平及特征就很有价值,值得重视。
虽早有学者指出《壁记》是现存辽代文论中“唯一最长和具有形而上性质的一篇”(2)陈应鸾:《杨丘文的文道理论初探——兼论辽朝文论之特征》,《中外文化与文论》第6辑,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85页-200页(按,以下凡引用此文,只注页码)。后收入氏著《中国古代文论与文献探微》(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一书。[2]185,其后又陆续有若干论文论著约略涉及《壁记》(3)就笔者所知而言,其中探讨相对详细的主要有:张国庆《相契与互融:辽代佛儒关系探论——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浙江学刊》2014年第5期,第33-39页);黄震云《辽代文学史》第三章相关内容(长春:长春出版社,2010年)等。,但这些成果普遍对杨丘文的生平资料缺乏关注,对其儒学思想及文论的具体阐释均似有值得商榷之处(4)如陈应鸾文说“杨丘文所谓的‘智’,恰恰正是佛教所谓‘智慧’‘智度’之义”“‘仁智’为道,实际上是儒释合一之道”(第188页),将“智”全部归于佛教;张国庆文说“在该石刻文篇首,杨丘文首先就儒之‘仁’‘智’与佛之‘性情’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一番理论阐述”(第36页),则以“性情”全归于佛,以“仁”“智”全归于儒。二文似均与《壁记》原意不符。不过,本文重点不在于与前贤商榷,故仅在此略加提及。,且未能揭示《壁记》对于我们认识辽代儒学水平及特征的价值,因此,笔者不揣浅陋,试作以下探讨。
1 杨丘文与释了洙
现存有关杨丘文的资料很少。1991年在北京房山区石楼镇石楼村西杨氏家族墓地出土的《大金故奉议签事杨公神道碑》,其中略有涉及:
及五代之初,始籍真定之稾城,□□者,实公(笔者按,指杨瀛)之九世祖也。后唐清泰中,以功授银青光禄大夫、定州兵马指挥使。晋少帝入辽,迁而北之,遂赐田□于兴城,仍世袭临海军节度副使。银青昆季三人,辽忌其枝叶浸大,分置临潢、平卢、辽东,公临潢之胤也。高祖□福。曾祖永,赠朝列大夫。朝列三子皆业进士,尝曰:“吾家久衰,是三子者,必能复大吾门。”乃目以“黄金三柱”,时号□“三台”。伯讳丘文,乾文阁直学士、中书舍人,世以“紫微”称之;仲讳丘行,通奉大夫、太子左卫率府率;季讳丘忠,正□大夫、秘书少监。通奉公生四子,并清真拔俗,卓荦不群,竟能该赡学艺,依次擢巍科,时人语曰:“杨氏旧闻‘三台’,□□有‘四辅’矣。”[3]54
此神道碑为金朝人杨瀛而立。据碑文,杨瀛九世祖时,杨氏由后晋被迁入辽,先聚居于兴城(今属辽宁葫芦岛市),后分置三地,其中一支在临潢(府治在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东南)。杨丘文即属于临潢一支,为杨瀛伯祖。杨丘文、杨丘行、杨丘忠兄弟三人,显然是据《论语·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而取名,显示出杨氏家族对于儒家思想的尊奉。
另据杨丘文《萧公墓志铭》记载:“仆与公乡人也,素辱公厚,又与其诸弟善,故托之文。”[4]266志主萧孝资,与萧孝恭为堂兄弟,均属初鲁得部族。(5)初鲁得,《辽史》作“楮特”或“锄得”。而陈芮《萧孝恭墓志铭》载萧孝恭家族“本帐”(即驻牧地)在丰山,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呼格吉勒图《初鲁得族系考》认为“丰山”乃辽代人对萧孝恭墓志出土之地——今内蒙古翁牛特旗乌丹镇北约14公里处朝格温都苏木包莫图嘎查的山谷——的称呼。[5]丰山在丰州(州治即在乌丹镇),而丰州为辽代头下军州之一。据《辽史·地理志》记载:
头下军州,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团集建州县以居之。横帐诸王、国舅、公主许创立州城,自馀不得建城郭。朝廷赐州县额。其节度使朝廷命之,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6]448
杨氏家族正是降辽而被安置者。丰州属上京道管辖,而上京即设在临潢府,《杨公神道碑》称杨丘文属临潢一支,应是泛指。因此,杨丘文应是今赤峰市翁牛特旗乌丹镇一带的人。
杨丘文著述绝大多数已佚,现存仅有《柳溪玄心寺洙公壁记》(6)按,以下凡引自此文者,不再出注。[7]282-283(乾统三年)、《大辽故相国梁中令赵国夫人清河张氏墓志铭》[8]566-569、《故梁国太妃墓志铭》[4]257-259(以上乾统七年)、《大辽国故永兴宫使左金吾卫大将军萧公墓志铭》[4]265-267(乾统九年)文四篇。据上述文章可知:杨丘文生活在辽道宗、辽天祚帝在位期间,乾统三年(1103年)曾奉命出使宋朝。乾统七年时,任乾文阁直学士或乾文阁待制。(7)按,《故梁国太妃墓志铭》署撰者杨丘文官衔为“乾文阁直学士、乾文阁待制”,不知何故。疑前一个为实职,后一个为出使时权充之职。后不知何故去职,乾统九年起复,为乾文阁直学士、充史馆修撰。
关于辽代的乾文阁,资料也不多。《辽史》载“(清宁十年十一月)丁丑,诏求乾文阁所阙经籍,命儒臣校雠”[6]264,可知至晚于辽道宗清宁十年(1064年)已设乾文阁,负责掌管、校雠经籍等。宋人朱彧《萍洲可谈》云:
辽人嗜学中国。先朝建天章、龙图阁以藏祖宗制作,置待制、学士以宠儒官;辽亦立乾文阁,置待制、学士以命其臣。典章文物,仿效甚多。[9]卷二
古人能够出任乾文阁官职者,学问、文章必有可称。其中,不少人有进士身份,如王观、姚景行、王鼎、梁援(状元)、王师儒、孟初、高士宁、韩昉(状元)等。李桂芝《辽朝进士杂考》将杨丘文列为进士[10],不过该文并未提供可以证明杨丘文进士身份的资料。金人贾益《杨公神道碑》仅称杨丘文兄弟三人“业进士”,并未明确记载杨丘文中进士;而高福顺《辽朝科举制度研究》内有多个关于辽朝进士的表格,均未见杨丘文之名。[11]因此,杨丘文是否进士,尚待考证。不过,结合《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可以发现:自辽道宗咸雍六年(1070年)起,出使宋朝的副使往往有乾文阁官员身份或以他职临时充任乾文阁官员。(8)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按,充任者往往前面列有其实际官职。因此,不管杨丘文是否进士,乾文阁直学士一职都可以说明其才学是受到认可的。杨丘文虽非大名鼎鼎,不入《辽史·文学传》,但据刘凤翥先生研究,时至今日,还有人利用其名炮制赝品以牟利。[12]具有乾文阁官员身份的杨丘文发声支持了洙,在当时应有一定影响。
释了洙与杨丘文为好友。杨丘文出使北宋,于天祚帝乾统三年(1103年)春返朝途中,特地绕道至柳溪(9)按,在今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西甘池村西,玄心寺所在地。玄心寺探望了洙,可见二人关系非同一般。了洙颇具文才,现存文章多于杨丘文。《全辽文》收其文《悟空大德发塔铭》(1101年)、《崇孝寺碑铭》(1102年)、《范阳丰山章庆禅院实录》(1104年)、《白继琳幢记》(1105年)、《六聘上方逐月朔望常供记》(1115年)五篇。据上述诸文所署撰者信息及《壁记》来看,了洙于乾统元年(或更早)至乾统三年住柳溪玄心寺,乾统四年则已转住范阳丰山(10)按,此丰山与上文萧孝恭家族驻牧地之丰山不同。释了洙《范阳丰山章庆禅院实录》载:“郡城西北两舍之外,峰峦相属,绵亘百有馀里。有山崷崒,俗曰‘太湖’。诘其得名之由,验诸图牒则无考焉,固弗之取也。三峰叠秀,远望参差,嶰然不倚,状如‘豐’字,因号曰丰山。”(《全辽文》第270页)唐代幽州范阳郡,治在今北京市西南房山区。玄心寺为章庆禅院之下寺,二者相距不远。章庆禅院,天庆五年(或更早些)复住柳溪玄心寺。
据《壁记》记载,释了洙字涣之,俗姓高。(11)另据《范阳丰山章庆禅院实录》一文题署,可知释了洙受赐“文雄慧照大师”师号及紫衣。了洙先辈世居燕京,为当地名家望族。了洙自幼接受儒家思想教育,但因个性中有绝世出尘的倾向,长大后嗜好禅学,遂出家游方。后来,驻锡丰山南麓之玄心寺,却又重新研习“六艺子史之学”,并勤于笔耕,历经十多年,其文名逐渐传至京师。其馀佛徒闻知,对了洙身为僧人却热衷于儒学和文学创作深表不满。了洙虽未因此而改变,却并非完全不受困扰。杨丘文探望了洙时,了洙将其遭受的质疑告知杨丘文,于是杨丘文撰此《壁记》,既为了洙辩解,也借机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文学思想。
2 性与仁智
《壁记》开篇云:
夫善治性者,必求其所以养之也。养之之道无佗焉,一诸仁智而已矣。仁,性之固也;智,性之适也。固之不已则阏,阏之甚,则猝乎溢之亡御也;适之不已则肆,肆则扰,扰则惮之,惴惴乎惟其有所为也。溢之亡御则礼之畔,畔之,亡信也;惴惴乎惟其有所为则义之衄,衄之,亡勇也。是二者,皆蔽之一而病之众也。故知道者以智养之仁,以仁养之智。仁焉,以智之养则安;智焉,以仁之养则给。仁之安,则恬乎其内而不流;智之给,则应答乎万变而弗殆。故畜诸己之谓德,履而行之之谓行,扩之错诸物之谓业,贲斯三者之谓文。德以实之,行以厉之,业以成之,文以明之,斯治性之道得矣。
《壁记》这段话集中表达了杨丘文的哲学思想和文学思想。其中表达文学思想的内容并不多,只是讲到文的性质和功用,即所谓“贲斯三者之谓文”“文以明之”两句,但实际上与其所表达的哲学思想不可分割,应联系起来考察。从哲学思想方面看,涉及到了人性论和修养论,运用了多个范畴,按其在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有:“性”“仁”“智”“礼”“信”“义”“勇”“德”“行”。“业”“文”二者虽与“德”“行”并举,但通常不属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范畴。在《壁记》这段话中,最核心的范畴是“性”,然后是“仁”和“智”。
2.1 杨氏“性”论之特殊
“性”指人性,按今天的解释来说,是指人的共同本质。不过,不同的学派和思想家对其具体内涵的解释存在差异。辽代以前,在儒家思想系统内,最有影响的人性论有孟子“性善”论、荀子“性恶”论、扬雄“性善恶混”论、王充及韩愈的“性三品”论;大致与辽同时,则有北宋理学家“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对立统一论。从《壁记》开篇来看,杨丘文讲要养性,所以他的人性论应该不属于性恶论;没有分品,所以也不属于性三品论;没有明确作“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区分,所以也不属于理学家的对立统一人性论。那它属于性善论还是性善恶混论?《壁记》没有提到本源性的恶,似乎是持性善论。但是,杨丘文认为任由仁发展其厚度会导致无礼、无信,任由智发挥其能量会导致无义、无勇。无礼、无信、无义、无勇,显然就是不善。那么,是否存在过度的善?何况,不善由过度的善所导致,这在持性善论者看来,逻辑上恐怕是有问题的,所以应该也不属于性善论。同时,这种不善并非外源性的,故乍一看似可归入“性善恶混”论,但扬雄讲“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13]85,善恶均与生俱来,恶并非由过度的善所导致,所以杨丘文“性”论似亦不宜归入“性善恶混”论。不过,由于他讲的不善是性中本有的善的一种可能结果,因而亦可视为一种特殊的“性善恶混”论。那么,《壁记》对于道统系列的陈述,下至扬雄为止,恐非偶然。
2.2 杨氏“仁智相养”说辨析
关于人性,杨丘文提到要“治”和“养”。“治”和“养”按其本义虽有区别,但在文中其实都指修养。对于修养的方法、渠道,杨丘文认为应该配合运用仁和智,以智养仁,以仁养智。对此,本文称为“仁智相养”说。
2.2.1 仁智并举之传统
“仁”“智”并举并非杨丘文的创造,早在先秦儒家文献中,就已大量出现。为节省篇幅,这里略举出自先秦儒家经典的几例: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易·系辞上》)(12)按,文中连续罗列的常见经典文献恕不一一注明版本。
择不处仁,焉得知?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论语·里仁》)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论语·雍也》)
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
(《孟子.公孙丑上》)
是故穷则必有名,达则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闵,明达用天地、理万变而不疑,血气和平,志意广大,行义塞于天地之间,仁知之极也。夫是之谓圣人。
(《荀子·君道》)
不仁,思不能清;不智,思不能长。
(郭店楚简《五行》)
先秦其他学派对此也有所涉及。比如法家,《管子》云“既仁且智,是谓成人”,持肯定态度。《韩非子》则偶尔肯定,如“不惮乱主闇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韩非子·问田》)(13)按,郭沫若指出这并非韩非子的本色,大体类似主人爱其牛马而已。见氏著《十批判书·韩非子的批判》,《郭沫若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89页。;更多的是否定,如“偃王行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韩非子·五蠹》)、“有道之君,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韩非子·说疑》)等。道家对于仁智则更是完全持否定态度。至于《国语》《战国策》等史书,也有仁智对举的内容。凡此种种,说明早在先秦时期,仁智对举即已成为普遍现象。
汉人董仲舒也有对此问题的专门探讨,比如:
莫近于仁,莫急于智。不仁而有勇力材能,则狂而操利兵也;不智而辩慧獧给,则迷而乘良马也。故不仁不智而有材能,将以其材能以辅其邪狂之心,而赞其僻违之行,适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恶耳。……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14]257
尚有其馀有关仁智对举的文献,亦时见学界引用,此处就不多加罗列了。需要补充的是,在儒家学说各种德目不断诞生或定型的过程中,“仁智”关系虽然重要,但并不完全凌驾于其他德目之上,比如“仁义”(14)如在郭店楚简中,“仁内义外”就是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仁勇”“知(智)仁勇”“仁义礼智”“仁义礼智信”“仁义礼智圣”等等。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五常”这一概念逐步形成并固定下来的过程中,“仁”和“智”始终都被包含在其中。
2.2.2 仁智相养说:“仁”的降格
就《壁记》的“仁智相养”说而言,无论与传统儒学还是北宋新儒学相比,“仁”的地位明显降低。孔子“把‘仁’从当时众多的道德规范、道德概念中升华为诸种道德规范的共同基础,统束诸种道德规范的总德”[15]33,两宋新儒学的学者对“仁”在儒家道德规范体系中的核心及总揽地位有进一步的确认,如:“仁义礼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体;四者,四支”[16]64“仁可兼知,而知不可兼仁”[16]345“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知者,仁之分别”[17]109“仁义礼智四者,仁足以包之”[17]113“仁者,心之全德,兼统四者。义、礼、智,无仁不得”[18]22,等等。这样,就像陈来先生说的那样,“仁有二种,一种是贯通总体流行的仁,一种是与义礼智并立的仁,前者是理一的仁,后者可谓分殊的仁;前者即二程所谓专言之仁,后者即二程所谓偏言之仁”,“偏言的仁需要义礼智来制约、协调以互补”[19]425。而杨丘文则把“仁”从孔孟以来儒学体系中的总德、殊德兼具,变为仅与“智”地位等同的单纯殊德,显然是降格了。
杨氏所谓“仁,性之固也”的说法,仅把仁看作性的一种迟滞、粘重的状态特征,恐怕有些不妥帖之处。孔子弟子有若说“孝弟为仁之本”,在儒家思想中,仁的实践从孝悌开始而不断向外推衍。孝慈恭谨之人看上去较为厚重朴拙,常被人认为缺少变通和刚断,但若以为仁者必然缺智的话,恐怕逻辑上也是讲不通的。孔子说“仁者安仁,智者利仁”(《论语·里仁》),如果单从外部表现来看的话,许多行为难以分辨是安仁还是利仁所致。更重要的是,孔子还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而《壁记》讲“(仁)固之不已则阏,阏之甚,则猝乎溢之亡御也”“溢之亡御则礼之畔,畔之,亡信也”,畔礼、无信显然是由仁入于不仁,而性也由善入于不善了。这显然与儒家思想中占主流的性善论方枘圆凿。
辽文化受唐文化影响颇深。在心性论方面,除了韩愈的性三品说之外,李翱《复性书》也很有影响。《复性书》云:
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过也。[20]卷二
这种说法,被宋代理学家所吸收。性和情的区别,被当做体和用的区别。喜怒哀乐未发时,只有性的存在;喜怒哀乐已发,表现出来的就是情了。怎么修养?其实就是要将情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当喜则喜,当怒则怒。但怎么才算“当”?不违背道德规范就是。
杨丘文生活在比北宋五子略晚的时期(15)其中年龄最小的程颐(1033年-1107年),在杨丘文作《壁记》时仍在世。,还曾出使过北宋,应该有机会接触到北宋新儒学。此文开篇一段,呈现出与辽朝其馀文章颇不相同的面貌,即便放在金代前中期也不多见。但要说杨丘文受北宋新儒学风气的影响,由于缺乏材料,倒也难以坐实。当然,当时的北宋新儒学仍然处在发展过程中,体系还有待完善,对辽代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即便杨丘文受过影响,恐怕也难以一下子全盘接受。更何况,在人性论方面,他甚至与北宋五子的观点相左,与新学、蜀学的观点也不一致。
新学、蜀学都以情言善恶,以性为未发、情为已发,不以善恶言性。王安石认为:“性生乎情,有情然后善恶形焉,而性不可言善恶。”[21]316苏轼也认为:“夫善恶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恶为哉!”[22]719对于苏轼的人性论,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但较多学者同意认为苏轼持性无善恶论的观点。既然性无善恶,那么,它的本质内容本身就不可能由善趋向不善,反之亦然。而从《壁记》来看,杨丘文显然把仁、义、礼、智、信、勇等视作性的基本内容,善恶虽非与生俱来,但恶可以由过度的善而导致,那么,善就内在地蕴含有恶的趋向性。这与王安石、苏轼的观点不相一致。
杨丘文讲仁的失控带来各种弊端,观点并不稳妥。所谓“仁,性之固也”,指仁具有一种稳定、专一、不易变动但又显得多少有点愚昧、固执、闭塞的特点。从“固之不已则阏,阏之甚,则猝乎溢之亡御也”来看,仁的增长似乎主要是量的增加,而且程度的提升不仅不能带来益处,反而会积累其过滥的风险,并最终可能招致“畔礼”“亡信”的恶果。然而,仁是否会太多?须知仁则爱人利物,而非自锢。孔子把“仁”视为最高的道德原则和道德境界,徐复观则认为:“仁有次第、有层次而无止境。”[23]12孔子虽曾说过“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论语·阳货》),但“好仁”毕竟没有到“仁”的地步。况且,按传统的儒家思想中,仁作为总德,本身就内在地涵盖着智。杨丘文之所以持有上述观点,与其对智的看法大有关系。
2.2.3 仁智相养说:“智”的“升格”
“智”作为名词,主要有两个内涵:一是智慧,一为智力。作为智慧的“智”,当然是合乎德性要求的,是善的(16)不仅国人这么认为,西方人也有这样的认识。比如柏拉图说“智慧是关于善的知识,知道善的人行事是正确的”([英]罗素著,张作成编译:《西方哲学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29页),到了十八世纪英国哲学家亚当·弗格森还是认为“智慧是关于善的知识和选择”([英]亚当·弗格森著,孙飞宇、田耕译:《道德哲学原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6页)。等。;而作为智力的“智”,却是中性的,既可以用于善行,也可以用于恶行,或者用于无善无恶的对客观知识的追求。正因为智力有不能循理而为、甚至作恶的可能,难怪孟子说“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而对于这种“智”,朱熹称之为“小智”[24]277。因此,儒家在高扬德性之“智”的同时,也对智力之“智”保持着警惕。
在中国历史上,有肯定“智”的传统,也有贬低“智”的传统,后者以道家、法家为甚。老、庄、商、韩等虽角度、含义不尽相同,但都对“智”持否定态度,例如: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老子》第十九章)
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老子》第六十五章)
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
(《庄子.天运》)
遣贤去知,治之数也。
(《商君书·禁使》)
圣人之道,去智去巧,智巧不去,难以为常。
(《韩非子.扬权》)
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屈贤者。
(《韩非子.难势》)
举士而求贤智,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以为治也。
(《韩非子.显学》)
废常上贤则乱,舍法任智则危。
(《韩非子.忠孝》)
余英时撰《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一文,揭露了黄老学派和法家的反智思想及其愚民目的。[25]51-66不过,从孟子开始,儒家学派也对“智”有所警惕,并有意无意降低其地位。孟子有时候讲“仁智礼义”,如“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公孙丑上》)等,还存留着前人的影响,但他更多地谈“仁义礼智”,“智”的位置就向后移了。后来,班固作《汉书·古今人表》,将上古至秦的近两千位人物分作九等,其中上上圣人、上中仁人、上下智人,然后依次降等,最低为下下愚人。[26]863“智人”低“仁人”一等,“智”的地位当然明确也低于“仁”。虽然与道家、法家相比,儒家有主智的传统,但自汉代起,儒家在政治思想上出现了法家化的现象,在“尊君卑臣”格局中一定程度上不由自主地走向了反智主义。[25]47-51、66-77此外,由于“智”的作用在儒家思想体系中被主要局限在成就德性的框架内,加上“智”本身具有指向不善的可能,人们还要时时警惕其成为“德之贼”,所以后来的儒家对“智”也常怀警惕(17)如程颐说“人只为智多害之也”(《二程遗书》第309页)等。,其除了道德实践之外的理性认知问题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从《壁记》来看,其所谓“智,性之适也”,“适”是指智具有一种灵活变通、趋利避害的特点。而从“适之不已则肆,肆则扰,扰则惮之,惴惴乎惟其有所为也”“惴惴乎惟其有所为则义之衄,衄之,亡勇也”来看,杨丘文认为任由智巧的发挥会导致当为不为,伤义无勇。但从“以智养之仁,以仁养之智”的“仁智相养”说来看,杨丘文将“仁”仅仅视作殊德的同时,却将“智”放到与“仁”同等的地位上,对“智”而言似乎是一种升格。不过,这种“升格”显然是建立在将“仁”降格的前提之上,从这个层面讲,其实也并非真正的升格。然而,即便“仁”降了格,能与之对等的也只能是德性之“智”,而非智力之“智”。《壁记》将智力之“智”与“仁”对举,从这个层面来讲,却又的确可以视作一种升格。因此,《壁记》所论之“智”,其内涵颇为混杂、微妙。
与儒家虽重视智、但不过分强调“智”相比,佛教却是特别重视“智”。佛教有“般若学”,般若即智慧之意。佛典中有关智的内容,真可谓不胜枚举。杨丘文为释了洙作文,虽然文中讲“吾仁智相养之道”,以“吾”字与“尔党”区别开来,以表明这个与“仁”对举的“智”不是佛教的“智”(以求获得涅槃的“般若”),但应该有出于立意和行文上的考虑:一方面,他不能完全丧失作为一位儒者的立场,并且要对了洙研习儒家经典的行为表示支持,所以不能不对儒佛二家的“智”有所区分;但另一方面,由赞扬历史上擅长文辞的高僧们“皆得吾仁智相养之道”可知,他的真正态度是希望多关注儒佛二家之同,而非刻意强调二家之异,否则岂非同于过分执着其本教的了洙反对者们?可作佐证的是,他虽借鉴了唐宋时期在具有新儒学思想者间流行的道统说,但是在道统系列中却不提韩愈,也许是韩愈反对佛教的态度过于强烈吧。而且,韩愈《原性》将“智”与其他四常做了区分,其他四常都属于道德规范,而“智”仅为一种能力。这对于重视“智”的杨丘文来说,也是难以接受的。
成中英认为:“人的存在可区分两个层面:一面是理性,一面是意志。理性以知为目标,因而产生知识化的宇宙以及科学的知识结构。意志以行为目标,促使人实践理想与价值。人的存在可视为知与行的集合,因此必须同时适应知与行的要求。”[27]222儒家有“仁民爱物”(《孟子·尽心上》)的追求,“仁”可说与意志相关联,而“智”则无疑关联着理性。随着思想的发展,关于仁智关系的探讨后来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对知行关系的探讨。在中国思想史上,提出知行关系问题的时间很早,但真正予以重视并专门开展探讨的,方克立先生认为是由宋朝开始。[28]2
由于宋明理学家不把智放在与仁真正对等的地位(18)如[宋]陈淳《北溪字义》说:“仁义礼智四者判着两边,只作仁义两个。……智之是非确定,只是义之裁断割正处。”(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页)陈淳是朱熹的得意门生,其《北溪字义》犹如程朱学派的“理学词典”,地位相当重要。于此可见,“仁智”关系之地位,在程朱学派学者眼中已不如“仁义”关系之重要。,甚至陆王心学被认为具有较为强烈的反智识倾向[29]294-309,故而在仁智关系中,智之一端在自宋至清的历史阶段略显失重。即便在“尊德性”与“道问学”两种为学功夫的争论中,不论是被肯定还是否定,智的因素虽始终在场,但却只是一种从属性的工具性存在。直到近代,康有为提出:
夫约以人而言,有智然后仁义礼信有所呈,而义礼信智以之所为亦以成其仁,故仁与智,所以成终成始者也。……就一人之本然而论之,则智其体,仁其用也;就人人之当然而论之,则仁其体,智其用也。……义礼信不能与仁智比也。[30]24
康有为虽然也说“人宜以仁为主,以智为辅”,但只是就人道之终始而言。从所涉及的范畴来看,他将智提到与仁同等地位而明确高于义、礼、信,表达了新见。现代新儒学则更是把仁智论当做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来探讨,探讨道德和知识的关系,并涉及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徐复观甚至认为:“能与仁的概念可以看做平行而真正是对举的,只有‘智’的概念。”[23]15牟宗三讲“转仁成智”,唐君毅主“摄智归仁”,以及徐复观倡“仁智互成”,学界一般认为,以上学者的见解虽有不同,但均旨在以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精神,来充实、提升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过,这种智与古代所言的智在内涵上并不一致,正所谓“仁是向内的沉潜,智是向外的知解”[23]17,与朱子所言“知(智)是分别是非之理”[17]466“知(智)者知有是非,而取于义理,以求其是而去其非,所谓知(智)也”(19)同上,第643页。肖群忠说:“中国儒家智德观的特点在于,它把知或智主要看作是一种人事之智或者说是知人之明。”(《智德新论》,《道德与文明》2005年第3期,第14页)。[17]643等大相径庭。
《壁记》开篇如此热衷于讨论理论问题的表现,有可能受到北宋时代潮流的波及,但其对于性、仁、智关系的阐发主要还是源于自身对于传统儒家思想的理解,并受到佛学思想的影响,而与北宋新儒学不尽相同。
3 模糊儒释界限的文道观
文道关系一直是中国古代联结着思想与文学的重要问题,学界对此已有相当深入的探讨,此不赘述。但在《壁记》中,文道关系正是与其“仁智相养”说相关联的又一重点所在,所以还是值得辨析一二。
《壁记》在开篇表达完仁智相养观点之后,接下来谈到:
故畜诸己之谓德,履而行之之谓行,扩之错诸物之谓业,贲斯三者之谓文。德以实之,行以历之,业以成之,文以明之,斯治性之道得矣。
上述引文讲到文章能使德性、善行、事业更加显耀,焕发光彩。其中,“德”“行”“业”实际上是上文所谈的“仁”及其履行、扩充,与由“孝悌”到“仁民”再到“爱物”“修齐治平”等次第同一理路。而“文”,则是“智”的展现。至此,文章开头所言仁智相养以治性的问题,为其下文转到文道关系问题做了铺垫。然而,由于引发此文之创作的人与事有些特别,从而使得其下文所讲的文道关系问题也具有特别的意味。
《壁记》的撰写是由一个争端所引发,争端的双方是禅僧了洙与其他诸多僧人,起因则是了洙之深研儒学及喜好文辞,激怒了其馀释子。了洙自幼饱读儒书,出家后“不数岁,尽得其术”。居玄心寺期间,却又“研探六艺子史之学,掇其微眇,随所意得,作为文辞而缀辑之。积十数年,不舍铅素,寖然声闻流于京师”。从“不数岁”与“积十数年”的对比来看,了洙在儒学及文辞方面所下的功夫要远多于佛学修为,难怪会招致远近僧人的诘难。诘难者的意见有两点:一、僧人不应致力于儒学;二、佛门修道,无需文章。也许是觉得出入儒释的现象很正常,杨丘文并未回应第一点,而重点就第二点为了洙进行辩护。在完成了仁智相养说的铺垫后,杨丘文提出更直接的观点:
夫道之在心,不言则不喻,故形之言而后达之也。言不及远,又不能人人乎教之,故载之文而遍天下、历后世,而无不至也。然文之于道,为力莫甚焉。
杨丘文主张文对于道的表达、传播有重要作用。接下来,《壁记》称颂孔子、子思、孟子、扬雄著书立说之功,以反诘句“文果累诸道乎”作结;又以释迦牟尼“倡之五教之说,以溢编轴”“燦肇融觉观密”(即僧燦、僧肇、道融、慧觉、澄观、宗密)等分属华严、三论、禅等不同宗派的高僧“率有辩论篇藻以翼其术而抪之世”为例,再度反诘道:“不亦谓之文乎?”杨丘文认为儒释二教均借文章以实施仁智相养之道,反击佛徒认为求道不需文字的看法,与二程等“作文害道”说亦背道而驰。此外,杨丘文虽亦如韩愈、柳宗元般持“文以明道”说,但他以“仁智相养”说来引出并比拟文道关系,实际上更大程度地提高了文的地位(20)陈应鸾认为“在文和道二者之间,杨丘文明确主张重文。这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是非常少见的”(第191页)。,使得文道并重,从而与通常意义上的“文以明道”说拉开了距离。
其实,在辽代,有众多喜好文辞的僧侣作家,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如华严宗高僧释海山为辽兴宗诗友,他与释鲜演的诗文作品甚至传到了高丽;寺公大师还用契丹字创作了辽代诗歌的扛鼎之作《醉义歌》,后由蒙元初期的耶律楚材以汉语译出。陈垣先生《中国佛教史籍概论》说:“辽时文化本陋,惟燕云十六州为中华旧壤,士夫多寄迹方外,故其地佛教独昌,观缪、王二家所辑遗文,属佛教者殆十之六七。”[31]71不过,陈垣先生所据的文献主要是缪荃孙《辽文存》、王仁俊《辽文萃》,二书所辑文章不够齐全。当今学者据阎凤梧等编纂的《全辽金文》进行统计,得出结论说:在辽代散文中,僧侣占作者总数的16%;作品内容完全或主要关于佛教的有259篇,占现存辽代散文总数的32%。[32]虽然所占比例不如陈先生所讲那么高,但亦可略见辽代僧侣文风之盛。然而,文风兴盛不等于不会受到质疑。也许正是过于兴盛,才招致其他僧人的激烈批评。
在这里,不得不提及陈应鸾先生《杨丘文的文道理论初探——兼论辽朝文论之特征》一文。该文是最早专门讨论《壁记》的文章,在对《壁记》内容的串讲上,在已有的成果中仍然最为准确,但在进一步归纳其理论特色并作引申、联系时,其观点却似有可商榷之处。该文第一部分重点阐明杨丘文的文道理论“具有强烈的崇实精神”,认为他以“仁智”为道,与唐宋古文家以“仁义”为道大不相同,但文章基本上将“智”归入佛教而排除出儒家的范畴,这恐怕是不符合实际的。而且,该文认为唐宋古文家的“道”是抽象的概念,而杨丘文所说的“道”则“非常具体、实在,实际上是借用儒家、佛教的字眼,来指人们进行思想修养、为人处世以及解决社会政治中的问题的原则、方法和能力,充分体现论‘道’的一种崇实精神”[2]189,亦恐不然。因为唐宋古文家所说的“道”是彻上彻下的,并非与实际问题毫无牵涉。而且,如果将“智”都归于佛教的话,杨丘文所说的“道”恐怕只会更加玄虚。纵观该文之所以如此强调《壁记》文道理论的崇实精神,应该是与作者对辽朝文论“尚质、尚实、尚用”的总体认识有关。然而,该文认为杨丘文在文道之间明确主张重文,而重文与尚质一般都被认为是相对立的,那该怎样才能厘清其中的逻辑关系呢?况且,了洙并未还俗,他被其馀僧人视为出格的行为仅仅是研习儒学和爱好文艺而已,《壁记》所表达的也只是个体修养之法和以文明道之意,何以见得就“具有强烈的崇实精神”了呢?笔者认为,我们固然不能脱离辽代文论的总体特征来讨论《壁记》,但也应该充分注意到《壁记》的独特之处,才能更好地把握杨丘文的文道理论。纵观《壁记》全文,杨丘文在发表对文道关系问题的看法时,并未指出“道”为何道。这可能与此文为了洙所作有关,不便特别强调是儒之道还是释之道。然而,这一做法却在主客观上都模糊了教派界限,似乎在更为根本的意义上讨论文道关系。若顺着这一思路加以延伸,就有可能像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之后所主张的那样:将“道”的旧有内涵去除,转指适应新时代的新思想,甚至变成纯粹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然而,《壁记》的做法只不过是杨丘文为了回避以儒士身份为僧人辩护的矛盾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实在看不出他有那样超前的自觉。至于有学者认为杨丘文受到了北宋理学之风北渐的影响,还有些道理,但要说《壁记》“已是充满理学古文的情调”[33]230,恐不尽然。另外,杨丘文极力推崇扬雄,也与二程对扬雄的鄙薄态度大相径庭。
4 从《壁记》看辽代儒学之水平及特征
辽朝统治者早早接受了儒家文化的影响。辽太祖依汉制立长子耶律倍为皇太子,并在太子的建议下,修建孔庙,置国子监,设国子学,春秋行释奠礼,推行仿中原地区的文教政策等。辽太宗朝设立太学,加上地方官学、私学的发展,对儒学教育有着较大的促进。这些儒治举措,早已为治辽史的学者们所熟知。从现存辽代文献中,学者们还钩稽出太宗朝之后不少关于儒家文化深入影响辽代社会并进而传播到更偏远地区的史料,这些史料足以说明:不仅汉人遵循着儒家传统,契丹人乃至更多的种族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影响。然而,这些史料却往往只能说明儒家文化在辽朝上至国家、下至家庭乃至个人中的实际存在,却难以体现其所达到的儒学水平。
4.1 辽代儒学水平之评价困境
儒学著作的失传,是后人难以评价辽代儒学水平的主要原因。杨家骆编《辽金元艺文志》(上册)之《辽艺文志》收录了从清初黄虞稷到现代黄任恒所著的10种书目文献,它们是:①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②清厉鹗《辽史拾遗·补经籍志》;③清杨复吉《辽史拾遗补·补经籍志》;④清倪燦、卢文弨《补辽金元艺文志》;⑤清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⑥清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辽代部分);⑦《钦定续文献通考·经籍考》(辽代部分);⑧缪荃孙《辽艺文志》;⑨王仁俊《辽史艺文志补证》;⑩黄任恒《补辽史艺文志》。上述文献在“经部”共著录有辽代著作 21种,而在“子部”不见任何一部儒家类著作(见表1)。
上述表格所列的著录内容问题很多:① 非辽人所撰:黄任恒认为应删去辽道宗所颁赐的《易传疏》、《书经传疏》、《诗经传疏》、《春秋传疏》以及属于抄进的《尚书·无逸》《五子之歌》(21)按,黄志在经部中也误收了西夏人的数种著作,本文不予列入。[34]67-68,并怀疑《辽朝杂礼》属于金朝人的著作。(22)按,仅黄虞稷与厉鹗将此书列入经部,卢文弨、缪荃孙、王仁俊均将其列入“史部·仪注类”。[34]72此外,笔者认为还应删去《洪范》,该篇只是辽道宗命耶律俨进讲而已[6]296;《五代史》《贞观政要》《通历》《方脉书》都是译本,同样不能算作辽人著作。② 重复著录:王仁俊考证《礼典》《礼书》属于同书异名,指出金门诏重复著录之误[34]24;而《五经传疏》显然与其他几种传疏著作是总与分的关系,金门诏均予著录,显然也不甚妥当。此外,黄虞稷在“经部·礼乐类”及“史部·仪注类”同时著录了《礼书》《辽朝杂礼》两种书,也是一种重复。③ 分类不当:《五代史》《贞观政要》《通历》是史部著作,《方脉书》属于子部,钱大昕于“经部·小学类”后设一“译语类”,将其译本置于其中。缪荃孙沿袭了这一做法。后来,王仁俊虽将《方脉书》译本移出“经部·译语类”,归入“子部·医家类”,却又增加了本该分别入子部、集部的《阴符经》《讽谏集》译本。上述做法显然是不顾内容,只重形式。相比之下,杨复吉、黄任恒的处理方式较为妥当。④ 分类不定:对于《礼书》(或名《礼典》),厉鹗《辽史拾遗·补经籍志》、王仁俊《辽史艺文志补证》入经部,清倪燦、卢文弨《补辽金元艺文志》、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辽代部分)、缪荃孙《辽艺文志》、黄任恒《补辽史艺文志》入史部,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同时列于经部及史部,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则误作二书,分列于经部和史部。《辽朝杂礼》的著录也有同样分类不定的情况存在。
凡此种种,再除去收录少数民族文字的《番书》《契丹大字》《契丹小字》(23)三书俱佚。番书不详具体所指,契丹大小字尚有部分碑刻存世。,属于经部文献且流传至今的辽人著作仅剩《龙龛手镜》,其作者却是一位僧人!《龙龛手镜》按汉字四声编排,虽四库馆臣言其“不专以释典为主”[35]546-547,但终究以多收辽以前佛书俗体、或体乃至误体等而著称,当今学者更是称该书之撰著“目的是为佛徒研读佛经提供一部形音义可靠的字书”[36]。因此,我们根本没有可资利用的辽代著作来认识辽代儒学的学术水平和理论高度,那么,杨丘文《壁记》一文的价值可想而知。
4.2 辽代儒学水平及特征
孟广耀《〈十三经〉不同地位考——浅论对儒家思想的取舍》一文通过考察辽代对十三经的引证、充当教材情况等,分析辽人对十三经的取舍,揭示十三经在辽代受重视程度之差异,认为可分三个等级:《周易》《尚书》《诗经》《论语》最受重视,其次为《左传》《礼记》《孝经》《孟子》,最不受重视的是《公羊传》《谷梁传》《周礼》《仪礼》《尔雅》,这种选择乃至取舍由经书的内容和思想特点决定,特别是辽人自身的需要所决定。[1]248、256不过,孟文未就辽代儒学水平作专门的探讨,大致提到“辽朝儒士无专门名家之学”,“经学水平与北宋相比,实是平淡”[1]215。
至于辽代儒学的发展阶段,前人研究或分为两期:“前期为辽太祖至辽穆宗时期,是确立儒学的统治地位时期”,“后期为辽景宗至辽末,是辽代儒学的发展、繁荣时期”[37]14;或分为三期:“辽朝的教育发展,根据辽代儒学在不同阶段的传播特点,大致可划分为初始(辽初-983年)、发展(983年-1055年)和兴盛(1055年-辽亡)三个时期。”(24)按,该文视辽代儒学与教育为同步发展,故其发展阶段是相同的。另外,孟广耀《契丹“儒化”过程及“夹生”现象例举》(《儒家文化——辽皇朝之魂》,第17-24页)从契丹民族接受儒家文化的角度分为“辽太祖建国至辽太宗接管燕云前夕”“太宗接管燕云至景宗朝”“圣宗即位至辽亡”三个阶段。笔者认为,就本文的论题而言,顾文的阶段划分比孟著、武文更合理些。[38]三期所对应的分别是建国至景宗时期、圣宗至兴宗时期、道宗至灭国。但不管怎么划分,杨丘文在世的道宗及天祚帝时期都被归入儒学发展的兴盛阶段。那么,就现有材料而言,我们可借助辽天祚帝乾统三年(1103年)问世的杨丘文《壁记》来窥探辽代儒学兴盛阶段所达到的理论水平。
首先,辽末儒学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思辨色彩。辽代儒学从总体上讲还属于传统的注疏章句之学,如辽道宗清宁元年(1055年)颁赐学校的还是《五经注疏》这样的著作。然而,《壁记》在一些儒学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上所展现的思辨水平,却超出了传统的汉唐儒学的范围,而呈现出与宋代儒学相近似的面貌。
其次,辽末儒学的理论水平远不及同时期的宋代儒学。正如上文所论,《壁记》中所表述的人性论观点有些特殊,其所持的“仁智相养”说也存在观点不够合理之处,这实际上是受到了思维水平的局限。早在杨丘文出生之前,北宋的周、邵、张、程、苏、王等已经建立了成体系的新儒学,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派,可见宋辽儒学水平差距之大。
辽、宋虽为敌国,互市之制时行时禁,但两国之间的书籍流通还是存在的。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辽圣宗统和二十四年),曾发布禁令,要求在书籍贸易方面“非《九经》书疏悉禁之”[39]4562。这说明,之前出口的书籍肯定不止《九经》书疏,同时还说明即便有了书禁,也不妨《九经》书疏在辽朝的传播。尤其是宋仁宗、英宗在位期间,两国“互市不绝”[39]4563。尽管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辽道宗大康四年)“复申卖书北界告捕之法”,但这也正说明了各种图书应该都有可能流入对方境内。比如辽道宗大安五年(1089年,宋哲宗元祐四年),苏辙出使辽国,返宋后上书说:“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40]937-938出于政治、军事的考虑,他建议朝廷禁止民间擅自开版印行,建立出版审查制度。由此可见,宋辽通过图书的流通而展开的文化交流始终是存在的。从《壁记》所罗列的道统系列来看,结合苏轼在辽代后期取代白居易成为辽人追捧对象的事实,以及杨丘文本人曾出使北宋的经历,可以推断杨丘文应该有可能受到北宋儒学新思潮的一定影响。(25)按,黄凤岐《试说辽代教育家》认为在杨丘文的生活时代,“理学已传入北方广大辽朝统治区域,对当时的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领域均有较大影响”(《辽金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第132页),其依据亦为《壁记》一文。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对北宋理学在辽朝的影响估计过高了。然而,由于直接材料的缺乏,我们难以坐实这一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作出两个推断:一、如果杨丘文受到过北宋新儒学思潮的影响,那么通过《壁记》,可以说明他在受到影响后,试图模仿却未能充分理解和吸收,或者不愿亦步亦趋,而力图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二、如果没有受到影响,则可以说明他在自发延续唐代思想家的思考,虽与北宋思想家分属不同国家,却不期然一同走在趋向新儒学的路上。不管怎样,《壁记》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思想文化的理论水平与阶段性特征,而这也许正是其主要价值所在。
至于辽代儒学的总体特征,曾有学者总结为“注重实践,讲求实用”和“儒学普及,深入民心”两点[37]18;还有学者认为,由于契丹统治者在学习儒家文化的同时,又有意识地维护其本民族文化,从而赋予辽代儒学以民族色彩。[41]应该说,这些归纳都有一定道理,但基本上都是着眼于儒学之应用而言,并没有结合辽代现存最具形而上色彩的思想资料(如《壁记》)来看。我认为,虽然《壁记》本身所表达的思想其本身价值并不大,甚至在逻辑上也存在一定问题,但是通过它,我们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当时的理论水平和发展阶段,还可一定程度上认识其特征。从《壁记》的内容出发,结合辽代思想文化状况来看,辽代儒学的主要特征恐怕还是儒释两者的融会。
辽朝虽推崇儒学,但由于受唐朝崇佛的影响,佛教也极为盛行,乃至后世有“辽以释废”的评价。[42]3823翻开《全辽文》,涉及佛教内容或由释子创作的作品比比皆是,充分体现了辽代佛教盛行的特点。(26)按,关于辽代佛教之兴盛,学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此不俱述。又,道教在辽代势力较弱,影响不大。辽代儒佛之间既有斗争,也有交融。(27)张国庆《相契与互融:辽代佛儒关系探论——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一文对此有专门探讨,可参看。从交融现象在个人身上的体现来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契丹皇帝往往二教并崇,均加研习,如辽道宗被臣下称颂为“儒书备览,优通治要之精;释典咸穷,雅尚性宗之妙”[7]213“阅儒籍则畅礼乐诗书之旨,研释典则该性相权实之宗”[7]268,可作其中的代表。宗王耶律宗政(1003年-1062年)“乐慕儒宗,谛信佛果”[7]157;其弟耶律宗允(1006年-1065年)同样在“佩诗书之教”“钟孝敬之性”的同时,也“谛慕佛乘”[7]184-185。上下同风,醉心于佛学的儒士往往而在,此处略举一二:身为统和十四年(996年)状元的张俭(963年-1053年),却“谛崇佛宝,力转法轮,深穷诸行之源,妙达无生之理”[7]131;开泰七年(1018年)进士王泽(989年-1053年)“素重佛乘,淡于权利”,“惟与僧侣,定为善交。研达性相之宗,薰练戒慧之体。间年看《法华经》千三百馀部,每日持陀罗尼数十本”[7]165,可见十分虔诚。破除教派壁垒的僧人亦有之:如释志才公开宣称“余虽为释子,三教存心。凡行其道,必须融会”[8]680;释了洙先是作为儒士而遁入空门,却又在禅院中重新探研儒学,等等。返观《壁记》,它作为体现辽代儒释思想交融的重要文本之一,无论是仁与智的并举,还是在文道观上的有意模糊,在具体人的层面透露出儒士杨丘文和僧人释了洙之间所存在的往复激发,在学的层面则显示着辽代儒学与佛学的两相浸润。杨丘文的“仁智相养”说不仅在儒学内部具备一定的合理性,而且还可以以偏重于仁的儒学去兼容偏重于智的佛学,反之亦然。由此,杨丘文与释了洙之间的契友关系,可视作儒佛交融现象的一个缩影,而《壁记》则是这种交融的结晶。辽代儒学的发展水平与特征经由《壁记》而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展现,这对于文献较为稀缺的辽代儒学研究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它还为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宋、金儒学的发展状况,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儒学创新发展的趋势与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