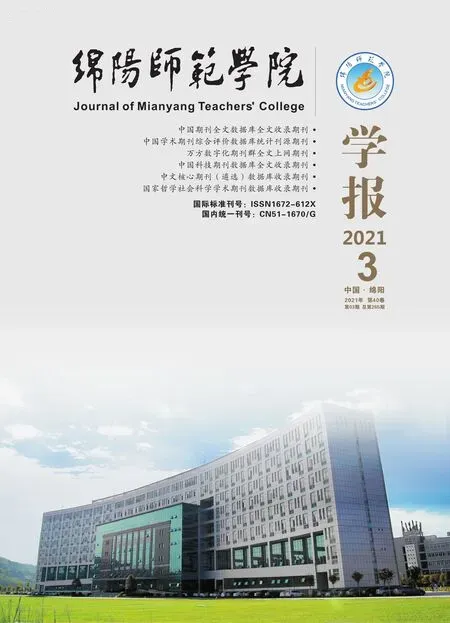馆阁文臣王士熙的诗歌创作与大元气象的书写
戴欢欢,任声楠
(1.合肥师范学院文学院,安徽合肥 230601;2.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王士熙(约1266—1343)字继学,东平(今属山东)人。其父王构,仕元为翰林学士。王士熙早年师从邓文原。至治初任翰林待制,泰定四年(1327)累官至中书参政。泰定帝薨后,卷入皇位争夺,失势后下狱。文宗即位后,便被流放至远州,次年得以还乡。顺帝即位,起任江东廉访使,于后至元二年(1336)迁南台侍御史,至正二年(1342)升南台御史中丞,未几卒。追封为赵国公。《图绘宝鉴》卷五载其“善画山水”[1] 154。王士熙与其弟王士点以文学世其家,士熙原有诗集,惜未传,清顾嗣立《元诗选》二集辑其诗116首,用原集名为《江亭集》。王士熙诗,长于乐府歌行,且其诗歌多为唱和之作,其唱和对象主要是袁桷、马祖常、虞集、揭傒斯、宋本等馆阁文臣。
一、王士熙的生平与思想
王士熙出身于文学仕宦之家,其父王构“少颖悟,风度凝厚。学问该博,文章典雅,弱冠以词赋中选,为东平行台掌书记。参政贾居贞一见器重,俾其子受学焉”[2]3855。世祖时期,王构入翰林,为侍讲学士。成宗即位,纂修实录,书成,为参议中书省事,生平事迹详见于《元史》。在《元史·王构传》后尚有对其二子的简介:“子士熙,仕至中书参政,卒官南台御史中丞;士点,淮西廉访司佥事,皆能以文学世其家。”[2]3856王士熙的家庭是传统的业儒之家,他在仕宦之路上虽历经沉浮,但也有一段时间得到重用,并有扈从皇帝巡幸两都的经历,这对汉族文臣来说是难得的。王士熙一方面延续了其家庭出仕的传统,另一方面也以文学世其家。对此,元人胡助在其《挽王继学中丞》诗中写道:“玉堂挥翰泻珠玑,家学光华世所稀。但觉高才无滞事,安知平地有危机。妙年台阁祥麟出,晚节江淮退鹢飞。惆怅百身曾莫赎,生刍一束泪沾衣。”[3]610第一句,胡助就对王士熙的文学才能予以称赞,并且分析了其背后的家学影响因素。而“妙年”“晚节”二句写出了王士熙的身世浮沉之境况。王士熙自小受儒家思想影响,所以有儒家典型的入仕之精神。但是对于儒家思想的学习,他有自己的看法:“生平不愿为慵书,亦不愿作章句儒。”(《赠广东宪使张汉英之南台掾》)[4]4,在王士熙看来,他是不齿于死读书的,也不愿作只拘泥于辨析章句的儒生,但是对于儒学大师许谦,王士熙还是颇为推崇的,曾“访谦于山中,谓谦清气逼人,可畏既退,论荐于朝”[5]40。王士熙作为北方儒士,在元代入仕相较南人容易许多,他对自身的才能亦较为自信,“才高不用长叹息,四海弥天岂无识”(《赠广东宪使张汉英之南台掾》)[4]4。王士熙至治初年时即任翰林待制,供职京师,后于泰定四年(1327)累官至中书参政,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可谓“圣主敷皇极,元臣建上台”(杨载《寄王继学二十韵》)[6]27,进入了统治阶级的高层。但是他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由于他之后卷入皇位争夺之中,因此下狱,后惨遭流放。元顺帝即位之时,虽又起用王士熙为江东廉访使,并于至正二年(1342)升南台御史中丞。但经历过宦海沉浮之后的他,不禁感慨“飘然阅浮世,独立寂无语”(《石人峰》)[4]15。王士熙没有了年少之时的豪情壮志,而是产生了“燕市尘深拂衣去,海门何处问鱼蓑”的想法,归隐的念头萦绕心中。对于王士熙的形象,柳贯有《王继学画像赞》:“粹然冰玉之英展也,星凰之瑞,用则盛之鸾台凤阁,不用则置之朱崖儋耳。老智虑于多艰,观夷险于一致,固将挟玉局之飞仙,以游夫鸿濛溟涬之际。所谓琅瑘之宗鲁公之子,而盛德之世者也。”[7]397此中多为溢美之词,可见王士熙在当时颇具名望,其落难时,比之于李德裕(贬朱崖)、苏轼(贬儋耳),其升官时,张翥有《王继学廉使迁南台侍御史诗以贺之》。
入朝为官是王士熙的主要人生追求,这是其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强烈的用世精神。元代社会,思想文化政策相对宽松,儒、释、道等各家思想对士人都或多或少的产生影响。王士熙一生并非只受儒家思想影响,还有较为明显的道家思想痕迹,在其行为上主要表现为求仙问道,这在其诗歌中有较为普遍的反映。王士熙在仕途上有起有落,面对如此的人生经历,心里难免有对闲逸生活的向往,这在其《题幽居》诗中有所抒发:
最爱幽居好,青山在屋边。竹窗留宿雾,石槛接飞泉。
采药蟾奔月,吹笙鹤上天。 世途尘扰扰,裁句咏神仙[4]7。
整首诗句语言浅近,易于理解,诗人表达了对纷纷扰扰的尘世的厌倦。他想深居简出,与自然为伍,过着神仙般逍遥自在的生活。因此,在王士熙的思想中,儒家的用世和道家的出世思想是并存的,积极用世是其现实之举,但当诗人仕途失意之时,道家出世想法又为其提供了精神慰藉。王士熙身为元代的馆阁文臣,与马祖常、虞集等同僚唱和馆阁,他交游对象的身份并不单一,与道士也有往来。如元代道士吴全节,同样出身于儒门,得到元朝廷的重用,时朝中儒臣如高昉、贾钧、王士熙诸人“多所咨访”(《河图仙坛之碑》)[8]365。另其有诗《送袁道士二首》其一:“五公旧谱汉廷传,之子飘飘去学仙。山里牧羊成白石,云间骑鹤上青天。黄庭夜月迎三叠,绿绮秋风度七弦。拂袖京城留不住,别离可奈落花前。”[4]10朋友袁道士要离京学仙去了,王士熙想象其学仙的场景,字句中透露出羡慕之情,对朋友的离别也十分不舍。王士熙所受的道教思想,其中的求仙行为对他有较大影响力,这在其诗歌中有多次书写。最能表达其求仙心切的有《送华山归隐西湖》:
方士求仙入沧海,十二城楼定何在。金铜移盘露满天,琪树离离人不采。
轩辕高拱圣明居,群仙真人左右趋。青牛谷口迎紫气,白鹤洞中传素书。
珊珊鸣佩星辰远,寂寂珠庭云雾虚。修髯如漆古仙子,玉林芙蓉染秋水。
九关高塞不可留,归去江湖种兰芷。山头宫殿风玲珑,玄猱飞来千尺松。
闲房诵经钟磬响,石壁题诗苔藓封。欲向君王乞祠禄,安排杖屦来相从[4]3。
此诗一开始便用大半篇幅描写神仙所处之仙境,最后诗人自己不免心动,想要就此罢职,而去管理道教宫观,去追求神仙般的生活。其求仙的思想,多半是其在仕途中遇到挫折之时所寻求的精神解脱。
二、诗画创作的互通
王士熙现存诗歌130首,诸体兼备,有五律、七律、五绝、七绝、五排等,此皆近体诗作,占现存诗歌数量的一半以上。就创作成就来说,他的乐府古诗水平更高。乐府始创于秦,两汉时期的乐府诗多出自民间,是创作者有感而发的结果,因此,乐府古诗多本性情。《汉书·艺文志》有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9]1756可知,乐府诗是诗人为具体事物所触动,激发了创作热情,不是为文造情的空洞之语。对于古乐府的发展历程,元人杨维桢在其《玉笥集叙》中有所论述:“《三百篇》后有《骚》,《骚》之流有古乐府。《三百篇》本情性,一出于礼义。《骚》本情性,亦不离于忠。古乐府,雅之流、风之派也,情性近也。汉魏人本兴象,晋人本室度,情性尚未远也。南北人本体裁,本偶对声病,情性遂远矣。盛唐高者追汉魏,晚唐律之敝极。宋人或本事实,或本道学禅唱,而情性益远矣。”[10]42册309杨维桢论乐府古诗注重书写情性,但自南北朝以来,尤其是宋诗的本之事实,重于说理,致使古乐府去性情甚远。至元代,“吟咏性情”成为诗人和诗论家们讨论的热点,其含义泛化,其中刘将孙主张性情得之自然,认为诗是“一时自然之趣”。王士熙的乐府诗创作也是注重吟咏性情、本之自然的。如其《青青河畔草》一诗:
青青河畔草,江上春来早。春来不见人,思君千里道。
千里君当还,夙夕奉容颜。青楼独居妾,含情山上山。
白雁归塞北,一行千万亿。团团月出云,却使妾见君[4]2。
此诗沿用古题,在诗歌内容上表现的是代思妇所写的闺怨之作。诗歌前两句描写早春时节江河两岸小草青青的景象,开头就描绘了清新自然的环境。写景不是目的,而是为表现人物服务的,一方面可以引出人物,另一方面为人物提供了活动场所。在这样美好的季节,本来应该和自己思念的郎君踏春游玩,而现实却是不见故人归来,独居的女子只能含情远望,期待与所思之人相见。诗歌语言浅近直白,但句子之间连接紧密。首先诗人由河畔青青小草的萌发,意识到早春已经来到,可是在这春回大地之时,却不见游子归来。那人应在千里之外,等待归来之日。闺中人定日夜守望,以美好的容颜来迎接心上人。可是,现在她只能遥望远处的高山,将自己的思念寄托给北归的大雁。当夜晚月亮出来的时候,她想象着和心上人共同欣赏这轮圆月。这首诗处处都体现着女子对远游之人深深的思念之情,语言不加雕琢,自然真切,一如其感情真挚,感人至深。除了此类柔情之作,王士熙也用乐府吟咏豪情之歌,如其《行路难二首》,前一首写了自然环境的险恶:
请君莫纵珊瑚鞭,山高泥滑马不前。请君莫驾木兰船,长江大浪高触天。瞿塘之口铁锁络,石栈萦纡木排阁。朝朝日日有人行,歇棹停鞯惊险恶。饥虎坐啸哀猿猱,林深雾重风又凄。
在行路途中面对如此多的困难,第二首便写了“男儿有志在四方”。虽然前景迷茫,路途险恶,依然要能“鸡鸣函谷云纵横,志士长歌中夜起”[4]4-5。这是一种不畏艰险的精神。此二首《行路难》,虽然在气势上不如李白的同题诗作,但是感情真挚自然,也能体现出其坚忍不拔之志。
竹枝词的主要特色在于吟咏风土俗尚,从而达到“志土风而详习尚”的目的。王士熙创作了《竹枝词十首》,其一“居庸山前涧水多,白榆林下石坡陀。后来才度枪竿岭,前车昨日到滦河”[4]17。此诗共四句,勾勒了北方的一段行车路程:出居庸,过白榆林,度枪竿岭,直到滦河。北方的一些地名出现在诗人的诗歌中,为人所知。其四“车帘都卷锦流苏,自控金鞍撚仆姑。草间白雀能言语,莫学江南唱鹧鸪”[4]18。此诗的后两句写了北方的鸟类白雀能够言语,发音不同于江南的鸟类,有自己的特点。此二首,载入杨维桢《西湖竹枝词》,序云:“竹枝本滦阳所作者,其山川风景,虽与南国异焉,而竹枝之声则无不同矣。”[11]554竹枝词由巴蜀民歌演变而成,其表现的内容多为江南风土人情。王士熙所作的竹枝词多用来表现北方的风土,对我们了解北方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王士熙所作的竹枝词,是其在去往上都的途中或在上都时的所见所感,表现的内容也具有北方特色。同时诗人也表达了自己的书写目的,即“要使竹枝传上国,正是皇家四海同”(《竹枝词十首》其十)[4]18。关于王士熙此十首竹枝词的创作背景,袁桷有言:“(至治元年)四月甲子扈跸开平,与东平王继学待制、陈景仁都事同行,不任鞍马,八月始达,留开平一百有五日,继学同邸,八月甲寅还大都,得诗凡六十二首。”[12]206继王士熙之后,袁桷作《次韵继学途中竹枝词》十首。王士熙、袁桷等人在有意识地拓展竹枝词的表现内容,将其表现范围由江南推向北方。此外,王士熙所作的《上都柳枝词七首》也应值得我们关注。柳枝词作为一种歌曲流行于中唐以后,歌辞通常是诗人借咏柳而抒写别情。上都是元朝的首都之一,为元世祖忽必烈所建,城址现在内蒙古境内。其一:“曾见上都杨柳枝,龙江女儿好腰肢。西锦缠头急催酒,舞到秋来人去时。”[4]18每年四月,元朝皇帝都要去上都避暑,等八九月份天气转凉时才返回大都。皇帝在此除了进行狩猎,还会举行传统的祭祀活动。因此,一些随行的汉族文臣也得以见识北方的风俗,而上都也因之发展了起来。王士熙的此首诗以上都的杨柳枝咏起,写到了所见到的北方女子,而最后一句从侧面反映了元代统治者上都之行的归期,也就是秋来之时,上都的发展旺季也就面临结束了。又其四:“侬在南都见柳花,花红柳绿有人家。如今四月犹飞絮,沙碛萧萧映草芽。”[4]18南方的春天花红柳绿,欣欣向荣;而北方的四月却是风沙多发的季节,一片萧瑟。王士熙的竹枝词与杨柳词是其作为馆阁文臣扈从皇帝至上京时所作,所吟咏的皆是北方风土人情,在其表现内容上有所创新,同时具有纪时纪地之特色。这在元代诗坛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元人吴当就有《王继学赋柳枝词十首书于省壁至正十有三年扈跸滦阳左司诸公同追次其韵》十首。
诗歌和绘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但二者存在紧密的联系。在元代,诗歌与绘画实现了高度的融合,这与能诗善画的文人的大量出现有关。王士熙作为一名文士,书画兼长,在绘画方面,《图绘宝鉴》载其“善画山水”。在诗歌创作上,王士熙也留下了他的题画诗作,如《题高房山青山白云图》《虞秘监山林小像》《题郭忠恕九成宫图二首》《骊山宫图》等。其中《题高房山青山白云图》一诗前有序文称高克恭:“能画山水,诗甚有唐人意度。……其作山水,人家多有之,珍藏什袭,其价甚高,为大元能画者第一。青山白云,甚有远致。”[4]22可见,王士熙对高克恭的山水画作极为推崇。诗云:
吴山重叠粉团高,有客晨兴洒墨毫。
百两珍珠难买得,越峰压倒涌金涛[4]22。
此诗的首句和末句将高克恭的青山白云图描绘出来:吴山一座座重叠在一起,粉团似的白云越过高峰,在阳光的照耀下如波涛般汹涌。“压倒”一词显得气势颇为磅礴,虽只两句,但将原本静态的画作十分灵动地呈现了出来,从而实现了诗画之间的相互补充。
三、以清壮伟丽之笔写大元盛世气象
关于王士熙的诗歌创作水平及风格,其友马祖常称赞其与袁桷的画松联句之作:“清壮伟丽,备体诸家,祖常实不能及后尘也。”[13]684此中虽不免有马祖常的过谦之辞,但清壮伟丽,确是王士熙诗歌的主要风格。王士熙清壮风格的实现,主要与其人生经历及性格有关。他出身于儒学世家,且有自己家传的文学创作经验,加上师承文学家邓文原,增长了其学识,又喜交朋友,有了文学创作上相互切磋的机会。王士熙颇为自信乐观,豪情壮志常充其胸间。这在《赠广东宪使张汉英之南台掾》一诗有所反映:
生平不愿为佣书,亦不愿作章句儒。酒酣诗成吐素霓,意气凛凛吞千夫。
前年排云叫阊阖,出门一夜车四角。去年海峤席未温,一舸乘潮又催发。
大江之西日本东,庐陵文物常称雄。决科岁占十八九,君当努力提词锋。
才高不用长叹息,四海弥天岂无识。壮年怀居亦何有,著眼带砺开胸臆。
岩岩柏府凌高寒,豪士倾盖宜交欢。我知屠龙不屠豨,食马政欲食马肝。
吴姬压酒飘香絮,谪仙神游歌白纻。敬亭惟有孤云闲,欲雨人间亦飞去[4]4。
王士熙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他不愿意做一个皓首穷经的白面儒冠,意气风发,满腹的豪情壮志溢于言表。在挥毫作诗时,他的情感表达常是喷发式的,一气呵成。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了创作的冲动,就直接予以抒发。而其诗歌的伟丽风格,与当时诗坛的风气有关。元初北方诗坛“承金氏之风,作者尚质朴而鲜辞致”,而后来值“延祐、天历,丰亨豫大之时”,随着元朝国力的日益强盛,文人士大夫们热衷于歌咏盛世,而“范、虞、揭以及杨仲宏、元复初、柳道传、王继学、马伯庸、黄晋卿”(《练伯上诗序》)[10]55册287诸人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实现了诗风的转变,一改以往质朴的诗风,而多绮丽之语。王士熙的诗歌也正是如此,如其《送巨德新》:
渭城秋水泛红莲,白雪梁园作赋年。金马朝回门似水,碧鸡人去路如天。
扬雄宅古平芜雨,诸葛祠空老树烟。小队出游春色里,满蹊花朵正娟娟[4]9。
此诗中虽提到古迹,如扬雄宅和诸葛祠,但诗中并没有怀古感伤的情绪,转而表达的是游春的快乐和春天的美好场景。身为画家,王士熙擅于构图,且十分注重颜色词的搭配使用。他在诗中大量使用颜色词,有红色的莲花,有白色的云朵,亦有金马,有碧鸡,有颜色鲜艳的花儿,加上空间的几度转换,让人目不暇接,仅用诗歌语言就呈现出了极强的画面感,营造出一种色彩明艳、景色秀美的清丽之境。又《寄上都分省僚友二首》其二:
画省熏风松树阴,合欢花下日沉沉。腐儒无补漫独坐,故人不来劳寸心。
紫极三台光景接,洪钧万象岁年深。 滦江回首九天上,谁傍香炉听舜琴[4]11。
此诗采用了欲扬先抑的写法。前四句描写诗人在松树阴里、合欢树下终日无所事事,表达了一种百无聊赖的情绪,与下文回忆与僚友在上都的美好生活形成对比;后四句通过描写“紫极”“洪钧”“香炉”“舜琴”等意象颇显绮丽,通过今昔对比来表现对过往生活的怀念和对友人的思念。
文学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同时也与朝代的更替、国家的盛衰有着密切关系。元朝是个大一统的时代,文学发展上也出现了“文运向明,文体为之一变”(《胡孟成文集序》)[14]68的现象。在元代,宗唐之声一直此起彼伏,元代文人将盛唐气象作为他们所崇尚的文学风貌。文学与世运之间的关系,在一个朝代的盛世和末世有更好的体现,盛世通常会伴随着“盛世之音”的出现,元代即是如此。欧阳玄曾说:“我元延祐以来,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一去金宋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罗舜美诗序》)[15]64元朝国力日趋强盛之时,在诗歌创作上也有了诗风转变的需要。元人有意要去宋金末世诗歌创作的弊端,追求雅正之风。“盖方是时,祖宗以深仁厚德涵养天下垂五六十年之久,而戴白之老、垂髫之童,相与欢呼鼓舞于闾巷间,熙熙然有非汉、唐、宋之所可及。”(《皇元风雅序》)[16]588追慕盛世,鸣国家之盛,颂时代之美,这是典型的歌咏盛世的雅正之风。在诗歌中具体表现为:注重于歌颂,颇为崇尚“盛世之音”,多“鸣太平之盛治”,不同于“风雅”有批判现实的精神。而王士熙作为至治、泰定年间较为活跃的馆阁之臣,在元代馆阁诗人发展的进程中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正如杨镰在《元诗史》中所说:“元代的台阁诗人真正产生影响,就是在这一时期,由袁桷、王士熙、马祖常等人唱和在前,‘元四家’虞杨范揭继起于后。”[17]29馆阁诗人在诗歌创作上有相同的特点,即对“雅正”之风的追求、对盛世的歌颂。如其《次霍状元接驾韵》:
关头晓日瑞光蟠,隐隐驼铃隔薄寒。金殿巧当双岭合,绣旌遥指五云看。
军装騕褭开驰道,仙仗麒麟簇从官。词苑恩波供染翰,秋风岁岁候鸣銮[4]8。
前四句写边关安定,国家内外一片祥和兴盛;后四句写皇帝身边百官拥戴,供奉翰林之士得以发挥自己的才能,并年年等候随从皇帝出行。每句都可见其对国家盛世的歌颂。这样盛世里馆阁文臣的生活在王士熙诗中有亦所体现,《上京次李学士韵五首》其二:“金烛承恩出院迟,玉堂学士草麻时。明朝出国新端午,彩笔供奉帖子诗。”[4]19臣子们往往需要议定国事、拟定诏书到很晚才能“出院”,但他们对国家和君主心怀感激。诗中称皇帝赐予他们的蜡烛为“金烛”,并感受到皇帝对他们的恩泽,在节日来临之时,他们也会用富丽的辞藻去创作帖子诗来歌颂太平。
王士熙作为馆阁文臣,与其同僚交往密切,也留下了为数不少的唱和之作。对此类诗,顾嗣立评价较高:“继学为诗……与袁伯长、马伯庸、虞伯生、揭曼硕、宋诚夫辈唱和馆阁,雕章丽句,脍炙人口。如杜、王、岑、贾之在唐,杨、刘、钱、李之在宋,论者以为有元盛世之音也。”[11]537此外,杨镰的《元诗史》说“就存诗歌量而言,王士熙并不算多,但在元代诗坛,特别是北方台阁诗人传承过程中,他却占据着比较关键的位置”[17]294。在杨镰看来,王士熙的诗歌创作不仅是馆阁文臣的代表,而且还有传承之功。对于王士熙在台阁诗人中的地位,元人傅若金在《呈王继学大参特领江东宪二首》中写道:“丈人文律擅风骚,往昔朝中属望劳。宣室近闻征贾传,汉庭重见遣王褒。”[18]239可见,王士熙在馆阁文臣中的地位较高,影响力很大。王士熙也在诗中多次写到在元代都城的各种见闻。如其《早朝行》:
石城啼鸟翻曙光,千门万户开未央。丞相珂马沙堤长,奏章催唤东曹郎。
燕山驿骑朝来到,雨泽十分九州报。辇金驮帛分远行,龙沙士饱无鼓声。
阁中龙床琢白玉,瑟瑟围屏海波绿。曲阑五月樱桃红,舜琴日日弹薰风[4]5-6。
此诗前八句记述了百官早朝的情景,渲染了一种严肃而紧张的气氛,但是后四句转向对宫廷建筑、环境的描写,写了用白玉雕琢的龙床、绿如海波的屏风、红似樱桃的阑干以及弥弥的琴声,视野一下子缩小了许多,具有馆阁诗的特点。此外,王士熙在馆阁之时,与袁桷、马祖常、虞集、揭傒斯、宋本诸人的唱和之作不在少数,他们都是元代馆阁诗人的代表。《石洲诗话》卷五就有相关论述:“至治、天历之间,馆阁诸公如虞伯生、袁伯长、王继学、马伯庸,每多唱和,如代祀西岳、上京杂咏之类。”[19]163这在其诗歌创作中有较多体现,如《送虞伯生祭祠还蜀用袁待制韵》:
蜀道扬鞭旧险摧,家山遥认碧崔巍。奉香暂别金銮去,题柱真乘驷马来。
祠罢汾阴迎汉鼎,路经骊谷吊秦灰。归釐宣室须前席,不似长沙远召回[4]7。
此诗用袁桷的韵来写对虞集的送别。袁桷在元廷颇受统治者的重视,“朝廷制册,勋臣碑铭,多出其手”。当袁桷为祭祠还蜀之时,王士熙作此诗有不少恭维之辞,如“题柱”“前席”等。另王士熙有《上京次伯庸学士韵二首》,其二:
长堤芳草遍滦河,谁买扁舟系树槎。金帐薰风生殿角,画楼晴雾宿檐阿。
万年枝上乌啼早,九奏阶前凤舞多。供奉老来文采尽,诗坛昨夜又投戈[4]11。
此诗作于诗人上京扈从之时,前两句写景,描写滦河芳草萋萋的景色,中间四句多写皇帝临时驻扎之时的景象,最后两句写文臣的供奉职责与不易。此诗乃次韵之作,伯庸即马祖常写了多首上京诗作,而元诗人柳贯在他们的影响之下,也创作出了《次伯长待制韵送王继学修撰马伯庸应奉扈从上京二首》。由此,元代馆阁文臣所倡导的“治世之音”诗风逐渐形成,并且影响深远,成为元代早期北方诗坛的特色。
随着人生境遇的变化,中国多数知识分子在出世与入仕之间犹豫徘徊,不论最终是否付诸行动,但是不同的思想在一个人身上也会实现思想上的和谐状态。王士熙出身于儒臣之家,从小接受儒家思想,走上仕途是必然的。作为北方的儒士,王士熙在仕途上有持续晋升的时候,虽中间有流放的经历,但总的来说,他属于统治阶级,其丰富的人生见闻使他留下了具有元代特色的上京组诗,又因其在馆阁之时,积极与同僚唱和,为元代馆阁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是元代“盛世之音”的代表诗人。王士熙又兼画家身份,其绘画创作的思路在其诗歌中也有所体现。不论是他的纪行诗,还是送别诗,都注重对环境的描写,其所描绘的景象在构图与色彩的组合上,均呈现一定的画面感,给人以美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