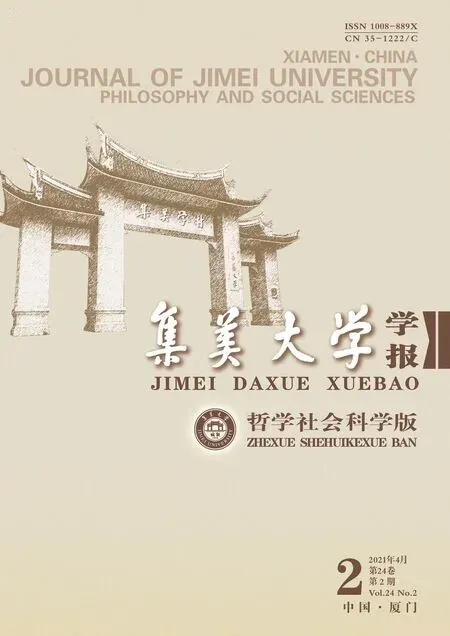陈嘉庚精神对第一代“落地生根”华人的影响
——以孙炳炎为例
黄海蓉
(集美大学 文学院,福建 厦门361021)
陈嘉庚先生一生的雄心是为公众提供教育的机会,对社会的慈善事业和教育事业总是慷慨解囊。在新加坡,他一共集资建了六所华文学校,就如他的儿子陈国庆所说:“教育事业上,我父亲的贡献成为新加坡以及东南亚各地兴学以及其他各地的宝贵财富,使许多新加坡以及邻近各地青年受到了华文、英文基本和先进教育的机会,这些学校过去和现在培养了许多社会各界领袖,他们成为能干的行政人员、卓越企业家、名流学者、著名教授,他们为东南亚国家做出重大贡献。”[1]21
嘉庚先生倾资助学,在东南亚有很多的受益者和追随者,他的精神也深深地影响了东南亚华人华侨。比如印尼侨领黄周规曾在“悼念母校创办人陈嘉庚先生”中写道:“陈嘉庚先生爱国爱乡,热心办学的事迹,早就传遍海内外,为人们所钦仰。回忆我进集美学校时,在入学考试所作《我所崇敬的伟人》一文中,写到所崇敬的几个人物,其中一个就是他。”[2]又比如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孙炳炎,他曾说:“我经历过无数的事,接触过无数的人,然而许许多多都如行云流水,没有留下多少记忆的印痕;虽经岁月磨洗,却仍久久难忘、历历如昨的,就是陈嘉庚先生。”[3]140
作为第一代在海外“落地生根”的华人华侨,孙炳炎深受嘉庚先生精神的影响。嘉庚先生的精神对孙炳炎的影响是那一代华侨华人的典型范例,尤其在对祖国深深的热爱、对中华文化传承的责任感方面。同时,嘉庚精神的浸染也使他们成为心胸开阔、有担当的人。他们对所居国不遗余力的做贡献,积极推进所居国的进步,热心社会工作,又自始至终不忘祖籍国。
一、东南亚第一代“落地生根”的华人
早期下南洋的华侨,在当地是没有归属感的,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衣锦还乡”“叶落归根”。1950年,嘉庚先生选择回国定居集美,也是当时所有华侨最想要的归属——回到故乡,安顿晚年。虽然华侨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出于各种原因留在了他乡,但绝非自愿的行为。新加坡地方小,在以前,是英属殖民地,本来就没有亲近感。新加坡作为世界自由贸易港,更是给人一种流动之感,这是一个做生意赚钱的地方,不是宜居之地。所以,海外华人并没有把新加坡当成故乡,当成自己的归属。
历史上,东南亚的华侨是拥有“双重国籍”的。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1901年清政府通过的《大清国籍条例》,该条例承认“双重国籍”。1912年和1929年的“中华民国国籍法”也是延续了清政府的这种制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南亚各国出现反华、排华活动,为了让海外的华侨们能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我国政府取消了“双重国籍”,支持华侨加入所在国的国籍,为所在国的发展做贡献。
在上述时代背景下,很多华侨成为第一代“落地生根”的华人。1959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1965年新加坡独立建国。孙炳炎就是在这个时候取得新加坡国籍,成为在新加坡的第一代“落地生根”的海外华人。
这一代华人为生存随父母下南洋,“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4]。因生活所迫,所以特别勤劳肯干,在这点,嘉庚先生和他们一样。对那一段创业的艰难岁月,孙炳炎晚年在新加坡森林公司编写的《森林五十年》中回忆说,那时候一门心思只想把生意做好,从早做到晚,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该休息,也不知道什么叫做享受。
嘉庚先生被誉为“华侨旗帜”,是因其汇聚南洋侨胞力量,振臂高呼,成就抗日救国之伟业。随着华侨的身份向南洋各国公民的转换,以孙炳炎为代表的海外华人,本着尊重所在国管理的政治环境、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开展有意义的社会工作服务。他们这一代既承载了叶落归根的老一代华侨的精神,又肩负着把中国的根传承给第二代、第三代华人的责任。因此,他们有着强烈的对祖籍国的热爱,同时,还特别重视文化传承与社会工作。
二、强烈的爱国情感与“超地域”爱国情
嘉庚先生的爱国行为多到不胜枚举。比如,其子陈国庆在《回忆我的父亲陈嘉庚》中写道:“1915年夏天,河北省天津市洪水为患,造成无数生命财产的损失,我父亲带头发动新加坡居民组织对灾民救济。共募捐20万元,这些钱全都汇到国内。1935年,福建省泉州和漳州遭受严重水灾,人民财产和作物遭受严重损失,为了救济灾民,我父亲领导的新加坡福建会馆集款坡币8万多元汇到国内。再来是‘济南惨案’发生后,我父亲帮助了那里因战争造成的灾民。‘济南惨案’使全国人民震怒,为了复仇,他们起来抵制日货,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华人在我父亲的领导下,发动募捐救济这一事件中的受难者。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汇给南京政府财政部超过130万元。还有,他抗议新加坡政府出售鸦片,这件事对东南亚特别是新加坡人民贡献很大。”[1]26早在20世纪30年代,嘉庚先生为祖国的贫民组织了形式多样的筹赈活动,孙炳炎都积极参与其中,正因为这样的机缘,他与嘉庚先生慢慢熟稔,深受嘉庚先生爱国精神的影响。
孙炳炎深得嘉庚先生的赏识和栽培,“早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时我和陈嘉庚先生就认识了,但经常来往却是在抗战后期”[3]140。抗战时期,在嘉庚先生的领导下,孙炳炎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支援祖籍国的爱国活动中。当时的“怡和轩俱乐部”成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的总部,孙炳炎为筹赈会芽笼区分会主席,做出了积极贡献。在维护华商合法权益上,孙炳炎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向日本讨还血债,建立日占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联合东南亚诸国反对船运载费殖民垄断等。1962年1月起,新加坡陆续发现战时被日军杀害的民众遗骸,华人是主要的受害者,因此中华总商会义不容辞地发起和组织了“讨还血债” 的群众活动[5]。1965年,孙炳炎作为中华总商会新会长,先后与东姑总理、日本政府多方交涉,把“讨还血债”与建立纪念碑作为重要的任务继续完成,虽有遗憾,意义却十分重大。1965年到2001年孙炳炎担任“怡和轩俱乐部”主席,时间长达36年。在孙炳炎的领导下,华人参与了为争取公民权运动、推动选民登记运动、火炬运动、创办南洋大学、大马计划以及全民投票等大事件。
孙炳炎14岁远渡重洋到新加坡,1932年创立森林公司。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努力,森林公司发展成为森林企业集团,在建筑、金融、电子、商业等领域为新加坡的建设与腾飞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他作为新加坡国民应尽的责任,但骨子里,他从来没有把中国当做外国。近现代华人最可贵的就是无论自己身在何处,无论自己是否加入当地国籍,都始终忘不了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因此,孙炳炎把自己对祖籍国的热爱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具体行动,回馈桑梓,时刻关心祖籍国命运。
他很早就注重发展与新中国的商贸关系,森林企业经营中国产品,为中国储备宝贵的外汇。20世纪80年代,他还是最早响应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华商之一,他率领新加坡商业考察团来中国开展商务活动,充分发挥了民间外交的作用。担任中华总商会会长时,他在区域内的跨国界运作以及巩固加强中华商会的影响力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战后的新加坡,孙炳炎是较早走出去大范围考察国际市场的华商”[6]245。他不仅为新加坡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始终拥有赤子之心,把自己的爱国思想深深地融入关心祖籍国的发展、为祖籍国服务中。
作为第一代“落地生根”的华人代表,孙炳炎在助力新加坡的经济和生活上,也做出应有的贡献。孙炳炎以中华总商会会长的身份接受采访,公开陈述对“新马分家”的看法,“希望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应当仍将抱有兄弟之邦的情感,维持友好,互相合作和提携,共同获得繁荣进步”[7]34。新加坡独立建国时,作为政治家的李光耀宣布独立时是仓促不安的,但他感受到了华人华侨对未来的信心,“就在我难受的时候,新加坡华人区的商人却欢欣雀跃”[8]。
孙炳炎这一代华人的爱国是超地域的,他们既承载了祖籍国的爱,又热爱着所居国。
三、嘉庚先生倾资兴学精神与华侨兴资助学理念的延续
陈嘉庚先生创办集美学校,开闽南华侨回乡捐资兴学的先河。“立志一生所获财利,概办教育,为社会服务,虽屡经困难,未尝一日忘怀”[9]。陈嘉庚先生倾资办学的时间,从1894年他出资2 000元在集美创办“惕斋学塾”起,至1961年在临终前交代把存款中的大部分作为集美学校的费用、“集美学校要继续办下去”止[10],67年间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但国内国外捐资助学从未停止。陈嘉庚先生创办的新加坡华侨中学,“便是全南洋的第一间华文中学,以后南洋才有雨后春笋般的华文中学出现”[11]。
陈嘉庚先生创办的乐安学校,就在孙炳炎的家乡——厦门集美孙厝。孙炳炎早年就在孙厝乐安学校接受了6年的现代小学教育。因此,孙炳炎虽然不是集美学校的学生,但他就读的乐安学校,嘉庚先生也是校主,拟定的校训也是“诚毅”。他是嘉庚办学的受益者。作为东南亚一带杰出的企业家,在他50多岁的时候,就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更多的社会工作中。受嘉庚先生“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精神的影响,孙炳炎也做到了牺牲自我成就社会。1947年,他创办的森林公司总资产不到50万,正是稳定扩容的关键时期,可是,受嘉庚先生的委托,他接办了乐安学校,接下来的将近20年的时间,他按期足额给予学校办学经费,“1961年1月30日,陈嘉庚生前的最后一封信,就是和孙炳炎讨论乐安学校建设问题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陈嘉庚将孙炳炎当成家乡学校事业的接棒人”[6]303。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长期支持陈嘉庚先生在家乡创办的华侨博物馆、同安同民医院、乐安学校,为建设乐安学校、乐安幼儿园,创办乐安中学出钱出力,还在厦门专门成立了孙炳炎教育基金,以资助教育和学校建设。
1990年,新加坡教育部第一次公布“教育服务奖”名单,奖励在学校义务服务20年以上的成员就有孙炳炎,称他“是这201位得奖中服务年限最长的,共34年”[7]119。他对新加坡的初级和中等学校用心最多,办学思想也不局限华人学校,还关注法国人创办的学校,关注学前教育。身处新加坡独立建国的时期,不局限于华人教育,而是以更宽广的胸襟办教育,立足“培养具有优秀品格并有一般常识的青年”[6]108,“把社会改造得更美好”[6]109。这些思想都是嘉庚先生兴学助学思想的继承与延续。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情感认同与华文教育的弘扬
中华文化、华人的文化信仰,是海外华人维系祖国、眷念故乡的情感纽带。新加坡开埠以来,当地的华人致力于华文教育。孙炳炎推广华文,在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上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领导华人社团,担任中华总商会会长,担任中华游泳会、同安会馆、福建会馆、中华医院基金会等社团的重要职位,这些社团不仅是友好交往的重要象征,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体。
嘉庚先生早年熟读四书,尤其喜欢儒家文化,这在他建设集美学校时,对集美学校的建筑冠名就可以感受得到。比如,现在集美大学校园里的“即温楼”、集美中学的“道南楼”“南熏楼”。同时,他不仅坚守传统,还善于汲取外来文化,创新求变。在集美现存的建筑中,可以看到“嘉庚建筑”的特色,闽南式样的屋顶,西洋式样的屋身,南洋建筑的线脚等。孙炳炎耳濡目染,对“嘉庚建筑”也情有独钟,他捐助的孙厝云龙岩庙,在建筑风格上也体现中国古典建筑特色。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福建会馆修建都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特色。
嘉庚先生在家乡开文化新风,孙炳炎则是致力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加坡的落地生根。他发扬嘉庚先生中华文化认同思想,比如弘扬中医文化,促成中华医院的建立,为推进中医服务新加坡社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陈嘉庚先生将东南亚华人联合起来,让华人抱团,形成战斗力,认同中华文化,陈六使先生、李光前先生都助力中华伦理道德在东南亚地区的成长。孙炳炎与这些前辈先贤一样,竭力促进中华文化在新加坡的存续、发展,促成中华文化的传播交流。孙炳炎弘扬传统文化,是有深厚的情感认同的。在乐安学校读小学的时候,就很喜欢国文一课。有一定的古典文学素养使他对传统文化有更深的理解。比如同安会馆会定期举办“诗词写作与欣赏培训班”。在新加坡的各类演讲中,他也力求讲出中国味道,比如1964年1月,在“新加坡学生家长联合会”新职员就职致辞中,他就引用《三字经》,还多次引用儒家经典名句和中国古典诗歌诗句、中国谚语。不仅如此,他还加强文化建设,受嘉庚先生影响,孙炳炎一直存有“中华情结”,他思索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全球化接轨,比如在同安会馆组织国际性的学术会议,讨论中华文化变迁问题。孙炳炎还强调文化内涵的充实,编纂和保存了有关同安的珍贵文献资料,他组织编纂了《新加坡同安会馆会史》《同安史实》《古今人物志》《各地同乡会馆史略》《文苑》,积极支持同乡开班免费普及诗词创作与鉴赏技巧,促成“华人传统文化的保存与发扬”国际研讨会,立足中华优秀文化在新加坡的开枝散叶。在维护新加坡的华人教育和华人地位上,受嘉庚精神的影响,孙炳炎都是竭尽所能去做。
在推翻清朝统治之前,中文教育在新加坡是不存在的。陈国庆在回忆父亲时曾说:“我父亲说:在推翻清朝统治之前,中文教育在东南亚几乎不存在,只有少数乡村和私塾讲授孔孟之道。有一些英语学校,他们只提供殖民主义类型的教育来培养青年,将来为殖民地的主子效劳。”[12]591911年后,随着清政府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海外华侨中的有识之士会把自己的子女送回国读书,“后来有民族意识的中国人,对南洋侨居国发展中华文化感到兴趣。这样,中文学校在殖民地首先在新加坡出现”[12]60。不到十年,新加坡出现了几百所的学校,“到1940年,整个南洋,出现了从小学到大学各种学校三千所;在校学生四十万人,半数来自马来西亚,也包括新加坡。在各类学校中教授华语,由此华语就成了该地区流行的中国民族语言”[12]60。
对于华人在海外接受华文教育的特殊意义,陈嘉庚先生有自己切身的体会和独到的认识,他说:“对侨居国外的华人学习中国文化比在国内更为重要,因为在国内,一个中国小孩没有接受中国教育,长大后仍是个中国人,而生长在海外的中国孩子,不学习中文,他将被外国文化所同化,最后丧失自己民族的特征”[12]60。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因为华人普遍缺乏专业的技术人员,才没有机会提供祖国急需的人才。相较而言,集美学校由于内迁大田,集美航海学子才得以继续学习,为日后祖国航海事业的建设做出巨大的贡献。1953年,陈六使在新加坡福建会馆执委会上,提议创办南洋大学,孙炳炎响应号召,发动捐款,支援南洋大学的创办。海外第一所华文大学的诞生,预示了海外华文教育更上一层楼。
为了维护嘉庚先生在新加坡的华文教育事业,孙炳炎可谓竭尽全力,用他儿子的话说,就是“父亲晚年捐出去的,都是‘血钱’(即用于养老的钱)”[6]304。孙炳炎在担任福建会馆建设科主任时,为防止公益基金被滥用,他连3000元的小账单都要亲自过目。而这个工作,持续了25年之久。如此的尽心,自己的公司就无暇顾及,以致业绩下滑,但丝毫不影响孙炳炎在助学方面的慷慨。
五、嘉庚精神的现代转换与社会工作新维度
在新加坡,孙炳炎长期致力于社会工作,1964年,新加坡第一任元首尤索夫向孙炳炎颁发了公共服务勋章。嘉庚精神在孙炳炎这里,实现了现代转换。以孙炳炎为代表的这一代华人,成为当地公民后,有意淡化对政治的关注,以现代民主精神关注社会发展,来弘扬嘉庚精神。
孙炳炎为人谦虚,曾说:“有机会为公众服务,乃国民应尽天职,所谓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纵有微劳,实不足称道。”[7]25所以,他竭心尽力地为公众服务,为华人争取权利。1954年9月,孙炳炎以会长名义发函,通知建筑材料枋商会公会会员,在规定时间前往中华总商会集合,集体出发谒见英国殖民部大臣,以支持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关于争取华人公民权和废除议院语言限制的行动[7]318。1963年,孙炳炎接手处于困境的中华游泳会,游泳会员以接受英文教育者居多,但孙炳炎认为,既然名为“中华”,就应该在会刊和通告中另增华文,以示中英文并重的立场。1965年5月,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在吉隆坡举行,孙炳炎还与陈六使等人提出议案,请求马来亚中央政府列华文华语为官方语言之一[7]31。1965年6月,孙炳炎强调了华人相关机构以集聚的力量,发扬华文教育,宣传中华优秀文化。1966年5月,孙炳炎主持“新加坡华校促进母语教育宣传月”并致开幕词,不断地强化华文教育的重要意义,让大家都能爱护母语。提倡接受母语教育是华人的光荣,中华优秀的文化教育不只是影响目前以及未来国家社会,还关系到千千万万的子孙后代。
孙炳炎筹建中华医院,“于1961年创办实龙岗第一分院,于1967年增办芽笼第二分院,赠医施药,为贫苦病患服务”[6]90。在任怡和轩俱乐部主席期间,他致力于社区公益与慈善文化事业,真正实现“集侨贤于一炉,寓娱乐于公益”的宗旨,并将华商的影响力从商场延伸到会馆、学校,三者紧密结合,形成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三结合”机制[13]。孙炳炎利用公司管理机制发展社会组织,提高了工作效率,保障了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孙炳炎在教育、卫生医疗等方面的社会工作,与嘉庚先生的理念相同,是嘉庚思想在新加坡的延续。
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华侨考虑,鼓励支持华侨加入所在国国籍,实现了“落地生根”。孙炳炎加入了新加坡国籍,成为第一代身份转型的华人,但在内心深处,中华文化依然是他安身立命的根基,他始终是受中华文化传统深深影响的华人。因此,对传统文化和乡亲的认识就成为彼此的纽带。作为一个有着中华传统文化认知的人,在内心深处,他从不否认自己对祖籍国的情感。他作为海外华人的优秀代表,毕生服务社会,不仅顺应新加坡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为所在国的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同时,他还保存了对家乡、祖国的感情。
嘉庚先生,这位具有英雄气概的华侨领袖,对孙炳炎的引导和扶持是孙炳炎成长发展的重要力量,对孙炳炎的影响是长久不间断的。嘉庚精神在新加坡传承下来,它不仅为目标远大的先贤陈六使等所学习,也为孙炳炎这样的普通华人所学习,更为我们大众所学习。这才是嘉庚精神最伟大的地方,不是口号,是人人可以学习的一种精神,是每个人的情怀所在。嘉庚先生作为一张文化名片,也必将一直是祖国和海外华人紧密联系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