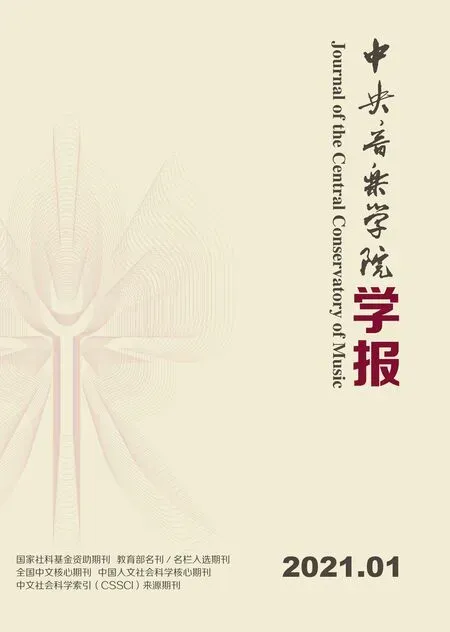新类他者
刘桂腾
查了一下亚马逊的购书记录,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的《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是2012年入手的。时断时续,直到今年疫期禁足在家才掩卷卒读。据说,作为格尔茨关门弟子的拉比诺准备出版这本书时,其导师曾劝其“莫出此书以免自毁前程”。(1)〔美〕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高丙中、康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1页。的确,一改经典民族志书写的传统,拉比诺带着后现代的反骨“把对对象的研究作为研究对象”,哲学地反思了与田野“资讯人”打交道的体验,并把所遇“他性”的种种不适和矛盾摆在了台面上,以从中反观自我。看起来,这与传统的学术伦理不太合拍。不过,一旦把当下的田野景观与其叠对而非镜像的话,拉比诺在20世纪70年代所反思的田野之问便被激活——当代的他者,其何人也?
从“他性”中反观自我
且不论拉比诺是否对那些“资讯人”做了典型化的文学修辞,得承认,一些熟悉、真切的身影不断地在我眼前走动。拉比诺的田野是一次典型的“参与观察”,他介入了乡村摩洛哥人的日常社会生活,与各阶层的社会角色打交道、交朋友。但“参与”与“观察”的比重并不是平衡的,游移其间的调查者难以做到游刃有余:“它们之间的张力界定了人类学的空间,然而‘观察’在这一词汇中居于指导地位,因为它安排着人类学家的行为。”(2)同注①,第84页。我认同这样的看法:无论一个人在“参与”的方向上走多远,到头来依旧是个局外人。亦即:将“不把他人当他者”的矫情视为崇高学术理想,只能是一个背包客终无所归的田野孤旅。因为无论“参与”的程度有多深,民族志书写的结果终究是由“观察”的外在性所决定。(3)保罗·拉比诺:“无论‘参与’能推动人类学家在‘不把他人当他者’(Not-Otherness)的方向走多远,情景最终仍被‘观察’和外在性所决定。在观察与参与这二极的辩证对立中,参与改变着人类学家并指引他走向新的观察,而新观察又改变着他如何参与,但这种辩证的螺旋式上升运动是由起点所掌控的,而这起点是观察。”参见〔美〕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高丙中、康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85页。所以,你永远不会成为他者。这个对自身社会厌倦、失望的学术青年,到摩洛哥实地调查和精神朝圣,完成了一个“剥洋葱”式的由表及里去认识他者,又从里向外来反思自我的循环周期。拉比诺那些形形色色的资讯人,就在这样的田野张力中出场了。
易卜拉欣是个经营食杂店的商人,这位泥瓦匠的儿子非常勤奋且有抱负,是拉比诺进入摩洛哥田野的第一个阿拉伯语老师。相处一个多月,拉比诺终于明白:“他愿意将我引向摩洛哥社区的边缘……,但却深深地抵制任何更进一步的渗入。”(4)〔美〕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高丙中、康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2页。在一次并不情愿的共同旅行中,易卜拉欣试图探知拉比诺是否会为他承担旅费。这是拉比诺第一次直接体验“他性”(otherness)的经历。他发现,易卜拉欣在最大限度地扩大他的资源,并在这个情境中攫取经济利益。但这种行事风格在摩洛哥文化中是标准和正常的。反观自己,拉比诺意识到犯了一个种族中心主义的错误——将田野调查对象“典型化”。他坦言,贪婪或任何其他唯利是图的恶习在自己的文化中俯拾即是。虽然易卜拉欣把调查人视作一种资源,但还没有把拉比诺与那些作为生意伙伴的欧洲人等同。摩洛哥田野的初见,使这位从芝加哥到摩洛哥追寻田野理想之梦的青年人陷入了与“他性”冲突的状态。
其实,这种与“他性”所遇的不适无时不在。与在田野四处游荡却心无定力的“田野漫游症”不同,这是一种因深度参与而遭遇不适的“田野焦虑症”。2017年,我到青海安多藏区作“勒若”(六月会)响器调查,平生第一次走进隆务河谷这个神秘而又陌生的田野地(5)2017年7月8日至18日,帶着上海音乐学院“中国生态音乐学团队”的任务,我携龚道远(摄像)、王晓东(录音)两位助手,对青藏高原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的传统民间祭祀仪式“勒若”(六月会)进行了为期10天的田野作业。。没有向导,进了寨子就蒙头转向。彷徨中突然听到了远处飘来了的鼓声。循着鼓声,我们意外地闯进了当地的一户藏家。这是一个殷实、好客的四口之家,他们正在备鼓准备参加寨子里一年一度的“勒若”。访谈的主要对象是这家的长子,他出家在本寨的一座佛寺修行并习练传统唐卡技艺。这是隆务河谷藏族青年普遍的成长方式。他用还算流利的汉语与我交流,相谈甚欢。奶茶、馃子和友善的眼神儿,一下子就把几天来在陌生环境中疲于奔命而产生的焦虑感化解。分别时,互相加了微信。几个月后,我突然接到了他要为一个为贫困小学募集捐款的私信。一种能够有机会回报的惊喜使我立马回复,请他把捐款账户账号发给我。答曰:“把钱发到我的微信里”。怎么会是这样?!我不知该如何拿捏这事儿。现在来看,或许我的臆测没错,或许在他们那里这就是正常的民间募款方式。但无论是哪一种,当时我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当一个纯粹的工作关系,突然转换为日常的生活关系,“他性”一定会给你带来某种不适。直面“他性”就是对文化差异的理解,但理解不等于无条件地接受;不接受的态度在田野现场应该尽力避讳,而在后期民族志的书写中就不该裁切了。在我们的学术规训中,似乎有一条默认的从业铁律:“不管遇到什么不便或者困扰必须忍受。”(6)〔美〕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高丙中、康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57页。并且,“为他者讳”似乎成了民族志书写的一条潜规则。于是,“赞美诗式”的田野叙事至今依然是主流。
坦率地说,我从未在文化意义、宗教信仰和审美旨趣上全盘、无条件地接受过“他者”。然而,我们的民族志书写总是习惯以想象中的“完美”呈现他者,努力表现对其喜爱的一面。这是真的吗?虽然我也曾努力“不把他人当他者”,但最终的结果依然是自欺欺人。只有坦诚地直面“他性”的田野图景,才是真实而鲜活的。不管一种文化与你如何的不同,甚至看起来有些荒诞不经,只要存在就一定有它存在的合理性。无论是喜欢抑或不喜欢,喜欢一部分还是全部,你都没有权利对其价值做出裁决。这是差别,而不是差距。诚如拉比诺所说:“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差别,当我们对传统赋予我们的象征系统保持扬弃式的忠诚,对话才成为可能。”(7)同注⑥,第153页。所以,尊重和理解就够了。
曾经做过宗教老师的马里克,既能引导拉比诺参加村里的婚礼和宗教仪式,也曾带他到外村夜宿摩洛哥村姑;既是拉比诺最主要的资讯人和最亲近的助手,又是与他发生过直接冲突的好朋友。不过,令我更感兴趣的还是阿里。他虽然不是拉比诺摩洛哥田野里最主要的资讯人,但这个阿里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使我可以“想象性地进入”拉比诺所描述的20世纪70年代的摩洛哥田野情境——见到了我的“熟人”。这个阿里“无所不知而且耐心、聪明、好奇且富有想像力”,是拉比诺在摩洛哥塞夫鲁及内陆地区的绝佳向导。与大多民族志中对资讯人一味示好,报喜不报忧的做法不同,拉比诺坦承他与这位资讯人是一种占有式的关系类型:“阿里知道他帮我越多,我就越依赖他,给他的回报也会越多,我也越发地成了‘他的’人类学家。”(8)同注⑥,第81页。阿里在他的社会圈里是个边缘人:既不是普通村民亦非标准市民,也不和法国人过于卷在一起——一个“局內的局外人”。(9)同注⑥,第81—82页。这位资讯人在局内的口碑不佳,甚至影响了拉比诺在西迪·拉赫森村落的田野进展。这类“无所不知”的资讯人,但凡有过真正田野经历的研究者一定不会陌生。但能够意识到有成为“他的”人类学家的危险,还真的需要一点做学问的勇气!拉比诺认为阿里“非常愿意为钱而工作”,而我们常见的这类“无所不知”的资讯人,更多的恐怕还是为了一种荣誉和权利——对地方性知识的占有和解释权。在“熟人社会”里,我们与资讯人往往是依赖于熟人而结成的新朋友。不过,资讯人“无所不知”的资讯里面也会参杂许多“自以为是”的东西。这样的分析,对于把你引向田野并给予你诸多帮助的朋友来说,是否有些“不够意思”呢?其实,理性的田野反思会比“农民爱”(10)“农民爱”:“中欧斯拉夫民族主义者的故乡在19—20世纪初曾被他国政权统治,因此而造成了他们独特形式的民族主义。在这样的民族/民粹主义的影响下,他们致力于探索和编纂自己民族的‘农民文化史’,将其保存和保护,不被其他对立的民族主义所侵蚀,并以此作为他们有朝一日建立一个具有自己民族文化的国家的基柱,由此出现了所谓的‘农民爱’(peasant love)田野工作范式。……‘农民爱’最为人知的一个例子是波兰知识分子纷纷娶农家女子为婚。”转引自“EM研习沙龙”微信公众号,姚慧主讲,曹本冶点评:Jerry Rutsate,“Mhande Dance in the Kurova Guva Ceremony:An Enactment of Karanga Spirituality”,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42:81-99,2010(发布日期2018年9月21日)。的故事更为真诚。此问无意以道德绑架拉比诺,当然也不想绑架自己。阿里们只是个“局内的局外人”,我们不能隔岸观火。任何道德上的顾虑,都不能将田野的脚步止于此。限定和控制住资讯人的支配趋势,成了贯穿拉比诺整个田野作业的中心问题。老实说,这不也是每个田野初入者的心结么?只不过所遇的支配、控制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沙滩上的可乐罐
拉比诺谈到《写文化》时提到了一个颇有意思的话题:民族志的现在时(ethnographic present)。(11)保罗·拉比诺:“我认为,看起来的确卓有成效,也的确导向新的研究和新的写作形式的一个主题是对‘民族志的现在时’(ethnographic present)的批判。”参见〔美〕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高丙中、康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9页。何谓“民族志的现在时”?我们可以用后现代新锐们一个精彩的比喻来理解这个问题,即:沙滩上的可乐罐——民族志主体日常生活中的当代元素。拉比诺力撑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等人的观点:不要用喷枪扫掉“沙滩上的可乐罐”。(12)〔美〕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高丙中、康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9—10页。这个美式人类学比喻,尖刻地讽刺了经典人类学家以自己对传统的想象来“裁切”田野事实的陋习,道出了民族志书写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的现象:为了看起来更传统,有意回避了那些民族志主体日常生活中的当代元素。认为传统一定是过去的才好的价值观,成了一把扫掉“沙滩上的可乐罐”的喷枪。
我也曾经使用过“喷枪”。2002年秋,我首次来到内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腰林毛都苏木色仁钦博(萨满)家里作调查。一进神堂,正墙自上而下挂有毛泽东画像、成吉思汗画像、萨满师傅良月的照片,香炉、酒盅等。这完全颠覆了我对科尔沁蒙古萨满神堂布置的“想象”。怎么回事?我向同行的那日松提出了这个疑问。他是当地著名的科尔沁萨满文化研究者白翠英老师的大公子。这次我来科尔沁田野,那日松做向导兼蒙语翻译。他不解地笑了:“家家都这样啊!”原来,家里悬挂毛主席像是当地农牧民家里的标配。这时我才注意到,墙面上还有一张时尚的美女图!科尔沁蒙古萨满没有专设的祭祀场所,一般都是在居室里临时设置神堂。其实,毛泽东画像和美女图就是色仁钦住家中的日常装饰。在接下来的仪式记录中,我的镜头取景,便有意避开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当代元素”。并且,在后来整理、编辑这次仪式实录片时,还特意剪掉了所有带有“当代元素”的画面。其实,我所刻意回避的“当代元素”还不止这些,譬如电线杆、楼房等,在后期非编时都被作为“沙滩上的可乐罐”剪掉。按照我对科尔沁蒙古人生活方式的想象,草原、毡房、奔跑的马才是真正的“蒙古文化”。于是,在接下来的一次田野调查中,我把采录地点安排在当地一个有名的旅游区——朱日河牧场的蒙古毡房里。而事实是,科尔沁蒙古人当时早已脱离了草原,土坯房才是他们的标准民居。虽然色仁钦萨满对此予以了友好的配合,但这个当时令我兴奋不已的摆拍——造假,多少年来却成了我心中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前些年我重新剪辑科尔沁蒙古萨满祭祀仪式影片时,终于“忍痛割爱”把这段场景放弃。但如今,这类有意脱离仪式情境的摆拍比比皆是。“民族志的现在时”的时代真相便由此被我们改写。当下的形势比拉比诺时代更加复杂:即便局外人丢在沙滩上的“可乐罐”也被视为合理,并美其名曰“被发明的传统”。倘若真的是民族志主体日常生活中的当代元素,我们的确应当尊重其存在的合理性;若是局外人的有意而为之呢?很不幸,这正是令人忧虑的一个现实。
在拉比诺那里,“当代”并非表示新时代的术语。其理由是:“在许多领域内,旧的元素和新的元素共同存在于多元化的变化之中。”线性进化观的灌输,使我们始终坚信新的一定是好的。断代似乎总是意味着新旧更替,改天换地。结果呢,就是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裸奔式的一味鹜新。在拉比诺的“当代”中,并不意味着新的元素是主导的,他强调的是“变化”和“共同作用”:“如果我们不再假设新的是占主流的,而旧的是以某种方式残留的,那么较旧的和较新的元素如何被赋予形式并(或和谐或不和谐地)共同起作用的问题,就成为一个有意义的调查点。”(13)〔美〕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高丙中、康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2—13页。这个“点”,被拉比诺称为“当代”。他对“当代”的诠释,成了一副观察摩洛哥当代社会的“拉比诺眼镜”,并由此形成了自己的分析主题。就这样,新旧元素交织、传统与时尚共存的摩洛哥的“当代”,理所当然成为拉比诺倾注了心力的“调查点”。对于传统社会来说,在现代化进程中都会面临文化传统延续与社会变革矛盾的问题。回答并因应这些问题,是各类人文科学的学术担当。尽管拉比诺的这个研究似乎并没有持续下去,但他对“当代”的诠释,已浸润在摩洛哥田野的反思中了。于是,“当代”就成了拉比诺人类学辞典中的一个关键词。值得格外注意的是,在这里,新旧元素不再是一个主流/残留的线性关系假设,而是一种共时的并存关系。
在新旧元素并存的“当代”中,乡村里的摩洛哥人努力寻找一种能够“再生产他们的文化遗产和深嵌其中的神圣权利”(14)同注,第13—14页。的手段,以抵御“新兴模式”——法国殖民文化的全面侵入。而当下,在一片功利化“利用”的潮流中,文化遗产及其深嵌其中的神圣权利在“再生产”过程中得到了尊重吗?
文化遗产的再生产
与传统社会不同,城市化背景下的文化遗产再生产已不再仅仅是文化持有者内部的事情了,政府、商界、学府,都成了利益攸关方。随之,“被发明的传统”“共谋”等新潮理论也纷纷落地生花。然而,这些富有启发意义的理论真的是解决“再生产”问题的灵丹妙药吗?在特定的国情中,尤其是在非遗运动与商业大潮的交互作用下,这些实验民族志理论的中国“实验”,极易成为某些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者破坏传统文化生态的说辞;它模糊了文化权利人的主体地位,使得识辨和理解一种传统变得十分困难。我们终于明白拉比诺为何主张“通过对他者的理解,绕道来理解自我”(15)罗伯特·贝拉在“序”中对拉比诺的“自我”和“绕道”做出了自己的解释:“我在这里想说的,也是作者想说的,不是个体的、心理的自我,而是文化的自我……我们从书中仅仅瞥见作者的一个观念:因为已经失去了一种传统的‘我文化’,现代西方知识分子让各种文化合成的总体为个人所利用。显然,这就是‘绕道’所指的全部意思。”参见〔美〕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高丙中、康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7页。却并未给出何谓“绕道”的答案了:“因为他深刻意识到了理解的重重困难……并且意识到了内在于‘利用’这种观念的暴力倾向。”(16)〔美〕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高丙中、康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7—18页。这真是一针见血!显然,他敏锐地看到了学者无度染指其间的弊端。而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远比摩洛哥田野复杂——“利用”文化遗产再生产的权利方不仅来自学府,还有地方政府和商界的过度介入;“再生产”的动因也因此而变成了多源。
2018年初春,带着上海音乐学院“西进南移”研究项目,我到四川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的理县、汶川和茂县作释比响器调查。时逢理县蒲溪乡一年一度的“夬儒节”。从东北转场西南,虽然有高海拔和饮食习惯上的不适,但从林海雪原到高山峡谷的田野情境转换依然令我兴奋不已。不料,几天下来我就陷入无法迅速接近预定目标的焦虑中。藏族舞蹈家扎西江措给我联系了一位县级羌族释比传承人,他长期在县里工作,在羌族释比文化圈里颇有名气,汉语也不错。访谈时,他还找了几位本寨参与组织“夬儒节”活动的青年骨干一起与我交流。他们应答如流,条理清晰。这与我以往的田野经验不同,民间执仪者对仪式一般不会有如此理性的认知。来之前,我曾利用两个多月的时间阅读了释比文化研究的相关著述,显然,他们也读过或听过这些东西,譬如关于释比的分类以及来源等。那么,究竟该如何定位其在田野关系中的角色呢?
这个问题难以一言以蔽之。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无论是用斯大林的“民族”标准,还是用“文化认同”理论,抑或从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来判断,他们都应算是局内人,但不是音乐民族志语境中“标准”的他者。在传统教科书的描绘中,他者的“原型”是异乡、异族、异于本己文化的人。然而,比照这样的“原型”来检视,此他者与彼他者并非完全相同。以这位非遗传承人为例,他自小在传统的羌寨里浸泡、成长,走出大山后又受过汉语文化系统的现代教育。在非遗运动中,因符合官方的遴选条件而被评定为非遗传承人。与从未走出大山的前辈释比不同,他在城里读过书,成年后接触了外部世界,又把自己的理解带入了“传统”,成为新一代的释比文化继承人和乡土文化的维护者。这类他者,并非乡村聚落中封闭式的传承人;而是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崛起的青年群体。与阿里的身份相似,在局外,他是一个局内人;而在局内,他并不直接参与寨子的日常事务,又被视为局外人。但与阿里不同,他是政府认定的“非遗传承人”,享有一定社会声誉。显然,这是一类与前辈释比有所不同的“他者”——局内的局外人。此外,那几位土生土长的青年传承人虽属“真正的局内人”,(17)这类青年人,有的已被认定为较低级别的非遗传承人,有的只是爱好者,或非遗传承人家族培养的继承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当地传统文化复兴的骨干力量。他们参与本寨的内部事务,有的还担任村长、书记职务。但与“局内的局外人”一样,也曾接受过不同层级的现代教育,能操母语并通晓汉语。他们的文化来源于两个文化系统,是游走于本己文化内外的“新类他者”。
权力博弈中的新类他者,已然成为文化遗产再生产的生力军。在乡村聚落中,新类他者正在为“再生产他们的文化遗产和深嵌其中的神圣权利”(18)〔美〕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高丙中、康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4页。积极行动。这种情势与20世纪70年代的摩洛哥乡村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非遗运动中的新类他者还肩负着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服务的责任;加之学界、商界的介入和影响,其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十分复杂且脆弱。如今,早期成为非遗传承人的那些前辈大多年事已高、体衰力乏,已逐渐被“符号化”。(19)在阿坝,几个国家级羌族释比传承人,如汶川的朱金龙除了为来访的旅游客人表演羊皮鼓外,已不太做传统法事了。茂县的肖永庆已离开山寨住在城里,只是在县里重大节庆活动象征性地出出场,日常也只是为求医者看看病。而随着非遗运动的全面展开和制度化,这些年富力强且具双语文化背景的青年传承人群体,已经成为传统复兴的生力军。在全国范围内这不是个案,而是文化遗产再生产中的普遍现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原本为聚落族人精神信仰服务的小众文化,正朝着为游客娱乐的大众文化方向演变。以传统之名而行当代节庆之实的展演——“人造”节,似乎成了时下最为时髦的文化遗产再生产方式。传统复兴的动因,已不单纯是信仰层面上的精神需求和乡村秩序的维护了。在羌寨里,释比作为聚落的智者、民间信仰代言人的力量日渐式微。在地方政府主导下,那些“超自然力”的民间绝技成了节庆、旅游观光活动中的表演项目,而释比仅仅作为传统的象征符号而被“利用”。深嵌于释比文化中的神圣权利,在“再生产”过程中逐渐被消解。于是,置身于文化权利博弈中的新类他者,在处于弱势的形势下是否能够坚守本己文化的主体地位,使传统不至于在“再生产”的过程中被异化乃至同质化,同时又能使其真正成为乡村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就成了音乐人类学持续关注的焦点。
当代语境中的新类他者,已然成为新的传统文化阐释者。“当代”中的传统是新旧元素共同存在于多元化变化之中的;所以,民族志书写的基本任务依然是要对其来龙去脉加以追索与还原。但来自于新类他者对传统的阐释,却往往源流模糊、今昔莫辨。皮埃尔·布尔迪厄在《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跋”中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当他向人类学家组织关于他自己的世界的表述时,他到底在做什么?他与人类学家合作,表述他自己的世界,关于这一表述,他永远也不能清楚地知道其提供信息和编码的图示究竟是从他自己的传统中独具特色的认知结构系统中借来的,还是从民族学家的系统中借用来的,抑或是从遭遇双方的集体分类编码的无意识协商结果的混合物中借用的。”(20)同注,第157页。尽管布尔迪厄的分析结果也许有些冷峻,却极具针对性。这些“自表述”的基本特征,也是构成新类他者现象的突出特点。应当明白:他们已经不是传统的复印机,而是一个新的传统文化阐释者。由此,我想起了阿坝的田野场景。寨子里,几乎所有释比都会讲述释比起源的故事,大同小异而已。然而,这些绘声绘色的故事并不令人感到新奇,在一些地方知识精英出版的著述中早有记述。显然,他们认同了这些由学者“整理”出来的传说。是的,他们需要这样一个故事来证明“传统”的古老。这些资讯究竟是本己文化固有的还是从他者所借?是双方“无意识协商的混合物”抑或有意“共谋”的结果?新类他者所做的文化阐释同样具有这种“自表述”的多源性和复杂性,对此,须加缕析分辨。否则,你所倾情并为之亢奋的那个研究,很可能就是一个被某专家发明的“民俗”,或是一个共谋出来的“非遗”。这并非意味着我们至今依然执念于传统的“本真性”,而是必须明辨“谁之变”的问题;说到底,就是要坚持尊重文化创造者的主体地位。对于新类他者的文化阐释,我取“不浪费的人类学”态度:学习庄孔韶,田野无废料。但是,并非“剜到篮子里就是菜”。不做深入辨析或辨不出啥菜并提出根据,也不会成为一个有效的研究。中国是个熟人社会,很多田野都是通过熟人而得以进入,对此我们应当感恩。但是,作为研究者,也不能任由熟人的牵引演化为牵制。尽管躬身倾听是田野人必备的学养,但放下身段的求教并非放弃原则的盲从。面对泥沙俱下、鱼龙混珠的非遗田野,切莫一不小心成了“他的”音乐人类学家。
田野关系中的新类他者,已然成为文化“互视”的主体。我们讨论新类他者现象,还要在维护文化持有人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廓清文化遗产再生产中的田野关系,以自觉避免内在于“利用”口号中的“暴力倾向”。殖民主义时代,“摇椅上”的民族志资源主要来自于早期殖民官员、传教士、商人和探险家的记述。他们居高临下地俯视田野,民族志的叙事大多是一些异闻奇观和对“他性”典型化的故事。而在某些后现代实验民族志话语中,由“他我对立”陡然跃升为“他我共谋”的田野关系看似界面友好、关系平等,本质上依然没有逃离“救赎思维”的圈套。当边缘文化处于主流文化的漩涡中,“共谋”就只能是一种保护者对他者的高姿态。我特别喜欢拉比诺的田野关系学:“两个主体相视,每个人都是那个自己所处的并限定了自己历史传统的产物,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传统中存在深刻的危机,但依然回溯传统,以期复兴,或是寻求慰藉。”(21)〔美〕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高丙中、康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52页。这是一种主体相视的田野关系模式。
主体互视的田野关系为我们定义了文化持有人的主体地位。与过往单向的“被观察者”不同,新类他者也是个主动的“观察者”。双语文化背景,使其除了无障碍地进行双向交流外,还可通过阅读以及大众媒体接收主流文化信息,检视自己的传统文化支系如何在时代的大河中流淌。主体互视田野关系中的文化遗产再生产,该是文化持有者的自主行为,而非任何局外人“利用”出来的结果。即使“沙滩上的可乐罐”——民族志主体日常生活中的当代元素会成为未来的传统,也该由文化持有者来决定取舍。音乐人类学家不断地看到一笔笔传统音乐文化珍宝因人而存,接着,又因人而逝。人走了,东西也就没有了。他们为此忧心忡忡,悲天悯人,自以为能够力挽狂澜,有意无意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譬如,对于以信仰为精神土壤的仪式音乐,我一直持“自然传承”的态度——自生自灭。信仰是个很“个人”的事。信仰在,仪式自然就在;信仰没了,你为什么要给人家去制造一个“信仰”?大山里缺少的并不是几个抱有救赎思维的专家学者。那山、那水、那方人——传统音乐生息、绵延的自然人文生态,才是需要倍加呵护的河流和土地。所以,当以培土固本为要,而非筑坝导流。倘若音乐人类学家对此感到力乏难竟的话,那么,最为紧迫且力所能及的则是对传统音乐物种做文化基因式的保存。如今,文化遗产再生产过程中既有自上而下的制度性操控(层级式的非遗认定),也有自外而内的社会环境因素影响(知识占有、文化消费)。在我看来,理想的文化权利结构状态,是主体相视、彼此尊重、各尽其责:地方政府给以开明宽松的文化政策保障,学界施以学术性的保存、研究与传播,商界辅以公益性的经济后援;同时,
文化主体也须抱以强烈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心。这样,官民商学间的权利结构才能得到合理平衡。应当承认:“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总是倾向于与它同时代的利益和价值系统保持一致,因为它……只是一种持续的选择和阐释。”(42)〔英〕雷蒙·威廉斯:《文化分析》,载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35页。但,选择的权利主体是传统文化的持有者。
置身于高科技发展的巅峰时代,传统音乐的生态环境剧变使文化遗产的再生产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新课题。对我而言,由《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引发的反思,是把目光投向了“新类他者”现象——谁是文化遗产再生产的主体?如何理解新老他者的差异并与之打交道?当代学术伦理观下的田野关系是什么?文化权利的建构对音乐民族志知识生产有何影响?
可以说,哲学的反思田野作业是拉比诺田野思维的底色;不过,他的哲学反思“没有任何辩证的终点”。(43)〔美〕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高丙中、康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7页。或许,不作终极式论断恰是音乐民族志书写的原动力:田野就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书——天书、地书、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