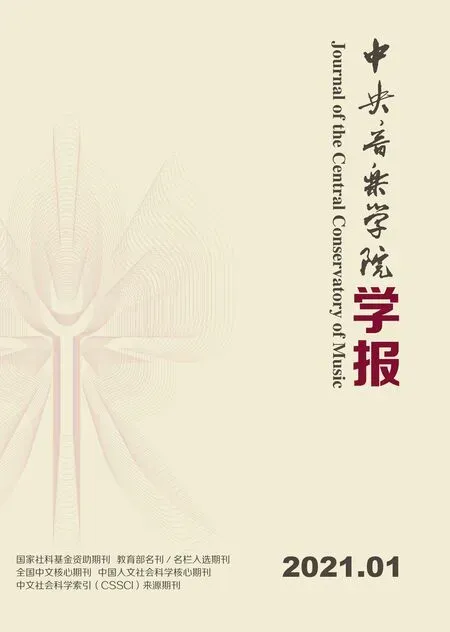中国当代专业音乐创作中的中国视野与个性表达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新时代中国原创音乐作品》学术研讨述评
邢媛媛
2020年11月6日,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新时代中国原创音乐作品》新书首发式暨“中国当代专业音乐创作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学术研讨会在中央音乐学院717会议室举行。此次活动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和国际交流处承办,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协办。
《新时代中国原创音乐作品》是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创作中心”2017年首批委约13位作曲家创作的中国当代音乐作品。其中的7部于2018年1月在美国纽约林肯中心首演;同年4月,其余6部作品在中国国家大剧院首演。这批中国当代原创音乐作品在国际、国内舞台上的集中亮相,引发了国内外业界的广泛关注,并获得了2019年度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此次研讨会以13部作品的出版为契机,邀请了多位参与本次作品出版的作曲家及来自兄弟音乐院校的作曲同仁、音乐理论家、评论家、国际出版界的代表,共同探讨中国专业音乐创作的发展之路。研讨会采用线下和线上两种方式进行,话题从原本的“中国专业音乐创作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扩展到音乐创作中的个性表达、中国音乐发展路径的历史反思,以及音乐出版、文化传播等多个领域。
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秦文琛教授以主办方代表和参与此次创作的作曲家的双重身份发表了致辞。他首先对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在打造音乐精品、促进音乐文化交流方面做出的努力表示了感谢。针对本次研讨会的主要议题,他谈道,今天,要把民族性放在世界性的范畴内,放在更广阔的视域里审视其独特性。民族性的理解不是表面化的东西,一定是深层的,民族性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审美。
一、创作引领:中国视野与个性表达
不同于理论家们的观察角度,音乐创作者的思考大多建立在自身艺术实践的感性体验之上,而这种思考无疑是最为鲜活,也是具有独特价值的。
郝维亚教授以“当代音乐创作中的妥协”为题的首个主旨发言,便跳脱出单纯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论域。他谈道,在具体创作时,民族性和世界性并非自己考虑的首要事情。无论是写作中、西编制或是混合编制,还是使用民族乐器或特色语汇,都不是单纯为了展现所谓的民族性,更多是从个性和作曲家自我表达出发,力求形成一些特殊的音色和乐队之间的组合关系。他将个性化表达作为创作追求的提法,很快获得了在场作曲家的一致认同。
郭文景教授认为,东方与西方,中国与外国,本土与外来等关系,曾经是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这种状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下的紧要问题是将作曲家,特别是作曲学生从各种观念中解放出来。虽然某种程度上民族风格可以掩饰个性的缺失,但光有民族性是不够的,个性要穿透民族性。
唐建平教授提倡用一种发展的态度来理解“民族性”问题。民族性是活的因素,要在不断交融发展中绽放光彩,它与世界性、时代性是兼容的。此外,在探讨民族性时,人们往往忽略这不是简单的风格问题,而是包含了思想精神和社会发展等多重内涵。只有在历史的纵深发展中审视民族性,才能真正彰显民族精神的伟大和力量。
作为70后的作曲家,陈欣若发言所显示出的“轻松”心态颇有代表性。他说,他们这代人对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态度已经没有那么沉重了。他们的生活和创作中混合了包括民族音乐在内的多种文化因素,西方音乐不再是一种外来品。作品只要真实地反映生活就可以了。青年作曲家张帅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认为,创作中最重要的就是作曲家有没有真实的表达。作为与会最年轻的作曲家,85后的田田的表述则更为直接:“民族性不是我作曲时考虑的。我更加关注作品中的精神力量、核心力量。”
值得玩味的是,虽然所有的话语都是指向“个性化表达”,但透过不同年代作曲家的表述,我们可以鲜明地感受到中国新音乐40余年发展历程在几代作曲家身上留下的时代印记。李吉提教授曾这样评价50后、60后作曲家:“如果说,上个世纪末的改革开放使不少作曲家几乎是随着西方现代音乐风潮‘跑步’进入新时代的话,那么随着步入中年,他们已经能够面对世界现代文化艺术的风潮迭起而‘处世不惊’,理智地汲取外来音乐文化中对自己有用的东西,重新建立起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心。”(1)李吉提:《在融合中稳定发展——兼谈朱世瑞和贾国平的音乐创作》,《人民音乐》,2013年,第3期,第25—27页。而对于正在逐渐成熟的70后、80后的群体,《人民音乐》杂志副主编张萌的总结也非常准确:这是有着双重母语的一代,也是“没有宣言的一代”,他们往往通过西方的镜子开始重新认识本土文化的独特意义。相比前辈的作曲家,他们以一种更为轻松的心态投入创作,既可以接受艺术标准的评判,又热情迎接着市场的洗礼。
作曲家们自然离不开具体创作层面的话题。研讨会上,贾国平教授提出“个体性”的概念,引发与会者的思考。他认为,作为作曲家,其职业特性就是永远不满足现状,挑战自我,不断完善自己的作品。只有从个体性入手,关注每一个个体的不同,进而形成群体的表达、群体的气质和群体的精神。因此,关注个体性的不同才是未来研究中国作曲家的正确方式。
陈丹布教授指出,为了给作品注入鲜活生命力,中国作曲家应该走出校门,走出围墙,走到老百姓中间去汲取养料,不光是采集音乐素材,更要体验生活与情感。这样,作品的呼吸、气息乃至情感,才会融进他们的音乐元素。常平教授指出,关于民族性的问题,20世纪初的作曲家更多是对技术方面的探索,20世纪中叶更多是对观念方面的思考,今天,关于民族性的问题,既无需强调,也无法摆脱,因此,他在创作实践中是以一种更为缓和、包容的心态泰然处之。有着多年海外留学生活经验的作曲家姚晨,则从一个更为现实的角度解读世界性和民族性问题。他指出,在国外留学工作很多年,他不得不考虑作为一个东方人,怎样与西方进行对话。这牵扯到在创作时肯定会考虑受众是谁,这是不可回避的。
总结自己的创作实践,郝维亚提出了“妥协”的概念。这里的“妥协”包含着“融合”“折中”“让步”的含义。即当下的创作无需纠结于何为体,何为用,而应带来一种舒适放松和听觉上更具美感、更多细节的创作。这是中国音乐发展的更高的境界。其实,这种逐渐摆脱各种文化标签的束缚,进入创作自由状态的蜕变,在郭文景、何训田、谭盾、瞿小松等上一代人的表述中早已有之。但如今,当它再次以一种个性化的话语被表述,标志着新一代中国作曲家正在迈向成熟和自信。
二、理论驱动:多维度观照下的当代音乐创作
相比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家们的有感而发,理论家和其他院校的作曲家们的发言,既有认知的契合互补,亦有观点的交锋碰撞。
姚亚平教授以“本土化和国际化是中国音乐发展的方向”为题进行了主旨发言。在梳理了近现代中国音乐发展有关“西方化”和“道路问题”的论争历史,以及其背后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之后,他乐观地指出:对于中国新音乐的创作来说,当下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中国的作曲家们能够以一种更为自信、轻松的心态投入创作。姚亚平教授还以民乐的发展为例,谈道:改革开放之初,民族音乐经历了一个时期的低迷,但很快以一种令人始料不及的态势重新获得了从民众到专业作曲家的关注。全球化带来了重新审视民族文化的契机,重塑了民族文化的繁荣。中国的国家命运,中国的音乐,中国民乐都得益于全球化。对中国音乐未来的发展,他提出四点期望:坚持本土自信,保持国际开放,尊重艺术发展规律,坚持艺术的多元化发展。
上海音乐学院贾达群教授的主旨发言题目为“关于‘西方音乐’‘西方技术’ ‘专业作曲体系’‘民族民间音乐’‘个体化’等概念的辨析”。他首先对上述几对在当前理论研究中正在被逐渐异化的学术概念进行了辨析,并指出,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是自我行为,而是互动关系。只有融入到全球化公共平台内,文化和学术的话语权以及影响力才能发挥作用。作为一位作曲家,他的发言自然而然地延伸到创作实践领域。他指出,经典作品在严谨地遵从专业音乐创作法则体系的同时,也自然妥帖而且个性化地将自己的文化传统、艺术意趣与专业创作法则体系融为一体,从而形成自身风格。很多作曲家会避免将民间音乐素材单纯作为风格表现、色彩效果来使用,而是将核心材料打造成具有逻辑意义的结构元素,提高结构层级。西方当代作曲家一方面精炼地保留原生民间音乐的核心材料,另一方面对原生民间音乐最大限度地陌生化处理的做法对我们很有启发。
中国音乐学院金平教授认为,对民族性的理解不能局限在音色、音调、题材上面,这些并不足以支撑作品的民族性。金平讲道:贝多芬作品的民族性与使用民歌并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在于作品既有所处时代的深刻烙印,又有德国文化中的美学和哲学思维。斯特拉文斯基作品的民族性不仅体现在俄罗斯民歌的运用,更体现在对俄罗斯音乐语言、节奏和句法的深刻理解上。巴托克把东欧民族音乐从人类学、音乐学、音乐理论等多个角度融为自己的音乐语言。谈及中国新音乐的民族性问题,他认为,“经过近40年的探索,也许我们现在需要中国音乐的2.0版本,重新明确自己中国作曲家的身份”。
张萌通过对新时代民族管弦乐创作的探讨,回应了会议的主题。他认为,作为中国音乐文化现代化进程中最具时代象征意义的一个文化存在,民族管弦乐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学习模仿、融合创新之后,从内涵到外延都发生深刻变化。今天,它作为国家和民族文化认同的功能已经大大削减,而以多样性的语言传达当代中国人的美学审美和力图与世界多元文化交流的价值取向日益得到凸现。这也让我们认识了包括民族管弦乐在内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历程。
李淑琴教授的发言指出,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伴随世界文化日益交融的大势所趋,民族性和世界性是可以超越的,其途径就是对中国文化的深度挖掘和创新。她特意举了谭盾《敦煌慈悲颂》和姚晨的古琴作品为例,并指出,《敦煌慈悲颂》虽然借鉴了西方受难乐、歌剧以及交响乐的形式和技法,却写出了中国人延续了千百年的精神内核。
三、出版支持:构建音乐生产的全链条模式
作为此次活动的承办单位,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参与了《新时代中国原创音乐作品》的前期采风、创作演出以及出版推广,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与会的作曲家,在感谢出版社工作的同时,一致认为,对于现当代音乐创作来说,这种合作不仅在于物质层面上的支持,还在于权威、确定文本的研究梳理、生产传播,最终对创作形成的强力回馈。郝维亚率先谈到了音乐出版社与作曲家的成长发展密不可分。他指出,历史上很多大作曲家都始终与出版商是密切相依的,出版社甚至会对作曲家的创作产生重要影响。中国作曲家群体与国内出版机构的这种合作还有待加强。
彼得斯出版社(EDITION PETERS)美国部董事长凯瑟琳·奈特(Kathryn Knight)女士和欧洲部的总经理琳达·霍肯(Linda Hawken)女士的联合发言,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这家在世界古典音乐界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国际出版机构 ,从1800年成立以来,便致力于出版当时最具有开创性的作曲家作品,从贝多芬、门德尔松、舒曼到约翰·凯奇、沃尔夫再到乔治·刘易斯(George Lewis)、瑞贝卡·桑德斯(Rebecca Saunders)等当下最先锋的作曲家,彼得斯出版社以一种独特的力量推动了世界音乐创作的繁荣。
过去7年里,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尝试以多种形式与彼得斯出版社展开合作,在两个不同体系的出版环境中不断磨合,摸索出一条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途径。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不仅在与国际同行的合作中获得了诸多有益的经验,更探索出一条向海外传播中国当代优秀音乐文化的途径。目前,这种充满探索性、挑战性的合作已经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并且这些合作对双方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使得彼得斯出版社能够“延续伟大作曲家周文中先生的遗产”(2)引自霍肯女士在《新时代中国原创音乐作品》新书首发式上的发言。她讲道,周文中先生于1949年与彼得斯出版社签约出版了作品《风景》,作为较早与国际出版商签约的中国作曲家,其作品是中国传统美学原则的当代表达,亦对亚洲的现代音乐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方面,此次13部新作品的出版乃是对周先生音乐美学和理念的延伸与继承。,向世界展示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另一方面,这些优秀的中国作品可以得到严格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从而确保世界各地的乐团能够顺利地在舞台上演出。
这些成功的文化传播合作范例,刚好呼应了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黄宗权教授关于“中国当代音乐创作何以产生世界影响”的论题。他指出,就这次出版的作品而言,我们的作曲家已经当之无愧地达到了世界水平。但在人文价值的可理解性方面,我们做得还非常的不够。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中国的音乐文化想要走向世界,产生深远广泛的影响力,除了创作以外,还要关注出版、演出、传播、研究、评论等一系列的工程。
《新时代中国原创音乐作品》即将向彼得斯出版社输出版权,全球发行。这一成果是中央音乐学院“全校联动、整合资源、协同创新”发展战略的集中体现。项目依托学院的优势,充分调动音乐创作、表演领域中青年专家的积极性,充分挖掘学院各方资源,实现了教学、研究、创作、表演与出版的相互促进。这种集“科研—创作—表演—出版”为一体的新型出版模式,将有力推动中国高水准音乐作品的产生和传播,促进音乐文化事业更为健康地发展。正如俞峰院长所言,它展示了中央音乐学院在新时代音乐创作上的综合实力和水准,也必将在中国音乐创作中发挥引领性和示范性作用,带动中国音乐创作向更高水平迈进。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展示出音乐文化领域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3)《新时代中国原创音乐作品》国家出版基金申请书专家推荐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