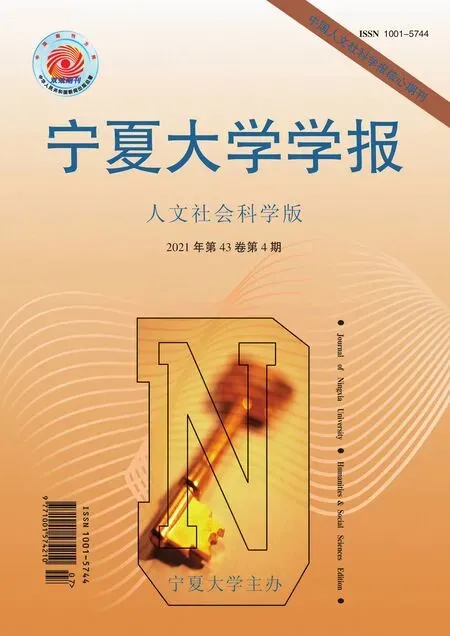陈维崧论词词中的词学观念及其批评价值
徐新武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2)
论词词,又名论词长短句,是词人通过词这一体裁表达对词学问题的见解,是传统词学在词话、笔记、序跋、评点之外的又一批评样式。清初论词词大量涌现,词坛大家大都涉猎论词词的创作。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学批评样式,论词词集中反映了词人们自觉的反思意识和重振词风的努力。如清初词人焦袁熹,在编选《乐府妙声》时,创作了论词组词《采桑子》56阕,其中8阕是其对词体特征的具体认识和评论,另外48首则分论唐五代及两宋词人,词坛名家大都涵括在内。这是最早以论词组词的形式完成的唐五代及两宋词简史,也是词史上第一组论词组词[1]。但焦袁熹的词学成就和声望毕竟有限,而在其之前,词坛大家陈维崧早有论词词的创作,且对清初词坛的影响更为显著。
一 “哀艳无端互激昂”:陈维崧的论词词与清初词坛风尚
据《湖海楼词集》粗略统计,陈维崧留下的论词词一共有44首,虽不成系统,却颇具规模。陈维崧创作的高峰期是在其50岁左右,时尚未赴“博学鸿词科”考试,曾“弃诗不作”而专力为词[2],其论词词也主要创作于此时。当然,没有大量创作经验的积淀,词学思想的孕育和产生就绝无可能。陈维崧经常把自己参与词坛唱和、创作时的心境、词坛要闻以及获读他人词集词作时的感受写进词中,展现了其对词坛的密切关注。他的论词词大致可分四类:一类是为他人词集题词,如《珍珠帘·题宋牧仲枫香词,次曹实庵韵》;一类是获读他人词集词作后的论评,如《鹊桥仙·蒙城舟中,读云臣〈蝶庵词〉》《念奴娇·读顾庵先生新词兼酬赠什即次原韵》;一类是赠别酬唱之作,如《沁园春·赠别芝麓先生,即用其题〈乌丝词〉韵》;还有一类是寿词、悼亡词和题画词等,如《摸鱼儿·春雨哭远公》《水龙吟·寿尤悔庵六十,用辛稼轩寿韩南涧原韵》。总之,陈维崧在构思论词词时,不分时地,不主一格,兼重词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因为他首先是将论词词作为词文学创作的一部分,故注重论词词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味,带有明显的个性特征;其次则是传递思想,借论词词来表达对词坛风尚和词人词集的看法。
清初论词词多产生在词人间的交游赠答和为词集题词的氛围之中,尤其是词坛上盛行的酬唱之风带动了论词词创作的兴盛。词人群体间彼此唱和往还,频繁互动,为词人孕育词学思想和表达词学观念创造了良好的契机。现存1600余首词作的陈维崧,集中交游酬唱之作就达900多首,占其词作总量的一半以上。他前后数次参与词坛上的大型唱和,特别是与词坛各派词人的交往唱酬,使他得以借论词词这一形式在社交酬应的同时,积极向同人传递自己的词艺风格和词学观念。如参与王士祯主持的“题青溪遗事画册”唱和(调寄《菩萨蛮》,维崧词存8阕)和扬州“红桥唱和”(调寄《浣溪沙》,存词3阕)、后期“江村”唱和(调寄《满江红》“涨”字韵,存词9阕)、广陵唱和(调寄《念奴娇》“屋”字韵,存词12阕)和以龚鼎孳和陈维崧为中心的京城步韵唱和,其中,京城步韵唱和前后共有三次活动,分别是《沁园春》唱和(存词3阕)、《念奴娇》唱和(存词10阕)与《贺新郎》唱和(存词11阕)。前两次王士祯主持的唱和,陈维崧、邹祗谟、彭孙遹、吴绮、曹贞吉等人刚刚登上词坛,他们在唱和时择调首选小令,表明其时风气尚未摆脱晚明以来的纤艳之风,但这两次唱和使得词人们初步团聚在一起,有助于词人之间彼此互通,进而切磋词艺,这是后来词坛风气渐变和词学思想交锋的初步征兆。须注意,陈维崧并没有参与当时享誉京城的“秋水轩唱和”,因为彼时其已离开京城,前往河南。但在此前三年与龚鼎孳在京城的步韵唱和中,陈维崧不主一格、哀感顽艳又激昂雄厉的词风已经形成,并对后来京师词人参与“秋水轩”唱和产生重大影响,为清初“稼轩风”的全面回归作了预演和铺垫。此外,作为没落清流公子,陈维崧的社交圈广泛,他与众词友交往赠答,也促使其写下许多论词词。刘东海《顺康词坛群体步韵唱和研究》于陈氏交游词论述颇详[3],其中亦涉及对其论词词的社交属性和批评价值的探讨。频繁的词学唱和,使陈维崧与广大同人团聚在一起,他们既是命运共同体,也共同构建了一个词学社交圈。他们在唱和中“逼出妙思”,一方面逞技炫才,切磋词艺,锻炼词笔而有意创新;另一方面,论词词即是“妙思”之后的产物,是词人词学思想的感性呈现。陈维崧积极介于各种唱和活动中,通过次韵赓和与评骘同人词集词作的形式,完成自己词学思想的输出。这些观念虽然零散感性,不如词话、序跋那般直接明了,却是其词学思想的初始样貌,是词人个性才情的体现。并且与序跋、评点等更富有理论色彩的批评形式一样,是词人词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考察词人创作风格和清初词学流派的重要视角。
论词词本身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统一,它兼具审美意义和批评意义,有着丰富多元的认识价值。陈维崧的论词词不仅准确概括出各个词人的风格特质,还指出词场上模拟雕琢的乱象,提出不主一格、兼容并蓄的创作观念。更进一步,论词词也是陈维崧向外推广词学主张的一种手段,特别是围绕《乌丝词》和《迦陵填词图》题词唱和,直接促使其词学风格和词学观念的广泛传播,最终确立其一代词宗的地位。
陈维崧论词词创作的背后,可能还蕴含着词坛风尚的变化。有学者认为,论词词比论词绝句更多地受到体裁格律的束缚,因此,论词者通常选择格律较简单、篇幅较短小的词调来填,使自己的观点能够更加自如地表达[4]。这种说法可能是指焦袁熹、朱祖谋、卢前等人以小令创作的论词组词,却不符合清代论词词存在的普通情形。实际上,大量的词集题词、词人唱和是通过慢词来完成的,可以说慢词才是论词词的主要形态。篇幅较短小的词调固然凝练精警,但受体裁的限制,内容含量有限,词人的观点基本无法得到充分的表达。而慢词的包容量更大,有助于词人更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词学见解,更能概括和容纳批评对象的特点和风格,丰富我们对词人词作的认识。以本文所论,清初论词词主要采用慢词体式,陈维崧创作论词词主要是选择《贺新郎》《念奴娇》《沁园春》等词调,基本都是长调,其中蕴含着丰富多元的词学元素。如论词词的创作大多是在其词风渐趋成熟前后而选择长调这一体式,又是词坛风尚渐变的反映。陈维崧早年受到词坛崇尚五代北宋侧艳绮靡之风的影响,麈尾时挥,不无声华裙屐之好,多为旖旎语[5],故在早期论词词中也颇欣赏这种纤艳词格。但随着时代风气和家族命运的变化,陈氏词风大变,视野不再局限于体格上纤艳柔弱的小令,又与南北词人频繁唱酬,创作经验和词学思想渐次成熟,逐步确定了具有个性特征的词艺风格,更加偏好以慢词长调来书写自己的行藏出处,更多赞赏苏辛一派的清雄词风,充分发挥词体抒情写志、反映社会的现实功用,在词坛上别具宗风。
陈维崧论词词还暗含一个指向,即是其自视甚高、傲倪词坛的宗主意识。我们现在固然可以视陈维崧为阳羡宗主、词坛大家,但这不无词学观念史层层累积和塑造的意味。而回到论词词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位个性突出的词人,如何通过词来传达他对词坛风气的看法、词人词集的评鉴以及词艺风格的选择。这其中或许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观念,但却是在感性经验基础上的审美判断,是词人个性才情的展现,也是其词学思想的原始形态。如在途经北宋词坛大家周邦彦曾经游宦三年的溧水县时,陈维崧曾作《念奴娇》,不觉发出“弹指六百余年,词人重过,此闲愁枨触。一自汴京时世换,绝调几人能续”[6]的叹惋,感于时移世换,词坛沉寂已久,而隐约以拯弊救衰、领袖词坛为己任。陈维崧曾在《余不作诗已三年许矣……因泚笔和荔裳先生韵亦得十有二首……》其六中宣称“诗律三年废,长瘖学冻乌。倚声差喜作,老兴未全孤。辛柳门庭别,温韦格调殊。烦君铁绰板,一为洗蓁芜”[7],以“喜作倚声”自勉,推举豪放强健的词风,势必要铲除词坛“蓁芜”乱象。正是在这种暗自期许之中,陈维崧敢于表达对词坛纤艳卑俗之风的不满,在论词词中高调地称赏那些大声镗鞳、情深义厚的作品,最终形成自成一体而又兼容并蓄的创作风格。
二 “一卷乌丝饶寄托”:论词词与陈维崧的尊体观
清初词人赵吉士有一首专门推尊词体的论词词,题为《沁园春·有以作词相戒者赋此示之》,词云:“有客告余,嘈嘈小词,亟宜舍旃。顾时日虚縻,公言良是,生涯冷淡,我岂徒然。风月情痴,烟花梦醒,赢得销魂曲里传。从吾好,尽呕余心血,费尽钻研。……熔制辛苏,鞭箠周柳,已种三生未了缘。君休矣,且含毫吮墨,快谱金荃”[8]。用主客对答的形式,表明推尊词体的决心,可以说是最早以论词词的形式宣示“词非小道”的观念,恰与清季王鹏运的《沁园春》“祭词词”遥相呼应。陈维崧亦是较早将尊体观念写进词中的词家,尽管在《词选序》中,他已经明确提出“词非小道”,能“存经存史”,但在论词词中,他以更加感性形象的方式表达对词体的推尊,与更具理论形态的序跋相比,这种形式更具个性特征,给人的印象也更为深刻。在《沁园春·酬赠黄交三,即次原韵并示尊甫仙裳、贤昆月舫》中,他说“三四年来,老惰亡聊,唯耽小词。任世皆嗤仆,为无益事,人方目我,是有情痴。花月前生,水天别馆,似梦年光暗里飞。菖蒲纸,把心情淡写,偷寄崔徽”[9]。黄泰来,字交三,号石闾,江苏泰州人,为黄云(字仙裳)次子,黄阳生(字月舫)弟,父子三人皆具诗名。这首给后学黄泰来的赠词,陈维崧坦言自己三四年来,慵懒无聊,只沉湎于作词。这里的“小词”并非对词体的贬称,而是清初词人用来指称填词的惯用代称。陈维崧坚信当世人都嘲笑他填词是无益之事时,他的一片痴情终将有所回报,所以要借“菖蒲纸,把心情淡写,偷寄崔徽”,积极地用词来宣导自己的心情志意。陈维崧把词视为陶冶性情的工具,重新唤回词体的抒情功用,故能跳出世俗的偏见,高调地推尊词体,并专意填词,在清初词坛极具引领风尚的作用。有意味的是,晚清词人项鸿祚主张“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10],逆其意而出之,但同样是把填词当成排遣治生之具。
既然专力作词,并用词来言志抒情,自然要求在创作时寓含寄托,有深致之思。陈维崧一生抑郁侘傺不得志,又逢国难家难,满腔悲愤无处诉说,只能发之于词,故其词举凡诗骚、经史子集、笔记皆可入内,几无事不写,故所作自然大气淋漓,寄托深远。当他用这一标准自许时,也在无形中称赏那些寄托深厚之作。易代之际,以陈维崧为主的阳羡词人群正是自觉将寄托理论运用到创作中,从而影响了整个清初词坛的风尚。
在《贺新郎·寄兴呈遽庵先生,用溪南词韵》中,他说:“一卷乌丝饶寄托,怪时人、只道填词手。说诗者,固哉叟”[11],《乌丝词》刊刻以后有众多题咏,但大部分人只是徒示夸耀之词,陈维崧对这一点深为不满,他不无自负地说出“一卷乌丝饶寄托”,正是点出了结集这部词集的良苦用心。宗元鼎为陈维崧《乌丝词》作序,引陈维崧论词语谓“丈夫处不得志,正当如柳郎中使十七八女郎按红牙拍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以陶写性情”[12]。这也表明陈维崧是借词体来陶写性情,来表达“丈夫处不得志”时的苦闷,所以表面上看似绮丽哀艳之词,实际上都有沉厚的情感寄托。陈维崧在《绮罗香·龚节孙录余所选今词,赋此奉柬》中谈到自己编选《今词苑》时的感受:
浪打新亭,霜飞故国,谁许词场称霸。红豆金荃,漫向夜深誊写。半闲钞、酒馆银墙,半偷传、妆楼罗帕。到如今、粗比牛腰,丛残卷轴蜗涎挂。 太息韦庄牛峤,问如何偏遇,极天兵马。珍重君家,重觅蛮笺细砑。看残秋、满箧香词,是老夫、半生愁话。嘱宵阑、好护乌丝,莫使缸花灺[13]。
龚胜玉,一名眉望,字节孙。江苏武进人,流寓嘉兴,有《仿橘词》。“所选今词”云云,即指由陈维崧等人编著并刊刻于康熙十年(1671)的《今词苑》(又名《今词选》)。据今人闵丰统计,《今词苑》各卷词作、词人数量分布为:小令79人214首、中调42人95首、长调60人152首。《今词苑》共存词461首,而其中的小令、中调占据大半,可见确实是“红豆金荃”“满箧香词”[14]。这固然和清初词坛尚未脱离晚明余习有关,但陈维崧怕龚节孙误解而专门解释“看残秋、满箧香词,是老夫、半生愁话”,说明这部当代词选是具有深厚寄托意味的,并不只是艳词丽语、无关痛痒之选。这一点,方炳也注意到了,在《金缕曲·书陈其年〈今词选〉后,用刘须溪韵》,他评价《今词选》“屈正则、行吟披发。留下楚辞多哀怨,怨灵修、空对他乡月。不见处,鼓湘瑟”,认为《今词选》的作品多类屈原《楚辞》,充满了哀怨之辞,这实际上是将词体的功用等价于《诗》《骚》,从而用词体来写题旨厚重的社会人生。不仅如此,方炳也和陈维崧一样,“看《草堂》《花间》各选,微多不合”,这类词“温柔无骨”,格调不高。故陈维崧又在《词选序》中专门批判了学步《花间》《兰畹》,“矜香若为当家,以清真为本色”,所导致的“闺襜冶习,音如湿鼓,色弱死灰”的词坛乱象,他明确表示“仆本恨人,词非小道”,故选编此集是为了“用存雅调于千年”,选词所以存词,是和“存经存史”一样重要的[15]。
陈维崧重视词的体用功能,“以秦七黄九作萱草忘忧”[16],在效法宋人佳致时,无论是学习何种风格,都是以“陶写性情”为旨归。他曾感叹“满箧香词,是老夫、半生愁话”,而填词正提供了释放愁闷的渠道。在《蝶庵词序》中,他引史惟圆语曰:“夫作者非有《国风》美人、《离骚》香草之志意,以优柔而涵濡之,则其入也不微,而其出也不厚”[17]。与史惟圆一样,陈维崧也重视词的立意,讲求比兴寄托,并将词上溯《诗》《骚》,实际是在本体论上将诗、词并举,将诗歌的社会功用转嫁给词,这是陈维崧等清初词人推尊词体时的一种策略。其中,“入也不微,而其出也不厚”说,更是启示了后来谭献等人的“入微出厚”说,指出“寄托”的步骤和方法,对清中叶以降词坛的重意思潮影响甚大。
然而,词要有寄托,要写得大气磅礴,还必须重视对创作主体情感的培养和挖掘。只有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有感发人心的力量,才具备史的厚度。实际上,以“情”为本,也是陈维崧词作中始终贯穿的理念,他那些大气磅礴、沉厚有力的作品,无一不是出于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实际的情感激发。可以说,重视挖掘创作主体的真情实感,才是陈维崧药治明词纤艳无格、浮藻俚俗的一剂猛药,也是其打出自家旗号,反对模拟,主张独创而自成一家理念的根本支撑。在《摸鱼儿·春雨哭远公》中,陈维崧哭悼亡友史鉴宗,读其词而感叹“衰年故国逢知己,天也把人轻妒。情最苦。记前日、文园一卷多情句。病中亲付”[18],指出其词“情最苦”和“多情”的特点,唯此真情贯注的作品,读起来才格外有震撼力。据陈维崧《青堂词序》,史鉴宗卒于康熙甲寅春(1674),临终前曾将《青堂词》托其收藏理董。后来他在《玉山枕·秋夜较亡友史远公〈青堂词卷〉竟凄然缀此》中,更是对史鉴宗词中“夜深健句怒盘空,看笔底,崖崩涛泻。更兴酣、蚁视群儿。掷琵琶、踞酒垆而骂”[19]的真情豪兴表示激赏。与史鉴宗的遭遇一样,陈维崧亦常年“浮沉学社,为生徒师”,羁志不达,相同的身世和经历,促使其对史鉴宗产生“了解之同情”,能看到《青堂词》中蕴含的不平侘傺之气。史鉴宗曾言“以词为萱苏焉”,这和陈维崧主张作词“以陶写性情”相一致。故陈维崧对“情”的呼吁和重视,与清初词人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和心理状态相适应。词人们不可能再回到模仿花间纤艳风格的逼仄老路上,而必须用词来抒写内心的愁闷和悲哀,寄托亡国破家的黍离之悲、漂泊羁縻的身世哀叹。须注意,主情之论和尚寄托的词学观念,经过陈维崧等人的大力提倡和实践,渐成为清初词坛创作蓬勃兴盛的一大动力,是词坛复兴的内在支撑,也是清初以降整个清代词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体非一格”:包容并蓄的创作观
在《词选序》中,陈维崧明确表示“盖天之生才也不尽,文章之体格亦不尽”[20],人的主体性情千差万别,决定了文章体格、气度的不同,故不应偏废一家。具体来说,词有多种体格,“夫体制靡乖,故性情不异。弦分燥湿,关乎风土之刚柔;薪是焦劳,无怪声音之辛苦。譬之诗体,高岑韩杜已分奇正两家;至若词场,辛陆周秦,讵必疾徐之一致”[21],从而主张不分奇正、体非一格又兼容并蓄的词学观念。沈松勤先生说:“阳羡词派以作者的性情意志为本位的主体论词学理论决定了他们包容并蓄的创作观,在包容并蓄中对多元艺术风格的追求与实践,自然孕育了‘取材非一体,造就非一诣’而众体兼备的宏大气象。”[22]这种“包容并蓄的创作观”凭借论词词的形式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在评论词人词作时,陈维崧既崇尚唐五代、北宋小令艳词的清丽柔婉,又主张兼取两宋慢词长调的结构章法;既欣赏艳词丽语、旖旎婉约之作,又推崇纵横变化、瑰奇兀傲之风;既主张融汇辛陆周秦于一体,包容并取,又拒绝以“豪苏腻柳”为蓝本,模拟雕琢,而专尚一家。
陈维崧论词词中,就欣赏艳词丽语、旖旎婉约一类风格而言,如《贺新郎·题郁东堂词,仍用前韵》中说,“我把《金荃》词一卷,字字写成钗脚。是吾友、东堂之作”[23],赞郁植(东堂)继承《金荃》艳体词风,并用“钗脚”形容其词环转婉约、遒劲有力的本色特质。而在《念奴娇·春日读京少梧月新词,寄题一阕并呈尊甫慎斋给谏》中,评价蒋景祁《梧月词》“字字俱精绮。高才妙作,定摩秦柳墙垒”[24],受秦柳词风的熏染,作品精密绮丽。又主张融会南北宋词风于一体,如在《摸鱼儿·早春接山阳陆密庵先生札,兼惠我月湄词,赋此奉酬》中,形容陆氏词“似脱线真珠、乱向窗栊洒。篇篇无价。便周柳纤柔,辛苏感激,材尽出君下”[25],兼举周柳纤柔婉丽之风和苏辛激昂铺排之调。《念奴娇·读顾庵先生新词,兼酬赠什,即次原韵》“评曹尔堪新词”“老颠欲裂,看盘空硬句,苍然十幅。谁拍袁綯铁绰板,洗净琵琶场屋。击物无声,杀人如草,笔扫柂毫秃。较量词品,稼轩白石山谷”[26],认为曹尔堪词品融辛弃疾、姜夔、黄庭坚等词风于一体。在为史可程(号蘧庵)的寿词《贺新郎·奉赠蘧庵先生仍次前韵》中说,“识得词仙否?起从前、欧苏辛陆,为先生寿”[27],也是认为史可程熔铸了“欧苏辛陆”多种词风,从而形成“豪气轩然独有”的清劲词风。
相对而言,陈维崧词学思想成熟以后,更偏好兀傲挺拔而又清爽磊落一类的词风。如《贺新郎·送吴瑹符归武林》中说,“词句沈雄兼感激,似尔惊才希有。论笔势、苍然最陡”[28],赞赏晚辈吴瑹符词沉雄激昂,笔势峻峭,是词坛上少有的气格;《水调歌头·题友人词并示方邺大匡》,赞赏友人“新词句,真磊落,太纵横”;《水调歌头·读董舜民苍梧词题后》中,评董舜民词“中有奇文兀傲,每夜必腾光怪,鳌掷与鲸呿。力压古声叟,气慑万獠奴”,词品兀傲诡怪,词气磅礴厚重,认为董氏词字里行间“既似苔纹瓦篆,又似碑残鼓罄,字里吼於菟”[29],如龙腾虎啸。另如《贺新郎·秋夜呈芝麓先生》其二“我得公词行且读,任侏儒饱饭嘲臣朔。大笑绝,冠缨索”;《贺新郎·题沙介臣词,并柬周翼微、郁东堂二子,仍用前韵》“评沙介臣词”“硬箭软裘推劲敌,爽气毫端喷薄。乍出手、双雕都落”[30],皆是对此种激昂沉雄之词风的推崇。实际上,陈维崧对龚鼎孳、董舜民等人词的评论,用来形容其本人的词风,又何尝不可。
陈维崧包容并蓄的创作观念,又使其内在地排斥模拟雕琢的习气。正如蒋景祁《陈检讨词钞序》所说“纵横变化,存乎其人……若规格一定,意境无异,如世摹画化人宫阙,纵极工丽,一览已尽,又况乎胶滞笔墨者耶?文章之道亦如是而已”[31]。作品风格的纵横变化固然与创作主体的性情差异紧密相连,但如果仅仅墨守一家,偏尚一格,都会导致笔墨胶滞、意境无异,写出来的作品千人一面,毫无艺术生命力,所以陈维崧对这种词场陋习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在给曹贞吉的《珂雪词》题词时,他说道:“满酌凉州酝。爱佳词、一编《珂雪》,雄深苍稳。万马齐喑蒲牢吼,百斛蛟螭囷蠢。算笛拍、莺簧休混。多少词场谈文藻,向豪苏腻柳寻蓝本。吾大笑,比蛙黾。”[32]他不满词场上许多人写词论词,专意规模“豪苏腻柳”,视之如小弱蛙黾,根本跳不出自己的狭隘视野而看到广阔的词学天地。所以,高度推举《珂雪词》的雄深苍稳,如“万马齐喑蒲牢吼”,向因袭规模的沉寂词坛发起了猛烈的冲击。前引《贺新郎·奉赠蘧庵先生》中也说,“不是花颠和酒恼,豪气轩然独有。要老笔、万花齐绣。掷碎琵琶令破面,好香词污汝诸伶手。笑余子,徒雕镂”[33],认为“花颠酒恼”式的叫嚣粗率并不等于轩然豪气,专意艳词丽语的香软词风,只是徒饰雕镂,而丝毫没有真气和活力。因此,在《珂雪词·咏物词序》中,他说曹贞吉“事皆磊砢以魁奇,兴自颠狂而感激”,故下笔“嘻嘻出出”“怪怪奇奇”[34],个性激昂颠狂,词风诡奇多变。
四 “一清难画”:追求词境之“清”的艺术品格
把“清”作为一个审美范畴,最早可以追溯到曹丕的《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至”,稍后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更是对“清”的内涵进行了深入开掘,如《风骨》篇发挥曹丕“气之清浊有体”之说,而进一步提出作文须“风清骨峻,篇体光华”,明确表示对“清俊”文风的崇尚。《定势》篇说“赋颂歌诗,羽仪乎清丽”,又对赋、颂、歌、诗等文体提出“清丽”的要求。在《章表》篇中论“陈思之表,独冠群才。观其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则专门落实到对曹植“表”文“辞清而志显”的赞赏[35]。 此后,“清”的审美内涵愈发丰富,杜甫的《戏为六绝句》第五首,直接提出“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36],则把“清词丽句”的创作审美观纳入诗学批评之内。南宋的张炎率先将“清”这一范畴引入词的审美领域,在《词源》卷下专门提出“清空”这一概念,明确要求“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味”[37],将“清空”和“质实”对举,反对《梦窗词》雕绘满眼、凝涩浓丽之作。“清空”是南宋清雅词派推举的一个核心审美范畴,对清代的词学批评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陈维崧是清初较早关注词学中“清”这一审美要素的词人,虽然他对此并没有详细、系统的论述,但在论词词中,却可以看到他对“清”的推崇。在《贺新郎·魏塘舟中读尔斐先生菊农词稿》中,陈维崧专门论及词境之“清”。词云:
笔补娲天罅。笑词场,止贪浓腆,谁餐龙蚱。只有《菊农词》一卷,竹翠梧光团射。向楮墨,蒙蒙欲下。爽胜哀梨清橄榄,更险如雪饯宵行怕。快瀑布,炎窗挂。垫巾野服神飘洒。句清圆,诸船易及,一清难画。把向鸳鸯湖上读,涧水奔浑似马。雪又向,篷窗乱打。好琢琉璃为砚甲,架霜豪,床用珊瑚者。还倩取,锦棱藉[38]。
“尔斐先生”,即钱继章(1605—1674),嘉兴人。他是明清之际柳州词派的代表人物,有《菊农词》。康熙十三年(1674)秋,陈维崧过访嘉兴魏塘,拜读其《菊农词》而有此作。这首词的上阕,陈维崧直抒对词坛“止贪浓腆,谁餐龙蚱”风气的不满,一方面嘲讽了仅仅贪恋浓词丽句、徒饰辞藻的词场群像,另一方面又对词坛“谁餐龙蚱”的寥寥无几和后继无人充满失望。将“浓腆”与“龙蚱”对举,明确表示对词坛清风的呼唤,故对《菊农词》透露出来的稀有的清劲之气十分赞赏,比之“爽胜哀梨清橄榄”。“哀梨”,用《世说新语》典,相传汉秣陵哀仲家种梨,味美而大,是为“哀家梨”,后用食“哀梨”来形容文辞清爽流畅之美,如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评论苏东坡诗,说“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也是用“哀梨并剪”来形容苏东坡诗风之清爽磊落。在《水调歌头·题友人词并示方邺大匡》中,陈维崧论友人“新词句,真磊落,太纵横。我作致师乐伯,摩垒更靡旌。爽若并州快剪,又若短兵狭巷,杀贼不闻声”[39],赞叹其清爽磊落的风格,这里“爽若并州快剪”与“爽胜哀梨清橄榄”所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都是对清爽词境的追求。“橄榄”,又名青果,味略苦涩而又芳香,盛产于南方沿海地区,此处也是形容读《菊农词》就像食橄榄,甘美清爽,而又回味无穷。另如《鹤冲天·题邹生巽含小像》,陈维崧形容看邹生画像所感,“风情何澹澹。乍展吴绫,回味略如橄榄”[40],此处虽是看画摹人,但却回味无穷,透露出再三把玩的审美余韵,“回味略如橄榄”恰可形容其追求青涩而有韵味的词境。
这首《贺新郎》词的下阕,陈维崧从读《菊农词》后的整体清爽之感转移到对局部字句的赏玩,“垫巾野服神飘洒。句清圆,诸船易及,一清难画”。“句清圆”当指词句的清美圆转,读起来谐婉顺畅,无生涩滞闷之感。陈维崧另在《无愁可解·题桢伯诗词卷尾,用黏影词韵》中说,“只佳句、清抵空山夜泉,剪灯读、睡难著”[41],也是对好词句清空峭拔、声情谐婉的赞赏。如果说“句清圆”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话,那么“一清难画”的混成词境则对词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毕竟很多人写词有句而无篇,拆碎下来不成片段。陈维崧在这里提出对词境“一清难画”的审美追求,既准确地把握住了钱继章词作风格的艺术特质,又丰富了“清”这一审美范畴的内涵,即词境之“清”,不仅要求字句层面的清圆妥帖无滞涩,还要求整体风格上的清劲有力、浑成而有余味。
陈维崧追求词境之清的艺术品格,与其实际创作中的“清美”取向高度契合。《迦陵词》中这种“一清难画”的作品并不鲜见,如《绕佛阁·寒夜登惠山草庵贯华阁》下阕“坐客松寮,钟鸣黄叶寺。喜今夜关河,一碧千里。感伤身世。看六代青山,月华如水。是千秋、倚阑人泪”[42],“六代青山”与“今夜关河”对举,身世之感和清寂之情境高度融合,词境清俊谐婉而又苍茫浑厚。晚清朱祖谋在论词组词《望江南》中称赞陈维崧“跋扈颇参青兕意,清扬恰称紫云歌”,即指出了其飞扬跋扈而又清扬婉娈的独特词风,故“清”这一审美范畴已经成为陈维崧词学观念和作品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注意的是,“清”和其他风格并不冲突,以豪放之气出之,可以写得清雄跌宕;以平和之气涵濡,可以写得清婉悠扬;以纤艳之笔摹之,也可以化为清丽哀婉。总之,“清”的内涵极为丰富,类似于批评史上的“元批评”范畴,结合词人的性情气格、审美偏好而能混融多种审美元素,如形成清丽、清雄、清圆、清艳、清空、清婉、清美等多元审美风格,最终并不拘泥于单一固定的艺术取向。然而稍后的浙西词派为适应康乾盛世的文治氛围,专意姜张,以清空为尚,逐步剔除了“清”的多元意蕴,将蕴含其中的创作主体的情感和思想排除在外,一味地讲究形式上的雅致妥帖、审美上的清空淳雅,而忽视情韵和思想的贯注,实际上已经背离了“清”的本质,重又使词坛陷入雕绘无聊的沉寂局面。
五 余论
论词词首先是一种文学创作,其次才是词学观念的表达,它融创作与批评于一体,是词人、词心和词境互融共生的产物。陈维崧的很多论词词如《贺新郎·题曹实庵珂雪词》《摸鱼儿·春雨哭远公》,情感真挚,结构细密,在对词人风格进行评赞的同时,往往将家国身世、周围环境贯穿其中,写得荡气回肠而又哀婉动人。一方面,论词词营造的词学意境,往往包含了词人的生活足迹、文艺活动、情感偏向以及审美崇尚,蕴含了十分丰富的词学元素,是我们认识词人词作及其词学思想的重要参考,另一方面,论词词的大量出现和词坛的繁荣局面紧密相连,借助词的形式来践行批评观念,除了形式上的创新,还有对词体本身的尊崇。作为词学批评的重要一环,论词词的涌现对清初词学的建构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但也需要注意,论词词对词人词集的评鉴大多是印象式、概括式的,用一整首词的内容来评价词人词作、表达词学观念的论词词毕竟不多。大部分论词词为兼顾词的艺术性和思想性,而只能作散点透视、蜻蜓点水式的批评,主题无法集中,意义指涉也较为笼统,很难全面而准确地概括评论对象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旨趣。因为一个词人的词学思想总是变化流动的,其创作也可能兼具多重风格,故论词词这种批评形态有着体裁上的限制。此外,词人借助论词词表达其词学见解时,又多使事用典,故表达时易流于晦涩难懂,还有一部分题咏词集的论词词,不过是词人间礼节性的标榜应酬,艺术性不高,陈维崧的论词词也有这样的不足。总体而言,论词词传达的词学观念是有限的、粗糙的,然而以词评词,本身就富有形式和技巧上的挑战,是词人标榜自我、参与词坛对话的一种方式,像那些题咏词集的论词词,性质和词集序跋一样,往往随词集的刊刻出版而流传四方,不失为传播词人声名及其词学思想的重要媒介。可以说,论词词基本贯穿了词人交游、创作、词集刊刻、传播的各个环节,是清初词坛复兴的一个重要表征。从这些方面来看,论词词的价值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
——评陈水云教授新著《中国词学的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