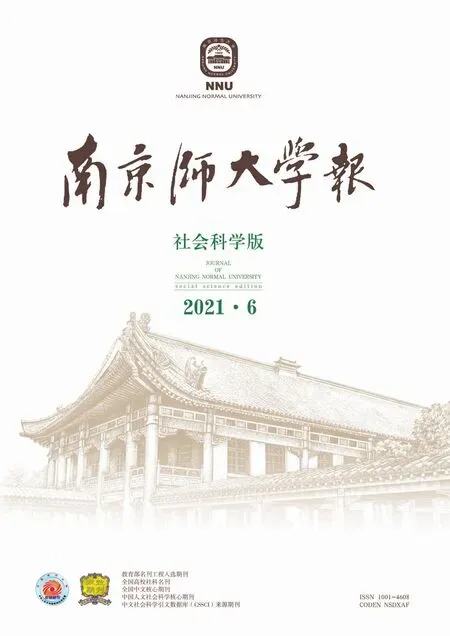文化工业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思想维度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的现代性反思
梅景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现代社会的文化发展已经与经济、科技和政治的发展相互同化。与传统社会的文化相比,现代性社会文化最大的特征就是文化创作已经与商品经济和工具理性结成同盟,使文化创作以工业化和产业化的形式占领了现代人的生活世界,从而导致大众文化的兴起和精英文化的衰落。这一现象也引起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深刻反思,即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的迅猛发展,对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会产生哪些方面的重要影响?
一、 大众文化批判与意识形态理论的现代性转型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领军人物逃亡到美国时,让他们最为震惊的不是美国的经济形态与政治制度,而是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工业的发展,美国的好莱坞现象让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人产生深刻的反思,从而导致了《启蒙辩证法》《单向度的人》等系列著作的诞生。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对现代性文化发展的问题及其对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了深刻的描绘与反思批判。他们最开始想用“大众文化”来描述工业时代的文化产业化现象,但最终,他们认为文化与工业的结合,已经形成了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一种独特语境,它是完全有别于传统社会大众文化创作的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因此只有“文化工业”这个新词才能完整地表述文化与工业合谋的时代文化景观。当然,在很多时候,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具有相同的含义。因为,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发展的现象不断发生变化,但其在科学时代和商品时代的共同的物化本质却始终影响着现代人的生活世界。
从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的生成语境来说,现代科技的发展使传统的文化创作和传播能够借助各种现代性工具与时俱进。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又使原本属于精英阶层的文化作品变身商品,进入大众消费的范围之中,获取文化艺术之外的商品价值。这一转变导致大众文化从原来民间的非主流地位,成为蔓延于整个现代社会的主流文化现象。而大众文化与现代工业化操作的联姻,使大众文化转变成可以无限复制的文化产品,成为现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消费品。在阿多诺等人看来,大众文化是指借助于大众传媒而流行于大众之中的通俗文化,包括通俗小说、流行音乐、电影、艺术广告等。它融合了艺术、政治、宗教和哲学等各方面,以娱乐消遣的方式操纵大众的思想和心理,培植支持统治和维护现状的顺从意识。
大众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发展,是文化自身发展的必然逻辑,因为文化经过阳春白雪式的传统孕育后,也必须从天上降到人间,经受下里巴人式的现代性洗礼。而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来分析,现代社会文化向大众化和工业化的转化,实质上具有意识形态发展的必然逻辑。即进入商品经济时代之后,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资本主义统治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反思与批判。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的发展,其实展现了现代社会中物化意识与阶级意识的对抗,从根本而言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之间的现实博弈。
如果对意识形态概念的思想内涵及其发展进行深层次解析,可以深入理解两种意识形态话语权博弈的本质及其表现。从马克思、恩格斯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卢卡奇、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他们在相关著作中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与阐释,都具有双重维度。在狭义的思想维度上,意识形态主要是指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马克思、恩格斯都强调这一点,因此他们虽然在批判维度上提出意识形态是“幻想”和“怪影”,也在建构维度上提出意识形态是“观念的上层建筑”。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8页。当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统治权力时,也必然要在意识形态上占据绝对统治的权力。当资产阶级在与封建主义和传统宗教作斗争,从第三等级的地位中脱身而出,成为占有绝对权力的统治阶级时,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意识形态的确是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但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及《资本论》的问世,毫不留情地撕开了资本主义虚假的温情脉脉的“自由”面纱,而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剥削”的本质予以深刻揭示,并展示了真正的人类理想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图景。让已经被资本主义所同化的“阶级意识”重新在工人阶级中传播。在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面纱之下,资本主义内部的深刻矛盾都被遮蔽,而一旦被马克思所揭开之后,的确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不同的阶级意识与统治意识之间的博弈与斗争。当然,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也敏锐觉察到马克思所揭示的的确是一个本质性的问题,但他们也能够因为马克思的批判来转变自身的统治逻辑和统治方式。从政治和经济领域来说,他们给工人阶级让渡部分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让资本主义社会从金字塔型的剥削统治社会转变成橄榄型的福利治理社会,让部分工人阶级逐步向中产阶级转化,甚至让他们感觉自身才是资本主义国家真正的统治者。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虽然没有直接导致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但通过思想观念的影响,让西方国家的统治逻辑和统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型。与此同时,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资本主义的精英们有意回避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所阐明的诸多问题,而是刻意塑造现代性的物化意识来消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而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的发展在物化意识的建构中发挥了核心的功能。
在广义的思想维度上,意识形态也包含着特定社会形态中各个阶级(阶层)的阶级意识,也包括各个时代人民群众的政治意识和文化意识等。广义维度的“意识形态”的思想内涵,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也是有所涉及的,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提出:“思想的闪电一旦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这就说明,每个阶级(阶层)的民众通过对于哲学和文化知识的学习,可以形成属于自己的群体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可能是与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相互交融,但也可能是相互博弈甚至相互交锋。当不同阶级(阶层)民众完全认同于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时,社会形态就属于稳定的发展期。而当不同阶级(阶层)的意识形态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发生严重的博弈与交锋,社会形态就必然进入动荡革命的时期,在历史上必然会形成重大的社会变革。当然,这种意识形态的博弈与交锋,往往与生产力的变革及经济利益的分配格局的转变相伴随。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卢卡奇、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广义维度的意识形态思想内涵有着更加深刻的阐释,他们从“阶级意识”“文化领导权”“工具理性”和“大众文化”等不同维度,分析了现代性的语境下不同阶级(阶层)的意识形态如何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发生着本质的关联。而且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狱中札记》《启蒙辩证法》和《单向度的人》等著作中,作为统治阶级思想观念和作为不同阶级(阶层)民众阶级意识的意识形态都是显性存在,甚至表现为辩证交融与相互博弈的关系。当然,在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的思想中,两种维度的意识形态更多是以“文化意识”的方式来发挥作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用“文化意识”来影响着人们的“政治意识”,并形成新的意识形态统治逻辑。而他们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对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进行深入批判,既是对处于单向度封闭社会领域中物化意识形态的反思与超越,也是两种意识形态话语权相互博弈的重要表现形式。
二、 传统与现代之辨:文化工业的物化效应
从本质而言,本真的文化意识应当是对物化意识的反思与超越。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文化最初的涵义都与“人化”相关,中国《易传》中最初出现文化是“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西方的文化概念最初与农业相关,意味着种植与栽培,无论是“人文化成”还是“种植栽培”,文化都是让人从物的品性中超脱出来,具有属于人所特有的品格与趣味,即使在从事某种文化创作时要借助于物品和工具,创作文化的人也一定要让这些物品和工具具有人的灵韵与思想。就如同艺术家用毛笔在绢帛上画一幅山水画,虽然笔墨和绢帛是文化创作的必需载体,但在画家的创作之下,笔墨和绢帛宛如具有了与人相通的灵韵,能够以最好的方式展现艺术家的构思与所要表达的情感。
文化创作中灵韵与思想的表达就使文化意识本身同物化意识相互疏离与博弈。文化意识追求的是人对物品的操控与役使,能够让物和工具完全按照人的思想意图来展现生命所领悟的悠然意象。并且能够完全超越物化意识而使文化的创作臻于最高的境界。但现代性的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却用工具理性完全替代了文化意识中的超越性追求,而将文化创作和文化消费普及到每一个大众的生活世界之中。如同《启蒙辩证法》中所言:“整个世界都要经过文化工业的过滤”。(3)[德]霍克海默、[德]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3页。
从大众文化自身所追求的将“文化创作”和“文化享受”从天上下降到人间的旨趣而言,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契合了现代性社会生活世界的发展趋势。因为作为普通民众,即便他没有创作的思想,也没有创作的技艺,但他却可能有从事文化创作的冲动,以及消费文化作品的欲求。现代性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最大的悖谬之处就在于,它同时具有肯定性和否定性的特征与功能。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的肯定性在于,它能够给予现代人最大的文化创作和文化消费的空间,让原本和文化创作及消费无缘的人都能够随时进入文化创作和消费的领域,而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人”。而其肯定性在另一个层面上就是,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能够让现代人无条件认同现代社会的商品经济和物化境遇,能够以自我肯定和相互认同的方式推进现代社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进程。如约翰·B·汤姆森所言:“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文化工业的发展是现代社会中增加理性化和物化过程的内在部分,这个过程使得人们越来越难以独立思考和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他们极少或无法控制的社会进程。”(4)[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11页。
现代大众文化的否定性在于,它受到工具理性和商品经济的双重宰制,能够将文化的本质降低到商品和工具的地步,从而将文化自身超越性的维度完全否定和消解。大众文化虽然让普通大众都能够享有创作与购买文化产品的自由,但这种创作和购买却在现代工业技术的辅助下产生,脱离了现代性的工业技术,大众文化的创作和传播都会成为问题。虽然传统的文化创作也需要借助于工具和包装,但文化思想却在其中占据主体地位。现代大众文化的创作和传播已经被工具和包装所裹挟,成为缺乏思想维度的平面的物化现象的生产与蔓延。就如同一首流行歌曲一样,如果没有各种声乐工具的包装,没有电视网络的传播,音乐和歌曲已经很难成为深入人思想和情感的旋律。大众文化在将自身变成产品和商品的同时,也改变了现代社会的商品结构和文化格局。
大众文化更深层次的否定性在于,它通过对于传统文化意识的否定来形成现代性的文化逻辑和统治逻辑。如同辩证法的自我否定维度一样,大众文化一定要通过对传统文化意识的否定来展现自身现代性的价值。传统文化意识从根本而言是一种精英意识,它所体现的是文化精英对于普通大众的统治地位,因此,传统文化意识其实与政治上的等级意识相互关联,即传统政治结构的不同等级身份可以享有不同特权。同样,不同的精英阶层也掌握着不同文化创作和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而现代大众文化借助于商品来传播蔓延,从表面看,它是要通过自由平等意识来否定精英阶层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特权,从而消解文化领域中的等级观念,让大众都认为自己在文化中已经获得全部的创作和享受的权利。但实际上,这种对传统文化意识的否定,却造成物化意识的生成,即在商品拜物教领域存在的物化意识渗透到文化领域,这种文化领域的物化意识以其自由平等的假象来为现代大众文化的价值正名。但实际上,文化领域的物化也导致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物化,在此物化意识的生成与蔓延过程中,不但传统文化的意识被予以否定,深藏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阶级意识”也被消解,每一个人因为大众文化的愉悦享受,而对现实的政治与文化意识形态下意识地接受。因为,“文化工业的权力是建立在认同被制造出来的需求的基础上,而不是简单地建立在对立的基础上,即使这种对立是彻底掌握权力与彻底丧失无力之间的对立。晚期资本主义的娱乐是劳动的延伸。人们追求它是为了从机械劳动中解脱出来,养精蓄锐以便再次投入劳动。然而,与此同时,机械化在人的休闲和幸福方面也会产生巨大作用,它能够对消遣商品生产产生巨大的决定作用,于是,人们的经验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劳动过程本身的残余影像。”(5)[德]霍克海默、[德]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123页。
当现代性的科学技术与大众文化联盟后,大众文化就成为现代社会独特的产物——“文化工业”。作为文化工业的大众文化将精英艺术与世俗欲望同化,将人的文化意识物化为现实的商品拜物教,文化艺术本属于理想和审美的维度,如今却转变为满足世俗欲望的工具。在这种转变过程中,现代人的意识形态也被物化,而成为工具理性和商品拜物教的衍生物。现代性的文化工业主要迎合在现代工业生产中身心疲惫的人们的需求,通过提供越来越多的娱乐消遣活动来消解人们思想深处的超越维度和反抗维度,使人们在平面化的文化模式中逃避现实,沉溺于无思想的享乐,与现实相认同。这正如《启蒙辩证法》中所描述的:“工业的力量留在了人类的心灵中……整个文化工业把人塑造成能够在每个产品中都可以进行不断再生产的类型。”(6)[德]霍克海默、[德]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114页。
从意识形态与现实生活世界的关联来看,传统文化所映射的意识形态是现实生活世界的理想性延伸,而现代文化工业所映射的则是现实生活世界的欲望化延伸。传统文化是精英阶层社会意识形态合理性的论证与凝练,表达的是统治阶级的理想性诉求。传统社会文化虽然也有娱乐化和大众化的倾向,但往往在历史的积淀中被排除在文化传统之外。因此,在历史中传承下来的经典文化都是意识形态的理想性维度,给予现代人一种哲学思想和伦理价值上的启发。而现代性的文化工业,以短平快的方式构建着大众文化的快餐形式,实际将现实生活世界变成平面化的结构,使整个生活世界的意义和意识形态的追求在娱乐化的商品消费中沉沦为欲望的幻觉。正如他们所言:“文化工业把娱乐变成了宗教畅销书,心理电影以及妇女系列片都可以接受的胡言乱语,变成了得到人们一致认同的令人尴尬的装饰,这样,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情感便可以受到更加牢固的控制了。”(7)[德]霍克海默、[德]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130页。
现代性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的生产与传播方式,也深刻地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及对于文化艺术价值功能的体认。从文化的本质价值功能而言,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现代大众文化,都具有不同层次的价值体现和功能定位。从文化的超越性而言,文化创作和文化交流的最高层次是追求人自身的自由与超越。因为文化的本质是人化,而人化的最高目标就是超越外在物质的束缚和人的内在心灵的束缚。就如同庄子所体验的与物俱化而又坐忘心斋的逍遥境界,可以说是达到了文化的自由与超越。而相比于自由和超越而言,对于幸福的追求则是文化的另一个维度的价值功能。当然,文化领域所追求的幸福既是世俗的幸福,也是道德意义上的幸福,只有个体通过文化的涵养,而使内在的道德操守与外在的礼法规则相融通,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时,从而让德福相一致,这才是文化发展的高层次的价值功能的体现。
当然,当文化创作和文化消费融入人的生活世界时,它所追求的就是现实中的愉悦体验。在这一层次上,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就充分发挥其独特的功能,让人能够获得文化创作、文化消费和享受中的愉悦、休闲和快乐。就如同一个创作经典乐曲的作者,他自身具有自由的心灵,对于生活世界的独特的生命感悟,然后将这种自由超越的思想和独特的生命感悟化为动人的旋律而流传后世,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高山流水》和《阳春白雪》莫不如是,这是最高层次的自由和幸福的文化追求与体验。但现代性的流行歌曲的创作和消费,如在KTV唱歌却是为了愉悦当下疲惫的躯体和紧张的心灵。
当大众文化进一步受到物化意识影响时,却可能导致大众化生活方式的庸俗与堕落,从休闲和快乐的文化意识向游戏、消遣和取乐的文化消费方式转变。也就是说,文化与娱乐的结合不仅导致了文化的腐败,同时也不可避免会产生娱乐知识化的结果。(8)[德]霍克海默、[德]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129页。当文化工业以游戏的方式进行批量生产并且完全统摄了世俗的生活世界时,就表明现代大众文化已经彻底与物化意识相融合,而将人从超越自由的文化意识中疏离出来。因为游戏本身是一种休闲放松的方式,是文化的一种剩余消费样式。从古典到现代,“游戏”从来没有在文化中缺席,但现代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所制作出来的“游戏”与传统文化中的游戏的最大区别在于,古典文化中的游戏是从属于精英文化和经典文化的辅助文化产品的创作,如古代社会的文字游戏,以及各类娱乐的游戏。传统社会中的游戏依然是现实生活的折射,是现实创作的剩余产品。而现代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所制作的游戏,已经从文化领域的边缘地带进入到中心地带,已经用游戏作品取代了经典式的文化创作。而且网络技术和媒介技术的介入,使现代社会的游戏具有了更加充实的主体性生命,游戏已经不仅仅是现实生活世界的反映与回声,而且可以自成一个系统,形成一个独立的、虚拟的文化的生活世界,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游戏自身才是有生命的主体,创作游戏和玩游戏的人却成为从属的客体。
现代文化工业所制作出来的游戏已经敉平了现实生活世界与虚拟生活世界,人与物之间的真实边界。游戏已经可以成为文化创作中的主宰。而且游戏通过物化意识渗透到人的心灵与个性结构之中,使现代人的文化理念被游戏观所充塞。当然,从正面看,游戏的心态使现代人在文化创作上具有了更多自由和超越的意识,能够摆脱物化的处境而创作出一些真正具有灵韵的作品。但游戏的负面效应在于,大多数人被游戏自身所物化,很难聚精会神于文化思想的反思与体验,而被游戏带入到消遣和取乐的境地。当文化工业通过游戏将人带入到消遣和取乐的层次,就表明现代大众文化已经彻底与商品经济相契合,成为了最为廉价和劣质的消费品。以消遣和取乐为目的的文化消费,也逐渐消解着人自身的自由和超越性的创作维度,而使人与物及商品日益趋向同一。这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言:“文化工业把艺术作品装扮成政治标语,并把这些作品在讲价之后灌输给反感的观众,于是,它们便像公园一样,成为了公众的消遣场所。不过,即便它们失去了真正的商品属性,也不意味它们真正退出了自由社会的生活,事实上,防止它们退化成为文化产品的最后一股力量,也彻底消失了。”(9)[德]霍克海默、[德]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145页。
三、 文化工业与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逻辑的融合
从意识形态的广义维度来看,文化工业似乎消除了传统意识形态对于生活世界的控制,但它却无处不在地表达着信息工业和商品经济对于大众精神生活的垄断。现代文化产业和传统文化表面最大的区别在于,传统文化总是披着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话语的面纱来对民众予以教化,因而经常受到现代人的非议和责难。而文化工业正好以“去意识形态化”的表象满足了大众对于“纯文化的”内在追求。文化工业表面上拒斥一切传统的意识形态,也拒绝和政治联盟,单纯地追求商业价值与利润和文化产品的单向度繁殖,为大众的生活世界营造一种文化繁荣的虚幻场景。但事实上,文化工业却给现代人植入了更加物化的意识形态话语,即商品拜物教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渗透到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中,使大众的思想与判断受到齐一化的文化产品的垄断与宰制,而沦为现代工业文明与商品经济的附庸。在此意义上,技术时代的大众文化成为一种新的统治形式,它的商品化和同一性特征消解了艺术的创造性和个性化,同时,它的消遣娱乐功能又消解了人们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和内在的超越维度。因此,大众文化虽然从表面上并不具有意识形态的特质,但它对现代社会的操控和统治更为深入,具有无所不在的特征。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从文化的维度表达了对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总体性批判,而这一批判建立在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和启蒙的基础之上。正如哈贝马斯所言:“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发现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已经动摇了,但他们依然想坚持启蒙的基本框架。因此,他们把启蒙对神话所做的一切再一次完整地应用到启蒙过程当中。由于他们反对理性作为其有效性的基础,所以,意识形态批判变成了总体性的批判。”(10)[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37页。
马尔库塞在意识形态研究上保持了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大致相同的思路。他的代表作《单向度的人》的副标题即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马尔库塞在此书中深刻批判了由现代技术理性所操控的单向度社会、单向度的人和单向度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在他看来,发达工业社会虽然给人带来技术上的福利,但技术理性的扩张导致现代人文化意识的物化与压抑,表现为精英文化与高尚文化的大众化与世俗化。如果将封建社会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前工业社会文化和发达工业社会文化进行比较,明显可以感受到文化艺术的失落与异化,与之相伴随的,则是价值判断与审美判断的堕落与异化。发达工业的资本主义社会主导的是“技术宰制了艺术,理性压抑着诗意,资本剥夺了道德”的时代,这正如马尔库塞所断言:“同马克思主义用以表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其自身和与其工作之间的关系的概念相对照,艺术异化是对异化的存在的有意识的超越,是‘更高层次的’或间接的异化。”(11)[德]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49页。而且,在现代文化的传播过程中,高尚文化被现实生活所排斥,文化意识形态屈从于技术合理性的进程,人们的文化天赋和艺术灵感逐渐物化为满足世俗化需求的文化机器的零件。
从社会结构和发展逻辑来看,现代大众社会和传统社会的文化逻辑与统治逻辑也大不相同。“传统的统治结构是把人的基本需要和高一层次的(体育、娱乐)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把经济剥削增加到最大限度。然而,今天的统治结构变成使大众的各种需要和资本主义的需要一致,废除基本需要和第二层次需要之间的差异,从而使统治增加到最大限度。”(12)欧阳谦:《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解放》,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116页。也就是说,传统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限制,生产与消费之间、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矛盾与张力,必须通过扩大生产而限制消费的方式来增强统治阶级权力的稳固。既要通过最大限度经济利益上的剥削来彰显不同阶级的地位差异,同时,要限制受剥削者的高层次需求和文化消费,来保障统治阶级思想的垄断地位。
而现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机器工业已经逐渐代替工人手工劳作,而且技术与文化的联盟,导致文化工业的发展,可以满足更多人的文化消费的欲求。此时,生产和消费之间,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就不是简单的对抗性矛盾关系,而成为多元化的、复杂的、同一性发展的辩证关系。如给予工人更多的文化消费和生活消费,不仅不会抬高无产阶级的政治地位,而是更好地培育其对于资产阶级统治的物化意识与顺从意识,即通过更多更好的大众文化娱乐的供给,能够让工人阶级消除其内在的抵抗意识与革命意识,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逻辑产生内在的认同。在此境况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差异随着消费差异的减少似乎得以消解,而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逻辑却变得更加内在而深入。
当然,我们要用辩证的思维来看待文化工业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双重影响。一方面,文化工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工人阶级的反抗性意识,使他们认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并顺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逻辑。但另一方面,文化工业的发展是否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精英和文化精英也会造成“物化效应”,让他们在文化产品的“拜物教”中消解自身的阶级意识。在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领军学者看来,文化工业所造成的大众意识形态的整体物化和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是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的一种“预谋”和“设计”,其目的就是消解工人阶级的革命与反抗意识,从这一目标来说,似乎他们也达到自身的目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西方依然是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如果作为个体的人,在这种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语境之下,的确也有物化的可能,比如资本家的“商品拜物教”,但这种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物化,是以个体性形式存在,它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来说,是一个逐步转变的过程,而不会立刻发生统治阶级自身统治意识的消解。这也如同马克思所言“异化和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具有自我物化和转变的可能,但是这种统治意识不会立刻消解。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也不会将意识形态的阵地拱手相让,而是需要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觉悟,以及通过意识形态的博弈和思想革命等多种方式完成这种转变,这也是当代依然需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引领社会思潮发展的必要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