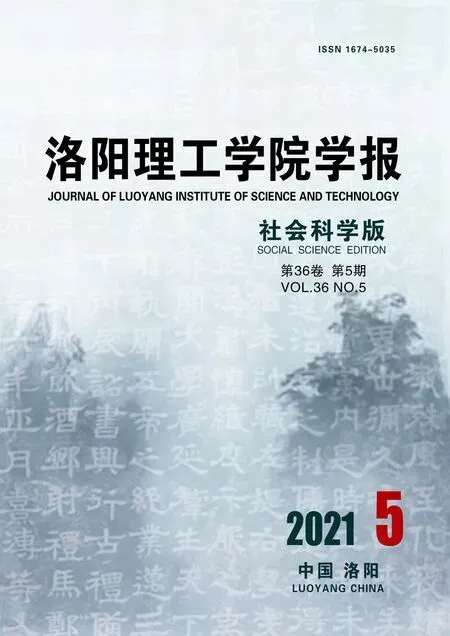以“三不足”为中心看王安石对皇权的塑造
韩 新 芝
(安徽大学 历史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在北宋崇文抑武的风气下,随着士大夫群体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在此情况下,王安石上承庆历新政以来经世致用的思想,对于北宋面临的内忧外患,欲进行改革。在改革中,王安石深感庆历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反对派的攻讦导致皇权支持的动摇。相比于以改善吏治、恢复官僚机构为改革主要内容,以除弊为目标的庆历新政,王安石的改革力度更大。王安石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展开的对朝廷法度的大规模变革,引起长期以来偷合取容、怠惰疲懒的广大官僚和士大夫的强烈反抗。王安石的改革举措面临的是整个士大夫集团的打压。面对如此孤立的局面,皇帝的支持是王安石变法最强有力的倚靠。如何保证皇权对于变法的持续、强力支持成为王安石自变法之初就亟须解决的问题。一方面,为使皇权有能力与士大夫阶层对抗,王安石必须努力解除皇权所受到的束缚;另一方面,王安石必须通过种种举措加深宋神宗对其变法思想的认同,以保障皇权对其变法的绝对支持。由此,王安石必须伸张皇权,并不断加深自己对皇帝的影响力,同时还要把反对变法者推到宋神宗的对立面,力图在最大程度上朝着推进变法的方向塑造皇权。
一、“三不足”与熙宁政治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1]10550。此“三不足”之说是否出自王安石,学术界颇有争论。但毋庸置疑,王安石正是以此作为变法的主要依据来影响宋神宗,抬高宋神宗的地位,解除宋神宗对于天命、祖宗之法和人言的顾忌,抵消反对派对变法的阻挠。
(一)天变不足畏
在儒家经典中,天人关系是约束君主言行的重要法器。在天人感应理论中,灾异是对君主的警告,灾异的发生意味着天人关系不和谐。面对灾异,皇帝需要内省修己、外施仁政,采取应对措施。同时,负有调和阴阳之职的宰辅大臣也需要承担责任,“古者大臣以论道经邦,燮理阴阳为职。故凡阴阳不和,雨阳愆若,皆大臣不职所致”[2]12。因此,对天变解释权的争夺,成为变法派和反对派的焦点。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司马光等反对派,通过天变灾异来警示宋神宗,诋毁王安石及新法,频频把灾异归咎于王安石及其所推行的新法,以此动摇宋神宗对变法的支持。由此,否定天变与人事的联系成为王安石的首要且必须做的事。
变法伊始,御史中丞吕诲把天灾归咎于王安石。熙宁二年(1069)六月,吕诲上书指出“方天灾屡见,人情未知。惟在澄清,不宜挠浊。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3]1182,请求罢免王安石以务清净。熙宁五年(1072)正月辛丑,司天监灵台郎亢瑛借天文星象的异常攻击王安石,“天久阴,星失度,宜罢免王安石”[4]1926,并试图联系太皇太后和司马光等反对变法者,以逼迫王安石引咎辞职。熙宁三年(1070)正月,翰林学士范镇上书把天变归咎于变法。范镇认为“乃者天雨土,地生毛,天鸣地震,皆民劳之象也。伏惟陛下观天地之变,罢青苗之举,归农田水利于州县,追还使者,以安民心,而解中外之疑”[3]1207,以此迫使宋神宗罢“青苗法”。同年十月,文彦博为攻击“市易法”,把华山崩裂归咎于市易司卖果实,“市易与下争利,致华岳山崩”[1]10547。反对变法者不断把灾异归咎于王安石和由其实施的新法,王安石不得不就此进行反击。王安石告诉宋神宗天灾非人力所能知悉,“臣谓天意不可知”[5]5810,否定天命与人事的关联,“天文之变无穷,人事之变无已,上下傅会,或远或近,岂无偶合?此其所以不足信也”[5]6597。王安石以此说明天变与人事有关的附会之言不足信。
熙宁七年(1074)大旱,宋神宗忧形于色,王安石劝诫宋神宗,“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陛下即位以来,累年丰稔,今旱暵虽远,但当益修人事,以应天灾,不足贻圣虑耳”[4]1959。然而,天变与政治之间的紧密关系,尤其是与皇权的联结由来已久,早已糅合于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中,无法轻易解除。一则,否定天变与人事的联系即否定天人感应,那么人君的天命合法性就难以立足;二则,自宋真宗神道设教之后,北宋士大夫尤其重视天变等灾异对君王的警戒。熙宁元年(1068)有人向宋神宗进言“灾异皆天数,非人事所致”[6]151。富弼说“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去乱亡无几矣,此必奸臣欲进邪说”[6]151。在这种政治环境中,王安石固然可以说天变为常数,然而,宋神宗却难以认同此理,也难以顶住天变论的压力。
(二)祖宗不足法
王安石既然以“变法度”作为目标,那么就要对北宋“祖宗之法”进行更张。因此,变法从根本上便与法祖宗对立。然而,“祖宗之法”在北宋政治思想中的崇高地位难以撼动。形成于宋太祖、宋太宗时期的祖宗家法,它的提出、核心精神的具体化以及涵盖内容的不断丰富都是在宋代历史中长期汇聚而成,并经由士大夫群体相继阐发而被认定的,它是一组动态累计汇聚而成的综合体[7]。“祖宗之法”作为当时社会文化传统与政治、制度交互作用的结晶,是国法与家法的混容[8]21,也是宋代皇帝和士大夫共同遵循的治国理念。“祖宗之法”作为国法与家法的混容,对它的触动,不但涉及政治问题,还涉及天子的孝道。王安石触动的不仅是治国原则,也是当时社会最高道德准则,必将引起士大夫群体的强烈反对。反对变法者以“祖宗之法”为武器对变法展开攻击,他们提出“祖宗之法不可变也”[6]260和“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5]5370的观点在朝野有很强的号召力。
对此,王安石一方面将新法附会为宋神宗在继承二帝、三王之法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政治变革,以师法尧、舜、禹、汤、文、武等先代圣王作为变法借口,抬高新法的地位。自宋仁宗朝起,恢复二帝、三代之政的政治理想在士大夫群体中兴起,王安石正是承借这一政治理想,以二帝、三王为师法对象进行变法。王安石认为“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余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矣。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设之方亦皆殊”“当法其意而已”[9]2。熙宁元年,王安石初次入对宋神宗时即旗帜鲜明地提出“陛下当法尧、舜”[1]10543。在变法实践中,王安石把宋神宗推到变法领导核心的位置上,称新法是“陛下作法”[6]340,是宋神宗通过“取法于先王”[5]5286变革朝廷法度。王安石附会先王之法推行新法,使其能够根据形势需要借先王之法为新法辩护。王安石提出的免役法、保甲法和市易法均由先王之政演变而来。免役法“出于《周官》所谓府、史、胥、徒,《王制》所谓‘庶人在官’者也”[9]19;保甲法则“起于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齐,子产用之郑,商君用之秦,仲长统言之汉”[9]19;市易法“起于周之司市、汉之平准”[9]19。
另一方面,王安石主张执政方式应因时而变,宋神宗不应完全以祖宗成宪作为执政准绳。在与宋神宗讨论政事时,王安石提出:“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4]1920王安石认为宋神宗在处理朝政时应乾纲独断,而不是被祖宗故事所束缚,“事果可,不须问故事。为物所制者,臣道也;制物者,君道也。陛下若问故事有无,是为物所制”[5]5218。熙宁三年七月,宋神宗想要采纳经略使蔡挺的建议,募西北民兵以固边防,却担心枢密院阻挠。王安石上言宋神宗:“陛下诚欲行,则孰能御?此在陛下也。”[5]5172对于祖宗法度的不合时宜之处,王安石坚持对其进行更张,认为“今日事诚与祖宗时异”[5]5981。熙宁五年,王安石劝谏宋神宗不应优容宦官,宋神宗以祖宗旧例为借口搪塞,王安石劝导宋神宗:“祖宗以来虽若此,陛下欲跻圣德及尧、舜之道,即不知此事在所消在所长?祖宗时崇长此辈,已是不当,然只令提点宫观,陛下更改令提举,增与添支,臣恐不须如此。”[5]5812对于朝臣因政见不合相互攻讦,王安石也认为不尽合理。熙宁三年,借司马光之事,王安石反对皇帝在执政时实行“异论相搅”,“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即治道何由成?愚以为朝廷任事之臣,非同心同德、协于克一,即天下事无可为者”[5]5169,并借此把反对变法的中坚力量司马光等人排出了权力核心。
王安石推宋神宗为变法的领导者,把新法归为宋神宗师法二帝、三王之法,为其变更祖宗法度取得道德上的依据,以减少天下人对新法的抵触。宋神宗虽未全然接受“祖宗不足法”的观点,但在不根本动摇祖宗法度的前提下,对“祖宗之法”和“先王之法”两用之,而“先王之法”无疑为变法提供了正当性,促进了新法的顺利推行。
(三)人言不足恤
北宋逐渐形成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提高了士大夫的参政积极性。宋仁宗以后,台谏势力增强,“人言”对政治的干预程度加大。“人言”即士大夫对朝政的议论,特别是对变法的非议会阻碍变法的实施,庆历新政即前车之鉴。因此,在变法之初,王安石即上言“人才难得亦难知。今使十人理财,其中容有一二败事,则异论乘之而起”,“要当计厉害多少而不为异论所惑”[6]156。王安石明白唯有宋神宗对推行新法意志坚定,不为浮言所动,变法才能成功。出于对“人言”的忌惮,王安石一方面向宋神宗灌输“人言不足恤”的观念,鼓励宋神宗打压反对新法的士大夫,以坚定宋神宗的变法信念;另一方面调整北宋的言事制度,以皇权压制“人言”,改变北宋皇权和政治为“人言”所制的状况。
为坚定宋神宗的变法信念,削弱“人言”对宋神宗的影响,王安石把反对变法者所持的言论斥为不合“道”和“义理”的异论和流俗之言,并向宋神宗提出为君之道在于明道,如能以道揆事,以义理断事即可不怕“人言”,“苟当于理义,则人言何足恤?故《传》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4]1919。熙宁四年(1071),面对宋神宗因“人言”对推行免役法的怀疑,王安石即上言:“陛下以道揆事,则不窥牗见天道,不出户知天下;若不能以道揆事,但问人言,浅近之人,何足以知天下大计,其言适足沮乱人意而已。”[5]5427为阻止士大夫利用民意动摇宋神宗的变法信念,王安石把从民间传来的反对变法的言论都归咎为士大夫的不实之言。熙宁三年二月,宋神宗担心常平取息(百姓向政府借贷青苗钱时需缴纳一定利息)会引起百姓不满,王安石劝解宋神宗,常平新法(即青苗法)是惠民之举,朝廷上流传的关于民间百姓反对新法的言论应是士大夫所散布的流言,其言论不足以代表民意。“常平新法乃振贫乏、抑兼并、广储蓄,以备百姓凶荒,不知于民有何所苦!民别而言之则愚,合而言之则圣,不至为此动摇。大抵民害加其身自当知。且又无情,其言必应事实;惟士大夫或有情,则其言必不应事实也”[6]305。王安石把推行新法成效不佳也归因于士大夫借民意进行阻挠,“自与闻政事以来、遂及期年、未能有所施为。而内外交构、合为沮议、专欲诬民、以惑圣听。流俗波荡、一至如此”[10]465。
为疏远宋神宗与反对变法者的关系,王安石向宋神宗反复进言:反对变法者是宋神宗变法事业的巨大阻碍。熙宁三年,宋神宗疑惑朝廷上下为何因变法争论不休,王安石即把此归结于朝廷内外反对新法之人想通过“人言”动摇宋神宗的变法事业,“陛下作法,宰相摇之于上,御史中丞摇之于下,方镇摇之于外。而初无人与陛下为先后奔走御侮之臣,则人情何为而不至此耶!”[6]340王安石建议宋神宗贬抑反对变法者,以打压反对变法的言论。熙宁三年,宋神宗想把司马光调入两府(政事堂、枢密院),王安石虽赞赏司马光的才学,但并不赞同将司马光调入两府,认为此举会为反对派树立旗帜。王安石对宋神宗说:“光虽好为异论,然其才岂能害政!但如光者,异论之人倚以为重;今擢在高位,则是为异论之人立赤帜也。”[6]317在王安石的阻挠和司马光的推拒下,司马光长期远离中央权利核心。
为更彻底消除来自朝野的异论,王安石支持宋神宗对北宋的言事制度进行调整。台谏机构最先受到冲击。台谏作为监察言事机构,对皇权和相权有很大的制衡作用。自王安石变法以来,反对变法者以台谏为依托不断对新法及王安石个人进行攻讦,因此,王安石主张宋神宗通过皇权对台谏机构进行调整。熙宁三年,王安石借右正言李常攻讦青苗法,向宋神宗提出“可令(李常)分析,是何州县如此”[6]315。而北宋为保证台谏官员敢于劝谏皇帝、辅翼朝政,允许台谏官员风闻言事,不论言事是否属实均不问罪。王安石用皇权命令李常分析其所言之事,破坏了台谏的风闻言事制度,台谏的言事权受到约束。
王安石还鼓励宋神宗调整台谏的用人制度。熙宁二年,王安石上言:“旧法,凡执政所荐,即不得为御史。执政取其平日所畏者荐之,则其人不复得言事矣,盖法之弊如此。”[1]3748在王安石的建议下,宋神宗当即废除了宰相不得干预台谏人选的制度。熙宁三年五月,宋神宗又下诏超格拔擢时任州郡幕府的李定为权监御史里行,打破了“三院御史须中丞、学士荐举朝臣”[5]5125的旧规,按资序选拔台谏官员的传统也被宋神宗去除,皇权与相权对台谏的干涉力度大幅上升。由此,宋神宗与王安石得以随意进退台谏官员。自熙宁二年六月至熙宁三年五月,反对新法的御史台官员吕诲、冯京、韩维等遭到罢黜。谏院官员赵抃、孙觉、范纯仁、吕公著、程颢、张戬等也因批评新法接连被罢免。在王安石的推荐下,宋神宗在台谏中安插支持新法的官员,陈襄、谢景温、杨绘、邓绾、蔡确、唐垌等相继被任用。
对于臣僚所上有关新法的奏章,王安石也要求进行核实。熙宁五年,王安石借文彦博批评市易法,进言宋神宗:“凡有奏中书者,乞一一宣谕考较,若架造事端,动摇人情使怨怒,即臣所无奈何。”[5]5811王安石还建议宋神宗严格限制民间言论,提出“治百姓,当知其情伪利害,不可示以姑息。若骄之使纷纷妄经中书、御史台,或打鼓截驾,恃众为侥幸,则亦非所以为政”[5]5427。宋神宗听取了王安石的建议,对民意进行镇压,并于熙宁五年“置京城逻卒,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1]281。
王安石对“人言”的压制和对言事制度的调整虽有利于新法推行,但也带来不少弊端。以宋神宗和王安石施政倾向作为台谏官员进退的标准,削弱了台谏对时政的监督权和对皇权、相权的制约。而王安石对台谏官等士大夫的贬低和打压也使宋神宗对台谏官等“只言道义而无实绩”的官员产生轻视,宋神宗曾明确提出“人臣但能言道义,而亡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5]7876。
二、王安石皇权思想的转变
宋神宗积极采纳王安石关于集权的举措,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被束缚的皇权,扩张了皇权,这在推进变法、革除北宋政治时弊等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面对长期积淀形成的政治文化,宋神宗不可能全盘接受王安石的“三不足”思想。起初对于理想皇权的构建,王安石认为:“庄周曰:‘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是说虽微庄周,古之人孰不然?”[9]325王安石认为皇帝执政时应注重修身省己,以道德、仁义、分守、形名、因任、原省、是非、赏罚等为序,内修己而外行王道。同时,王安石认为对于宰辅的权力也应给予制约。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朝廷下诏“今后舍人院不得申请除改文字”[9]365,王安石即奏陈《论舍人院条制》言:“大臣之强者,则挟圣旨造法令,恣改所欲,不择义之是非,而谏官御史亦无敢忤其意者”,“宜以至诚恻怛、欲治念乱之心考核大臣,改修 政事。”[9]365王安石提出君主应加强对宰辅的监察,防止宰辅弄权。在皇权与士大夫的关系上,王安石认同皇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在行政上,王安石认为君臣应各尽其道,皇帝固然有进退人才的权力,然而在任用人才时应给予他们一定的自主性和发展空间。王安石曾在《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中提出对于人才“取之既已详,使之既已当,处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专焉,而不一二以法束缚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尧、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众工者,以此而已”[9]5。
然而,王安石的皇权思想,在其作为宰相主持变法后被迫发生改变。进入中央主持变法后,王安石的立场发生了改变。王安石以前多以地方官员的身份参政,彼时,他认为只有减少皇权对地方事务的干涉,增加地方官员的自主性,地方官员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治理地方。那时,王安石需要构建一个受制约的皇权,以扩张地方官员管理事务的权力。进入中央后,王安石作为宰相辅佐皇帝变法,面临的是庞大的反对变法的士大夫集团,身为百官之长却要与朝野上下众多的新法反对者进行斗争。面对朝廷大多数官员对新法的攻讦,王安石必须依靠宋神宗的支持来推行变法。在此形势下,王安石提出“三不足”来伸张皇权,消除皇帝对于天命、“祖宗之法”和“人言”的顾虑,最大限度地扩展皇权,借助皇权增强相权,对抗反对者。在《周官新义》中,王安石充分展现了其所设想的以加强皇权为核心的国家权力分配格局,既强化了皇权,也强化了相权。王安石把宰相之外的官员的事权收到以皇权为主、相权为辅的权力结构中。皇帝发号施令,宰相辅佐皇帝,“大治,王与大宰共之也”,“小治,大宰得专之也”[11]27。在皇权之外,宰相可以参与国家大政,而其他大臣则负责执行,“只治朝言王,而作大事不言王,则作大事者大宰故也。盖命者君所出,而事之者臣所作,故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余官言大事未有言作者,则大事独大宰作之而已”[11]47,“若其小治,则大宰专之”[11]48。这样宰相以下的官员只需依照朝廷法度,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处理事务,不得超越法度而自行其是,“小宰掌戒而不掌誓,掌具而不掌修。盖誓听于一,而修则有所加损;戒与众共,而具则具之而已”[11]63。为推行变法措施,王安石设计了一套以皇权意志为中心的官僚机构,皇帝的权力和意志被无限扩张。
三、“三不足”理念下皇权与相权的矛盾
王安石的“三不足”理念目的是解放皇权,然而在变法过程中,王安石屡屡侵犯皇权威严,相权对皇权的挤压和侵夺使宋神宗对王安石充满警惕。王安石在执政期间,因相权对皇权的侵犯导致其两度罢相,最后黯然离开朝堂,退处金陵而终。
在变法伊始,王安石虽宣称新法为“陛下作法”,但王安石变法的施政纲领及具体措施都是其假借皇权强力推行。王安石高估了自己在变法中的地位,实际上变法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宋神宗手中。王安石认为是其以“大有为”之言说动宋神宗进行变法,但事实上,是宋神宗以“致君行道”的政治理想吸引王安石入朝辅政,为实现二人共同的目标——变法,宋神宗用皇权全力支持相权,并和善处理皇权和相权之间的矛盾。变法前期,宋神宗多依王安石意见裁定朝廷政事,所以曾公亮说“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6]320。在皇权与相权发生冲突时,宋神宗屈己听之,使王安石得以致君行道。在王安石因宋神宗变法意志动摇而托病甚至辞官时,宋神宗以理想和道义安抚挽留王安石,“卿所以为朕用者,非为爵禄,但以怀道术可以泽民”,“朕所以用卿,亦岂有他?天生聪明,所以乂民,相与尽其道以乂民而已”,“卿,朕师臣也”[5]5661,又说“君臣之义,固重于朋友”[5]5685。宋神宗的安抚使王安石心甘情愿继续辅佐宋神宗进行变法。正是宋神宗用皇权对王安石相权的支持、配合,变法才得以顺利实施。
随着变法深入和宋神宗帝德渐成,宋神宗与王安石之间即皇权与相权的分歧不断加深。宋神宗与王安石都想扩张皇权,但二者目的不同:前者是为集中皇权以实现自己的“大有为”为目标;后者则是借皇权的伸张,扩充相权,推行新法。王安石试图凭借自己与宋神宗的君臣情谊,把皇权纳入相权的运行轨道之中,这恰恰阻碍了宋神宗进行集权。熙宁六年(1073),宋神宗说:“太宰以八柄御群臣,谓宜如此,正宰相之任也。”[5]6002然而,这不过是因为宋神宗尚需要王安石在朝廷为其对抗反对派,推行富国强兵之法,不得不对王安石进行安抚。王安石虽然说“驭群臣曰柄,驭万民曰统”,“于八柄八统曰‘诏王驭群臣万民’则是独王之事也,大宰以其义诏之而已”[11]27,但王安石并未察觉潜藏在宋神宗言语中皇权与相权的矛盾。随着宋神宗在政治上的成熟,新法的雏形已成,支持变法的新锐官员成为朝廷骨干,此时王安石对宋神宗而言已经没那么重要,宋神宗自然想把王安石排出权力中心。在王安石二度罢相离开中央核心权力后,宋神宗开始独掌政权。元丰元年(1078),迩英阁讲官黄履进讲《周礼》时,宋神宗与黄履的对话颇能说明问题:“上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而八柄非太宰所得与,何也?’履曰:‘八柄以驭群臣。驭者,主道也,故非太宰所与。’上曰:‘善’。”[5]7052宋神宗的言论,表露出其作为皇帝的强大权力欲与控制欲。宋神宗极度排斥相权干涉皇权,而王安石借助皇权扩张相权,甚至试图掌握天子八柄之权的行为自然受到猜忌。王安石离开朝廷后,宋神宗摆脱了相权对皇权的束缚,转而放弃了王安石为相时所坚持的“异论相搅”政策,朝廷政事皆出于宸断。元丰四年(1081)宋神宗对辅政大臣说:“夫家自为政,人自为俗,先王之所必诛;变《风》、变《雅》,诗人所刺。朝廷惟一好恶,定国是,守令虽众,沙汰数年,自当得人也。”[5]7586
四、结 语
在变法中,王安石通过“三不足”理念不断对皇权进行塑造为其推行新法服务。宋神宗虽部分吸收了王安石所提出的“三不足”之说,但只是在不触动统治秩序的前提下进行的。然而,王安石在进行变法时,为获得皇权支持,不断向宋神宗灌输“三不足”理念,借皇帝之手清除反对新法者,破坏了北宋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制度,背离了宰相职责。而作为王安石变法的合作者,宋神宗始终不曾全然倚靠王安石。宋神宗作为皇帝,首先考虑的是皇权的稳固与加强。变法作为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共同目标,虽为皇权和相权之间的短暂合作提供了契机与保证,但从长远来看,王安石作为宰相,其权力增长必然与皇权产生冲突。因此,当皇权得到加强和面临新的威胁时,这种本身就不坚固的联盟就会破散。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分歧早有端倪,宋神宗对包括“异论相搅”在内的有利于集权的祖宗法度的保留,对以司马光等反对派的优容,和在天灾发生时下诏求言的举动都说明宋神宗对于王安石的不信任。因此,熙宁后期,王安石对宋神宗已失去大部分影响力。王安石二次复相后,宋神宗对于王安石的主张已多不听从,而以皇权为变法依仗的王安石一旦失去宋神宗的支持,便在朝中难以立足。此后,随着“上意颇厌之,事多不从”[5]6803,王安石在朝中肘腋尽去。面对如此形势,王安石被迫再度罢相,彻底离开朝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