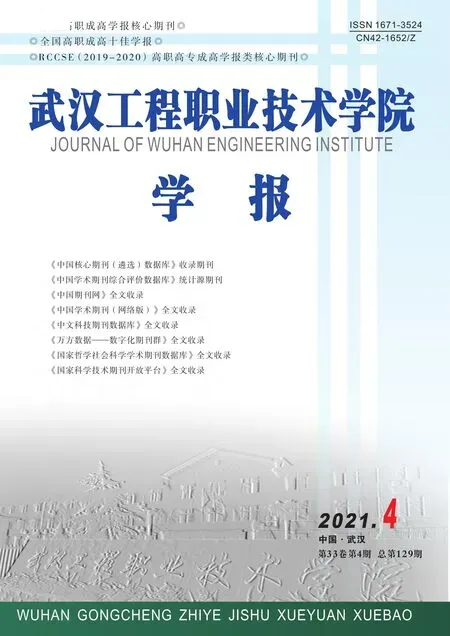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
——基于公共服务满意度的中介效应研究
李奕泠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430072)
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保持高速增长。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元大关,取得瞩目成就。与此同时,中国基尼系数整体呈现出下降趋势,但数值长期维持在0.46以上,按照联合国的评价标准,属于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古人云“不患寡而患不均”,在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一定成就的新时代,民众不仅仅关注社会的经济效率,也更加重视社会公平问题[1]。促进社会公平,提升民众的社会公平感,对于实现社会的长期协调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关于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因素,学术界提供了两种微观解释框架,即社会结构决定论和局部比较论。
社会结构决定论[2]认为,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会影响他们对社会不平等体系的认同,在社会分配中获得越多利益,社会公平感则会越强。国内学者也基于实证研究提出[3],客观社会地位会影响公平感,社会经济地位可以通过对社会不平等的归因影响民众的分配公平感[4],社会结构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结果公平感和机会公平感,其中收入能够极为显著地促进结果公平感,而机会公平感更多地由受教育水平所决定[5]。
而基于相对剥夺理论[6]和社会比较理论[7]的局部比较论则认为,社会公平感不仅仅与自身享有的绝对资源和社会地位有关,也受到参照群体的影响,社会公平感是人类个体以过去的“自己”和当下的“他人”为参照,与自身处境比较后产生的结果。基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比较产生的相对剥夺感越强,个体的社会公平感则会越弱。根据对中国城市居民的调查,无论是基于和周围人群还是自身过往经历的比较,居民对自身目前的社会经济状况给予越高评价,则分配公平感越强[8]。基于对青年人群的调查,发现局部比较影响分配公平感,其中与同龄人进行横向比较产生的相对剥夺感是最重要的因素[9]。有学者研究教育程度与分配公平感发现,伴随教育投入所产生的期待收入与实际收入差距越大,越容易感到分配不公,即心理失范[10]。这两种微观解释框架解释了社会公平感的形成机制,但是对于宏观的制度因素存在一定的忽视。
有学者提出社会救助假说,从制度主义视角出发,认为社会救助制度的完善,能够促进弱势群体社会公平感[11]。通过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社会保障,可以维系社会平衡,为弱势群体提供必要保障,促进社会公平[12]。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基于自身的公平性能够为社会创造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另一方面,也能通过多种途径如关注弱势群体、普及教育等方式为社会成员提供参与竞争的基本条件,提高起点公平[13]。 从实证研究角度出发,基于武汉市的研究表明,在中国低保群体当前生活水平仍旧艰苦的条件下,低保政策较好地提高了相关家庭的社会满意度[14],社会保障支出的提高也能够降低基尼系数,减少客观的社会不平等[15,16]。相比于社会经济地位和相对剥夺因素,社会救助对于社会公平有着更加稳健的促进作用[11]。
实际上,政府救助制度属于公共服务的一环,制度建设和政府管理水平影响社会公平,政府公共服务质量与人民期望的差距会降低公民的公平感,要实现善治、维护社会公平,不仅需要扩大政府公共服务的范围,还需要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17]。学者通过调查发现,贫富差距、医疗问题和住房问题能否得到解决会显著影响公民的公平感[18];而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实证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越高,民众的社会公平感越强[19,20],但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对于不同群体的影响存在差异,对中等以上收入群体表现出显著正向作用,而对于低收入群体则不存在明显影响[20]。通过政府支出测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无法衡量居民对于公共服务的微观感受,通过对居民对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主观评价进行测量,发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提升居民社会公平感,这种影响机制根据公共服务的类型不同有所差异,且对于中低收入人群的影响更加显著[21]。
整体而言,已有研究采用了微观和宏观两种视角对社会公平感进行解释,其中,两种微观解释框架在多位学者的研究中被采用,且学术界已有了大量的交叉分析;宏观视角下,学者往往从客观的公共服务供给和政府社会救济制度出发,测量公共服务和社会救济与社会公平的关系,也有一部分研究涉及到了这些宏观因素对居民公平感的影响,但更多集中于客观制度、政策水平,对于民众的主观感受测量较少,实际上客观制度与主观体验密不可分,宏观的制度政策将会影响微观的个体体验,本文试图探究客观的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是否会通过影响主观的民众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方式对社会公平感产生影响。
2 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2.1 中介效应
以往对于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民众社会公平感的研究,往往只限于对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社会公平感的相关性进行探讨,对于其中的影响机制和影响路径探讨不足,为了探索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社会公平感之间的影响机制,本文引入了中介变量。
作为一个统计学概念,中介变量是解释变量X对被解释变量Y产生影响的中介,是X对Y产生影响的内在性和实质性原因。考虑解释变量X对被解释变量Y存在影响,如果解释变量X通过影响变量M而对被解释变量Y产生影响,M则被称为中介变量,M在解释变量X对被解释变量Y的影响路径中发挥了中介效应。[22]例如,“长辈的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影响“子女的教育程度”对“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产生影响,其中“子女的教育程度”就是中介变量,“子女的教育程度”在“长辈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路径中发挥了中介效应。
中介变量的作用原理如图1所示,c是解释变量X对被解释变量Y的总效应,ab是由中介变量M导致的中介效应,c'是解释变量X对被解释变量Y直接效应。如果只存在一个中介变量,中介效应、直接效应和总效应之间的关系即:c=c′+ab。

图1 中介变量示意图
2.2 研究假设
当前民众的公平感已经从早期的“不患寡,而患不均”逐渐发展为“患不均,更患不公”,对社会的分配公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3]。政府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依赖于政策手段,作为重要政策手段的公共支出,能够调控社会公平的结果,促进社会公平[24]。公共服务供给是公共支出的重要环节,也是近年来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扩大公共服务供给能够切实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25]。公共服务的正义体现于政府能够通过公共服务回应公众诉求和追求社会公平,优质的公共服务供给,不仅能够促进程序正义,也能够实现实体层面的结果正义[26]。在中国公共服务供给存在区域差异的情况下[27-29],研究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社会公平感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公共服务供给对客观社会公平的影响已有许多学者做过实证研究,而公共服务供给和主观社会公平感的关系,有学者发现公共服务供给可以通过积累人力资本和增强风险承担能力的方式提高民众社会公平感[30],也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越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提升越能够促进居民社会公平感[20,21]。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越高,居民社会公平感越高。
公共服务满意度受到城市层面的公共财政支出影响[31],有实证研究发现,公共服务资源的增加能够影响公民的主观评价,提升公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公共服务满意程度[32]。
个体的社会公平感,不仅与客观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有关,也与主观的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有关[33],政府不仅需要增加公共服务的投入成本,也需要提升公共服务的投入效率,才能提升公共服务满意度[34],进而提高社会公平感。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提升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且公共服务满意度提升居民社会公平感,即公共服务满意度在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居民社会公平感的效应中起到中介作用。
3 分析框架和变量操作
3.1 数据来源
本文的微观数据来源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CGSS)。该项目始于2003年,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联合全国各省市区学术机构共同执行,是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2015年CGSS项目采用多阶分层抽样方法,对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478村居进行调查,共收集10968个样本数据。本文在剔除了数据缺失的无效样本后,一共收集到9593个有效样本。
本文的宏观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参照李秀玫等学者的研究,由于人们的主观认知往往基于过往的获得感,地区层面宏观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性[20], 因此采取《中国统计年鉴2015》,即2014年度的客观数据来衡量公民2015年度的主观感受。
3.2 变量设置
3.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解释变量为居民社会公平感(Perception of Social Justice),采用CGSS2015微观调查数据中“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今的社会公不公平?”进行衡量。问卷对被测量者回答的“完全不公平”、“比较不公平”、“说不上公平但也不能说不公平”、“比较公平”“完全公平”五个选项,分别赋予1、2、3、4、5的值。
3.2.2 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Public Service Supply),通过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进行衡量。本文的公共服务支出包括教育、 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社会保障和就业等四方面的支出,其中,分项公共服务供给水平通过分项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进行衡量。
3.2.3 中介变量
本文的中介变量为公共服务满意度(Public Service Satisfaction),采用CGSS2015微观调查数据中“我们想了解一下您对政府所提供的下面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如何?”进行衡量。公共服务满意度包含公共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社会保障和就业四方面的满意度,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满意度通过对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取平均数进行衡量。
3.2.4 控制变量
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引入了6个相关的社会人口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包括性别(Gender)、年龄(Age)、户籍(Hukou)、受教育水平(Education)、自我社会地位认知(Status)和个人年度收入(Income),并对个人年度收入取对数处理。
3.3 样本描述性统计
如表1所示,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均值为3.202,社会公平感更接近于样本最大值,说明整体而言居民公平感较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公共教育供给水平、医疗卫生供给水平、社会保障和就业供给水平的均值分别为0.404、0.168、0.079、0.122,均接近于样本最大值,仅住房保障供给水平为0.035,更接近于样本最小值,整体而言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处于较高水平。公共服务满意度、公共教育满意度、医疗卫生满意度、住房保障满意度、社会保障和就业满意度的均值分别为69.536、73.214、69.954、66.879、68.096,同样更接近样本最大值,说明公共服务满意度处于较高水平。

表1 变量说明及样本描述性统计
3.4 统计模型设定
利用温忠麟等学者提出的依次回归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35],并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Justice=α1+β1Supply+β2Controls+ε1
(1)
Satisfaction=α2+γ1Supply+γ2Controls+ε2
(2)
Justice=α3+δ1Supply+δ2Satisfaction+
δ3Controls+ε3
(3)
其中,Justice代表居民社会公平感,Supply代表公共服务供给水平,Satisfaction代表公共服务满意度,Controls代表所有控制变量。β、γ、δ为变量系数,α为常数项,ε为误差项。
公式(1)放入了被解释变量Justice、解释变量Supply和控制变量,用于检验假设1中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公式(2)中放入了中介变量Satisfaction、解释变量Supply和控制变量,用于检验假设2中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公式(3)放入了被解释变量Justice、中介变量Satisfaction、解释变量Supply和控制变量,公式(2)(3)的结果共同用于检验假设2中公共服务满意度是否在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居民社会公平感的效应中起到中介作用。
4 实证分析
4.1 回归分析结果
由于被解释变量居民社会公平感属于有序离散型变量,因此表2采用 Ordered Probit模型进行检验。其中,模型1仅放入解释变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模型2放入解释变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控制变量,模型3放入解释变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中介变量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和控制变量。根据表2结果可知,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回归系数均为正数,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对居民社会公平感的提高有着促进作用,因此,假设1得到证明。

表2 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
同时,根据表2结果可知,性别、年龄、户籍、教育水平、自我社会地位认知等控制变量都会影响居民社会公平感。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越高、自我社会地位认知越高,社会公平感越强;男性相比女性有更强的社会公平感,农村户籍的居民比城市户籍的居民有更强的社会公平感,而个人年收入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并不显著。
为了进一步研究不同类型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本文分别对教育、 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社会保障和就业进行Ordered Probit回归,分析各类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机制。由表3回归结果可知,住房保障供给水平、社会保障和就业供给水平正向显著影响居民社会公平感,而公共教育和医疗卫生供给水平对居民社会公平感无显著作用。

表3 不同类别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
4.2 中介效应检验
表4是公共服务满意度在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居民社会公平感影响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由模型2可知,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显著正向影响了居民的公共服务满意度。根据中介效应的逐步检验步骤,可以得知,模型1中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系数为1.2659,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模型2中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系数为26.5406,模型3中公共服务满意度的系数为0.0170,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且模型3中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系数0.8313小于模型1中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系数1.2659,根据逐步回归法可以证明,在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中,公共服务满意度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表4 公共服务满意度的中介效应检验
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居民社会公平感的总效用为0.8313,公共服务满意度的中介效应为0.4512(26.5406*0.0170),由此得出公共服务满意度占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提升居民社会公平感的中介效应比重为54.28%,因此假设2成立。
4.3 异质性检验
表5是根据户籍类型分组研究后的分组回归结果。由表5可知,城镇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居民社会公平感呈现出正向显著关系,而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居民社会公平感不存在明显相关性。无论在城镇或者农村地区,公共服务满意度与居民社会公平感呈现出正向显著关系,且农村地区大于城镇。

表5 分组回归结果
由于城镇和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存在一定差异,存在不均等化分布的情况,城镇公共服务供给能够切实改善居民的生活空间,对居民社会公平感起到促进作用,而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不一定能够很好地作用于居民,因此与社会公平感的关联不够显著。但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提升,可以提高居民的社会公平感,说明公共服务供给量的变化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公共服务供给是否能够让居民满意,才是提升居民公平感的关键。
5 结论和建议
5.1 结论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公平越来越被提到一个重要的位置,民众的主观社会公平感则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环节。公共服务供给作为政府宏观政策的重要环节,可以通过提升公共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就业等方面的供给质量来提升民众的社会公平感,而民众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又在其中扮演着中介影响的角色。本研究将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和CGSS2015数据相匹配,在控制了基本的个体特征变量后,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和作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并从城乡户籍角度进行了异质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
(1)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对居民社会公平感的提高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假设1得到证明。
(2)公共服务供给水平通过提高公共服务满意度提高了居民社会公平感,假设2得到证明。
(3)根据进一步分析,在公共服务供给当中,住房保障供给水平、社会保障和就业供给水平会正向显著影响居民社会公平感。
(4)根据分组回归分析显示,城镇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居民社会公平感呈现出正向显著关系,无论在城镇或者农村地区,公共服务满意度与居民社会公平感呈现出正向显著关系。
5.2 建议
近年来,我国正在建设服务型政府,要做好服务型政府,就需要保证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一方面,需要继续加大公共服务供给的投入,在住房保障和就业等民生服务方面提高供给量,针对不同地区需要对症下药,判断民众的真实诉求,并针对性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调整公共支出比例。
另一方面,公共服务不仅需要关注“量”,更需要关注“质”,公共服务要达到使民众满意的水准,就需要优化供给结构,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倾听民众意见、畅通沟通渠道,从而提升民众的社会公平感。